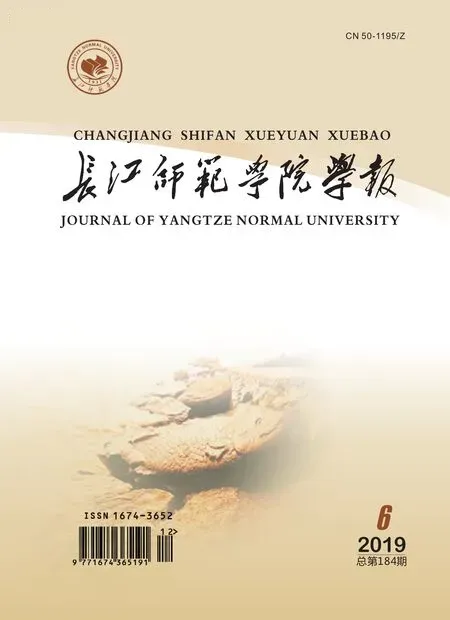春秋嘉言“敬”义发微
胡晓红
(太原师范学院,山西晋中 030619)
“敬业”是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范畴之一,溯其渊源,当与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的“敬”观念有关。从现有文献来看,“敬”已是西周青铜器铭文、《诗》《书》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语与概念。春秋时期,贵族文化人的言论为当时史官记录,并作为“嘉言善语”载录于《国语》《左传》中而流传至今,即本文所谓“春秋嘉言”,其中不乏对“敬”观念之论说。考以春秋时人的思想世界,则神祇、天命、人本等观念侧重于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而统归于“德”行范畴的敬、忠、信、勇、仁等则更指向人的内在品性的修养;综观春秋时代思想研究,认识论范畴多为学者所论,对具体而微的德行范畴的纵深研究则有所不足。因此,本文拟以“敬”观念为例,立足文本解读,试探其丰富内涵与微义。
一、春秋嘉言“敬”义溯源
“敬”观念不是春秋嘉言的发明,至少在西周初年,已经产生了这一观念。西周青铜器铭文、《诗》《书》等西周文献中,有大量“敬”字的使用。许慎《说文》解“敬”为转注字,“敬,肃也。”段玉裁注:“肃者,持事振敬也,与此为转注。”又进一步举近义字以释其意:“忠,敬也;戁,敬也;憼,敬也,恭肃也;惰,不敬也。义皆相足。”[1]434“敬,肃也。谦与敬义相成。”[1]94此释作为字义之“敬”。若从两周文献语料来看,作为一种价值观念的“敬”,其内涵已包含了敬畏、恭敬、严肃、认真、警戒等多层意义,那么,除了直接使用“敬”字,文献中凡表达此一意义的其他语词如“肃”“恭”“祗”“慎”“儆”等,皆属于周人“敬”观念的范畴。
青铜器铭文是目前所见的最为确定的西周原始文献,内容多叙赏赐事,部分金文在叙事之外加告诫教导语,“敬”多出现于此类金文中。“敬”为动词,按照动作指向区别,可以分为敬天、敬王、敬德、敬事等,对象不同,“敬”义所指侧重亦有不同,对上天、周王之“敬”多敬畏、恭敬义,对德性、事务之“敬”则多敬重认真义。以西周成王时期的何尊为例,其中所载的成王诰辞中,既有敬天的表达,如回首往日云:“隹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眂于公室有爵于天”“廷”,马承源引《广韵》曰:“敬也”,释“爵”为“恪”,“敬也”。亦有对上、对事之敬,如云:“徹令敬享哉”,其义为“通晓命令,敬事奉上”[2]21。总体来看,西周金文以“敬事”居多,如同为成王时的大保簋云:“大保克敬无谴。”[2]24意谓大保能常慎敬其事而无灾谴之咎;康王时期的大盂鼎云“若敬乃正,勿废朕令”[2]38,义为“谨慎地履行你的职责,不能违弃我的诰诫”[2]41;恭王时期的师酉簋、懿王时期师虎簋皆有“敬夙夜勿废朕令”[2]126之句;孝王时期大克鼎“敬夙夜用事,勿废朕令”[2]216;懿王时牧簋、孝王时师克盨皆有“敬夙夕勿废朕令”[2]223等,此类表述多见,其义主要为认真负责地对待职务、履行王令。
《尚书》中的《周书》部分,学者普遍认为是其中最可信的西周史料,自《大诰》至《顾命》产生于武王、成王、康王时期,其时限虽短于金文,而对“敬”这一观念的应用和阐发竟达三十余处,其内涵意义也更为详细丰富。首先是敬畏义,常以“畏”“忌”“惧”等词表达,或与之连言。如《无逸》篇云:“其在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3]1532。传达的都是“敬畏”天命与人事的心态。其次是谨慎认真义,多属于对职事之“敬”。和西周铜器铭文有所不同的是,除了对即将赴任的诸侯进行敬业的劝勉外,更多的是表达对待刑法的谨慎之义,如《康诰》反复言说对法之敬:“呜呼!封,敬明乃罚”[3]1319;“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3]1341。《酒诰》曰:“惟助成王德显,越尹人、祗辟。”[3]1403《立政》篇云:“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3]1657再次是敬重义,侧重于对一己之“敬”,常与“德”相连。“德”是人后天通过修养而拥有的品质,《周书》中多次言“敬德”,实质上是自我看重并不断在行为上修养德性。
《诗经》无论是作者队伍、创作时代还是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都比金文和《尚书》广泛,“雅颂”之诗有别于政令式的《周书》,“敬”观念在《诗》中有独特的阐发。《诗经》对“敬”的心理状态有形象描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4]414“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4]420《诗经》中“敬”的对象同样广泛,有于天、帝、神之“敬”,如:“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驱驰。”[4]636“昊天上帝,则不我虞。敬恭明神,宜无悔怒”[4]662“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4]718有于职事之“敬”,如“嗟嗟臣工,敬尔在公”[4]722;“嗟尔君子,无恒安处。靖恭尔位,正直是与”[4]447。有于人之“敬”,在此意义上,《诗经》更为突出对于一己之“敬”,不泛言“敬德”,多论对自己威仪的敬慎,“敬尔威仪”之类的表述在《小雅·小宛》《大雅·民劳》《大雅·抑》《鲁颂·泮水》等多首诗中频频出现。因为对一己威仪之“敬”,《诗经》作品发展出“敬”的审美意义,“祗祗”“肃肃”“穆穆”“翼翼”等常用来形容一种严肃、整饬、端庄之美。如“有言有翼,共武之服”,毛传“翼,敬也”[4]358;“宾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仪反反”[4]495;“有来雝雝,至止肃肃。相惟辟公,天子穆穆”。郑笺“肃肃,敬也”[4]734。皆是“敬”由心态而表现的外在审美。
从缘起和历史文化演进来说,“敬”的心态最初应当和祭祀有关,主要指对昊天、上帝、神明等恭敬、敬畏意。随着社会人事的发展,面对大邑商为小邦周所灭,周人深深反省历史,“敬”观念在西周得到极大的丰富,不止于神明上帝,更有对于王事、对于一己的言行举止的敬畏、敬重、严肃、认真之义,成为西周上层统治者所普遍认同和倡导的重要价值观念,也是春秋嘉言阐说“敬”观念的基础和源头。
二、自律警戒的春秋嘉言之“敬”
《左传》兼记言记事,刘知几《史通·申左》云:“斯盖当时发言,形于翰墨;立名不朽,播于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语,就加编次。”[5]391韦昭《国语解叙》亦言《国语》之作,乃是采录前世“邦国成败,嘉言善语”而成[6]661,《左传》《国语》所载嘉言善语是了解春秋时期“敬”观念的主要文献。遍检《左传》《国语》所载言论,依照上文对于“敬”观念的内涵界定,《左传》论及此一价值范畴有五十余处,《国语》近三十处。综观春秋嘉言对于“敬”的论说,其内涵首先突出于指向一种普遍的警戒心态。
普遍的警戒心态来自周人敬畏天命的观念,如前所论,这种观念在《诗》《书》中得到反复表达,春秋时人对上天、神祇的敬畏仍然普遍地存在。公元前683年,宋国发生水灾,鲁庄公派使者慰问,宋闵公答曰“孤实不敬,天降之灾”,臧文仲赞曰:“言惧而名礼,其庶乎!”[7]153《国语·楚语下》载观射父论祭祀强调“敬其粢盛”,又曰“其谁敢不齐肃恭敬于神”[6]567,“敬”在这里都是侧重于对上天、神灵的恭敬、敬畏、虔诚之意。之所以敬畏天神,是以为人类的命运为上天神灵所掌控,对天、神的敬畏又常及天命,文公十五年《左传》季文子引《诗》批评齐侯不敬畏天命:“不畏于天,将何能保?”[7]340然而“敬畏天命”的观念本身包含了人的理性的觉醒,敬畏不是一味地畏惧和顺从,而是试图通过人对自身进行约束,从而求得上天神灵的佑护,春秋嘉言正是在这一点上发展了“敬畏天命”的观念,大量地从警戒之心的角度阐说“敬”的内涵,“敬畏”的观念于是逐渐从以神为本转向以人为本。
警戒之心是获得成功时应该保有的,宣公十二年《左传》载晋栾书言楚人取得克庸的辉煌战果以来,“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7]393。警戒之心是面对弱小势力也不应当放松的,僖公二十二年《左传》载邾人出师于鲁,鲁僖公因其为小国而轻视邾,臧文仲引《小雅·小旻》《周颂·敬之》以敬畏之意劝谏僖公要时刻保有儆惧之心:“君其无谓邾小,蜂虿有毒,而况国乎!”[7]247警戒之心在春秋嘉言中无尽蔓延,包括警戒安逸与享受、赏赐与财富、情感与欲望等。
安逸与享受是春秋嘉言所警戒的。公元前585年,晋国欲迁都,韩厥以“国饶,则民骄逸”[7]442反驳诸大夫,力主迁都新田,其主要理由即是警戒人心的骄逸;鲁国臧氏代有良卿,臧僖伯、臧哀伯,皆有对鲁君的谏诤良言,规劝鲁隐公、桓公作为人君应当警戒安逸。楚国在春秋时期,偏居一隅而能够入主中原称霸诸侯,或许和楚人警戒安逸的文化观念有关,如晋卿栾书在邲之战前夕所论楚国国情:“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7]393这种心态在楚人言论中尤其多见,倚相《谏申公子亹老耄自安》举例历史名人自警故事,劝谏申公应当时刻保持对安逸的警戒,其文曰:
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蒙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没也,谓之睿圣武公。子实不睿圣,于倚相何害。《周书》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犹不敢骄。今子老楚国而欲自安也,以御数者,王将何为?若常如此,楚其难哉![6]551
以卫武公之年高,本当安享晚年,而卫武公却要求在朝卿大夫勿忘劝谏自己,自是对安逸的儆惧心态。又蓝尹亹《论修德以待吴》(《国语·楚语下》)云:
夫阖廬口不贪嘉味,耳不乐逸声,目不淫于色,身不怀于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闻一善若惊,得一士若赏,有过必悛,有不善必惧,是故得民以济其志。今吾闻夫差好罢民力以成私好,纵过而翳谏,一夕之宿,台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从。夫差先自败也已,焉能败人。子修德以待吴,吴将毙矣。[6]578-579
这段言辞以前后两代吴王阖闾与夫差为材料进行对比,其主旨则表达对安逸的批评与警惕。阖闾不贪于口、耳、目、身的感官享受,这是对安逸生活的自律和警戒,因而“得民”“济志”;相反地,夫差则唯“私好”是务,放纵安乐,进而推论说,安逸必然导致失败,不足为惧。
赏赐与财富是春秋嘉言所警戒的。赏赐代表了一种“得”,在春秋政治活动中主要包括物质与礼节名誉。面对物质与名誉,春秋嘉言所反映的观念不是汲汲于获取和占有,而是戒惧,即侧重于反问自己:是否有资格拥有这种物质、名誉。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占有和自己的功绩、德性等不相当或不该有的赏赐,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公元前672年,齐陈完因政权之乱而从陈国逃奔齐国,以“不辱高位”拒绝齐侯任其为卿的赏赐;公元前623年,卫国宁武子聘于鲁,文公以大礼晏享,宁武子《论干大礼以自取戾》(《左传》文公四年)解释不敢接受越礼之赏;公元前562年,郑人贿赂给晋侯一批女乐,晋侯分而赏赐魏绛,魏绛以《请以赏乐辞晋侯》(《左传》襄公十一年)予以拒绝,皆属此类。这些赏赐常常关乎富贵,晏子《语子尾论不欲富》(《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表达对财富的警惕;郑国卿大夫公孙黑肱临终之际,亦以此警戒其子曰:“吾闻之:‘生于乱世,贵而能贫,民无求焉,可以后亡。’敬共事君与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7]599富贵可能导致灭亡,因此对富贵保持警戒,可以避免灾难。
情感与欲望也是春秋嘉言力主保持警戒之心的事物。情感与理性相对,《左传》中多有记载缘于人的情感意气而处理事情的案例,具体表现为“逞意”一词的多次出现,“逞意”在这些语境中的基本意义就是情绪的发泄与快意。以晋国为主的战争中,晋齐鞌之战的爆发和晋国卿大夫郤克因为在齐国受辱而求报复不无关系;晋楚邲之战,荀林父和士会看到楚君已还,皆不主战,而先縠则以晋国失霸的耻辱为由坚决主战,最终以晋国失败而告终;鄢陵之战中,郤至同样以逃避楚国为耻辱为由极力主战,虽然晋国取得胜利,但是埋下许多后患,均是意气用事的例子。因此一些贵族文化人看到情绪意气对人事的影响,基于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以言论表达对感性、情绪等保持警戒的思想,范氏家族是典型代表,范武子、范文子均有对后代进行情感警戒教育的言辞,如士会《戒子书》:
燮乎!吾闻之:“喜怒以类者鲜,易者实多。”《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乱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乱于齐乎。不然,余惧其益之也。余将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尔从二三子,唯敬。[7]412
杨伯峻注解曰“喜怒合乎礼法者,曰以类”[8]774;杜预注:“易,迁怒也。”[7]412士会以引证论说情感的强大力量,不容易为礼法与理性控制,进而勉励告诫其子士燮以敬畏和警戒之心面对。
情感和欲望相关,春秋嘉言通过对“度”的警戒表达对欲望的克制。多见于两个方面的论说:其一戒女色不度。晋平公是晋国历史上过度放纵女色的国君,以至生疾,《左传》载诸侯前来慰问,秦国医和以《论六淫致疾》的一篇言辞,从音乐和医学的角度阐说人应当对情欲保持警惕与节制,其文曰:
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德也。物亦如之,至于烦,乃舍也已,无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7]708-709
其二是戒奢华不度。奢华的追逐本质上反映的是人的物欲膨胀,对物欲的警惕在楚人言论中多有体现。楚国创业之初时时对安逸保持戒惧,在国势强大之际又追逐奢华,楚灵王可谓典型代表。如果说虢之会盟上公子围以令尹身份而服饰奢华饱受非议,或者是因为违越礼制,为国君后筑章华之台等举动,则无疑是对奢华的疯狂追逐,因此楚伍举作《谏楚子示诸侯以侈》(《左传》昭公四年)以劝止,又作《登章华台谏楚子》(《国语·楚语上》)详细论说,反对不顾民力的过度物欲享乐。
从敬畏天命到警惕安逸享乐、赏赐财富、情感欲望,春秋嘉言阐发了“敬”包含的普遍警戒心态之义,相对于周人敬畏天命的思想,体现出理性的增长。
三、自重不怠的春秋嘉言之“敬”
如果说以普遍的警戒之心阐说“敬”的观念,侧重于一种自觉的反省与强烈的自律意识,那么春秋嘉言大量批评怠、惰、傲等“不敬”的表现则偏向于从个体自尊自重的角度阐发“敬”观念。
溯其上源,春秋嘉言突出“敬”的自重义当和西周“敬慎威仪”观念相关,“各敬尔身”“各敬尔仪”“敬慎威仪”等说法在《诗经》中多次出现,其义为对自己言行举止的敬重,因为诗的文体所限,没有过多阐发。春秋嘉言继承西周“敬慎威仪”的观念,多次引《诗》并展开更为充分的言说,对这一观念进行详述。《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卫北宫文子答卫侯问威仪,先论在上位者尤其要敬重自己的威仪:“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有其国家,令闻长世。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顺势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再论威仪的内涵:“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7]690春秋人所认为的威仪,表现为外在的容止、言语、行动、声气等方面。北宫文子所论重于理论,既论“敬慎”,又释“威仪”,为正面论说,春秋嘉言大量的言论则是针对人的具体言行容止,通过批评“不敬”来阐发敬慎威仪的自重观念。具体来说,“不敬”主要表现为怠、惰、傲、偷等,这些行为表现略有差异,而本质相同,即自弃,不自敬重。
春秋嘉言对于怠惰的批评十分常见,如公元前649年,周襄王赐晋侯命,晋侯“受玉惰”,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周内史看到后评论曰:
晋侯其无后乎!王赐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继之有?礼,国之干也;敬,
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7]222
先言晋侯受瑞而惰的表现,进而论礼与敬的关系,进一步指出惰即是“不敬”,即不能够自重。又,公元前578年,刘康公、成肃公代表周王室会同晋侯伐秦,成肃公在接受祭社后颁发的祭肉时不敬,刘康公论曰:
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仪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7]460
刘康公认为,勤礼为敬,怠惰不仅属于对礼的不勤,失敬更是对命的不敬。这两则言论都是对于礼仪上怠惰、自弃的比较笼统的批评,而单襄公批评晋厉公在柯陵之会上“视远步高”,已是从具体而微的言行容止批评不自敬重,其文曰:
夫君子目以定体,足以从之,是以观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处义,足以步目,今晋侯视远而足高,目不在体,而足不步目,其心必异矣。目体不相从,何以能久?夫合诸侯,民之大事也,于是乎观存亡。故国将无咎,其君在会,步言视听,必皆无,则可以知德矣。视远,日绝其义;足高,日弃其德;言爽,日反其信;听淫,日离其名。夫目以处义,足以践德,口以庇信,耳以听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6]91-93
在单襄公看来,“敬”具体表现为目光、脚步、语言、视听等细微言行方面,不合礼仪的言行是一个人内心“不敬”的表现,其根本原因是不能自重。单襄公这篇言辞的观点或结论是晋国必乱,而大段讲述的道理却是批评对容颜举止的不敬;在另一篇言论中,单襄公又从正面肯定晋周“立无跛”“视无环”“听无耸”“言无远”,进而得出推断晋周将能够享有晋国,无论批评还是赞美,其对敬重自身容止威仪的观念是始终如一的。不只是周王室卿大夫有此观念,诸侯国的卿大夫亦然。公元前531年,周卿大夫单成公和晋国韩宣子会晤,单成公目光朝下,讲话声音不够洪亮,叔向论曰:“朝有著定,会有表;衣有襘,带有结。会朝之言必闻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视不过结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则有阙。”[7]786-787这种在外交场所、社会活动中对于表情、目光、脚步、衣着等细节的注重,尤其表现了春秋贵族文化人的自重观念。
傲是和惰相近的行为表现,都属于对自我的放任与放弃,春秋嘉言亦不乏对于“傲”的批评,有时和“惰”连言论说。如公元前577年卫侯因郤犨送孙林父回卫国而设宴享之礼,宁殖观察郤犨表现后发言说:“苦成叔家其亡乎!古之为享食也,以观威仪、省祸福也,故《诗》曰:‘兕觵其觩,旨酒斯柔。彼交匪傲,万福来求。今夫子傲,取祸之道也。”[7]464-465又,公元前545年,郑伯宴享蔡侯,子产评蔡侯不敬,曰:
蔡侯其不免乎!日其过此也,君使子展迋劳于东门之外,而傲。吾曰:“犹将更之。”今还,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国,事大国,而惰傲以为己心,将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为君也,淫而不父。侨闻之:“如是者,恒有子祸。”[7]652
在这些言论所表达的思想中,“傲”同属于一己威仪的表现,同是不自敬重,都受到严厉的批评。
春秋嘉言还有对“偷”的批评,偷为苟且之意,苟且也是对自我的放弃,即不自敬重。如公元前610年,鲁襄仲到齐国拜盟归来,向鲁文公汇报说,齐国将不会攻打鲁国,因为在此次外交事务中“齐侯之语偷”,然后引臧文仲之言“民主偷,必死”[7]350以论证,言论虽简短,却能集中表达鲁国卿大夫对“偷”的批评。又如公元前542年,鲁叔孙豹从诸侯澶渊之会回国,对孟孝伯论赵武曰:“赵孟将死矣。其语偷,不似民主。且年未五十,而谆谆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7]685在这两则材料中,“偷”的主语皆为“语”,语言是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语偷”反映出一个人得过且过的状态,是对自己的放弃,即不自重,同“怠”“傲”同属于春秋嘉言所认为的“不敬”。
春秋嘉言通过对惰、怠、傲、偷的批评,实际上从反面来阐释人对于一己的容止言行应有之敬,就是不怠惰、不傲慢、不苟且、不自弃。这种对自己的敬重更多地体现在礼仪与社会外交活动中,带有仪节形式的意味,所以又常和“礼”相提并论,属于礼的行为表现。综观春秋嘉言对敬慎自我的言论,其背景多为朝聘、晏享等礼仪场所,主体多为周王室、鲁国、卫国、郑国、晋国之卿大夫等贵族文化人,尤以周、鲁为多,反映出这些中原国家对礼的形式之坚守。春秋后期,对礼仪形式的认识发生变化,代表为晋国的女叔齐。公元前537年,即鲁昭公五年,鲁侯前往晋国朝聘,对于鲁侯的言行举止,晋侯与女叔齐有礼仪之辩。女叔齐以为,鲁侯不能守其国,行其政令,失去民心,即使熟悉琐碎的外在礼仪形式,也是不知礼的。就整个春秋时代而论,一方面礼崩乐坏,礼的形式不断被抛弃,所以“惰、怠、傲、偷”比比皆是;另一方面,贵族文化人努力维护礼的形式,阐发容止言行的“敬”乃是礼的外在表现,并对不能敬慎威仪、不自重的行为进行严肃的批评。
春秋嘉言对“怠、惰、傲、偷”的批评带有因果的思考,即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敬重自我的言行,则将会导致遭遇灾难乃至灭亡的结果。如上文所论诸篇言辞,在单襄公的观念中,敬慎威仪与否对成败乃至命运具有决定意义。实际上这种观念在春秋贵族文化人的思想世界里十分普遍,公元前552年,齐侯、卫侯在商任之会上不敬,叔向评论二人“怠礼,失政,失政,不立”[7]593,并因此预测二人将不免于难。客观来说,这一因果判断属于道德伦理而不是科学判断。早在唐代,柳宗元对此即指出“其说多诬淫”,因而“本诸理作《非国语》”,于此文有针对性地加以批驳,曰:“是五子者,虽曰见杀,非单子之所宜必也。”“若是,则单子果巫史矣。视远步高犯迂伐尽者,皆必乎死也,则宜死者众矣。夫以语之迂而曰宜死,则单子之语,迂之大者。”[9]754其因果关系虽未必恰当,而反映的思想观念却是真实的,这种主观设想的因“不敬”而导致的巨大后果,从另一方面正反映出春秋嘉言对敬慎威仪的自重观念的突出与强调。
四、敬业敬人的春秋嘉言之“敬”
春秋嘉言阐发的自律警戒与自重不怠的“敬”之观念,主要指向自我。对于指向“我”之外的世界,春秋嘉言也从于人、于事的态度上对“敬”观念有所阐发,共同构成春秋嘉言所论“敬”之内涵。如前所论,对事业、职责的敬重在西周金文中多有记载,是西周初年已有的“敬”之观念,此义从敬畏天命引申拓展而来,主要反映人与事务的关系,指对王命、职事的应有态度。春秋嘉言沿袭此论,甚至其语言表述亦与金文相仿佛,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周襄王赐晋文公命曰:“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7]274;襄公十四年周灵王赐齐灵公命曰:“敬之哉!无废朕命”[7]564;昭公二十八年晋国魏舒勉贾辛云:“行乎!敬之哉!毋堕乃力!”[7]914此类“敬”为上对下的勉励之辞,常用于执行事务之前,强调做事之前敬重认真的心态,所谓“敬其事则命以始”[7]193。不仅是初始时候的保持敬重认真的态度,春秋嘉言还强调对于职事自始至终的敬重,而且因为敬重,进一步强调谨慎,“敬”之此义又常与“慎”连言,所谓“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7]625。无论是对于事业开始时的勉励,亦或对于整个职事始终的认真,这一层面的表述,多止于言辞概念,更多的属于对西周以来的敬职、敬业思想的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强调对于某一种具体职责的严格履行的观念,属于春秋嘉言在“敬”观念认真负责义的拓展。如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听闻夷吾的上诉而责备士在为二公子筑的城中置薪,士为晋国司空,回答自己所做都是坚守司空之职的使命,因为他认为“守官废命,不敬”[7]206。又如公元前570年,诸侯在鸡泽会盟,晋侯之弟扬干扰乱军行,魏绛为晋国中军司马,不畏晋侯而杀戮处决扬干之仆,以生命来捍卫对职责的敬重,在写给晋侯的《请罪书》中说“军事有死无犯为敬”[7]502,表达的正是他敬重职守的观念。春秋晋国是法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起源地,晋国两位卿大夫关于敬重职守的言论,本质上反映了法则至上的观念。
“敬”于对他人而言,侧重于恭敬、孝顺、尊敬等义。这个意义在金文与《尚书》中不多见,《诗经》有之,如《小雅·小弁》说“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毛传:“父之所树,己尚不敢不恭敬。”[4]421表达对父母恭敬的观念。春秋嘉言对“敬”在这一层面的意义亦有阐发,本质上反映的是处理人际关系时的应有态度,这种关系首先是上下级关系,强调下对上的态度,包括子对父、弟对兄、臣对君、小国对霸主等,如作为在大国中艰难生存的郑国,其卿大夫子驷曾论小国生存之道曰:“敬恭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7]521表达小国对大国的恭敬义;齐国晏平仲曰:“君人执信,臣人执共。忠信笃敬,上下同之。”[7]599刘康公之论云:“敬恪恭俭,臣也。”[6]76指出作为臣子须当恭敬。鲁国公不悦其父季武子任命自己为马正,不愿就职,闵子马见之,以子侍父之道劝勉曰:“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无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7]605“敬”在此一层面的意义反映出春秋时人的伦理观念,属于礼的范畴,如晏子所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7]906比较全面地罗列了人际伦理,“敬”的态度正是对臣、子、弟的要求,这是春秋嘉言于他人之“敬”的主要意义。当然,除了上下级关系,“敬”也含有指向平等的人际关系之义,强调对于他人的尊敬与尊重。如公元前627年,臼季向晋襄公举荐冀缺,理由是他曾经看到冀缺于其妻,“敬,相待如宾”,并言“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7]291,此一“敬”义即是侧重于平等关系中的尊敬。
综上,春秋嘉言继承和发扬着自西周以来“敬”的观念,包含了敬畏、警戒、敬重、谨慎认真等丰富内涵。这些意义相近,难以绝对区分。一方面“敬”因具体对象不同而意义侧重有别;另一方面虽然对象有别,重心却不在对象,而在“我”。“敬”归根结底是春秋嘉言对待“我”和自身、宇宙、他人、事务等的关系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自我修养范畴,和信、礼、义、勇等共同构成春秋上层统治者所认同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范畴中,“敬”又有其独特性。其一,因“敬”更多层面地实践于自我,故为诸多修身范畴的根本,嘉言所谓“敬,身之基也”[7]460;“敬,民之主也”[7]657。强调的正是“敬”为立身之本;其二,“敬”已属于人物评价的范畴。“敬”作为对一个人一生的评价,是一个比较好的谥号,春秋人物中多有以“敬”为谥号的,如管敬仲、田敬仲等;而“和安而好敬”[6]439是祁奚从人物品质鉴定的角度对其子祁午的评价。因此“敬”的品质培养成为贵族教育的重要内容与目标,《国语》所载申叔时《施教论》阐述如何教导楚国太子时曰:“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而戒惧焉”;“明敬戒以导三事。”[6]529总之,作为修身范畴的“敬”在春秋嘉言中被大量言说阐述,丰富和拓展了西周以来的价值观,成为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精神传统的重要构成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