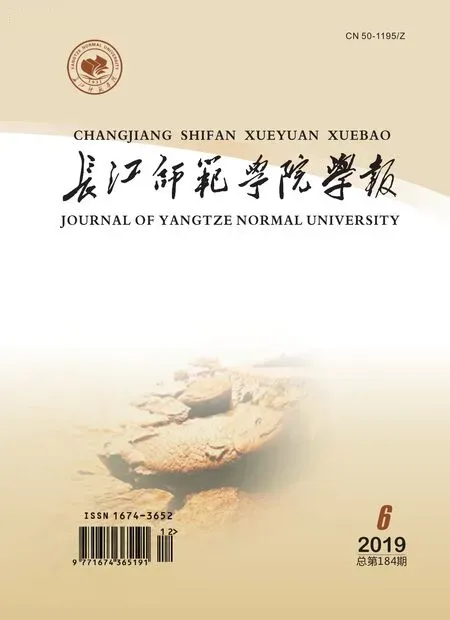林纾《傅眉史》与“武侠小说”的兴起
林保淳
(台湾师范大学 国文系,台湾台北 116)
一、“武侠”肇兴与“强种保国”
武侠小说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与发展,一般多认为与晚清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备受鸦片之毒害,因而导致民病国贫、体弱多病,故有识之士起而呼吁提倡体育、发扬国术,企图“强种保国”[1]、“增强中华民族体质,洗刷东亚病夫耻辱”①此为徐一冰在1908年所创的中国第一所体操专门学校的校训,参见徐元民《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体育思想的传播》,师大书苑,1999年,第99-121页。的一片武术热潮有关②如最早完成的王海林《中国武侠小说史略》(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第6章、罗立群《中国武侠小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第7章,其后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皆对当时蓬勃的武术发展做了扼要的描述。。尽管其中最关键的“SICK MAN OF ASIAN”(东方病夫)一词③“SICK MAN OF ASIAN”原为英国伦敦《学校岁报》用以批评当时中国清政府的用语,后来被上海《字林西报》于1896年10月17日转载。同年11月,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第10册(光绪二十二年,即1896年,十月一日,第650-652页)翻译刊登,题为《中国实情》,其后即广受瞩目,激起甚大的反响。实际上,此词本是针对中日战争后腐败萎弱的中国政府的“政体”而发,并未指涉到中国人的“身体”,且原意为“亚洲病夫”,亦非“东亚病夫”,但在梁启超转译时,以“政体”“身体”相互涵摄,中国传统向来以为国家为人民所组织而成,“身体”与“政体”之间,常是一而二、二而一无法分割的,故此,原为针对“政体”而发的评语,后来被普遍认为是西方人(后来似有意无意间特别强调是日本人)嘲讽、鄙视中国人“身体”的谑称,虽为“误读”,但却是中国人用以激励自己自立自强的重要推动力量。有关此一词语的来龙去脉及意义的转化,杨瑞松《想象民族耻辱——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东亚病夫”》(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3期,2005年5月,第1-44页)一文,有详尽的分析,可以参看。,原意与后来流传的寓意有相当大的差距,但从国族想象到身体喻义之间的自然联系,其所可能激发的自立自强意识,无疑是强劲且庞大的。因此,当时不仅全国各地纷纷成立有关弘扬体育、国术的社团,若干文学作家(尤其是具有武术根底的),亦不乏有藉传述中国名武术家行实、轶闻以作激励者,如形意、八卦拳名家姜容樵(1891—1974)就曾写过《当代武侠奇人传》(1930),书中历述当代武术名家传奇,是书用意,姜侠魂评论说“国病民弱,为我国近世耻辱之一。开篇即揭出武术不发达原因,是著者提倡国术洗雪国耻一片婆心”[2],而众所周知的武侠鼻祖向恺然(平江不肖生,1889—1957)在《近代侠义英雄传》(1923)中,于第十四回刻意虚构了一个西洋大力士说出一段话:“鄙人在国内的时候,曾听得人说,中国是东方的病夫国,全国的人都病夫一般,没有注重体育的。鄙人当时不甚相信,嗣游历欧美各国,所闻大抵如此;及到了中国,细察社会的情形,乃能证明鄙人前此所闻的,确非虚假。”[3]此段话语,无疑是为了强调西方人桀骜骄横、蔑视嘲讪中国人而设计的,并以此为后来霍元甲“三打大力士”的故事作张本,为中华英雄扬眉吐气,一雪国耻,一抒积郁,这是何等大快人心,而这非得凭借着强健的体魄、精湛的武术不可。向恺然于1951年回顾当年的创作心路历程,云“志在提倡武术,打击豪强兼并分子”④见向恺然《自传》,收入《江湖奇侠传》(岳麓书社,1986年)书前,文中提到除众所周知的《江湖奇侠传》及《近代侠义英雄传》外,并言及《拳术见闻录》《拳术传薪录》《拳师言行录》《猎人偶记》等小说,“多为提倡国术”。,可见藉小说以弘扬武术精神,当为民初武侠小说家创作的共同心声——武术其重点在“武”,而“打击豪强兼并分子”则无异于“侠”,向恺然之武侠说部,被视为武侠小说开山鼻祖之作,良有以也。
尽管清末以来有关武术、行侠主题的小说如此丰硕,但相关作品,叶洪生曾“据马幼垣考清末民初众多小说期刊所收作品”,认为“最早标明为‘武侠小说’者,厥为林纾在《小说大观》第3期(1915年12月)发表的短篇小说《傅眉史》”,并列举“以‘武侠’为书名之荦荦大者计有:钱基博与恽铁樵编撰的《武侠丛谈》(1916年)、姜侠魂编撰的《武侠大观》(1918年)、唐熊所撰《武侠异闻录》(1918年)、许慕羲所编《古今武侠奇观》(1919年)以及平襟亚主编《武侠世界》月刊(1921年)、包天笑主编《星期》周刊之《武侠专号》(1922年)等等”,叶氏由此得出结论说:“至此,‘武侠’之名不胫而走;透过报纸、杂志的宣传鼓吹,社会大众也逐渐接受‘武侠小说’存在的事实。”⑤见《武侠小说谈艺录》(台北联经出版社,1994年),第13页。马幼垣之文为《水浒传与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收入首届“国际武侠小说研讨会”论文集中(香港中文大学,1987年),见原文附注7。
1915年,在包天笑主编的《小说大观》第3集上,刊出林纾的一篇题为《傅眉史》的文言短篇小说,编者包天笑在目次与内文中皆明标“武侠小说”四个醒目的字样。论者皆谓这是中国小说以“武侠”分别类目之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叶氏此论后半段大体无误,但《傅眉史》却并非国内首用“武侠小说”类目之始。“武侠小说”兴起于民初,由于年代久远,资料难寻,导致一孔之见而未窥全璧。随着早期文献资料大规模数字化,数据库检索已经十分方便,一些稀见资料得以发现,过往的既成定论由此改写。在2019年6月出版的《长江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上,韩云波根据“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查询结果指出,“中国报刊首次以‘武侠小说’作为文学类型名称的个例”有可能是《香艳杂志》第2期署名见南山人的《金钏缘》,在该篇题目“金钏缘”上方明确标示其类目为“武侠小说”[4]。《香艳杂志》由民初文人王文濡主编,据马勤勤考证,第2期大约出版于1914年8月①有关《香艳杂志》的刊登时期,由于预订出版日程屡遭拖延,故颇有异说,本文取马勤勤《〈香艳杂志〉出版时间考述》(《汉语言文学研究》,2013年第4卷第3期,第60-66页)之说。。赵海涛引录了《金钏缘》小说全文,并对前人认为见南山人即杜求煃的观点进行了详细考证,结论是“我们只能说,见南山人有可能是杜求煃,但不能确定”。《金钏缘》对于“武侠小说”而言,“这应是该词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最早出现之时”②见赵海涛《“武侠小说”作为专有名词的最早出处暨见南山人考释》,见《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3期第32-37页。到2019年10月本文最后修改定稿之时,由于《天水师范学院学报》延迟出版,中国知网及该刊网站均未见到此文,由赵海涛向笔者提供此文排版清样,特此致谢!。
《金钏缘》之所以标目为“武侠小说”,自有其道理,正如韩云波所指出:“这是一篇描写英雄盗窟救美的具有典型明清传奇风格的文言短篇小说。”[5]《金钏缘》之内容,叙述天台胡孝廉精通武艺,人品端正,有一女子仰慕其为人,夤夜私奔,赠金钏以为信物,而为其所拒,宁可先上告父母,寻求正规婚姻之道,遂决计上京禀知其父。在路程中曾仗义骇退强行索物之乞丐,亦力败炫技之僧人。未料此僧率众寻仇,设下鸿门之宴,胡孝廉谈笑用兵,力退其党,并适巧救出前此赠金钏之女子,遂共往京城,商得双方父母同意,完成鸳盟。其中有武技、有行侠,亦有儿女之情长,已粗具后来“武侠”之元素,若仅从“武侠小说”一词作为小说类目的出现时间层面而言,当足以取代《傅眉史》为中国首篇之“武侠小说”。

图1 《香艳杂志》创刊号封面及第2期“武侠小说”《金钏缘》首页
虽然《香艳杂志》首标“武侠小说”,但也要注意到,《香艳杂志》月刊于1914年6月在《礼拜六》刊登发行广告,随后出版,仅刊行12期即告停刊,远远不如《小说大观》流传之广且久。同时,编者王文濡的知名度未若包天笑,且见南山人名不见经传,故影响力自不如林纾,后来更是寂寂无闻,是以论“武侠小说”之源起者,仍多集矢于林纾之《傅眉史》,虽于文献之考究有所缺失,亦无怪其然。
二、林纾的“武侠观”
林纾(1852—1924)为晚清古文大家、翻译名手、说部翘楚,自身谙熟武术,更喜描绘有关武术、异侠事迹,所著《技击余闻》(1908)①《技击余闻》版本甚多,据林薇《林纾自撰的武侠小说——〈技击余闻〉最早版本辨正》(《新文学史料》1999年3期,第195-196页)考订,确定是在1908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庚辛剑腥录》(1913,后改题为《京华碧血录》),自来为谈武论侠者所津津乐道②如钱基博(1887-1957)即对《技击余闻》之“叙事简劲,有似承祚三国”赞赏不已,而决意不让林纾专美于前,因而特别写了《技击余闻补》(台北广文书局,1983年)。。
《技击余闻》共48则,所描述的多为具有勇力、武技的奇人异士,或取之于历史如《张李成》,或采之于传闻轶事如《浮水僧》《黄长铭》,或亲身闻见如《洪厓二郎》,或友人转述如《刘彭生》,其中和尚、道士、俳优、舵工、纫工、菜佣、小吏、盗贼、老人、妇女、小儿、侏儒,乃至外国力士,出身背景、身份、职业、性别、年龄,可谓形形色色,涵盖面甚广,其共同特点在于皆身具不凡的艺业、勇力,且多令人瞠目结舌者,这与《太平广记·豪侠类》所收的唐代剑侠传奇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尽管其中如《康小八》之“足心生毛,能疾走如飞,日行百里”、《徐安卿》之“出二手挽枯骨之腕,力拗而折之”、《浮水僧》之“蹑足履水如平地”,可能不无夸张之嫌,但多数都还算相当平实,力袪唐人小说神奇飞剑、隐身变化之神怪,盖林纾自身曾习武③林纾《七十自寿诗十五首》云:“少年社里目狂生,被酒时时带剑行。列传长思追剧孟,天心强派作程婴。”见朱羲胄《贞文先生年谱》卷二,见《林畏庐先生年谱》(上海书店,1991年)第46-48页。此诗可以为证。,自知武术的极限何在,故不为荒怪诡异之说,实可谓是新开了技击摹写的新风气,其后若干仿效之作,有关接续仿效林纾《技击余闻》而撰写的系列作品,有钱基博的《技击余闻补》、雪岑《技击余闻补》、朱鸿寿《技击遗闻补》及《技击述闻续录》、江山渊《续技击余闻》、顾明道《技击拾遗》、山宗《技击余谈》(《技击琐录》)、金惕夫《技击琐闻》等[6]。其开启“武侠”先声,实已蔚然成风,可以为证。
值得一提的是,《技击余闻》中特别强调“少林”宗派及“内家”功法,如《铁人》之江右某寺住持“精少林剑术”、《浮水僧》之可能为“少林宗派”、《横山二老》王趡之“少林的髓”、《祖塔院石桃》济颠塔寺僧之“精少林之学”,以及《瘿叟》之“内家拳术”、《汤教师》之“精于内家之学”,皆屡屡致意,这对后来武侠小说之以少林为武林最大门派,以及侠客多以“内功”取胜的摹写惯例,亦不无影响;至于《侏儒》中所说的“绝脉”“点穴”,以及《鹿鹿》中“以指点渔者臂腕相接处,渔者忽立而笑不已”的“笑穴”,也是后来武侠小说的常见模式。由此可见,《技击余闻》一书,诚如蔡爱国所论,洵可视为“现代武侠的先声”[6]。
《京华碧血录》共52章,其中的主角邴仲光,实即林纾自身之写照,小说中藉书生邴仲光游历京师的闻见,将庚子义和团事变的前因后果及当时风声鹤唳、局势混乱的情状,有相当写实深入的描绘,而对假托神佛的义和团颇致讥评。其中邴仲光巧获古剑,并前后得受僧履、僧蠲二老和尚传授剑术,虽未大成,而骎骎然剑术精奇的情节,与后来武侠小说惯有的“获宝”模式,相当接近,可谓已发武侠小说之先声,该书第三章记僧履自言其习剑的历程,谓:“自言为开封人,居嵩山,曾事少林妙善师,习剑十年。初时强人而就剑,久乃剑与人合,闭目中,剑恒旋折身之左右,又久则并其身而忘之,跃跃然身已成剑矣。”[7]这段描绘,上承唐代剑侠小说,下开还珠楼主的剑仙之风,而又隐隐与后来新派武侠小说常用的“身剑合一”吻合,在《技击余闻》之外,也别具其影响力。
林纾之喜于摹写武术异人,固然与其曾身习武术有关,但更可能的创作意图则是在当时总体“强种保国”的普遍思潮影响下有心而为之的,尽管《技击余闻》《剑腥录》中并未明显透露林纾创作这些小说的确切命意,但我们从林纾所翻译的一些小说序文中,却不难发现其命意之所在。
1903年,林纾在《埃司兰情侠传》序中,对中国自汉光武以来的“柔道”大表不满,“哀其极柔而将见饫于人口,思以阳刚振之”,故企图藉此书“其中男女,均洸洸有武概”的故事,“以救吾种之疲”,因此,尽管“是书所述,多椎埋攻剽之事,于文眀轨辙,相去至远”,还是“取而译之”,最终极的目的,则是“亦特重其武概,冀以救吾种人之衰惫,而自厉于勇敢而已”[8]。这与清末民初的武术名家之欲藉武术提振国人体魄,宛然出于一辙。
在《鬼山狼侠传》序文中,林纾亦特别强调“吾国《水浒》之流传,至今不能漫灭,亦以尚武精神足以振作凡陋”,因此虽明知此书中人“不驯于法,足以兆乱,然横刀盘马,气概凛烈,读之未有不动色者”,是“仍有益于今日之社会”[9],因而特加翻译的。
1907年,林纾更在《剑底鸳鸯》的序文中,深切表明:“余之译此,冀天下尚武也。书中叙加德瓦龙复故君之仇,单帔短刃,超乘而取仇头,一身见缚,凛凛不为屈。即蛮王滚温,敌槊自背贯出其胸,尚能奋巨椎而舞,屈挢之态,足以震慑万夫。究之脑门人,躬被文化而又尚武,遂出撒克逊不列颠之上,今日以区区三岛凌驾全球者,非此杂种人耶?故究武而暴,则当范之以文;好文而衰,则又振之以武。今日之中国,衰耗之中国也。恨余无学,不能著书以勉我国人,则但有多译西产英雄之外传,俾吾种亦去其倦敝之习,追蹑于猛敌之后,老怀其以此少慰乎!”[10]这篇序文,简直可以视为林纾翻译外国若干以“侠”为名的相关小说的一篇总序,故1924年周瘦鹃在一篇题为《侠客》的文章中,以读者立场,推崇林纾于1910年所译的《大侠红蘩露传》云:“我思侠客,侠客不可得,去而读游侠列传,得荆轲、聂政诸大侠;我又于西方说部中得大侠红蘩蕗,得大侠锦帔客;我又于西方电影剧中,得侠盗罗宾汉,得侠盗查禄。千百年后,犹觉虎虎有生气。”[11]以此,蔡爱国谓“自梁启超以来,进步知识分子对侠的精神的重视,可看成是《技击》系列的思想根基之所在”[6],是确有卓见的。
不过,林纾虽然译介这些以侠题名的小说,却未必完全认同这些侠的行径,“椎埋攻剽之事,于文眀轨辙,相去至远”“不驯于法,足以兆乱”等语,基本上还是将侠客定位于“贼”的,只是期盼着“脱令枭侠之士,学识交臻,知顺逆,明强弱,人人以国耻争,不以私愤争,宁谓具贼性者之无用耶”,这与民初知识分子盛称侠客,如章太炎等,还是有若干的差距,不过也为侠客后来在武侠小说中的形象,开启了逐步导归于正、富理想化色彩的契机。
三、“武侠小说”名义溯源
林纾尽管在他的自撰或译介的作品中,往往武与侠并举,已可目为武侠小说的先声,但他却从未连用过“武侠”二字,恐怕更未设想到可以用“武侠”二字当作一种小说的类目,直到1914年明标“武侠小说”类目之后,“武侠”才开始正式被定为类型小说。究竟此二字,其渊源脉络如何?叶洪生认为,“武侠”一词,“是日本人的杰作;而辗转由旅日文人、学者相继采用,传到中国”,“至迟在清末之前,尚未出现‘武侠’”[12],由此可见,“武侠”这一概念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就武侠小说“名义史”的角度来说,此一观点半对半错,的确,晚清学者使用“武侠”一词,是深受日本人影响的。叶氏特别标举了日本明治时代后期的通俗小说家押川春浪(1876—1941)三部轰动日本而以“武侠”命名的小说。据日本学者冈崎由美所述,押川春浪首先是在儿童小说《英雄小说——武侠之日本》(1902)使用了“武侠”一词,其后《战时英雄小说——武侠舰队》(1904)①此书的创作时间,据《新潮日本文学辞典》(东京新潮社,1988年)第226-227页所云,为1900年,网络数据亦多持此说,然冈崎由美则定在1904年。、《英雄小说——东洋武侠团》(1907)、《武侠小说——怪风一阵》(1911)、《冒险小说——武侠海杰》(1912)陆续出版;甚至还主编了《武侠世界》(1912)杂志。尽管押川春浪所谓的“武侠”是“科幻惊险小说,深受法国作家维恩(Jules Verne)的影响,大都以现代的冒险家漫游各国,探索秘境为主要内容”[13],与后来中国所称“武侠小说”大相径庭;但一经沿用,不仅在日本广为流传,而且也影响了曾经赴日留学的许多文人。1903年,梁启超在横滨所办之《新小说》月报中,刊有“定一”评论《水浒传》的文章,云此书“为中国小说中之铮铮者,遗武侠之模范”①定一,本名于定一(1875—1932),字瑾怀,江苏武进人,该文收入《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9页。,应是当时国人首度使用“武侠”一词;1904年,梁氏著《中国之武士道》一书,自序中两处提及“武侠”②梁氏于《中国之武士道·自识》中云“季布以武侠闻名于世”,并致慨于自季布以后,“武侠无闻”,此盖基于救亡图存的观点抒论,见《饮冰室全集》第44册(台北文光图书公司,1959年)。;1908年,徐念慈(觉我)于《小说林》月报第11期发表《余之小说观》一文,略谓:“日本蕞尔三岛,其国民咸以武侠自命、英雄自期。故博文馆发行之……《武侠之日本》……《武侠舰队》……一书之出,争先快睹,不匝年而重版十余次矣。”徐氏更亲自翻译了《武侠舰队》,改题为《新舞台三》③此一题名极怪,颇疑为《新舞台》,盖书口及目次虽题《新舞台三》,而书眉多题《新舞台》也。,从《小说林》第2期开始连载到12期结束。凡此种种,显然都足以证明此一词语的流传,实与日本有莫大的关系。
不过,叶氏据此而论断在清末以前,中国典籍中从未有“武侠”,恐怕就大有斟酌的余地。尽管传统典籍中以“武侠”二字连读者甚为罕见,如《韩非子·五蠹》的“侠以武犯禁”、《淮南子·说山》的“喜武非侠也”,都以“武”与“侠”分立;但元、明之间,已有不少文人开始使用“武侠”一词,最早应是元代苏天爵(1294—1352)《滋溪文稿》卷五《曹南李时中文稿》所云“昔宋之季,文日以弊,而江、淮俗尚武侠,儒学或未闻也。”此处的“武侠”意为“尚武行侠”,与今日的习惯用法相吻合;其后明、清两朝,亦有使用者,基本上正反两义皆有,以下除张佩纶一条材料之外,兹以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为检索来源,得到相关数据,依大致年序胪列如下:
夫吴虽一邑乎,而寔江以南一大都会,闾井骈阗,比屋相望,而中间轻俊佻达、服奇志淫、徂徻市魁,武侠犯禁者,何日蔑有也。——明范允临(1558—1641)《输寥馆集》卷二《吴县袁侯考绩并贺封公时岳先生六袠寿序》
故天地示变,兵荒酿乱,武侠者不难揭竿,鲁脆者易于簧鼓。——明朱吾弼(1589年进士)《皇明留台奏议》卷一《君道类》
丈夫固多事游,游之所至,登山临水,旷然易悲;越国怀乡,凄然易感。况古名臣杰士孤孽之伦、文藻之客、武侠之英、闺房之秀、释道之流,人往代新,过其地者,古城残垒、故宫遗剎之间,常立马维舟,低徊而不能去。——明万时华(1590—1639)《溉园集二集》卷三《陈子厚两游草序》
叛儿以白花遁祸,季跖以柳下称强,斯则柳之武侠也。——陈元龙编《御定历代赋汇》卷一百一十六收录明徐世溥(1608—1657)《柳赋》
有圣贤之豪杰,有武侠之豪杰,有道义之气节,有愤激之气节。武侠者,能以其材略集天下之事,愤激者,能以其意气树一世之标,不可谓无裨于世。然或安卑近而未光大,或始奋励而鲜克终,则不学无术故耳。——明汪应蛟(?—1628)《汪子中诠》卷三
芷园文豪武侠,闯贼陷神京时,大节不屈。——明邝露(1604—1650)《峤雅》卷二《二臣咏·张侍郎家玉》
盖敝邑凋疲之区,恂悫绌而武侠横,侘傺无聊之日久矣。——明昌日干《存笥小草》卷四,《柬陈小衡父母》
因戏言:生平知己,惟二李相公,然论其人,则合肥以为儒,公以为侠;论其书,则合肥以为宜瘦,公以为宜肥。兼取之,则品当在文儒、武侠之间,书在燕瘦环肥之际乎!——清张佩纶(1848—1903)《涧于集·书牍》卷五:《致李兰荪师相》
由上可见,从元至明,乃至于清末,皆已有文人断续使用“武侠”成词,其中徐世溥的《柳赋》引北魏杨叛儿毅然去魏投梁及春秋盗跖的典故而云“武侠”,虽未必尽合今意,而勇毅果敢、据乱作盗之举,实与古代的侠客观念颇为相合①《杨叛儿》为乐府旧题,属《清商曲辞·西曲歌》,新、旧《唐书》的《乐志》都提及此曲本事,实为北魏胡太后与其所幸少年杨华(白花,一作杨旻)故事,杨华因畏祸率众投奔于梁,胡太后思之不已,为作《杨白花歌》,词曲凄艳哀绝。杨华之去魏,勇毅果敢;盗跖相传为柳下惠之弟,为春秋时著名大盗,徐世溥此赋咏柳,特引此二人为“武侠”象征,荀悦《汉纪》卷十谓:“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皆仍承续古代的侠客观念,而在此处以“武”加以形容,应是取其“勇武”之意。。换句话说,“武侠”二字,并非日本首用,中国历来也有此语,但这些书籍流传不广,较鲜为人知,固无怪其然;但张佩纶为名臣李鸿章女婿,著名的清流党人,于晚清甚有名望,所用“武侠”二字虽与武术、侠客无甚大关联,却始终无人察知,倒是一件颇令人惊诧之事。不过,以此也可侧面印证,当时“武侠”一词的流传、援用,是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
四、林纾《傅眉史》与“武侠小说”
尽管“武侠”二字经旅日文人力加宣扬,由日本舶来中国,渐成熟语,到1914年8月的《香艳杂志》第2期方才有见南山人的《金钏缘》标目为“武侠小说”,但流传未广。1915年2月20日《礼拜六》杂志第38期,刊登了署名“小草”所写的《武侠鸳鸯》,虽有“武侠”二字,但却仍题署为“教孝小说”;即便是类目有九的《小说林》,但连徐念慈在翻译押川春浪的《武侠舰队》时,也只是用“军事小说”而已。林纾的《傅眉史》是继《金钏缘》之后第二次用“武侠小说”类目的,但衡之往例,恐怕也不是刻意为之或有所仿效,而是“武侠”这个在中国文化中本就固有的词汇,在偶然之下又被提上了日程而已。

图2 《小说大观》第三集刊载林纾《傅眉史》首页
《傅眉史》一文,究竟因何会被包天笑题名为武侠小说?可从其故事梗概大抵窥出,其情节内容大致如下:书生吕居翰,年方二十,而博通经史,受荐为某部部郎,部务闲暇,每以闲游、吟诗为乐。一日于陶然亭偶遇身怀武功之黄虎三,两相倾慕,互授文武。吕居翰进境甚速,不二年,即已艺过乃师,黄虎三则因母病返乡。辛亥革命,京师扰攘,吕家隔邻有傅姓母女,女即傅眉史,与吕居翰于患难间相识,共为援助。吕居翰与傅眉史过从密切,爱苗渐长,而未有成说。适京师兵变,乱兵四出抢掠。吕居翰精通武艺,先败其先行者二人,后又携眉史匿于屋檐瓦沟间,乱兵大至,索而未得,挟赀重而去。乱定,两家议订婚约,并决意远赴新加坡,另辟事业。就通篇而论,《傅眉史》写乱世儿女的故事,理当入“社会”或“言情”之类,与“武侠”二字实际上还有颇大的差距。然而,小说分类本就非常困难,尤其是当时所谓“文类”的观念尚未建立,编者为各种小说“巧立名目”,通常是随意题点,故泛泛而称的名目甚多,《小说大观》中以言情、社会、侦探、政治为大宗②据郝奇《〈小说大观〉的研究》(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统计,其中言情52篇、社会27篇、侦探26篇、政治9篇,居前四位。,其他爱国、军事、外交、家庭、警世、搜奇、哲理、宗教等类目,琳琅满目,不一而足,颇伤芜颣。《傅眉史》是《小说大观》全部5集中唯一题为“武侠小说”的作品,其余作品中有“侠名”者如《髯侠复仇记》《卖花女侠》《游侠外史》则分别被题为“侦探小说”“社会小说”“侠情小说”而不名“武侠小说”,篇名无“侠”字的《南飞子》则又题名为“侠义小说”,可见其命名纯为“自由心证”。这基本上可以反映当初中国小说在西方小说传入的刺激下,编者亟欲为小说类别重新定位、分类,以清眉目,并藉耸动的标题以醒豁读者心目、以达到宣传效果的心理。其所以被目为“武侠”者,大抵是因吕居翰曾向黄虎三习武,精通少林武功、击石之技,具有“武”的特色;尤其是黄虎三的名字,乃是曾“殪三虎”而来,且显露了一段“指端风出,触狗,狗噤而退,如当巨拳,跛不能步,伏于碑下”的绝技;而其后吕居翰艺过乃师,亦在乱兵入侵时,“连发二石,二卒皆中目,呼曰:汝不畏弹耶?生直前,以两手分执二卒之背,掷诸门外,力阖其扉”,显示了不凡的艺业。同时,吕、黄二人倾盖相交,有类于气义相结;而吕居翰之援助幼寡,虽不能力歼群匪,亦不失“侠”的行径。因此编者遂笼统以“武侠”概之,未必有深究名义之意。
但是,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包天笑当初的偶然戏题,却因“武侠”二字在字面意义上贴近于中国传统观念,且“武侠小说”新词语的出现又具有耸人耳目的刺激,在追新逐异的心理下,运用此一语以示与当前社会接轨,应是人同此心的。因此就在林纾的《傅眉史》被题为“武侠小说”后未久,《小说大观》所属的文明书局(当时已归并到中华书局),在《小说大观》第4集中①1990年由上海书店及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出版的《小说大观》,编辑者未察,误将原附于《小说大观》第4集外交小说《眢井轶谈》前的这则广告,错植于第2集社会小说《纨袴镜》之前,原来的地图广告则消失不见,经比对河南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小说大观》第2集,可以明显证明其疏失。就刊登了一则广告,明白标举“绘图武侠小说廿种”,主标题下面还绘了一柄宝剑。这20种“绘图武侠小说”分别是:《大明奇侠传》《仙侠五花剑传》《风月传》《三门街》《升仙传》《忠烈传》《红(弘)碧缘》《前后七国志》《金台传》《铁冠图》《五剑十八义传》《奇中奇》《木兰奇女传》《天宝图》《三合剑》《女军人》《小红袍》《英烈传》《正德外纪》《年公平西》。除《女军人》不详出处外,大抵都是各种不同类型的古典小说(旧小说),名目混淆,同样难以究论。但却可略窥当时对“武侠小说”的理解,仍在一片混沌之中。而在其后,“武侠小说”之名不胫而走,在1923年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与《近代侠义英雄传》刊出之前,以“武侠”为书名的重要著作已有不少,可见其影响力之深远,而林纾的《傅眉史》则俨然就成了中国武侠小说的开山大作!

图3 河南大学图书馆藏《小说大观》第四集武侠小说广告及第二集原有地图广告
五、结语
包天笑主编的《小说大观》以季刊方式出刊,当时即获有很高评价,以为“在杂志中最伟大最充实的要推《小说大观》为第一”[14]。范伯群亦谓:“小说杂志而有季刊,《小说大观》为首创。”[15]当初规划的是“每季发行一集,年分四集,每集字数在三十万以上”①见《小说大观》第一集《例言》。然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之十八云:“《小说大观》是预备每年出四巨册,每册约二十多万字,大型本。每年出四册的,名之曰季刊,现在出小说杂志的,都是出的月刊,出季刊的却还是没有。”所云“二十多万字”与此略有出入。,但其创刊日期,据1990年上海书店的《影印说明》,是始于1915年8月,而于1921年6月发行最后一集[16],可《小说大观》前13集分别是每年4集,而第四年则仅有“民国七年第十三集”之目,第14、15两集均未标明年月,殊为可怪。同时,既是创刊于1915年8月的季刊,则何得于1915年仍有4集?盖当时出版的期刊杂志,每多拖期,往往与预订时间不符,想来即使要确定《傅眉史》的发表时间,都还得做一些考订。
据范伯群统计,《小说大观》共出版15集,“刊登的小说创作有短篇100篇,创作长篇小说18部;翻译短篇50篇,翻译长篇26部”[17],当时名人,如叶楚伧、姚鹓雏、陈蝶仙(天虚我生)、范烟桥、周瘦鹃、张毅汉等人,都是重要的作者,尽管多是文言作品,但对中国通俗小说的流行与传播,却有一定的影响。以此而论,《傅眉史》虽不是第一部以“武侠”冠名的小说,但显然,由于林纾本身对武侠的热衷、包天笑及《小说大观》的影响力,“武侠”名目的广为流传,林纾之功,是绝对不能轻估或抹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