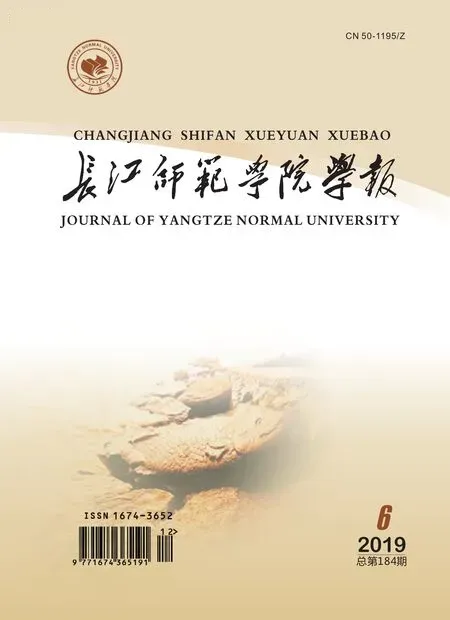滇西土司国家认同研究
——以南甸宣抚司为例
李 然,字荣耀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一、研究缘起
国家认同是近几年民族学、政治学关注的重点课题,来源于英文短语“National identity”。有关国家认同的研究始于近代民族国家诞生之初,西方对于国家认同研究起步较早,最为知名的是美国民族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相关论述,他在诸多著作中将国家与民族视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并以此展开论述。除此之外,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国家认同感就是公民认同感而不是宗教、文化、种族或民族”[1]。其实关于民族国家的研究有很多视角,其定义大相径庭。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现如今在多边主义与全球化视野的背景下,西方传统的民族国家概念受到了挑战,许多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而是多民族国家,他们对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的反思十分深入。其中,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全球化时代也是民族主义复兴的时代。这既表现在对现存的民族国家的挑战,也表现在到处存在的以民族性为基础的、总是声称反对外来者的认同建构和重构。”[2]29在这里,卡斯特主要想表述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认同已受到了挑战,逐渐向多民族国家演变,其中的民族主义正在愈演愈烈,值得警惕。
中国学者对国家认同的思考源于传统文化的“家—国—天下”观,其内化了国家认同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认同层次中,天下为最高,国家为中,而基础来源于家。知名学者许纪霖认为这种家国天下与自我认同的关系密切,他指出:“古代中国乃是一个家国天下连续体。个人的行动和生活的意义,只有置于这样的框架之中才能得到理解并获得价值的正当性。”[3]因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的国家认同不同于西方近代的国家认同,它是源于个人对于家国天下的认同,是一个联系紧密的认同观,天下远高于国家的认同。也正如许纪霖所言,它是一个“连续的共同体”。这个连续体一直持续到清末社会转型之初,当时正是西方民族国家成型之初,受到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国家认同观逐渐受到冲击,这种现象引起了当时国内许多学者的关注,梁启超就是其中之一。勒文森(Joseph Levinson)在《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中指出,梁启超从文化视角出发将这种国家认同称之为“国家主义”[4],并以此展开了论述。现代学者江宜桦、贺金瑞、燕继荣、郑永年等从不同视角论证国家认同的构建与意义。台湾学者江宜桦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出发认为国家认同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那①似乎应该为“哪”。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灵性活动”[5]。贺金瑞与燕继荣则认为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6],并视其为“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维系一国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6]。郑永年强调了国家认同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没有民族国家的制度基础,民族主义只能表现出一种情感。没有国家认同感,已经建立的民族国家就没有稳固的心理基础。民族国家制度基础和心理基础是相辅相成的。随着国家的崛起,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转型。如果说以前的民族主义主题是如何追求富强,那么现在则开始表现为如何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表达日益强盛的声音。”[7]
作为我国封建王朝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土司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土司的国家认同研究是近几年民族学与历史学关注的重点,其中,詹进伟、田敏从社会治理视角出发,分析土家族马氏土司与中央王朝、内外势力、本地土民的互动,从而概括其国家认同的表征[8];葛政委从地域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和身份认同四个方面出发,认为土司的国家认同维度是相互支撑的[9]。综上所述,前人研究虽然涉及边疆土司,但绝大多数集中于内地土司的研究,对于边疆土司的国家认同关注度稍显不足;而不管在地理空间上还是政治权利网络中,边疆地区的土司核心与边缘的关系更加明显,土司原生文化与华夏文化差异更大,各种互动关系也更加复杂。本文以南甸土司为例,力求系统地概括和挖掘南甸土司的国家认同表征,总结并提炼其国家认同的经验与价值。
二、南甸土司国家认同的表征
著名的社会学家卡斯特认为所有的认同都是建构的,他所说的认同主要包括“性别、宗教、民族、种族、地域、社会、生物等方面的认同”[2]4。结合卡斯特的观点,笔者认为南甸土司的国家认同主要表现为文化认同、身份认同、体制认同及其与边境的互动等。
南甸位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境内。依据史料记载,公元10世纪以前这里就有傣族先民居住。自元朝设立南甸路军民总管府后,南甸开始被纳入中央管辖。明永乐十二年(1414)为南甸直隶州,属布政司管辖;到明正统九年(1444)南甸土司被升为宣抚司,为滇西土司十司首领。民国时期实行土流并治制度,即由土司与国民设置局共同治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52年南甸解放,土司政权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
(一)文化认同:汉地文化与儒家学说的推崇
“土司地区国家认同的基础是文化认同。”[10]南甸土司崇尚汉文化,首先表现在其官署整体布局是按照汉式衙门打造的,梁河县文管所周德才、赵毅在所撰《南甸土司衙署建筑文化初探》中指出:“南甸宣抚司署建筑群受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极深,建筑成汉式衙署式布局。该建筑群按汉式衙署形式布置。由四个主院落,十个旁院落,四十七幢,一百四十九间房屋组成。分为大堂、二堂、三堂、正堂,一进四院,逐级升高,粗梁大柱、青瓦屋顶,古朴大方,雄伟森严。”[11]从南甸土司衙门内部看,其布局为汉式衙门布局,以公堂最为明显,公堂正中设公案桌,桌上放签筒、笔架、朱笔、朱砚、惊堂木等,背后放置一扇象征四品品级的麒麟屏风,下面放置刑具,大堂两侧分插“肃静”“回避”木质高脚牌,陈列御赐銮驾半副,其顺序为龙头、关刀、金瓜、钺斧、朝天蹬、安民、除毒、一手掌乾坤、官衔牌,侧置喊冤鼓,左侧放暖轿、凉轿各一乘,公堂台阶前两侧各置礼炮一架、石狮一只,堂上悬挂“卫我边陲”“南极冠冕”两块匾额,房屋横梁上写有“钦赐花翎三品卫世袭南甸宣抚使司宣抚使刀定国暨阁司绅民重建”的字样。总的来说,土司官署整体布局与中原地区官署差异不大,可见汉文化对其影响之深。笔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南甸土司衙门建筑中设置有专门的儒家学堂,供土司后代学习儒家文化,史料记载学堂多授《三字经》《千字文》等汉式文化精髓,以傣、汉两文标注进行教学。在土司内部行政体系中设置有“秘书”一职,秘书分为内、外两幕,主要为土司建言献策。据《德宏历史资料·土司山官卷》记载:“土司对于秘书极为重视,重金聘请外地汉族文人充任,地位很高。”[12]351因此,从官署的建筑布局、土司后代的教育教学和内部行政人员的构成方面不难发现,南甸土司对于王朝主流文化与儒家学说是十分推崇的,这些建筑遗存与史料便是南甸土司国家认同的重要例证。
(二)身份认同:族源的“追溯”与姓氏的改变
“身份认同是指个体或群体对自身在国家社会关系中处于某一位置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身份认同本质是一种社会认同,即在国家、社会中、个人或群体处于什么位置。”[9]由此可见,葛政委认为身份认同是国家认同的核心,这一点在南甸土司族源的追溯与姓氏的改变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从族源上看,《元史·地理志》载:“平缅路,北近柔远路。其地曰骠赕,曰罗必四庄,曰小沙摩弄,曰骠赕路,白夷居之。”[13]2061963年重编的《南甸司刀龚氏世系宗谱》记载道:“粤稽刀龚氏之先,自有记载以来,起于后汉。当时虽雄长一方,并无文字制度之可纪,逮至有明贡猛公始发扬光大,纳土归国,接受汉封。”[14]从这两条记载笔者发现,元以前中央王朝并没有在南甸设置行政机构,而南甸土司祖先却在元朝以前就开始在这里居住。在《新纂云南通志》中则有着与家谱不同的记载:“其先,刀贡猛。本姓龚,江南上元人也。明初以百夫长从大军征云南,迁千夫长,驻南旬,旋以招曩猛功,授腾冲千户,改姓刀。盖以卫千户,而防南甸者也。”[15]351这里记载的南甸土司族源为江南上元县,是随军征战留守南甸地区的外地人,与族谱记载存在巨大差异,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在历史时期里土司对于中原文化与中原王朝的推崇,他需要论证身份的正统化与合法化,以利于自己的统治。从南甸族源与姓氏的转变足以看出土司对中华正统身份的向往。
(三)政治认同:封建政治体制与礼法的认同
葛政委认为,“政治认同是国家认同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个人或群体对某一政权和政治体系所产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9]。而南甸土司政治认同主要体现在对封建王朝政治体系和封建王朝礼法的认同,即政治上认同封建制度与土司制度,生活上认同封建礼法。
1.封建政治体制的认同
南甸土司对于中央王朝体制的认同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是对于土司制度的认同。土司制度是“将我国西南等地各民族的首领纳做‘王臣’,敕授职衔,渗延国家权力,建构完善国家治理体系能力,使各族土司在‘大一统’历史框架和地方行省管理体制下,成为国家间接统治民族地区和各族土民的‘关键少数’”[16]的一种政治制度。对于实行土司制度,南甸土司对扮演国家戍边大臣的身份十分认同。在元明清王朝更迭之时,只要统治者保留南甸土司世袭罔替的土司制,土司就没有出现过与中央王朝的军事对抗;而从南甸土司衙门公堂中悬挂的“卫我边陲”四字牌匾,也可以看出南甸土司对中央王朝统治疆域与土司戍边职责的认同。
第二是对封建统治体系的认同。南甸土司一直认为自己是封建王朝统治体系中的一部分,这一点体现在其对疆域与统治关系的认同之中。首先,南甸土司认同自己统治的疆域属于中央王朝,这一特征可以在诸多史料中得到佐证。在《明史·云南土司传》中记载,“洪武十五年改南甸府。永乐十一年改为州,隶布政司……(正统)九年升州为宣抚司,以知州刀落硬为宣抚使……”[17]。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四百九十八中记载:“清代南甸宣抚司初隶永昌府腾越州,嘉庆二十四年,升腾越州为直隶厅,南甸宣抚司仍隶属腾越直隶厅。”[13]207这些都证明了南甸土司认同其与中央是被统治与统治的关系。其次,封建统治体系认同的第二个特征是行政体系认同。除了是民族首领、地方豪强外,南甸土司还是朝廷四品命官,是封建国家官职体系中的一员,在其公堂后挂有相应品级的麒麟屏风,这些表征不仅是南甸土司对于封建统治体系认同的实践,还从侧面证明了南甸土司对于中央集权制度的认同。
2.封建礼法的认同
南甸土司的政治认同还表现在其与中央王朝的互动之中,主要体现在对封建礼法的认同方面。据《德宏史志资料》记载,南甸土司世袭须遵循封建王朝礼制,首先在土司世袭更替时由土司提出申请,申请经由中央王朝机构逐级核准,最后由朝廷颁布相关文书信号纸,从而完成委任。在《清世宗实录》中就有这样一条记载:“云南南甸宣抚使刀起元故,请以其子刀恩赐承袭,下部知之。”[18]此外,对封建礼法的认同还表现为对君主的忠孝。据《德宏史志资料》记载,明末永历帝奔缅逃至南甸时,为报明朝对南甸宣抚司的关照之恩,时任土司刀呈祥派刀乐保护驾入缅,刀乐保因此死于“咒水之难”[12]323。这种频繁的互动,既是因为南甸土司受家国认同的情感所驱,也是因为其受封建王朝礼法约束,南甸土司的行为可谓是忠君爱国的体现。
(四)边境互动:对领土与国家主权的捍卫
在土司的国家认同构建中,有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因素影响着土司国家认同感的形成,这便是边境地区外国势力的影响。在统治梁河地区的数百年时间里,南甸土司与英国、缅甸、日本等国家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军事斗争上。也正是通过与这些国家的军事斗争南甸土司才形成了牢固的国家认同观念。
《明史·土司传》《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道光《云南志钞》、明朝天启《滇志》等文献,记录着南甸土司因随同中央王朝征战和戍边受到嘉奖的大量史实资料,他们随明军“三征麓川”,随清军征伐缅甸,随国民党抗击日军。这一系列的戍边卫国战役不仅使南甸土司的势力得到极大发展,也令其得到了中央王朝的大力嘉奖。在《道光云南志钞》中就有南甸土司从政嘉奖的记载:“贡罕子落硬,从征有功,九年,升为宣抚司,以落硬为宣抚使。”[15]351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贯穿了南甸土司统治的五百年的时间。
滇西战争时期,在日军攻入梁河之后,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土司龚授退居小陇川避难,消极抗战,纵容其子投靠日伪政权。滇西反攻开始时,龚授重回司署执掌大权,积极投身抗日,成立了军民合作站,供应军品支持国军抗日。龚授曾致电民国副总理李根源表达抗日决心,在电文中他表示,“我司世受国恩,同仇敌忾,当师体德意,死抗战,与疆土共存亡”[19]。除此之外,与南甸土司有亲属关系的盈江土司刀京发表了《滇西土司否认企图独立》的声明[20],否认了滇西土司与境外帝国主义勾结企图独立的流言[20]。
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南甸土司虽然出现过松懈,但最终选择了正确的道路,积极抗击外来侵略者,维护了家族百年的清誉。
三、南甸土司国家认同表征下的思考
(一)双向的认同:土司与中央
1.政治中的双向认同
在互动中,土司与中央王朝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上相互依附、相互认同的关系,即土司认同中央的统治,认同自身属于中央王朝的一部分并承担相应的义务与责任;而中央王朝也认同南甸土司在滇西地区的统治地位,甚至将其纳入封建官僚体系中,给予其相对于流官地区更大的自由度。这种政治双向认同的根源在于南甸土司与中央王朝双方的利益需求。首先,对于南甸土司而言,在面对边疆麓川政权、缅甸等敌患危机时,他需要依附更大的势力才能保证自己生存与发展的利益不受侵害,而内地的中原王朝就是南甸土司最理想的靠山。也正是通过与中原王朝的联合,南甸土司消除了麓川政权、缅甸等的威胁。其次,对于中央王朝而言,由于行政力量的羸弱与交通的阻隔,难以有效控制边疆民族地区,需要有一个“代言人”来代为治理这些区域,而作为民族首领和地方豪强的南甸土司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了这份职责。因此,土司制度就成为土司与中央双向政治认同的一个关键纽带,两者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认同互动模式。
2.身份中的双向认同
身份认同是一个双向认同的过程,不仅需要土司自己的认同,也需要中央王朝的接纳。自古以来,历代王朝都将少数民族列传视为史志的一部分。自南甸试行土司制度开始,元朝就将土司与土司领地视为国家行政体系的一部分,弱化了其蛮夷的身份,并授予其朝廷重要官衔,使其成为中央王朝戍边征战的重要力量。这一点在前文中已经有诸多的例证。
(二)文化的互构:民族与国家
陈季君认为:“土司地区国家认同的基础是文化认同。自华夏民族形成之日起,无论是华夏民族、汉民族,还是中华民族,她们都是文化民族,华夷分野不在于血缘而在于文化。”[10]如陈教授所言,文化是民族的重要标志。南甸土司是世袭傣族土司,傣族文化是其独有的原生性民族文化。不过,随着中央王朝主流文化的不断传播,南甸土司开始推行儒学,设立学堂文化。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不断整合,从而形成了一种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建构的关系,这一点在南甸土司的生活习惯及其司署的建筑风格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南甸土司衙门虽然属于汉式官署建筑,但其中“太阳门”(如图1所示)的建造,以及主要建筑飞檐顶端装饰的傣族传说中龙头鱼尾的瑞兽ao yi①当地傣族对传说中龙头鱼尾的瑞兽的称呼。,都是本民族重要的民族符号。此外,据史料记载,“在司署的戏台上,既上演汉文化的滇戏,也上演傣戏(傣戏至今有100多年历史)”[12]330。在节日习俗中,“清代中期以前,有过傣历新年的习惯。受到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影响,近代的南甸司署也过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等”[12]330。

图1 汉式官署建筑中的傣族太阳门
(三)土司的实践:爱国主义与边疆建设
1.爱国主义的贡献
民族团结与爱国主义教育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课题。在封建王朝时期,作为滇西世袭土司,南甸土司管理着大片边疆土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汉、傣、景颇等多个民族。据《德宏史志资料》记载,在统治疆域中除了实行头人制外,南甸土司还在景颇族等地区实行原有山官制,即缩小范围进行民族自治[13]207,这不仅体现了南甸土司过人的政治智慧,客观上也维护了区域民族团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甸土司的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观体现得比较明显。1950年梁河逐步实行民主改革,在改革的初期末代土司龚授还是比较顾虑的。据资料记载,1951年龚授接到保山专区通知,让其到北京参加全国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会议,因为对共产党缺乏了解,龚授以为自己有去无回,出发前他向家中亲属讲道,“这次离家,吉凶末卜,可能永别相先,挤①疑为“祈”。求护佑”[21]。参加会议之后,龚授游历了许多城市,在看到社会主义的蓬勃建设后,他的错误认知逐渐消失。就在此次会议上龚授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他向主席讲道,“我是云南省保山专区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梁河县傣族代表龚授。此次当代表来北京参加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我感到非常荣幸和兴奋,当得知可以与全国各民族代表欢聚一堂,互相学习、互相商讨我们少数民族自己当家作主的大事——区域自治时,我感到无限的光荣”[22]10。在此次游历之后,龚授回到故乡做了题为《共产党真伟大》的报告,他详细介绍了中原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并讲道,“我们新中国的伟大,实在了不起。就以我们少数民族方面来谈,一国范围内,各民族团结成一家,如兄弟一样,彼此亲爱,万众一心,当家作主,力量多么强大,所以我们祖国的前途真是伟大,真是光明”[22]17。
在民主改革后,末代土司龚授还先后担任了梁河县行政委员会主任、县长,德宏自治州副州长,省政协副主席,全国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等职务,为我党推行民族政策、维护边疆民族团结与国家领土完整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2.民族边疆治理的贡献
民国时期,以南甸土司为代表的滇西土司积极投身边疆社会建设,在他们联合拟定的《九土司呈中央文》等文件中详细谈及了民族边疆地区政治改革与建设的意见。其中在南甸土司参与的《九土司呈中央文》的呈报中,滇西土司详细论证了滇西地区的发展与改革问题,将其细化为“政治改进、边防整理、农村的维护、教育的普及、公路的完成”[23]456-459五个方面,其中最有见解的是关于教育普及的论述,滇西土司认为,“教育的普及司地人民,夷多汉少,知识多未开化,其间尤以山头最为低下,谋生无术,性质剽悍,以杀掠为技能,以报复为生理,各司每年之收入,多数用于安抚此种民族……拟请派教育专家,调查斟酌设立,最好能拨专款,司地教育经费独立,由十司组织一教育经费保管委员会。盖以夷民教育,须强迫劝导相施并行,非得多享利益,万难入学,故不得不多筹专款,以期推广”[23]458。值得一提的是,在呈书之前,南甸土司已经在其辖境内开设小学教育,进行儒学教育。梁河解放后,在担任梁河以及德宏地区要职时,老土司龚授提出了边区建设的三条途径:“第一,我仍傣族地区,是全国闻名的瘴病之乡,迫切需要医药卫生,拟请多设几个卫生院,使人民健康有保证;第二,我们少数民族文化落后,请帮我们多办几个中、小学校,并请编译教科书,以便教读;第三,边区交通甚感不便,城乡物资交流困难,土产不能远期②似应为“运”。别处,日用品又必须从他处运进,以致常被奸商垄断,物价提高。拟诣多设贸易机构,并修筑公路以利发展经济和保卫国防。”[24]从不同的史料佐证可以看出,南甸土司为我国西南边疆治理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结语
南甸土司统治梁河地区超过500年的时间,在这段历史时期里南甸土司逐渐形成了国家认同的观念,这些认同相较于内地土司有所不同,呈现出政治上相互认同、身份上相互认同、文化上相互建构整合的特点。同时,南甸土司与国外势力存在互动交织关系,这反映了南甸土司国家认同的复杂性与构建的多样性。在这些复杂的关系网中,南甸土司仍然不忘家国天下的中国传统文化,事事以天下为先,百年来他们积极投身民族边疆地区的社会建设,抗击外来侵略者,维护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纵观今日国家认同的构建与边疆地区的建设,我们应以史为鉴,汲取土司治理的经验,从国家与百姓、意识与物质多纬度出发,思想上筑牢国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物质上给予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更多切实的援助,以此来实现多元一体、一国多族和谐共处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