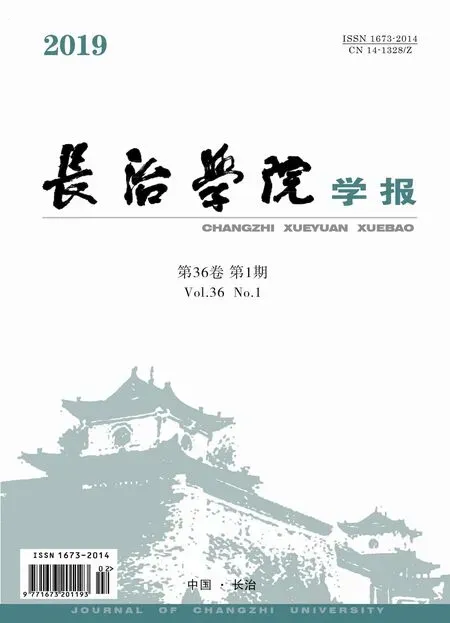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烛照下的九叶诗派
——以里尔克与郑敏为例
车晨阳
(太原师范学院 文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
一、引言
任何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的发展与进步都离不开异质文化的冲击和推进,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冲击才带来了本土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九叶诗人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不容忽视,这既体现在九叶诗派的诗学理论建构上,也体现在他们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对“九叶诗派”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艾略特、里尔克和奥登,例如艾略特的非个性化、客观对应物和思想知觉化以及奥登的人格面具、戏剧化理论等,这些如果要细细阐述开来,并非三言两语能描述清楚的。而在对里尔克的接受化合中,首推九叶派诗人郑敏。郑敏是一个拥有不老诗心的诗人,自1939年写出第一首诗《晚会》起,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笔耕不辍,艺术生命长青,她用源源不断的艺术创造力为我们创造了丰富的文学财富,本文选择将里尔克与郑敏作为论述的中心,或许更能切中其典范意义和现世价值。
二、取向西方现代主义的动因
首先,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在战火纷飞年代的“世外桃源”——西南联大,那里优越的教学资源和浓厚的学术氛围为九叶诗派取向西方现代主义诗学培育了优良的土壤。当时的西南联大人才济济,闻一多、冯至、李广田等都汇聚在联大,这些学者自身本就在文学方面成绩斐然,有很多都是当时已经赫赫有名的作家和诗人,再加上他们大多都在西南联大承担相关课程的教学任务,所以对于青年学生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批人在联大期间翻译了许多西方文学,其中也包括西方的诗歌,如《给青年诗人的信》就被冯至翻译并传播给联大学生,这为些都为联大的学子们营造了良好的学习西方的氛围。对于郑敏和里尔克,冯至在他们中间起到了关键的桥梁作用,郑敏就读于西南联大哲学系期间选修过德语文学课程,而这门课的讲授者正是冯至,这影响了她一生的诗歌道路,郑敏曾回忆说:“……当时我的精神营养主要来自几个渠道,文学上以冯先生所译的里尔克信札和教授的歌德的诗与浮士德为主要……”[1]所以我们可以相信,郑敏在这样耳濡目染的熏陶中,是能够深得里尔克的诗学精髓的。
沿着西南联大这条线,放眼国外,我们会发现九叶诗人中有许多人都曾经有海外求学的经历,这些人或多或少直接接受过西方现代主义的滋养,例如穆旦在西南联大直接受燕卜荪的指导,辛笛在英国留学期间师承艾略特,毫无疑问,这种直接的师承关系比间接的外国文学教学影响更为深刻,孤身处在异国他乡,面对新的文化语境,即使母国文明再根深蒂固,恐怕也很难抵挡周身西方文化的“吞噬”,从而在耳濡目染中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取向。郑敏也于1948—1952年在美国攻读英国文学,再加上当时的美国现代主义正风靡,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西方现代主义肯定“润物无声”地对郑敏产生了影响,这必然会影响她日后的诗艺道路。
其次,作为现代主义的重镇,里尔克的名字早在抗战之前的30年就已经通过冯至等人的介绍进入了中国,然而,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到了抗战进入持久的阶段,他却非常贴合地走进了西南联大学子的血液中,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循环,他们与里尔克的亲近,除了与冯至在德国进行文学研究的背景有关之外,还应当归结于当时的中国在精神世界上与里尔克的亲近。“他们要开花,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这叫做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2]这是里尔克曾经写下的诗句,里尔克这种在喧嚣的年代做一名默默无名的努力者的思想,与40年代中国诗人的意识和灵魂缺口完美契合,这使得他们对里尔克这种默默坚忍努力的精神具有一种自然的亲近。
再次,除了上述外部环境的推力,九叶诗派取向西方现代主义也有重要的内因,这也是体现他们“自觉汲取”的地方,他们希望通过引进西方现代主义诗学而改进当时中国诗坛的缺陷,九叶诗派重要的诗学理论家袁可嘉认为,当时中国的新诗创作流于“感伤”和“说教”,如果想要克服这两大弊病,就必须实现新诗现代化,因而在学习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过程中,袁可嘉把“新诗现代化”理论阐释为“现代诗歌是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3]
三、借镜西方:郑敏与里尔克
西方现代主义诗学在“东渐”的过程中,本土的历史文化传统、现实境况以及中国现代诗歌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也会制约外来文化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九叶诗派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吸收、改造、融合的缓慢过程,无论是对艾略特、奥登,还是对里尔克,再加上不同诗人艺术个性的差异,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会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所以本文选择九叶诗派中某个具体的诗人郑敏对里尔克影响的接受作为论述的主要内容。
(一)哲人式的思考:向死而生
约翰·邓恩、华兹华斯和里尔克可以称得上是对郑敏影响最大的三位西方诗人,他们能够成为郑敏心仪对象的共同原因是“深沉的思索和超越的玄远,二者构成他们的最大限度的诗的空间和情感的张力。”[4]而在这三位中,无论经过怎样的文化冲击,至始至终能和郑敏心灵相通的诗人非里尔克莫属。郑敏曾说她从40年代就非常喜欢里尔克,“因为他跟我念的德国哲学很配合。”[5]
生与死一直是哲学中一个永恒的命题,被哲学家反复思考,也被文人反复书写。关于这一命题,郑敏与里尔克有着“相通的诗心”。郑敏认为,诗歌与哲学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哲学不应被查封在知性的阁楼中,诗也不应该被禁足在感性的花园内。下面就谈谈郑敏如何在里尔克的影响下完成对这一命题思考。
里尔克有许多描写死亡的诗作,通过这些作品表达了其在探索“生与死”这一哲学命题时的思考,里尔克认为生死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死亡也只是生活的一个侧面,“只有与死者享过/罄粟花的人/才能永久不会失去/他最微妙的声音”。所以,在里尔克那里,死亡是作为把人引导到生命的最高峰,并使生命第一次具有充分意义的东西出现的。”[6]里尔克对于死亡的认知深刻影响了郑敏。从数量上而言,在郑敏的诗歌中,“生与死”也被多次提到,与生死主题有关的作品占了很大的篇幅,《墓园》、《诗人与死》、《时代与死》、《死难者》等作品,都反复描写着生死。从精神意蕴上看,郑敏的诗歌体现出一种“向死而生”的内在品质,这与里尔克“‘死’是最高潮的‘生’”的观念一致,“在死的火里曾找到了生”,死在诗人那里成为了另一种形式的生,有时生之美可能就蕴藏在死亡之中,“树木死亡/埋没地下成为煤炭”。郑敏在《诗人与死》中,用更加理性的目光看待死亡,由个体生命的陨落上升为对群体知识分子命运的反思,郑敏在《诗人与死》中写道:“你的随后的沉寂/你无声的极光/比我们更自由地嬉戏”,在诗人看来,死亡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是从苦难人间解脱的一条逃逸路线,这与里尔克的观点如出一辙,“里尔克在他的《杜依诺哀歌》之八中将死亡看成生命在完善自己的使命后重归宇宙这最广阔的空间,只在那时人才能结束他的狭隘,回归浩然的天宇。”[7]
死亡是生命列车的最后一站,人们对于死亡的感受大多是冰冷、残酷和恐惧的,郑敏却在里尔克的影响下,在追寻“生死”意义的过程中,超越了死亡,用理性和哲思阐释了死亡在某种程度上的崇高意义,虽然郑敏笔下的死亡可以看到某些现实的因子,但是透过现实的因子从深层次上看,仍然有里尔克式的专属烙印。
(二)雕塑式的静观:对物的皈依
如果说诗歌与哲学的完美融合体现了郑敏诗歌的思想高度,那么像雕塑一样对物的静观与皈依则代表了郑敏诗歌的独特的艺术追求与艺术风范,而这种具有雕塑感的定形之美也来自于里尔克。
里尔克的诗歌因对客观事物精细的观察和准确的描述而著名,他内心敏感,善于沉思,在诗歌中更多的转向对内心世界的追寻,通过对物的观察,把经验融入哲学,而后凝结成隽永的诗行。里尔克和法国雕塑家罗丹的结识使得他的诗风更趋沉稳,静止,具有一种雕塑美。里尔克认为,要想还原物的本来面目,让物以真实面目示人,就必须尊重物,让物成其为物,把自身化为存在物中的一份子,诗人要学会平息自己内心嘈杂欲望的喧闹,倾听事物自身的声音。[8]
静观的品格体现在里尔克的许多作品中,如《豹》、《罗马喷泉》、《旋转木马》等。诗人这种静观的品格,是自身与外物,与世界和谐相处,完美融合的一种奇妙关系,也是诗人将诗情外化为诗行的一种神奇手段。受里尔克的滋养,一种冷静客观的诗风在九叶诗人那里得到了集中体现,对这种“静观品格”熟练掌握并运用的主要是郑敏,她的一系列咏物诗《马》、《鹰》、《树》、《荷花》、《金黄的稻束》等都体现了这一方法,诗人就像一个雕塑家一样,用独到的眼光创造和打磨自己的作品,用心灵的静观创作,使她笔下的艺术品显现出深刻的内在涵义,表现出静中见动的雕像之美。郑敏富有哲思的性格,使她与里尔克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心灵的契合。郑敏在给诗友袁可嘉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希望能走入人物的世界,静观其所含的深意,里尔克的咏物诗对我很有吸引力,物的雕塑中静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但它的静中是包含着生命的动的,透视过它的静的外衣,找到它动的核心,就能理解客观世界的意义和隐藏在静中的动。”[9]
在郑敏前期的作品中,《金黄的稻束》就具有雕塑式的沉思与美感,金黄的稻束“站在割过的秋天的田里”,宛如一尊雕塑,这是物的静态,不过这些静止的稻束却“肩荷着那伟大的疲倦”,稻束在“低首沉思”的同时,诗人也在沉思,在静默中感受到母爱的深厚和博大,诗人把金黄的稻束与母亲和人类历史活动的意义联系起来,向读者传达了灵魂的声音——盛大的收获必须通过“肩荷伟大的疲倦”来获得。这整首诗从外在形式上看体现了一种“雕塑式”的静穆美,稻束是静默的,但是那种属于诗歌的灵动的生命气息却不可阻挡的从内向外散发出来,而这种艺术的气息正是通过诗人“雕塑式”地静观和思考获得的,郑敏把对具体物象的静观与哲学的思考结合在一起,使诗歌呈现出一种里尔克式的雕塑之美。再如郑敏的《马》,通过“静观”,写的虽然是一匹静止的马,但是诗人却在“静”中突显出“动”,它“原是一个奔驰的力的收敛”,“披着鬃发,踢起前蹄/奔腾向前像水的决堤”,诗人多次凸显马的力量,英雄的本色,“默默前行”的精神品质,其中涌动的原始生命力蕴藏在静止的马的形象中。这与里尔克《豹》中的诗句有异曲同工之处:“强忍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在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10]郑敏深谙里尔克的“静观”之法,用敏感细致的视角观察事物,再用富有哲思的头脑探求事物背后蕴含的深层意蕴,将鲜活的生命流动寓于雕塑般的静穆中。诗评家唐湜这样评价郑敏:“她仿佛是朵开放在暴风雨前历史性的宁静里的时间之花,时时在微笑里倾听那在她心头流过的思想的音乐,时时任自己的生命化入一幅画面,一个雕像,或一个意象……”[11]
四、结语
随着世界文化的不断发展,诗人们都有一个在中西文化之间选择的问题,诗人是这样,一个文学团体、诗歌流派也需要在博采众长中求得汇入世界诗歌潮流的门票。九叶诗派对于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和融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本文选取了九叶诗派中唯一健在的重要女诗人郑敏作为论述的主要对象,主要阐述了在里尔克的影响下,郑敏诗歌创作中所体现的诗与哲学的融合,一种向死而生的生命哲学,以及通过对“物”的“静观”而挖掘内在的深层意蕴。郑敏凭借自己的敏感和智慧把哲理和思辨融入所描写的形象之中,既有哲人式的思考,也包含雕塑式的静观,深谙里尔克诗学之道,这种诗歌创作实践对于当今的的新诗创作都不无启示作用。最后,对于异质文化的借鉴、吸收与化合,这是每一位诗人、每一个诗歌流派、每一个文学团体在新诗发展道路上必须肩负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