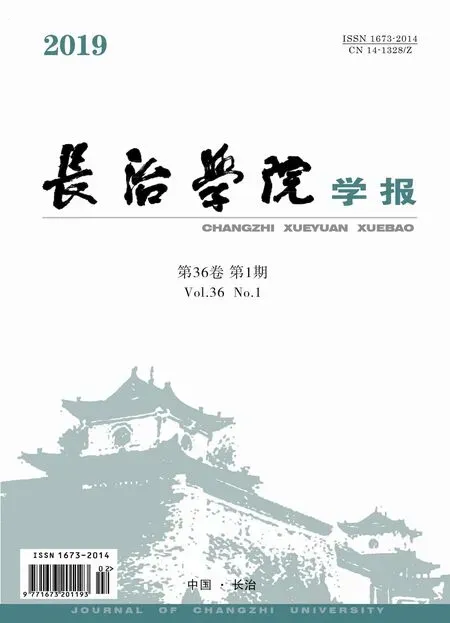传统悲剧的再生产:论陈凯歌电影《赵氏孤儿》的“求真性”
张林霞
(长治学院 中文系,山西 长治 046011)
一、引言
陈凯歌电影《赵氏孤儿》是继纪君祥元杂剧之后对古典悲剧《赵氏孤儿》一次大胆的改编。各界文艺学者对此次改编反应不一,驳斥者大多是因为其中对“忠义”的稀释。“忠义”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应该做出不同的解释,而且弘扬文化精髓和正能量更应该选择符合时代人们能够接受的方式,这比一味的弘扬和灌输所谓崇高的“忠义”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文艺创作的求真,求得不光是故事真实,人性真实,还有生活真实,艺术真实。
二、电影《赵氏孤儿》的故事真实
《赵氏孤儿》最初详见于《左传》,“宣公二年”载:晋灵公残暴不仁,赵盾屡次进谏,晋灵公多次加害他都没有成功,后来晋灵公被赵盾之弟赵穿诛杀。“成公八年”又载: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蓄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保天之禄。夫岂无辟王,赖前哲以免也。《周书》曰:“不敢侮鳏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因焉。
《史记·赵世家》在《左传》的基础上,结合民间传说对这一故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增加了屠岸贾,程婴,公孙杵臼三个核心人物,赵氏灭门的灾难源自于屠岸贾的奸诈狡猾,他嫉妒赵盾和赵氏家族在朝中的显赫地位,所以才造成了这一惨案的发生。从《左传》到《史记》,这场由昏君忠臣,家族内讧引起的斗争演变成了忠臣奸佞、正义邪恶的斗争,似乎这样的斗争才更符合中国大众的观赏心理。
元代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再一次进行了改编,把屠岸贾写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人,他不但奸邪、残暴而且篡夺皇权。而且将故事发生的大背景从晋景公时代转移到了晋灵公时期,并且把其中一个关键性情节,就是把他人之子换成了程婴自己的儿子,增加了程婴主动献子,然后揭发公孙,并且亲眼目睹自己的孩子被屠岸贾给摔死这一情节。二十年后,孩子长大成人后杀死屠岸贾。在这以后,程婴舍子,赵孤复仇成为《赵氏孤儿》的主干情节,为人流传。
陈凯歌的这次改编也是非常有力的,他继承了《赵氏孤儿》的主干情节,也含有十分浓郁的悲剧气氛,但是对于悲剧产生的原因,以及主要人物的行为进行了更为合理的处理,这是符合人物性格的,也是合乎伦理道德的,更是吻合二十一世纪时代大背景的。这样的改编使得“复仇”这一主题的意义重新得到思考,要不要复仇,应该怎样复仇,复仇究竟为了什么。并且,人物性格的多重性彰显也更显得真实,观众也正是在这样真实的文艺作品中受到了爱、“忠义”和饶恕的洗礼[1]。
三、电影体现出的人性、真相、事理真实
(一)电影中屠岸贾形象体现出的“反忠义”
电影中屠岸贾形象身上的“反忠义”相对容易,屠岸贾在《史记》中就是作为一个反面人物,他篡权谋逆,嫉妒忠臣,最后嫁祸他人,灭赵氏全族三百多条人命。
如果一定要用善恶之观来定义屠岸贾,那他一定是“恶”之代表。其身上的“反忠义”元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于国于君。身为臣子,屠岸贾为了一己之私不顾国家大义,私自屯兵,甚至为杀赵盾不惜弑君。弑君是他作为臣子的第一大“反忠义”之罪。二,于同僚。身为重臣,他与赵家本该同气连枝,共谋国家兴盛,当事事以国为重,赵家出征与自己出征并无本质区别。可屠岸贾心怀嫉妒,并由嫉生恨,最后弑君嫁祸赵家,将其满门抄斩。三,于百姓。身为朝廷命官,当为百姓安居而谋,但屠岸贾得知赵孤逃逸之后,下令抓捕全城婴儿,为了一个赵孤不惜赔上全城百姓家庭的希望。此为其“反忠义”之三。
“反忠义”元素体现出的人性、真相、事理真实。纵然“反忠义”不符合屠岸贾大将军的身份,但是这些“反忠义”的元素却符合事理之真、人性之真。从影片中所反映出的情节可以得知,屠岸贾和赵家一样,都是武将,他也曾为平定江山立下汗马功劳,但现在已无人记起,嫉妒之心并非空穴而来。而赵盾当着国君和将士的面逼屠岸贾吞下了一颗石头。种种情节铺垫为屠岸贾灭门赵家埋下伏笔,这体现的是真相、事理之真。由影片的开头我们可知,屠岸贾也是一位将军,但是赵盾赵朔却并未对其有尊敬之意,反而不屑鄙夷,这对于屠岸贾来说是不公正的。奸佞小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因为人性本身的污垢,这是不容易被改变的;一种是环境形势所逼迫,很显然,屠岸贾不能算是彻头彻尾的奸臣,如若早有谋逆之心,也不必等到赵家势大、自己儿子死去。尽管屠岸贾符合传统悲剧构造的“恶人”形象,但这部电影的改编却让屠岸贾的“恶”有了三分人之常情。
(二)电影中赵盾、赵朔形象体现出的“反忠义”
本次电影改编中,尽管尊重原著将赵盾赵朔作为忠臣的形象保留下来,但从电影情节来看,赵家形象的“反忠义”元素也依然存在,首先,赵盾是相国,他位高权重,面对昏庸的国君,赵盾电影开场第一句话是“大将要出征,你就没有一句正经话要嘱咐吗?”虽然国军昏庸,可是毕竟君臣有别,由赵盾的口气可知,他这样说话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了,国君心中就没有一丝不满?其实是有的,从电影后面的情节中可以看出,当赵盾的马车迟迟未能到达皇宫内时,晋灵公就已经表现出了不耐烦和反感,“不去!告诉赵盾,寡人等,多久都等”。其实。这个传话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韩厥,韩厥在剧中是屠岸贾的人,这句话很有可能是屠岸贾故意让韩厥这么说,然后激怒晋灵公,让他对赵家人不满,以便于他后来的嫁祸。但是,屠岸贾的利用并非是没有基础的,赵盾赵朔确实表现的过于傲慢,不把屠岸贾,甚至国君放在眼里,虽然这个国君是无能昏庸的,也很有可能真的是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但是,按照传统忠义的内涵来说,赵盾确实逾越了封建君臣该有的礼仪,呈现出“反忠义”的色彩。
总而言之,赵朔是个正面人物,是忠臣,可是电影中反映出他傲慢一面,对国君不满,对屠岸贾更是嗤之以鼻,甚至有些时候表现的过分,比如逼着屠岸贾吃下了那颗打伤马眼的石头。主持正义本来应该由君主来做,也是皇帝来做才显得合理,可是晋灵公做不了这样的主,他是个无道的君王,靠他来主持正义是基本不可能的,所以赵盾自己就站到了最前面,他的傲慢之所以让人感觉到不舒服只是因为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是为人臣,如果他是君主,那么观众也不会觉得他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还会为他的惩恶扬善而喝彩。由此可见,赵盾赵朔形象体现出来的种种不合乎为人臣子的行为只不过是寄他人无望而挺身而出该有的正常反应,也更合乎实际的反应,这样看来,这也是一种真实[2]。
(三)电影中“救孤三义士”形象体现出来的“反忠义”
“救孤三义士”是指程婴,韩厥,公孙杵臼。程婴和公孙杵臼都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增加的,程婴在以前的故事里是赵家的门客,韩厥是将军,公孙杵臼是大夫,这三个人被后世人称为“救孤三义士”。
程婴在剧中并不是赵家的门客,而是一个郎中,他是以一个民间郎中的身份进入到这场家族政坛的争斗中的,有人批评说程婴是以一个莫名其妙的身份陷入这场漩涡。是的,他的确是莫名其妙的进入了这场争斗,但是这也是为后面的情节做铺垫,程婴本来就同赵家只是很普通的关系,甚至谈不上什么关系,可是电影中却反映出程婴对庄姬夫人有种莫名的尊敬,我认为这种尊敬一是来自于庄姬的身份,二是来自赵家的地位,赵盾一家是忠是奸,像程婴这样的平头百姓其实是很清楚的。如果说程婴在人们的预想中是一个大义凛然,大义灭亲的形象的话,那么在这部电影中程婴的形象确实不够高大,他瞻前顾后,在整个过程中有许多次犹豫不决。第一,在庄姬夫人让他把赵孤装在药箱里带出去的时候他甚至假装忘记拿药箱,被庄姬叫住,不得已才拿着药箱走。第二,他在告诉屠岸贾孩子是给公孙杵臼大人送去时,以为公孙大人已经带着孩子出城了,所以才告诉屠岸贾。第三,他在剧中后半部分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要把这孩子养大,然后把他带到屠岸贾面前,告诉他,这孩子是谁,我是谁”。这说明,程婴已经不是那个只顾家国大义不顾小家安稳的高大形象,而是一直周旋在大和小之间,一直想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可是事与愿违,他还是阴错阳差的失去了自己的儿子。他这样的“忠义”是明显不同与春秋时期宣扬的那种大忠大义,可是这样的“忠义”却是那样的真实。
程婴是一个不够高大的形象,可是他真实,他的真实让人反而觉得他是那样的伟大,他没有什么大愿望大目标,报仇也想的仅仅是为自己的家人,为自己报仇,虽有利用赵孤之嫌,却是真实的存在在每个人的心里,因为这样的做法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从某种角度上说也是正确的,因为,毕竟赵孤本身就不是程婴什么人,可是却因为赵孤失去了几乎生命中的所有,难道赵孤就不欠他一个交代吗?这样的“反忠义”我认为恰似对个体生命价值最真实的呼唤。
韩厥在原先的故事情节中就是存在的,算是一个古老的人物,在《左传》中他向国君进言恢复了赵氏孤儿的权位。在纪君祥的元杂剧《赵氏孤儿》中他为了保护赵孤不得已而自杀。可是在陈凯歌导演的电影《赵氏孤儿》中韩厥的命运又不是前两者那么简单,首先韩厥最初并不是定位在赵盾这一边的,而是屠岸贾的下属,就是韩厥在赵盾的庆功宴上报告的假消息骗走了赵朔,也是他奉命去拿下庄姬,然后想办法杀掉她的孩子,可是他去了之后就发现庄姬已经生下了孩子,屠岸贾的意思是只杀婴儿,不杀庄姬,他在庄姬的恳求下说了一句话“夫人,我不杀这个孩子,我就会死”,是的,屠岸贾是不会放过他的,他没有那么光辉的选择自杀,他首先考虑的是自己,我想说这是合情合理的。这是韩厥身上体现出来的“反忠义”的第一点。第二点,与程婴类似,由于他的不忍,放过了杀害赵孤的机会,当然是被庄姬的自杀和理由被说服了。从严格意义上说,他这是对屠岸贾的不忠。第三点,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韩厥并没有被屠岸贾杀死,而是砍瞎了一只眼,从此他心里就带着恨,对屠岸贾的恨。但是被屠岸贾遗弃的韩厥不能去找任何人,只能来找程婴说说话,“如果知道那个孩子迟早都会死,还不如被我杀了”,他跟程婴密谋十五年的报仇计划其实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想报自己的仇,这样的“忠义”似乎大打折扣[3]。
公孙杵臼一直都是一个正面的人物,在影片里的公孙杵臼为了保住赵家最后一个独苗,他不惜与屠岸贾作对,最后还搭上自己性命,临了还说了最后一句话“对得起赵家了”,这样看来他身上似乎不存在什么“反忠义”元素。其实他身上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程婴的妻子告诉他自己现在抱着的这个孩子不是赵孤,而是自己的孩子,但他还是在屠岸贾面前拼死抵抗,使得屠岸贾很大程度上相信这个孩子一定就是赵孤,虽然后来屠岸贾说是程婴亲手把孩子交给他的时候他才相信那个孩子是赵孤,但是无疑公孙杵臼的死是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的。公孙杵臼明白,如果这个孩子真的是程婴的孩子而不是赵孤的话,那么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保住已经在屠岸贾手里的赵孤,尽管这样的方式对程婴的孩子来说是残忍的,因为无论如何,这个孩子都是保不住了,因为没能出城也是出乎公孙杵臼的预料的,但是公孙杵臼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把程婴的妻儿藏在了夹壁墙里,并且在屠岸贾来了之后还是殊死抵抗。我把这点归结为公孙杵臼形象体现出来的“反忠义”元素。
(四)电影中“赵孤”形象体现出的反忠义
上面说了许多的人物,他们的所有行为和命运都与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赵孤。赵孤的“反忠义”元素极其特殊:第一,屠岸贾是他最大的仇人,可是他的成长却很大一部分依赖于屠岸贾的照顾,比如屠岸贾教他的武功,可是最后,他却用屠岸贾教他的功夫去杀他的干爹。第二,程婴是赵孤的恩人,可是影片故事发展的过程中,赵孤多次亲近屠岸贾嫌弃程婴,并且最后赵孤的复仇是以程婴的死为代价的,如果程婴不是出于对赵孤的爱,程婴不会用自己的身体去挡刺向赵孤的剑。
赵孤身上体现出来的“反忠义”极其特殊,他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屠岸贾和程婴相处,所以这样的“反忠义”算不算“反忠义”还有待进一步商榷,可是就全剧“反忠义”氛围浓重的情况来说,赵孤摇摆不定的复仇情绪是起到很大作用的,因为屠岸贾带给他的是亲情,尽管没有血缘关系,可是屠岸贾在已经知道了事实之后还是救了赵孤,而赵孤最后还是杀了屠岸贾,这样的复仇让原本应该大快人心的恶有恶报,变得凄凉。屠岸贾对赵孤有养育之恩,赵孤将养父杀害,让整部电影的“反忠义”元素大增。最后的复仇带给观众的不是酣畅淋漓的快感,而是一种深深的思考,赵孤同时失去了两位“父亲”,这对于他来说是卧薪尝胆终报仇的解脱还是更大的悲哀和不幸。
五、结语
总体来讲,陈凯歌的这部电影更多地考虑了当下的人性因素,人性的求真也是文艺创作求真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改编造成经典的“打折”,让崇高的悲剧成为了小人物任意攀岩的场域。但是电影本身是一种现代前卫的呈现方式,接受它的人群也是多元的。即使存在这样的非议,《赵氏孤儿》也仍然是一部不错的电影,虽然“反忠义”元素频频出现,但是这些元素并不完全偏离“忠义”,并且也极大程度的表现出了人性的向善,只是采用了一种更为委婉的方式,但这就是人性,我们常常要求一部小说要表现圆形的人物形象,那种“高大忠”的英雄虽然存在却离我们遥远,就像雷锋在现代人心中的形象,几乎已经神化了。可是影片中的人物离我们很近,不得已而为之的程婴,似恶非恶的屠岸贾,饱含母爱的程妻,拥有自私心理的韩厥等等,他们不是活在历史上的,也不是活在荧幕上的,而是活在我们身边的,这种改编恰恰是解决传统经典如何契合当下市场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观《程婴救孤》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