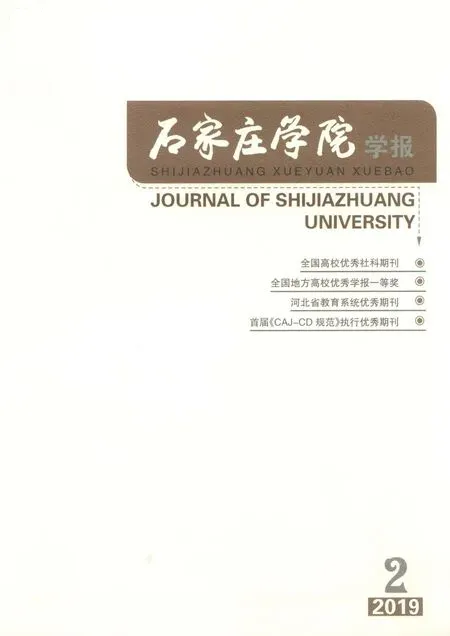唐代中后期河北豪族的个案研究
——以鹿泉“土门崔”为例
袁丙澍
(石家庄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5)
唐人李吉甫作《元和郡县图志》,内中恒州获鹿县(现为石家庄市鹿泉区)鹿泉条载:“鹿泉出井陉口南山下。皇唐贵族有土门崔家,为天下甲族,今土门诸崔是也,源出博陵安平。”[1]481几乎同一时期,李肇撰写的笔记《国史补》载:“四姓唯郑氏不离荥阳,有岗头卢、泽底李、土门崔,家为鼎甲。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钑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2]6此两部著作中提到的“土门崔家”“土门崔”此前并未见诸史籍。此后,历代文人著述论及此均援引这两种说法。有趣的是,唐代中后期号称“甲族”的“土门崔家”,此后却如隐形了一般,即使河北地方性史料中都很少看到他们的身影。
一、土门崔家与鹿泉的关系
李吉甫所作《元和郡县图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理总志。[3]1890李氏自言,作此书是为了“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1]序,可见其认识到了地理对政治治理、国家安全、民族繁荣昌盛的重要作用。李氏编撰此书,本着精益求精、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但纲目完善,内容丰富,而且在体例上还有所开创,“在府州下增加府境、州境、八到、贡赋等项内容……这个创新为后来的地理志、地理总志所效法”[3]1894。因此,《四库全书总目》将该书列为地理总志之首,并称赞说:“舆记图经……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今录以冠地理总志之首,著诸家祖述之所自焉。”[4]595由此可见,《元和郡县图志》学术价值极大。可是,该书中提到的之前从未见诸史籍的、其后地方性史料中也难觅踪影的“土门崔家”真的存在吗?
井陉与井陉关是两个既紧密关联又有所区别的地理名词,自然地理概念早于行政区划。严耕望先生的《唐代交通图考》载,井陉自古以来“为山西太原东通河北之最主要大道”[5]1441,史称“太行八陉之第五陉”。据严氏考证,“太行此陉道,东西长达百里,西口在广阳东八十里,东口在获鹿西南十里,皆两崖夹峙,中崩一线为通路,故皆有井陉口、土门口之名。唯中古史料所见,其置关乃在西口,不在东口耳”[5]1452。简言之,井陉是地图上的一条线,所谓“百里陉道”。而井陉关,则是地图上的点,是陉道进入山西、河北的两个出口,而这两个出口在史籍中都有明确的记载,也都有井陉关、井陉口、土门关、土门等多种称谓。以获鹿井陉关为例:
《新唐书·地理志》载:“镇州常山郡获鹿县,有故井陉关,一名土门关。”[6]1015
《困学纪闻》载:土门口在镇州获鹿县,即井陉关也。[7]1901
《通鉴地理通释》载:“井陉口,今名土门口,在获鹿县西南十里,有井陉关,一名土门,即太行八陉之第五陉也。”[8]69
因此,李吉甫所谓“鹿泉出井陉口南山下。皇唐贵族有土门崔家,为天下甲族,今土门诸崔是也,源出博陵安平”,从其所记地名来看,确指唐代获鹿地方无疑。
二、土门崔家与博陵崔氏的关系及迁徙至洛阳
唐代能够称得上“天下甲族”的崔氏,一为清河崔氏,一为博陵崔氏,官方史料中从未有“土门崔家”的记载。李吉甫出身赵郡李氏,世家子弟,两度拜相,名相李德裕之父,记述本朝掌故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吗?
(光绪)获鹿县志载:唐代崔行功,“本井陉人。祖谦之,仕北齐钜鹿太守,徙占鹿泉”①(清)俞锡纲修(光绪)《获鹿县志》卷十二,《人物志·流寓》,《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页下。崔行功条,(嘉靖)《获鹿县志》、(乾隆元年)《获鹿县志》均未载。(乾隆四十六年)《获鹿县志》及(光绪)《获鹿县志》有载。基本内容源自《新唐书·崔行功列传》。。该条只说明崔行功为井陉人,自祖父崔谦之迁徙到鹿泉。
(光绪)续修井陉县志载:崔行功,“恒州井陉人。北齐钜鹿太守伯让曾孙,博陵徙家”②(清)钟文英纂修(光绪)《续修井陉县志》卷二十一,《名臣》,《中国地方志集成》,第296页上。崔行功条,(雍正)《井陉县志》未载。。该条的信息有一些不同,崔行功为井陉人,曾祖父为崔伯让,自博陵迁移而来。
《新唐书·崔行功列传》又有一些新的内容出现,“恒州井陉人。祖谦之,仕北齐,终钜鹿太守,徙占鹿泉。……(崔行功)孙铣,尚安定公主,为太府卿。……行功兄子玄暐别有传”[6]5734-5735。
以上三条资料都说明,崔行功家族源自博陵崔氏,自其祖父起迁居鹿泉。崔氏出自姜姓,食采于崔,遂为崔氏,最早居住于济南东朝阳县西北。或因灾祸,或因仕业,流散四方,历时既久,成员迁移新贯,本就是自然而然的状况③详见《新唐书》第9册,《宰相世系表二下·崔氏》,中华书局1975版,第2 729-2 730页。,但是,虽数代居于新贯,无论从其自身的心理归属,抑或是外人对其的仰慕鼓吹,时人并不十分重视新贯,多称其望,这也就是所谓“郡望、籍贯两分”的现象。并且,一些大士族还会形成新的郡望,例如,郑州崔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之分即是如此。新郡望的获得,没有数代的经营和强大的势力则不足以形成,李吉甫所称“土门崔家”虽处于唐代中后期,亦可见其影响之大。
前辈学者在研究中古时代豪门士族的过程中注意到了这种迁移现象,将它作为研究切入的视角,并提示了一些重要的方法。例如,陈寅恪先生认为:“吾国中古士人,其祖坟住宅及田产皆有连带关系。观李吉甫,即后来代表山东士族之李党党魁李德裕之父所撰元和郡县图志,详载其祖先之坟墓住宅所在,是其例证。”[9]2对此,毛汉光先生总结指出:“关于田产之记载,后市有鱼鳞图册,唐代边陲地区因均田之法而有片断资料,中原一带之私产地则已无记载留下。坟茔之所在地,成为今日研究某家族重心的重要标杆。”④毛汉光《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2期第3分册,第429页。本文后收入毛汉光著《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集团,2002年版,第224页。基于此,自博陵徙占鹿泉的“土门崔家”,其主要成员较集中的归葬地,就成为“土门崔家”是否存在的主要指标和论证方向。
根据新表,《旧唐书》《新唐书》所记载的迁徙鹿泉的博陵崔氏的情况稍有出入,需预先予以说明:《旧唐书·崔行功列传》载,“北齐钜鹿太守伯让曾孙也,自博陵徙家焉”[10]4996。新表载,崔行功曾祖为伯谦,曾叔祖为仲让[6]2779,2785。两《唐书》显然把二者混为一谈,误记作伯让。《新唐书·崔行功列传》载:“祖谦之,仕北齐,终钜鹿太守,徙占鹿泉。”[6]5734新表载,崔行功祖父为崔渊,字孝源,青、冀二州司马[6]2779,参考《北齐书·崔伯谦列传》,这显然又将其曾祖与祖父混为一谈。比较三份史料,可以确定博陵崔氏大房自崔伯谦始将家族迁徙至鹿泉。
新表记载了博陵崔氏大房伯谦支情况,见图1。在新表中,自崔伯谦迁徙至鹿泉后,能够获得籍贯、归葬地的成员情况如下。
崔行功:“恒州井陉人,北齐钜鹿太守伯让曾孙也,自博陵徙家焉。”⑤(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第15册,《崔行功列传》,中华书局1975版,第4 996页。《新唐书》与此略同,见前揭文。
崔玄暐:“博陵安平人,本名曅……少以学行称,叔父秘书少监行功器之。……玄暐三世不异居,家人怡怡如也。贫寓郊墅,群从皆自远会食,无他爨,与升尤友爱。”[6]4316-4317
又,“公讳曅,字玄暐,博陵平安人。……曾祖孝源,北齐御史、行台郎中,青、冀二州司马……祖父君维,隋宁州罗川县令……父行谨,皇朝华州郑县主簿、雍州澧泉县主簿、泾阳县丞、宁州丰义县令……(玄暐)以神龙中,薨于白州之官舍,春秋六十有八。以景龙元年南还,权殡于汝州界。……夫人范阳卢氏,皇朝陆浑县丞,赠易州长史元礼之第二女也。……以开元三年岁次乙卯十月己酉朔合袝于恒州鹿泉之旧茔礼也”[11]1168-1170。

图1 博陵崔氏大房伯谦支情况
崔升:“(崔升夫人郑氏)春秋卅有七,以长安三年八月廿地日终于京兆府永乐里之私地。以开元五年十月廿五日□窆于恒州之旧茔礼也。”[12]13288-13289该墓志铭经沈涛考证为崔升夫人墓志铭。开元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立,嘉庆年间仍在获鹿县北新城村三官庙内。以现在的位置关系看来,沈氏所言北新城村距土门村直线距离不过七八公里。另,《大唐特进中书令博陵郡王赠幽州刺史崔公墓志铭并序》中,崔玄暐之弟为崔昪,而两《唐书》均记作崔升,或可证其讹误,此处暂从《唐书》所记。
崔涣:“皇唐相国博陵公姓崔氏,讳涣字某。……历官二十三,享年六十二。以大历三年冬十有二月二日薨于道州刺史之寝。明年归袝于洛阳北邙山。”[13]8192-8195崔纵:“崔氏长女名某,先笄之某年,不幸遘疠。未几,丁烈考太常卿赠吏部尚书常山公难,至哀乘之,共迫正气,以贞元七年秋八月己酉夭於东郡。冬十月乙巳,兄元方哀奉尚书从先相国於北邙山,以长女袝于尚书之侧。”[13]8217
综上,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及推测:
首先,伯谦支迁徙至鹿泉后,将鹿泉土门作为家族发展的新据点,家庭主要成员都葬于此,崔玄暐夫妇“合袝于恒州鹿泉之旧茔”。既然是“鹿泉旧茔”,说明鹿泉土门有可能是伯谦支迁徙以来的葬地。另外,其弟媳郑夫人的墓志铭亦有“窆于恒州之旧茔”之说,更增加了上述的可能性。另外,其叔父崔行功虽未有墓志资料,但从其列传“恒州井陉人”看来,也不能排除其葬于鹿泉土门周边的可能性。
其次,“土门崔家”自崔玄暐孙崔涣开始移葬河南洛阳。其墓志铭载:“奉二夫人合於此室(指洛阳北邙山墓地)。既定,而常山祔焉”,可见其葬在洛阳,其子常山公崔纵也与父亲崔涣一同葬在了洛阳。关于崔涣葬于洛阳的原因,说的很含糊,“推周公合袝之事,凡龟从筮逆者数”,且有“先志未从,不敢以见先祖”之说,不知确指何事,但颇耐人寻味。崔涣子崔纵殁,“从先相国於北邙山”。
总之,博陵崔氏大房崔伯谦支发生过两次家族迁移,其一自安平迁至鹿泉土门,其二,自鹿泉土门迁至洛阳,其根据就是坟茔所在地的变迁。伯谦支迁至鹿泉土门之后形成了新的地望,称“土门崔家”,这与其子弟的强势表现密切相关,出任宰相的即有崔玄暐、崔损、崔涣等,其他如崔行功、崔升、崔纵等文名、官声亦起到强化、弘扬的重要作用。
三、崔涣葬洛阳原因考
从崔涣的墓志铭可以得知其确实葬于洛阳北邙山而非土门旧茔,虽说土门并非博陵崔氏大房的郡望所在地,但自崔玄暐之曾祖父崔渊开始,家庭主要成员都葬在土门,并形成了新的地望。
崔涣葬洛阳的原因既有大势所趋,也有家庭的原因。
首先,中央集权世家地位下降。在唐以前,主要以九品中正制作为选拔官员的途径,而这一制度给予了世家大族选拔人才的权力,并逐渐使得官员出自世家大族,并且形成垄断局面。而唐代以科举制度作为吸收人才、巩固其官僚体系的制度,加强中央集权。与九品中正制不同的是,科举制不再以地方世家的举荐作为唯一标准,而是以考试的形式引进人才。这使得以门第为主要条件的世家地位受到威胁,打破了长期由世家占据朝廷高位、垄断选举权力的局面。把引进人才、选拔官员的权力收归中央,加强中央集权,从而削弱了地方士族的权力。另一方面,使得大量的中等阶级的家族得以向上发展,从而进一步削弱士族的势力。虽然科举是面向全体民众,但对于寒素来说,其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少之又少。对于中等阶级来说,其拥有基本的经济基础支撑日常的生活,并有机会获得良好的教育,他们缺少的是一个向上发展的机会。而科举打破了大族垄断的局面,使得一些相对小的家族进一步向上发展,从而削弱了大士族的势力。
731-755年间,士族人数占据了统治人员的大部分。而到805-826年这一期间,士族所占比例大幅下降到41.2%。中等阶级所占比率有所上升。可见,在唐代这一段时期内,士族地位的下降是明显的。世家大族的权力受到削弱,而中央集权的加强,导致他们不得不更加依靠中央来获得更多的利益,以维持家族的发展。

表1 唐代统治阶级社会成分统计表[14]45
唐代还有其朝代的特殊性,由于常年没有战事的困扰,士族地位的巩固由最初的通过武将谋取军功逐渐转向了文官参赞谋略。仕途的出路就是在朝廷为官。再者,世家大族有充裕的资源和家学渊源来培养其家族成员通过考核,世家大族可以付出较小的努力而通过参加科举获取功名。最后,迁徙到两京附近有利于谋取功名。“唐代科举的试卷并不弥封,应考举子先得造出有才华的声誉在容易入选,居住两京附近者有种种便利,同、华亦佳。”[14]224此外,“自北魏定都洛阳,以迄隋唐之发展,洛阳已成为当时人文荟萃之所”[14]330。在洛阳地区更有利于科举。因此,在地方势力逐渐衰弱的时候,世家大族迁徙到两京附近是首选的利益需要。
世家大族逐渐通过科举进入中央而减少其在地方的影响力,慢慢官僚化。地方影响力的下降又促使世家更加依附中央,形成一个循环的链条,而使得越来越多的士族逐渐剥离地方,进一步中央化。
对于崔氏大房来说,崔涣的被贬使得家族的发展受到一定的打压。自崔玄暐开始,崔氏走上仕途,加之崔涣在朝中为官也颇有地位,使得其家族脱离地方、依附中央来获得更多的机会。再者,河北地区又在胡族的入侵下难求抗敌的办法,紧跟中央、迁徙到中央地区是出于他们自身家族利益的需求。
其次,地方权力的衰落。在安史之乱后,“河北士族由胡族侵入,失其累世之根据地”[9]8。“今忽遇塞外善于骑射之胡族……卒以力量不能敌抗之故,唯有捨弃乡邑,出走他地之一途。”[9]5河北地区受到胡族的入侵,河北士族不得不放弃其居住已久的地方,出走他地。加之“在唐后期河北藩镇中,统治支柱和社会基础是以牙兵为核心的职业军人集团”[15],士族在地方的利益受到这些军人集团崛起影响。虽然对于地方士族,在早期也是“以雄武为其势力之基础”,但是随着士族融入唐统治阶级,进入中央,由崇尚武力到进入官场为官,其逐渐丧失了在地方的社会声望和影响力,并被这些职业军人掌握了藩镇的统治权。因此,大量世家选择迁徙到中央不单单是一种风气,或者是迫于胡族的无奈之举,更是以其家族利益、发展为出发点。他们放弃在地方逐渐削弱的势力,而转向中央获得更多的机会,维系家族的发展。博陵崔氏大房原位于河北鹿泉土门,这一区域受到胡族的入侵。安史之乱后,中央为了平定战乱,增添了许多节度使,更加削弱了地方士族的地位,使得原居住地已不适宜他们继续居住。地方权力的衰落使得博陵崔氏大房选择依附于中央,从而获得更多的家族利益。
第三,北方豪门士族迁徙至两京一代成为大趋势。唐朝初期,地方世家进入统治阶级,常常搬迁到中央地区。一部分家族仍有家族成员留守。但随着时间推移,家族之间联系减少,老一辈成员逐渐离去。家族间联系的纽带变得越来越松散,迁徙到中央地区的成员便逐渐脱离郡望所在地,另一部分举家搬入的更是与郡望联系减少。因此逐渐出现了郡望与士族的居住地、籍贯并不相同,呈现出分离的现象。郡望仅仅作为世家的一个标志、名号。
在唐代,大规模的士族迁徙已然成为一个大的趋势。下面为著名世系在唐时期的迁徙“新贯”[14]332。
清河崔氏:七个著房支都在河南府。
范阳卢氏:八个著房支,河南府四个,相州一个,河中府一个。
陇西李氏:六个著房支,河南府五个,郑州一个。
赵郡李氏:九个著房支,河南府五个,京兆府两个,郑州一个,汝州一个。
太原王氏:七个著房支,河南府四个,京兆府两个,河中府一个。
琅琊王氏:七个著房支,河南府五个,京兆府两个。
彭城刘氏:著房彭城丛亭里刘氏在河南府。
渤海高氏:两个著房,河南府一个,京兆府一个。
河东薛氏:十二个著房支,河南府五个,京兆府四个,原籍两个,河中府一个。
兰陵萧氏:六个著房支,河南府三个,京兆府三个。
河东薛氏:五个著房支,京兆府三个,河南府一个,河中府一个。
河东柳氏:五个著房支,京兆府三个,河南府一个,原籍一个。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得出,在唐代,大都数世家支系选择迁徙到中央地区,尤以河北士族向两京一带迁徙为代表。其次,虽然各个士族迁徙到河南府或中央区域的时间不相同,但是绝大多数著房著支是集中在唐安史之乱(755-763年)之前。[14]332这样的迁徙高潮使得越来越多的大士族愿意跟随主流迁徙到中央地区及洛阳。“安史之乱或对未完成新贯的房支有促进作用。”[14]332崔涣卒于769年,在大量士族迁徙的大背景下,崔涣的儿子崔纵选择将父亲葬在洛阳而非旧茔,也是顺应了当时大背景的选择。
第四,土门崔家对于崔涣葬洛阳的纠结。除了大势所趋,土门崔家还有特殊的家庭背景。崔家内部对崔涣葬于洛阳还是葬于鹿泉,有过争议。虽然现有资料尚不能准确复原这一事件,但崔涣墓志所载其葬于洛阳之事,欲语还休,让人不禁充满好奇和揣测。
“(崔涣)薨于道州刺史之寝。明年,归袝于洛阳北邙山。……推周公合祔之事,凡龟从筮逆者数。”[13]8192死葬之事对于传承有序的豪门世家来说,除非出现重大变故,一切皆依惯例和程序即可。崔涣两位夫人与之合葬洛阳的决定需要“占卜”,例如,决定墓地位置、丧事行程、时刻等,还算不得特别。蹊跷的是,文中提及反复卜算的结果均是“逆”,并且强调是“地清天和……四者皆违”的不利结果,这就显得非常不合情理。中国人视死葬之事为大事,即使过程偶有波折,都通常会有应对、变通的手段。且中国人对待“占卜”的态度本身就值得玩味,何况世家大族子弟?卜不好就再卜,总有顺应人意的结果。从“凡龟从筮逆者数”也可以看出崔家的态度。真的相信占卜一次就够了,何必“数次”呢?这种反复占卜的行为本身就值得推敲,更何况是公之于众?
一般情况下,葬礼的仪式和过程,关乎家族及子孙后代的利益,多体现的是生者的意志而非逝者。因此,平时长久的积怨会爆发出来,发生的波折也就多是争吵和纠纷等上不得台面的事情,必须在家族内部处理,对外秘而不宣。而崔涣墓志却将“合祔”不利的事情示人,并且感慨道:“天不以西汉韦平之美惠于吾君,使常山下世,永怀不集,故有没代之庸者遗令焉。”[13]8192“韦平之美”是借用了一个典故,西汉韦贤、韦玄成与平当、平晏两对父子相继为宰相,后世以为美事。表面看起来,将崔涣、崔纵父子与之相提并论是溢美之词。崔纵虽然没有做过宰相,但官亦至太常寺卿,故有“亚相”之称。墓志借用“韦平之美”与崔涣、崔纵父子并列,说明“合祔”之事对于崔氏家族之影响“重大”。所以崔纵的决定才称得上“没代之庸者遗令”。
崔涣去世后,长子崔纵成为“土门崔家”的掌门人。崔纵作出“合祔”于洛阳的决定,“贞元元年秋九月,季子京兆府三原丞扬、孙前渭南尉元方,哀奉常山之志,逮乎在殡。是月壬午,启博陵公之隧,明月丁酉,以华阴郡太夫人洎继夫人陇西李氏之丧归,礼也”[13]8192。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时间。崔涣,“大历三年冬十有二月二日薨于道州剌史之寝。明年,归祔于洛阳北邙山”[13]8192,也就是说公元769年葬于洛阳北邙山。到贞元元年(785年),崔纵决定将崔涣与早已去世的二位夫人合葬于北邙山,两者间相差有16年之久。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子女将去世的父母早日合葬,是检验儿女孝行非常重要的考量指标之一。没有特殊的原因,而崔纵合葬父母的间隔时间确实有点长,超乎情理。我们是否可以大胆推测,崔家对于崔涣葬于何处有重大分歧?这也侧面说明了崔纵作出“没代之庸者遗令”的困难。
崔涣之前,包括先他去世的前两位夫人郑氏和李氏,按照惯例都是葬在鹿泉旧茔,也是“土门崔”的家法。崔纵无论是为人子,还是作为“土门崔”的大家长,早日合葬父母都是其分内之事,操作起来于情于理本不应该有什么困难。时间延宕的最可能的原因,就是将崔涣葬在哪里,家庭内部发生了分歧。洛阳北邙山,还是鹿泉旧茔?所以,才有崔纵决定后,二位夫人的迁葬之说。
延宕16年,最终尘埃落定,可见作出决定之难。崔家迁葬洛阳的难度到底在哪里?河北世家大族的迁徙,不是一个单纯的死葬问题。它既涉及向中央或地方势力靠拢的问题,也涉及家学门风的保持问题[15],这些都是决定一个家族兴衰的关键,自然不能轻忽,选择起来也尤为艰难和纠结。崔涣、崔纵两父子的行事做派也可以作为当时河北世族家风的典型。崔涣墓志载:“公三娶……夫人磁州刺史曾之孙,颍州太守长裕之女,年若干。捐公之馆,子曰纵,实常山公。继夫人舒州刺史绍之孙,左羽林录事参军晃之女”[13]8192。夫人郑氏,二夫人李氏,三夫人郑氏,依旧保持着高门通婚的传统。崔纵,以孝著称。“公之清德重望,洎天官亚相之位,事后夫人荣阳郑氏恭。公之理命,以无违为大,而黾俛拘忌,出入衔恤。”[13]8192所谓后夫人荥阳郑氏,即崔涣的三夫人。这位郑氏却把崔纵树立成了孝子的典范,据史籍载:“涣有嬖妾,纵以母侍之。妾刚酷,虽纵显官而数笞诟,然率妻子候颜色,承养不懈,时以为难。”①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14册,《崔玄暐列传》,中华书局1975版,第4 320页。《册府元龟》《弘简录》等亦有载。所谓“承养不懈”,可以推知,父亲去世后,崔纵对郑氏行孝依然如故,为时人所称道。世家大族对门风传统保持所作出的努力,由此亦可见一斑。对于有些家族而言,“中央化”固然是如毛汉光先生所言河北豪族“冀图跻身新贵”的结果,而对于另外一些家族而言,跻身藩镇势力高位,而“背弃其传统的家学门风”[15]的压力,也不容忽视,不可一概而论。崔纵正是在这种重压力之下,纠结了16年之久,而最终决定迁徙至洛阳。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冯金忠在《唐后期河北藩镇统治下的世家大族》一文中的结论:在河北藩镇的统治下,士家大族在河北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一过程延续的时间非常长。安史之乱后,在籍士族的疏离倾向进一步加重。这也同样可以解释崔涣墓志中“占卜”不利依然迁徙,且发出“痛先人存殁不伸之志”感慨的原因。
总之,博陵崔氏大房伯谦支,至安史之乱后,依然将家族的重心放在鹿泉土门地方。贞元初,鹿泉土门崔家正式决定迁徙至洛阳,以保其学业因承、优美门风。土门崔家的艰难选择,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唐中后期河北士家大族的情况。但是无论是依附地方,还是归附中央,既是家族命运的抉择,也改变了其后中国的政治格局。
——谈大型古装淮剧《马前泼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