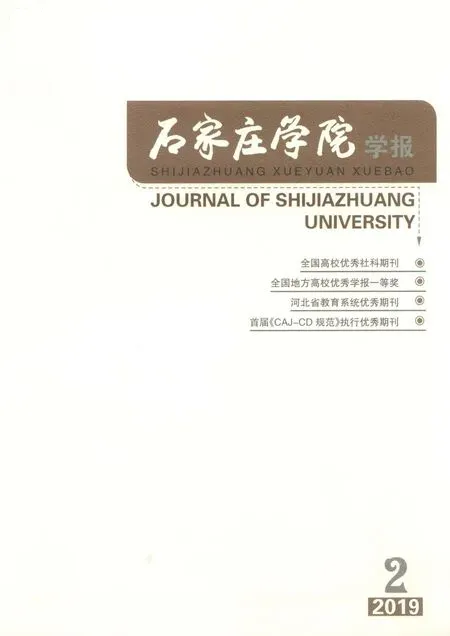刘贺“乘七乘传诣长安邸”考议
曾 磊
(1.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2.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732)
《汉书·武五子传》载,昭帝崩后,大将军霍光以太后名义征昌邑王刘贺赴长安典丧:
玺书曰:“制诏昌邑王:使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征王,乘七乘传诣长安邸。”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①“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资治通鉴》卷二四“汉昭帝元平元年”作:“及征书至,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79页。)王子今指出,这可以看出“玺书”传达到昌邑后刘贺反应的紧迫。参见王子今《刘贺昌邑—长安行程考》,载《南都学坛》2018年第1期。。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郎中令龚遂谏王,令还郎谒者五十余人。[1]卷六三
《汉旧仪》卷上:“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行千里为程。”[2]63太后玺书若是以“驿骑”的方式传送至昌邑国,其速度可以达到惊人的一昼夜一千汉里。不过,负责迎立刘贺的“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乘“驰传”赶赴昌邑国的可能更大。刘贺车驾自日中至晡时行“百三十五里”,以当时条件来看已属高速②关于刘贺车驾速度的推算,参见王子今《刘贺昌邑——长安行程考》,载《南都学坛》2018年1期。。而侍从者的马匹脚力不足,不能跟上刘贺车驾的速度,以致出现“马死相望于道”的情形。刘贺所乘之“七乘传”究竟是七匹马拉之传车,还是七辆传车呢?
一
从马车的驾驶技术来看,马匹越多,对马匹的配合程度和驭者的技术要求就越高。如果马匹和驭者未经良好训练和磨合,马多反而可能更难以驾驭,车速亦未必最快。以当时的马匹系驾技术来看,无论是单辕车还是双辕车,七马驾车均难以想象。表示驾车之马的古文字中,“骖”“驷”“馬六”可分别表示三马驾车、四马驾车和六马驾车,未见有“马+七”的组合。根据学者研究,车马配驾有一马、二马、四马、六马、八马之数,三马、五马驾车虽然少见,但仍有文献学和图像学证据,唯七马驾车没有相关资料支持。③参见王振铎遗著,李强整理、补著《东汉车制复原研究》,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6-88页;郭宝钧《殷周车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萧圣中《曾侯乙墓竹简释文补正暨车马制度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5-230页;罗小华《战国简册所见车马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225-245页;练春海《汉代车马形像研究——以御礼为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8-255页。
自昭帝崩至昌邑王贺即位,一说为43日,一说为37日。④参见廖伯源《制度与政治——政治制度与西汉后期之政局变化》,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66页;王子今《刘贺昌邑——长安行程考》,载《南都学坛》2018年1期。因霍光与群臣意见不合,确立王朝继承人的问题,已拖延月余。虽然刘贺接到消息后即刻启程,但霍光等迎立刘贺,首先要保障的是未来天子的人身安全,在此基础上再兼顾行车速度。即使当时存在七马驾车的技术,其危险系数也要比四马驾车高得多。从路上刘贺还有时间“求长鸣鸡,道买积竹杖”[1]卷六三的行为来看,赶赴长安的日程似乎并不十分紧迫。可能在“龚遂谏王”后,刘贺车驾降低了速度。况且,对刘贺来说,当时朝廷的情况并不明晰,贸然赶赴长安其实也是一种冒险。而按辔徐行,亦可给人以稳重低调的印象。
二
与此类似的还有代王刘恒自代国“乘六乘传”赴长安即位的故事。《史记·吕太后本纪》说:
(诸大臣)乃相与共阴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辞谢。再反,然后乘六乘传。裴骃《集解》引张晏曰:
备汉朝有变,欲驰还也。或曰传车六乘。①《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11页;又见2014年修订本,第520页。张晏提出了两种说法,“备汉朝有变,欲驰还也”,显然是认为六马驾车车速更快。“传车六乘”,则认为是六辆马车。裴骃《集解》对两种观点并未轻易否定,而是两存之。《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所载袁盎之语说:
夫诸吕用事,大臣专制,然陛下从代乘六乘传驰不测之渊,虽贲育之勇不及陛下。②《史记》卷一〇一《袁盎晁错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 739页;又见2014年修订本,第3 317页。
“乘六乘传驰不测之渊”前的主语为“陛下”,“再反,然后乘六乘传”的主语承前省略,当为“代王”,与“陛下”所指一致,皆为刘恒。但如果代王刘恒一人乘“传车六乘”,未免浪费。袁盎此语似乎也支持“六乘传”为六马驾车的观点。
《史记·孝文本纪》的记载则与《吕太后本纪》和《袁盎晁错列传》有所不同:
(代王)乃命宋昌参乘,张武等六人乘六乘传诣长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③《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2014年修订本,第526页。“乘六乘传诣长安”,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作“乘传诣长安”(第414页)。2014年修订本校勘记说:“‘六乘’二字原无,据东北本补。按:本书卷九《吕太后本纪》、卷一〇一《袁盎晁错列传》,《汉书》卷四《文帝纪》、卷四九《爰盎传》皆云代王‘乘六乘传’。”王叔岷《史记斠证》卷一〇:“案古钞本乘上有‘乘六’二字,《汉书》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81页。)
《汉书·文帝纪》的文字与此相同。从汉代传车规格来看,“六人乘六乘传”不太可能为六人乘坐一辆传车(详下文),暗示此“六乘传”非六匹马拉之车,当是“六人分乘六辆传车”之意,所以颜师古所引张晏的观点只取“传车六乘”一种,隐去了“备汉朝有变,欲驰还”之说。由此看来,《吕太后本纪》和《袁盎晁错列传》中的“代王”与“陛下”所指,不仅包括刘恒,还应包括与其一同奔赴长安的宋昌、张武等人。
吴楚七国之乱时周亚夫亦曾“乘六乘传”。《史记·吴王濞列传》载:
条侯将乘六乘传,会兵荥阳。④《史记》卷一〇六《吴王濞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 831页;又见2014年修订本,第3 426页。
《汉书·吴王刘濞传》的文字与此相同。此事发生的背景,是景帝遣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⑤《史记》卷一〇六《吴王濞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 830页;又见2014年修订本,第3 425页。。不过,“条侯将乘六乘传”之“将”,是“将要”之意,不能理解为“将领”。此事《史记·游侠列传》就作:“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车将至河南。”⑥《史记》卷一二四《游侠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 184页;又见2014年修订本,第3 869页。《汉书·游侠传》作:“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东,将至河南。”[1]卷九一《资治通鉴》的记载为:
亚夫乘六乘传,将会兵荥阳。
“条侯将乘六乘传”与“陛下从代乘六乘传”文意类似,并非指周亚夫/刘恒一人乘六辆传车,而当指周亚夫/刘恒及其部属分乘六辆传车之意。胡三省注:“张晏曰:传车六乘也。”直接将张晏对代王乘六乘传的解释移植于此,看来也认为二者语义一致。胡三省又说:“余据汉有乘传、驰传;文帝之自代入立也,张武等乘六乘传,今亚夫乘六乘传,六乘传之见于史者二,盖又与乘传不同也。”[3]卷一六认为“乘传”与“六乘传”有所不同。这一理解有误,“六乘传”应是六辆“乘传”之意,二者并无根本不同。
乘传是传车的一种规格。《汉书·高帝纪下》:“横惧,乘传诣洛阳。”颜师古注引如淳曰:
律,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轺传。急者乘一乘传。[1]卷一下
类似记载又见《史记·孝文本纪》:“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索隐》引如淳云:
律,四马高足为传置,四马中足为驰置,下足为乘置,一马二马为轺置,如置急者乘一马曰乘也。⑦《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22-423页;又见2014年修订本,第535-536页。
两条引文有所不同,“置传”“驰传”“乘传”“轺传”,司马贞《索隐》引如淳注写作“传置”“驰置”“乘置”“轺置”。对此,富谷至已有详细辨析,认为律文当以《汉书·高帝纪下》如淳注为准,其论可从。[4]225-229此条律文规定了汉代传车的规格,可能属汉代的《厩律》。《汉书·平帝纪》如淳注和肩水金关汉简73EJT23:623还记录了与此相关的另一条《厩律》:
诸当乘传及发驾置传者,皆持尺五寸木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传参封之。有期会累封两端,端各两封。乘置、驰传五封之。轺传两马再封之,一马一封。诸乘轺传者,乘一封,及以律令乘传起□……①《汉书》卷一二《平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360页;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肩水金关汉简(贰)》,中西书局2012年版,彩色图版见上册第191页,红外线图版见中册第191页,释文见下册第100页。此条律文的复原参见曾磊《肩水金关汉简中的〈厩律〉遗文》,待刊。
此条《厩律》是对使用传车的凭证——传信进行封印的具体规定。根据两条律文可列表如下:

表1 汉代传车及传信规格
“乘传”即“四马下足”规格的传车,需加盖三封或四封印章。敦煌悬泉汉简中有一类“传信”简,其中亦涉及传车规格,可与以上两条律文对读。如:
元康元年十月乙巳前将军臣增大仆臣延年承
所长吓了一跳。这时才闻到了牛爹身上的汽油味。嘿嘿嘿牛爹,至于吗至于吗?!至于自焚嘛。有事好商量。什么事都好商量。
制 诏侍御史曰将田车师军候强将士诣田所
为驾二封轺传载从者一人 传第二百卅
御史大夫吉下扶风厩承
书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
令IIT0214③:45②张俊民《敦煌悬泉置出土文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446页。“当舍传舍”,张俊民释文作“当居传舍”,疑误。又如:
鸿嘉三年正月壬辰遣守属田忠送
自来鄯善王副使姑彘山王副使鸟不腞奉献诣
行在所为驾一乘传
敦煌长史充国行太守事丞晏谓敦煌
为驾当舍传舍郡邸如律令
六月辛酉西 II0214②:78③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页。此简现藏甘肃省博物馆。简文格式据原简照录。悬泉汉简中的传车规格有“为驾一封轺传”“为驾二封轺传”“为驾一乘传”“为驾二乘传”“为驾四乘传”“为驾一乘轺传”等格式,以前两种最多。其制度与上引《厩律》基本相合。因轺传分一马驾车和二马驾车两个规格,因此在传信文书中要明确到底是“一封轺传”还是“二封轺传”。而乘传的传信虽然有三封和四封之别,但日常使用应以三封传信为主,且只有“四马下足”一种规格,因此只需注明所用传车的数量即可。如“为驾一乘传”,“一”是数词,“乘传”是传车规格。简文中的“为驾二乘传”“为驾四乘传”亦可为证。④《汉书·武帝纪》:“初置刺史部十三州。”颜师古注:“《汉旧仪》云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绶,有常治所。常以秋分行部,御史为驾四封乘传。到所部,郡国各遣一吏迎之界上,所察六条。”(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7页。)《汉旧仪》中出现了“为驾四封乘传”的说法。从《厩律》原文看,乘传应当“参封之”,只有有“期会”时才“累封两端,端各两封”,这本就属于特例,说明乘传还是应以三封为常置。若用四封乘传,当会在传信中另外注明使用传车的数量。刺史以秋分行部用“四封乘传”可能是武帝置十三州刺史后另设的新规定。《后汉书·贾琮传》说贾琮为冀州刺史,“旧典,传车骖驾,垂赤帷裳,迎于州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 112页。)类似记载又见《续汉书·舆服志上》“皁盖车条”刘昭注补:“旧典,传车骖驾,乘赤帷裳”(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 648页);《三国志·蜀书·刘焉传》说刘焉“领益州牧”,裴松之注引《续汉书》:“旧典:传车参驾,施赤为帷裳。”(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66页。)说明刺史所乘传车规格和等级可能有详细规定,“传车骖驾”的形式也与“四封乘传”不同,可见其制度又有所变化。
因此“乘六乘传”“乘七乘传”也当是乘六/七辆乘传规格的传车之意。《汉书·高帝纪下》如淳注所引《厩律》中的“急者乘一乘传”,当即紧急者乘一辆乘传之意。《史记·孝文本纪》如淳注的“如置急者乘一马曰乘也”一句,语义不通,文字或有遗漏。《汉书·郊祀志下》说:“及陈宝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余岁矣,汉兴世世常来,光色赤黄,长四五丈,直祠而息,音声砰隐,野鸡皆雊。每见,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一乘传驰诣行在所,以为福祥。”[1]卷二五下“遣候者乘一乘传驰诣行在所”的行为,当即《厩律》所说的“急者乘一乘传”的情况。
三
据《汉书·王吉传》记载,刘贺“好游猎,驱驰国中,动作亡节”,曾经在巡幸方与县时“不半日而驰二百里”,其速度可能还高于日中至晡时“行百三十五里”的纪录。昌邑中尉王吉曾对此进行劝诫,无奈刘贺不听,“其后复放从自若”[1]卷七二。汉文帝也曾“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袁盎谏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圣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骋六騑,驰下峻山,如有马惊车败,陛下纵自轻,奈高庙、太后何?”文帝于是放弃了冒险。①《史记》卷一〇一《袁盎晁错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 740页;又见2014年修订本,第3 317-3 318页。。可见嗣继大统者应当沉着稳重、举动有节,以社稷为重。与文帝接到欲立其为天子消息时的沉稳谨慎相比,刘贺得知消息后即刻出发的行为就显得十分冒失。②相关记载详见《史记·孝文本纪》《汉书·文帝纪》。又参见王子今《刘贺昌邑—长安行程考》,载《南都学坛》2018年1期;刘新然《汉文帝登基与朝廷政局变动——围绕二代危机展开的思考》,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因此,班固记录刘贺驰行“百三十五里”的行为,似暗含贬意。③张敞在向宣帝报告废帝刘贺的精神状态时,称他“清狂不惠”。颜师古注引苏林曰:“凡狂者,阴阳脉尽浊。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痴也。”(《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 769页。)直言刘贺不通人事。张敞还曾提到这样一个细节:“臣敞欲动观其意,即以恶鸟感之,曰:‘昌邑多枭。’故王应曰:‘然。前贺西至长安,殊无枭。复来,东至济阳,乃复闻枭声。’”(《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第2 767-2 768页。)枭是不祥的恶鸟,枭鸟聚集之地,常有灾祸发生。(参见曾磊《贾谊居舍的猫头鹰——关于“野鸟入处”的文化解读》,待刊。)张敞言“昌邑多枭”的目的,其实是以恶鸟警示刘贺,促其反省。然而刘贺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顺着张敞之语谈起自己关于枭鸟的见闻。班固记录此事应该也是对刘贺“清狂不惠”的认同。
《汉书·文帝纪》“乃令宋昌骖乘”,颜师古注曰:“乘车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处车之右,以备倾侧。是以戎事则称车右,其余则曰骖乘。骖者,三也,盖取三人为名义耳。”[1]卷四以为一车承载三人。其实颜师古所说为按礼法驾车的情形。汉代的传车以轻便的轺车为主,从大量汉画像所见汉代官吏乘车出行的画像来看,以二人共乘一车的画面最多(一为驭者,一为乘者)。肩水金关汉简:
使者一人 假司马一人 骑士廿九人 ·凡卌四
人 传车二乘 轺车五乘
吏八人厩御一人 民四人 官马卌五匹 马
七匹 候临
元康二年七月辛未啬夫成佐通内73EJT3:98④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肩水金关汉简(壹)》,中西书局2011年版,彩色图版见上册第74页,红外线图版见中册第74页,释文见下册第35页。
此简当为一队车驾经过肩水金关时的记录。“传车二乘”当是使者、假司马各乘一辆。“厩御一人”当来自厩置,驾一辆传车。另一位驾传车者或为“吏八人”“民四人”中的一人。其余乘车者共11人,乘剩余5辆轺车,平均每车2.2人,即1车载3人,其余4车每车载2人。
元方回续《续古今考》卷二三“附论骖乘”条说:“文帝之诣长安,以宋昌骖乘,则文帝一车有三人,又张武等六人乘传车六乘,共为车七乘,一行二十一人、二十八马也。”[5]卷二三方回误将文帝一车重复计算,其实《史记》《汉书》皆明文说文帝等人“乘六乘传”⑤韩兆琦《史记笺证》:“宋昌之与张武等所不同的,仅在于他是和文帝同乘一辆,为文帝‘参乘’而已。此处似应作‘宋昌参乘,与张武等乘六乘传诣长安’。”(韩兆琦《史记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10页。)当是。。即使以每车3人计,包括驭者在内,文帝一行也仅有18人。从这个角度考虑,袁盎说代王刘恒“乘六乘传驰不测之渊,虽贲育之勇不及陛下”,不仅仅是强调其速度,更多的是赞颂他以单薄势力赶赴“不测之渊”的勇气⑥该句裴骃《集解》引臣瓒曰:“大臣共诛诸吕,祸福尚未可知,故曰不测也。”(《史记》卷一〇一《袁盎晁错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 739页;又见2014年修订本,第3 317页。)同句《汉书》颜师古注引郑氏曰:“大臣乱,乘传而赴之,故曰不测渊。”(《汉书》卷四九《爰盎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 270页。)《史记会注考证》卷九《吕太后本纪》引董份曰:“袁盎言帝乘六乘传,驰不测之渊,所云‘六乘’者,盖文帝料汉事已定,止用六乘急赴,不多备耳。”([汉]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杨海峥整理《史记会注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81页。)按,从《史记·孝文本纪》《汉书·文帝纪》的记载来看,文帝赴长安时的举动十分谨慎,对朝廷戒心很重。他即位后与功臣集团也进行了持久的权力争夺。“文帝料汉事已定”之说恐不确。。玺书要求刘贺“乘七乘传”赴长安,实际上限定了侍从者的数量(包括驭者在内,最多也仅有21人),其实也是对刘贺势力的限制⑦《汉书》卷六八《霍光传》载,刘贺即位后,令“从官更持节,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2 940页。)可见大多数昌邑国侍从是刘贺即位后方才召至长安的。此亦可旁证刘贺至长安时,随行人员确实不多。。但从“令还郎谒者五十余人”的记载来看,从昌邑出发的刘贺车队至少有50多人,可见刘贺一开始没有听从太后玺书的命令,而郎中令龚遂之所以“谏王”,也许并非仅因为“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
我们看到,《汉书》后文说刘贺到达霸上,“大鸿胪郊迎,驺奉乘舆车。王使仆寿成御,郎中令遂参乘”[1]卷六三,刘贺这才坐上“乘舆车”,依礼前行。
(责任编辑 程铁标)
——海昏侯的“Two Faces”(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