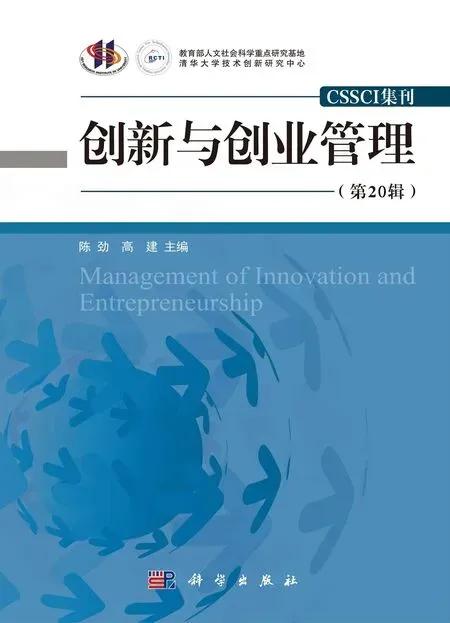数据赋能驱动文化产业创新效率:研究进展*
刘静,惠宁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西安 710127)
伴随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推进产业结构转型的时代变迁、国家提高文化软实力和人们对高质量精神文化的需求,大数据驱动文化产业创新升级已经是普遍现象。在数据赋能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需要思考大数据引发的技术冲击如何影响文化经济的资源配置问题,且这种驱动力能在多大程度并以怎样的方式对文化产业数字化高效率运行产生作用。首先,文化产业发展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深水期经济走向高质量阶段的重要途径,但同时需要研究创新驱动文化产业数字化中的发展效率问题,因为驱动效率的高低能够影响文化产业在多大程度上成为21世纪支柱型产业的战略选择。其次,数据赋能是大数据影响经济运行的复合名词,因其具有多领域交叉性质而难以测度,构建多元化评价维度可以形成较为完整的衡量体系,从而对经济绩效产生直接与间接的驱动作用。再次,数据赋能对文化经济资源配置的影响体现在大数据的数量效应、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三个方面,如何合理确定数据资产的价格体系、技术支持和产业结构配比既是文化产业创新设计的瓶颈,也是大数据时代需要深入思考的课题。最后,数据赋能驱动文化产业创新效率的冲击体现在经济总量关联和结构关联上,因为数字经济是通过改变文化产业中产业链与价值链的创新环节实现文化经济总量增长的,而结构性影响则体现在文化产品创新与技术结构创新两个方面。因此,有必要深入剖析数据赋能与文化产业的内涵,研究其影响因素及经济效率,并寻求两者的内在关联及运行机理,确保数据赋能对文化产业结构性调整的顺利进行。本文旨在对国内外数据赋能与文化产业创新的学术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并提出数据赋能驱动文化产业创新的研究方向。
1 数据赋能驱动效应
产业融合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是产业间融合的实质,通过产业技术边界的收缩与模糊化可以形成业务融合、技术融合与市场融合并推动新一轮产业创新。大数据、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将带动经济增长与文化消费,从而为数据赋能推动产业创新提供丰富的学理基础与现实参考,数据赋能驱动效应具体体现为数据资产的数量效应、数据要素的技术效应、数据产业的结构效应。
1.1 数量效应
海量数据的出现使得传统商业模式与产业结构面临被重构的风险,面对这一问题,要素投入数量将施压于传统数据资产价格形成数量效应,其影响体现于“数据”聚焦研究与“赋能”扩散研究两个相辅相成的层面。
“数据”主要指“大数据”,是“数据赋能”的内涵,聚焦传统商业活动的数据要素与资产。“数据”即一系列符号组合,具有记载客观事物的性质、状态及作用关系的价值。广义的数据包括数字、文字、音频、视频、图像等,而狭义的数据单指数字[1]。因此,在研究范畴上,数字是数据的组成部分,而在研究内容上,数字是数据的内核,数据是数字的载体。互联网时代的数据主要指“大数据”,即相对于专注特定问题进行信息搜集的“小数据”而言的海量数据。早期托夫勒在1980年将大数据的价值称为“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2],但真正将大数据的理念普及开来的是麦肯锡公司于2011年6月发布的大数据报告。在报告中,他们对大数据的影响力、技术路径与作用领域进行了详细说明,之后大数据才得到各行业的广泛关注[3]。2014年3月“大数据”概念首次正式写入我国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一年内,国务院常务会议六次提及大数据运用,国内关于大数据理论研究文献才呈现“井喷”趋势。《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①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16年12月18日为推进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促进大数据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编制的规划部署。规划从我国发展大数据产业的基础、“十三五”时期面临的形势、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保障措施五个方面阐述了建设数据强国的战略思想与实施细则。分析了大数据产业发展趋势,指出我国“大数据产业体系初具雏形”,“到2020年,技术先进、应用繁荣、保障有力的大数据产业体系基本形成”,“推动大数据应用”,“能够为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提供新动力,为重塑国家竞争优势创造新机遇”。徐宗本等[4]、金元浦[5]、王倩和李天柱[6]概括性地认为大数据能够以其精准、全面、多量的特性形成新的管理决策模式,产生创新性技术路径与融合性创意方式。但以往研究通常仅将大数据与技术积累相联系,往往忽略将其运用于商业决策中经营方式的显著变化,而近年来这些变化对经济增长构成重要影响。
“赋能”是“数据赋能”的外延,指数字经济的扩散力,强调将新的生产活动注入传统产业链与价值链,从而形成大数据带来的精准需求信息与高效率运营模式。因此,“赋能”体现大数据数量带来的数字经济效应,也是数字经济发展形态与客户需求结合的产物。热叙阿等[7]指出,数字经济伴随新进入企业的增加,其运营收入呈边际效用递增的结果。例如,免费的软件带来高附加值的市场需求,颠覆了传统企业的组织形态,将量贩式生产赋予专业化特点且形成符合客户意愿的“量身选定”。由此,数字经济成为获得财富和提高生产率的主要形式。但是,目前对数字新经济体的解释性与理论性系统尚待构建。尼夫[8]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指出数字经济与大数据之间相互作用,一方面,大数据会影响商业,全球商业经济运用数量级的数据形成数据洞察力,从而带动数字经济。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将消费者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相结合,连同非结构化数据及新技术共同推动大数据现象的产生,赋予商业新的洞察力、客户需求、盈利模式与高效供应链。马化腾等[9]也认为数字经济赋予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已占到2016年中国GDP 的30.6%,带动280 万新增就业人口,引领全球数字内容变现并实现创意变现的最高价值。
大数据通过价格传导机制影响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力毋庸置疑,但其改变不同产业的运行方式不尽相同,依赖于数据赋能的技术外溢效应、数字化程度产生的规模经济、产业融合中的产业链主体差异与需求市场的接受度等因素。在经济增长领域,数据赋能的技术创新及影响占比最大,因此自第四次产业革命以来,数据赋能驱动一直被定义为产业结构与技术升级的关键[10,11]。
1.2 技术效应
数据赋能形成互联网时代大数据与经济融合的纽带,一方面能够通过影响科学技术的扩散效应产生产业交替迭代,另一方面也会加速监管风险,因此难以尽数大数据的技术经济绩效。
理论研究对大数据发展基本持认可态度,强调其技术特征在经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较早Kim 和Song[12]认为在大数据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时,应构建一个将大数据技术拟合理论与创新扩散理论相结合的理论模型,并通过提高大数据接受度促进区域增长效应。随后Soegoto和Akbar[13]采用定性数据支撑的描述性分析,指出数据技术与网络分析可以改善商业模式从而影响业务增长。Xu 等[14]则通过知识分类学视角研究发现,BDA(big data analysis,大数据分析)水平的提高和推广对企业战略与数字经济发展有积极影响。而Vidgen 等[15]总结了大数据创造价值的三个方面,分别是实施数据驱动的文化变革、挖掘数据价值的技术问题及建立与大数据战略相匹配的经济分析生态系统,这三个方面共同搭建起大数据业务分析与经济价值相关性的研究框架,为Gunasekaran 等[16]关于确认BDPA(big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大数据处理与分析)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以及进一步研究大数据的同化性对供应链与组织绩效的影响提供理论解释。此外,芮明杰[17]通过对现代产业体系的解构,认为大数据作为中国现行创新型产业体系的关键要素,是推进产业价值链的重组、经济复苏、需求升级和国际竞争力重建的重中之重。何大安[18]也指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将以新人类思维融合的方式对经济增长的各个领域产生影响与作用,由此构建创新微观经济学理论与产业组织理论分析框架,用数据与数据的对话改变经济学理论中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人的理性选择。李纪珍等[19]则从专利知识信息角度探索了知识数据要素的运作绩效后发现,专业性的技术信息文献对知识密集型企业的影响尤为突出,其作为国家开放体系的重要环节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的资源配置效率。王天恩[20]同时指出大数据出现后的新信息社会能推动经济增长的质量提升,也更符合人的需求发展和社会经济生活进步。因此,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经济模式创新可以丰富大数据对经济创新的理论领域[21]。
实证研究集中于对数据赋能经济绩效的波动效应进行检验。Barbierato 等[22]通过对典型的内存数据和数据管理行为建模,分析了大数据的客户评估方式对经济绩效的影响。Bughin[23]基于数百家企业的随机样本测试了大数据投资与大数据价值的互补性关联,得出使用大数据的公司比同行的生产率高出2.5%的结论。Liaw 和Le[24]以越南太原大学372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估算了大数据发展与电子供应商、消费者影响效应的相关程度,并分析发现大数据量每增加10%,经济效应增长0.56 个百分点,研究认为大数据是经济领域与技术效能拓展的必然趋势。但尽管如此,大数据带来的潜在风险与方向性问题也不容忽视,是未来探索的重要方向。Müller 等[25]使用814 家企业2008~2014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大数据与商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认为大数据能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但对于信息技术密集型企业和技术竞争性行业以外企业的影响力研究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与此同时,Dong 和Yang[26]以系统论作为基础,对意大利2014年30 312 家公司的社交媒体数据进行研究,分析表明大数据基础设施的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决策创新贡献率每提升10 个单位将促进经济绩效增长率提高0.52~0.75个百分点,并证明在初创阶段中小企业的大数据驱动效应可能更强的结论。Johnson 等[27]则通过对261 名管理人员调查研究发现,在传统的新产品开发模型中,划分数据三维(体积、变化与流速)后分析数据勘探与开发导向对数据市场使用绩效的影响效应,实证表明,数据勘探与业务绩效呈正相关关系,而数据开发与业务绩效关系不显著。Wamba 等[28]也尝试建立大数据分析能力模型,基于297 名数据分析师的数据进行分析验证并提出大数据分析能力对经济绩效的作用,强调数据动态分析能力的中介效应。此外,部分文献发现大数据的经济绩效在不同主体与区域间的非线性关联。Dubey 等[29]通过建立反射模型测算了190 名受访者运用大数据分析和预测经济的行为,检验企业大数据组织能力的生产协作绩效,结果显示,企业大数据组织能力与组织兼容性协作资源合作呈显著正相关,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企业大数据组织能力每提高10 个百分点,供应链绩效提升0.51 个百分点。
对大数据技术效应的质疑也是近年学者关注的重点。例如,Tian[30]将大数据与知识管理进行概念比对,认为将其称为“革命性的变革”还为时过早,将其纳入知识管理与战略组织分析更为科学。Caesarius 和Hohenthal[31]进一步指出,大数据虽然被视为一种前沿优势,但对于不同组织的作用力不同,而且可能会打破原有经济体的平衡而形成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另外,从数字经济的安全性角度考虑,重要信息系统与关键性基础设施所面临的挑战与威胁将远超过互联网,因此加强大数据安全保障与健康发展尤为关键[32]。由于大数据的技术体系尚未成熟,目前在数字经济监管方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还较为欠缺。
1.3 结构效应
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源于19世纪,是研究一个文化意义通过结构关系表达的理论机制,强调透过表意系统构建的各种现象与活动。运用在经济领域,结构效应是指产业结构及其变化影响效果的表达框架。
大数据以高度市场黏合度通过融资、贸易、新闻传播、社会治理等多种途径改变商业规则并形成产业间新的数量比例。Kshetri[33]通过中国金融业市场中大数据的部署案例,发现大数据对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中的中小企业与低收入家庭金融供给结构有显著影响,且现阶段出现的信誉缺失问题的原因在于缺乏大数据评估与外部信息处理能力,因而降低了经济体的活跃程度。Cameron 等[34]运用TRADE-DSM(trade-decision support model,贸易决策支持模型),验证了大数据发展对农业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认为大数据对新兴市场与利基产品的贸易量影响尤为显著。Wells 和Thorson[35]也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数据量与公众关注度密切相关,大数据每渗透1 个单位,公共事物的关注度增加4.5 个百分点,因此大数据信息的流动程度塑造了现阶段经济信息的产业结构环境。而Messacar[36]利用1990~2010年加拿大行政税收数据发现,调查数据中延迟信息与经济结构分析之间关系不显著,不存在偏见性估计,运用大数据分析税收的经济影响时可以忽略其偏差。
另外,大数据在社会生产中形成产业内技术结构之间的经济联系。迈尔—舍恩伯格和库克耶[37]指出大数据能为投资人做出更好的决策提供依据,可以成为中国市场经济转换增长引擎的主要动力,且诸多大数据先锋企业已经形成典型应用案例。岳云嵩和李兵[38]运用多产品异质性模型基于2000~2009年阿里巴巴的微观企业数据实证发现,大数据显著提高了企业进出口市场的概率与出口规模,并确定数据平台对企业出口国广延边际存在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集约边际没有显著影响。曾建光和王立彦[39]则选取A 股上市公司2004~2012年的9264 个样本数据,实证探讨了互联网数据信息治理对降低我国上市公司代理成本与提升企业价值创造的作用。沈颂东和亢秀秋[40]进一步采用聚类—灰色关联法,依据2008~2015年监测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伴随大数据技术的成熟,物流与电子商务呈现协同发展,但协同效果尚不确定,而大数据与信息技术对产业链协同作用的影响力依旧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从现有文献看,当大数据迅速发展时,普遍出现数字经济与产业资本的融合成本不断下降、产业创新的投资回报率上升态势,但数字经济产生的效应大小事实上与不同产业形态及制度政策等其他因素息息相关,因此相关研究仍有待深入。
2 文化产业的创新效率
文化产业的发展迄今已有百年历史,但直至20世纪50年代霍克海默尔和阿多尔诺[41]首次提出文化产业(最早称之为“文化工业”)的概念后,这一领域才成为热议的问题。文化产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文化经济到创意产业再到文化产业的过渡,当前与数字经济结合形成文化创新经济体。围绕文化产业创新的研究主要源于两个方面:来自文化经济学与文化产业领域的理论研究及来自文化产业创新效率测度的实证研究。
2.1 文化产业内涵
理论层面,早期文化产业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属性的争论上,即文化属性与经济属性的关系问题,霍克海默尔和阿多尔诺就是站在批判文化产业、去文化性立场上陈述其观点。直至20世纪80年代文化产业从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过渡,才成为产业经济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20世纪90年代后,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研究且从不同行业进行分析。普拉特和邱美艳[42]从产业链的角度分析了文化产业的战略意义,认为文化产业是一套核心要素集合的生产体系。Nichter 等[43]将广告宣传的经济利润与社会接受度相结合,指出文化产业应发挥其经济效益。奥哈拉[44]则比对了新古典经济学与非古典经济学中关于文化的经济属性问题,认为制度经济学最具有文化倾向,并且经济理论不仅是文化经济的一部分,也等同于文化系统本身。大量文献认为探索经济学研究就是将其置于文化经济的解释框架中,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与文化属性应是非二元性的,文化濡化使文化经济学具备可持续的经济效应。Gotcheva 等[45]进一步指出企业的设计与共享安全文化对产业的重要性,这种观点建立在文化产业的“物质形态”基础之上,强调文化产业的理论基础是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同时,也有相关文献从文化产业的“精神形态”展开。Bertoni[46]认为文化产业无约束力的“去文化”市场导向会使其置于文化的边缘。而从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考虑,森[47]指出文化经济所涉及的边界应具有拓展性,认为文化产业活动具备经济学科与文化部门的双重属性,并从组织结构信息理论和文化产品异质性角度分析了国家干预文化产业的合法性。此类文献强调文化经济的发展形态是由文化领域内深入的经济知识与丰富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共同构成,由此引起经济学界对文化经济领域的关注与兴趣。然而,真正将文化产业的文化与经济属性系统化集大成的是Throsby[48],其研究采取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认为文化产品的价值可以用市场交换与交易衡量,但若对单个文化产品作价值判断则体现其文化特性。
而将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延伸至中国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形成了文化市场化与市场文化论的研究路径。其中,一是对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研究。早期刘诗白[49]指出商品性文化与文化产品市场是实现经济发展与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价格杠杆,是时代化生产的方向。张晓明和闫坤[50]进一步强调文化产业是复制性技术,即网络数字技术的商业应用和市场经济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强调文化产业的产业链创新与商业属性。二是对文化产业的文化属性研究。胡惠林[51]综合梳理国内外文化产业发展内涵后指出,文化产业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文化产业的文化性是其更为本质的属性,在此基础上从国家安全治理的角度阐述了文化市场准入与文化传播的重要价值,并从文化产业的新维度——国家治理层面得出了文化治理是社会发展最高级阶段的结论,强调文化具备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是文化产业的方向与趋势,从而开拓了文化产业性质的新视野。此外,尹世杰[52]也以经济活动与经济研究中的文化因素为切入点分析了商业研究框架中人文属性的重要作用。三是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研究。张曾芳和张龙平[53]也较早从文化产业的基础性质研究出发,运用价值的双重属性分析了文化产业中文化的“超经济”特征,认为文化产业兼具社会价值属性与经济价值属性,并应该充分发挥其双重导向的作用。顾江[54]则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到文化产业中,提出文化产业的经济学SCP(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结构—行为—绩效)范式,概括出文化产业发展的四重含义,即文化产业的利润导向、精神需求功能、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内容集合、媒介交互的产业内部结构,使文化产业的经济溢出效应与社会文化功能有机融合。文化与经济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历史逻辑形成了对文化产业的现代诠释,文化产业的多重性的价值使之成为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性调整的重要方向之一。
因此,文化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无关的论述面临重大挑战。基于此,对文化产业创新效率的深入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与测度。
2.2 文化产业创新效率测度
实证层面,相关研究重点关注文化产业创新效率的总量与结构测度,因为总量与结构是反映国民经济发展总过程的两个基本变量。总量测度包括非线性特征研究、文化产业创新效率测度系统研究,结构测度包括文化产品创新效率研究、文化产业技术创新效率研究。
第一,文化产业创新效率的非线性特征方面。以往研究常常把文化产业发展的线性分析作为主要内容,而事实上文化产业创新效率存在非线性关系与特征。为检验非线性特征,大量文献展开实证研究。袁连生和傅鹏[55]利用非线性模型实证分析了文化产业发展对区域生产总值与人均GDP 的作用,得出结论,文化产业发展与GDP 之间呈“U”形关系特征。靳涛和林海燕[56]则考察了文化资本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交替变化趋势,并指出文化资本的正向溢出效应与物质资本的负向替代效应是决定经济阶段性增长趋势的主要原因。此外,李村璞和何静[57]使用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分析了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特征。胡宗义和刘春霞[58]同样运用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对不同区位高技术产业中劳动、资金、人才资本要素与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关系进行研究。陶长琪和周璇[59]进一步运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刻画出多要素变量的非线性关系,考察其促进产业技术创新效率的过程。而孙坚强等[60]构建了非线性系统模型,通过产业链与价格机制分析了生产价格指数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双向传导效应。
第二,文化产业创新效率测度系统方面。部分文献认为以完善的指标体系与行业指南建立文化产业的评价机制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环节。周锦[61]研究了我国文化产业创新指标体系并构建了文化产业创新效率的动力系统,将文化产业的内外部创新要素与机制纳入研究框架,绘制出文化产业创新因果图,说明经济发展与文化产业创新的正向关联,由此论证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此外,部分学者将文化产业的测度目标划分为文化产业技术效率与文化产业技术进步两方面。例如,柯平等[62]认为技术效率、人力资本、科技水平、产业集聚等是构成文化产业效率水平的重要指标。杨祖义[63]也通过实证研究构成文化产业影响的指标体系,指出包括文化体制、经济发展、文化聚集、科技与政府支持在内的指标均应纳入文化产业的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评价范畴。李丽梅[64]则综合性运用市场需求潜力、经济环境、基础设施与经营绩效4 个一级指标与35 个二级指标系统构建了休闲文化产业的研究体系,并从整体、分区、分部门层面探讨了休闲文化产业发展效率,研究结果发现,我国休闲文化产业发展效率影响因素复杂、整体效率较低、区域不均衡、结构差异显著。而部分文献认为单一的文化产业指标也可以补充反映文化产业创新效率。例如,樊贵莲和郭淑芬[65]对文化产业创业者的胜任特征进行度量,从而深入研究创新型文化产业的运行绩效。此外,麻书豪[66]从差异化视角探索发现政府职能的提升也可以带动文化产业创新增长点。
第三,文化产品创新效率测度方面。文化产品创新效率测度主要从文化产品的分类测算与实证研究角度进行。产业层面,Li[67]使用了TEA(technology-education-art,技术—教育—艺术)模型测度了文化产业五种类型的发展效率,分别涉及艺术发展集团、旅游业、影视业、游戏业与娱乐产品,并指出中国文化产业组织发展在注重文化传承性的同时还应考虑产品商业利益与价值。企业层面,Liu 和Zhang[68]探索了京津冀地区文化产业中艺术品——钢琴的创新发展路径,认为应从文化产品的区域认同度、合作产业链网络建立及政府文化产业可持续性方面强化文化产业效率的测度力度。而Alexe C G 和Alexe C M[69]通过罗马尼亚信息发展领域与商品制造领域的比对发现,个体层面的文化创新动力才是组织效率测度的重要因素。由此得出结论,文化产品创新在信息技术领域投入比在其他方面更为重要。此外,大量实证研究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探讨了文化产品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Zeng 等[70]测评了2011年中国31 个省区市(不含港澳台)的文化产业发展效率,运用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数据包络分析)得到文化产业的规模与产品效率的评价结果,认为中国文化产业生产具有整体效率偏低、环境制约性强、企业主导、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特征。吴慧香[71]也运用DEA-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法测度出我国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特征与规律,发现1999~2009年全国及省际文化产业发展的波动率与差异度较大,产品生产效率普遍较低。而杨春宇等[72]以系统论为理论基础,将文化产业的测度范畴划分为由文化产业系统和旅游产业系统组成的两个部分,并将两者合并成文化旅游产业创新系统产品结构,在此基础上,运用PDF(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概率密度函数)研究并进行差异度与均衡度分析。此外,也有学者以创新性网络文化产业为研究视角,探析互联网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后的新型文化产品业态,并从产品普及率、产品模仿创新性角度测度其效率发展水平与瓶颈[73]。郭新茹等[74]则借助引力模型,基于2004~2015年31 个文化产品贸易国的面板数据,研究文化距离与贸易壁垒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效应。
第四,文化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方面。典型的研究有:郭淑芬和郭金花[75]分析了中国31个省区市文化制造业、文化批零业与文化服务业纯技术效率,结果表明,文化制造业效率呈现“西低东高”特征,文化批零业与文化服务业效率呈现“低集中—高分散”的空间异质性,且区域分布存在明显的非均衡性与显著阶段性形态,其原因在于文化产业纯技术效率偏低。高云虹和李学慧[76]则对中国西部文化产业效率进行测算,认为中国西部文化产业发展纯技术效率存在普遍较低的状况,且外部与随机因素对其影响较大,但各无效率省区市的产业规模却呈现递增趋势。此外,部分研究利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文化产业生产创新与经济效率的关系。吕洪渠和董意凤[77]利用国内31 个省区市2006~2016年面板数据分析了中东西部文化产业效率中开放度与城市化程度,测度了三大区域Malmquist 指数并进行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我国文化产业生产率呈下降趋势。其中,中部区域因开放晚,其文化产业技术效率最低,但对外开放度、城市化与政府导向对西部区域的作用力较为显著,因此西部区域技术效率变化升高,而东部地区的区位优势使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效率较高。而张亚丽[78]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研究文化产业中制造与服务业的科技投入对相关行业的拉动效应、关联效应与波及效应。吴石磊[79]也基于中国2002~2007年整合为四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分析了文化产业技术关联度与波及效应。上述研究是学界对文化产业创新效率测算主要研究内容的梳理。总之,进行文化产业不同层面的实证测度是将文化产业的影响力研究带入微观领域并继续深入。
总体上,目前还无法精确估量不同区域、层次文化产业发展效率和数字技术创新之间影响力的差别,但可以肯定的是,文化产业数字化已经促使产业创新与结构升级效率发生显著变化。
3 数据赋能与文化产业创新效率关联研究
数据赋能文化产业的历程就是产业创新的过程,其实质都反映科技革新突破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因为,数据信息本身是一种表征性资源,它的利用状况决定一个国家生产率高低与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80]。而文化产业是经济增长的组成与社会分工细化的结果。如前所述,经济增长可以从总量与结构两方面探讨。其中,一方面,库兹涅茨[81]从总量分析的角度论述了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对生产率高增长的静态推动作用,强调有用知识的储存和科学发展是经济均衡的必需条件。另一方面,罗斯托[82,83]从结构分析的角度发现,科技、需求变化之后的资源将无迟滞性地配置到各个部门中,从而形成动态性、分解性的产业结构变迁。因此,将两者对于经济增长研究的争论引申到文化经济的实践中,可探究如何推进文化产业创新效率的问题。基于此,文化产业数字化与创新效率关系的研究同样可以从总量关联与结构关联两个方面进行。
3.1 总量关联
数据赋能与文化产业创新的总量关联中,目前相关文献研究主要聚焦于商业活动的增长性关联与波动性关联环节,而且普遍采用经济增长模型或调研数据进行预测。在增长性关联中,较多通过产业链和价值链增值研究将数据赋能与文化产业增长相联系。例如,Liu 和Yi[84]通过电子商务网站交易与行为数据进行产业开发需求管理研究,结果表明,大数据能够预测新的客户需求从而改变整个产业链。同时,Sharma 等[85]通过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文献梳理验证了大数据和业务分析在价值链中的市场创造力,并分析了数据洞察力在不同层次组织绩效中的差异性,结果表明数据驱动的业务分析对文化企业流程再造有显著作用。Shamim 等[86]利用108 家中国企业的原始数据,运用最小二乘估计法检验了大数据与企业价值链中决策环节的质量关联,研究表明,大数据是企业决策环节的重要前提。而国内较早的相关研究中,刘友金等[87]在阐述创意产业价值链的基础上,剖析了由信息流构成的若干组织节点对创意产品市场影响的自循环系统,由此构建系统结构模型,为信息系统与文化创意产业增长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基础。赵小平等[88]则进一步从艺术价值链“陷阱”问题出发,分析了信息不对称形成的产业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行为,并改进了文化艺术价值链模型。但也有研究认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链始终涵盖上下游所有企业,是市场需求和科技艺术的结合,因此技术经济的关联性至关重要[89]。张杰和郑文平[90]考察了中国本土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作用,指出在进口中运用数据学习效应能够拉动产业创新升级。但是,上述研究在大数据与文化产业的增长性关联分析中普遍考虑文化产业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却往往忽略了技术冲击带来的短期波动,因此具有局限性,需要进行时段性动态分析。
波动性关联模型较好地改进了文化产业长期增长模型的局限性,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数据赋能对文化产业创新的产业周期与经济波动展开。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模型是较早描述产业波动的理论工具。蒋园园和杨秀云[91]由此选取2006~2016年我国1008 份政策文本,定量分析出产业政策波动与文化创意产业生命周期的匹配性,研究得出,2012年网络信息产业发展推动我国文化产业达到产业周期峰值。桑硼飞[92]则基于文化创意产业生产函数建模,测算出文化创意集聚对生产率的波动效应,发现科技与人才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显著作用。盛垒和权衡[93]总结性地指出引领新经济周期的三重变革,认为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拓展能够带动经济发展长周期,但在数字化尚未全面进入商业领域阶段,难以成为驱动长期经济波动的中流砥柱。另外,黄滕[94]首次将分析经济周期波动的典型工具即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引入商品价格波动中,利用商品价格大数据分析中国经济波动,并进一步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探讨中国商品价格黏性的成因。而骆嘉和王中云[95]通过剖析互联网数字技术内涵,提出推进文化产业数字化与新媒体联动效应的必要性,由此整合波动性区域文化资源形成世界扁平化。值得说明的是,文化产业数字化的波动性增长模型在实际应用中还较为匮乏,此类文献有待进一步丰富。
3.2 结构关联
由上述研究发现,数据赋能引发的文化产业创新增长效应为文化产业结构升级研究带来新的契机与空间,现有关于数据赋能与文化产业创新结构的文献为此提供了较好的补充。但从当前数据赋能产生的多层面文化产业结构性关联来看,文化产业核心层的高质量文化产品与技术需求将日益扩大,而文化产品供给和技术支持力度却相对匮乏,结构性缺陷与供需数量缺口大小因数据赋能的精准度与客户需求偏好差异度各有不同。
在数据赋能与文化产品供给结构关联研究方面,相关研究众说纷纭。其中,Kubler 等[96]开创性地基于标准化数据同步模型,将大数据与各个系统网络及产品信息结合,形成具有新结构特征的抽象智能化产品,并服务于各产业领域。Badin[97]进一步将大数据引入文化产品与服务中,认为大数据足迹能改变营销产品组合结构从而造就新的利润模式。Zhan 等[98]则通过搜集电子公司新产品六个月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大数据能识别产品需求偏好,挖掘产品信息,改进产品设计结构与用户体验,将客户满意度提升了0.71 个百分点。而杨连星等[99]基于1996~2013年中国文化贸易HS(the 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六位码数据,采用回归模型实证分析表明,文化产品出口品质与文化贸易呈正向关联,而出口价格对贸易联系有负向抑制效应。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具备丰裕的人力资源禀赋,更适应于形成文化产业服务优势。例如,黄文迁[100]运用引力模型与静态面板数据,对中国文化产品与服务模式结构进行测度,验证了我国文化产品服务贸易模式结构存在的失衡问题,强调文化产品服务贸易结构的改进需要进一步将技术与文化融合。李晓标和解程姬[101]同样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交叉项与文化资本共同作用于文化旅游经济,但中国文旅业的产品结构转型升级不能单纯依靠粗放型物质资本,更应注重集约型人力科技投入。
应对数据赋能的技术冲击,是文化产业技术结构调整的目标之一。为此,Bail[102]较早基于文本数据探索了大数据新技术与文化领域定性化研究的结合,指出大数据技术与文化环境刻画、文化区域拓展、文化元素跟踪等的关联,强调大数据对文化社会自动化与技术专长的驱动作用。而Holtzhausen[103]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大数据作为公共文化环境研究的驱动因素,能够将现实问题转换成结构性数据的可能性,并可以进行技术层面的回归分析,但同时强调大数据应致力服务文化参照物并保障数据安全。然而,随着数据赋能技术的显著性提升,文化产业技术性缺陷却日益凸显,寻求文化产业技术结构标准化呼声随之出现。因此,构建标准的经济模型可以解决文化创新及其影响因素问题,并且因为大数据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技术方法提升显著相关,所以应深入研究大数据的技术方法潜能[104]。因此,斯塔布斯[105]从宏观层面将大数据与文化价值相结合,指出大数据作用于文化创新的关键在于从信息中获取创新动力,激发人们测试与应用各种创新技术的能动性并将其投入商业分析中。顾洁[106]进一步将数字经济划分为三大特征并引领五大商业变革,认为大数据能够打破现有技术结构与资源边界形成产业开放性创新。从现有的研究看,数据赋能如何在促进文化产业技术结构中同时具有标准化的规范功能和系统性的保障功能,还能兼顾文化产业数字化的技术安全,是理论研究与制度设计的重心与依据。另外,相关研究更多针对部分区域与个别领域,缺乏全国不同区域、领域的研究。基于此,学术界关于大数据与文化产业技术结构的关联效应问题还有待深入,需要从多层次寻求理论与实证支撑。
4 结论与展望
4.1 基本结论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数据赋能驱动文化产业创新效率的研究从三方面展开。
一是从数据赋能的内涵出发,研究大数据的内在属性与外延价值及在数据资产中的数量效应、全要素挖掘中的技术效应与产业经济中的结构效应,并提炼出大数据对文化经济形成的配置方式与影响力;二是通过界定文化产业的基本概念并梳理其嬗变机制,总结出文化产业创新效率提升需要将数字科技、信息化有机融合的必要性,并且得出文化产业创新波动、创新系统、文化产业产品与技术创新是衡量创新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重要指标的研究结论;三是在分析数据绩效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文化产业数字化与产业创新效率的总量关联度与结构关联度,形成数据赋能对文化产业创新效率量化与质化驱动力的研究框架。
具体内容如下。其一,大数据影响文化经济资源配置。相关研究主要从大数据的数量效应、技术效应、结构效应等维度展开。通过“数据”与“赋能”的解析,说明互联网背景下大数据的海量性资产属性,普遍证实数字经济以要素投入数量影响资产价格从而产生经济内驱力的资源配置作用。而技术传导机制和结构动力机制为研究大数据的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提供理论支撑及现实依据,并为个体层面的数据技术、中观层面的产业经济结构、宏观层面的文化经济的结合提供枢纽。
其二,文化产业及其创新效率测度。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文化产业的属性、机理与演进历程及非线性特征、指标体系、文化产品与文化产业技术等内生变量的测度、建模、评价与检验。一方面,以文化产业经济属性与文化属性的争论为切入点,形成现当代文化产业创新理论的产业融合论基础。另一方面,从文化产业创新效率的非线性测度、文化产业测度系统构建角度进行文化产业总量研究发现,文化产业效率呈非线性波动,并且能够通过体系化测量指标深入进行复杂度检验与影响机制剖析。然而,这些实证分析尚未形成基于创新视角的文化产业发展效率模型。
其三,数据赋能文化产业创新效率提升。以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关联为切入点与理论依据,将大数据作为创新行为表征,研究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文化产业的驱动机制发现,数据赋能经由产业链与价值链对经济增长产生长期影响,而短期技术冲击形成文化产业周期性波动,共同构成数据要素对文化产业创新效率的总量关联。此外,作为促进文化产业结构升级的文化产品与文化产业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对文化产业创新效率产生结构关联。其中,数据与文化产品信息结合的目标是改善文化产品结构性供给,与数字技术结合则是文化产业技术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
4.2 研究展望
首先,深化数据赋能与文化产业创新的关联度研究。上述研究代表了数据赋能驱动文化产业的最近进展,且能为数据赋能对文化产业发展创新的影响分析从不同角度提供较为完整的支撑。就文化产业数字化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也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以往的研究也达成一定的共识。前人的研究积累是后续研究的基础,同时也为进一步探索提供新的方向。但是,相关文献还存在亟待研究与解决的诸多问题,关于数据赋能与文化产业创新效率关联性问题研究还相对较少,且更多文献集中于理论与经验研究,缺乏系统的相关实证研究与深入挖掘。后续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数据赋能驱动文化产业创新的机理、数据赋能对文化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特征、对文化产业创新不同区面层面的效率差异的影响等问题。
其次,注重数据赋能驱动文化产业效率的机理研究。数据赋能虽然作为中国经济与全球管理的新模式,已有相关文献进行研究,但完整概念剖析与动力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现有的文献大多从相关学科角度切入分析。学者们也主要从大数据赋能内涵、大数据赋能的评估、数据赋能的经济效应等方面进行探讨,尚缺乏关于大数据对文化产业创新影响的理论机理与模型构建研究。并且虽然较多文献肯定了大数据对经济发展与创新的作用,但鲜有文献以宏观与微观机理为纲剖析大数据为什么会影响文化产业创新,以及如何影响文化产业创新效率等问题。而应将数据赋能驱动下文化产业制度创新、产品需求创新、技术投入创新结合,从大数据施策与技术运用的角度进一步完善数据赋能对产业结构创新驱动的理论与现实框架构建。
再次,重视文化产业的产业经济属性与产业创新效率的研究。随着现实中文化产业这一新分支领域的不断扩展,作为特殊性生产要素,文化产业经济调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重心,更加关注产业结构的内部运行与转变方式,而现有的文化产业文献中较少体现这一内容,尤其是将文化产业数字化思维引入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研究相对欠缺。另外,对于文化产业创新效率的测度,以往多数文献侧重于以某一方面指标反映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少有研究构建综合性指标体系衡量其创新效率。相关的定量文献分析也多集中于文化产业发展线性测算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缺乏文化产业创新效率的非线性特征测算,且鲜有研究从效率角度对数据治理影响文化产业创新问题进行探索。
最后,拓展文化产业数字化趋势与结构差异度研究。现有文献多集中于概览性分析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因素,且多基于微观层面的调查与经验分析,集中于相同时间节点的截面数据,缺乏数据赋能对文化产业创新的长期趋势性研究。此外,将大数据的商业发展潜力纳入文化产业创新内部,直接研究大数据对文化产品与文化产业技术的作用机理、规律的文章较少,尤其是文化产品的市场供给效率与产业关联度分析、文化产业技术结构创新的门槛特征及识别等。缺乏对区域性产业结构升级与文化产业关系的深度解读与实证分析,且进行区域比较性与行业关联性的研究有限。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文化产业在数据赋能产业结构创新逻辑下的运行机制。
综上,学界为数据赋能与文化产业创新效率的相关研究奠定了翔实的基础,也为后续探索提供借鉴与方向。进一步研究应紧密联系新常态下中国大数据发展与文化产业创新的区域性阶段性特征,结合文化产业创新发展中存在的效率波动与结构性失衡问题,通过数据赋能驱动文化产业创新效率的非线性机制与结构性机制,分析大数据对中国文化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产业关联、区域差异。同时,应深入研究数据赋能驱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非线性特征、文化产品供给结构、文化产业技术结构的运行规律,为推进新时代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提出更具针对性的理论与现实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