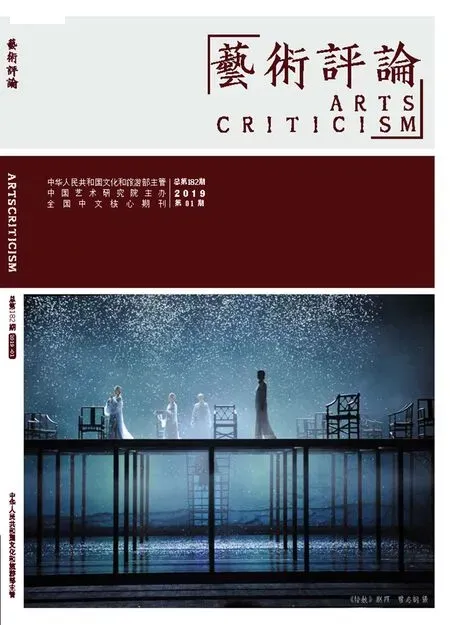执此一念 已度十年
陶 冶
现代舞课可以展开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身体本身,这种观念源于我在部队上的一节现代舞课。舞者是很容易顺从的,我却是一个异类。部队的传统让我产生了质疑,这使我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观察者。在这些传统舞蹈中,我一直在怀疑“真我”在哪里。在现代舞课之后,我感觉展开了一个方向,好像不用去想为了表达而表达的事情,而是发现原来有那么多动机在舞蹈中,现代舞的丰富性和对事物的探索都存在于动律中。
在众人的劝说下,我还是非常决绝地离开部队去寻找“真我”。退伍之后我来到金星舞团当实习舞者,虽然没有工资,但这些都不是问题,我只想浸泡在这个环境里跳舞。金星舞团给我打开了另外一扇窗、一个世界。当我走进这个世界的时候发现:对待身体、对待舞蹈、对待自我的办法有那么多,其实这回到了现代舞的核心,这个核心是从个体开始,不是集体。
之后我到了北京现代舞团,慢慢地,个体的问题一点点往回收缩,直到2008年做“陶身体”。当我跟随舞团巡演的时候,看到了国外的优秀作品,他们开始推拉扯拽,他们的身体已经解放到没有边界了。在这个没有边界的过程中,我看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现象、不同的实验都在展开。反观国内,我们还在纠结如何表现一个人物、一个故事,这体现出国内对待身体的整体性落后。
这时候国内的一些学校也在做中国的现代舞,但是现代舞不是中国的,而是个人的。因为没有才会不自信,所以我们才说“中国的现代舞”,这是我做独立探索最大的养分。我想做个人的探索,改变国内身体的现状,而且我和段妮的身体有许多自带的内容。我知道我的身体走在了前面,它蕴藏着让我惊叹的内容。
2008年做陶身体剧场几乎就是一念之间做出的决定,建团是三人一拍即合的。王好是一个单纯、热爱的舞者,在中央民族大学学了10年的民族舞,拿过各种奖项。她的毕业论文是《情绪如何表达》,却被老师否定了。民族舞本身就是有情绪的,但是它表达的情绪是不真切的,王好在此时就已经在思考作为舞者应该如何表达民族舞中的自我情绪了。段妮也是一拍即合,她已经走到了最顶级的平台上,她的平台是高于我们的。在没有成立陶身体剧场之前,她已经进入美国林肯中心两次,在世界最厉害的两个舞团担任过舞者。三个人置死地而后生,没有任何退路。我们的理想是:在这个环境中,可以和世界接壤,不是我,不是王好,不是段妮,而是我们与世界接壤。
2008年的第一次演出是在南锣鼓巷的一个画廊里面,我们进行了一场即兴。虽是即兴,却有很严谨的编排,是一个空间沉浸式的演出。演完后,北京舞蹈学院的一位研究生问:“为什么可以这样没有边界地呈现?”这无疑打破了剧场文化的严肃。当时我们是完全以一种脱离的姿态进入市场和公共空间里面,如咖啡厅、文艺气息浓厚的胡同,而且每次选择空间都是有些限制的,人在里面都是要被空间所主导,或者说是被切割掉的。
2008年建团后,2009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个时候我们终于把《重3》这部作品创作完毕并且带出国门,在荷兰和比利时两个国家公演。大约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期间我们做了文化学者的访问、演出和工作坊。我们在荷兰以文化学者的身份访问了一些现代舞团,参与了他们的一些对话、观看了作品和参与工作坊,由此了解了欧洲比较前沿的、主流的舞团以及他们的运动方法。同时,我们也把自己的训练体系、组合、作品分享给他们。《重3》在国外的首演就是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一个非常前沿的剧场,这个剧场是专门做表演艺术的实验剧场。之后又到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拜访了当地的现代舞团,并做了我们的专场演出。这是陶身体剧场第一次带着技术和作品以一个舞团的形式出国演出,与国外的环境进行交流。
从这个时间节点算起,2010年和2011年都是一个非常顺利的发展趋势。2009年和2010年这两年的时间还在继续做作品,与国外的关系也保持得刚刚好。陶身体剧场也不是大家所认为的先从国外发展起来的,而是国内外同步的。2010年我们在国内做了工作坊,推广国内的公共教育,同时也受到了国际上的关注。比如伦敦最有名的艺术制作中心的艺术总监来到北京做考察,与我和段妮进行对话,在对话结束后,直接拍板决定要邀请我们。同是这一年,“新加坡艺术节”也邀请我们开展艺术对话。在2011年这个阶段上,陶身体自身已经积蓄了很大的能量了,之后借助媒体的曝光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从2009到2011年“纽约城市剧院”“美国舞蹈节”等七八个艺术机构向我们发出邀请,通过这些平台我们得到了美国《纽约时报》最好的评论,这直接推动了陶身体在美国的影响力。
在2011年,国家大剧院就向我们发出了邀请,但是时间冲突没有达成共识,两年之后的2013年,“陶身体”才有了首次进入国家大剧院的契机。现代舞并不是国家大剧院的主流演出,因而票房普遍不好,但是我们的演出打破了这个规律,黄牛票甚至被炒到1000元以上。
在建团之初我们并没有确定要做“数位系列”作品,但“重”这个主题却是一定要做的。因为重量本身就是身体的本身,我们身体就是物质,这个物质身体的重量一定会有精神上的向往,也是一个重量,就是精神的重量,然后就是生命的重量。为什么叫“重”,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垂直往下坠落的过程,而结果就是死亡本身。这个过程是无法避免的,在整个坠落过程当中会有许多的预设,比如我们想要再上升,或是想要再展开一下身体,甚至背上一些道具,去减缓这个过程,往反方向去使劲,这是有一定意义的。这个往上拔的过程是很难的,哪怕是一点点都非常困难,但你要想堕落下去却很快,是一个加速度的堕落过程。所以,重量本身就是我们要去对抗的本身,这是具有终极价值意义的。
“重”即是立点、立论。陶身体剧场从《重3》开始已经在思考特别“形而上”的东西了,《重3》有三部作品,分别是两个双人舞和一个独舞。这三个舞蹈都在探讨循环本身,怎么循环?就是从细节开始,从简单开始。身上已经有十八般武艺了,但这个时候要做减法,减到只能从“走”开始。只有从基本运动开始才能了解人的根本,因为人都是从走开始的,走就是我们的目标。“棍舞”是一个人的诉求,因为人和人是无法连接的,我进入不了你,你也进入不了我,我们都是孤独的个体。我们想要不孤独,希望互相连接,所有才会产生“爱”这种情感。

《重3》 (棍舞) 范西 摄

《9》剧照 范西 摄
再到作品《2》,我们遇到了音乐家小河,并与他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磨合音乐。《2》是我和段妮的愿望之舞,我们在金星舞团认识的时候就打算编一个双人舞。双人舞是最难编的,双人舞就代表着二元对立,二元对立的创作很容易形成套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相对度是非常清晰的:大与小、远与近、强于弱、高与低、黑与白等。双人舞最难的是进入到二元探索当中,于是,我们干脆就从从本质来表现大小、远近、高低、快慢……所以这个作品就像两个量子在纠缠一样。
排练的时候,我们在地上不断地推动,然后停止,惯性转换,用非常极致的50分钟在舞台上非常纯粹地存在下去,像磁场一样一直在抗衡,到最后消失在舞台上。这个作品一开始我们选择在舞台上趴了足足三分钟,只有噪音,观众在这三分钟里忍受着极限的煎熬,同时按耐不住地平复自己。这些观念在国内肯定是很难理解的,国外观众对于这种东西的理解相对接受度比较高。让“陶身体”走出去的《重3》只是第一步,使舞团加速发展的作品是《2》。这个作品几乎走遍了全世界,也确定了我们在观念上先行的“数位系列”。
编完《2》后,我们才想到如果做“数位系列”应该从“1”开始。但是《重3》并不是我“数位系列”的起源,而“重”才是,“3”只是3个人。我觉得“数位”是把“人”给剔除掉了,但这一部分在国内很多人是看不到的,在西方大家就更为关注,他们指出我们的内容是极其东方的,又看到我们的身体思辨路径是非常西方的,于是对于我们这样一种现状,他们充满了兴趣去研究究竟。
《4》就是发展技术,在经历了逻辑和技术上的沉淀之后,要把内容、智慧、体系建立起来。《4》是关于“圆”的运动,圆运动会使人摇摆、失衡,进而导致重量的转换,进而结构身体。直线是路径,而曲线是真理。“陶身体”的整齐不是划一,而是划圆,把所有的点都要连接起来,我们能把圆做到整齐了,技术体系的根基才结实。《5》就是把圆运动之外的观念整合,人与人、人与人的公转、人的自转、推拉与支撑本身……这些作品都在限制,限制也是理解自由的一种办法,要知道想要什么,减什么。去发现动的规律,然后才会形成动律。《6》《7》《8》就是在做观念,完全脱离了舞蹈,让纯肢体的探索展开更深入的指向性,或者说是让身体视觉艺术化。我们进行了更极致的设限,光的限制、声音的限制、呼吸的限制,最后到身体运动的空间限制。当作品《9》公演于国家大剧院的时候,由于没有音乐,很多观众接受不了。作品《9》只传递了人与人之间的呼吸以及摩擦,还有在地面的磕撞,这些声响在发生的时候,人和介于人之外的存在是并存的。对于国内的一些观众,去理解这样极端的创作方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下一个十年,“陶身体”会继续在“数位系列”上创作,但不一定从《10》开始,有可能会从《11》《12》开始,按照数位的惯性继续进行。递进代表着人数的增加,增加就代表着运营成本,实际经营的扩充。之前是半年一部作品,现在是两年做一部作品、再往后叠加,可能就是三四年做一部了。重要的不是“数位系列”的增加,而是过程中的增叠,对我来说,这其中生命力给予了多少、付出了多少、共建了多少,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印证。
这十年过得很快,安排得特别满,事情赶着事情,休息一天都是奢侈的,总感觉时间不够用,也总是感叹这一生能办好一件事更是太难太难的。十年,感觉却是一瞬间,但是有一种东西始终没有变,那就是十年前的“念”。这十年就是一念而已,接下来的这十年,还是执此一念。
——东西方现代舞艺术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