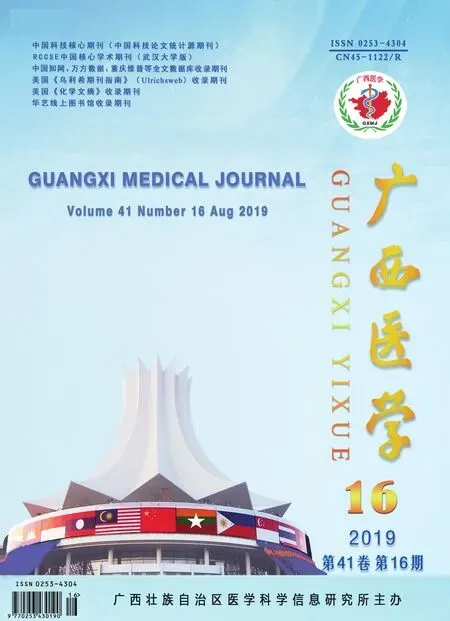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骨水泥及磷酸钙骨水泥的材料性能及改性的研究进展
张 磊 唐晓菊 黄有荣 刘汝专 恭德飞 黄 立 吴晓飞
(1 广西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南宁市 530001,电子邮箱:1063991500@qq.com;2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骨伤科,南宁市 530011)
【提要】 经皮椎体成形术和经皮后凸椎体成形术是目前外科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的主要治疗手段,而所使用的骨水泥材料主要有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骨水泥、磷酸钙骨水泥(CPC)、生物活性陶瓷骨水泥、硫酸钙骨水泥以及其他经过材料复合形成的新型骨水泥。目前,有关PMMA骨水泥及CPC的研究较多,应用最广泛,但其材料本身仍有大量缺陷,改良上述材料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本文主要针对这两种骨水泥在放热反应、骨传导性、生物力学强度、生物降解度、生物相容性、生物载药性方面的性能以及改性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逐渐加重,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OVCF)成为威胁老龄人口健康的主要疾病,其在全世界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1]。传统保守治疗如卧床、佩戴治具以及药物治疗,在短时间内难以取得明显的疗效,并且长时间卧床可导致坠积性肺炎、褥疮、泌尿系感染等严重并发症。近年来,随着椎体成形术的快速发展,通过微创向伤椎内注入骨水泥材料能够迅速稳定损伤椎体,恢复椎体强度,疗效显著。目前主要的骨水泥材料主要有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olymethyl methacrylate,PMMA)骨水泥、磷酸钙骨水泥(calcium phosphate cement,CPC)及其他复合骨水泥材料。其中,丙烯酸类骨水泥作为第一代骨水泥材料,临床应用最广泛,但具有产热过高、生物相容性差、不可生物降解等缺陷;CPC又称自固化磷酸钙人工骨,其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骨传导性及生物降解性能,但其存在力学强度较差,无法满足临床应用要求等不足。通过材料的复合,取长补短,能有效优化骨水泥材料的性能。本文主要对PMMA骨水泥及CPC的材料性能及改性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 放热反应
骨水泥材料在其聚化的过程中释放出一定的热量,释放的热量容易引起骨水泥-骨界面处产生热坏死,导致植入骨水泥松动以及灼伤脊髓、神经根等。
1.1 PMMA骨水泥及CPC的放热反应 PMMA骨水泥由含有甲基丙烯酸甲酯的液体主分和含有聚合物和共聚物的粉体组分构成,液体单体进行渐进式聚合,产生固体质量,每摩尔甲基丙烯酸甲酯单体产生57 kJ的热量[2],导致聚合过程中产生大量热量,骨水泥-骨界面温度超过47℃即可导致热性骨坏死和组织损伤的发生[3-4]。Belkoff等[5]通过热电偶对24个骨质疏松椎体进行PMMA骨水泥椎体成形术后检测,发现椎体前皮质的峰值温度为44℃~113℃,椎体中心的峰值温度为49℃~112℃,而椎管内的峰值温度为39℃~57℃,认为在骨水泥聚合过程中椎体的内部温度升高明显,有引起热性骨坏死的风险。Urrutia等[6]对24只新西兰兔进行PMMA骨水泥椎体成形术实验,发现有一半的新西兰兔发生早期局灶性骨坏死。Lai等[7]将12只猪椎骨浸入37℃盐水中以观察热损伤是否与骨水泥发生渗漏有关,发现若未发生骨水泥渗漏,固化温度不会直接导致附近软组织的热损伤,如骨水泥渗入椎管,后皮质的放热反应则可能导致神经组织的热损伤。而CPC主要由水化反应生成,无明显放热反应[8]。
1.2 PMMA骨水泥的改性 长久以来,人们都认为PMMA骨水泥固化期内短暂的温度高峰是导致周围骨组织热坏死以及神经损伤的主要原因。最新的研究表明对PMMA水泥进行复合能有效改进其产热性能,能有效降低其聚合时的峰值温度。有学者发现在PMMA骨水泥中加入羟基磷灰石可以有效降低峰值温度[9-10]。Kim等[11]将羟基磷灰石、壳聚糖粉与PMMA骨水泥复合后发现,其放热温度明显低于纯PMMA,且比纯PMMA更具有生物相容性和骨传导能力。Tai等[12]在PMMA骨水泥中加入蓖麻油后进行预冷却,形成了模量低、聚合温度低、处理时间长、适应性强、安全性好的理想骨水泥材料。此外,PMMA骨水泥的温度峰值也受液相甲基丙烯酸甲酯的影响,其聚合时的温度也与单体配方有关。椎体成形术中PMMA骨水泥聚合时的放热反应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聚合时在椎体不同部位的温度以及对周围组织、神经的影响仍需要大量的实验及临床研究加以证实,并通过改性降低其峰值温度,使PMMA骨水泥更安全地应用于临床。
2 骨传导性
骨传导性是指促进新骨进入材料表面或体积内的生物材料特性,其中生物材料被用作支架为骨和纤维血管组织的长入提供引导,以引导新骨形成[13]。
2.1 PMMA骨水泥的骨传导性及改性 PMMA骨水泥虽广泛用于脊柱外科手术,但缺乏骨传导性,从而限制其更好的临床应用。大量的学者试图改善PMMA骨水泥的性质和生物学性能,通过材料的复合使其具备骨传导性。Lopez-Heredia等[14]发现,多孔PMMA骨水泥能有效地负载不同剂量的磷酸钙,从而使其具备潜在的骨传导性;其他学者将羟基磷灰石微球作为添加剂与PMMA水泥复合,在保持相当高的压缩强度同时,其生物相容性和骨传导性也显著增强[15-16];Oryan等[17]发现,与单独使用PMMA相比,添加血小板凝胶可以改善PMMA骨水泥的骨传导和骨再生特性;Wu等[18]研究开发了由聚富马酸二羟丙酯/α-磷酸三钙/羟基磷灰石和聚富马酸二羟丙酯/磷酸四钙/磷酸二钙组成的可注射和可生物降解的复合水泥,发现该复合水泥具有低固化温度、不透射线性等优点,以及良好的生物降解性和骨传导性。
2.2 CPC的骨传导性及改性 CPC通过附着、增殖、迁移和骨细胞的表型表达,引导新骨的形成,而具备良好的骨传导性[19]。研究表明,将人诱导多能干细胞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与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共同培养后,与CPC支架材料复合,能有效增强其骨和血管的再生作用,显著增强CPC植入材料的生物活性及成骨活性[20-21]。此外,Aparicio等[22]在CPC材料中加入锶,能增强其骨传导能力并加速其降解;Kuang等[23]通过体外研究也发现,锶-CPC组的成骨细胞增殖率较高。
3 生物力学强度
椎体的强度指椎体在发生塌陷之前所能承担的最大应力;椎体的刚度指椎体在外力作用下抵抗形变的能力,刚度越高,椎体表现得越“硬”。骨水泥生物力学强度应以接近正常骨组织为宜,既能提供即时的稳定性,又能避免骨水泥由于强度过大引起邻椎的骨折。
3.1 PMMA骨水泥的生物力学强度及改性 PMMA骨水泥具有高压缩刚度,注入骨折椎体后能即时稳定伤椎而迅速止痛,但由于其刚度过大,因此引起邻椎骨折的风险也相应增加。研究表明,使用较低模量的PMMA骨水泥材料能明显降低椎体成形术后邻近椎体骨折的风险[24]。Schröder等[25]将等渗盐水以10%、20%、30%的体积比混合到PMMA骨水泥中,铸造测试体,并进行压缩和弯曲测试,发现通过添加盐水可以将PMMA水泥的压缩刚度降低三分之一左右。Li等[26]将PMMA水泥与纳米羟基磷灰石包覆的骨胶原(矿化胶原)复合后研究其机械性能和生物活性,发现矿化胶原-PMMA骨水泥明显降低了PMMA水泥的压缩模量,但不影响其压缩强度和凝固。Zhang等[27]将蓖麻油与PMMA骨水泥复合,发现PMMA骨水泥的屈服强度从88 MPa降至15 MPa,杨氏模量从1 500 MPa降至446 MPa,最大聚合温度从41.3℃将至25.6℃。Yang等[28]将PMMA骨水泥与丙烯酸和苯乙烯复合成亲水的可膨胀骨水泥,发现新水泥的弹性模量和抗压强度以及细胞毒性低于PMMA骨水泥,并且具备一定的成骨能力。此外,Zhang等[29]将双相磷酸钙引入PMMA骨水泥中,发现双相磷酸钙/PMMA骨水泥的抗压强度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并且通过对兔桡骨缺损模型进行的体内试验,发现双相磷酸钙的存在可以显著改善PMMA骨水泥的成骨功效。
3.2 CPC骨水泥的生物力学强度及改性 CPC抗压强度较低,但可以通过水泥基质的致密化和(或)均质化,生产具有与皮质骨相当的抗压强度的CPC材料,但较差的机械可靠性限制了其临床应用。Baudín等[30]发现石墨烯与CPC材料复合能有效增强其机械可靠性;康明等[21]复合壳聚糖、晶须和CPC以制备的新型增强复合材料支架,其力学性能明显优于纯CPC支架材料,可以满足皮质骨和松质骨的力学性能。
4 生物降解度
生物降解是指在新骨的生长过程中,植入材料逐渐被改建和吸收并最终从植入部位消失,新生的组织完全替代植入材料的位置[13]。
4.1 PMMA骨水泥的生物降解度及改性 PMMA骨水泥的不可降解性是其明显的缺点,长期存留于体内容易出现椎体松质骨与坚硬骨水泥界面发生吸收、松动的现象[31]。Zhai等[32]通过在PMMA基质中加入镁微球来开发一种部分可生物降解的新型复合骨水泥。PMMA中的镁微球对生理环境敏感,可逐渐降解生成生物活性镁离子,同时在水泥基质中形成相互连接的大孔结构,并且镁微球的掺入没有显著影响骨水泥的机械强度。这种可部分生物降解的PMMA-镁复合材料可能是椎体成形术和椎体后凸成形术的理想骨水泥。
4.2 CPC的生物降解度及改性 CPC具有生物降解性能,其主要通过化学溶解的被动吸收和细胞介导过程的主动吸收[33]进行生物降解。Klein等[36]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椎管CPC植入物被缓慢吸收,而不会影响稳定性和临床结果,渗漏于骨外的CPC材料在泄漏发生后的2年内几乎完全被吸收。因此,CPC水泥是用于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椎体后凸成形术PMMA基骨水泥材料的重要替代品。
CPC主要通过酸溶解降解,加入快速可降解的成孔剂如聚乳酸-羟基乙酸共聚物[poly(lactic-co-glycolic acid),PLGA],在PLGA降解后产生大孔,并且PLGA水解降解产生乳酸和乙醇酸单体,使CPC具备良好的生物降解性。有学者发现,将CPC-PLGA注入兔股骨缺损模型中可表现出良好的骨反应,术后26周降解率>55%,骨形成率>13%;基于同样的机制,将降解率高于PLGA的葡萄糖酸δ-内酯为作为产酸微粒加入CPC,可以加速CPC的降解,在植入2周后组织形态学评估结果显示,含有10%葡萄糖酸δ-内酯的CPC被更快地降解并被更多的骨组织替代[34-35]。
5 生物相容性
生物相容性是指材料与活组织相容的特性,具有生物相容性的材料在植入体内后不会产生毒性反应[37]。
5.1 PMMA骨水泥的生物相容性及改性 PMMA骨水泥被广泛用于关节假体固定以及经皮椎体成形术和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38]。尽管完全固化的骨水泥具有生物惰性,但PMMA骨水泥具有固有的细胞毒性。既往研究表明,将PMMA骨水泥植入椎体后,其可引发周围组织坏死、纤维化和骨重塑受损等不良反应[39-40]。体外研究表明,PMMA骨水泥的提取物可能会损害不同细胞类型的活力和增殖,包括成纤维细胞、成骨细胞、早幼粒细胞和淋巴细胞[41-42]。特别是未反应的甲基丙烯酸甲酯单体,通常被认为是细胞毒性最强的水泥组分,且其具有组织毒性,这是因为它的含量明显高于任何其他液体成分[43]。另外,残留的N,N-二甲基对甲苯胺通常被认为也具有毒性,Taningher等[44]指出,N,N-二甲基对甲苯胺会对染色体造成损害并抑制蛋白质在体内的合成。其他水泥成分,如过氧化苯甲酰也具有细胞毒性,可诱导炎性细胞因子在成骨细胞中的产生[45]。Tsukimura等[46]通过大鼠实验发现,在PMMA骨水泥中掺入N-乙酰半胱氨酸,可通过原位清除自由基和增加细胞内抗氧化剂储备,以降低PMMA骨水泥的毒性。
5.2 CPC的生物相容性 CPC的溶出-沉淀反应的最终产物包括透钙磷石和磷灰石(羟基磷灰石或缺钙羟基磷灰石),因此具有生物相容性。Guo等[47]通过将CPC支架构建体植入兔下颌骨并进行组织学研究,发现其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骨传导性。Zhang等[48]将CPC注入有缺陷的兔股骨中,在植入后的第1周、第6周进行组织学观察,并没有发现不良的异物反应。
6 生物载药性
6.1 PMMA骨水泥及CPC的生物载药性 使用负载抗生素的骨水泥可以有效治疗感染性骨缺损、骨髓炎以及其导致的病理性骨折,并且能克服全身应用抗生素治疗的缺点,以及控制活性成分的初始爆发和总释放。在理想情况下,与骨水泥混合的抗生素应能提供活性药物的洗脱浓度,且不应改变骨水泥材料的力学性能,万古霉素和庆大霉素是目前这种临床适应证最常用的抗生素[49]。PMMA骨水泥与CPC均具有良好的生物载药性,搭载不同抗生素的骨水泥能有效控制骨组织局部感染,但其释放抗生素的浓度与其洗脱动力血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材料本身机械性能的影响仍需要大量研究。CPC具有良好的释放效率,因此已被用作术后感染的药物输送系统,使用抗生素浸渍的CPC已成为治疗局部骨髓炎的重要方法[50]。
6.2 PMMA骨水泥及CPC的改性 Chen等[51]认为,加载10%万古霉素的CPC具备最佳的物理化学性质和药物释放曲线。Daley等[52]研究发现,使用加有多西环素的CPC刮除术治疗动脉瘤样骨囊肿能有效降低复发率,其中含15 mg/mL多西环素的CPC能维持较高的平均浓度。Letchmanan等[53]在PMMA骨水泥中复合介孔二氧化硅纳米粒子,发现其能显著增加负载的庆大霉素的扩散和延长药物释放时间。Pealba Arias等[54]研究发现万古霉素在体外抑制葡萄球菌黏附方面优于达托霉素和庆大霉素,装载有达托霉素并结合庆大霉素的PMMA骨水泥能完全抑制表皮葡萄球菌 - 生物膜形成,能有效治疗多重耐药性葡萄球菌引起的骨感染。
7 小 结
PMMA 骨水泥是传统椎体成形术中应用最普遍的骨水泥材料,但有聚合温度过高、强度大、不可降解等不足;CPC因其具备良好的生物相容性、骨传导性能一度成为研究重点和热点,是最有希望成为替代PMMA的骨水泥材料,但因其强度不足等缺陷仍需要改进。通过两种材料的复合以及加入羟基磷灰石、纳米离子、蓖麻油、间充质干细胞等能有效弥补其单一性能的不足,但对于复合材料的整体性能以及疗效的稳定性、可靠性仍需要大量的临床研究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