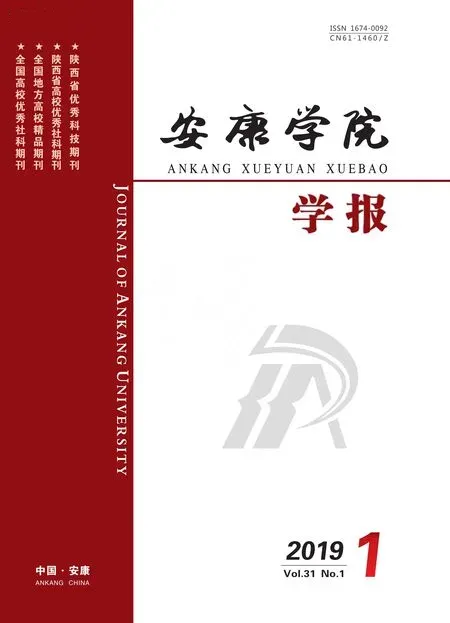《安提戈涅》与《窦娥冤》悲剧冲突比较研究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安提戈涅》 (以下简称《安》) 与 《窦娥冤》(以下简称《窦》)两部剧作因作品中女性的悲剧命运历来被学界所重视,学者们从不同侧面对其进行了比较研究,主要涉及女性形象比较、女性悲剧命运成因比较以及两部作品中所呈现出的悲剧观念比较等。但“我们如果要打开悲剧艺术之门,真正的钥匙就是必须承认一切悲剧在于人类的冲突”[1],所以悲剧冲突比较研究也是不可忽略的一个侧面。因此,本文从两位女性角色及围绕她们展开的相关情节入手,尝试比较分析两部悲剧中所表现出的各种冲突及其异同。
一、人与法的冲突
“法律除了是一组文本之外,也是一种社会控制的体系,而且法律的运作有社会科学阐明,并根据伦理标准进行判断。”[2]从口头的约定俗成到成文成规的公共准则,法律逐渐成了一种控制系统,它直接作用于社会本体,引导并规范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与行为规范。人类作为法律的创造者与践行者,不仅享受着它的规范性带来的公正秩序,也在不断出现的法律与情感、伦理等的具体碰撞中不可避免地与其产生冲突。而在《安》与《窦》中,两位女主人公以及她们的悲剧命运不约而同地都与法律联系在了一起。但透过她们与法的冲突的表象去看,其呈现出的精神内涵是不同的。
《安》是索福克勒斯的代表性悲剧作品,它讲述了悲剧主人公安提戈涅与克瑞翁相抗衡,执意埋葬自己已被定为叛国罪的哥哥,最终嫁给冥王的一系列悲剧故事。面对哥哥波吕涅克斯被抛尸野外,安提戈涅一心要埋葬自己的血亲,而克瑞翁,作为一个城邦法的拥趸者与制定者,他坚决不允许任何人埋葬悼念勾结外敌、破坏城邦安全的叛国者。当克瑞翁询问安提戈涅是否真敢藐视法令时,安提戈涅说道:“我敢。我不认为来自凡人的一道命令就能把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不成文的律条置之不顾,它的存在不会局限于今日和昨日,而是永久的”[3]205。可以看到,是否埋葬血亲其实是二人所遵从的律法形态不同而产生的矛盾冲突。
首先,安提戈涅以波吕涅克斯至亲的身份,把不应将至亲暴尸街头的神法当作是超越任何人、超越时空的信条。她执意埋葬哥哥的表现就是对神法的绝对遵守。其次,安提戈涅主张的也是习惯法,因为虽然埋葬血亲一条在当时的法令中并无明文规定,但这也是长久以来约定俗成的,是民意。同时,使自己的血亲得到死后的安息也是自然法、血亲法,是基于民众所普遍认可的、对血缘关系的重视而形成的。而克瑞翁所秉承的城邦法律则是一种国王法、一种人法,即以人的意志,为了符合某种目的而制定的法律,它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克瑞翁不顾伦理亲情执意不允许他人埋葬波吕涅克斯,其实质是为了维护城邦法的权威。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律法之间的对立,是导致冲突发生的根本原因。
面对这种冲突,作者的情感带有一定倾向性。我们可以看到一意孤行执行城邦法的克瑞翁最终失去儿子与妻子的下场是极其悲惨的。在克瑞翁下令处死安提戈涅之时,他遇到了一个占卜者,说他冒犯了诸神。克瑞翁后悔了,但为时已晚。在作家看来,安提戈涅的法是神圣的,她的选择符合神法,符合道德,而克瑞翁的定法违背了神法、民意和道德,所以非法,这才给了克瑞翁痛不欲生的结局。尽管作家本人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认为国家的法应该考虑神意、民意、自然和人情,但以现代眼光及历史的发展眼光进行审视,克瑞翁的选择代表了为加强国家管理而要全体公民共同遵守的一种强制性制度的努力。这两者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并不能单纯的看作一种道德原则对另一种法律命令的批判。也正因为如此,冲突与矛盾不可避免,而作家所表现的冲突——民意与人法,神法与人法,血亲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也就具有了永恒性。
再来看《窦》中人与法的冲突是如何在剧中体现的。《窦》讲述了窦娥悲惨的人生遭遇,其一生是悲剧的一生。窦娥7岁时就被父亲卖给蔡家作童养媳,在今天看来这是一种剥夺他人人权的非法行为。在封建时代,妇女守寡不能再婚,在今天看来是没有人性的,这也是对妇女人格的践踏,但窦娥在夫亡之后却有决心一辈子守寡,可见她对女性守节这样一种封建思想是何等的维护。无论是三从四德还是烈女守节,这些封建伦理在当时之所以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就是因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封建的习惯法、传统法和人情法,它早已无形中成了约束个人的枷锁。窦娥用尽一生都在维护和遵守这些伦理纲常,而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所谓的约束都是封建社会中奴役人的刑具。作者极力描写的窦娥与这些封建的传统法的冲突与矛盾也就没有了永恒性,只能使我们以批判的视角去审视过去,而无法给予当下以启示。
窦娥与法的冲突还体现在剧本第二折中。窦娥与张驴儿一起对簿公堂,官府老爷只听张驴儿一面之词,并以杖打其婆婆相要挟,窦娥最终被屈打成招。作为一个平民百姓,她在自己蒙受了冤屈之后,只能寄希望于官府老爷,希望其还自己以清白。她在剧中说道:“大人,你明如镜,清似水,照妾身肝胆虚实。”[4]23在这里官府老爷成了法律的代言人。她对于实在法的诉求就转移到了官府老爷的身上。但显然这位法的代言人并没有秉承法的公正性,而是仅凭个人判断与滥用法的外在辅助手段将窦娥屈打成招。
幺书仪指出:“对于元杂剧中出新的这种现象(对于“法”的渴望)恰就从一个侧面证明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确实缺少可以保护无辜,可以俱以主持公正,维护社会公理,保护人权的‘王法’。”[5]法的缺失使得窦娥与法的冲突实际上变成了人与人的冲突,变成了窦娥与昏官之间的冲突。其实质就是法律废弛背景下人与法的冲突。我们在面对这样的冲突时能够非常容易地用法律的正义性标准与理性的道德标准对二者进行评判。二者的冲突在戏剧中也因为昏官的被处死、窦娥的冤屈得以平反而得到了消解。
通过以上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在《安》中,悲剧产生的根源来自贯穿历史发展、在民间形成的地方性习俗与普遍性国家法之间的冲突。“国家法获得独立地位后,在迈向理性化的过程中与传统习惯法的断裂和错位,这是制度转型过程中常见的,往往是不可避免的悲剧现象。”[6]法律的完善永远在路上,其与传统习惯法的冲突自然也一直在发生,也必将会在未来产生新的表现形式。故《安》中所表现出的法的冲突具有永恒的价值与意义。而在《窦》中,法的冲突却表现为法律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下的危机。窦娥的悲剧“主要体现在封建的孝节观念和对清官的幻想上”[7],故其表现出的冲突也就没有穿越时空的永恒性。
二、生与死的冲突
海德格尔曾指出:“在固执己见的人的心目中,生只是生,死就是死,而且只是死。但是生之在同时是死,每一出生的东西,始于生,也已入于死,趋于死亡,而死同时是生。”[8]生存还是死亡,无论人类如何不断进化,不断自我完善,这个问题总是如梦魇般萦绕在人的头脑中。正如海德格尔所表述的那样,人类永远无法摆脱这两者其中的任何一个,生与死的矛盾是人类所面对的终极矛盾。在《安》与《窦》中,两位悲剧女主人公虽然身份不同、经历不同、身处的环境不同,但是最终都是以死亡为自己的命运涂上了一抹最浓重的悲剧色彩。但面对生与死的冲突时,两位女主人公的态度并不相同。
安提戈涅从一开始就对自己死亡的结局有清醒的认识。死亡,从她决心埋葬自己哥哥的那一刻起就成了悬在她头顶上的剑。她对自己的妹妹说:“让这可怕的风险降临在我和我的愚蠢上吧,大不了就是光荣的死去。”[3]195面对克瑞翁对她的死亡裁决,她选择了坦然接受。当死亡之剑还未落下时,安提戈涅心中的无畏代表了生的自觉。生与死的矛盾冲突虽然并不是剧作想要突出表现的,但它在剧作的开端就显露无遗并逐步深化。两者的冲突爆发在安提戈涅行刑前。她清楚地感知到了死亡的迫近,死亡就要吞噬她时,她对生产生了无限的留恋。“这如钻石般璀璨的太阳光将会是我眼睛里最后的光亮……我还没有在充满祝福的迎亲歌中感受幸福的痕迹,也没有听见任何人为我唱起悦耳的洞房歌,就这样带着遗憾与不舍嫁给冥河之神。”[3]215无论是之前安提戈涅表现得无畏与果敢还是此时对生深深的眷恋,我们都能从生与死的冲突中感到一种强烈的悲壮感。“死亡来自生命内部,内在地与生交织在一起。再任何一个时刻,我们都在走向死亡。”[9]死亡的威胁一直存在并永远处于逐步逼近中,生与死的交锋是人类永远无法避开的矛盾冲突。如果毁灭是一种必然,那么对生的不舍无疑体现了一种最残忍的殉道。但即使如此,我们看到,无论是面对法令的威胁、克瑞翁的逼问还是即将到来的死亡宣判,安提戈涅既没有向克瑞翁求饶,也没有在死亡的面前表现出认命地绝望,而是选择了勇敢面对。生与死的冲突产生了一种张力,让我们在直面死的同时也产生了对生的留恋与敬畏。
如果说安提戈涅是主动拥抱死亡,那么窦娥则是被动地走向死亡。窦娥“捱千般打拷,万种凌逼,一仗下,一道血,一层皮。”[4]24此时生与死的冲突第一次摆在了窦娥的面前。在生与死的分岔口,怕婆婆挨打的她选择了认罪。即便是上刑场,她还要求从后街走,怕被婆婆看见,冷静理智地考虑婆婆的感受。窦娥并没有展现出一个年轻女子应该有的对于生命的留恋,而是到死也要表现自己的孝道,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封建伦理。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如果描写窦娥对自身生命的热爱与拯救其婆婆性命愿望之间的矛盾,也许会构成内在的悲剧冲突。这一点尽管如此重要,剧作者却没能将其把握住。”[10]364她的哀怨与痛苦也不是因为马上就要消逝的生命,而只是觉得自己遵守了三从四德却依然要承担违背封建纲常的罪名。对伦理纲常的死守使生存变得毫无意义,而最终窦娥对天发出的三桩誓言也并非是生的抗争,而是对现世的认命与哀叹,这是对死亡的消极的躲避。这种躲避与无奈激发了人们对恶的厌恶以及对善的无限怜悯。生与死的矛盾冲突在妥协中变成了死亡的单方面胜利,只让我们感觉到了对死亡的恐惧却没能激发对生的渴望。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能够看到,当生与死的冲突同时降临在两位女主人公的身上时,安提戈涅的结局揭示出死亡的必然性与人类顽强的生命力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贯穿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而在窦娥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在中国传统的“来生”观念下形成的一种消极生死观,“在此观念下……现世生活的痛苦与不幸是短暂的,亦是可以忍受的,因为可以在死后或来生获得补偿”[10]381。所以在窦娥的身上,并没有表现出安提戈涅身上那种生的顽强意志,生死冲突表现的也就没有那么强烈,无法彻底地揭示出人类发展长河中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与死亡的冲突碰撞所投射出的永恒意义与悲剧色彩。
三、女性的社会存在与自我意识的冲突
造成安提戈涅与窦娥悲剧命运的原因虽然各不相同,但是作为女性主人公,她们在剧作中所面对的社会环境无疑都是恶劣的。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西蒙·波伏娃曾经说过,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11]。可见社会环境以及在社会中所形成的成见、习俗等各种外在观念对女性的塑造和影响。对于安提戈涅与窦娥而言,带有强权性与压制性的社会环境使得她们的社会存在是艰难的。而面对这样相似的社会环境,两位女性主人公的行动与选择表现出的却是不同的自我意识。
伊斯墨涅对于姐姐一心想要违抗克瑞翁的命令埋葬哥哥的想法表达了自己的担忧:“首先,我们时刻记住我们是女儿身,女人生来斗不过男人;其次,我们身处强者的统治之下只好服从这道命令。”[3]194伊斯墨涅的话从侧面反映出了女性在当时社会境遇下的艰难。面对由男性话语以及男性所掌控的社会强权机制,女性被排挤至社会的边缘。而面对这样一种重压,女性自然处于毫无反抗能力的弱势地位。这种地位迫使女性采取了一种默认与隐忍的态度。通过安提戈涅极其不满的对答我们可以看到,她的自我意识在这种社会存在中反而被激发了出来,她的这种自我意识是对强权的挑战,也是对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存在的抗争。剧作家对这种冲突下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给予了热情褒扬。
安提戈涅与克瑞翁的正面交锋是她直面权威与压迫并与之抗争的一次冲突的集中爆发。面对挑战自己的权威且没有丝毫悔意,只是一心求死的安提戈涅,克瑞翁的怒气在于他认为自己的男性权威受到了挑战。所以他说:“要是她举起了胜利的高杆,而不受到任何惩罚,那么我就变成了女人,她倒成了男子汉”[3]206,“从今以后她们应该乖乖的当女人,不准随便走动”[3]209。这种言论是男性权威对于女性身份的藐视与贬低,强调女性在社会体系中的一切应该由男性规定。而安提戈涅的顽抗与不屑就是其自我意识的体现:她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被强权压制。
窦娥所承受的男权文化压迫更是深重。她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被自己的父亲送给蔡婆婆抵债;她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为丈夫守节,而是被逼屈从于张驴儿父子;她更是无力反抗统治阶级强加于她的死亡裁决。“爹爹,你直下地撇了我孩儿去也。”[4]5窦娥的啼哭与控诉是她自我意识的萌芽,但这种萌芽是十分脆弱的。在强大的男权秩序下,这种自我意识很快就被孝与节的伦理纲常取代了。
张驴儿与窦娥对簿公堂,在封建统治系统下,这场对峙更像是窦娥自我意识的回归。她深知自己无罪,也不屈从于毒打,面对张驴儿与楚州太守的双重压迫她依然义正词严。这种自我意识表现出的是反抗意志。但随后,窦娥的自我意识在孝节观念的压迫下被瓦解了。这之后,窦娥身上的自我意识就再也没能复苏。在走向刑场的途中她没有对生命的留恋,没有反抗。她被动地接受了死亡的裁决,被动地站在刑场上谴责老天的不公。鬼神申冤看似体现了她死而不灭的生命意志,实则延续了女性作为弱势一方的存在状态。申冤也并非剧作家赋予她的自我意识,而只是借她的申冤表现善恶终有报的民间传统观念。女性的社会存在与自我意识的冲突在此完全被消解了,变成了形而上的善与恶的冲突斗争。
在索福克勒斯与关汉卿的笔下,两位女性主人公都承受着女性的社会存在与自我意识的冲突,但冲突的结果却截然不同。《安》用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强化了二者的冲突,也突出表现了自我意识对于人类的重大意义:自我意识是对自我价值与自由选择的肯定,这种自我意识是人类尊严的体现。而《窦》虽然也涉及了二者的冲突,但这种冲突最终却因为自我意识的缺失而达成了一种和解。二者之间短暂与微弱的冲突弱化了人类的精神力量与主观意志,作者用窦娥这样一个女性角色的社会存在展现了弱者面对强权时的软弱无力。
《安》和《窦》虽然同属于展现女性悲剧的作品,剧作中也展示出了相似的矛盾与冲突,但其精神内涵以及表现形式是存在差异的。《安》中所反映的悲剧冲突因为揭示出了人类所面对的普遍矛盾而更具永恒性。在《安》中,面对安提戈涅的悲剧,“我们对他们面临毁灭时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他们坚决维护自身价值所做出的壮烈举动感到既惊讶又羡慕”[12]62,而《窦》只是揭示出具有时代特征的矛盾冲突。窦娥作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使我们更多的只是产生了一种痛感与同情。这种冲突带来的恐惧与痛感,正如黑格尔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有限的、平凡的,消极的感情”[12]72。可以说,在揭示人类面对的永恒的冲突与矛盾,并引导我们思索人类的存在价值与生存之道方面,《安》更具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