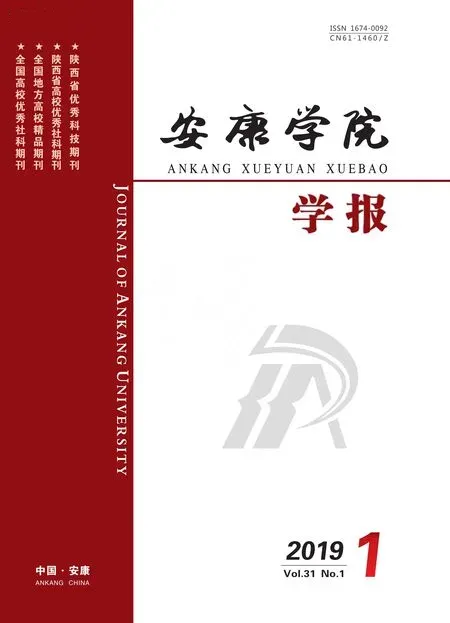“性”与“伪”:荀子“性恶论”的概念架构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一、荀子“性恶论”的基本思想
时人所言“性恶论”,顾名思义,人性本恶也,与之相对的便是“性善论”。纵观中国古代人性论的发展,这二者与其说是在回答人性是什么,不如说更侧重阐述人性是怎么样的。正如唐君毅先生所言:“至于中国古代思想之克就人之自身而言人性,则又始自即就人之面对天地万物,与其人生理想,以言人性。由此所言之人性,在先秦诸子中,或为人当谋所以自节,以成往而与天地参者,如在荀子;或为人当谋所以自尽,以备万物,上下与天地同流者,如在孟子。”[1]
孔子之后,时人所言人性,无论是“善”,抑或“恶”,总是侧重于其在伦理维度中的阐述。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言:“自来论性者,并非专为研究性而研究性,而是为讨论修养、教育、政治,不得不讨论性。在应如何施教等仅为政,需先看人之本来状态是如何,于是便提起性的问题;而亦如此,乃特别注重人本来是好或不好。即性与善恶的关系。在形式上是问:性是善的亦是恶的?实际上却是问:善是性亦恶是性?所注意者不在性之实际内容,而在善恶之起源。其目的在探究善是固有的还是外烁的。中国性论所以特重性善或恶的问题,实际因为根本上所注意者,原在于善与性之间关系。”[2]“推天道以明人事”是中国人骨子里便流淌着的实用性取向,或与后世马克思所持的“实践性”不谋而合,而此,亦恰合笔者文以时而作的行文习惯。这“时”既蕴含了时间绵延的一维性,也囊括了当世所勾勒的现实。这是符合中国人传统伦理思维习惯的,即将“心性论”写照入生活世界,这恐怕是“心性论”论辩古今未断绝的缘由,也是其意义之所在。
(一)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
1.时代背景
荀子,名况,时人尊而号为“卿”,故又称荀卿,战国末期人。随着井田制崩溃,封建土地所有制始兴起,铁骑牛耕逐步推广。在经济形态转变过程中,周王室衰微,展开了长达两百多年的战争。社会格局不断变革,各诸侯间混战吞并,逐渐形成了区域一统的对峙局面。千古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铁骑践踏之处,蹂躏着人心,折磨着人的道德伦常。征伐无度,在社会激荡下人性的恶相原形毕露。于此,便不难理解,在这样的环境中应运而生的“性恶论”为何会打下现实性和经验性的深深烙痕了。呈孔子“外王”之学,荀子主“礼治”,试图用外在的人为规范来治理社会,将“礼”作为治国之要,治民之本,乃至人类一切行为的准则。事实上,这里的“礼”已经近乎法了。
2.思想渊源
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者,论“心性论”的源头,从儒士的角度而言,应追溯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一悬笔。这个命题,将“人性”点于儒学的长卷上,牵入人们的视野。而之所以言其为悬笔,在于孔子只是沿着从同到异的生成维度揭示了人类“性”和“习”的关系,并由此为纽带,将先天性和后天性统一于“人”这个主体,同时,亦并未赋予其“善”与“恶”的属性。虽然,从其“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3]91的所持,以及“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3]110等主张中可窥得其向善的指向,但却仍然不可断言其完全承认“人性”的伦理维度。恰因此,为后世在伦理向度中发展“心性论”留下了空间。某些学者认为,沿着“性相近”的路子发展,便有了“性善论”,如孟子所持人皆有“善端”之说;而相对的,沿着“习相远”的路子发展,便有了“性恶论”。这个看法有一定合理性,不过,笔者以为,若因此便推断孔子持有“性具善恶”之说恐太过草率了,毕竟,后学对“性”的定义随着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皆有所不同,凭此反推孔子所持的“性”,并不构成充足理由。
此外,荀子明确以自然禀赋的材质为“性”,亦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道家顺“道法自然”而下的人性观,如庄子所言“素朴而民性得矣”[4],且论述为:“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5]432-433,成就其“性者,本始材朴”之观。其《正名》所载:“‘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欲不可去,性之具也’。”[5]487-507由此观之,其以“情”乃至“欲”为“性”,即以此二者为“天”,是故《天论》又称:“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夫是之谓天情”[5]365。由是,不难得出“此情性观与早期儒家‘性自命出’一派的思想有关”[6]177这一结论。但是,早期儒家以“情”为“天”之观念所引出的是“自然主义和情感主义”的生存格调,显然,荀子并未沿袭这条路数,而是开拓出“人之性恶”这一新的疆域。
(二)“性恶论”的含义
开宗明义,于荀子而言,“性”所指为何?
蓝泽南城撰作《荀子定义》一书,其中有“性论”。据藤川正数的整理,南城主张今之学问者都要了解孟荀之性说,若互相比较,孟子所谓“性善”者是好义之心之异于禽兽者,而荀子之所以主张“性恶”,是因为他在性中取与禽兽同然者。不过,因为荀子屡次说明人能化性,此点是“性恶说”窒碍之明证[7]。
持此论而责难荀子理论逻辑混乱者,学界不在少数,那么果真如此吗?
先秦儒学“性善论”之倡导者,应自孟子始。公都子所举告子“性无善无不善”皆是指对于“性”之内容的判断,然而对“性”之定义尚不明确,实为外延定义。而后,告子所持“生之谓性”,实乃言“性”为人与生俱来之生理本能,如知觉运动之内容。不同于此,孟子由人不同于犬牛这一命题推论出必有不同之“性”,其认为,大凡一切生物,皆有其本性,而人之所以为人,乃是人具有“仁、义、礼、智”之内容,即人之本质。故而,孟子所言“性”,实为内涵定义。
《正名》道:“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5]487《性恶》载:“‘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目明而耳聪,不可学,明矣’,‘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5]515-517更有《荣辱》称:“饥而欲食,寒而欲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5]74,“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5]71。
由是观之,荀子之“性”,似乎类同于《孟子·告子》中所载的“生之谓性”以及“食色,性也”[3]305的属性特征。人作为一个生理生命之存在,“性”普遍存在于每一个生理生命之本能中。就先后而言,“性”是先天具备的,生而便有,而非后天所习得。就内容而言,以“目明而耳聪”为例,“性”所囊括的是人类的原始欲望和追逐欲望得到满足的自然本能。就其追逐欲望得到满足的自然本能及其衍生出的趋利避害的本能而言,圣人和暴君,君子和小人等是无差别的。这一点,恰暗合了孔子“性相近”的命题。
比起孟子所持的“人生而有善端”的道德唯心论调,荀子对于“性”的解读更趋向于一种中性色彩。对于“性”本身而言,是人类生而便有的自然属性,其存在的事实无可厚非。在这一层面上,荀子并未将其强行扯入伦理领域,相反,他是承认人类这一属性的存在的。如《礼记·礼运》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8]
既已明“性”,那么,何为“恶”呢?“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5]513-514
荀子看来,人生而“好利疾恶”,这种类趋利避害的本能,会经由某个环节而最终导致社会无辞让之心、忠信之义及礼义文理之教。那么问题来了,这个环节所指为何呢?文本中有“顺是”这两字,字面直译大概为“顺着这个”。为何说顺着“性”便会引发如此严重的社会困境呢?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义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5]409-410
由此,便明了“顺是”的语境意应为顺欲而无节度,近乎“纵”这个字的意思了。作此解,也恰应和了郭齐勇先生将“从人之性”的“从”作“纵”解的意图了[6]180-189。诚然,人生而有欲,追求欲望的满足是人的自然本能,从这个角度来说,并无对错可言。然而,世人皆从忙里老,几人肯向死前休?这欲望,无疑是一簇熊熊燃烧着的烈火,一方面可作为人行动的源动力而存在;另一方面,若靠得太近亦会引火烧身。而对这个“度量分界”的拿捏,便关乎前文提到的“某个环节”。若为纵欲而不知节,必然“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5]514,而此等社会现实放入伦理领域便是“恶”。故而荀子言“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5]513。笔者以为,荀子所言“性恶”,应为纵性而不知节然后恶。这是一个综述概念,将人的自然属性放入社会领域中,揭示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的产生便将人类无节度的欲求本能引入社会伦理领域,且赋予其“恶”的价值判断。
于此可知,荀子所言“性恶”乃发生历程之判断,而非本质意义之定义,故不可“以恶释性”,进而“以性释人”,若将荀子所谓“人之性恶”理解为人之本质为恶,乃是“倒果为因”。
(三)“性恶论”在荀子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意义
“性恶”的提出,只是一个概念的生成么?不然。
如荀子言:“故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5]520-521其点出探究人类自然属性和群体生活下所赋予的社会属性之间的矛盾,是为了解决现实中欲望横流而造成的偏险悖乱之社会恶相。于是,便有了“化性起伪”之说。“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5]517-518,以师法之化和礼义之道使人们“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5]514。由此,可以看出荀子强调后天道德习得过程对人“性”的教化作用。即认为,所谓道德,是经过人后天思虑的积累和官能的反复运用然后形成的行为规范。所谓礼仪,是由圣人所制定,人们通过学习和践行而逐渐内化为一种道德品质。
后世有人批判荀子“化性起伪”的“伪起者”站不住脚。持此论者认为,既然人性本恶,无善端,圣人又何从起伪呢?
首先,荀子所言之“性”,并非区别于动物的类社会属性的“人性”,而是指人的自然属性。其次,所谓的“恶”,是将失去节度的自然本能放入社会生活领域中作出的价值判断。而“善恶”本为相对概念,在认识到什么东西对于社会群体性的生活秩序而言是“恶”的同时,自然也会认识到维持建构此秩序所需者名唤“善”。这个认知是一个过程,是人类拥有自我意识后,试图站在高于自然的位置上,从心性论的角度去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自然人拉入社会领域而逐渐得出将其社会化而需要依照的规律或准则。合乎规律的便是“善”,反之,便为“恶”。这个社会化的过程,荀子称为“伪”,即化恶存善的过程。
至于“圣人”如何区别于常人而拥有“化性起伪”的能力,笔者以为,即便荀子列出了些古圣先贤的名字,我们也不应将圣人局限在某个个体身上。这些名字应只是代表了社会中一部分群体,综合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考量,于经验世界中锻炼出从某些方面而言高于常人的认识能力。相应的,这群人制定礼仪也并非凭空而生,想必是基于对前文所提及的“矛盾”之认知以及对解决“矛盾”的诉求之省察,结合现实经验而最终落笔成卷,敲定出“礼仪”的条款。
综上,“性恶论”既非荀子对人之所以为人即人之特质的诠释,更不是荀子价值理论之最后依归处。荀子所言“性恶”,是对经验世界中普遍现实之人性(nature)之掌握,同时也是达至治世之政治工具与手段。故而,“性恶论”虽然无法断言为荀子整套理论体系中的核心,但无疑在这座名为荀子理论的楼阁中起着奠基性的作用。由此作为逻辑前提,顺理成章地阐释出“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观和“隆礼重法”“强国裕民”的“外王”思想。
二、理论价值:对当代人性论理论建构的意义
法国学者阿尔凡斯·博瓦思特 (Boistel,Alphonse Barthelemy Martin,1836-1908) 在其所著《天然法》中提出了“人格”与“性”的概念[9],而细川润次郎将其译为“ペルソナリデー”(即personality) 和“ナチュール”(即nature)。按细川所解,“人格”是“人之所以为人者”,而“用意熟考”则是从此呈现,相对的,“性”则指“在精神中应物直发者”,是“属于人的精神之下位者”。如其所言,这种“性”基本与动物的欲望属于同一水准,不同的只是人类还有其他不同的欲望而已,因此,人之所以能够保持人的特质就是因为“人格”严重控制“性”的发泄。故细川说此“性—人格”的关系就符合荀子所提出的“性—伪”的概念架构[10]。
此看法有一定的合理性,承认了人自然属性的存在,且意识到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之间的矛盾。问题在于,“伪”完全等同于精神层面的“人格”么?人之所以保持人的特质,只是因为“性”的发泄受到“人格”的严重控制么?
首先,所谓“人格”,指的是当人产生自我意识时看到外物与我相异,从而产生的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草木的意识,属于精神层面的辨识。而荀子所言“伪”,乃“师法之教”“礼仪之化”,源自对人类所具有的双重属性及其矛盾的反思,故而一开始,便有了禀形而上且流散入形而下的双重指向。于此,便可明此二者不尽相同。
其次,荀子解“性”为“欲”,实则是对人自然属性的揭示。即,人生而具有好利嫉恶、趋利避害之本能,且总是自觉不自觉顺本能而行以足欲。而其“从欲而不知节”投入社会伦理领域,便有了“恶”的价值判断,故而需要“师法之教”“礼仪之化”来去恶存善。其中,若单看“从欲而不知节”,的确容易导向只要严格控制欲的发泄便可去恶从善这一路径,然而,问题在于只要控制住欲望,人格便足以保全了么?换言之,对于人而言,区别于外物而成就自身者难道只是在于欲望的自控么?这显然是不具足的。如前文所言,与荀子对“性恶”的定义乃发生历程之判断而非本质定义,故不可“以恶释性”进而“以性释人”,荀子关于“伪”的提出亦是基于社会现实而对人类善性之由来进行考量的结果,从一开始便不是对所谓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抑或称之为“人格”的本质意义之定义。故而以“人格”释“伪”,未免草率了些。
性者,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者也;伪者,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前者强调生物本能,后者强调人文化成。荀子虽以“性”“伪”二分区别先天本能与后天人为,但若因此将恶归于天生,将善诉诸于后天,以至于将荀子之“伪”理解为仅是客观化的后天人为构设,未免失之过简。“性”固然无所谓善恶之内容,且就礼仪法度之“伪”而言,其亦未必全然是善。但是,荀子肯定了“善”必从“伪”中生发。“性”无礼义且不知礼义,便不可能成为创造礼义之价值根源,故而荀子认为,创造礼义之善者乃生于人之“伪”,而且是“圣人之伪”。由此,便有了“善之所由生”的双向通路,即“积思虑”和“习伪故”。前者指内在主观意识不断思虑反省,从而建立起一套自我主观之价值准则,而后者指效仿先圣所制礼义法度。一方面,肯定了客观存在的先圣所制之礼义对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更强调了在继承传统礼义的过程中,亦需要主观道德意识不断地反省思考已然客观存在的礼义法度与社会现实之需求的相洽性,从而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形态。故而,荀子曰:“礼者,人道之极也”[5]421。由此观之,所谓“礼”乃出于圣人所制,而后人若可在礼中思索、互易,又加好之者,则亦可以称之为“圣人”。前者是道德完备的理想人格之完成者,而后者则为臻于理想人格之未完者。是故,“虑”与“伪”便是“途之人可以为禹”之功夫历程,亦为“化性起伪”所以可能之关键。
综上,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其一,荀子基于社会现实,不以先天善恶论人,而将人作为客观的认识对象投入生活世界,省察并承认其固有的双重属性,从其社会实践中揭示出其善恶的由来。这种基于事实判断而作出预设和得出结论的理论思维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空谈妄论的可能,于当今人性论理论建设而言是具有启发性的;其二,荀子不以性论人,而以人论性,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将人们的视野由“天”拉回“人”本身,区分了客观的实然和道德的应然,将善恶的判断回归于人自身,从而揭示出道德主体具备双向选择的可能性。这就为当代人性论理论架构中如何区别人性与善恶的关系、善与恶的关系,乃至如何存善去恶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三,荀子“化性起伪”的提出,标志着人们由趋利避害的直接本能逐渐过渡至更有长远性、计划性的道德规约,而此规约起于人且传于人,这也为当代人性论理论架构中如何指向实践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