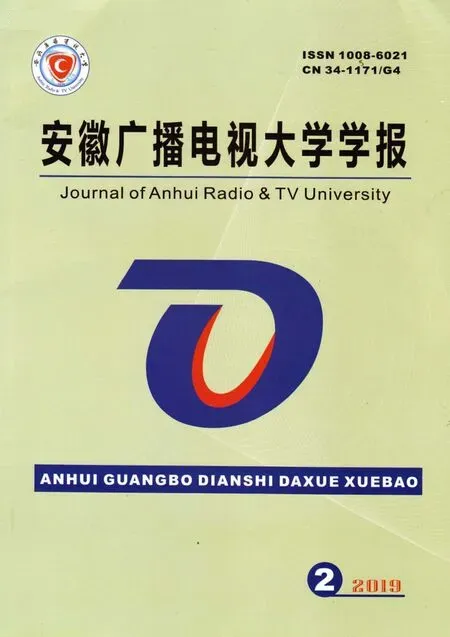关于徽州文化发轫阶段的研究
江声皖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 黄山分校,安徽 黄山 245000)
“徽州文化崛起于南宋、鼎盛于明清”, 这已成为徽学研究的定论。围绕着这一定论,“从改革开放以来至今,徽学的研究已出版各种专著近600部,发表论文近万篇”[1]。这些研究均是针对延续保持了800年的徽州行政地域所呈现出的一种地域文化而进行的。
然而徽州文化实际上兼具地域文化与全域文化的两种特质,言其为地域文化,是因为她确具备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表现,地域烙印明晰,具有独特性。指其为全域文化,理由是徽州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全局上,也具备代表性。即如果从徽州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来进行观察,来进行研究,更容易看清中华文化连续发展而未中断的特征。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连续未断的文明,因而连续发展而未断便正是中华文明最为显著的特征。而要观察清楚,研究透彻徽州文化的这一兼具的特质,便必须从徽州文化发轫阶段的研究中来探本穷源。因为徽州文化发轫阶段,便正与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过程中的儒家文明、游牧文化及南蛮文化三大文化板块位移重构的轨迹相吻合,而这一历史阶段便也正是后被更名“徽州”的这一地域的新安时期。
在此时期内,集大成,继道统而走上经典地位的理学思想嫩芽;由邹鲁礼统转化而来的“礼失求诸野”之礼仪;由北方百姓的南迁,在篁墩立足后溢向新安全境的宗族文化;在南移汉人与土著少数民族碰撞融合过程中形成的尚武风俗与爱国观念等等都是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儒家文明、游牧文化及南蛮文化三大文化板块位移重构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徽州文化便与邹鲁文化一样,是中国传统文化链条中有代表性的一环,是其发展的典型标本之一。所不同的只是邹鲁文化是儒学源头的文化标本,而发轫阶段的徽州(彼时名新安)文化则是儒学复兴的文化标本。正因为如此,历史上,人们才会赋予徽州“东南邹鲁”的称号。
综上所述,对于徽州文化历史渊源的表述则应修订为徽州文化发轫于南北朝,崛起于南宋、鼎盛于明清 。但问题是,徽州文化发轫于南北朝,真的有能立足的证据吗?
一、徽州文化发轫于南北朝的研究古已有之
纵观历史,关于徽州文化发轫于南北朝的研究实则古已有之,只是古人是从理学先驱程颢、程颐的祖籍考证的角度来提出问题的,走的是一条迂回的道路,即试图从文化的家族传承上来证实徽州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链条中的代表性。从元代到清朝,相关学者与程氏家族进行了大量的文献考证与族谱编纂工作。
但苦于“魏晋南北朝,则是一个文献和考古资料都极度匮乏的时代,这一时期在中国古代书写史上很‘不幸’地处在纸张广泛使用,而印刷术尚未发明的历史阶段。依靠手工传抄的大量图书文献,既无法如秦汉简牍那样历经岁月而长久保存,又不能像宋元典籍那般通过版刻印刷化身千万。”[2]故而相关学者只能从碑刻与墓志中去寻找史料,终于在《宋宜春县令追封冀国程公元白神道碑》中找到了一段文字,其中有“中山之程,出自灵洗,实昱裔孙。仕于陈季,陈灭散亡,播而北迁。”[3]因为这碑文是北宋名臣欧阳修为“二程”族叔程琳的父亲所撰,对“二程”祖籍的研究很有价值。碑文证实了相关学者与程氏家族后人的猜测,即定居于河南中山的程氏一族为南北朝新安篁墩人程灵洗的后代。
程灵洗是《陈书》《南史》与《资治通鉴》上均有正式记载的一个历史人物,是“侯景之乱”时保家卫国的一位大英雄。他先是被当时的梁元帝授予象征皇帝的权杖,任通直散骑常侍,都督新安诸军事。辗转归陈后,他率领以新安人为主体的一支劲旅,奉“佐国安民”的宗旨,两战王琳,平叛华皎,抗击拓跋定,攻克沔州,屡屡打赢入侵的北寇,甚至罕见成功地收复了部分失地。
程灵洗最后病故于郢州刺史任上,被追赠镇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壮”。 他死后,军队由长子程文季统领,一直在湖北、河南一带苦战。陈国灭亡后,以新安人为主体的这支军队最终解体,而存活下来的将士,其中自然包括在军中任职的程氏子弟(程灵洗有20个儿子,仅其一支,在军中任职的人数就极其可观)自然而然地会散落在这一带定居,并繁衍生息。这便都与欧阳修所述的“陈灭散亡,播而北迁”相吻合。
但由于这是孤证,当有学者试图建立包含“二程”的明确而清楚的谱系时,却反而在程氏宗族內部爆发了纷争,使得这一看似确信无疑的结论成了千载之疑。谱系上存留的千载之疑,便也使关于徽州文化发轫于南北朝的研究失去了一个可借以用力的踏石。因为,在古人看来,若要研究清楚徽州文化是否真的发轫于南北朝这一问题,便不得不要率先厘清“新安理学”与“理学”的关系; 而要厘清“新安理学”与“理学”的关系,似乎又必须先厘清理学创始人“二程”“一朱”与徽州抑或新安的宗族关系。
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与徽州,抑或新安的宗族关系不难讲清楚,诚如有学者所言:“新安理学作为朱熹理学的重要分支和一种地方性哲学流派,既是理学与徽州社会地方特色和时代要求相结合的产物,又反过来对徽州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4]而实际上,要找到“新安理学”乃至“理学”在南北朝时期发轫的源头,并不一定完全据谱系寻根问祖。我们不妨换一条思路,从宏观世界切入,以南北朝时期的三大文化板块的位移与重构为依据,直接让记录新安地域居民意识形态的相关文献说话,来破解这一难题,使孤证不孤。
二、南北朝时期三大文化板块的位移与重构
比较全球各古代文明的发展,被称为世界四大文明的古国中,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连续未断的文明。但实际上,中华文明也曾经遭遇过中断危机的,这就是南北朝时期。对于儒家学者如张载来说,这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中,“往圣”已成“绝学”:儒家圣人之学,自两汉以下,而魏晋,而南北朝,甚至到隋唐,千百年间,一直未能妥善地传承先秦儒家的学脉了。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呢?这是因为自晋至南北朝,中国四分五裂,南北分治,各路豪强为争夺皇权,频繁反复地发动战争,致使整个九州大地,战云密布,生灵涂炭。从东晋至隋的近200年间,北有五胡十六国,南有宋、齐、梁、陈,四个王朝兴亡交替,导致大量的族群迁徙,因而使得九州大地上,原有的文化板块发生大幅度的位移。
提起文化与文明的差异,中国自古就有定义,《礼记·王制》中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这讲的是文化,论者把九州大地上的文化分成了五个板块[5]。而到了南北朝时期,我以为用三个文化板块就可以概括,那便是原来位处中原的儒家文明文化板块、长城以外的游牧文化板块与原居住着百越的南蛮文化板块。而对于文明,则有古代学者孔颖达作出了注解:“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 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这就是说,同样是文化板块,文明程度是不一样的[5]。
在中国古代,不可否认,“一定程度上儒家文明就代表了中华文明”[6],它位处中原,以自己的华美影响着周边的文化。但文明板块也有自我颠覆的时刻,西晋的“八王之乱”引发了北方游牧部落的南下,从而使长城以外的游牧文化板块随着五胡十六国的交替而位移到了儒家文明文化板块区——中原,这当然也包括了儒家文明发祥地——邹鲁。而原来位处中原的儒家文明文化板块则随着三国至西晋末年几百万北方人口的南迁而位移到长江以南,甚至到达了南蛮文化板块区。
如此的文化板块位移是潜藏着中华文明中断危机的,因为从军事上来讲,在这长达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存在着“北强南弱”的现象。更何况正因为儒家文明失去了它原所占据的道统地位,致使玄学兴起、道教勃兴以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而最为严峻的挑战是,由于佛教的急剧兴盛,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了不可预测的变化。
在这个历史阶段,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来到了它的转折点。其转折的去向有三种可能:一是被游牧文化所吞噬; 二是由外来文化,如佛教所融化; 三是以儒家文明为基础,由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作用,吸收其他文化的精髓,形成新的知识、思想、信仰体系,从而使中华文明的发展非但不中断,并从此跃上一个新台阶。我们中华民族的先人,以其自觉的传承意识和传承实践选择了上述转折去向中的第三种可能,以“新儒学”即“理学”继承了“儒学”的道统,取得了文化板块大幅度位移的最佳重构结果,实现了儒、佛、道的文化大融合,保住了中华文明的连续不断。
其后的许多中华文明的要素,都可以从这一历史时期中找到发轫的源头。徽州文化自然也不能例外,其最重要的内涵“新安理学”嫩芽的被催生,演奏的便正是整个中华文化转折、发展的一段主要旋律。
三、文化板块位移,致使南蛮文化板块区播下了儒家文明的种子
作为儒家文明文化板块位移南下的前锋,孙权麾下的威武中郎将贺齐是为“讨丹阳黟、歙”而来的。当时这块土地上,“歙贼帅金奇万户屯安勒山,毛甘万户屯乌聊山,黟帅陈仆,祖山等二万户屯林历山。”是山越土著与逃亡汉人的天下[7]。而南蛮文化板块区的文化特征是“断发文身,刀耕火种,住干栏居”; 是“依阻山险,不纳王租”; 是“好为叛乱,难安易动”[7]7。显然,南蛮文化板块区的文明程度要远远低于儒家文明,因此它的被同化,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
文化板块的位移便意味着战争,讨伐虽然也是残酷的,一次战斗便“凡斩首七千”[7]9;但这两个文化板块的碰撞,并未出现那种发生在中原的、近乎灭绝种族的血洗千里、屠城毁屋、饱则奸淫、饥则宰杀的野蛮行为。而代表儒家文明的外来者,取胜之后,便也采取了有计划的移民,安顿流民以发展生产:“绥辑流民,疏通畎浍,教民孝悌力田”[3]22。可以看出,这与长城以外的游牧文化板块位移到儒家文明文化板块区的情况有很大不同,虽说也是入侵,也有杀戮,但却不是那种试图灭绝种群的血腥大屠杀。新移民所带来的农耕稻作,有着明显推动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
从开始的“新都郡”“始新县”,尤其是东晋以后易名的“新安郡”“新宁郡”这些行政区域的命名来看,外来者的意图很明确,即要使这个区域里的居民安宁下来,开始新的生活。其实就已蕴涵了儒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仁政与民本思想,对主导新安地区民众的意识形态无疑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得不提到程元谭,他便是在东晋立国之初,即南北朝拉开序幕的时候来新安郡担任新安太守的。这位因北方动乱而南逃的儒家士人,秉持一颗勤政为民之心,以卓越的才智,整顿吏治,为民办实事,办好事:实行仁政,向朝廷推荐有才能的人,发挥他们的聪明才干;发动和组织百姓疏浚河道,兴修水利,垦荒种粮;悯农爱民,曾向灾民散发了两千石粮食,安抚流离失所的灾民;开办学校,培养人才,教导百姓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教化风气。因而当他任期期满,离开新安,临别之际,闻讯从四乡八邻赶来慰留他的新安民众挤满了大道,使他竟然无法离开。晋元帝获悉后,甚为欣慰,下诏褒奖元谭公,并让他继续留任新安太守。他去世之后,其子孙又因皇上赐宅第于新安篁墩,自此便留在新安篁墩安家[3]22。
从程元谭的事迹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文明落地生根的过程。历朝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这一区域地方官的选授。罗愿在《新安志·叙牧守》中综述道:“自建安中置郡,不轻选授。故梁高祖尝谓徐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诸人并经为之。卿为我卧治此郡。’……是以六朝置守,多一时名胜。”[7]11罗愿笔下的“名胜”并非指的是有古迹或优美风景的著名的地方,而是对有名望的才俊之士的美称。譬如梁武帝口中提到的新安太守任昉,便是南北朝著名的文学家和地理学家。他为官清廉,体恤百姓的事迹人人皆知。有一年地方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洪水,他身为太守没有把老百姓扔下不管,而是把自己家里的米全拿出来,熬粥分给大家吃,救活了几千人,还挽救了很多婴儿的生命。自己与妻小却只能吃一点点粗粮充饥。 所以梁武帝对准备派到新安去任太守的大诗人徐摛讲,新安郡那个有大好山水的地方,经任昉等多任太守的治理,已是越发太平无事、风光怡人。你这次去,就只管躺卧在那里顺势而为,清闲自在地过快活日子吧!
由此可见,经历近200年的教化熏陶,文化板块位移,不但在南蛮文化板块区播下了儒家文明的种子,而且因为此地远离战争与纷乱,俨然成了儒风浩荡的儒家文明模范区。
应该郑重指出,在各地战事连绵,一直无法妥善传承先秦儒家学脉的南北朝,这肯定是一个特例。同时也证明,新安文明确实起到了延续将断未断的中华文明的作用。所以,我们说,这之后的“新安理学”“理学”和徽州文化发轫于斯,绝非妄下断言。
四、文化板块位移,重组了新安居民的结构,重塑了新安居民的品质
新安郡成为儒风浩荡的儒家文明模范区以后,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居民有着什么样的品质特征呢?
在原来的南蛮文化板块区中,新安的地理位置有着特殊性。它地处万山之中,“万山回环,郡称四塞”“略无平处”,因而不利大部队行动,所以尽管天下大乱,到处战火纷飞,这里却是“战争罕见之地”,往往“无兵燹之虞”[7]13-14。它又位居南蛮文化板块区偏北的一端,与南朝的京都及前线都最为接近,并且有“大好山水”, 这就自然吸引来了从儒家文明文化板块区南迁的名门望族。同时,也使在此地任职的官员们乐意在这块“世外桃园”选择自己家族的居留场所。长而久之就逐渐改变了新安居民的构成,重塑了新安居民的品质。
如徽州方氏始迁祖方纮,世望河南,为汉司马长史,于西汉末年举家迁来,“遂家丹阳,……歙之东乡”。其次子方储“举孝廉,授洛阳令,赠黟县侯。”后裔由歙县东乡向西扩散,成为显姓[7]14。又如,汪姓始迁祖汪文和,世望平阳,“以破黄巾功为龙骧将军。建安二年,因中原大乱,南渡江。孙策表授会稽令,遂家于歙,是为新安汪氏始迁之祖。”其后人向四方发展,终于成为徽州第一大姓[7]14。
当时新安以北长期战乱,恶劣的时候非但人杀人,甚至人吃人,可以讲是人性尽丧,因而儒家最为重视的礼统便也在这些地方崩塌不存。但正所谓“礼丧求诸野”,而相对安定的新安便成了这能寻访到先贤遗风的“野”。 因为从中原南来的望族往往是举族而迁,来到这民风强悍的山区之后,又是聚族而居,自然而然地要把儒家的传统礼制、传统道德带来新安,代代传承,对内凝聚族人之心,对外促进与原住民和谐相处。
最为典型的例子要数程氏家族。程家始迁祖程元谭于东晋初年病逝于新安太守任上,其子孙又因皇上赐宅第于新安篁墩,自此便留在新安篁墩安家。那么,他的后裔在新安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一二百年之后,又生活出了一个什么状态,给新安居民带来了什么影响呢?
目前文献史料中可以查的是程茂,他便是程灵洗的曾祖父。在程敏政辑撰的《新安文献志》中保存了他所写的一封名为《责萧衍犯顺书》的信,信中写道:“ 假中郎将、征虏长史程茂,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将军学擅文武,权兼中外,国家之寄,悬于将军。……茂愚懵,意谓将军……过计误听,反斾内向,甘为戎首。……茂实不爱死,敢献腹心!……令闻当以伊霍,为得失之监。不具,茂死罪!”[8]
程茂写这封信历史背景应该是,萧衍为报南齐国君东昏侯萧宝卷杀兄之仇,先是设计拥戴萧宝卷之弟萧宝融在江陵登基做了皇帝,造成国家分裂的局面。而后率军东进,灭了萧宝卷。他也因此而升任大司马,掌管了中外军国大事。但他却迟迟不肯迎萧宝融回京,还相继杀了萧宝融的三个弟弟。且又搬出了宣德太后,让她封自己为建安郡公,在萧宝融未进京之前,代行皇帝权力。此时,正因为萧衍掌握了朝廷实权,故而有人劝其篡位,而萧衍也跃跃欲试,准备向萧宝融所在的郢城发动攻击。出于利害关系,官场上自然是一边倒,大家纷纷通过各种方式向权臣萧衍献媚以示效忠。
然而程茂作为假中郎将、征虏长史的这样一个高级官员,却为了正义,为了国家的稳定冒死给萧衍写了这样一封斥责他“因错误的谋划,错误地听信谗言佞语,而要举旗造反,不惜做发动内战罪魁”的想法。如此的义举,危险是不言而喻的,所以程茂在信的开头就坦率表白:“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在信的结尾也要再一次声明“茂死罪!”
想想看,这样的冒死之举,需要何等的理念引领,又需要何等的道德支撑。这故事中所表现出来的道德价值观,应该就是孔子所尊崇、所倡导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9],亦即孟子所言的“舍生取义”[10]吧!
在程茂身上,我们所看到的,便正是当时新安人的境界和风貌,因为这样的境界和风貌也可以从其他人身上看到。
程茂的儿子程詧在朝廷中担任梁武皇帝顾问,掌管经籍图书,是一个从三品的朝官,也是一名文学家,所作的《东天竺赋》为天下文士广为传诵。他以雪天仍鲜红夺目,经久不落的天竺,亦即南天竹自况,可见其推崇与追求的也是那种傲霜斗雪、不畏严寒、身处逆境而不屈服的崇高品质。
程詧的儿子程宝惠,梁武帝末年被选拔到太学,是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的博士。就因为对梁武帝任用奸佞小人朱异,而后又为准备收留侯景而制造舆论等行为的不满,他竟舍弃高官厚禄,毅然决然“举族还乡”“尽室归黄墩”[3]23。
而新安郡的家乡人也未因此而避凶趋吉地来嫌弃他,倒反而举荐他担任了“仪曹掾”, 即地方上掌握刑律的吏胥。
南北朝时期的新安郡人就已如此崇尚道德,且形成一种风气,这对于其后辈是必然要潜移默化地施加巨大影响的。而作为“新儒学”的“理学”,宋朝时便曾被人们广泛地别称为“道学”,即它是以推崇道德为鹄的学派。“理学”的观点强调,人所应遵循的所有的伦理与道德原则都来源于作为本体的天理,天理不仅是自然世界的自然法则,还是人类社会必须遵守的道德法则。
五、南蛮文化对外来植入的儒家文明添加新品质
儒家文明文化板块与南蛮文化板块的碰撞,其重构的结果自然是相互影响。
现存的文献资料中,在描述南蛮文化板块区的原住居民——山越时,往往都是使用贬损的词语,如“山越恃阻,不宾历世,缓则首鼠,急则狼顾。”“山越深险,皆不宾附!”[7]10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进行解读,便可以窥察到这里描述的,正是山越人热爱自己的家园,不肯屈从于武力征服,长时间地进行反抗斗争的可贵品质。而且他们“临高下石,不可得攻。”使外来的军队“军往经日,将吏患之。”[7]9是一个有着尚武风俗,英勇善战的族群。
很明显,山越人的这种热爱家园,不屈从武力征服的可贵品质和尚武的风俗习惯深深地影响了来自儒家文明文化板块区的“南渡衣冠”们,使之后生活于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在儒风浩荡之中,又增添了一层热血尚武、保家卫国的情怀。依据就是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两场保家卫国战争。一场是发生于梁末“侯景之乱”时的程灵洗聚众卫国,取得反击羯胡全国首捷的事迹。另一场是发生于隋末的汪华揭竿而起,占据六州而保境安民的故事。两例历史事件说明了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新安居民,有着尚武的风俗,有着爱国的思想。这对于其后辈也是必然要潜移默化地施加巨大影响的。
因为若要讲忠义爱国,这并非古圣贤语录中就有。而朱熹及其理学非但在民本思想上还原了孔孟之道,在政治学范畴之内却继承并发扬光大了汉儒的爱国观念。他要为“万世臣子”作“忠义之劝”,要为温情的儒学注入凛然正气与血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理学便正是以民本观念为基础,注入了爱国思想的儒学。再联系到朱熹祖孙三代——其叔祖朱弁出使金国,坚贞不屈;其父亲朱松勇斗秦桧,不惜弃官;他自己支持抗金,怒怼主和派——爱国情怀与爱国事迹来看,不可否认,由南北朝时期延续下来的新安居民的爱国思想,应该也正是朱熹理学发轫的源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