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坚守与和解之间:谈作为“晚期风格”的《黄冈秘密》
■
武汉大学文学院
风格,是作家创作个性的外现,是作家艺术创造力成熟的标志。然而,理论家和批评家有关风格的论述却常常使得“风格”与古典、适度和节制等文化特征紧密联系,对作家创作个性的理解往往趋于固定化和模式化,难以全面呈现作家创作个性、作品审美呈现与读者阅读体验之间异常复杂的关系。刘醒龙在2018年推出的长篇小说《黄冈秘卷》在风格上既呈现出与此前小说一脉相承之处,同时又显露出独特的新变,是一部难以用某种固定化的“风格论”去阐释的小说,这值得我们对之进行深入考察。
小说《黄冈秘卷》以父辈为中心的家族历史和《黄冈秘卷》发行背后的秘密演进为叙事主线,讲述了黄冈刘家大塆刘姓几代人所经历的历史与现实,表现了黄冈人执拗、刚强和坚毅的文化品格。刘醒龙此前小说的叙事视角多为第三人称,而《黄冈秘卷》却以带有几分自传性质的“我”为叙事者,这使得小说的自传性、传奇性和可读性大大增强。一反刘醒龙此前在《圣天门口》和《天行者》中对历史或教育问题进行“正面强攻”的创作姿态,他在《黄冈秘卷》中以从容、自在,甚至不乏幽默的方式讲述历史与现实各种隐秘的来龙去脉。同时,小说中对苏东坡在黄冈的经历、刘氏家族的时空流变、黄冈本地的方言与风情都有知识考古学式的生动呈现。尽管《黄冈秘卷》内含以《组织史》《刘氏家志》《黄冈秘卷》为中心的三条主要线索,由此延伸开来多条时隐时现的次要线索,但小说结构十分严谨,行文丝毫不显紊乱,这体现了刘醒龙驾驭文本的实力。换句话说,尽管刘醒龙早在《黄冈秘卷》之前就已形成独特的创作个性,但《黄冈秘卷》再一次展现了刘醒龙高妙的叙事能力与创作境界。在对家国往事与当下现实的关联叙事中,被黄冈的山水和精神滋养过的先辈们所继承的优秀文化品性像旗帜一样被树立起来,并通过代际传承不断向下延伸。
《黄冈秘卷》虽不乏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冷峻社会现实的表现,然而小说同时也呈现了丰富、细密而诗意的生活场景。由于《黄冈秘卷》是阅历已十分丰富、并取得一定成就后的“我”对刘氏家族、故乡黄冈和文化品性的寻根溯源,因而“我”时时刻刻与“我”的精神脐带和家庭人事紧密相联。返回到滋养“我”的文化母体之后,“我”变得亲近和温馨起来,就像刘醒龙在后记中所说的那样,“直到现在,都一把年纪了,只要回到那片原野,害羞的滋味便油然而生”,“原野所在,遍地温情”。在小说中,“我”对故乡方言(如伯伯,嘿呼等)、巴河镇小秦岭的藕塘、孩子对长辈们的撒娇、父母之间的争吵等日常生活片段的不断复写,体现出刘醒龙对日常生活的细腻把握,小说也因此呈现出更为包容、沉静和活泼的一面。
这是一个沉稳作家所具备的能力和境界:大气宽阔而不显呆板,活泼生动却不流于俗套。与《圣天门口》《天行者》和《蟠虺》相比,《黄冈秘卷》显然更加温和而从容,体现出历史与现实的多重“和解”。由于刘醒龙一直以来都是具有强烈的历史批判和现实批判精神的作家,对此有人或许会质疑《黄冈秘卷》中的这种变化是否就偏离了他以往的批判立场,是作家对历史与生活的一种顺从和妥协。质疑的声音大多从单一的理论视角出发对作品做出直接的评判,比如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对“晚期风格”的论述就是可被用来质疑《黄冈秘卷》对历史“和解”的理论资源。萨义德在阿多诺讨论贝多芬晚期作品美学风格的基础上,将“晚期作品”分为“适时”与“晚期”两种类型,认为前者“反映了一种特殊的成熟性”,“一种经常按照对日常现实的奇迹般的转换而表达出来的新的和解精神与安宁”,而后者“包含了一种不和谐的、不安宁的张力,更重要的是,它包含了一种蓄意的、非创造性的、反对性的创造性”。在萨义德看来,“适时”的作品只是艺术家年龄增长后对现实的放弃和妥协,而充满褶皱和破坏性的“晚期”作品才真正体现了一种不妥协的“晚期风格”。萨义德这番论述对我们理解《黄冈秘卷》有着重要的启示,但面对杂芜而又开阔的《黄冈秘卷》,直接的理论套用又显得局促而无力。
《黄冈秘卷》是已过花甲之年的刘醒龙带着温情与敬意回溯故乡和家族历史的小说,因而我们以“晚期作品”称之并不为过。由于小说采用第一人称自传性质的“我”作为叙事者,小说情节具有了某种“温柔敦厚”的情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小说是对历史与现实矛盾的顺从和妥协,而是在更高层面上呈现了历史与现实各种矛盾的复杂性与开放性。《黄冈秘卷》着力塑造的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父辈形象,正是刘醒龙反思与批判精神的延续,体现了萨义德所言的“晚期风格”。毫无疑问,“我们的父亲”形象中包含了许多刘醒龙父亲的影子,但又不断地逃溢和偏离他真实的父亲形象,是在再现与虚构中建构起来的父亲形象。小说中,向来固执己见的父亲与这个欲望时代之间的关系“格格不入”:这体现在他对川流不息的汽车的憎恶中,体现在他对永远相信组织的信念上,并落实到他永远忠于组织的种种行动上。父亲的言行与品性受到先辈们的影响,父亲也就因此成为“贤良方正”黄冈人的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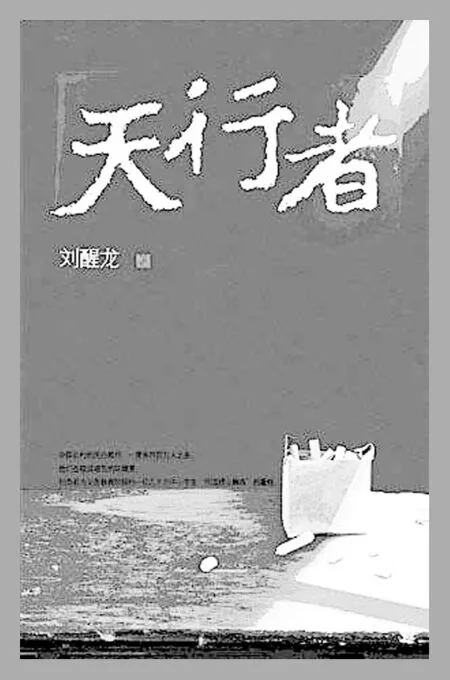
《天行者》
这些先辈遗留下来的精神遗产,与世俗时代人们对欲望和利益的疯狂追逐形成了鲜明对比。继承革命年代精神遗产的老十哥与在世俗年代乘风破浪的老十一在待人接物上的差异,将“志”与“智”之间的差异发挥到了极致。老十一在审讯中为了自我保存,将毁坏福特车的罪名诬陷给老十哥,而老十哥虽被诬陷,却没有在审讯中说出老十一的名字,最终他替老十一承受了牢狱之灾。老十一为了利益同他人结婚,接连换了六任妻子,而老十哥却将情感和婚姻视为神圣之物,始终坚韧不渝。老十一在商战中打拼唯利益是从,并不惜为了《黄冈秘卷》在全国的发行同政府秘密达成合约,而老十哥却固守着上级组织发给自己的微薄的工资,对钱权交易等腐败行为恨之入骨。父亲的这些言行突显出父亲“贤良方正”的人性品格,使得“我们的父亲”成为一个充满正义感和无私精神的英雄形象。由于刘醒龙在小说中注重对人物性格进行多重的刻画,父亲形象的塑造虽显崇高,却并不单薄。
萨义德认为,“不合时宜”是“晚期风格”作品的重要特征,“只有在艺术没有为了现实而放弃自身权利的情况下出现的东西,才属于晚期风格”。萨义德所论的“晚期风格”与他本人的身份认同以及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紧密相连,因此萨义德不断强调叛逆性、否定性和斗争性,并不断强化艺术家与作家晚年“死亡”的生命主题。《黄冈秘密》后记中所谓的“为故乡立风范,为岁月留品格”,正是通过塑造以父亲和王朤为代表的父辈形象来再现故乡的精神文化品格。父亲和王朤只是贤良黄冈人的典型代表。由此延伸开来,与黄冈有密切联系的众多人物都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坚韧的文化品格。比如写到苏东坡时,“我”认为“苏东坡的执拗只相当于半根筋,所以只能算半个黄冈人”,是黄冈的山水、性格与情怀造就了苏东坡的性格与诗才。写到五大队时,“我”借海棠父亲之口说到,“五大队是消灭不了的,因为五大队是黄冈人执拗性格的特殊表现,要消灭五大队,就必须首先消灭所有黄冈人”。曾祖母靠乞讨养活一大家人,但她在外乞讨的食物必须经过加工之后才给后辈们食用。当曾祖母起了刘声志和刘声智这两个发音相同的名字后拒绝给任何人起名字,就是为了给“我”的父亲长志气,不为他人耻笑。同时,“我”的祖父在面对红卫兵拷问时,总以轻描淡写的回答处处为他人考虑,表示林家“只是比穷人略富一点”,而自己只是林老大家的雇工,而不是“长工”。这些都是“贤良方正”文化品性的延续与传承。
可见,执拗只是黄冈人文化性格的外在呈现,而在这种执拗精神的内核深处,却早已融进了勤劳、正义、自律、坚毅和忠诚等文化品性。老十哥与时代之间的“格格不入”并不仅只是个人情感的表露,更是对革命年代遗留下来的优秀品性的致敬与弘扬,但这些优秀品性在世俗年代已几乎被遗忘。萨义德认为,“晚期风格是内在的,但却奇怪地远离了现存”,而刘醒龙在《黄冈秘卷》中以父辈们的精神旗帜为家族和地域立传的同时,也是在以“贤良方正”的人格品性为混沌时代开出了他的诊治药方。刘醒龙在《黄冈秘卷》有关品性和时代状况的呈现,与《天行者》和《蟠虺》等作品中对现实问题与知识分子品格的探讨一脉相承,作者质疑和批判的创作主线依然得以延续。
在后记中,刘醒龙谈到他创作《黄冈秘卷》时所面对的两种疼痛:一是手指腱鞘炎带来的身体疼痛,二是“湾”、“塆”与“垸”字写法差异所带来的文化心理的疼痛。刘醒龙在如此不适的环境下依然笔耕不辍,通过多重视角的并置再现和建构了新旧两个时代的精神差异与隐秘联系。“可以低头,可以弯腰,决不下跪求饶”,正是刘醒龙所书写的以黄州为中心的原野上的一种可贵品格。借用萨义德有关“晚期风格”的概念来讨论《黄冈秘卷》,作家的身体状况,作品的美学风格,与混沌时代的精神联系得以重新勾连起来。《黄冈秘卷》是刘醒龙对自己几十年来创作经验的总结与融会,是刘醒龙对家乡原野和家族历史的溯源和致敬,同时还包含着“黄冈精神”之于当下时代的重要意义。由此看来,《黄冈秘卷》的主旨诉求并非是对辅导书《黄冈秘卷》发行来龙去脉的追溯,而是在日益世俗化的时代重新树立起以父辈们为代表的黄冈人的文化品质之大旗。通过父辈形象的“格格不入”和“不合时宜”,我们所处的时代病症得以揭露,而这正是《黄冈秘卷》“晚期风格”的典型呈现。
《黄冈秘卷》体现了萨义德所言的“晚期风格”,是因为刘醒龙同萨义德一样都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巧合的是,萨义德晚年将他的回忆录取名为《格格不入:萨义德回忆录》(Out of Place:A Memoir),这体现了萨义德和刘醒龙之间既遥远却又亲近的精神联系。然而,萨义德所论述的“晚期风格”体现了他关于民族之间矛盾斗争的强大的理论预设,同时与萨义德敏感复杂的身份认同相关。萨义德不仅仅是一位流亡的巴勒斯坦人,一位基督教信仰者,同时还是西方文化传统培育起来中的知识分子,因而他的论述是阿拉伯世界民族文化与西方民族文化的杂糅与综合,而他对“远东”中国的文化及其精神并无多少了解。刘醒龙不仅是一位富有责任感和文化情怀的作家,他同时还对中国的书画传统与文学传统有深入透彻的把握。《黄冈秘卷》不仅体现了刘醒龙的现实关怀和批判精神,同时还以温情的姿态达成了历史与现实的部分“和解”,其丰富性、复杂性,及其开放性,是萨义德有关“晚期风格”的论述所不能全然囊括的。
我们应看到,中国古代的许多诗人(如杜甫、李商隐、李煜、苏轼、李清照等)和现代作家(巴金、沈从文等)的文学作品都在其晚年步入了更为沉郁、开阔和大气的艺术境界,同时像陶渊明、王国维和汪曾祺等人的晚年作品却走向了更加自然而纯净的方向,而所有这些“晚期作品”却并不完全都是否定性的,甚至完全不是否定性的。萨义德所论述的“晚期风格”对断裂、否定和批判性的强调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我们也不能将之绝对化和单一化,更不能将之作为评判文学作品成就高低的标准。刘醒龙近作《黄冈秘卷》不仅仅有着像秋天果实中发现的那种成熟,同时还是有褶皱的,具有反叛性和创造力的那种成熟。从对现实进行“强攻”,到与历史与现实达成部分“和解”,《黄冈秘卷》并没有选择以绝对的姿态去进行简单的批判和否定,而是以包容和理解的方式去探究历史与现实的微妙、复杂与人性的复杂,这其中包含着并未熄灭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体现了一个作家对家乡和人性至深至切的热爱。
一个作家要形成自己的风格大致需要经过三个阶段:开始创作时的模仿,逐渐摆脱其他作家的影响,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作家只有一种风格或一种创作姿态。汪曾祺认为,“风格,往往是因为所写的题材不同而有差异的。或庄,或谐;或比较抒情,或尖刻冷峻。但又看得出还是一个人的手笔。一方面,文备众体;另一方面,又自成一家”,我们将汪曾祺所言用于刘醒龙及其《黄冈秘卷》也丝毫不为过。刘醒龙在《黄冈秘卷》的后记中表示,他在创作的过程中“不需要有太多的想法,处处随着直接的性子就行”,这正是他经历万千险阻和无数历练之后自信坦荡的表现,造就了《黄冈秘卷》中宽阔、大气与诗意并重,理解、包容与批判并存,实现了家族志、地域方志与民族志的融合。有关病痛、回乡之路,甚至死亡的情与思,一起累积起生命的重量,使得刘醒龙在《黄冈秘卷》中不仅是像萨义德所说的那样以折射和反讽的方式来表现对于世俗时代的离弃与厌倦,同时他还以温情的笔墨实现了更高程度上的“和解”。这些都足以说明,《黄冈秘卷》文备众体,而又自成一家,是一部同时呈现“适时”与“晚期风格”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