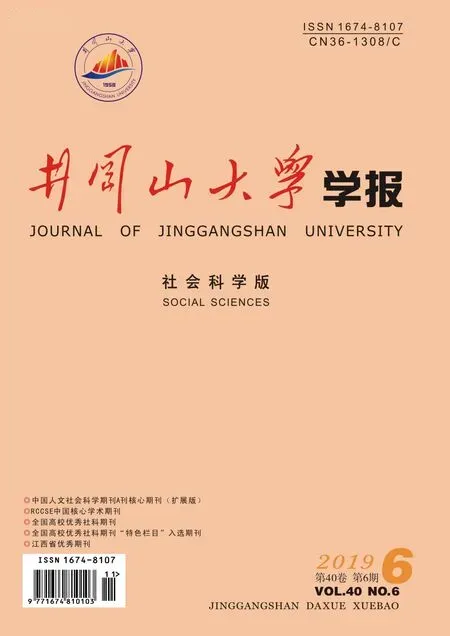章潢性气思想探微
——从《明儒学案》的一处文本错误谈起
文碧方,卢添成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章潢①章潢,字本清,别号斗津,祖籍临川,后迁至南昌,生于明嘉靖六年(1527 年),卒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 年),终年八十二岁。 章潢自幼聪颖,七岁即入小学,十六岁时受督学苏公推荐,补郡庠生,二十岁开始一直到三十四岁都在正气堂学习举业,四十二岁构“此洗堂”,联合友人弟子讲学,此后一生都在致力于讲学活动,六十四岁聘主白鹿洞书院,成为书院山长,六十八岁与罗汝芳、邹元标、王时槐等人会讲于青原山。 章潢一生品行高尚,颇有美誉,死后弟子友人私谥章潢为“文德先生”,并与吴与弼、邓元锡、刘元卿并称“江右四君子”。 关于章潢的生平与著述,可参见《图书编》所附《章斗津先生年谱》《章斗津先生行状》以及《明儒学案》及《明史·儒林传》中有关章潢的记述。在其《图书编》一书中论述其性气思想时指出:“气即性,性即气,混然无别,固不可矣。谓气之外有性,性之外有气,亦不免裂性与气而二之也,何怪其分天地之性、气质之性而自二其性哉! ”[1](P2605)这段文本与《明儒学案》所摘录的文本有较大出入。 《明儒学案》里的江右王门学案中有关章潢的这段文本,摘录的这一句是:“气即性,性即气,固不可谓气之外有性,性之外有气,不免裂性与气而二之也”[2](P572)。这两个文本出入较大,四库本《图书编》较之《明儒学案》多出一个“矣”字和“亦”字,然而,二段文本的句读也是大为不同,所表达的意思也有很大出入。 四库本《图书编》表达出章潢的思想是,“性”与“气”是合一的,但不是浑然无别的;《明儒学案》 则是站在浑一性的立场上而言的,即“性”与“气”是等同起来的。参考四库本《图书编》的底本,即明刻本的万历万尚烈本的《图书编》, 这两个版本关于这段话的文本是相同的。 为何两个关于章潢性气关系表述的同一文本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我们应该遵循哪一个文本呢?
《明儒学案》自成书于清代康熙十五年(1676)以来,至今已经有二十余种刻本,其中康熙三十二年贾润紫筠斋刻本、 乾隆四年郑氏二老阁刻本以及道光元年莫晋教忠堂刻本三大刻本成为各个版本的基础参照,但众多版本之中,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 这是因为最早的康熙本和乾隆本的文本就存在许多问题, 而这些问题又是传统的版本校勘不能解决的,版本之间的互校并未能解决《明儒学案》的版本问题。 因此,《明儒学案》的文本问题历来饱受诟病,今之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研究。朱鸿林的《明儒学案点校释误》以及赵文会的《明儒学案研究》,两本书都列举了《明儒学案》中存在的数百条文本的错误问题, 其中文本摘抄的错误问题也是不胜枚举,可见《明儒学案》在文本的选取摘抄上存在很大问题。 朱鸿林教授采用“史源学”的方法对《明儒学案》进行校勘,从《明儒学案》摘抄的文本源头来进行对比校勘, 这是一个较为可行且可靠的方法。 对于《明儒学案》中的这段文本问题,我们也可以以明刻本的《图书编》为准,去对校《明儒学案》的文本。因此,我们应当回到《图书编》的原文中去, 把章潢整个性气思想的全貌给勾勒出来, 以便形成对章潢性气思想的一个清晰的认识。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明儒学案》中,黄宗羲对章潢的评价也是说“辨气质之非性,离气质又不可言性”,从这句评语来看,黄宗羲也认为章潢在论述“性与气”的关系时,是就“性”与“气质”而言的,既然如此,它们就不应是混然无别的, 章潢所表达的意思应该是可以确定的, 只是《明儒学案》的文本有错误。 笔者甚至可以大胆推测,黄宗羲的最初摘录是没有出错的,应是版本流传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要清楚这个文本问题,需要对章潢性气思想有一个清楚的定位, 辨析其性气思想的具体内涵与旨趣,以佐证上述猜测。 为此,有必要对章潢的性气思想做一个深入细致的梳理,还原出章潢性气思想的原貌。
一、性气合一:章潢性气思想的理论背景
性之善恶问题一直是中国哲学中比较核心的话题之一, 它关涉到各家各派对于整个人性论的思想主张,从先秦时代孟子提出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以及告子的“生之谓性”,到秦汉以后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扬雄的“性善恶混论”、韩愈的“性情三品说”等等,这些都是较为主流的人性论观点。 宋代以前关于性之善恶的讨论尚没有联系着“气”来论说,对于性气关系的辨析也还未进入到他们的视域中。及至宋以后,张载提出气本论思想,将“性”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揭橥宋儒性气二分模式的形成, 程朱更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理气二元论”的思想①朱子虽然认为“气质之性只是此性堕在气质之中,故随气质而自为一性”,即本然之性体不可见,“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气质之性便是性体的外化表现,但朱子并未处理好形而上的“天理”与形而下的气质之性之间的关系,气质有清浊,连带着气质之性有善恶,那么纯善的本然之性如何会开出带有浊气的气质之性。,把至善之性与参杂善恶的气禀统合在一起。 然而, 宋儒对性气作“二分模式”的处理,存在着一个关键性的难题,即至善之天理何以开出恶浊之气,也就是说“恶”也成了一个与生俱来的东西,这样一来,既然“恶”已经被先天给予了, 后天的变恶向善的修养功夫如何可能。明儒认识到“性气二分”的理论缺陷,便逐渐转向“性气合一”的模式,把性与气统合在一起,将“恶” 的产生归于后天的私欲习气, 从而解决“恶”的根源问题。
明儒之中,王阳明对“性气合一”的论述是最为完备的, 也影响着整个明代关于性气关系的论述模式。王阳明从“生之谓性”的角度提出“性即是气,气即是性”的性气浑一论,阳明认为性本体本身不可见,需在气上见得,因而性之发用即是气。心之四端七情,都是性所显现处,也是气之流行运用处。因而,陈来先生在其《有无之境》一书中就指出,“二程是从气禀的先天影响立论, 阳明则是从体用不二的角度来说明气的积极意义”[3](P88)。 同时,陈来先生也指出,在阳明的性气思想里,潜藏着“性即气质之性”的苗头。 阳明的“气质之性”是指本然性体通过气之流行表现出来的性, 而朱子所谓的“气质之性”则是性体堕在气质中,并受气质之清浊的影响②如前所言,朱子也是说性之本体不可见,它落在气质上便成了气质之性,似乎与阳明论说一致,其实不然。 朱子所讲的“气质之性”是将性落在气质上,但气质有清浊之不同,连带着气质之性有善恶之分;阳明则是把性气关系从一个体用不二的角度来论说的,阳明并未说性即是气质,而只是说“性即是气”,性通过气之流行而表现出来,使得本然之性体具象化为可见之性,所以此性还是纯然至善的,不含气质之清浊在其中。 作为“性”所显现的载体,“气”也具有了积极性的意义。。 从朱子到阳明,“气质之性”的定义是有所滑转的,阳明从“性气合一”的角度将性与气统合起来,将气质与性截然二分,从而抽离出它的价值属性,回归“气质”的本来含义,即才质、禀赋。阳明的“性即是气,气即是性”思想,也为整个阳明学派对于性气思想的讨论定下基调,后来的阳明学者纷纷在此模式下提出自己对性气关系的看法,而章潢就是其中之一。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在谈到章潢时指出:“先生论止修则近于李见罗,论归寂则近于聂双江,而其最谛当者,无如辨气质之非性,离气质又不可觅性,则与蕺山先师之言,若合符节矣。 ”[2](P571)作为阳明后学的章潢,他接续了王阳明对气质的看法,区分了气质与气质之性,批判了宋儒“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分模式,站在“性气合一”的立场上否定了天命之性的存在,将“天命之性”统摄到了“气质之性”之中。与阳明不同的是,章潢的性气思想更多地是就着“气质”与“性”的关系而言。在阳明那里,“气”与“性”是混然无别的,从“生之谓性”的角度,把“性”与“气”之生生不息、化育万物之意义统合在一起, 从体用一源的维度说明性气之不可分。因为阳明思想中已经潜藏着“性即气质之性”的话头,此“性”不是“性”之本体,已经是通过气的流行运用而表现出来的性, 这一主张基本被阳明后学所继承, 而阳明后学的学者在谈论性气关系时更多转向对“气质”与“性”的讨论,而其焦点不再是作为体用不二意义上而言的性气关系,其共同的旨趣便是将“恶”之根源问题定位到后天之习气上,剔除宋儒所讲的“气质”的价值属性, 从而把修养功夫落实到明确的变化习气的实修功夫上来。本研究正是在明确这样的背景下,对章潢的性气思想做更为深入的探究。
二、辨气质之非性,离气质又不可觅性
章潢认为气质是天性,是每一个人都赋有的,“然未有人而无气质也, 故孟子谓形色天性也,是气质即天性也”[1](P2604)。气质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天性是无有不善的, 因而章氏认为此外再没有一个“天命之性”的概念,“性”就只有一个,不能二分为天命、气质,宋儒所讲的“天命之性”在“性气合一”的语境下与“气质之性”相同,即“性”是无有不善的,此性通过气之流行运用表现出来,这个表现出来的、具象化的“性”就是“气质之性”,这个“气质之性”亦是本善的。 如此一来,只有“气质之性”而无“天命之性”,作为性之本体的“天命之性”已经通过“气质之性”表现出来。在章潢看来,气质是性的载体,正所谓“人不能离气质以有生,性不能外气质以别赋也”[1](P2604)。章潢认为,如果强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那么会出现两个问题:
彼天太虚也,气也;地,大块也,质也。 天地之气质浑浑沦沦,六合之内充塞无间,天地之性安在哉? 人即小天地也,若云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则未有人而无其形者,亦止得其气质之性,已尔而天命之性又安在哉?[1](P2604-2605)
太虚为气, 大块为质, 气质充塞天地六合之间,那么天地之性何存?在未有人之前便已经有气质,所以人未形之前也只有气质之性存在,那么天命之性在哪里?之所以产生这两个疑问,是因为宋儒把“性”强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将其分裂成形上与形下两截, 但又没有处理好形下之气质与形上之性之间的关系。 阳明已经把“性”定义成了“气质之性”,这个“气质之性”便已经是具象化的东西,也是本然至善的东西,不需要再说个“天命之性”出来,而“气质”本身是天性,是一种禀赋才质,所以二者是两个面向,气质之性即是性本体之外化表现, 气质则是不可以善恶言之的人的才质性情。
章潢认为气质虽是人先天所禀, 但也有刚柔缓急、厚薄强弱之不同,气、质与性分开来讲,可以分属三个不同层面,“阴阳,气也;刚柔,质也;仁义,性也”[1](P2605)。但章潢认为从天地人三才角度来讲,并不是天得其气,地得其质,而人独得仁义之性并且兼有气质之性的。 在章潢看来,“性”与“气质”是合一的:
气即性, 性即气, 混然无别, 固不可矣。谓气之外有性,性之外有气,亦不免裂性与气而二之也,何怪其分天地之性、气质之性而自二其性 哉
章潢这里所言的“气即性,性即气”,早已不是像阳明一样单讲“性与气”的关系,而是转向了对“性与气质”关系的讨论。 “性”与“气质”浑为一体不作分别是不可的,如上文所言,它们是两个不同的面向;“性”与“气质”分而为二更是不可的,“性”与“气质”是内在统一的,“气质”是“性”之具象化的载体,是“性”之外化表现的介质,但“气质”与“性”又不可以简单地等同起来,也即它们不是浑一的,是有所区别的。
章潢继承了阳明的“性气合一”思想,“性”须借助“气”而表现出来。 我们通常所讲的“性”已不是性之本体,是“性”落在“气”后的“气质之性”,阳明的性气关系是就着阴阳二气化生万物的角度而言的,因而性气关系是即体即用的,所以它们的关系是“性即是气,气即是性”。但章潢在探讨性气关系时,这个“气”更多是指“气质”而言的,所以性气关系是“性外无气、气外无性”,不似阳明那种性气体用不二的粘连关系,这是因为它们对“气”的指向不同。 性气关系在章潢这里是一种不离不杂的关系,“气质”是“性”之载体端绪,“气质”与“性”不可二分,所谓“气外无性,离气则性亦何从而见之哉? 故孟子指平旦之气以观仁义之心, 仁义即性也”[1](P2613)、“则知此性之生生, 又不可分性气而二之矣”[1](P2600)。 “气质”虽是“性”所安放的载体处,但章潢更强调“性”之主宰义,所以章潢指出:
虽云生即气也,性之外无气,气之外无性,而专于气上言之,则资始流形,各正性命,人与禽兽所异几希何在耶? 且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孰为之敦化?孰为之川流?至于氤氲化生,则气固万殊矣。然气之流行,一本之天命之自然者,性也,人皆得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而气不得以拘之。[1](P2600)
在这里,章潢认为“性”与“气质”虽不可分,但“性”具有主宰性,不被“气质”所局限,是天地万物敦化流行的源泉。如果专从气上讲,人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独特性无法显现,只有“性”之敦化不同,使得人与禽兽相异。如果说前面所讲章潢在论性气关系时,是把“气”指向“气质”的倾向还不够明显的话,这里章潢明显已经是把“气”作为“气质”来讲,它是从“形色天性”一以贯之下来的,“气质”是才质性情,是人之个体独特性产生的根源, 但与本然至善的性又不是同一的。 人之天赋如何, 不会对本然之性善有所影响,所以说“气不得以拘之”。此外,需要分疏的是,“气”与“气质”是不相同的,前面已经提及到这个问题,“气质”是“气”与“质”结合的产物,“气”是指阴阳五行之气,是氤氲化生之气,“质” 则是由气之聚合而成的形质。 章潢自己对“气”与“质”的关系有一个明确的分疏,他认为,“生之者气也,成之者质也,气质何可离也”[4](P1211)、“有形体而分峙于昭昭之间, 其质也;无形体而默运于冥冥之表者,其气也”[4](P1213)、“质虽以气而成, 然其体一定而不可易; 气虽行乎质之内,而其用则循环而不可穷,二者相次以成造化”[4](P1210)。 “气”与“质”在章潢看来是相须不离的, “气” 是循环氤氲的“用”,“质” 则是不易的“体”,“质根于地, 气运于天”, 二者是体用相成的关系。日本著名学者山井涌先生指出,“质是比气更接近于具有现实形态之物的某个层次上的东西”[5](P423)。 “气质”作为气与质的结合物,它必定是具有现实形态的,表现在人身上的“气质”,则是人的天性与特质。 蒙培元在《理学范畴系统》一书中给“气质”的定义是:“主要用来形容生理、心理学上所说的素质、才质一类特征,属于感性经验一类的存在。 ”[6](P231)可以说,“气质”已经是“气”落在“质”上的产物,是指人的才质与禀赋,因为“气”之刚柔缓急不一,落在人身上的“气质”自然也各有不同, 这也是人的独特性与个体性产生的原因。但是,“气质”并不是如宋儒所讲的气禀,它是已经剔除了价值成分的才质性情,与“性”是有所区别的, 故而章潢说:“诸儒每兼言之, 未免认气质为性,指方法作用为道,此所以性道愈晦,无怪学术多歧。”[1](P2646)章潢明确反对将气质等同于性,这也就是他在谈到性气关系时所说的“混然无别,固不可矣”。
三、变化习气:章潢性气思想的落脚点
章潢既然把“气质”视为天性,为人生而有之,只是刚柔缓急各有不同, 但人之后天趋于不善的原因究竟何在?章潢把它归结到后天之“习”上。前人将孟子的“性善”看成是义理之性,而把孔子所说的“性相近”视为气质之性。 章潢以为, 孔子之所以以“性相近”言气质之性,正是要把人变为不善的因果落到后天的“习”上,“何为不以理义至善者示人而只示以气质之性, 又何为不归咎气质而独归咎于习耶?殊不知善与恶相远矣”[1](P2605)。在章潢看来孔子之所以不归咎于气质而独归咎于“习”,目的就是把“恶”的根源问题追溯到后天的“习”上来。 人们初生之性是善且相近的, 因为“孩提气质未免尚有理义之性, 故不虑之良知、 不学之良能, 一本诸天性之真”[1](P2605), 但是等到气质壮盛, 受后天习气扰染, 被私欲习气所变化, 就会丧失这些天性,“特习日远而廉耻日丧, 以至梏亡之殆尽耳”[1](P2605), 先前孩提时的恻隐羞恶之四端之情都因为习气而消失隐退, 本心良知也被遮蔽不现。
章潢认为性是至善的,“统体为善, 发用也是善,恶只是善之反,不是天命之本然,故不可以善恶对待言性”[1](P2589),恶的产生是善之反,是动后私欲生出造成的,故而“圣人说得恶字煞迟”。所以恶并没有先天的依据, 它是后天遮蔽本心良知而后出现的,因而不能把气质等同于后天之“习”,宋儒所讲的善恶相混的气质之性也就立不住脚了。“故人之所禀清浊厚薄,亦因以异,是不齐者,气质也,非气质之性也”[1](P2606), 人天性各有不同是气质先天决定的,并不是气质之性。 气质虽是天性,但性不受其影响而失去本然之善, 章潢举出了阳明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性与气质的区别:
善乎阳明先生曰:气质,犹器也;性,犹水也。有得一缸者,有得一瓮者,局于气也,气质有清浊、厚薄、强弱之不同,性则一也,能扩而充之,器不能拘矣。 信斯言也。 气质万有不齐,性则一也。 水不因器之拘而变其润下之性, 人性岂因气质之拘而变其本然之善哉。[1](P2606)
章潢认为,性是本然至善的,不需要区分一个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出来,把性割裂为二。 同时,气质虽万有不齐,亦不是人们变恶的原因,它只是人的天性而已,人之所以为恶,全然是因为受后天习气熏染,遮蔽了至善良知本性,因而“恶”没有其先天根源,宋儒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反倒使人“自诿于气质之性而莫知自变其习也”[1](P2606)。 所以, 章潢指出这种弊病危害颇深:“嗟夫, 由宋以来,士之识卑守固者,或偏于刚;或偏于柔,而诿罪于气质之性者,固不能溯流穷源以窥乎性善之蕴,然求之高旷虚寂者,谓修性不修命,万劫英灵难入圣”[1](P2602)。 “气质”如果掺杂善恶的价值属性在其中,成为了人的与生俱来的性质,那么就会使人把后天的趋恶私欲归结到“气质”上来,而不思改过迁善之修养功夫, 这是宋儒功夫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阳明学者正是看到程朱理学中这一内在的两难问题,转而寻求“性一元论”,把先天至善的性与后天的私欲客气严格区分开来, 并将功夫落在变化习气上。章潢正是承继了这一模式,因而提倡实修功夫, 对治后天因私欲客气而被扰乱的“放心”状态,从而回复本心之纯善。
性只有一个, 且它是本然至善的, 无先天后天、天命气质之分,“所以认定性本善,情亦本善,才亦本善,而其功夫只在直养而无害”[1](P2611),全部修养功夫只在存养这个本然至善的“性”。 章潢沿着这一功夫进路,形成了自己止至善、求放心的修养功夫论,把功夫的着力点落在了变化习气之上,从人伦日用的实际生活中出发,倡导实修功夫。章潢极力排斥佛老,在其《图书编》一书中,随处可见章潢对佛老的大力批判,并指责宋儒堕入佛老,陷入虚寂本体,此外还指责词章之学,泛滥人心。 如他说,“圣人既没,心学晦而人伪行功利,训诂辞章之徒纷沓而起,支离决裂,岁盛月新,相沿相袭,各是其非……然指禅学而群訾之。呜呼!心学何由而复明乎!”[1](P2676-2677)章潢对佛老的玄虚之学以及词章之学的极力排斥,是因为他想把功夫落到实处,避免像宋儒那样堕入虚寂中, 章潢整个思想都是带有一种经世致用的色彩的,所以他的《图书编》一书起初定名为《论世编》①《图书编》所附的《章斗津先生年谱》记载《图书编》的成书时间时写道:“夏,《论世编》成,从者益众。 ”可见《图书编》起初定名为《论世编》,后改为《图书编》,书的内容也是不断修订增删的。,书的内容也是包罗万象,山川地理、职官建制等等,都是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的。这一点体现在他的哲学思想上,尤其是修养功夫论上,则带有一种实修的倾向。
章潢既然认定此性无有不善,其所以为不善,是后天习气私欲的扰乱,回复本善之性,亦即对治这种习气私欲,就是章潢修养功夫的主要内容。无论何种修养功夫,其最后的落脚点都在变化习气、“明性善”之旨上,所以他很明确指出其功夫的指归,他说:
继善成性,此是极归一处,明善明此也。 如主敬穷理,致良知,言各不同,皆求明性善之功,岂必专执一说,然后为所宗耶?[2](P571)
如前所言,宋儒分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来,将性裂为二,性本纯善无恶之旨不明于世,因而章潢认为学问之道首先在于“明性善”,无论致良知之教,抑或主敬穷理,先要把捉到为学的宗旨和归宿, 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断锻炼自身的习气,变化其气质,回复本然之性善。 关于章潢的整个功夫论的脉络可以从他的“学箴四条”中大体把握,其为:
学箴四条:一曰《大学》明德亲民,止至善;《中庸》经纶立本,知化育。此是圣人全学,庶几学有归宿;一曰虞廷危微精一,孔子操存舍亡。 此是心学正传,庶几学有入路;一曰颜子欲罢不能,曾子死而后已。 此是为学真机。 庶几不废半涂;一曰明道每思彝伦间有多少不尽分处, 象山在人情物理事变上用功夫。此是为学实地,庶几不惑异端。[2](P574)
章潢提出为学的四条箴言, 已经把他的为学功夫大致勾勒出来了, 其修养功夫的最终旨趣是“止至善”,而达到“止至善”则需要“操存舍亡”和在人伦日用上着力的实修功夫。操存舍亡即是“求放心”,保有其良知本心,使后天被习气污染的“放心”收摄归一,这是心学的正宗,也是其功夫的不二法门;“求放心” 以及变化习气都需要从人伦日用处着手,这是章潢认为的“为学实地”,是其实修功夫的具体体现。 除此之外,还需要欲罢不能、死而后已的毅力去持志,不断的去除私欲客气,持之以恒的去长养自己的本心良知,使其无纤毫染污。总之,不论是“止至善”,抑或是“求放心”,章潢修养功夫论的对治对象都是后天的私欲习气, 这是与章潢性气思想相贯通的。
四、结语
综上所言, 章潢的性气思想是继承了阳明的“性气合一”模式的,但把对“性”与“气”的讨论转向了对“性”与“气质”的讨论上去,这是阳明后学的一个普遍趋势, 与章潢同时代的思想家们在论述性气关系时也都聚焦到性与气质的讨论上来。正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对章潢的评价所言,“无如辨气质之非性,离气质又不可觅性,则与蕺山先师之言,若合符节矣”[2](P571)。章潢与刘宗周在性气关系的看法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章潢与其同时代的刘宗周对于性气关系的讨论都更多的把关注点聚焦在“性”与“气质”的关系上,他们对性气关系的讨论具有某种契合性。 如刘宗周在提到“性”与“气质” 的关系所言,“性是就气质中指点义理者,非气质即为性也。 清浊厚薄不同,是气质一定之分,为习所从出者。气质就习上看,不就性上看。以气质言性, 是以习言性也”[7](P513)。 刘宗周严分“性”与“气质”,并强调“性”之主宰作用,这与章潢的性气思想基本一致。
从阳明的“性气合一”甚至说是“性气浑一”,到章潢及阳明后学的“性”与“气质”合一但不同一,可以看出,作为阳明后学的一个代表,章潢试图严格划清至善的“性”与后天习气的界限,并厘清“性”与“气质”的关系。 在阳明“性即是气质之性”这个话语背景下,“性”不再是直指本体,而是具象化的且至善的, 那么在面对阳明后学异端四起、流弊日甚,加之朱子学后劲兴盛的情况下,作为阳明后学正统派的章潢,有必要讲明“恶”之根源问题,以保全这个至善之“性”的“地位”。身处于江右王门中心的章潢, 其思想必定带有收摄保聚的笃实之风,加之其多年的讲学互动,其思想还杂糅止修学派、泰州学派等思想,兼采众长,形成了其修养功夫的务实风格。 章潢的修养功夫的指归是“明性善”,为学之前提是要明此“善性”,不论何种功夫,都要严分“性”与“气质”,给“性”、给“气质” 一个清楚的定位, 从而建立人们的道德主体性, 使其不能将后天变恶的原因归结到先天气禀上来。 基于此, 我们再回顾到前面所说的文本问题,就可以清晰地断定《明儒学案》的文本是错误的,不是从版本而是从思想上看。思想的发展有其时代的背景,对性气思想的讨论也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阳明后学学者在面对种种困境与挑战时,积极做出改变与应对,不断寻求新的发展出路,并形成多元互动、多向展开的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