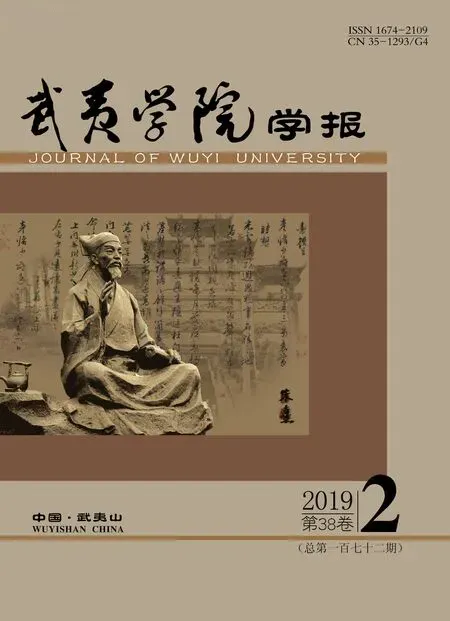破碎的世界:麦卡锡《路》中的“隐身”叙事
焦艳格
(郑州大学 外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路》是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1933-)的代表作,出版于 2006年。2007年,《路》荣获普利策最佳小说奖和国家图书奖,奠定了科马克·麦卡锡的大师地位。科马克·麦卡锡曾获誉“海明威与福克纳唯一的继承者”。《路》讲述了一场大灾难之后,世界失去了原有的生活秩序和道德秩序。在死亡和残暴的笼罩下,一对父子历经磨难向南方寻找温暖的求生历程。深刻揭示了在破碎的世界,逃亡者如何在异化的社会环境下,掩盖自己的“真”存在,久而久之,变成“假”存在的可悲。旨在探讨“我是谁”的深刻命题。小说一出版就引起了很多评论家的关注,被称为是一部“残酷的诗学”,充满着启示录般的庄重意味。
《路》一经问世,国内外众多评论家和批评家采用多种方法从不同的视角解读该部作品:有的从象征手法及其深刻的蕴意的角度对其进行阐释,有的从寻找圣杯的角度进行探讨,有的从互文性角度对文本进行分析。还有学者从创伤理论视角对故事进行研讨的。
上述的不同视角无疑对读者深入研读小说是十分有益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小说中的人物置于“隐身”叙事加以阐释,我们就会对人物关系的冷漠,社会关系的异化有更深刻的思考。本文将尝试从隐身与叙事进程、叙事的潜文本和叙事投影三个维度进行分析,着力探讨小说中的人性关怀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
一、隐身与叙事进程
詹姆斯·费伦认为:叙事进程是文本驱动(人物与人物之间以及人物与环境之间的不稳定性)与读者动力(读者与叙述者,读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张力)共同作用的结果。[1]这部小说以一场末日灾难展开叙述。“荒芜、静寂、邪恶”[2],勾勒出破碎的世界,给读者带来强烈的绝境体验。随着叙事焦点的移动,一对父子凸显在读者的眼前,值得思考的是:父与子无名无姓,让读者感受到留白带来的强大阅读驱动力。读者动力,自然地推动了小说的叙事进程。关乎身份认同的意识,人们仿佛已经看得不再重要抑或是活下去的唯一“麻醉药”,麻醉自己的灵魂,让自己变成一个没有知觉的流亡者。读者进而得出结论:破碎的世界造成了人的堕落,即:人的身份缺失和人性的退化。人们开始逐渐模糊“我是谁”这一命题,他们都选择将自己“隐身”起来。文中,一个叫“伊里”的老人不愿说出自己的真实名字和年龄是为了保全自己。宁可选择“遗忘”和“欺骗”而不愿选择身份认同。从文中“已有好几年没有使用过日历了”。[2],读者可以基于认知体验,“日历”这个意象具有时间属性和社会属性。在时间方面,映射出时间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活着”。在社会属性层面,象征着人与人从事社会活动中产生相互关系的时间总和,进而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完全隔离状态,这是一个“隐身”的世界。
简单的父子对话中,多次出现“我们不能留在这里”“这里不安全”“危险”“那里有人怎么办”“害怕”,这些反复出现的短句或词语无不让读者感受到不确定性带来的巨大恐惧感。父与子为了求生,躲避食人者和掠夺者,不得不“时刻放哨”。“嘘”这一叹词的频繁出现,暗示父与子“隐身”的潜意识反应。小说出现了“人怕人”的社会怪象。人性中隐藏的暴力倾向被残酷的生存环境唤醒。人们互相厮杀和掠夺,食人者甚至吃掉自己的孩子,这种人性丧失激发出的邪恶力量让读者感到窒息。暴力场景的不断切换,时刻挑战着父与子的心理防线。生与死的快速切换,震颤着父与子的心。“仅靠一口气熬着,一口颤抖的、短暂的气。真希望我的心是石头做的”。[2]触目惊心的经历,给父子带来了巨大的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熬”给读者强烈的带入感,将父与子的生存困境表达得淋漓尽致。文中儿子多次问“我们会死吗”“我们不会吃人对不对”,这样直言不讳的话,直击读者的灵魂。漫无边际的黑色,灰色和白色构筑了世界的色调和流亡者情感基调。读者沉浸在这样的世界里,感知到死亡因子的无处不在。死寂的一切,对抗着父子的道德尺度。“整个世界浓结成一团粗糙的、容易分崩离析的实体……最后,人们原本确信存在的事物的名称,也被忘却了”。[2]随着世界的破碎,人们曾经确定的,坚信的,如今变成了模糊的,易碎的。脚下踏着的毫无生气的世界,曾经也是充满生机和文明的世界。这样天翻地覆的转变震颤着读者的心。
正如文中所述“人每天都为明天准备着。明天可没为我们做什么准备”。[2],读者感受到生与死快速转换的不确定性,父亲开始选择淡化“存在”的意识,变得冷漠和麻木,逐渐丧失身份认同意识。在异己环境压迫和驱使下,不想也不愿和其他的逃难者建立任何的关系。他选择“躲避”来保持与其他同类的安全距离,隔离一切不安因子。除了儿子以外,他对别人来说,就是一个“隐身”人,关乎别人的生死,他“看不见”,文中多次出现的“我们不能帮他”颠覆了读者期待,让读者一次次体味到人性中“善”在异化状态下的苦涩和无力感。在这样破碎的世界里,也许“隐身”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读者在作者精心安排的故事框架里,不断与叙述者、作者建立联系,叙事进程在不稳定性的状态下和“假”存在与“真”隐身之间的对立产生的张力推动下顺利实现。人类“隐身”的深刻寓意和反讽在于:人虽然具有社会属性,却失去了人性的核。文明世界的重构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重大课题。这些暗示出麦卡锡对异化现象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切反思和关照。
二、叙事的潜文本
申丹在《叙事、文体与潜文本》中强调:结合社会历史语境等因素,挖掘作品的潜藏文本以及其深层意义。[3]“潜文本”与显文本对立,作者的深层意图往往隐藏在独特的叙事结构中。《路》主要叙述了灾难过后,一对父子向南方寻求温暖的求生历程。作品没有错综复杂的情节,也没有复杂的人物关系,更是没有交代灾难发生的原因。故事的开头设置在灾难的大背景下,读者基于认知建构,很容易联想到2001年的美国“911事件”,事件发生后,黑色硝烟和尸首遍野,无不震动着所有美国人的灵魂。每个人都深切意识到了生命的脆弱和渺小。因此,我们不难联想到麦卡锡选用一对无名无姓的父子旨在映射所有人类,进而挖掘出《路》的潜文本——人类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意指对整个美国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和担忧。
根据《旧约·创世纪》第三章的详细记载:原罪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受蛇的诱惑,违背了上帝的意旨,偷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而被驱赶出伊甸园的故事。这是人类罪恶的开始。因此,人生来是有罪的。根据《以赛亚书》十四章,详尽描写了撒旦的堕落。撒旦依靠自己的智慧,背叛了上帝,最终被赶入黑暗的地狱。作者将撒旦回归—人性的堕落—自我救赎的历程抽象化建构在小说《路》中,读者能够感受到灾难给人类带来的报复与毁灭。“一年间,处处能听见屋梁失火时杂乱的人声,生命被谋害时的尖叫。白天,路旁的木桩尖上插着死尸”。[2]这种对人类的惩罚让读者深刻地意识到人类的罪恶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惨重代价。
大自然是有生命的。动物,甚至是日月都在一直审视着人类的所作所为。人类一直以来的狂妄、愚昧、贪婪等罪恶无不触怒着大自然。上帝的“眼睛”注视着人类的罪恶。小说《路》中出现的“地图”“可口可乐”“左轮手枪”“火车”这些字眼折射出工业文明带给人类的美好与不安。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人类的文化身份出现缺失。人类的“七宗罪”释放的人性暴力一再对大自然发出挑战。最终历史证明:人类无法与大自然较量。《路》中灾难的降临,一夜之间吞噬掉所有的美好和安逸,取而代之的是苦难、暴力和死亡。父与子在灾难后,砥砺南行,寻找生的希望。“食物”成为他们生存下去的可能。“我们必须冒一次险。我们得找到吃的东西”。[2]一路上为了求生,不得不小心谨慎。他们害怕遇见其他有生命的群体。当他们听见有声音的时候,父子俩会本能地藏起来。文中多次出现“如果里面有人怎么办呢,爸爸?”“路上有人。把头埋下。别看。”让读者深刻感受到异化状态下“人怕人”的悲哀。脚印是父子求生路上留下来的存在证据,但很可能会被其他人发现其行迹。父与子为了“隐身”,不得不想方设法处理他们的“脚印”。“他们踢了些雪灭了火,朝树林中走,然后绕个圈又倒了回来。他们快步走着,留下一串串让人捉摸不透的脚印,最后才开始向来时的北边走,二人穿行于树林中,时刻都观察着大路上的状况”。[2]这足以让读者感受到人类的可悲和可怜。为了生存,不敢有一丝懈怠,煞费苦心,使尽浑身解数和聪明狡猾只为躲避同类。
“一路上都可见这些不久以前留下来的讯息,是讯息,也是警告,这些刺激的场面证明,屠杀和猎食确实存在”。[2]残酷的暴力场面,映射出人类在绝境下,人性的邪恶和信仰的缺失。读者深刻感知到人类的堕落和残暴,进而挖掘出父子“假”存在与“真”隐身鲜明对立背后的动因。父与子是文明世界破碎的见证者,同时也是苦难历经者。潜文本的深意,更启发读者思考小说表层文本悲剧背后的“因”。
三、叙事投影
叙事投影[4]是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提到的关于选择性视点的语式调节方式。读者可以发现,《路》中的叙述者不是人物,不在情节中出现。《路》采用了零聚焦和外聚焦的视角。零聚焦就是全知聚焦。叙述者无所不知,进而对作品中的人物,环境,心理等各个要素进行细致入微和全面统一的把控。叙述者聚焦父子的动作和语言,冷静客观叙述。学者阿思海姆认为“运动是最容易引起视觉强烈注意的现象。”[5]整个作品的叙事过程主要以父子的一串串行为和动作构成。动作的下意识和连贯构成了故事内部的发展脉络。动词侧重于生死一线的迅速切换。父与子的下意识行为都是隐身的具体化和保全性命的权宜之计。文中对话都由短句构成,简洁恰恰带来了速度和力量。含蓄陈述实现了深层意图和表现形式的统一。读者跟随作者的叙事节奏快速地调整切换,完成跌宕起伏的感官体验。
小说中多次将叙事焦点投射到父亲的梦境。“剧院里与她同坐,她倾身向前听着音乐。金色的涡云饰纹、墙上的烛座、舞台两侧高垂下圆柱般的雅致帷幕”。[2]这映射出父亲对妻子的怀念。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愿望的实现”。[6]这也恰恰反映出现实的残酷和无奈。让读者深刻体会到过去与现在的时间距离在父亲心灵中撕扯的痛。这样形成的时间张力映射着过去,再也回不去的苦涩。小说中父亲将妻子的照片丢在路上,这个细节让读者感受到父亲的理性与无奈,要想活下去,就必须丢掉所有的牵挂,保留精力和体力为“隐身”时刻准备着,斩断所有干扰自己“活”的念想,淡没自己的存在感。
焦点的投射,完美地折射出父亲性格的悖论特质。坚强与柔软、真情与麻木。父亲对儿子的一举一动自然地流露出爱的印迹。“可口可乐”“糖水”“维生素D”这些词无不表现出父亲的细心和对儿子的关爱。“拉紧”“看”“摸”“亲吻”这些感官动词,让读者为父亲静默的爱而潸然泪下。父亲的手对儿子而言,是爱,是安全感,是力量。而父亲面对他者的生命,表现的是麻木和“看不见”。面对路途中遇见的小狗,可怜的小男孩和受伤的老人,父亲毅然决然地选择“不管不问”。然而父亲的“假”存在并非真的没有知觉,视觉,感觉和情绪。“真”隐身也并非真的没有眼泪和痛。在小说的结尾,儿子问父亲,那个小男孩会不会有事?会不会迷路?而父亲的回答终于卸下了伪装的面具。父亲认为“善”可以找到那个小男孩。这种巨大的对立,让读者感受到父亲角色的深度和厚度。在这个破碎的世界,父亲只好蒙上自己的眼睛,丢下一切的挂念,冰冻自己的思想,麻木自己的灵魂,才能活。父亲想要变成一个别人看不见,自己也看不见别人的“隐身”人。这是对儿子的负责,因为儿子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动力。而他本身从始至终都希望自己和儿子维护人的尊严,做“好人”。他用行动捍卫道德伦理和人类的尊严,甚至不惜将自己保管的左轮手枪朝向自己和儿子的脑袋。父亲矛盾的特质恰恰增加了叙事感知的美感,启示读者思考生命的价值。
四、结语
科马克·麦卡锡善于运用独特的叙事技巧,探讨深刻的社会命题。本文尝试从“隐身”叙事的角度出发,从隐身与叙事进程、叙事中的潜文本以及叙事投影三个维度来分析和挖掘《路》的审美价值。通过父子的求生历程,启发人类重新审视“认识自己”的深刻哲思,从而铭记“我是我”的深刻含义。小说映射了人类文明的退化和缺失,渴望唤醒人类的灵魂,回归真善美的人性,重拾美好的道德。进而人们不再试图“隐身”,而是人们愿意互相交流,互相包容,共同打造一个和谐美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一个色彩斑斓的美丽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