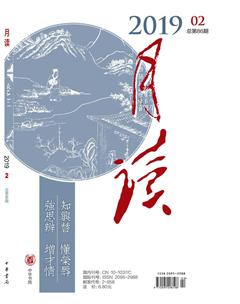《古诗十九首》:与《诗经》相媲美的五言古诗选
钟岳文
《古诗十九首》是南朝梁萧统编《文选》时,从传世的古诗中选录出的。这十九首五言抒情短诗出现后,得到了诗论家的广泛赞誉,比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称其为“五言之冠冕”,钟嵘在《诗品》中赞其“一字千金”,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推其为“古诗第一”,并做出“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这样的评价,吕本中在《吕氏童蒙训》中则说“诗皆思远而有余意,言有尽而意无穷也”。可以说,《古诗十九首》是中国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后人往往将其与《诗经》相提并论。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及创作年代
谈到诗词,首先要说的就是作者和创作时间,然而《古诗十九首》中的诗歌在这两点上却是模糊甚至存在争议的。
当初萧统编选这十九首诗的时候,就是由于无法考证清楚诗的作者和创作年代,因而总题为“古诗”,并以诗的首句为题,列入“杂诗”一类。稍晚于萧统的南朝梁陈间的徐陵编纂了一部诗集叫《玉台新咏》,他将《古诗十九首》中的《西北有高楼》《东城高且长》《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明月何皎皎》八篇题为“枚乘杂诗”,后来甚至有人认为这十九首诗都是枚乘的作品。
对于这个观点,学者在研究后给予了否定。钟嵘《诗品序》中说:“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褒)、扬(雄)、枚(乘)、马(司马相如)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说的是五言诗起自李陵,而枚乘的生活时代在李陵之前,那时还没有五言诗出现;而且枚乘是“吟咏靡闻”,就是说他没有从事过诗的创作。
另外,《文选》中有陆机《拟古诗》十二首,凡是《玉台新咏》中认为是枚乘的作品,均已擬及,如《拟行行重行行》《拟迢迢牵牛星》等;又刘铄《拟古诗》二首,也在《玉台新咏》枚乘诗之内。但陆、刘称其为“拟古诗”,而不是“拟枚乘诗”。陆机和刘铄生活的时代要早于徐陵,其说法应该是可信的。
正如钟嵘所说“古诗眇邈,人世难详”,《古诗十九首》中每首诗的作者如今已难知其详。当今学界一般认为,这些诗为中下层文人的作品,非一时一人之作。
至于这十九首诗的创作年代,从西晋陆机的拟作我们可以得知,这一类的诗在西晋初期已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肯定是西晋以前的作品。从《文选》的排序看,是认为这些诗创作于汉代,但不确定是西汉还是东汉。当今学者研究认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并综合现存的汉代诗歌来看,不到东汉末期,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出现像《古诗十九首》这样成熟的五言诗,这十九首诗虽然不是成于一人之手,但却是同时代的产物。
《古诗十九首》的诗歌渊源
清初诗人、文学家王士祯在其《渔洋诗话》中说:“《风》《雅》后有《楚辞》,《楚辞》后有《十九首》,风会变迁,非缘人力,然其源流,则一而已矣。”这段话告诉我们一个文学现象,就是《古诗十九首》与《诗经》《楚辞》乃至乐府诗有着一个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弄清这个关系,对我们理解这十九首诗是很有帮
助的。
有学者提出:《古诗十九首》可以兴感人之情意,可以考见得失,观察流俗。其辞温柔敦厚,和而不流,言情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写家庭之情感,陈政治之得失,刺人伦之道,无不赅括,其中多托物比兴,用鸟兽草木为譬,足以资多识。凡诗之性情、倚托、比兴三者,莫不包涵,其所以能独高千古,盖得助于《三百篇》之遗意。《三百篇》指的就是《诗经》,这段话高度概括了《古诗十九首》与《诗经》的继承关系,无论是题材内容、情感抒发、诗歌风格还是写作手法都有《诗经》的遗风。
就题材内容来说,《古诗十九首》是以游子怀乡和思妇怀人为基本内容的,这类题材的作品在《诗经》中多有反映。如《诗经·小雅·采薇》就是一首典型的思乡诗,“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唱出了从军将士的艰辛生活和思归情怀。《古诗十九首》还反映了士人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以及人生观的转变。这类诗歌在继承《诗经》传统的同时,又融入了汉代士人阶层的生命意识,是因时代背景不同而产生的思想改变。
就情感表现方式来说,《古诗十九首》语言质朴凝练,有《诗经》之遗风。诗的作者还擅长引用和化用《诗经》中的诗句和典故。比如《迢迢牵牛星》中“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提到的牛郎星和织女星,在《诗经·小雅·大东》中就出现了:“跂彼织女,终日七襄”,“睆彼牵牛,不以服箱”。
就叙事和抒情手法来说,《古诗十九首》继承了《诗经》的“赋”“比”“兴”,像“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就是托物比兴。
就诗体来说,《诗经》以四言为主,《古诗十九首》对此有所突破,以五言为体。这是由于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人们情感的增加,四言的形式已经不能承载所要表达的内容了,于是必然要产生新的形式。这反映了文学表达形式和情感内容的辩证统一。
再说《古诗十九首》与《楚辞》的关系。《楚辞》以屈原的《离骚》《九章》《九歌》等为代表,从主题来看,主要反映了被流放之人的失意、求索、怅然,以及去国离乡的悲伤苦闷之情。《古诗十九首》同样是汉末失意文人的抒情作品,同样反映了去国怀乡的流离之苦以及被时代贻误的哀怨苦闷。这是与东汉末年的社会状况相符合的。当时,宦官、外戚把持朝政,社会动荡不安,卖官鬻爵之风盛行,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文人由于没有门路,只能游宦于世,用诗歌将自己的失意、愤懑表达出来。
以《古诗十九首》中《涉江采芙蓉》为例。第一句“涉江采芙蓉”中的“涉江”就是《楚辞·九章·涉江》的题目,同时也活用了《涉江》的本意,即诗人起早贪黑在江畔求索,采鲜花和芳草,以寄托所思。后面的“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活用了《楚辞·九歌·山鬼》中的诗句“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句意相同,并且在诗中都起到了点明主旨的作用。
最后看《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的关系。这里有必要先解释一下什么是“乐府诗”。乐府初设于秦,是当时“少府”下辖的一个专门管理乐舞演唱教习的机构。汉初,乐府并没有保留下来。到了汉武帝时,重设乐府,职责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乐府搜集整理的诗歌,就叫“乐府诗”,简称“乐府”。
《古诗十九首》在语言上继承了乐府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平浅自然的特点,如“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等句,亲切而又朴素,浅近而又真切,无需注释,今人也能知道它所描述的意境和内容。同时,《古诗十九首》的语言还具有凝练和蕴藉的特点,契合了古代文人创作的习惯,其凝练来源于典故的运用,其蕴藉来自于真情实感的流露。
《古诗十九首》还继承了乐府诗的质朴之风。明代钟惺、谭元春合编的《古诗归》中则说“苏(武)李(陵)、《十九首》与乐府微异,工拙浅深之外,别有其妙。乐府能著奇想,著奥辞,而古诗以雍穆平远为贵。乐府之妙,在能使人惊;古诗之妙,在能使人思。然其性情光焰,同有一段千古常新、不可磨灭处”。这是道出了《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在格调、境界上的差异。
从诗的写作手法上来看,乐府诗长于叙事,《古诗十九首》长于抒情。前者多采用铺叙的手法,其人物形象比较鲜明;后者侧重融情于事,人物形象带有普遍性。前者多以事情本身的发展脉络和走向为结构,后者侧重以情感的起伏转换为线索。
总之,《古诗十九首》从《诗经》《楚辞》、乐府诗中汲取了充沛的营养,同时又有所发展,从而使五言诗成为一种成熟的文人诗体。
《古诗十九首》的叙事内容
纵观这十九首古诗,其叙事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生命价值的叙事。《古诗十九首》中不乏对生命的描述,像《青青陵上柏》中“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就描述了人生命的短暂。对前两句诗,后人注解称:“前者就颜色言之,后者就形体言之,都是永恒不变的。用以兴起对生命短暂的感慨。”《回车驾言迈》中“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表达了作者见到花草树木容易凋谢,感叹人生易老,岁月易逝,而自己还不能功成名就。从中我们能够看出诗人的生活状态,以及他对生命的关注和思考。
此外,还有作者提出了不必因生命的长短而放弃人生乐趣的观点。如《生年不满百》中所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又如《驱车上东门》是诗人游经北邙山时,远远望见一片墓地,突发的感叹。诗中最后两句“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表达了作者对求仙、追求长生不老之术的反对,和对及时享乐的赞同。应该指出,这是诗人在东汉末年黑暗动荡的社会环境下所反映出的人生态度,难免带有消沉、消极的色彩,我们今天在读这些诗的时候对此应当有所注意。
其次,是思妇怀夫的叙事。《古诗十九首》中有各种离别情形,夹杂的也是不同的思念。以一個遭“弃捐”的女子的口吻写的《行行重行行》一诗,“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一连四个“行”字,写出了丈夫远行的漫长,也意味着归期未定。最后一句“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将对丈夫的思念、埋怨统归于切切的关怀,一片柔肠,令人动容。
思妇的情节在《古诗十九首》中往往呈现为内心的寂寞苦闷,对丈夫的无比思念。如《青青河畔草》一诗:“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其中“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写出了女主人内心的寂寞。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表明了诗歌的人格魅力和真实性。南宋诗论家严羽也说:“一连六句,皆用叠词,今人必以为句法重复之甚。古诗正不当以错论也。”六个叠词,写出了思念的不间断性和延续性。其他像《客从远方来》《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也是关于思妇在家中思念远行丈夫的诗,感人
至深。
第三,是对游子思归的叙事。对于每一个身处异乡的游子而言,回家往往成为一种奢侈。对家人的思念,对故乡的眷恋,成了漂泊异乡的游子心中的期盼。《古诗十九首》中的《涉江采芙蓉》一诗:“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作者睹物思归,看见路边的一草一木都会勾起自己那份浓浓的思归之情。
第四,是对士人失意的叙事。东汉末年,社会动荡,危机四伏,许多士人有能力却没有一展身手的机会,只能苦闷、忧郁、彷徨、苦叹,对社会的不公表示不满。《西北有高楼》这首诗叙述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情形,其中的“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表明诗人不苦恨自己的才华没人赏识,而是恨朝廷不能给有志之士施展的舞台,主人公的苦闷,恰恰反映了当时社会腐朽不堪的状态。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
《古诗十九首》之所以能在中国诗歌史上产生巨大的影响,主要源于它的艺术性。
首先,如前文所说,乐府诗长于叙事,《古诗十九首》长于抒情。这十九首诗中有不少关于自然景物和环境的描写,但它不同于晋、宋以后的山水诗和咏物诗,而是为表现作者的主观心情而做出的必要渲染和衬托。比如《回车驾言迈》中“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四句,写的是春天野外的景色,但我们读过之后,会自然而然地体会到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空虚无着落的悲凉感。又如《生年不满百》中“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夜苦长,何不秉烛游”四句,表面看是在阐明一个道理,其实这是一种人生的感慨,是感情的波澜而非理性的观点。
这种抒情,《古诗十九首》用最点睛的笔墨将其描绘出来,有些是委婉含蓄,余意无穷;有些是慷慨激昂,淋漓尽致。在变化中寻求统一,在参差里取得和谐,表现出了高度的概括性。这种高度的概括性,源于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使其全部的感情发酵、酝酿出来,这样,从他心底流露出的语言,就会像美酒一样,量越少,质越醇,越能使人沉醉。刘熙载《艺概》中说:“《十九首》凿孔乱道,读之自觉四顾踌躇,百端交集,诗至此,始可谓言之有物矣!”正因为作者把大量的生活材料加以高度的概括,才使人感到“言之有物”,同时在抒情效果上具有独特而深刻的感染力。
其次,具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其形象性必然很强,《古诗十九首》也不例外。《行行重行行》中用“衣带日已缓”“思君令人老”来写离别之情,使人从身体、容颜的具体变化中看出久别深思的苦痛。《今日良宴会》中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尘”,用暴风和被暴风卷起的尘土来形容人生短暂。《西北有高楼》中的“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是用音乐的旋律表现人内在心情的激动。《明月皎夜光》中的“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是用具体的行动和事物来形容曾经友情的深厚以及现在的漠不关心。这种例子还有很多。
尤其要指出的是,这十九首诗的每一篇都自然地构成了一个完整而鲜活的艺术形象。《青青陵上柏》描写洛阳,于是我们面前就浮现出一幅动乱时代都市生活的画面。《驱车上东门》描写墓地,它所展示的就是一个阴森萧瑟的世界。《今日良宴会》把失意之士酒酣耳热、慷慨激昂的场面刻画得十分逼真。无论哪一篇,都蕴藏着诗人的思想感情,诗中所体现的不仅是生活的具体画面,更是诗人的心灵感受。
《古诗十九首》所描绘的形象虽然丰富多样,但无论它的内涵如何复杂深广,其给予我们的感受却是异常的单纯与清新。陆时雍《古诗镜》中说:“《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深衷”和“长情”是就诗的思想而言,“浅貌”和“短语”是就诗的形象而言,短短八个字的评语,体现了诗歌单纯清新的风格,以及诗人高度的概括能力。
最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是文人,诗的语言自然带有文人诗的色彩,但是,它不同于汉赋,这十九首诗的语言是质朴又生动自然的百姓口语的集中和提高。究其原因,大概缘于诗的作者是中下层失意文人,他们对自然或人生的体验是比较深刻的,又了解民间文学的特点,同时更愿意将自己的情感用诗的形式说给与自己身份、地位相似的人听。这就使《古诗十九首》呈现出民歌的气息,以及一种生动而自然的语言风格。正如谢榛《四溟诗话》中说:“《古诗十九首》格古调高,句平意远,不尚难字,而自然过人矣。”又说:“《古诗十九首》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举例来说,《孟冬寒气至》中“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明月何皎皎》中“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这些语句让我们感觉诗人像是透过文字在与我们对话,把诗的语言运用得像口语一样亲切质朴。
当然,由于诗的作者是富有才气的文人,所以诗中也运用了典故、成语,从而把丰富的内涵融入到简约的语言中。像《明月皎夜光》中作者用“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来述说他和友人今昔交情的变化。“携手好”,用的是《诗经》中的词语。《诗经·邶风·北风》中说:“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其虚其邪,既亟只且。”后面的“遗迹”一词,是比喻的用法,说的是友人丝毫不顾念旧情。这个词来源于《国语·楚语下》:“(楚)灵王不顾其民,一国弃之,如遗迹焉。”我们了解了“遗迹”这个词的出处和含义,就能深刻体会到诗人对这位曾经的友人是多么怨恨了。
总之,从手法,到形象,再到语言,《古诗十九首》都有着很高的艺术性,这使它成为流传千古,至今仍被人们吟诵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