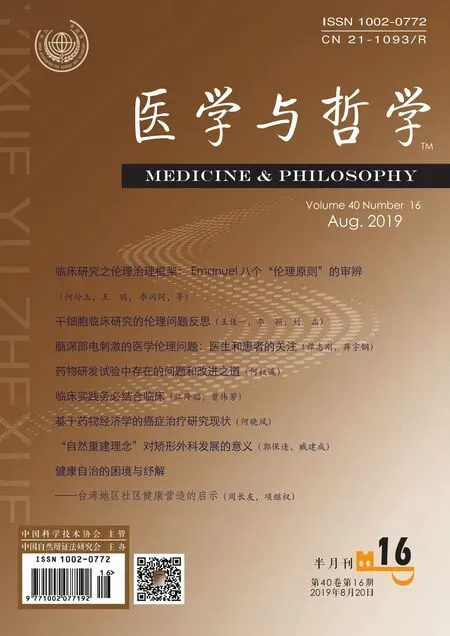美国医生的语用身份建构研究*
林馥嫌
医患会话是指在医疗工作状态下,医生和患者(或家属)就疾病、治疗、健康等方面所展开的口语活动[1]。通过医患之间的沟通,医生实现了询问病情、给予建议、找到解决方法、治疗疾病等目的[2]。医患会话具有典型的机构性话语的特点,即遵循一定的标准模式,具有一定的规律性[1]。研究医患会话中医生的语用身份建构,有助于发现医生对角色的期望和对实现和谐医患关系所采取的语言策略,值得学者们关注。本文拟从语用学角度分析医生在与患者对话的过程中,如何随着交际语境的变化调整语用身份以实现特定的交际意图。
1 语用身份理论
身份是主体的自我认知[3]。学术界对身份的解释主要分为两类: 其一,传统社会语言学认为身份是个体进入社会互动前的固有属性或自我标签,如出生地、性别、职业、年龄等[4]。此派观点从身份的本质主义概念出发,持身份静态观,排除了身份具有动态性、可选择性和蓄意性的特点[3]。其二,语用学主张从身份建构的言语交际特性出发,分析交际双方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有意选择某种语言手段,建构某一身份的人际交往动机[5]。因此,身份与话语息息相关,说话人意欲建构的身份影响他如何生成话语,而生成的话语又有助于塑造身份、促进交际[6]。
身份动态观点最具代表性的国内学者为陈新仁,他认为“语言交际者有意或无意选择的自我或对方身份,以及说话人在其话语中提及的社会个体或群体的他者身份统称为语用身份(pragmatic identity或identity in use)”[7]。语用身份试图探究交际者如何在特定的情况下施为目标、调节或巩固人际关系等交际效果[8]。
语用身份是语境化的、伴随特定话语的某一个或多个社会身份,具有以下特征:(1)语用身份的选择与建构以交际的发生而开始,以交际的结束而停止,具有交际依赖性;(2)身份的选择依赖于交际对象,且随着交际的推进而不断被调整、更改,而被调整、更改的语用身份在交际中起了不同的作用;(3)交际者在特定的交际阶段选择、建构什么样的语用身份具有主观性和蓄意性[7]。综上,语用身份并非交际前就确认的,而是交际者根据交际目的、交际语境以及交际对象有目的选择建构、变更的,不同身份的选择反过来对交际产生不同的影响[7]。
2 医生的身份研究现状
目前,学术界在研究医生身份方面已经取得一些成果。袁周敏等[9]以中文医药咨询会话为语料,分析了语用身份建构的可变性表现和商讨性运作。梁海英[10]从会话分析的角度,剖析国内门诊医患会话中的医生角色。夏玉琼[11]以身份表征为框架,从群体、人际和个体三个层面考察国内医生多元身份的建构。刘畅等[12]解析了医生如何灵活地运用语用身份,与其心理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相顺应,实现具体的交际目的。夏玉琼[13]则基于Simon的身份自我方位模式,考察国内医生通过网络与患者互动时构建的身份。谭晓风[14]从群体身份、关系身份和个人身份三个层次探讨国内医生身份建构和语言表征的相互关系。综上,现有的研究成果大都基于国内门诊会话语料分析中国医生的身份,探析英美国家医生语用身份建构的研究成果甚少,而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如何建构和谐的中国医患关系具有启发作用和现实意义。鉴此,笔者拟以语用身份为视角,以美国医患会话为语料,阐析美国医生如何通过语言策略建构语用身份,促进医患交际顺畅进行。
3 美国医生的语用身份建构策略
本研究的医患对话均来源于美国经典医疗剧《急诊室的故事》(EmergencyRoom)。该医疗剧已获得多项大奖和提名,其语言场景源自于医疗环境,取材于现实生活,且大多数病例具有真实性和典型性,因此可作为研究医疗对话的英文语料。对话包含了不同的疾病,即心内膜炎、溃疡、艾滋病、癌症,以下例子均注明语料来源。笔者意欲探讨的是医患会话中医生的语用身份建构,因此选取视频中涉及医生和病人对话的部分,医护人员之间的会话不列入统计范围。
笔者在充分研读语料的基础上,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分为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定量研究,手工标识并统计体现美国医生语用身份建构的人称、情态动词和语气等语言策略的数量。第二阶段根据定量研究的结果定性分析这些语言策略分别建构哪些语用身份。两个阶段的分析旨在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其一,在医患交际过程中,美国医生主要建构哪几种语用身份类型?其二,每种语用身份如何通过语气、情态和人称等语言策略实现?
视频语料中医生话语共174句。在语气层面,陈述句所占比例最高(104句),其次是疑问句(51句)和祈使句(19句)。就情态动词而言,含有低量值情态的话语最多,占21句;而中、高量值情态的句子各为7句和0句。
医患会话作为机构性话语,具有不同于日常言语交际的话语程式、话语角色、话语权力与权势关系等,其身份建构也有别于日常交际[15]。考察美国医患会话语料后,笔者发现美国医生在与患者及其家属言语互动的过程中,会根据交际语境及交际目的建构多种语用身份,以下将从语料中选取例子逐一分析美国医生在医患会话中的语用身份。
3.1 建构医学专家身份
Heritage[16]认为交际双方掌握和熟悉各自的信息域,对具体知识吸收程度也不尽相同。因此,交际者在认知梯度上的位置也不同,掌握较多知识的一方处于(K+)的位置,掌握知识少的另一方则处于(K-),此相对的位置为个人的知识状态,包括交际者对具体知识的认知、知识的丰富程度和与某些知识域相关的权利等。交际双方的知识状态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具体交际状况的变化而变化。他们的相对位置可能处于从完全的不对等到几乎完全对等之间的任何一个状态。知识表达就是交际者在话轮中如何表现自己的知识状态从而定位自己与知识的关系[17]。
语料中陈述句占总句子数量的59.8%,医生运用陈述句的场合包括对病情或检查结果进行判断、分析与评估以及提出诊疗或康复方案等。在这些语境下,医生需要建构医学专家身份,语言上主要表现为专业医学术语的使用,这体现了医生的专业性特征,表明医生在认知梯度上处于(K+)的位置;而树立的专家身份凸显了医生的权威和权势地位,有利于赢得患者的信任与尊重,促进交际顺利进行。
例1:格林医生:你女儿最近受过伤吗?接受过治疗吗?
病人的母亲:两周前她去看了牙医,清洁了牙齿。
格林医生:她可能患有心内膜炎。细菌在血液中扩散并在心脏瓣膜周围引发感染,这可以用抗生素治疗。(心内膜炎)
向患者解析病情是展现医生专业知识的重要场合,医生在这些场合需要主动建构专家身份。例1中格林医生使用许多专业性和学术性的行话,如判断病情时用“心内膜炎”;分析病情时使用了“细菌”、“感染”和“心脏瓣膜”;在提出治疗方案时使用了“抗生素”。医生的个人知识状态处于(K+)的位置,而患者的母亲属于(K-)的一方;医生在选用一系列的专业词汇解析患者病情中建构了专家身份。这一身份的选择有助于格林医生在患者及其家属面前塑造一个具备较高医学专业水平的权威医生形象,更容易取得患者的尊重与信任,推进诊疗工作顺利开展。
和美国医生一样,中国医生解析、诊断病情时亦借助专业词汇构建专家身份,该身份在一系列的医学专业词汇、患者因疑惑发问和医生进一步解释中建立起来,实现解析病情和诊断分析的目的。换言之,使用医学术语是中国医生有意识塑造专家身份的语言策略[2]。
3.2 建构平等的朋友身份
医生通常会根据特定的交际语境,并基于自我和患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断调整身份,这表明语用身份存在可变性、蓄意性和互动性[7]。机构性话语的特殊性在于医患之间原本不认识对方,双方的心理距离较远。出于缩短与患者之间的社交距离以及安抚患者情绪等交际目的,医生在某些场合偏向于建构带有情感色彩的朋友身份[7],这一身份可以服务于医生的交际目的——调节医患之间的人际关系。语料中美国医生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建构朋友身份。
3.2.1 称呼语的选择
称呼语反映了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和亲疏关系。使用不同的称呼语表明美国医生有意识地顺应不同的交际语境而采用的相应的元语用策略[18]。他们根据语境对病人选用不同的称呼,均体现医生有意弱化自己权威、强势的形象,建立朋友身份,缩短与病人间的距离。
例2:嘿,小伙子!比利,你吐血了吗?你感觉到疼痛吗?好的,你能指出疼痛的地方吗?这里痛吧?你以前吐血过吗?吐过多少次?噢,这是我见过的第一例8岁胃溃疡病人。(溃疡)
例2中比利是一位内向、害羞的小患者,他因为紧张不愿意配合医生的问诊。此语境下,医生没有以高高在上的机构身份和患者谈话,而是称呼他为“小伙子”,这一称呼语的使用,树立了亲切的医生形象,建立了与病人的朋友身份。该身份缩短了医生和比利之间的心理距离,安抚、劝慰了小患者,使其克服了之前的恐惧,实现了医生的交际目的。
例3:艾莉森太太?嗨,我是本顿博士。 我们需要您的许可才能进行紧急结肠造口术。(艾滋病)
例3中本顿医生不仅对病人使用尊称“您”,主动抬高对方身份,降低自己的地位;且亲切地打招呼并做自我介绍,这些语言策略缩短了双方之间的语用距离,和患者成功搭建了较为亲密的朋友身份;这一身份的确立使后续交际更加顺畅,维护了和谐的医患关系。
3.2.2 人称“我们”的选择
例4:苏珊医生:根据你咳血、体重减少和X光检查的情况,有可能得了癌症。但诊断尚未得到证实,很可能是另一回事。在我们确诊之前,我们都不应该匆忙下任何结论。(癌症)
例5:格林医生:我们还需要验血和胸部X光检查,这可能是肺炎,也有可能是早期心力衰竭。
病人的母亲:哦,天哪!(心内膜炎)
研究语料发现,美国医生会在特定交际语境选择使用人称“我们”建构朋友身份,调节与病人之间的人际关系。语料中医生使用的“我们”指称包括两种情况:其一,包含患者和医生的“我们”共3例。例4的“我们”兼指医生和患者,病人可能是癌症患者,心情比较沮丧。格林医生有意用“我们”,意欲预设一种联盟关系,以此建构朋友身份,打破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对立,与患者结成情感共同体,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号召力[19];其二,不包括医生和患者的“我们”共20例,如例5。就语义而言,此处用“我”替代“我们”并没有改变话语的含义。医生在自我指称时有意采用“我们”而不是“我”,其交际目的在于使医生从权势或主体性地位向平等关系方向下移,向亲密、谦逊方向倾斜,以此造成增加双方共同点的假象;建构了心理距离较近的朋友身份;这有利于病人在情感上产生同类感而服从或接受医生的主体性地位[20]。换言之,医生在人称选择上使用“我们”,是其根据特定语境主动选择的结果,目的在于与患者建立较为亲密的语用身份,缩短医患间的心理差距,使言语行为更容易为病人接受。
在医患交际过程中,如何选择得体的称呼语对建立融洽的医患关系起了重要作用。调查中国医患门诊会话结果显示,国内医生也使用“我们”、“您”和“小伙子”等称呼语主动降低权势地位,拉近医患间的距离,表达了他们谋求与病人平等的意愿[21]。
3.2.3 情态动词和祈使句的选择
美国医生倾向于选用中、低量值的情态动词“也许”、“可能”等,避开诸如“必须”、“不得不”之类的高量值情态动词。这些语言策略表明他们主动降低权势地位,建构较为平等的朋友身份的意图。
例6:洛根太太,在我检查你儿子的时候,也许你最好在外面等。(溃疡)
例6中,医生增加了低量值的情态动词“也许”,减弱自身的权威身份,建构朋友身份,有利于实现该语境下医生的交际目的,即与患者维持较为和谐的人际关系。医生降低权势地位,好言劝说,洛根太太同意在诊室外面等候。如果医生直接用“我检查你儿子时,你必须在外面等”,则表示他的权势地位高,与患者之间的心理距离远,亦不利于维持医生的亲和力,增加患者的抵触心理,也许会使交际受阻。
医生由于其职业声望、拥有的医学知识、情景权威以及病人的情景依赖等原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交际中的权势一方[10],在知识状态中处于(K+)位置,但是研读语料,笔者发现美国医生并不倾向于使用祈使句建构权威身份,而是建构朋友身份。
语料中祈使句仅有16句,主要分为两类:其一,语气较委婉的命令,如“洛根太太,在我检查你儿子的时候,也许你最好在外面等”和“请您在外面等候”;其二,美国医生以患者利益出发,指引他们在当时语境下如何配合医生执行动作的祈使句,如“好吧,只要抬起你的腿就可以了”,“只要放松就可以了,轻松呼吸”。观察美国医生使用祈使句的语气,这两类均不属于语气强硬的命令型或禁止型的祈使句。医生选用语气较为柔和的祈使句是出于交际需要,意图在于主动降低权威地位,与患者保持相对亲密的关系。
与美国医生不同的是,中国医生使用的情态词的量值均处于中高位,如高量值词“得”、“必须”、“务必”等,中量值词“难于”、“不宜”等[21]。情态词量值差异是由中国医生和患者的角色关系和社会地位决定的。国内医生给予建议时还会使用语气较强的祈使句来构建权势较高的权威身份。祈使句具有无人称、语气强、言辞肯定、态度严肃等特点,带有强制性要求对方必须服从的意味[2]。医生大量使用中高量值情态词和语气强烈的祈使句都凸显医患不平等地位的现状,是语言服务于权力的表现[21]。
3.3 倾听者身份
可变性是语用身份最为突出的交际特征,它表明人们有意建构的任何身份并非稳定不变的。为了实现交际目的,他们需不断地协商、选择并调整自己的语用身份[7],又在具体的语境中体现出身份建构的动态性特征。因此,语用身份并非固化的,而是集流动性、变化性、复杂性、蓄意性和语境敏感性于一体的符号体系[3]。因此,医生的语用身份选择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具有动态性和策略性[7]。当病人情绪比较激动、低落、不稳定时,美国医生会根据交际目的,建构倾听者的角色,降低自己的地位,让病人在话轮中处于主导地位,以此达到安抚病人情绪的目的。
例7:病人:好的。是的,我想知道(我还有多长时间),因为我一直想带我妻子去那索。我们谈论过,但从没去过。所以我想,春天来了,再不去那索就太晚了。你知道嘛,她一直想在冬天晒黑,然后向邻居炫耀。
苏珊医生:我理解。
病人:是呀,所以我想最好去趟那索。夏天很快就来了,所以我想很快就该动身。医生,我要谢谢你,感谢你的帮助,感谢你告诉我真相,我真的很感激。我不想戒烟了。
苏珊医生:帕克先生,我的工作经验告诉我,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没有什么看起来非常糟糕,没有什么看起来非常好。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没有。(癌症)
因为医患关系的不平等,医生在医疗对话中经常处于强势的地位,控制着话语权,但也有例外情况,如例7。病人得知自己可能患了肺癌时,心情有些低落,跟苏珊医生谈论着生命结束之前的计划。医生在此特定语境下,没有控制话轮,没有使用专业术语建构专家身份,而是选择了倾听者的身份,让病人控制了话语权:例7中病人说了11句话,而医生仅说了4句话。患者在话轮占有量和长度上均占有优势。苏珊医生建构了倾听者的身份,提供给病人倾诉和发泄的渠道,有效地安抚了患者情绪。
医患会话属于较正式的机构性谈话,一般情况下,中国医生亦处于主导地位,掌握着话语权,占据高位。但有时为了达到治愈目的医生也会打破这种规则[2],且主动缩小医患间权力、地位对比,提高对患者疾痛体验的移情、共情能力[21]。
4 启示
医生可以利用药物和语言治病。药物的治愈作用不言而喻,医患会话过程中医生使用何种语言建构什么语用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医患关系是否融洽、治疗是否有效。本研究发现美国医生根据不同的语境建构以下几种身份,促进医患交际顺畅进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其一,医患门诊会话属于机构会话,中、美医生在需要强化医生的专业知识与说服力时,首先构建的都是既定的医学知识权威者身份。医生使用专业术语建构专家身份,能有效说服患者,有助于诊治工作顺利进行。美国医生使用语气较为委婉的祈使句,维持医生权威的同时增加了自身的亲和力,营造医患和谐的氛围。而中国医生给予病人建议时会使用语气较强的祈使句构建权势较高的权威身份,强制要求病人服从[2],医患之间的心理距离较远。本研究结果给国内医生的启发是,在树立专家身份的同时,更应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解释医学知识来改善因医生专业身份带来的医患权势失衡[14]。用语言策略表达与患者沟通协商的意向,如使用语气较为缓和的祈使句,以消弭因医患社会地位不平等产生的隔阂为取向,实现双方情感、思想趋同,构建和睦的医患关系[14]。
其二,除了专家身份,医生可根据语境需要建构朋友身份,多使用可以缩短与患者距离的称呼。例如,对长者使用敬称“您”;患者为年轻人直接称呼名字,若为孩童,可称之为“宝贝”,显得双方更亲密些。此外,医生亦可根据语境灵活使用第一人称复数指称语“我们”,以表明医生站在患者的角度编码语言,传递出医生设身处地为其着想的意愿,这有助于营造和谐、融洽的交际氛围。
就情态词而言,中国医务工作者使用中、高量值的情态动词居多。高量值情态动词使病人明显感觉到医生收缩与患者协商的空间,有意识地建构权威和权势地位,不利于亲密型医患关系的建立。医生应把握话语盟主优势,积极发挥话语资源建构身份的效用[14],减少使用“必须”这类高量值的情态词,转而根据交际目的适当使用“会”、“可以”、“也许”和“可能”等中、低量值的情态词,淡化自己的权势地位,顾全处于弱势的患者的面子,实现医患间的情感趋同[14]。
其三,国内医患对话中,医生处于主导地位,掌握着话语权,占据高位。医生应主动缩小医患间的权力、地位对比[14],不妨视语境需要有意弱化自己的权势地位,建构倾听者身份,如当病人身患重病、情绪低落时,医生可让病人暂时处于主导地位控制话语权或畅所欲言,这有利于安抚、稳定病人情绪。
美国医生语用身份的选择和呈现过程是动态的,是在特定语境下同患者共同建构的结果;此外,医生对语用身份的选择不是被动地反映在语言层面,而是在语气、情态和人称方面主动选择相关的言语策略并运用到话语表达中;随着语境的动态变化,美国医生也灵活地运用语言来建构不同的语用身份以实现具体的交际目的。总而言之,语用身份是医生在医患交际中为了满足某一交际目的而刻意选择的自我表达,是根据交际语境的变化积极、主动建构的。本研究成果有助于启发医生如何通过语言策略主动建构语用身份,维持医患之间的和谐关系,同时对其他机构性话语的语用身份建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