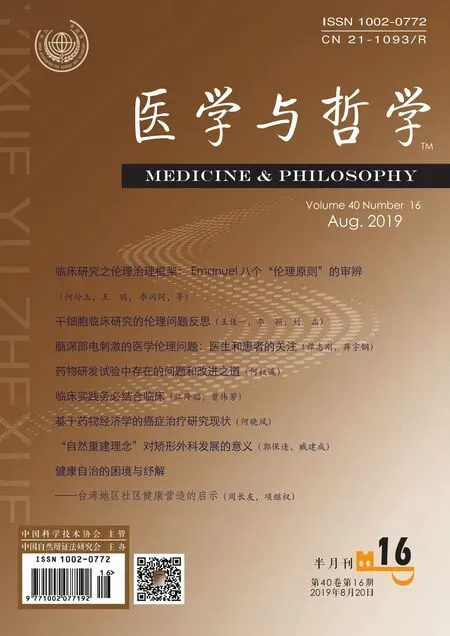脑深部电刺激的医学伦理问题:医生和患者的关注
谭志刚 蒋宇钢
脑深部电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是通过立体定向技术将刺激电极植入脑内特定核团,并同时在体表植入脉冲发生器(implantable pulse generator,IPG)以连接电极脑外端,发射可调节的电脉冲刺激神经核团,达到控制和改善症状的治疗技术。DBS不会对脑组织造成永久损害,且可根据患者症状变化调节参数来控制症状,基本已经取代了核团毁损技术。该技术1987年首次用于特发性震颤的治疗,取得鼓舞人心的效果,随后逐步扩展到中晚期帕金森病、肌张力障碍等运动障碍性疾病的治疗。我国北京天坛医院王忠诚院士于1998年指导实施了国内首例DBS手术治疗帕金森病[1],经历20多年发展,DBS在治疗功能性神经外科疾病,尤其是运动障碍性疾病方面取得了较快发展。DBS治疗中晚期帕金森病、肌张力障碍疾病、特发性震颤等疾病的疗效获得业内共识,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及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分别就DBS治疗肌张力障碍、帕金森及术后程控撰写了中国专家共识。国内开展DBS手术的医疗机构从仅有少数几个北上广大的神经外科中心扩展到各大医学院校附属三甲医院、省市三甲医院,甚至部分县级医院也“磨拳擦掌”,已经开展或准备开展。DBS治疗的疾病谱也有扩大的趋势。DBS技术的推广能使更多适合手术的患者获益,但在其应用过程中也存在一些新的问题和乱象,有必要对临床应用过程中出现的新老问题展开讨论,尤其是部分涉及医学伦理的问题,以进一步规范DBS的临床应用和临床研究,保护患者和医务工作者的权益。
1 不可忽视手术的并发症
相对于开颅手术而言,DBS手术属于通常意义上的微创手术,随着手术经验的积累,手术的并发症率处于较低水平。但微创不是无创,更不等同于无手术风险。并发症包括三类:(1)手术操作相关并发症:严重并发症主要出现在颅内,包括颅内出血、脑梗塞、颅内积气、癫痫、电极位置不佳等,这类并发症一旦出现轻则影响手术效果,重则可能危及患者生命。Fenoy课题组[2]统计了728例接受DBS手术的患者资料,术后无症状脑实质出血的发生率为0.5%,无症状脑室内出血为0.3%,症状性脑实质出血和脑室内出血发生率为1.7%、0.4%,其中有1.7%的患者出现偏瘫或意识障碍。(2)植入材料相关并发症,包括装置外露、颅内感染、导线断裂、囊袋血肿、异物感等。这类并发症过可以通过清创、抗感染治疗、更换装置等治愈,严重时也面临被迫去除所有植入材料的可能。(3)神经刺激相关并发症,包括感觉异常、异动症、肌张力障碍、头痛、胸闷、复视、抑郁躁狂等。多为非目标性刺激症状,主要原因是电极位置欠佳或靶点/参数选择不合适,是发生率最高的并发症类型。国内外有报道因刺激导致的暴躁伤人毁物的个例[3]。与刺激相关并发症可以通过调整电极位置、变换刺激触点、调整刺激参数等得到改善或消除。
2 充分关注手术的安全性
安全性和有效性是包括DBS手术在内的所有手术的基本要求之一。神经外科医生不可选择性关注和宣传DBS的疗效而忽视手术的安全性的挑战。DBS手术的安全性源自对手术全程的管控:术前对患者的严格评估筛选、术中细致的操作、术后患者自身对设备的保护。
以DBS治疗帕金森病为例,对有意向的患者首先应确定诊断,帕金森患者早期多对药物反应好,故不建议过早(在“蜜月期”内)接受DBS,同样太晚期患者生活自理能力差,并发症多,手术的作用也大打折扣。患者关期(患者关期是指抗帕金森药物药效过去的时期,是一个比较通行的说法,相对应的是“开期”,指药物起效的时期)处于Hoehn-Yahr 2.5期~4期是合适的手术时机,要求患者对多巴胺冲击试验改善率≥30%,同时需排除严重认知功能障碍,严重精神性疾病的不适宜手术情形[4]。DBS手术过程复杂,主要包括安装定向框架、术中磁共振/CT定位、植入电极、术中测试、植入脉冲发生器、连接电极和脉冲发生器。步骤繁琐,每一步还涉及许多细节和精细操作,只有经过专门学习和训练的神经外科医生才能胜任手术。DBS手术也是一个团队工作,要求麻醉医生、影像医生、护理人员密切配合。围手术期维持血压稳定、使用可视化的核团定位方法、器械护士的密切配合是提高安全性的重要保证。手术顺利的情况下,术后患者需注意保持设备的安全运行,注意及时给电池充电,远离强磁场环境,DBS设备在强磁场环境下可能会突然关机,所以DBS术后患者在进出安检门前、行磁共振检查前应向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做好关机准备。Nutt等[5]曾报道1例接受DBS的帕金森患者,在未关机的情况下于口腔科接受脉冲射频治疗,导致中脑损伤而成为植物人。
3 严格掌握手术指征,慎重对待扩大治疗范围
经过20多年的发展,DBS技术已经成为治疗中晚期帕金森病、肌张力障碍、特发性震颤等运动障碍性疾病的主要疗法。临床医生和设备研发人员并不满足于DBS在上述疾病治疗上的良好治疗效果,他们开始研究推动DBS能否在更多的疾病上发挥作用。相关研究表明,对于临床上药物治疗效果欠佳的难治性癫痫、抑郁症、老年痴呆等可能有潜在的治疗效果。癫痫患者中约有20%~30%为药物难治性癫痫[6],对于这类如能找到明确的癫痫灶,首选手术切除癫痫灶治疗,但对于癫痫灶不明确或癫痫处于发作的患者,治疗比较棘手。研究表明,DBS可通过提供电刺激改变癫痫网络的内在电生理特点,增加癫痫发作的阈值,产生抗癫痫作用[7]。Papze环路在癫痫的起源和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DBS治疗难治性癫痫的靶点多采用Papze环路中的丘脑前核[8]。Fridley等[9]发现以丘脑前核为靶点治疗药物难治性癫痫能显著减少癫痫发作,随访2年以上,癫痫发作平均减少70.4%。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 disease,AD),又叫原发性老年痴呆,是一类以记忆力减退、认知和语言障碍为主要表现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我国估计有500万~600万AD患者[10],AD的治疗手段有限,以药物治疗为主,但治疗效果欠佳。研究者观察到部分PD患者在接受DBS术后认知能力提高的现象,提出DBS治疗AD的想法。DBS刺激穹隆、丘脑前核或内嗅区可使海马发生增多。DBS治疗AD主要的靶点是大脑穹隆和下丘脑。2010年,Laxton等[11]报道了6例应用DBS治疗AD症状得到改善的患者病例。抑郁症是常见的精神疾病,患病率高达15%~20%,约有30%为药物难治性抑郁症(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TRD)。DBS治疗TRD的可能机制是DBS调节靶区细胞代谢功能,调节递质代谢增加快感,对抗抑郁[12]。研究最多的靶点是胼 胝 体 扣 带 回 (subcallosal cingulate gyrus,SCG)。Holtzheimer等[13]报道90例抑郁症患者接受DBS-SCG术,分为刺激组和对照组,刺激组抑郁症状也明显改善,但是术后6个月DBS刺激组和对照组无显著差别。
DBS对上述三种疾病治疗的研究处于不同几段,有的已经比较成熟,国外已经批准其临床应用,有的还处于探索阶段。欧盟和加拿大分别于2010年和2012年批准DBS用于药物难治性癫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也于2018年5月批准DBS用于部分发作的药物难治性癫痫的辅助治疗。约有8个DBS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临床试验正在开展中。目前,DBS的临床应用研究远不止这三种疾病,还包括强迫症、慢性顽固性疼痛、植物状态等,但是也应当看到,DBS对运动障碍性疾病的治疗机制尚不十分清楚,对这些新应用的疾病的治疗机制更加不明了,要区分临床研究和治疗的目标,鼓励创新的同时,加强基础研究,进一步把DBS的作用机制研究清楚,充分了解DBS在新的疾病应用时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审慎扩大DBS的治疗范围。
4 切实履行知情同意原则
医生或者临床研究者应该告诉患者手术操作过程、手术的必要性,手术风险等关键信息,征得患者或其代理人同意后方能实施手术。知情同意原则是临床诊疗的基本原则之一,包括知情和同意两方面内容。充分知情同意的前提是患者具有足够的认知和行为能力以及临床决策能力,但罹患帕金森、抑郁症、AD等疾病的患者本身就是认知行为能力不完全或丧失的人,或者其知情同意权部分被其家属剥夺,如何评估患者的行为能力可能是一个比手术更复杂的事情。
因此,临床医生在介绍这一新的疗法时应如实介绍其疗效,引导患者树立合理的手术效果预期,不可在术前夸大手术效果或给予不切实际的承诺。临床医生也应在术前详细向患者介绍手术过程和手术风险,告知术后安全使用DBS的注意事项。微创手术不等同于简单手术,要严格准入机制,神经外科医师开展DBS术前应经过严格的手术培训和术后患者管理培训。当然,随着手术技术的发展和经验的累积,目前总体手术风险是可控和可接受的。
根据这类患者的病情特点,制定相应的认知和决策能力评估表,如术前行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量表评估、蒙特利尔认知评估等。由无利益关系第三方客观评价患者的认知和决策能力,并制定适合本单位的标准,如患者的认知和决策能力受限不足以履行充分知情同意权时,应与患者的监护人沟通,由监护人行驶知情同意权。上述程序及临床研究应报伦理委员会审批。评估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只能说目前可行的方法是根据一些认知量表、智力量表结合医生和患者的交流后综合评估。医生会提供适合做或者不做的建议,但一般不会诱导患者去做,让患者或者其家属自己做决定。这个是基本原则。
DBS手术并不麻烦,只是步骤多些。目前基本在3小时~4小时可以完成,相比于某些颅底肿瘤手术, 这个时间算是一个中等大小神经外科手术的费时。DBS手术与其他有植入设备的手术的一个重要不同点是,DBS手术同时在颅内植入电极且在体表植入IPG,需启动IPG并完成程序设置(即程控)设备才能发挥作用。程控是医生根据患者临床症状调节刺激参数和靶点,调整刺激模式以达到治疗效果的过程。鉴于DBS设备的特殊性,我们必须意识到不相关人员恶意攻击DBS设备获取程控权限(非授权性程控)即所谓“brainjacking”的可能性。这种非授权性程控可以使针对某一特定患者的设备被劫持,也可以是非特异性的广泛的侵入DBS设备[14]。设备劫持者可获取患者的隐私病情信息,改变程控参数或者靶点,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导致患者的情绪和行为失控。目前,尚未见DBS设备被劫持的报道,但有其他设备被劫持的可行性报道,有研究者证实非授权性“劫持“植入式胰岛素泵的可行性。在实验室已经证实劫持这种智能设备是可行的[15]。因此应未雨绸缪。
没有设备和技术安全就谈不上治疗的安全。与其他植入设备的靶器官不同,DBS的治疗器官在脑。治疗效果需要程控调节实现。设备的安全运行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还可能影响人的行为和情感。所以设备生产商应在提高设备性能时应对设备安全给予足够重视,在研发时设置防止非授权性程控的保护措施。医疗器械审批机构在审核时用充分考虑到这一问题,以应对这一新技术可能面临的信息安全风险。
5 结语
随着DBS疾病治疗谱的扩展,越来越多的患者将受益于这一技术。鉴于需要接受DBS患者的特殊性,在开展这一手术时需根据实际情况严格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详细告知患者手术的获益和手术可能造成的并发症以及手术存在的风险。临床医生在扩大DBS治疗新的适应症时,应持严谨审慎态度,需要在多中心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的基础上,严格评估确认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扩展疾病治疗谱。设备生产商应格外关注设备和信息的安全,在设备信息安全上设置保护屏障,相关行业协会和医疗器械审批机构应该制定相应产品标准,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也应提上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