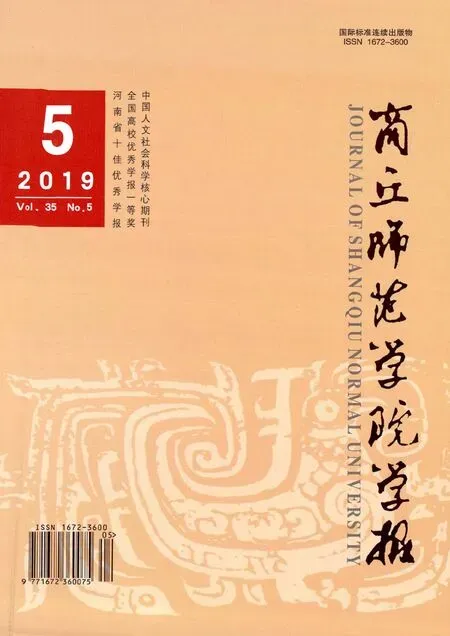天地整体及其秩序与自我的双重持守
——《庄子·天地》开篇的哲学阐释
郭美华 余敏
(1.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200433;2.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200234)
天地就是世界整体,是万物和所有物共在的整体,它必须保持自身的自在性,而不能被狂妄的僭越者据为私有之物:“世界是这样一种共同性的东西,它不代表任何一方,只代表大家接受的共同基地,这种共同基地把所有相互说话的人联结在一起。”[1]570无论以物性力量的方式,还是以观念力量的方式来“独占世界”的企图(尤其二者勾结起来独占世界的企图),都是对于世界整体本身共同性的毁坏,从而也必然引向对于差异性他者的毁灭。而每一个“我”,无疑都是一个他者的他者,自我以自身作为他者的方式遵循秩序容身于世界整体,这就是《庄子》生存论的要义之一,即一方面捍卫天地整体及其秩序的自在与自然,一方面持守自身的自然与自在(让自我以他者的方式实现自身)。如此观念,构成《庄子·天地》篇的主题,并充分地体现在《天地》篇的开端论述之中。
一
《天地》云:
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人卒虽众,其主君也。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观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以道观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泛观而万物之应备。故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记》曰:“通于一而万事毕。无心得而鬼神服。”
无限广袤的整体世界,无论多“大”,其变化都是“均匀”的:“均于不为而自化也。”[2]232对于无限整体而言,其变化之“均”,实质性的意义就在于,其内在的无数差异性个别物之自为其自身,或说自然而在其自身;同时,没有任何一物可以在其自身实现天地整体与其他无数差异性事物的存在:“天地之大,万化而未始有极也。”[3]225这是整体性世界及其万物存在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则是无数差异性个别物,其存在之实现遵循于同一个秩序,即“其治一也”,亦即“一以自得为治”[2]232“一则各复归其根”[3]225。“一”而又“自得”,“一”意味着普遍的秩序,“自得”意味着普遍秩序并不是无数差异性个体的“目的”,相反,普遍秩序以无数差异性个体为其目的。
两个方面的意义合起来看,就是无限性整体及其秩序,超越于任一个体而持存自身的自在性与自然性,从而使得每一个体都能成其为自身:“天地无心,所以均化;物物自治,所以齐一。”[4]369就此而言,人的存在就是同与异的统一:“于人见异,观于天则几无不同矣。”[5]102将仁义—政治之域的生存,回置于天地之间,则以普遍而相同之整体及其秩序为基,担保并让与每个人之自得其自身(独特之自然而自在),就是仁义—政治自身的目的与归宿,也是仁义—政治之域克服自身、避免扭曲的根本之处。
在无限性世界整体中,与万物并处共存者,有人。人群相聚而居的境域,并不悖于世界整体的本质及其秩序。人群整体并不以人群之中某一个独特个体为目的,而是经由群而让每个人自成其目的——在其自身并成其自身。这是人生存的自然(天)与本性(德)。人群作为社会,因为异于一般动物的世界而有礼义之治,但礼义之治并不构成其本质,更不能穷尽人自身存在的所有内容与意义。在此意义上,“君”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社会的治理者,一方面是每个人的自为主宰与自为目的。因此,社会治理之“君”,依据于无限性整体世界之“天德”(即自在整体及其秩序与每一物自在其自身的统一),使得每一个人都能自为其“君”。每一个人之自有其君,是人群之有君的本体论前提。任何一个人并不需要外在的他人来为之做主,也不需要外在地被赐予某种观念觉悟来使之自为做主。人群之君不能担保人之各有其君,就是人群之君本身的堕落与扭曲。
人之作为人而存在,并没有一个为君的圣贤作为起点。“玄古之君天下”[注]另一种断句是将“玄”属上句:“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后一句则是“古之君天下”。参见吕惠卿的《庄子义集校》第225—226页及王夫之的《庄子解》第101页。,即是无君而自然任运——“无为而天德”。天与德的统一,就是道,就是自然无为于他物而万物自正其自身。
每一个人之在,总是言行统一体,而言行都是心之官——身之君的外显[注]钱穆说:“‘君’或‘名’字之伪。”(钱穆《庄子纂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03页)如果是“以道观言而名正”,那就意味着从道的角度看,人类在认识论上以语言来把握事物,可以获得恰如其分的理解。不过,这个恰如其分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否定意义上来理解言说与命名的认识手段,即领悟于言说与命名不能切中事物自然之正。。从道的角度看每一个人存在的语言表现,每一个人之心作为其言行的主宰之君,都自为实现而正:“无为者,自然为君,非邪也。”[2]232而就人类社会治理而言,从道的角度看,君之获得其“正”,依据在于“天地、君、民之各得其自然”。君在人群中有某种殊胜之位,易于有为而戕害天地及其万物,因此,一般意义上,天地与万物(万民)之自然,就反转逼迫为君者有为于自身限制,而无为于天地与万物(万民)之存在。但是,为君者往往并不会自行限制自身而逾越为害,因此,万民(万物)反过来必须有为于限制为君者之作为而使得自身及天地整体得其自然。所谓“自然之正”,并不是一种直接现实性,而是一个“过程”,其中蕴含着无数的曲折与抗争。
每一物的存在均有两层关系:一是在无限整体中,其自身与无限整体及其秩序之关系;二是与同处整体之中的无数相异之它物的关系。相互关系构成一种对于关系任何一方的制约,使得相关者各处一定之“分”(即自是其身的位置)。从天道的角度来看每一物之“分”,无论就群体而言,还是就个体而言,其治理之君与其被治理之臣[注]尽管表面上臣似乎是君主用以治理百姓的“官员”,但是,在“臣民”的连用中,臣与民都是被君所宰制的对象。,都各是其自身而不相陵越。就个体而言,心为君,身为臣,这仅仅只是一种言说上的分别,而非主人与奴仆、本质与附属物的关系。人总是心身一体而在,心之为心,身之为身,虽相与为在,但心自为其自身,身自为其自身,身心共同从属于生命整体、共同依循于生命整体之秩序而在,并非简单地就是心支配主宰了身,或身是心之从属工具的存在样式。在生命整体的无边广袤与深邃中,潜蕴着无数的可能性,并非世俗的仁义—政治之域的君臣关系所能囊括。就人类群体而言,作为治理者的君与作为被治理者的臣,在流俗的意义上就是主从、本末等不平等的关系,但从道的角度看,一方面君臣同属于无限的整体世界及其秩序,一方面君臣各在其自身。因此,君与臣的意义,仅仅只有某种事实分工的不同,而无价值、等级上的分层。在一定意义上,君之治理人群,就是为了防止人群中的个别存在者侵犯整体及其秩序与其他个别存在者,而君由此取得的特殊位置,使得其自身成为最容易堕落而坏的侵犯者。因此,社会治理首要的前提就是防止治理者本身的腐化与堕落,担保整体及其秩序与其他无数个体不被侵犯。如此之意,就是社会治理中的君臣本然之义。
每个人都有自身的才能,无论是细民苟活,还是知效一官、行比一乡乃至于德合一君、能征一国(《逍遥游》)之人,这些“不同能力”的自然而恰适的使用,按其本质都是“自为自得”。但是。在流俗的扭曲中,知、行、德、能之“能”,与官、乡、君、国之“域”,取得了占有与被占有、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并以占有之量的大小来作为能力本身的证明,这就在个体与天地整体、个体与无数他者的关系上,造成了扭曲和纷争,使得一切物包括占有者自身都丧失了其自然之正。从道的立场看,能力之顺乎自然的实现,就是每一物之自为治理,以及社会治理之各有其序(尤其不同层次的治理者都受到秩序的制约),这就是“天下之官治”——既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 “每一不同位分之人的各得其治”,也是每个人自身所有官能的各得其治。然而,在历史与现实中,人类群体中的不同位分的人,以及每一个人的不同官能,并非都依循于自然而实现。以悖于自然的方式而展开的社会与个体的活动,在更为深一层的意义上显露了“天下之官治”——一方面是悖逆、扭曲以滚雪球的方式自我崩溃,一方面是悖逆、扭曲湮没中的自然微明亘古未绝而招引着复归与返回。恶的自我消解,也是一种“官能之治”,尽管大多时候这是过于昂贵的代价,但是,它是不能普遍而自由地坚持自然的必然。在庄子哲学的深处,由持守自然而自由之生存,所反逼出来的对于仁义—政治之域窄化人自身生存的抗拒,捍卫整体性及其秩序的自在性与个体的差异性,有着更为深邃的意义,即让有能者有所不能而无能者能自为其能:“以道观能,则无能也而无不能也,无能者无所不能则有能者有所不能。”[3]226
无论在自然之正的展开中,还是自然的扭曲展开中,每一物都或正或曲地“展开”自身。在“万物刍狗”的意义上,都是天地及其万物“得其治”。在自以为圣而担当天下责任的仁义之士看来,这不免有些犬儒主义的冷酷。殊不知,以对于尘世的情怀与抱负来为自身辩护,自以为圣的仁义者要么就是高蹈的空想主义者,要么就是沆瀣于权力的现实主义者,无论如何,都湮没了天地整体以及万物和每一物之自得其自身的通道。道作为无限整体及其秩序的统一,持守其自在性,而非为某种自圣化的理念所僭越,更不为流俗基于力量的斗争进行润饰与掩饰,反倒显露出天地与万物之本相——即“以道泛观而万物之应备”。换言之,在已经悖逆与扭曲的展开之后,让真实与朴素洗尽铅华而呈露自身,较之仁义—政治之域的夸夸其谈与伪为矫饰,更能昭示天地整体与万物回归自身的可能性通道。以遮蔽、欺骗与强压相结合的方式(即使理性的机巧或“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之类的思辨造作,也包括在内),堵塞天地及其万物回返自身自然而本然之存在的道路,这是庄子哲学对于仁义—政治之域的基本批评之一。在仁义—政治之域,尽管无数的有限性存在物不能以自然真朴之风吹散伪作之气,乃至于为仁义—政治的强制与伪作所侵袭束缚不得自身自然,但是,逸出狭隘仁义—政治之域的无名自然之朴,最终必将一切矫揉造作、欺骗伪饰、强制野蛮之气,扫荡洗涤尽净而入于滚滚洪荒之流中:“万物虽多,主之者一,造化而已。”[6]183
“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郭象注说:“万物莫不皆得,则天地通;道不塞其所由,则万物自得其行矣。”[2]233尽管郭象注一定意义上顺通了义理,但从道与德的意涵而言,这与德作为万物之得自道者,似乎扞格不通,可能是道与德字传抄错误了,应该是:“通于天地者,道也;行于万物者,德也。”[注]王叔岷说:“陈碧虚《阙误》引作:‘故通于天地者,道也;顺于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义也。’今当从之。”(王叔岷,《庄子校诠》上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13页。钟泰以郭注反对这个说法,《庄子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46页)陈碧虚加入一个“行于万物者,义也”,累赘了。实际上,可能只是原文道和德二字写反了。整体及其秩序自在其自身,即是道;而万物之各自得其得,即是德。唯有整体及其秩序不为任一个别物之德所僭越,才成其为道之自然,天地才能成其为自身而不为任一个体物所私有;如此天地在其自身而真正成为公共之物,道在其自身真正成为普遍者,每一物与所有物才能“共处一个天地,共由一个道”,并各自得其自身。郭象注,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更好理解,更为通透:每一物乃至万物自得其自身,是由天地整体及其秩序不为任一个别物所僭越、阻碍才得以可能,而不是相反;不是某一个别物之行造就出天地及其秩序,而是天地及其秩序不为任何个别物所僭越、阻碍,每一物乃至万物才得以顺其自身自然而行,并自得其自身,而不是相反。只有出自自我仁义膨胀的自圣之心,才会认为从自身之觉悟与行动中生成、创造出了世界整体及其秩序。
道—德的顺然畅通可能被碍阻而断,并不断堕落扭曲。在仁义—政治之域,有在上的治理者,他们以自身之心“意向”出物,湮没他物和天地的自然与自在,以为天下一切都是他们能力与责任范围内之“事”:“礼、乐、刑、政诸事。”[7]272在事中,一切成为在上之治理者手中的把玩之物,把玩完全指向把玩者自身的内在心境与情意,亦即他们炫技而为享乐之艺。万物在治理者的“技艺”中的展现,显然悖于万物之自在其自身。这个从道—德向技艺的堕落,《老子》第38章即已言之:“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在如此这般依然悖逆与扭曲的流俗生存中,从谋生之技需要不断返回于天。人类生存从天堕落的深度,相应着返回于天的难度。从技返回于事,从事返回于义(义是行事之合宜,一般是心物两方面的合撰),从义返回于道,从道返回于天,就是一个将丧失真朴的生命不断统归于更高真实的过程,这个过程,一定意义上就是“倒追过程”:“兼,犹统也,倒追上去,总归于天。”[8]87背离天道自然是一个堕落的进程,堕落日深,流俗习焉不察而以堕落为常情。由此,克服堕落回归真实,就是一个“倒行”的历程。人类自身的生存,在一定意义上,鲜于自然而顺畅地展开,而常是一种不断返归回撤的行进。回到源初真朴已经成为人类难以企及的梦想,更不用说从真朴自然顺畅地走向深邃与广袤了。
最大的阻碍无疑就是基于权力的政治治理,而且如此治理还笼罩着仁义的伪饰。无疑地,逆而返归的路程,首要便在于消除权力的肆意妄为,其次是要剔除仁义与权力之间的沆瀣一气之关联。在没有君主治理天下的远古,天下的养护,就是让天下成为天下,天下在其自身而不为任何个别存在者,尤其物性力量的突出者所僭越和妄占。天下及其万物不作为任何个别存在者,尤其某些特殊个别存在者的欲望对象而在其自身。所有物、每一物在其自身,整个天下在其自身,这是本然而真朴之足;在流俗以天下及其万物为占有对象的悖谬状态中,权力与仁义以对于天下及其万物的占有量之大为足。所有物、每一物持守自身之自然,处身天地之整体,依循自在之秩序,基于自身自然而不断展开、化成自身而进于深邃与广袤,并不需要治理者越俎代庖而外在地作为于它们。实际上,只要治理者及其仁义吹鼓手停止其肆意妄为,自行潜入其渊深与静定之境,百姓便会得其自身而宁定自然[注]相似的话,在《老子》第57章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此理正如故籍所说:让天地整体保持普遍可通达性与其秩序的自在普遍性,则所有物、每一物都能自得其自身而完成其自身;每一个别存在者无心于占有天地或天地中任何一物,让天地整体以及万物都各在其自身,作为人之存在特殊样态的心灵之觉,无论是个体生命之生之神,还是其归之鬼,都是自在而自为地肯定自身。
二
《天地》云:
夫子曰:“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无为为之之谓天,无为言之之谓德,爱人利物之谓仁,不同同之之谓大,行不崖异之谓宽,有万不同之谓富。故执德之谓纪,德成之谓立,循于道之谓备,不以物挫志之谓完。君子明于此十者,则韬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为万物逝也。若然者,藏金于山,藏珠于渊,不利货财,不近贵富;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不拘一世之利以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为己处显。显则明,万物一府,死生同状。”
此所谓“夫子”,无论其为何人[注]成玄英以为是老子(《南华真经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34页),宣颖以为是孔子(《南华经解》,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页),《经典释文》引司马彪认为是庄子,林希逸认为“夫子,言其师也”(《庄子鬳斋口义》,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85页),陈碧虚说:“首称‘夫子曰’者,庄子受长桑公微言也”(《庄子义海纂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73页)。,其所言无疑体现了庄子之学。
道,在其无数的意涵中,整体性世界或天地整体及其秩序是其最为基本的方面,所以是“覆载万物”的洋洋乎之大[注]王叔岷认为,“覆载万物”应当为“夫道,覆载天地,化生万物者也”(《庄子校诠》上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15页)。。洋洋之大的道,其覆载万物之意,既是“无所不在”[4]374,又是“包罗万有”[7]274。道之无所不在,即道作为秩序制约着天地及其万物;道之包罗万有,即道作为整体在其自身且容纳着万物。
道作为天地整体及其秩序,要持守其自身洋洋之大,最为本质性的就是保持自身的自然与自在,并让共存其间的每一物以及万物在其自身。如此,对于处身整体之中的任何一个个别存在物而言,就必须克制其僭越为天地整体及其秩序的存在冲动,此即是“刳心”的基本内蕴,包括摒除一般的感觉认知之心,“刳心者,剔去其知觉之心也”[6]185。刳心,并非指将心中的固执之见加以消除而容纳道,比如所谓“非刳心使虚则无以容道”[4]374或“去知觉,则虚可入道”[8]87,如此将道个体化的指向,与庄子对于道之自在性的捍卫是相悖的。实质上,刳心的意思,就是将自身内在可能逸出自身而妨碍道与万物之自然的主观偏执加以克制、清除,刳心的指向,是不以有限之自我妨碍无限之道、不以偏私之我僭越为普遍之道,消除自身对于道的囚禁,而使得道能返回其自身。在此意义上,刳心意味着将自身回置于自然之道、归属其中而顺受其则:“刳心者,去其知识之私,而后可以入于自然之道也”[9]169;“刳心,去其私以入于自然也”[10]121。
天地及其道之洋洋乎大哉,儒家和庄子都一样赞佩不已。但是,其间却有着本质之别。《中庸》赞佩天说:“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中庸》第27章)在天和仁义(礼仪)生活之间,有圣人作为中介,如此中介本身跨越了仁义—政治之域与天地世界整体的界限,自身成为无限存在者,不但弥漫了天地,甚而至于消解了天地自身的无限性与自在性。这恰好就是庄子哲学坚决拒斥的,庄子认为仁义—政治之域是对天地万物之自然的扭曲与背离,反对任何个别存在者尤其圣人僭越为天地之整体及其秩序,力图保持天地整体及其秩序的自在性与自然性。这也就是《天地》篇突出“天地整体”而强调“刳心”的要义。
无为为之,不是“无心而为”;无为言之,不是“无心而言”[7]73。如此无心而为,无心而言的解释,实质上是以虚妄的个体洒脱证成侵夺性言行,走向的是庄子哲学的反面。无为与无言,是就任何个体与其他万物共存于同一个有序整体而言,即特定个体不能从自身有为于它物与天地整体及其秩序,且不能以一己个体性之言说将万物与天地整体及其秩序概括尽净。任何具体的行为与言说,都与特定个体内在的情识、利欲、观念等相联属,而体现为悖于道—德之间油然通畅的成心之实现。以基于成心之言行束缚天地与万物,反过来也束缚了自身。将天地与万物从自身成心的束缚中释放出去,也就是将自身从成心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如此,天作为自然之道,就与自身本真素朴之德畅然交通;天地整体及其万物也在其自身自然而在,此即“无为为之之谓天,无为言之之谓德”。
基于无为无言,而任天地与万物回到自身,天地与万物的自遂其自身,就不是特定个体给予其外在之爱使然,而是“人自蒙其爱,物自蒙其利”[11]132——即摈除特定个体自圣自雄的责任、情怀等抱负(这种抱负以为没有自己的担当,天地整体与万物都无法存在,或者没有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而是让每一物自爱自利、自然而自遂。这就是“爱人利物之谓仁”。如此“让每个人自爱自利”的“仁”,就不再是“因我之爱而使它者成人”的“仁”。
差异性与丰富性之不同万物的呈现,是天地世界的本然之状;每一物呈现为与众不同之状,这是每一物的本然。每一物之在其自身而与物相异,这是“不同”;而各自不同的万物,又共处于一个天地整体之中,循同一个秩序,这是“同之”。使得不同之物能如其自身之不同而显现自身,“同之”之天地整体及其秩序必须保持其自在性。在此意义上,每一物之与物不同的“异”,不能成为“同之”之“同”。进而,这个“个别物之异不能成为所有物之同”,成为所有物共同的规定性——否定任何个别物僭越而为自身之外的无数他物的共性,这才是真正的“同”。每一物之“一样地”“相同地”保持自身之“与众不同”而“共存在一个天地整体”,如此含蕴无边的世界才是真正的大,而个别物之异僭越为同则是以小为大。让所有物、每一物之异都能共同地实现,即是“不同同之之谓大”。
每一物都在与万物共处天地之中的基础上,各成自身而独一无二。但是,个体自身之自成其异,一方面不能造成对于天地整体作为“共同生存境域”的损害,另一方面也不能妨碍无数他者自成其异的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各成其异是一种无言无名的生存论状态,而非流俗声名之域的夸夸其谈。生存论上自成其异的生存者,在世俗意义上反倒是和光同尘而不僻异于世[注]王叔岷以崖异为僻异,参见《庄子校诠》,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16页。。但本真意义上的同,并非就是从世俗意义上理解的和光同尘。本真意义上的同,是以多样性差异的普遍化实现为内容的。因此,崖异的意思,就是从无穷众多之异中突兀地超升出来,某种特定的异成为突出而陵越他者之上的异。如此陵越之异,就会遮蔽天地整体自身,就会湮没无数他者的差异性。所以,自成自身之独一无二,必须以将自身回置于无数差异之中而存身整体世界的方式来加以实现为前提:“不立崖岸以自异,使万物皆得游于其中而无所隔阂,是宽无不容也。”[11]132实现并持守自身之异,却不以自身之异占据天地整体而阻碍其他万物也在此天地整体中实现其自身之异,此即是存在的厚实宽度——“行不崖异之谓宽”。
自成其异而又不碍它物之成其异,是宽,也是大。任何一个具体个体,其存在都是有限的,但不让自身的有限画地为牢而自限限他,又是个体有限性的克服而具有无限性倾向。当一个具体个体自悟自身之有限性时,他就在自己存身于天地之际持有任顺它物之心:“任庶物之不同,顺苍生之为异,而群性咸得,故能富有天下也。”[2]234一切差异性毕现于天下,是天下富有差异性万物;但任何个体所成之异,能自视其“异”为无数差异之“一”,而将自身置于与无穷多样性差异共存的天地整体之中,则此个体在生存境界上就是“富有万物”。
任何个别之物存在的法则,就在于如何持守其“德”。德既是一物之成其为自身的基础,也是一物之开放自身的基础。因此,存在之“纪”,就是要在“自持其德而成其为自身”与“开放其德以与天地大道相畅通”之间,处于一个合理之度,使得天地整体与自我相偕而存。
如此,德就在自我与世界两方面取得其实现——一方面任何个体自我实现在天地之中,另一方面天地实现为无数个体自我的共同存在之中。世界和自我都在德的展开中实现自身,此即“德成之谓立”。
德在自我与天地两方面的实现与挺立,有一个合理的尺度,此尺度就是作为秩序的道。天地整体有其序,天地整体及其秩序,就是道。“循于道”与“成德”相比较而言,一般主要就是“遵秩序”之意。在自我与天地整体的对举实现中,在无数差异个体并存而在中,此“循于道”,就意味着道作为秩序是自在的普遍物,因为其自在,所以才是普遍的。只有当秩序本身是自在而普遍地被遵循时,一切自有其异之物以及天地整体,其自然自在,才能得到担保。
在自在而普遍之道的制约下,有天地,有自我,有他人,有万物,而且四者混而为一。在整体的含蕴下,在秩序的制约下,任一一物与他者都有着多种多样的关系。在相互关系中,每一个体捍卫整体的自然性,守护秩序的自在性,从而守护自身之为独一无二,这是每一个体的存在之志。拒斥任一一物僭越为整体及其秩序,以避免其戕害任何个体自身之志;经由保全天地整体及其秩序的自在普遍性而保持自身的存在之志不受它物挫坏,这才是存在的完全或完满。
天、德、仁、大、宽、富、纪、立、备、完十个方面,实质上就是反复其说,归根结底就是指向存在的完满实现。而存在的完满实现,可以归结为两方面,即一方面是自我之志的葆有,一方面是自在天地整体及其秩序的捍卫。志作为心之所之,要求着“心能动地以广袤和幽深作为自身的内容”,这既是一种生存论意义上力动的“立心”:“事心,犹立心也。言其立心之大也。”[12]255也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静观的“大心”:“韬,藏也,包括万事无遗,皆归于心,此心之大,无外矣,故曰‘韬乎其事,心之大也’。”[6]185
“沛乎其为万物逝也”,意味着在有限个体主体自身存在的展开中,让经由自身的异在而自在之流畅然自行:“逝者,往也,‘逝者如斯’之逝也,万物往来不穷,而吾与之为无穷,故曰沛乎其为万物逝也。”[6]184-185有限个体得以刳心而让天地及其万物回到自身的内在根据,就是在其自身之内“经验着体验着领悟着”经由自身的异己之流——某物流入我们,我们并不能以自身意识完全透视而明亮之,它保持其无以明之的幽暗深邃,而又流出我们;如此“流入与流出”的莫名而无知的体验,使得我们不但要释放天地整体以及万物,还要释放我们自身。唯有释放我们自身出离于狭隘而沾沾自喜的仁义—政治觉悟之域,天地整体及其秩序乃至于万物,才能真正被释放出我们的“拘禁”而回到其自身,即“任万物之自往”[7]274。从诠释学的角度说,异在性他者的经验总是自我理解的本质性内容:“不可支配的他者,即外在于我们的东西是这种自我理解不可去除的本质。我们在永远更新的经验中对某个他者和许多他者所获得的自我理解……在某种本质的意义上说总是不可理解的。”[1]694
如果天地整体及其秩序的自在普遍性得到了捍卫,每一物与所有物便皆在其自身,而非“为我所占有”。以我占有物的方式来显现物的存在,则“在我”状态的丧失,就会被理解为“某物丢失了”。实质上,有序的天地整体中,从来没有任何一物丧失自身;物之丧失自身,不但不是无人占有它,毋宁说,正是因为人以占有而属我的方式对待物,物才会丧失自身。人因求长生而悲短命,以富贵为荣而以穷困为耻,就占有金银、珠宝作为货财,以彰显人之富贵,这就是人“占有”天地整体及其中万物的体现;而人对天地和万物的占有,反过来使得天地与万物以扭曲的方式占有了人;占有天地万物使得天地万物丧失了自身,天地万物对人的占有,也使得人丧失了自身。把天地整体及其万物从人的“占有”中解放出来,从而也就是将人从天地及其万物对人的“占有”中释放出来。如此,金银回到山脉,珠宝回到深渊,如此逸出人类因于欲望而有的“占有”,金银珠宝永远存在于天地整体之中在其自身,不再丧失自身。天地整体及其万物的解放,也就是人自身的自我解放。
如此对于天地、对于万物和自身的释放,就是“不拘一世之利以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为己处显”。“不拘一世之利以为己私分”即不能让任一个体膨胀其“我”,占有天地及其间的万物,视之为一己私有之物,“私分,犹言私有也”[13]250,从而让天地及其万物回到其自身,由此而让无数他者获得共同存身天地世界的可能性:“一世之利与一世共之,不拘以为我之私分。”[6]186天下作为整体,它不为其中的任何个别物所占有或拥有,它以此“无”主属性而“利”天下本身及其万物之自遂其身。倘若天下为特定个体所占有而丧失其自在性,则天下便不复为万物乃至每一物之自遂其自身之所。因此,从根本上看,庄子拒斥着以“有利于自身”的眼光看待天下;唯有任何个体不以利于自身的方式囚禁天下,天下乃成为天下自身,天下才成为天下万物之天下。
人类现实生存不可缺乏政治,但政治的核心,即权力的占有者,不能因其作为掌握权柄之王,而自以为天下及其万物归属于自身,以自身占有或拥有天下及其万物,而“以湮没天下及其万物的方式闪耀自身”。这就是“不以王天下为己处显”。在某种意义上,如何让掌有权柄之王成为天下及其万物自显其明的保障,而非成为遮蔽、湮灭天下及其万物之自性的盗贼,这是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主题。
任何个体,尤其掌握权柄的治国者,不能以湮没他物以及天地整体的方式显现自身。当且仅当每一物不以耀眼夺目的方式湮灭他物和天地世界整体之际,他物和天地整体才能自得其明,且如其自身而显现。此即“不显则明”[注]郭象注说:“不显则默而已。”(《南华真经注疏》,第235页)这表明,郭象所注本是“不显则明”,而非“显则明”。王叔岷说:“窃疑‘显则明’三字,乃郭注误入正文者。盖郭注本作‘显则明,不显则默而已。’重默不重显也。‘万物一府,死生同状。’乃玄同物我、死生之义,非显明之义也。”(《庄子校诠》上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18页)林疑独注:“不显,则闇然而日章也。”(《庄子义海纂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72页)。
由此,多样性的万物作为万有不同就存在于同一个天地整体之中,此即“万物一府”,万物而处于一府,此府即是作为“天府”[5]102的天地整体。天府,是天地整体及其万物的解放。
天地及其万物的解放,同时也就是每一物之自我的解放,亦即从死生分别或乐生哀死中解放出来,而抵达“死生同状”,即“同于天”[5]102,亦即同于自然——同于“每一物之自在其自身”。换句话说,就是“每一物之在其自身”是“天下每一物或所有物之同”,如此之同,是“玄同”,即“同于玄”[5]102。人与人之间的存在都是各成其自身之异,但如此各成其异,却是自然之大同:“于人见异,观于天则几无不同也。”[5]102
“刳心”作为一种政治—生存论工夫,表面上是对于自我的消解。实质上,刳心是对于天地整体与自我的双重建立:“心虽刳也,刳其取定之心,而必有存焉者存,‘见晓’、‘闻和’,‘官天地’,‘俯万物’,而人莫之测。”[14]89-90
《天地》篇在此之后,除却“泰初有无”一段进一步从抽象论说上阐明开篇的两重持守外,其余大多是以“寓言”从各个侧面喻示两重持守的道家生存论。实质上,如此两重持守的生存论道理,贯穿于整个《庄子》文本之中,不过在《天地》篇开篇得到一个较为主题化的彰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