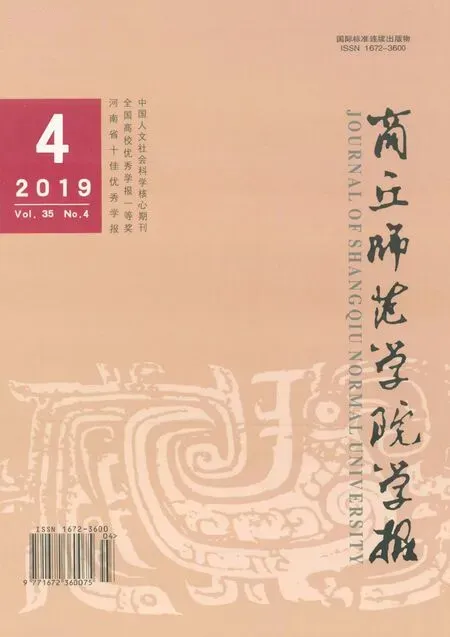论庄子对语言的质疑与批判
陈 之 斌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庄子对语言的质疑与批判不仅停留于语言自身,而是有感于语言在社会实在的建构过程中可能带来的遮蔽与暴力。语言作为文明的重要载体,自从诞生之日起,就承担着传递文明的重任。照实言之,文明的异化可归结为语言的异化,因为一切的价值观念、知识体系以及权力运作,都离不开语言的参与。从表面上看,庄子所批判的对象是语言,其真正的目标却是由语言所构成的价值观念、社会实在、知识体系以及政治权力,其中尤以知识及政治权力为最。换言之,庄子对语言的质疑与批判,实际上就是对知识与权力的批判。一方面,道家认为,先秦其他各家所讲的知识都属于物,这与道的知识相差甚远,因而对知识的批判,就在于如何从物的知识跃升到道的真理;另一方面,在一个无道的世界里,知识往往沦为权力的附庸与争夺的工具;先秦诸子希望自己的思想学说能够见用于统治者,如孔子一生奔走呼告,试图恢复周代的礼乐文明,不放过任何为官的机会;墨家也从兼相爱、交相利的角度积极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惠施甚至把名辩当作获取名利的工具;等等。庄子对此有深刻的感受,其思想处处散发着敏锐而深刻的权力批判色彩。
一、对知识的批判
“知”乃庄子哲学的重要议题,这一字在《庄子》中出现六百余次,足以说明“知”的重要性。这并不意味着庄子要向我们展示一种知识论。知识论一直是哲学研究的重点,西方哲学发展至近代,有一知识论转向,西哲如笛卡尔者,经过对现有之一切知识普遍怀疑后,认为只有正在进行怀疑之自我乃真实不妄。因而其哲学体系以“我思”为根基,以上帝为保障,并由此建立一切知识与科学。此知识论传统到康德达至顶峰。康德之纯粹理性批判,也是对知识自身的批判,其核心问题之一就是“我能知道什么”。为此,康德区分了现象与物自体,并把人类的知识严格限定在现象界,而物自体非人类知识所可及,但属于实践与信仰之界。反观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像西方一样发展出知识论传统与语言哲学传统,但是对知识与语言同样非常重视。尤其是道家之庄子,对知识与语言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把“知”与“言”严格限定在物的世界,由此揭示出那个“不知”与“不言”的形而上的道的世界。换言之,道家哲学所真正关注的乃无形无名、不知不言之道,而不是有形有名、能知能言之物。此一分际,乃中西哲学之重要分水岭。庄子哲学正是从知与言的批判开始,以彰显那超越知识与语言之道。
从知识论的角度探讨《庄子》哲学,胡适的《中国哲学大纲》已开启端倪。他认为,哲学史的中心问题就是知识思考的方法,哲学史上的各家各派都有其自己的思考方法,而哲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这种方法揭示出来,他称之为名学方法[1]159-160。从中国哲学乃至世界范围的哲学来看,《庄子》中所讲的“知”的问题都非常特殊,因为他讲的是“不知之知”“无知”,并认为这才是“真知”。与“知”相关的是“言”的问题,“知”与“言”在《庄子》中非常重要,“知与言是一篇(《齐物论》)之眼,然言又本于有知”[2]12,都是通达庄子之“道”的必由路径。知识和语言相表里,知识需要用语言去表达。“知”与“言”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如何认识或把握“道”的问题。“道”虽然不是知识的对象,我们也无法获得关于道的任何知识,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从知识论的向度进行探讨。事实上,庄子正是通过对“知”与“言”的突破与超越,进入了一个不知、无言的形上之境——道。
(一)知止——知识的局限性与相对性
早期哲学普遍认为,认识能力是人的天赋之一,人的知识来自于经验世界,《庄子》也不例外:“知者,接也;知者,谟也。”(《庚桑楚》)“知”由“接”和“谟”两种方式产生,“接”是与外物相接触,“谟”则是出自理性思考,两种方式大体对应于现代哲学所讲的感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知识的获得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知识都是正确的,《庄子》中也讲了知识的标准问题:“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大宗师》)知的正确与否依赖于知的标准“所待”,只有有“所待”才意味着知的正确。这里有两点要注意:一是知形成后就是确定的;二是知的标准是不定的,例如同样的知在不同时代以及不同区域,其含义都随之不同。
既然知识的产生依赖于外物,所以“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北游》)。可见,知识的对象是我们现实的经验世界,也只有与经验世界发生关系,才能产生相应的知识。因而我们获得的“知”主要指关于“物”的知识,所谓“知之所至,极物而已”(《则阳》),意味着我们的知识无法超出经验世界。《庄子》中的“物”不仅仅指可见的有形有名的世界,如天地万物以及人自身,也包括现实世界中所发生的一切活动及事件。“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秋水》)言说与意致的界限也就是能知的界限,而不能言说、不能意致的世界则远远超出了物的世界,所以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齐物论》)六合之外超出人的经验感知范围,因而不可能形成任何知识,只能存而不论。
事实上,即使在物的世界内,人类之知也是有限的,一方面由于人生命的有限性,不可能穷尽世界万物,“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养生主》);另一方面,人所知的仅仅是万物中的很小一部分,人所知之外的世界更大,“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秋水》)。其次,人的认知能力也是有限的,“目之于明也殆,耳之于聪也殆,心之于殉也殆。凡能其于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给改,祸之长也兹萃”(《徐无鬼》)。这种认知能力的局限性来自于“知”自身,《逍遥游》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观点:“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可见,知自身也并不完美。再者,世界之物也是无穷无尽的,“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秋水》)。时间是无限的,万物之变化也是无穷的。因而,以有限之人生、有限之认知能力,追求无限之世界,必定遭遇失败。此外,《庄子》中还揭示了人所不能知、不可知的许多领域:
今彼神明至精,与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圆,莫知其根也。(《知北游》)
化其万物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山木》)
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达生》)
死生存亡,穷达富贵,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德充符》)
孟孙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将化,恶知不化哉?方将不化,恶知已化哉?(《大宗师》)
庄子认为,人的认识领域只是“物”的世界,一旦超出此一世界,感性和知性则无能为力。因此,庄子特别提倡“知止”。此一观念来自《老子》:“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老子》第32章,以下所引《老子》,只注明章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第44章)《老子》中的“知止”主要是就名与身而言的。老子认为,名是一种社会建制,决定了人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因而为争名逐利埋下了祸根,所以要对名加以制止,使其复归于朴。知止则可以使生命更加长久。“知止者,惧后进之有损,盖知几而固守者也,岂有知几而至于危殆乎!”[3]188庄子所讲的知止则主要是从认知的角度来讲,指心知(智)的界限,而非认识的界限[4]94。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齐物论》)
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养生主》)
知止乎其所不知,至矣。(《庚桑楚》)
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德充符》)
庄子认为,我们的认识必须止步于物的世界。换言之,感性和知性只能认识物的世界,一旦超越此界限,将失去效用。这让我们想起了康德在现象与物自体之间作出的区分。当然,知止的作用还不仅仅在此,更重要的是这会使我们反思知自身以及所知的对象。这正是道家的洞识所在。知止,意味着心知的界限;而界限,则必然预示着要被超越。因此,“知止”即是一般之知的终点,同时也是另一种知(真知)的起点,它迫使我们在此处绝境逢生,另寻出路。也只有突破此界限,才能突破物的束缚,从而进入一个新的境域——道的世界,所以关键就是要知止。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庄子对以惠施、公孙龙为首的名家多有批判。因为辩者如公孙龙,虽能“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秋水》),然终不过“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同上),始终纠缠于万物之是非之中;而惠施“遍为万物说”(《天下》),“以善辩为名”(同上),其历物十事也终究不出物的范围。
(二)不知之知与真知
由上述分析可知,一般意义上的知,即通过感性和知性所获得的知,并不是庄子所追求的知。庄子或者说是道家,最特别之处就是追求“不知之知”,也叫真知。在庄子看来,一般意义上的知与道家意义上的知,两种知不仅仅是程度上的不同,更是种类上的不同。真知不是由感性和知性认识的途径所能达到的,故其为以彻底排除感性和知性认识条件、超越物的世界的“不知之知”。《庄子》中最高的“知”是不知,对于道的最佳回答也是不知。《知北游》用一个寓言故事传达了这层含义:
知北游于玄水之上,登隐弅之丘,而适遭无为谓焉。知谓无为谓曰:“予欲有问乎若: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 三问而无为谓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问,反于白水之南,登狐阕之丘,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问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将语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问,反于帝宫,见黄帝而问焉。黄帝曰:“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知问黄帝曰:“我与若知之,彼与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黄帝曰:“彼无为谓真是也,狂屈似之,我与汝终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
从三人的回答来看,最发人深省的是无为谓的“不知答”,而揭示这一秘密的黄帝却是“终不近也”。吊诡的是,知得到的答案是不知,恰恰是自己的反面。 至于知是否从中领会到“道”的内涵,我们不得而知,但其中确实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力量牵引着我们,去思考无为谓的“不知答也”。此外,黄帝之语也值得重视,虽然黄帝自称“不近也”,但是如果没有黄帝的一番阐释,知和狂屈的重要性也无法突显出来。
最高的知是对“未始有物”的认识,例如,“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齐物论》)。这种知也就是对无形无名之道的认识,因为道的存在超出了通常的认识范围,且没有任何感性特征,因而可以说是一种“无”,而对道的认识就是对“无”的认识,我们可以称之为不知之知。郑开教授认为,“不知”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1)表明了知性和感性的局限性;(2)启示了形而上学的知识境域,该境域越出了感性和知性力所能及的认识范围,因而不属于感性和知性的对象;(3)“不知之知”即真知的另一种表达[4]94-99。
《庄子》中所说的“不知”往往跟万物的终极原因联系在一起,而且我们发现,一旦碰到对终极和本根等问题的追问时,《庄子》常常以“不知”作为回答。而“不知”在《庄子》一书中出现频率也非常之高,加上各类“不知”含义的联合使用,一共出现有169次之多,这足以说明“不知”在《庄子》中的重要性。《老子》就认为“不知”要高于“知”,“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第71章)。进而把“无知”当成爱民治国的法宝,“爱民治国,能无知乎”(第10章)。正因为此,朱谦之认为,“无知”是庄子哲学的出发点,也是庄子的哲学方法[5]136。这确实是卓见。庄子真正的关注点是“道”,也只有勘破了感性与知性之知的界限,从“无知”出发,才能走向不知之知的真知。
究竟何谓真知?张岱年认为:“庄子所谓真知,与荀子所谓智,都是现在一般所谓真理的意思。其实在知识论中,真理一词不如真知一词之确当。真理是真实的道理或真确的原则之意,乃指知识的内容而言;真知是真确的知识之意,乃就知识本身而言。”[6]520张先生把庄子的“真知”当成一种对象性的知识,并认为庄子所讲的真知同荀子所说的智[注]《荀子·正名》曰:“知有所合谓之智。”一样。这种把真知归结于知识论并与真理相等同的观点显然与庄子之意不符。庄子讲的真知不是一种对象性的知识,跟一般所讲的真理更是不同。庄子的真知并不是建立在与对象相符合的基础之上,而是专属于真人的,所谓“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大宗师》),而真人的含义却让人很费解。《大宗师》云:
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
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
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
此处对真人的描述超出了一般对人的理解,似乎在描述一种精神境界或心理状态。张默生认为,这是“籍真人的体相,来说明‘道’的体用;兼以示范于人类,以期合于天。……真人,便是道的具体化,或说是道的拟人化”[7]198。换言之,真人就是体道之人,而真知就是体道之人的一种特质,这种特质必须借助于主体的内在精神体验才能得以显现。由此,真知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精神境界[4]124。既然是一种精神境界,当然是不可能通过言说来传达的,它需要借助体道者自身的修养工夫方可达致。要之,庄子之所以说道不可知、不可言,其重点并不是说道不可知,而是说不能从知上去把握道,他要我们中断概念性思维、转换视角,从生命实践的角度去体悟。这里存在一个从言到行的转变,如此便可从知的困境中走出,转而从“行”上实践之。
(三)知识层面的社会批判
《庄子》对知识的批判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知性问题,更是一种社会批判。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不仅仅是思想和学说的相互交锋,更是知识和权力的竞逐。知识总是为特定的阶层服务,总是与政治权力相互勾连,所以知识也成为权力争夺的对象,这一点庄子说得非常明确:“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人间世》)知识已经变成跟名一样的东西,这表明庄子对知识的沉沦与异化有深刻体认。《庄子》甚至认为,社会动乱的根源就在于知识,“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胠箧》),所以庄子提出了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知识到底是为谁服务的?其云:“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道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同上)庄子在此揭示了知识作为权力工具的本质,这在儒家思想那里表现得非常清楚。从孔子开始,儒家就积极寻找同政治权力相结盟的机会,以求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学而优则仕”就是这一理念的最佳表达。知识学习的过程,不仅是一整套社会习俗、礼仪规范、意识形态等不断建构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系列权力不断强化与整合的过程。用这样一套知识系统去治理国家,必定会滋生很多问题。老子对此就有清醒的认识,所以他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第18章)老子之所以反对智慧,就是因为他看到了知识异化为奴役他人的工具,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所以老子主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另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第19章)“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第65章)庄子也同样拒绝承认这一知识体系,“曲士不可语于道者,束于教也”(《秋水》)。在他看来,由仁义礼智等建构起来的社会实在以及社会角色的分配,束缚了人性的发展,把人变为对象化、工具化的存在,因而无法理解无形无名之道。
二、对权力的批判
上文在论述知识层面的社会批判时,已经对权力批判有所涉及,但这对《庄子》全书所表现出来的无处不在的权力批判来说,还显得十分不够,接下来笔者将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究。
众所周知,《庄子》思想表现出很强的批判性,尤其是对来自政治与权力的隐秘暴力十分敏感,而庄子对此也一直保持着一种高度的警惕感。这在有关庄子的几个小故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例如,当楚威王重金聘庄周为相时,庄子拒绝的理由是:“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8]2145;当他的朋友惠施害怕庄子抢夺其相位时,庄子用极尽刻薄的言辞来嘲笑惠施,把其相位比作鸱喜欢吃的腐鼠;当庄子面对魏王为何如此疲惫的质问时,庄子不卑不亢地回应:“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山木》)诚然,这些生动形象的故事表现出庄子渴望自由、抵抗政治的精神气质,但并不意味着庄子对这个世界的逃避,而是他有感于来自权力的压制与暴力,所作出的一种反抗与拒绝。尤其当庄子因“昏上乱相”而倍感疲惫时,那种无处不在的政治暴力已经非“批判”二字所能承受,其生命已受到实实在在的威胁。可以说,庄子对权力的批判,已经完全融入他的言行举止当中。更有甚者,庄子还组织了一种身体的抵抗,如他所创造的那些身形怪异、言行骇俗的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也更加直接地展示了来自权力的隐秘暴力。从这个角度说,庄子对权力的批判乃是庄子思想的中心。法国汉学家毕来德指出了这一批判思想的重要性,并批评了历来的庄子研究对这一主题的忽视:
郭象以及其他注者将一种主张人格独立与自主、拒绝一切统治与一切奴役的思想,变成了一种对超脱,对放浪不羁、放弃原则的赞颂,使得那个时代的贵胄子弟,即使对当权者满怀厌恶,还是可以心安理得地为他们服务。他们解除了《庄子》的批判思想,而从中得出他们在权力面前的退却,即是说他们“顺从”态度的理论根据。[9]121-122
权力的行使离不开语言的参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权力的游戏对于以治世报国为目的的知识分子来讲,可以归结为一种语言游戏。“全部的国内政治以及国际外交活动,完全是在词锋语剑之间,由权力行动者们高明的台前谎言和有组织的幕后谣传所组成。以庄子与惠施这样名噪一时的政治人物的联系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庄子对语言的警觉可能直接来自于政治上的触动。”[10]语言的批判离不开权力的批判,或者说,权力的批判就是一种语言的批判。郭象在注释“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累于形名,以庄语为狂而不信,故不与也。”[11]1100前面已经讲到,形名双关政治与语言,乃先秦诸子共同的知识背景。语言符号必然挟带着权力支配与意识形态的宰控和暴力,庄子正是有见于此,才创造性地使用“三言”来消除语言中的权力隐患。
(一)始制有名:名言的权力本质
庄子对政治权力的批判与拒绝,可以说始于对“名”的权力本质的洞察。前面已讲到,道家对语言的反省与自觉,就是来自“名”的深刻启发。在先秦思想的脉络里,名除了最基本的命名之义外,最重要的莫过于与政治体制和权力利益的隐秘关联,这就涉及对宗法制度与封建制度本身的考察,也只有从当时的社会与思想背景出发,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理解老庄道家对“名”的洞见。叶维廉说:
在周朝,宗法制度的建立即是为巩固权力架构的一种发明,而在宗法制度中,“名”,名分,这些语言的符号,正是砖石间最重要的黏土。……“名”的应用在周朝是一种析解的活动,为了巩固权力而圈定范围,为了统治的方便而把从属关系的阶级、身份加以理性化。天子、诸侯、元子、别子等等的尊卑关系的订定,不同的礼数的设立,也完全为着某种利益而发明;至于每个人生下来作为一种自然体的存在的本能本样,则因此受到偏限与歪曲。老子是从体制中这些圈定行为的“名”之活动,看成“言”(语言文字)的偏限性及“名”与“言”可以形成的权势。语言的体制和政治的体制是互为表里的。所以说“始制有名。”[12]46-48
“名”意味着分封、限定,因而不可避免地隐含着某种属人的权力意向。宗法制度的建立加强了此种权力意向,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赋予其一种实际的权限。命名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建构秩序的过程,因而在命名的主动者和受动者之间也就形成了一种从属关系,所以说语言的体制与政治的体制是互为表里的。老子正是有见于此,才发出“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第32章)的感叹。更有甚者,儒家通过“礼”制把名的这种权势散布于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把人限定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的角色之中,而使人失去其本真的存在,完全沦为名、礼的奴隶,这在道家看来是最大的悲哀。
《庄子》认为,名已经成为各势力集团互相角逐的权势,庄子对名的权力本质感受极其深刻:“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人间世》)既然“名”意味着一定的权力,象征权力的知识就必然会成为相互争夺的利器,“名”成了赤裸裸的权力工具,成为互相倾轧的凶器。名利所在之处,也就是危险所生之地。庄子在《养生主》中用血淋淋的解牛之例来映射养生之道,其本意在于以此隐喻险象丛生、无处不在的权力角逐的社会。王夫之早就点出牛体结构的复杂性和“名”的关系:
大名之所在,大刑之所婴,大善大恶之争,大险大阻存焉,皆大车瓜也。而非彼有必触之险阻也,其中必有间矣。所患者:厚其情,厚其才,厚其识,以强求入耳。避刑则必尸其名,求名则必蹈乎刑。名者,众之所聚争,肯綮之会,即刑之所自召也。[13]106
名与刑同系相生,大名则必定意味着大刑。所以《庄子》一再强调“无名”,如“圣人无名”(《逍遥游》)、“为善无近名”(《养生主》)、“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人间世》)、“能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同上)等,他希望摆脱名的束缚与控制,对“名”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
“名”所暗藏的此种权力宰制,在现代学术理论中也有明确揭示。例如,罗兰·巴特就特别强调了语言的暴力支配:
在人类长存的历史中,权势于其中寄寓的东西就是语言,或者再准确些说,是语言必不可少的部分:语言结构。语言是一种立法,语言结构则是一种法规。我们见不到存在于语言结构中的权势,因为我们忘记了整个语言结构是一种分类现象,而所有的分类都是压制性的:秩序既意味着分配又意味着威胁。……同样,语言按其结构本身包含着一种不可避免的异化关系。说话,或更严格些说发出话语,这并非像人们经常强调的那样是去交流,而是使人屈服:全部语言结构是一种普遍化的支配力量。……语言结构运用之语言不是反动的也不是进步的,它不折不扣地是法西斯的。因为法西斯主义并不阻止人说话,而是强迫人说话。[14]147-148
这里对语言霸权的批判集中在语言结构上。所谓语言结构“便是结构主义所着迷并认定的人类普遍思维方式之基础:二元对立的分类方式”[15],庄子对二元对立的语言结构有着深刻的认知,而《齐物论》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破除此种对立。“名”内蕴的权力宰制可以从语言结构的二元对立来分析,《庄子》破除此种二元对立,实际上就是对其中权力宰制的破除。《齐物论》云: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
命名的过程,就是把事物进行二元区分的过程,所有事物都因此落入彼是相分的二元圈定中,由此便产生彼我、是非、可与不可、然与不然的二元区分。对任何一方的肯定,都意味着对另一方的否定。更有甚者,庄子认为,“我”已经是二元区分的结果,因而在《齐物论》一开始就提出“吾丧我”作为全文的纲领。语言结构的二元对立,再加上人类自以为是的偏见与成心,势必造成立场和观点的争议。政治上的话语权之争更加惨烈,《人间世》中所描写的孔子与颜回之间的对话清楚表明了这一点:“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夫风波易以动,实丧易以危。”在这一充满暴力与危险的政治话语操作中,任何一点差错都是致命的,而其中的个体也不得不在话语权势的逼迫下争夺话语权。所以说庄子对语言的自觉并不是纯粹出于语言自身的考虑,而是基于对政治权力的警觉。以《人间世》为例,孔子和颜回乃知识分子的象征,他们承担着对政治和社会的批判责任。“在专制社会中,这种批判最后针对的一定是君主。庄子刻意地选择这几个角色出场,其实显示着政治仍然是他思考的背景,甚至是最重要的背景。”[16]30同样,《养生主》《说剑》篇中也都是以君王作为言说对象。孔子和颜回的对话,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话语的具体实践过程。
《齐物论》对名言的勘破以及对各家思想之辩驳,也可以看作是对当时主流政治主张的解构,而且庄子是从根本上解除了各家政治建构的正当性。在他看来,建立在“名”之上的政治伦理秩序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对名的拒绝,实际上意味着对现行政治的拒绝;《齐物论》通过“莫若以明”“休乎天钧”的方式来跳出彼我是非的二元之争,暗示了庄子思想通向以精神修炼为主的内圣进路。这一点在《庄子》中非常清楚,庄子也是当时唯一反对王权统治的思想家,他对名的质疑与批判,意味着对承载意识形态与权力运用的语言的否定,这一思想旨趣引出了无名之朴的浑沌之世。
(二)无名:至德之世的回归
如果说儒家试图通过“正名”的方式来加强语言(名言)的权力属性,道家则意图通过“无名”来消解名言中暗藏的权势,重建社会秩序。事实上,在庄子看来,以“名”为主的政治建构在根本上是一种“有为”政治,而庄子对“有为”政治的有效性是持怀疑与批判甚至否定态度的。《庄子》认为,儒家的仁义不但不是人之真性,反而会造成对人性的戕害并且会导向乱政。《骈拇》:“吾所谓臧者,非仁义之谓也,臧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可见,庄子最看重的是性命之情,能够依循或顺任此种性命之情的政治就是最好的政治。遗憾的是,在庄子看来,任何现存的有为政治都是与性命之情背道而驰的,所以《庄子》反对任何“为天下”的尝试:
天根游于殷阳,至蓼水之上,适遭无名人而问焉,曰:“请问为天下。”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问之不豫也!……” 又复问。无名人曰:“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应帝王》)
庄子认为,“为天下”这样的问题本就不该问,天下是无法通过“为”的方式来治理的,由此无名人给出了“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的治世方略。事实上,“无名人”就是“道”的化身。显然,这则寓言是道家无为思想的表现,其意在要求统治者提升自己的修养,不妄加干涉万物之性命之情。另外,《在宥》云:“故君子不得已而莅临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这也是道家以治身为内、治国为外的一贯思路,在完身养生面前,任何国家大事都是次要的:“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让王》)
因而,庄子眼中的理想政治模式就是能够因循万物的性命之情,保持万物之真性,而这样的世界并不是治理的结果,而是放任、因顺的自然产物。由此,《庄子》提出了“在宥天下”的主张:
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尧之治天下,使天下欣欣焉人乐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长久者,天下无之。(《在宥》)
“在宥”即宽裕自在、任其性命之情之谓也,在宥天下则意味着万物能够自由兴发,而不会淫其性、迁其德,这和《应帝王》所说的“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一致,都说明最好的政治应该顺应万物德性之自然发展。这也是《庄子》所指认的政治正当性的来源所在。《庄子》所考虑的并不是政权的归属以及合理性,而是以“人类整体的普遍德性作为公共生活秩序的内在依据,在现实的政治架构里也就成了考量政治行为是否正当的核心标准。只有确保了‘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政治行为才有可能具备正当性,否则的话,任何统治形式的合理性都是值得怀疑的”[17]。前文已述,庄子一直以政治社会为思考背景,其核心关切是如何在乱世中安顿个体之生命。所以,庄子既主张生命主体的自我转化与提升,又主张在“不淫其性,不迁其德”的基础上展开对政治合法性的合理建构,如此才可保持天地万物固有的性命之情。
庄子向往的理想社会是所谓“至德之世”:
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马蹄》)
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天地》)
“至德之世”在《庄子》中又称之为“至德之隆”(《盗跖》)、“建德之国”(《山木》)。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任何礼仪法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人类社会中的一切差别如君子与小人、贤与不肖、好恶美丑等都消失了,名与知不再成为人们竞逐的对象,人类与万物和谐相处,因而人们也不再有机巧存于心中,他们都凭素朴之性行动,人性因此得到了彻底的自由与解放,万物之“天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有些学者认为,“至德之世”仅是《庄子》对远古社会的浪漫主义的构想,并不存在于任何现实之中,因而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然而笔者认为,这是庄子思想之内在逻辑的必然的理论结果,其以内圣为主导的精神旨趣,实际上已经暗示了庄子对素朴之德的重视,因而他必然反对任何以规范为主导的统治形式。
“至德之世”不是一种无政府或者无秩序的混乱状态,毋宁说这是一种没有秩序的秩序,或者说是自然的秩序,在其中,自然而不是任何外在人为之规范成为万物的尺度。这实质上是庄子之“浑沌”的另一种显现方式,它“为我们的秩序预留了向浑沌开放的空间,从而提醒我们去反省秩序本身的意义与边界,由此一切统治活动及其所采用的组织化、体制化作为的性质与条件才能得到真正的阐明与限制”[18]。对浑沌的向往,意味着对秩序的否定,因为与浑沌相对立的秩序化过程,其实是以名言和知为基础对世界进行分类与化约的过程,这一过程必须动用语言才能完成。
难道秩序只能通过知识与名言来建构么?当然不是,《庄子》已经清楚地向我们揭露了这种有为政治的种种弊端,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对“名”的信任,也就是对人为建构机制的信任。无名,则要求我们勘破名言中所暗藏的权势与暴力,回归到无名之朴的“至德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