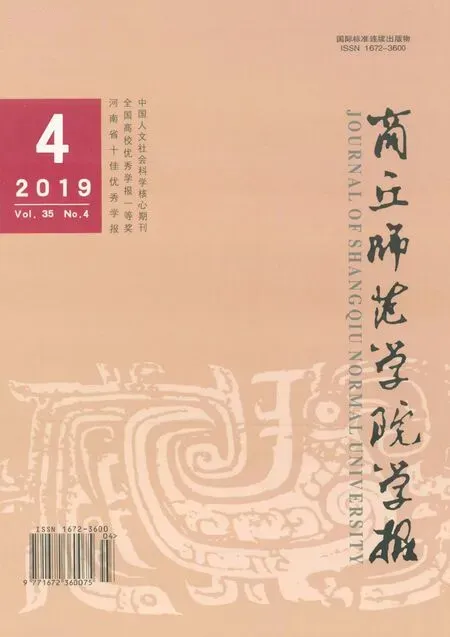美国课程论百年发展及其启示
刘 蝶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 400700)
一、学科化研究的形成时期(1918—1948年)
现代课程论发端于西欧,在此之前对课程的研究处于前学科化研究时期(1890—1917年),虽然有对课程方面的研究,但并没有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课程思想和课程理论还处于孕育之中。
直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教育者从欧洲引进大量的教育心理学和课程理论。尤其是瑞士的裴斯泰洛齐、德国的福禄培尔以及赫尔巴特等人都对教育领域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对美国的课程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课程发展呈现一种臃肿的状态,迫使课程编制者以及课程研究专家将其重心放在学科之间的改革与发展之上。
(一)十年孕育时期(1918—1928年)
1918年,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家克伯屈发表了《设计教学法》一文,并且将此具体运用推广到中学。克伯屈将其视为一种课程理论。同年,美国著名的课程研究专家博比特出版的《课程》一书,被视为课程理论建构的起点,是课程作为专门研究领域诞生的标志。随着美国教育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1919年进步主义教育协会成立。
随后,美国课程论专家查特斯于1923年出版《课程编制》,博比特于1924年出版《如何编制课程》。虽然博比特和查特斯都注重课程编制的问题,但却在如何选择课程目标的观点上存有分歧。博比特认为,课程目标应该与工业的运作流程是类似的,而工业的作业环节便是各个学科的内容,应通过这种手段来发现课程目标,即工作分析法;而查特斯则主张以活动分析法来确定课程目标。
总体而言,博比特与查特斯两位课程研究者创立了以教育目标为中心的课程编制模式,这为20世纪30至40年代泰勒创立课程原理奠定了基础。继博比特和查特斯之后,一大批“课程专家”脱颖而出。与此同时,对课程编制、课程目标等方面的研究不断涌现,使得课程论研究逐渐学科化。美国课程论从1918年到1928年的发展,实际上是基于内在与外在因素的共同作用,在教育研究专家们的推动下,得以向前发展。美国课程论十年孕育时期的发展整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十年孕育时期课程论的发展
在课程研究初期,课程论专家把社会、工作效率与学校教育联系起来,“教育的过程与生产过程是非常相似的,学生就好像是生产‘原料’,是学校这架机器的‘加工’对象,要提高加工过程的‘效率’,就要必须运用科学的管理、技术和方法”[1]43-44。通过把科学管理与学校的教育过程作类比,使得教育的性质带有机械性。
(二)二十年发展时期(1929—1948年)
到1929年,由于美国爆发经济危机,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深陷严重的经济大萧条,美国生产力水平急剧下降,失业率骤增。美国教育的发展不适应经济的需求,学生的学习与社会脱节,美国中学课程暴露出以下主要弊端:1.片面强调系统知识和专注于升学的目标,不注重人的发展;2.课程体系以分科课程为主,学科之间界限分明;3.大学教育与中学教育脱节。基于此,20世纪30年代,部分教育者由课程编制转向了课程开发研究,所以便有了进步教育协会后来的改革课程之举。1930年,“进步教育协会”呼吁要对美国中学的课程进行变革,要求课程要协调大学与中学教育的衔接,要注重学生个体的发展,要构建综合课程体系等。同时,全美教育研究协会针对课程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项长达八年的课程实验研究。美国“八年研究”取得的成果:
1.课程编制既满足了学生的需求和兴趣,也为学生进入大学或学院提供了教育计划,如改革分科课程,实行活动课程、核心课程、分科课程、综合课程、单元课程等多种课程编制形式[2],为学生在新一阶段的学习提供课程选择上的准备。
2.改变对学生的评估方式,不是测验具体的内容,而是评估一般的技能。
3.在职研讨班的建立与发展,为教师培训与成长提供途径。
4.以问卷、观察、产品样本和测验等手段对学生在每个目标上的进展状况进行评估。
经过时间的检验,事实证明,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了这八年课程研究的成果,同时,这也为泰勒创立“现代课程研究范式”的“泰勒原理”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到20世纪30至40年代,拉尔夫·泰勒(Ralph Tyler)出版的《泰勒原理》,使得课程论成为一门独立、专门学科。《泰勒原理》倾向于课程设计的方法, 而不是课程本身的内容[3]1778-1783。这就为课程设计中出现的复杂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利条件。随着1932年课程研究学会的成立以及1938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课程与教学系的建立,课程研究取得了独立地位[4]215。

表2 美国课程研究的重要著作及实验研究
1918—1948年期间,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欧美掀起的工业革命热潮,都为美国教育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契机。美国课程论在这二十年出版的相关著作以及所进行的重大课程实验研究(见表2),都是其后来课程体系建构的铺路石。虽然美国课程的专门研究人员队伍、著作以及实验体系等都逐渐庞大起来,但是在这个阶段课程研究者对课程的研究重点还聚焦于课程编制上,关注对课程编制的技术和方法[5]47。尤其是“八年研究”的生命力,虽然如昙花一现,但也为后人继续研究课程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以及意义重大的教育文献。
二、课程体系的建构与发展时期(1949年以后)
1949年,泰勒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课程论专著《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而“泰勒原理”是关于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泰勒基于课程研究的四个基本问题,提出了四个课程目标。其具体内容见表3所示。

表3 “泰勒原理”的提出
随着美国课程研究的继续推进,课程研究的思想潮流及学派纷纷涌现,其中对美国课程理论以及课程变革实践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三大范畴六大类课程思潮”[6]序2-4,在美国课程的发展与演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根据曹文婕与马庆涛的《研制西方课程理论的学术谱系——〈西方课程思潮研究〉介评》[7]一文,归纳列出下表(见表4)。

表4 “三大范畴六大类课程思潮”概览表
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冷战格局推动课程研究发展,结构主义课程理论指导了课程改革运动。结构主义课程在课程目标、课程编制、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方面都使得课程具有现代化的特征,关注学生的发展以及知识的掌握,都体现了结构主义课程顺应了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20世纪50年代后,美国课程理论研究活跃。美国心理学家布鲁姆对泰勒四个问题中“教育目标”进行研究,将“教育目标”分为三个领域:认知领域、情义领域、动作技能领域。至此,20世纪上半期以进步主义教育为基石的教育理论,对当时的美国学校教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帕克的昆西教学法、约翰逊的有机教育学校、沃特的葛雷制和后期的以儿童中心取向的帕克赫斯特的道尔顿制、华虚朋的文纳特卡计划及社会中心取向的教育理论和实验等。
20世纪60年代以后,课程研究逐渐转向对课程本质的关注,尤其是科学知识结构问题的探讨,以及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配合,代表人物是布鲁纳。以布鲁纳为首提出的“学科结构” 课程理论直接影响到60 年代世界性的课程改革运动[8]。20世纪70年代以来, 西方课程理论开始“概念重建”之旅, 逐渐把西方课程理论的发展引领到后现代主义的旗帜之下, 后现代主义课程认识论的特点逐渐显现, 后现代主义课程认识论的理论主张基本形成, 体现出当代西方课程认识论明显的后现代转向[9]。同时,课程研究转向人文方面,强调尊重个体及其主体的能动性。一直到70年代前,整个美国课程的编制与理论研究都是基于泰勒的课程原理。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各课程流派竞相发展,课程研究趋向于多元化。其他国家如英国、苏联等其课程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美国课程理论及编制的影响。首先,各国展开的课程改革与实验研究相伴而行,同时也促使了现代化的研究工具与课程理论相结合。其次,由于其他学科,如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与教育学的融合发展,使得课程理论与其他学科也逐渐相互渗透发展。最后,以自然科学实证方法为研究范式的课程研究局面逐渐发生改变。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社会和国家对基础教育的技能训练极其重视,美国课程研究整体受到了滞后的影响。
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占优势地位的课程理论研究取向转变为通过政治学、现象学、后现代主义等视角去理解课程。20世纪末21世纪初,受到各种相关教育思想与教育理论的影响,课程研究主要表现为以统合性活动课程为主[10]103。整个20世纪,美国的许多学校行政人员、课程专家和工商业领袖一直采取一种通过生存模式的学校教育及其各种外部强加的控制而达到的效率观,如学校教育中的权威以其说道等形式强加的道德控制[4]393,385,让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受到社会的控制,从而达到学校乃至社会所期望的学习结果。
21世纪美国的课程研究范式将如何选择、发展是当前美国课程专家及其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三、启示
我国的课程研究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现代意义上的课程论的起步与发展在我国却较晚。因此,基于对美国百年来课程理论发展的梳理,以期为我国新一轮以课程为核心的基础教育改革提供以下几点启示。
(一)以史为鉴,另辟蹊径
首先,自课程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以来,不少研究者、学者、专家为课程理论科学体系的建立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所以从美国乃至西方课程论发展史的一些成名之作中汲取营养,有益于我国课程理论的研究。其次,西方课程理论的发展在立足于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还紧密地与实践相联系。由此启发我们要注重实践的路向,以各种实践来检验课程理论的正确与否才是马克思基本原理以及我国所倡导的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英国、德国等国家都曾照搬美国课程研究的范式,将其直接嫁接到本国的教育上。事实证明,脱离本国社会和现实的研究成果,直接拿来就用,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今后的课程研究必须立足我国国情,在厘清现实的基础之上,创新课程的研究范式。
(二)主线研究,广涉领域
不论是西方课程论专家泰勒的《目标模式》、查特斯的《课程编制》,还是我国课程研究专家单丁的《课程流派研究》、李臣之的《西方课程思潮研究》或是靳玉乐的《课程研究方法论》,以上研究者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研究必须基于一条主线来确定研究的范围,而不是漫无目的地去摸索。因此,对课程理论的研究在确定一个主题、一个视角的基础上,还要扩大视野。一是以其他学科为切入点,将其作为课程论研究的相关理论依据,如心理学中的智力理论、人格结构理论等;二是借助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如心理学对人认知、性格等发展规律的解释,哲学对人类发展以及教育原理本质的解释,来帮助课程论领域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型研究,不断促进课程论的发展。
(三)上下一心,协同合作
纵观美国的课程研究改革发展史,除了有前人不辞辛苦地研究,为后代教育的发展留下宝贵的财富以外,还有政府这个极其重要的掌舵手。如全美教育研究协会进行“八年研究”收获的成果,正是基于广大课程研究专家以及政府携手努力得来。课程研究专家和政府是指向针、掌舵手,一线教师便是进行船上作业操作的水手。课程研究专家和政府负责对课程方针政策、课程理论的上层研究,而一线教师在参与课程研究以及改革中是其政策等措施的实施者和实践者。正如美国进步教育所总结出的经验之一:教师应积极地参与实践改革,并与作为这种实践改革的基础理论联系起来。所以,对于中国课程论的发展,乃至中国教育的发展,都需政府、专家、一线教师上下一心,协调合作。当然,这也是目前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呈现的一种趋势。
(四)精神不泯,业精于勤
对于庞大课程体系的研究,不是一蹴而就的。不仅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及前人的课程论研究,还需要依靠广大课程研究专家以及研究者的坚定不移、贯彻始终的研究精神。对课程研究的追求是要在勤奋的前提下,加以技能业务的熟练和各种知识的学习,达到业有所精。至于当代课程研究学习者,更要在日积月累的锻炼中,磨炼意志,锤炼品格。所以,研究是集知识、技能、精神三者于一体的。相信在前人的引领下,通过当代研究者的辛勤探索,立足于我国本土课程理论的研究,会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