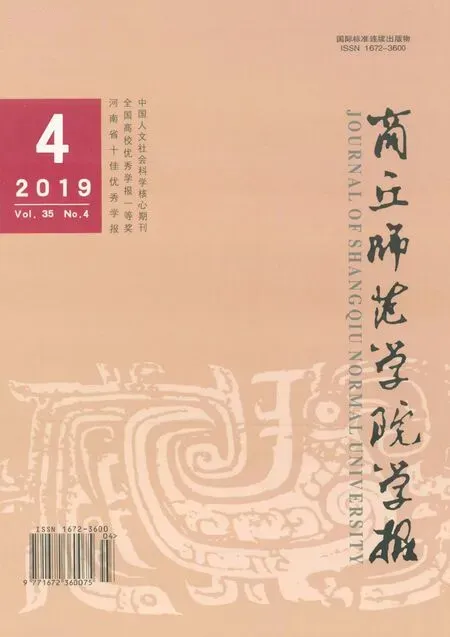《庄子》“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辨析
张 朋
(上海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上海200235)
《庄子·寓言》被认为是《庄子》一书的“序例”[注]王夫之《庄子解·寓言》有“此内外杂篇之序例也”。,而《庄子·寓言》所着重阐述的寓言、重言、卮言是《庄子》特有的三种言说方式,其对于《庄子》文本的理解具有关键意义,因此被称为“解庄的金钥匙”[1]。关于“三言”(寓言、重言、卮言)的讨论,学界已有许多[2],其中对寓言的内涵争议最小,但是误解最为突出[3],而关于重言的内涵争议很大,对于卮言的内涵新说最多。实际上综合《庄子·寓言》的上下文就可以发现,在对《庄子》寓言、重言和卮言三个概念进行正本清源的探究过程中,只有把“十九”和“十七”这两个非常关键的数量词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才能够给寓言、重言以及卮言以全面而准确的解释。进一步来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一句中“十九”和“十七”两个数量词非常珍贵,它们是《庄子》文本留给后人的重要线索,可以为我们理解《庄子》的独特言说方式提供巨大帮助。
以对“十九”和“十七”两个数量词的解说为中心,当前学界对于“寓言十九,重言十七”一句的解说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
第一种,郭象首倡的“寄之他人,十言而九见信”,“世之所重,十言而七见信”[4]947,成玄英、郭庆藩等学者都接受了这种说法。
第二种,林希逸最早提出了“十居其九”“十居其七”的解说,宣颖、陈鼓应、张默生、张松辉等古今学者都服膺这种主张[注]林希逸:《庄子口义》。宣颖:《南华经解》。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37页,其中有对张默生先生观点的直接引述。张松辉:《庄子疑义考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79页。。
第三种,王焕镳、曹础基认为,“十七”应该是“十一”之误,而“十一”正好与“十九”对合[5]421。
第四种,著名学者孙以楷慧眼独具,提出了“寓言十之又九条,重言十之又七条”这一新解释[6]10。
就第一种解说而言,郭象的说法明显是添字解经,妄加推测,说服力实在是不强,而且其中还有一个很大的逻辑漏洞:既然重言是“世之所重”,那么为什么其可信度“十言七见信”反而低于“寄之他人”的寓言的“十言九见信”呢?所以第一种解说经不起推敲,也就不能让人信服。第二种解说实际上是把“十九”和“十七”解说为分数“十分之九”和“十分之七”[注]中国古代分数有多种表述方式,其中母数加子数也是其中一种。参阅杨树达:《高等国文法》,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40页。,并且必须把“重言”解说为“寓言”的一部分,即“十之七”被包含在“十之九”之中,这样才能够理顺隐含的数量关系。第二种解说虽然在逻辑上有所欠缺,但是其含义尚属浅近,所以总体而言第二种解说目前在学界的接受度最高。第三种解说明显是在改字解经,而且没有证据支持。况且按照这种解说来看,既然十九与十一相合,即十分之九与十分之一相加为一,那么“寓言十九,重言十一”这一解说实际上是认为《庄子》一书全部是由寓言和重言组成,而卮言所占比例则被直接归零——这个分类比例实在是令人难以信从。第四种解说则紧紧抓住了“十九”和“十七”两个数字作出了最直接最简明的解释,可以说是在最大程度上尊重了《庄子》原文,所以综合来看这种说法可信度最高,但是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全面的文本验证。只可惜孙以楷在2007年业已仙逝,其当初的论说也不够充分和完整,以至于其首创的“寓言十之又九条,重言十之又七条”这种解说至今仍然应者寥寥。笔者不揣浅陋,对孙以楷所提出的这一解说进行必要的补充完善和进一步的讨论,以期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一、“寓言十九条,重言十七条”
作为《庄子》一书的体例说明,《寓言》篇对《庄子》“三言”的解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其应该是庄子思想的直接恰切表达。《寓言》篇对“寓言十九,重言十七”的解说是:
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
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
首先,《寓言》篇没有对“十九”和“十七”两个数字作任何说明,其中隐含的意义就是:“十九”和“十七”两个数字过于简单,所以无须解释。因此,对“十九”和“十七”两个数字作任何迂曲解说都很可能是不恰当的,其应该作字面直解,即“十又九”和“十又七”。
其次,在对寓言和重言的描述性定义之中,突出的是一个“信”字,即为了取信于人,庄子不直接宣讲而借助于他人之言,借助于德高望重的“耆艾”之言。就“信”这一点而言,郭象等学者的说法是有见地的。但是,因为某些原因,《庄子》本为避嫌求信所引述的他人之言往往不被看作是“据实引用”,而被看作是“子虚乌有”;《庄子》中所出现的先秦人物事迹往往不被看作“真实历史”,而被看作是“虚构捏造”。这就涉及了对《庄子》寓言的理解问题,对此笔者有专文讨论[3],这里就不再展开了。笔者的主要观点是:在没有历史资料证明其为伪造的情况下,《庄子》所引述的历史人物之言大都可以看作是“据实引用”,《庄子》中所出现的历史人物事迹大都可以看作是“真实历史”。
总体而言,笔者同意孙以楷的看法,寓言“藉外论之”之“外”是指“道外之人”[6]8。准确讲,这个“外”是相对于道家学脉而言的“外”,即在道家传承之外的各色历史人物,比如孔子、颜回等。学脉有内外之分而道学无内外之别,庄子认为,这些“外人”所言之中大有可取者,于是记录下来以作存留,这便是寓言。重言则有双重意义:一是相对于寓言之“外”,重言则为“内”。孙以楷以“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之“己”与寓言之“外”相对待,可谓见地独到[注]孙以楷认为,“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之“己”可以解为“自己”,实际上原文为已经之“已”(郭庆藩辑,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949页),“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说重言十七条是(耆艾)已经说过的话。。重言则是指在道家传承体系之内的人物所言,或者说是孙以楷所说的“道中人”所言,所以是为“内”。重言的第二重意义是指德高望重的“耆艾”之言。这也就是说,《庄子》中言道的诸位“耆艾”都可以看作是在道家传承体系之内的人物。对于年高德劭、道德圆满的前辈高人所言必须加以引述,否则就是“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天下》篇 “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的论述,可谓是深得寓言和重言概念的个中三昧。
按照“寓言十九条,重言十七条”这种理解,孙以楷曾经对《庄子》内七篇逐一进行检索最后列出两张表格进而使得每一条寓言或重言都得到明确指证[6]12-13。笔者甘附骥尾,对其表格的错漏疏失进行修正补充,最后得到下面这张表格(见表1):

表1 孙以楷“寓言十九条,重言十七条”表补正
其中把寓言十九条和重言十七条按照其在文本中出现的顺序一一列举出来。现对这张表格进行如下说明。
第一,从孙以楷所列表格和笔者进一步完善而得出的上述表格可以看出,《寓言》所谓的“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完全是针对内七篇所言,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寓言》篇特别是其前半部分的“序例”性质,内七篇在《庄子》之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寓言”和“重言”两个概念具体之所指。
第二,在孙以楷最初所列的表格中,十九条寓言和十七条重言都被列举出来,笔者所作的修订补充有三:一是把原来的罗列双方或多方对话人人名的列举方式改为引用部分原文,特别是保留了原文之中标示言说的动词“曰”;二是依据《庄子》原文对旧表中寓言和重言排列顺序的错乱进行订正,即原表格中寓言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前后次序错谬,将之对调,同样的还有《人间世》三条重言次序调整,《德充符》三条重言次序调整;三是对于寓言所在篇名的改正和次序调整,即寓言第二条出自于《逍遥游》,原表格错谬,而且原重言第十四条应该上调到第九条。
第三,“言”字的最显著含义有二,一是说,二是所说的话。“言”在《庄子》文本中直接体现为“曰”字开头的引用,而言说如果不是自言自语的话就必须有言说的对象,即有甲乙二人乃至多人之间进行对话。所谓的寓言和重言,在《庄子》文本中就是指各个篇章中所引述的一系列历史人物对话。与寓言和重言之“言”相对应,在《庄子》文本中频频出现的“曰”以及“问……曰”标示了绝大部分寓言和重言,个别寓言则是以与言说相关的“问”(寓言第一条)和“说”(寓言第十三条)为标志。
第四,就一个相对完整的寓言和重言来说,需要有对话双方同时出现。或者说,有一人提问而另一个人回答,这就构成了一个寓言或重言。在上表所列举的十九条寓言之中,只有第十三条“闉跂支离无唇说卫灵公”一段没有言说内容引述,其他的寓言以及所有重言都直接出现了标志着言语发生的“曰”或“问”(寓言第一条),并且都引述了言说内容。其中第一条寓言比较特殊,“汤之问棘也是已”一段有“问”无“曰”,是大意引述棘所说的话,属于间接引述而不是直接引述。第十三条寓言“闉跂支离无唇说卫灵公”一段也比较特殊,是讲述闉跂支离无唇游说卫灵公前后的情况,既然发生了游说而且游说成功,那么两人之间肯定有言说内容,只不过具体的谈话内容在《庄子》中没有加以记载。
需要强调的是,由此可以得出判断一条寓言或重言是否可以判为独立条目的依据:对话的双方如果都发生变化,则算作新的一条;如果对话的双方之中只有一方发生变化,则仍然算作一条,不重新计数。比如《大宗师》中的第十一条重言“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语曰”一段是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互之语,而第十二条重言“俄而子舆有病……曰”一段则是子祀、子舆二人相互之语,同样的第十三条重言“俄而子来有病……曰”一段则是子犁、子来二人相互之语。所以笔者将以上三条重言分列。另一个例子则是《大宗师》中的第十四条寓言“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曰”一段,其中首先是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互之语,然后是子贡与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互之语,最后是子贡与孔子二人相互之语。在这条寓言中有三个对话连续转换,而在言说双方之中每次只转换了一方,即在第二次对话中子桑户转换为子贡,在第三次对话中孟子反、子琴张二人转换为孔子,所以这三次对话只能够算作一条寓言而不是三条寓言。从每一条寓言或重言内容的完整性来看,这种界定也应该被确立起来。
第五,《逍遥游》有“惠子谓庄子曰”两则,《德充符》有“惠子谓庄子曰”一则,孙先生认为其“似为后学弟子所补缀,非出庄子之手”[6]11,这也就是说凡是涉及庄子这一人物的内容都是后人补记,不属于寓言或重言。实际上这三条对话根本就不符合上文所述寓言和重言的定义,因为惠施和庄子的对话既不是“藉外论之”的他者之言,也不是德高望重的“耆艾”之言。在《庄子》书中出现庄子与他人的对答,就庄子而言这属于直接言说,而且在先秦子书之中直接引述作者本人之言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其不属于“三言”中的任何一种。
综上所述,只有这样理解寓言和重言才能够切近“寓言十九,重言十七”之原意,也只有这样理解寓言和重言,才能够使得《庄子》内七篇中寓言共有十九条,重言共有十七条,二者数目做到丝毫不差。
二、“寓言十九,重言十七”与《庄子》历史文本
笔者看到孙以楷所提出的“寓言十九条,重言十七条”这一见解时的第一感觉也是难以接受,对此提出的第一个诘难就是:为什么只统计《庄子》内七篇而对外杂篇忽略不计呢?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展开,笔者的疑虑很快消失。必须承认,孙以楷认为“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其“只能是就内七篇而言”[6]15,这一判断是非常有道理的。笔者斗胆就《庄子》的历史文本作出以下论述,冀稍补孙以楷原著论说之不足。
在逻辑上,《庄子》一书一定有一个“层累地造成”的历史过程,即庄子首先亲自创作部分篇章,然后门人弟子在其生前和身后不断增益补充,最后扩展至司马迁所言的“十余万言”。 《庄子》内篇与外、杂篇的区分就是这一“层累地造成”的历史过程在文本上最直接的体现。整体而言,内七篇是《庄子》的核心篇章,而外篇和杂篇是《庄子》的附属篇章。但是外、杂篇之中的若干篇章,比如《寓言》以及《天下》(关于《天下》篇,笔者有专文讨论,这里不做展开)就需要特殊对待。从上文所进行的对“寓言十九,重言十七”的讨论来看,《庄子》文本的最初样貌应该是以内七篇为主体,而至关重要的《寓言》按照惯例应该居于书末:
北冥第一 (郭象本此篇名为“逍遥游”)
南郭子綦第二 (郭象本此篇名为“齐物论”)
吾生第三 (郭象本此篇名为“养生主”)
颜回第四 (郭象本此篇名为“人间世”)
王骀第五 (郭象本此篇名为“德充符”)
知天第六 (郭象本此篇名为“大宗师”)
齧缺第七 (郭象本此篇名为“应帝王”)
寓言第八 (序例)
对于上面所列出的《庄子》早期目录,特进行以下说明。
第一,作为《庄子》的核心篇章,内七篇理应是庄子自著,而《寓言》则很可能是庄子亲自为内七篇所作的序例。
崔大华根据崔譔《齐物论》之注推断,“至少在班固时《庄子》内外篇之分已为学者所熟知了”[7]53。在总体上把内七篇与外、杂篇区分开来,这无论从历史沿袭还是从文本研究都可以找到充分的依据。古今绝大多数学者也都对作为《庄子》核心篇章的内七篇最为重视,认为其思想体系相对完整,论说比较集中,可以视为庄子本人思想的忠实记载[注]任继愈曾经提出,《庄子》内七篇“决不是庄周的思想,而是‘后期庄学’的思想”(任继愈:《庄子探源》,《庄子哲学讨论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从他的见解提出至今,经过长期和反复的讨论已经愈见其谬,绝大多数学者都不接受这种看法。。
如上文所述,《寓言》对“三言”的解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应该是庄子思想的直切表达,特别是“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这一句解说更是把《寓言》篇与内七篇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以至于密不可分。“寓言十九条,重言十七条”,这清晰无误地说明《寓言》篇是针对内七篇所设置的“序例”,或者其不必排列在全书之首末,但是《寓言》篇作为《庄子》入门之必由之路却是确定无误的:不读《寓言》,无以明《庄子》——在两千年之后,这一设定仍然有效。
第二,张恒寿很早就注意到了郭象本《庄子》内篇篇名的“奇特”。这种“奇特”可以说“首先表现在题目的字数上,其次表现在题目意义的隐晦上”[8]26-27。 “内篇题目的奇特,更在于有些题目,和内容没有紧密的关联,而有勉强牵合的痕迹。”[8]26-29在对相关历史材料进行仔细研究后,张恒寿认为,“内篇题目是由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加上去的”[8]30。崔大华则根据西汉刘向大面积整理先秦典籍的情况认为,是刘向“给内七篇拟定篇名”[7][8]54。邓联合根据其对汉代思想史的考察,投给张恒寿一张赞成票[9],笔者也赞同张恒寿的主张,并在上面的目录中把七篇篇名恢复为篇首二字,使其与《庄子》其他篇名相统一,以还原历史文本面貌。其中“南郭子綦”是人名,不宜分割为两字,因此这一篇的篇名为四字。
当然,除了“十九”和“十七”两个数字之外,作为专门为内七篇所设置的“序例”,《寓言》关于“三言”的描述定义对于外、杂篇也是适用的。或者说,内七篇之中的“三言”为外、杂篇的创作树立了典范,而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寓言》也是《庄子》全书的“序例”。
三、“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是对卮言提供的一种新解释
寓言、重言、卮言三者的关系问题是“三言”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对此一问题大体上有四种观点:一是卮言为本,二是寓言为本,三是混融交叉,四是三者并列[2]。其中必然涉及对于寓言、重言、卮言以及《庄子》文本的不同理解,众说纷纭,难以统一。上文对“寓言十九,重言十七”的讨论,特别是对内七篇文本进行检索而形成的寓言和重言一览表格,或可对此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帮助。
首先,寓言、重言、卮言三者应该是并立关系。
寓言和重言区分的关键在于言说者学派所属的差别,即言说者或处于道家学派之外或处于道家学派之内,所以寓言和重言无疑是一种并列的关系,二者互不统属,泾渭可判。《寓言》所谓“寓言十九,重言十七”的重点是说明寓言和重言的数量,而在接下来对寓言和重言的定义之中则着重说明了言说者身份的不同。“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明显是在强调其言说内容如日出之新新,如天运之无穷,即所谓“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始卒若环,莫得其伦”。由此可以推导出作为“三言”之末的卮言应该是与寓言和重言并列作为第三种独特言说方式而独立发挥作用。
其次,如果认定《庄子》内七篇的寓言和重言就是指其中所引述的一系列以“曰”为标示的历史人物对话,那么卮言首先就是指那些虚拟人物的话语,这里所说的虚拟人物当然就包括《庄子》中那些堂堂作人言的各种小动物。
第三,从《寓言》对卮言的描述性定义来看,卮言应该具有新颖和机变这两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庄子》中这些虚拟人物的假造话语,既为行文创意打开了新的话题和视域,如日出之新新,又使得关于道的言说可以无穷无尽地延伸下去,如天运之无穷。具体来说,卮言在《逍遥游》之中至少有以下两则: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
鹏鸟“培风”九万里,直到“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对于这种厚积薄发的宏图大展,蜩与学鸠表示难以理解:为什么要到九万里那么远的地方去呢?斥鴳也认为,鹏鸟之怒而飞毫无必要,自己只是在数仞之间跳跃,在蓬蒿之中飞翔,它认为这样已经是飞翔的极致了,无须再求。庄子虚拟了以上两则言语,进而以鹏鸟之飞对比蜩、学鸠和斥鴳之飞,新颖别致而又充分完美地阐释了大小之间的难以想象的差距,真真堪称是“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通过卮言对“大小之辨”的阐释在庄子后学那里仍然在进行,并且引向深入。比如《秋水》篇中望洋兴叹的河伯就是见到北海之后方知自身之小,并且对“大小之辨”这一问题进行了总结:“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最能够体现卮言特征的是河伯与北海若之间接下来的对话,活脱脱就是两个古代修道者在讨论关于认知的基本理论问题,最后以北海若颇能体现庄子精神实质的一句话“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结束。可以说,对于“大小之辨”的讨论在虚拟的卮言之中获得了完全而充分地展开,而卮言新颖和机变的特征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此外,卮言应该还包括那些新颖隽永的对话以及故事,比如《齐物论》中“罔两问景曰”一段,还有《应帝王》中的“南海之帝为儵……曰”一段。这些虚拟的对话以及故事在《庄子》书中虽然没有被充分阐发,但是其在庄子思想中无疑占有重要地位,是庄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我们试图按照一般的西方哲学著作阅读经验而在整体上理解和把握庄子思想时,这些对话以及故事往往就会以一种游离或跳弹的状态提醒我们《庄子》文本的开放性和不可通约性,这是卮言的另一种独特文本意义。
四、寓言、重言、卮言与道之言说
老子在《道德经》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了道的言说困境:“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方面,道不可言说,可言说者并非恒久之道,名谓之可称者,皆非道之所属;另一方面,对道之言说又必须展开。为了启迪后世或者教诲后学的目的,修道者又必须把自己的认知和体会通过语言或文字传达出去。所以老子本无意著书立说,但是为尹喜强留而著五千言。《老子》中对得道之人和得道的状态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对道的存在、称谓、意义和功用等进行直接的概括,此外还使用了大量的譬喻以及引用。五千言乃是老子一生“修道德”的总成,言简而义丰,阐述道德之幽深玄奥、宏阔博大。太史公对五千言的概括是“言道德之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而所谓“言道德之意”也就是直接言说道德之意旨,就形式来看,老子《道德经》主要是对道的直接言说而不是间接言说。
《老子》之后,有列子及其门人弟子作《列子》存世[注]《列子》一书,先秦两汉流传不广,晚至魏晋张湛作注后方为世人所熟知。自唐代柳宗元《辨列子》开始,后人多疑《列子》为伪作,很多现代学者都将其作为魏晋玄学的思想材料而不是作为先秦道家思想材料开展学术研究。其实《列子》一书大体可信为列子及其门人弟子所作,即使有少量后人思想羼入,但其仍然是先秦道家的重要著作。近年来,已经有很多学者对此反复申明,比如许抗生《〈列子〉考辨》(《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马达《列子真伪考辨》(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其中对道的言说方式又有增添:在直接言说之外,又有间接言说。具体来说,“无所由而常生者,道也”这是对道的直接言说,这种言说方式在《老子》之中曾经多次出现,而在《列子·周穆王》之中出现的这句话,无疑是列子及其门人弟子对道的看法的直接表达。除此之外,《列子》还记载了许多历史人物之间的对话,比如《天瑞》有“舜问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舜问丞如何能够得道。)丞的回答显然贯彻了“道不可言说”这一原则:“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身体都不是你所有,你还能够保有道吗?)这显然是“道不可言说”的深层次原因,而这一句以及其他历史人物的论道言语都可以看作是凭借《列子》文本而出现的非列子所言。相对于列子直接言说而言,《列子》收录的这些历史人物所言是间接的论道言语,而根据《庄子·寓言》的观点来看,这些无疑都是“藉外论之”的寓言,虽然《列子》之中并没有出现“寓言”这一概念。此外,《列子·黄帝》有对黄帝言语的记载,有对老子言语的记载,这些德高望重的“耆艾”之言也是间接的论道言语,而根据《庄子·寓言》的观点来看,这些无疑都是重言,虽然《列子》之中也没有出现“重言”这一概念。在寓言和重言之外,《列子》中还有很多可以看作是卮言的小故事,比如愚公移山、塞翁失马、歧路亡羊、杨布打狗等,以及“海上之人有好沤鸟者”一段。就道之言说来看,这些小故事都新颖深刻,并且具有多向阐发的可能,这也正是卮言所具有的特征。所以,《列子》之中虽然没有像《庄子》出现明显的序例说明,但是其“三言”(寓言、重言、卮言)特征已经具备,对于《庄子》的创作而言其无疑具有先导的意义。
《庄子》完全继承了《列子》的言道方式,并且更进一步,自觉地对“三言”的内涵和特征进行概括和总结,有意识地对三种间接言说方式的效用与意义进行归纳和提炼,并对其加以数量统计和全面应用实践,进而给道之言说拓展了一系列的新视阈,增加了一系列的新话题。在《庄子》之中,“三言”的运用圆熟而自然,其数量、其人物涉及范围、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太史公以“散道德,放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概括之,可谓恰如其分,而《天下》以“万物毕罗,莫足以归”称许之,可谓实至名归。
五、结语
按照现代学术的眼光来看,“三言”之中的寓言和重言因为记载了很多历史人物的言语,所以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在黄方刚、陈鼓应、孙以楷等前辈学者的努力之下,《庄子》寓言和重言的历史文献价值正在逐渐开显。笔者非常赞成孙以楷的判断:“《庄子》的作者是造伪无意而取信有心,对《庄子》的怀疑是缺乏根据的。”“《庄子》是关于道家文化最古、最丰富、最完整的资料,考证道家源流,必以《庄子》为门径,而考证《庄子》中的道家人物,又必以对‘三言’的辨证为支点。”[6]27-28斯人已逝,而其远见卓识仍然启迪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