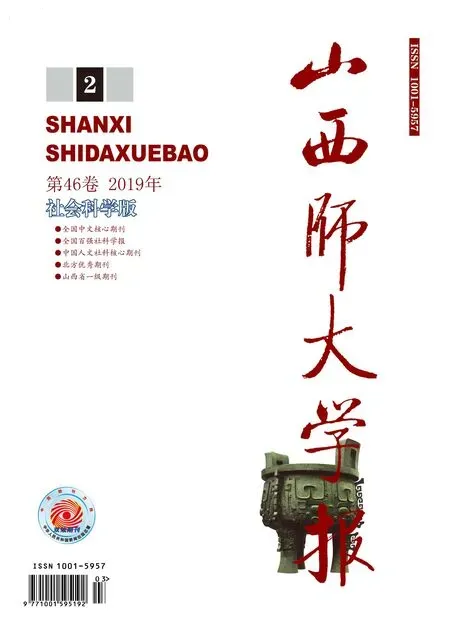庙堂与江湖:从修省弭灾看明代士大夫的时代性格
余 焜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所谓“修省弭灾”,即通过修身反省来消弭灾祸。《周易》中“渐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1]62对“修省”的阐释当为这一概念之滥觞。这种修身反省的思想经历代统治者的继承和发展,迨至明代,仍为统治阶级所奉行。明代继唐宋以及元朝制度而来,对前代制度多所损益。明太祖鉴于前代相权过重威胁到皇权的教训,在唐宋分割宰相权力的基础上,直接废除宰相制度,集权于皇帝。如此,制度范畴内对皇权进行约束的机制减少,而通过“修省”来对皇帝言行和施政方针进行规谏就显得很有必要了。士大夫通常借灾异发生进行修省之机上言时政以使政统在正常轨道内运行;同时,对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维护也是士大夫群体坚定不移的愿望,这些都是在修省弭灾活动下精英群体所发出的时代声音。明人黄绾曾言:“我朝自太祖皇帝创业以来,守文继体,百有余年。以迄成化、弘治之间,文恬武嬉,日极豫泰,朝廷始不亲政,故当时臣寮始事援结,内交宦官,外植私与,命官用人,一视其好恶为贤否,靡然成风,皆为当然。”[2]629明初太祖革旧布新,明帝国蒸蒸日上,到中后期,各种社会问题和政治积弊迭出,作为制度体系维护者的士大夫,常借修省弭灾之机充分展现自身的政治抱负和人格魅力。明代士大夫在修省弭灾政治活动中所秉持的身居庙堂则为君分忧,退处江湖亦心忧社稷的政治理念,正是宋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3]的政治风范在明代的深刻实践。
一、矫治政统:心系社稷与对君主的规谏
(一)指陈时政阙失。明朝享国近三个世纪,在这漫长的时间段里,各种灾异也较历史上其他时期频繁。在灾异发生之时,明廷最高统治者通常发布修省诏令,实行各项弭灾措施以消灾弭祸,其中皇帝下诏求言是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弭灾举措。此时,官僚系统内的士大夫精英们纷纷借机向皇帝进言,指陈时政阙失的章疏俯拾皆是。
明英宗九岁登极,朝政大多委以张太后及内阁三杨,仍承仁宣之治的余绪。随着杨士奇、杨荣等顾命大臣和张太后的离世,为英宗信任的太监王振日益恃宠称骄,进而把持朝政。“初,张太后既崩,王振遂无忌惮,作大第于皇城,又作智化寺于居东,以祝釐,自撰碑,始弄威福”[4]446。正统八年(1443年),“戊寅,雷震奉天殿鸱吻”[5]1647,次日,英宗宣布辍朝三日,遣官致祭天地,在下诏罪己的同时,敕谕文武群臣同加修省。随即,时任翰林院侍讲的刘球上疏言修省十事,其中大多涉及朝廷大政方针。在以刘球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看来,“所谓国家失道,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此天心仁爱人君也。”[6]220上天降灾意味着政治运行中出现了纰缪,以灾作为惩罚的形式以引起统治者的警省。针对正统年间的政治趋向和社会情态,刘球劝谏英宗要远离宦官,分别贤否,并指出若“皇上察之于己,询之于人,果贤而可亲也则亲之,果不肖而当远也即远之,则君子日进,小人日退矣”[6]220—221。这主要是针对正统初期宦官王振势力日益膨胀而对年少的英宗进行提醒。此外,正统年间,云南麓川宣慰司思任叛乱,明廷为之劳师糜饷,财用大匮。刘球在奏疏中言及此事,劝谏英宗放弃征伐麓川,以体现修省弭灾之诚。上疏切谏的刘球因为忤逆王振之意,且言麓川之失,被逮下诏狱。刘球为指陈时政阙失不惜身陷囹圄,这种性格的养成是儒家思想体系下士大夫独有的一种政治关怀。
弘治时期任职首辅十余年的刘健,历侍四朝,在士大夫群体中享有极高的声望。武宗继立,身为孝宗托孤重臣之一的刘健,借正德初年出现灾异,武宗敕群臣修省之机上言时政。鉴于明中期织造工役繁兴、官场奸弊丛生的现状,刘健指出:“天下之事,有轻有重,有缓有急,得其序则治,不得其序则乱,而所不当为者弗论也。夫事之重且急者,不过亲贤爱民,赏功罚罪而已。”[6]403意在指陈武宗耽于政事,历数时政积弊希望引起武宗的重视,以杜绝政刑乖谬、滋事扰民的现象。可惜的是,这封题为《论圣政疏》的奏章没有引起武宗的重视,刘健也与正德元年(1506年)罢去首辅职位,辞官归里。
每逢灾异发生,皇帝下诏求言,诸多士大夫上疏指陈时政阙失,这是他们政治生活的一种常态。虽有时不免流于形式,但与当时政治社会状况息息相关的奏疏言论基本上反映了士人心中“食君之禄,担君之忧”的政治取向,也是他们政治性格得到凸显的绝佳方式。
(二)规范君主言行。在传统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君主向来被赋予“神”的力量,“天命观”和“君权神授”观念已然深入人心。君主的一言一行关乎整个时代的发展走向,由此对君主言行进行规谏和调整就显得极为重要,尤其是在各种灾异迭见,王朝面临忧患之时,借修省弭灾,及时规范君主言行就更为必要了。
一直以来,明武宗就被史家所诟病,在其当政期间,因其视朝政如儿戏,且耽于逸乐,言官多次上疏劝谏。正德元年(1506年),武宗初即位,“先是正月天鼓鸣,二月陕西地震,星斗昼见”[7]1582,各类灾异不断出现。于是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纷纷上疏,指陈时弊,认为此次灾异的发生与朝廷的政策施行不当相关,但更多的是来自弘治旧臣对武宗圣学荒殆、纵情逸乐的指责与规劝。这年四月,五府、六部等衙门会同英国公张懋合词上疏,并借周公辅成王之例引起武宗注意。“仰惟皇上嗣位以来,日御经筵,躬亲庶政,天下喁喁望治。迩者忽闻宴闲之际,留心骑射,甚至群小杂沓,径出掖门,游观苑囿,纵情逸乐,臣等闻之,不胜惊惧。”[7]1583章疏言辞恳切,在对武宗好玩乐进行批评指责的同时,透露了群臣对武宗回归圣治的希冀。
“人主之在天下也,犹人之有心,天之有斗柄也。心之所运,视听持行,罔有或违。斗之所指,春秋寒暑,罔有勿应。故天下之治乱,未有不系于人主之一身者也。”[8]399明末著名学者陈子龙关于君主于天下治乱中所扮演角色之分析,正体现了士大夫群体共同的圣君致治理念,为士大夫奉为圭臬。至嘉靖时期,阳明心学备受崇奉,将自己的内心体认和治国平天下之理念相结合,即是这一时期流行于士大夫群体中的普遍观念,他们通常将其融合于政治实践,在灾异多发之时对君主言行进行规范和劝导。嘉靖二年(1523年),各种灾异在各地不断出现,“礼部左侍郎贾咏等以久旱风霾疏请修省。”[9]695随后,星变异常,“辛未,岁星、太白同昼见。”[8]1920此处所提到的“岁星”,即我们通常所熟知的“木星”。而太白星则指“金星”,俗称“启明星”,通常在夜间出现。岁星、太白于白天同现,在时人看来与天象运行的正常规律相悖,而反映在人间秩序方面,则必定是社稷不稳或是人君失德。此时,给事中章侨上言:“乞举祖宗故事,早朝班退,许百官以次门上启事。经筵日讲,时赐清问;密勿大臣,时勤召对。”[9]695—696上疏言勤经筵日讲来批驳嘉靖帝“高拱穆清之上,而付万几于章奏之间,空文太多,未必尽经睿览”[9]695的慵懒怠政行为。
明代中后期的皇帝大多怠政,甚至视国家大政如儿戏,耽于游宴的诸如武宗、熹宗,不问政事幽居深宫者如世宗、神宗,而活跃在政府各部门的儒家正统思想规范下的士大夫对朝廷社稷的稳定和发展多所擘画。在灾异频发之时,上章与闻时政,向皇帝表达自己对时政的看法和对最高统治者言行的规范,正是明代士大夫群体关切时政、忠君体国的政治性格的彰显,而这一性格又通常是在弭灾活动中得以展现的。在儒家士大夫看来,他们所期待的圣治又是政统和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支撑的道统的统一,对儒家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捍卫在修省弭灾活动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捍卫道统:对儒家正统思想的维护
(一)对佛老恣意盛行的态度。明朝初立,明太祖朱元璋就极力提倡儒学,起用元末名儒叶琛、章溢等人以咨求治道。在以儒学立国的旗帜下,还明确提出佛老之教“阴翊王度”的作用。在与臣下谈论佛老时,明太祖曾言:“近代以来,凡释、道者,不闻谈精进般若、虚无实相之论,每有欢妻抚子,暗地思欲,散居空世,污甚于民,反累宗门,不如俗者时刻精至也。”[10]213在明太祖看来,佛道两教对人的教化作用是不能与正统儒家思想相提并论的。明中期,南直隶苏州人袁袠对明太祖的宗教政策也有自己的看法。“高皇帝既定天下,欲遂灭佛老之教,当时诸臣,无傅奕之深识,而袭萧瑀之庸愚,因循苟简,渐以滋蔓。周颠仙、张三丰、天眼尊者之徒,妖荒迂诞,怪乱不经。”[11]16诸如佛道之教尊崇的“圣人”也只是用来愚惑民众的,大多荒诞不实,不足以信。这种思想代表了有明一代大多数以儒学正统自居的文人士大夫对于佛老之教的看法和观念。
与明初对佛道之教在承认其合法地位的基础上又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不同,成化至正德三朝佛道泛滥的现象开始凸显。明宪宗在位的23年中,曾多次沉迷于修斋建醮,宠信方士,大修寺观塔院,以延至弘治、正德时期,出现“寺院宫观,斋醮无时,佛书道经,刊为相继”[6]404的不和谐局面。以儒家正统居之的士大夫群体纷纷上疏指斥佛道泛滥对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发展诸多方面带来的危害。在大多数文人士大夫眼里,孔孟之学是自古以来佐君治道的既定法则,不可变更,而对于佛道的渗透则持批判和否定态度。成化七年(1471年),出现星变,明宪宗下诏修省。时任文渊阁大学士的彭时以灾异上言,直斥佛道为异端。“夫天下之道,正与邪而已。正者,帝王之道也;邪者,异端之教也。邪正之间,治乱系焉。皇上聪明圣智,岂不知所以抉择?而颇留意佛事者,聊以试之,非诚信之也。”[12]1893彭时把帝王之道与佛道二教之间的对立,上升到正邪之分的层面,其对佛道的态度尤为明确。弘治时期,以刘健、徐溥、商辂等人为代表的高层官僚群体,经常利用修省之机对孝宗提出建议,以期恢复登极之初朝政欣欣向荣的局面。弘治八年(1495年)十二月,内阁大学士徐溥上疏,“臣等读儒书,穷圣道,道家邪妄之说,未尝究心。至于鄙亵词曲,尤所不习,不当以非道事陛下。所以连日忧惶不敢奉命者,实不愿陛下为此举也。”[12]1951—1952徐溥的言辞虽然没有彭时那般犀利,直斥佛道之教,但也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其观点代表了当时高层士大夫的普遍心态。
至正德、嘉靖时期,心学在思想界占据主流地位,士大夫在修省弭灾活动中排抑佛道的倾向更加明显,但也日渐显露出将其杂糅进儒学系统的尝试,这与此一时期最高统治者耽于佛事修道相关,又源于士大夫对内心世界的体认和对佛道之教的认识。正德十年(1515年),西番进献佛骨,明武宗花费重金举行隆重佛事以庆祝。时逢明帝国境内多地灾伤不断,盗贼横行,心学泰斗王守仁上疏劝谏明武宗毋耽于佛事,当以国事为重。在他看来,“夫佛者,夷狄之圣人;圣人者,中国之佛也。在彼夷狄,则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导愚顽;在我中国,自当用圣人之道以参赞化育”[13]357—358,并以舟车为喻来论证不可将做佛事当作治理国家的途径,应窥见其利害。至嘉靖时期,世宗崇奉道教,一意修玄,这就更加引起了士大夫对道教的指斥。嘉靖初,以方士邵元节为“真人”,至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又“加封陶仲文恭诚伯”[4]789,而后,“诏修太和山玄帝宫”[4]790。有鉴于此,诸多士大夫纷纷上章疏谏,加之世宗在位的四十多年里灾异频仍,时而下诏修省,以此为契机,久居官场的儒家士大夫们都竞相从维护王朝社稷的立场出发抵触佛道对世俗政权的渗透,以及对最高统治者精神的腐蚀。
明代士大夫群体大多视佛道之教为危害社稷的异端,虽然在明中期出现儒释道相互糅合的趋势,但儒家文人通常都对其异常的发展趋势持否定态度。尤其是在灾异发生后,把佛道异常发展的现象作为士大夫们维护道统、抨击时政的引子。这一态度的形成不仅来自为朝政和社稷的担忧,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思想培育下的社会精英们为了维护儒学在思想体系层面的主体地位而做出的努力。
(二)儒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与实践。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士大夫服膺纲常名教,向来将宗族和礼法制度视作一切伦理道德的核心。如若遁迹空门,委身佛教,则通常被一般士大夫斥为异端。明朝建立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以儒学为本,明太祖在国家机器建设和各项政治制度建立方面都极力贯彻儒学之道,儒学在明帝国思想精神层面居于主导地位。“明兴,嘉尚儒术,敦崇教本,乡社有学,郡县有庠,即党遂之规也。”[11]9正如明人袁袠所言,明初在重建社会秩序的同时,也确立了儒学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尊崇地位。
在明王朝统治的近三个世纪的时间里,大大小小的灾变可谓数不胜数,由此而进行的修省活动也格外频繁,每逢修省,官僚系统内的士大夫群体在指陈时政的同时还极力维护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导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到明中后期,心学的发展独树一帜,至王守仁集其大成,而后王门后学罗汝芳、聂豹等人将心学推向新的高度,形成众多流派。作为儒学体系内的重要一支,心学的发展在儒家士大夫群体中影响广泛且日益为大多数人所奉行。每当佛道之教的发展过分干预世俗政权的运行时,他们往往借修省之机毫不留情地批驳和痛斥之。如嘉靖二年三月,出现星变,“金木星俱昼见”,“四月壬申朔,敕群臣修省”。[5]3278大学士杨廷和上慎始修德十二事,其中说道:“祈祷之事,帝王弗尚,何况僧道邪妄之书,岂可轻信!……夫斋醮之事,乃异端诳惑,藉以为衣食计者。佛家三宝,道家三清,名虽不同,同一虚诞。”[8]1924针对佛道虚无、荒诞的特点直接指斥,以突出儒学在帝王修习和治国方面的重要作用。
对儒家思想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还是大多数理学家终身恪守的教条之一。他们在指斥佛道泛滥的同时,坚守本心以维护儒家思想的尊崇地位,极力将佛道之教与儒学划开界限。他们普遍认为:“禅家存心有两三样,一是要无心,空其心,一是要羁制其心,一是照观其心;儒家则内存诚敬,外尽义理,而心存。”[14]41由此推知,“儒者心存万理,森然具备,禅家心存而寂灭无理;儒者心存而有主,禅家心存而无主;儒者心存而活,异教心存而死。”[14]41由此可知,明代士大夫通常借修省之机指斥佛道而维护儒学正统,主要是基于佛道二教本身所具有的神秘感和虚无主义易于诳惑人心,以至于渗透进世俗政权之后会产生不可想象的消极影响。而儒家思想作为历代王朝推崇的正统思想,将其纳入明帝国统治体系中与佛道对立,这也是明代士大夫极力维护儒学道统、排斥佛教并视其为异端的初衷。
生活在明代的士大夫,随着科举考试的日兴,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士人以其知识来支持本质上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把它看作是既定的前提。”[15]119与西方社会政教合一,宗教参与世俗政权并在国家体制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大相径庭的是,中国古代传统王朝始终未能将富于浓郁意识形态的宗教与政治发展并驾齐驱,而是将儒家思想深嵌于治国理念和施政方针之中,即使于唐宋之际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之时,儒学思想体系也并非如佛道二教般有着明确的教义和神明崇拜,其最初的旨归仍源于儒学经世和事功之理念。
三、修己致治:士大夫进退之间的政治性格
(一)乞休自劾,躬身自省。儒家思想贵乎“诚”,尤其到了明代,经宋儒二程、真德秀等人的糅合与推演,理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开始注重内心之体认和对外物的充分感知,即“格物”与“致良知”学说紧密结合。“夫一者,诚也,天之道也;诚之者,明也,人之道也,致良知是也。因明至诚,以人合天之谓圣。”[14]7这种内心之诚附之于政治实践,则主要表现为士大夫群体忠君体国,每遇灾变则主动修省,反省自身阙失。在明代这个灾变频生的时代,心怀天下的儒家士大夫们通常以修省为契机来实现自身报国的理念,完成自我内心世界的修炼,其中,遇灾修省时乞休自劾就是这一政治性格最好的反映。
清人彭孙贻曾言:“在古天变日食,往往贬斥大臣,或至赐死,以塞天谴。”[16]14历代王朝均有遇灾修省以弭灾祸的事例,如彭氏所言遇天变则将臣下以罪论死的情况,在明代并不多见。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在官的士大夫群体在遇灾变时通常上疏自劾,乞休告退。正嘉之际,京师数次地震,朝野人心惶惶。曾经三次入阁的费宏曾上疏明武宗,应“昧爽临朝,修举圣政”。[17]170嘉靖三年(1524年),“春,正月,丙寅朔,南京地震有声”,[7]1893后数日,“庚戌夜,南京地震。辛亥,苏、常、镇三府地震”,[7]1897于是世宗下诏修省。时蒋冕、毛纪等人因“议大礼”论劾而离职回乡,费宏担任内阁首辅,他因受嘉靖帝厚恩,在“议大礼”被弹劾后未忍立即离去。值修省之时,费宏上疏乞休,认为自己虽身居首辅然威望不足以服众,“每负愧而怀忧,恐妨贤而病国。盖群臣之中,惟臣官最尊,不职最甚,而致灾之罪,臣尤不得而辞也。”[17]184—185著名理学家吕坤与费宏有着同样的政治性格。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九月,时任刑部郎中的吕坤,奉旨将内犯陈忠等人拟军,因失误而致多人以斩首论罪,恰逢灾异非常,由此吕坤深切悔悟,上疏乞罢。“三年大旱,由匹妇之含冤;六月飞霜,因一夫之抱屈。今刑部狱中含冤抱屈者不止一人也,不平隐愤,上徹云宵,郁结穷愁,散为灾祲”,[18]69即是他内心的独白。以避位的方式来希望灾变消弭,是吕坤完成内心体认的重要一步。
明代士大夫遇灾乞休致仕,并非简单地逃避责任,远离是非,这种乞休退隐也与消极遁世的道家精神大相径庭。儒家思想在古代士人的思想观念中起着主导人生观的作用,并且随着儒学的发展,到明代日渐内化为士大夫的人格旨趣和心理结构。明人焦竑曾言:“王端毅鲠亮峭直,好善恶恶,出於诚意,悯时悼俗,有甚获疾。故身虽在外,而其心无日不在朝廷。”[19]43—44许多士大夫虽然在修省时乞休,但多是一种积极承担自身责任的表现,这在传统社会积极入仕的思想范畴内也属一种无奈之举。儒家士人群体的最高追求,在于出仕行道,而非退处隐居。正如《庄子·让王篇》中提到的,“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20]980,道出了隐士心中既希求恬然自得的隐居生活,又颇想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矛盾心理。这一说法与明代多数士大夫的心理诉求不谋而合,因灾乞休退罢,是一种希望以此举来消除灾祸的方式,虽身在“江湖”而心系“庙堂”,绝非真正的隐士所怀有的那种厌倦官场、甘于老死山林的人生追求。
(二)忠臣死社稷的别样情怀。深谙儒家忠孝节义思想的明代士大夫在修省时通常能积极主动地去承担责任,反省自身阙失,除了乞休致仕之外,还有一部分人采取较为激进的方式,即冒死上疏皇帝,抨击时政。他们秉持忠臣死社稷的理念,在灾异发生时,直言不讳,虽然难免冒犯皇帝而致身死或是被黜,但于士大夫群体来说是对自身人格的重要提升,也是实现自己忠君为国理想的一种途径。
洪武九年(1376年),多次出现天变现象。三月,“辛酉,荧惑犯井宿。”[21]1749“壬申,太白昼见。”[21]1749秋七月,“癸丑朔,日有食之。”[7]339至闰九月,“壬午朔,有星自天船东业行,约流丈余,光芒焕发,入紫薇,至四辅没。”[21]1809随即,明太祖以灾异下诏求言。时任山西平遥训导的叶伯巨闻训上疏明太祖,“臣观当今之事太过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6]52所言切中时弊却反引明太祖大怒,将其下狱,后庾死狱中。至隆庆时期(1567—1572年),北方蒙古俺答频繁犯边,骚扰边地,掠夺边民,加之各种灾异频发,紧张氛围弥漫朝野。先是“俺答犯大同,掠山阴、应州、怀仁、浑源等处”,[7]2522入冬以后,“辛酉朔,彗星见天市垣,东北指,凡二十日而灭”,接着“京师地震有声”,[7]2522于是明穆宗下诏百官修省三日。尚宝司丞郑履淳应诏陈言,他认为灾异频发是因为近年“纪纲因循,风俗玩愒;功罪罔核,文案徒繁;阍寺潜为厉阶,善士渐以气短;言涉宫府,肆挠多端;梗在私门,坚持不破”[7]2524等现象所导致的,直陈时下弊害,希望引起隆庆皇帝的警省。不料,隆庆帝大怒,将郑履淳处以廷杖之刑,并投入刑部监狱,后在言官的疏救下得以释放为民。这件事后,“淳之像文文山而事之也,意念深矣,卒以忠谏显”,[22]748深受其父郑晓忠诚敢言、心忧社稷之为官情怀的影响,由此闻名于儒林。
“死社稷”自古以来是儒家思想体系下对君主在国政治理以及社稷维系方面的最高要求,也是王朝国家面临危难甚至社稷倾颓时君主当保有的那种为社稷而尽忠死守的志节。而于灾异频发的明代,深受儒家思想侵染的士大夫群体多秉持此种为社稷献身的风节,每当修省弭灾之时,他们多上疏论谏,以期消灾弭祸,力挽政治颓势,使国家顺着正常轨道运行,甚至逆君主之意也在所不惜。“死社稷”的理念由之也更加扩大化,流行于明代士大夫群体中,而不仅仅是对君主个人为社稷身死的要求。而这一变化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明代政治生活中频繁的修省弭灾活动催生的。
四、结语
活跃在明政权各级重要职位上的士大夫,作为社稷基石和社会精英群体,他们对明政权的建设和巩固,以及对不同时期政策的变动与调整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明代士大夫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参与政权建设,其所生活的明代社会作为一个儒家思想高度发展的环境空间,对这些在官的社会精英不论是参政还是在野,都将其思想意识紧紧束缚在儒家道德伦理的框架内,其忠君报国的固有理念更加实践化。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享国的近三百年时间里,政治发展与社会变迁基本上与灾异频发和应对相联系,而为消弭灾变所进行的修省活动也相对频繁。在修省弭灾这一富于政治意味的活动中,明代士大夫扮演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每遇灾变,身居庙堂的士大夫们则基本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职责,尤其是身负“风闻言事”之责的言官,纷纷上疏指陈时政阙失,或者规谏皇帝当以身作则,以期朝政恢复正常。在意识形态方面,士大夫也始终坚守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实际上,明代士大夫通常借修省弭灾之机发起儒家思想与佛道之间的论战,以儒家正统地位贬斥和打压佛道二教的过盛势头,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维护明政权赖以教化民众的儒家思想的主流价值观念和固有地位。从这一角度而论,明代士大夫在修省弭灾中又扮演着“卫道士”的角色,而修省弭灾也不仅仅旨在消除灾变,而上升到了维系王朝正统思想的高度。
深受儒家教育的明代士大夫,还有着一种独特的志节,即主动将致灾之由归咎为自身的失职而上疏乞休,退出“江湖”,以躬身反省。他们虽然去职,但与历史上各时期隐士的旨趣大相径庭,即使不在其职也时刻心忧社稷,渴望为君分忧、为民造福。在遇灾变而修省时,其中一部分人则选择更为激进的方式向皇帝进谏,即使身陷囹圄也要保全自身志节,坚守忠君报国的精神理念。
由此可见,明代士大夫的时代性格在修省弭灾的政治活动中向我们展现了明代特定政治环境下官僚士大夫群体的整体精神面貌。透过修省弭灾这一政治文化活动,明代士大夫不论在朝还是在野,都散发着浓郁的家国一体、社稷为重的政治情怀,同时也努力坚守和维系着其精神支柱即儒家思想理念的主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