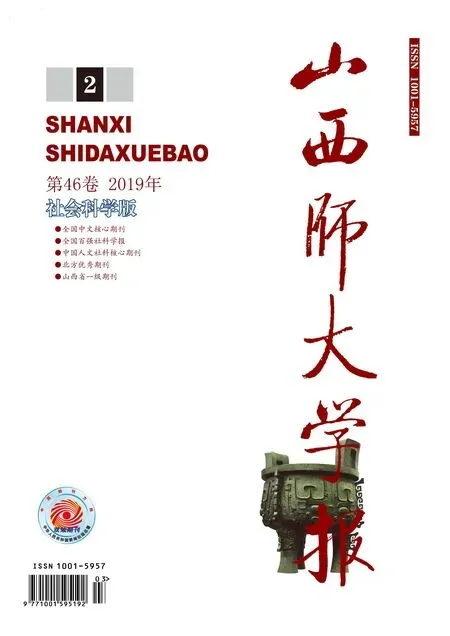马克思遭遇物化:空间生产对资本批判的逻辑僭越
熊 小 果
(四川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 611130)
一、问题缘起:当代资本批判的空间本体化倾向
资本批判空间本体化倾向始于列斐伏尔。他在《空间的生产》中谈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最好的方式是重构它,用“空间生产”“修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把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时间—社会—空间唯物主义”,将资本批判“推进”为“时间—空间批判”。他以空间生产为要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用空间生产逻辑置换资本批判逻辑:资本以空间生产的方式存在。[1]空间生产理论都是以此批判资本关系的。[2]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把空间从外部镶嵌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中;苏贾后现代地理学建构了“空间本体论”;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空间理论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关于空间”的,“现代主义是关于时间”的;卡斯特网络社会空间理论把空间理解为“时间的结晶化(物化)”。
该倾向在国内学界亦很明显。有人把资本运动与资本的空间运动等同起来,认为空间路径既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资本批判当代出场的根本路径,①这种观点意在强调,空间是马克思经典理论的当代形态,这种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资本批判当代出场的根本路径。显然,这并没有很好地理解空间的逻辑层次。例如,《论空间生产与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任平,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和《空间生产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庄友刚,学习论坛,2012年第8期)。又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认知范式的理论创新。[3]资本批判空间本体化使马克思资本批判逻辑被空间生产逻辑僭越了,即空间生产逻辑重构了资本批判逻辑。笔者不否认这项工作的理论价值,但概念的逻辑学反思也是必要的。马克思是否“忽视”了空间?马克思在何种维度“忽视”了空间?这要在资本与空间、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这两组概念上进行逻辑学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一般的规定并无“空间原子”,那资本与空间在概念一般层面发生关联?若能,又如何关联?通常认为空间生产与马克思资本批判的理论对接是“空间是社会关系”[4]26。但这恰是问题的根本:马克思为何不把空间视为认知社会关系的中介范畴?空间是否属于资本批判的基本范畴?资本一般是否有空间性质?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是否有区别?
显然如下分析是很重要的:遵循《资本论》逻辑学思路研判空间生产理论本身,劈开纷繁复杂的历史具象,探讨资本与空间、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的逻辑问题,分析其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关系。
二、问题症结:资本、空间的概念解析
资本批判空间本体化的逻辑起点是列斐伏尔对空间的概念规定,这既有资本与空间耦合的可能,也有耦合的必然。马克思论述了资本在自然、社会和精神三个空间维度上的运动,可并未将空间与空间关系纳入资本本质,即在根本上拒绝了资本批判的空间本体化。
(一)资本一般拒绝空间
马克思如此规定资本一般:其一,“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5]130,“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6]611其二,马克思从经济支配权深入到经济生产行为,考察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运动,认为“正是这种运动使价值转化为资本”[6]269即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其三,资本只能是特定的生产关系。[7]345
马克思对资本一般的规定并无“空间原子”。认为资本不断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所以资本和空间必然内在地联系起来,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当然离不开空间,但这一过程的资本已是资本作为资本的现实运动和经验展开的实存。共相存在于殊相、本质存在于现象,但共相不是殊相、本质不是现象。资本本质不是资本本质的外化。马克思认为,作为增殖的资本只能是人类劳动,时间是内涵,强度是外延。《资本论》第1卷讨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时候才出现“空间”:价值—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资本是资产阶级这一特定的生产关系本身。”这个特定的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生产关系。显然,马克思并不打算把这种关系解释为某种空间。
资本的三层规定是递进的,后者是前者的积极否定。马克思发现,在买卖中无法体现资产阶级的经济支配权,便对此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界定:支配无酬劳的经济权力,从而推进了资本的本质层次。虽然资产主义生产关系必须以价值增殖为条件和基础,但资产主义生产关系既不是对价值增殖的外部吸纳,也不是价值增殖的同义反复。所以,资本一般最终指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对资本一般的规定富有历史内涵,却又将历史经验剥离出去。
(二)空间与空间生产的性质规定
空间生产理论赋予空间以社会关系性质,拒绝视之为僵死的、静止的“空的容器”。[4]56“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吗?当然是……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生产。”[8]48列斐伏尔把自然空间当作“第一空间”,认为社会空间是以此为物质基础的“第二空间”,从而将自然空间排除在社会空间之外:随着资本主义的技术征服,自然界的对立面就是生产出的空间。[9]列氏的目的是突出空间的社会性质,但他未将“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核心观点贯彻到底。因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5]130。如果把空间规定为社会关系,那么自然空间也应被纳入其中:在概念一般层面的社会空间包含了作为具体范畴的自然空间和作为具体范畴的社会空间。国内学界试图主动从外部经验“克服”列氏的逻辑矛盾,可惜他们把资本逻辑的经验现象直接等同于资本的空间生产逻辑,却置资本与空间在概念一般层面的关系不理。
顺承“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理路得到,空间生产一般之规定:空间生产就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是社会存在,也就是空间存在。这种关系或这种存在的自我投射就是空间生产的过程。[4]117不同于马克思理解的“生产”概念,空间生产理论认为,生产是社会关系的秩序化和结构化生成,从而空间生产就是社会关系的秩序化、结构化的形塑、扩张和重组,即空间中空间本身的生产。空间生产有三方面内容:首先,“(社会)空间就是(社会)产品”[4]30,那么“空间的生产类似于任何同类商品的生产”[10]34,进而空间既是社会生产资料也是个人消费资料,既是人的存在手段也是生产目的,从而构成社会和个人生命进程的“本体论概念”[11]235。其次,扩张的城市化和社会的都市化。[8]47土地、建筑、城市都成为价值(剩余价值)化、全球化和日常生活的空间秩序化。[9]第三,空间组织和空间结构的变迁。既然空间是社会关系,那么空间组织和空间结构的变迁就是社会关系组织和社会关系结构的变迁。
不难发现,空间生产理论对空间一般概念和空间生产一般概念的规定是不一样的。“由空间中的生产转变为空间的生产乃是源于生产力自身的成长,以及只是在物质生产中的直接介入”[8]47的论述可以佐证,最初把空间规定为社会关系,而在规定空间生产即本应规定为社会关系生产时,却把空间规定为已经外化的具体范畴。这里存在逻辑冲突:空间生产从社会关系本身的生产变为社会关系之物质载体的生产,把空间生产解释为空间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的重构和扩张。如此,不难理解列斐伏尔对空间的规定竟有35种之多。[12]21—22
(三)资本与空间的内在断裂和外部耦合
1.逻辑思辩:资本与空间的内在断裂。虽然“把握资本与空间的内在关联,必须从资本的内在规定出发”[13]是对的,但认为“资本本性决定了资本内在蕴含了空间性质”[13]则值得商榷。这个结构似乎顺理成章: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空间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因此资本一般便有了空间性质,而且资本无限积累和增殖的扩张逻辑必然通过外部空间的侵占、重组、开掘来实现,此为“资本—社会关系—空间”结构。可是,马克思对资本最深层次本质的规定很明确:“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14]922资本并非一般意义的社会关系,资本只是无产者与资产者间的雇佣劳动生产关系。该关系能被称为(社会)空间?显然,“空间—社会关系—资本”的逻辑结构是对资本的物化,具有独特社会性质的空间是资本物化的表现。
赋予空间以社会性质没有问题,承认空间是社会关系的外化表征也没有问题,因为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本原则,但不能据此把社会关系等同于空间,更不可将秩序化、结构化的社会关系等同于空间(再)生产,因为社会关系概念比社会空间概念要内在和本质得多。任何关系的实存都必须借助一定的时空结构,而逻辑学剥离了实存状态的关系的一切外部要素去分析关系本身。剩余劳动本身并不是资本,“资本既可理解为社会关系又可理解为生产资料”的逻辑是混乱的,“空间本身也是资本”[13]中的“资本”是已展开的具体范畴了。空间生产理论在把空间规定为社会关系,又认为“空间是一种生产资料”[8]44,这只是提供了资本批判的一个外部视角,仅在认识方面提供了一种补充。然而,把作为外部范畴的空间塞到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批判的逻辑层面,会遮蔽对资本一般和空间一般的逻辑学分析。
2.经验陈述:资本与空间的外部耦合。外部耦合是指资本与空间在经验中相互关联的现实运动,并且是作为主体的资本去占有、重构、开掘空间以实现自身的历史过程。既然资本一般不含空间元素而资本的空间扩展却是实实在在的,且空间也不直接等同于社会关系而是社会关系的外化表征。那么,二者的关联机制只能发生在实际的经验运动中。在经验运动中,作为概念一般的资本和作为具体范畴的资本二者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呈现出的外化表征(社会空间)二者间的界限亦变得模糊。这时,空间才物化为一种具体的资本。明白此理之后才可讨论空间生产:自然空间如何被资本形塑,全球化如何构建了不平等的地理学景观,等等。马克思资本批判与空间生产的理论对接并不发生在逻辑学中,而是在资本本质的外化运动中。空间生产并无自己的独立逻辑,资本逻辑无须在空间和空间生产中被规定,空间生产不能自我规定,空间生产逻辑只是资本逻辑的衍生物,是资本本质在空间维度上的展开。从剩余价值方面看,逻辑上空间生产并非始于20世纪70年代,而是始于资本运动的“最初”。[15]空间不可能成为剩余价值的来源,但却是相对剩余价值的来源,空间只是剩余价值生产的条件。“用时间消灭空间”是资本循环积累的加速化,是时间无距离的“内爆”。
三、问题延伸: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的逻辑辨析
(一)概念考察: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
1.资本空间化:资本的空间构序。从尚未展开的资本一般出发分裂出空间的任何载具性质可知,资本空间化是资本本质由内而外、由抽象到具体、由一般到特殊的展开自身的历史过程。该过程包含了占有和生产两个方面。在此,空间生产就是资本空间化,是资本依从自身逻辑、根据自身需要对空间的构序。这是资本本质展开自身的“下降”过程。空间绝对地服从资本逻辑,空间化只是表征自己的现实化。“抽象是资本主义自己的杰作。”[16]265。资本通过摧毁和改造非资本化的空间确立其抽象统治,并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断改造和开掘空间。这一切都呈现为资本空间化之丰富的历史具象过程。资本空间化得以经验直观是因为,资本在经历了几百年的空间构序后凸显为庞大的空间实体,成为盛装环裹的空间景观,仿佛空间占据了本体位置。事实上,任何寓于空间形式且担负着资本职能的实体完全可以在另一种社会制度中保留其空间形式而丧失其资本功能。空间和空间生产的社会性质并不依存于空间的某一形式。这说明,空间本身不是资本。
问题是,在本应抽象分析的地方,空间生产理论却给予资本空间化的经验过程以过度重视。这很容易将资本空间化构序过程中的抽象与具体、理性和直观的二重维度混为一谈。因此,资本空间化是资本外化和现实布展的“下降”的构序过程,讨论资本的空间生产就是在分析资本空间化构序过程而已。
2.空间资本化:资本的空间去序。空间资本化是空间转化为资本,成为具体范畴和特殊形态之资本的过程,是资本对空间的历史去序运动,即资本不断剥离空间的具体存在形式和特殊物质载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具体范畴的空间越发不重要,空间是资本一般的外化存在物,自然、社会、精神三维度的空间不存在质的差异而只有量的区别。空间资本化的程度越深,空间就越远离自己的具体形态。可见,空间资本化即资本对空间的历史去序过程是一个“从外到内”、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的逻辑“上升”过程。首先,空间的自然界限被打破,资本的空间去序逐渐消解空间的自然形式,经验上就是资本空间化。其次,资本空间就是资本空间化的产物,因此,这里的空间不是空间本身的生产,而是资本本身的生产。作为资本运动的直接结果,这里的空间终归是资本的具体范畴和特殊形式,它和资本主义的利润、利息、地租没有任何本质区别,虽然其“出生”就带着空间的庞大盛景。由此,在资本对空间的历史去序过程中,无论是“占有”还是“生产”,空间资本化是剥离空间形式直指资本一般的历史运动。并且,按照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层次性规定,空间资本化的两层含义是递进关系,后者包含前者并与前者相区别。
(二)理性狡黠: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的“闭合”逻辑
于资本一般而言,资本正是通过资本空间化这一构序过程完成空间资本化这一去序过程的。在经验上,“下降”与“上升”是同一过程。在逻辑学中,首先是分析的过程,把二者的经验同一性剥离为看上去像逻辑概念的某种先验观念。其次是把逻辑概念在经验中展开,并清醒认知这个展开过程的内在思路也是一个“上升”的逻辑综合。易言之,不应该把资本一般的外化运动理解为黑格尔式的逻辑,因为“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7]111。
一些学者对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概念的考察来源于列斐伏尔的定义:“资本占有空间,并生产出一种空间。”[18]21所谓占有就是资本对一切非资本化的空间进行殖民改造,而生产是空间资本化的重构开掘。观点一[19]: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的历史形式,资本空间化发生在19世纪,空间资本化开始于20世纪。这种阶级性差异产生了现代性话语和后现代性话语的差别。观点二[20]84:二者的区别是资本化和空间化,其对应关系和交叉关系均体现为资本逻辑和空间生产逻辑的双重关系,认为空间化逻辑先于资本化逻辑,在非资本化的空间化逻辑具体化为资本空间生产的时候,空间就进入到资本化的境遇中。观点三[13]:资本空间化是资本运动的空间结构,空间资本化是空间商品的资本属性。不难发现,观点一的核心主张已经被观点二批驳了;观点二比观点三更具宏大的历史视野,且试图将空间生产逻辑独立化和主体化;观点三是在描述经验现象,其实马克思对分析土地、建筑等不动产资本就是对资本外化为具体范畴的分析。
其实,一旦抛开空间本体视角,遵循马克思的资本本体视角分析会发现:首先,空间资本化并不是讨论某种形式的空间被资本占有的经验过程,而是空间在资本空间化的展开过程中脱离自身的空间形式的分析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逻辑抽象的过程,在经验现象中恰恰就是资本空间化的过程。因为空间占有也是一种空间生产方式。其次,在经验上,资本空间化的确包含了空间资本化不具备的历史内容,多重空间的开掘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资本空间运动的过程,但该过程并不是区分空间生产逻辑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变迁的自变量。作为经验上不同于占有形式的生产,空间资本化的“现象显学”只是资本空间化之当代历史构序的经验罢了。最后,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绝非两种并列的历史过程,而是并列的逻辑过程,是经验中的同一历史运动。当然,资本一般外化自身的历史过程必定是阶段性,可外部呈现的不同经验现象并不构成内在的相异逻辑结构。从逻辑二重性看来,资本对空间的历史构序即资本空间化,空间就被占有和生产。同时,这也是空间剥离自身成为资本对空间的去序即空间资本化,空间资本化便是这个过程的逻辑抽象。“下降”与“上升”的二重思辨构成了二者的“闭合”逻辑。
四、问题后果:资本批判空间本体化的后现代魅影
空间生产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批判理论发生的多重理论转向之一,不可避免地受到后现代历史语境的影响。空间生产理论本身只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溢出,是资本运动的具体化。
(一)马克思资本批判逻辑遭遇物化
资本批判空间本体化的后果是,马克思资本批判逻辑被物化了。马克思资本批判逻辑之所以始终围绕着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展开,是因为揭示资产阶级隐蔽剥削的秘密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证资本主义灭亡、共产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最终都根植于无产者与资产者的对立统一关系。很显然,这压根就不是空间或空间生产问题,这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生产关系问题。列斐伏尔、苏贾、哈维等人提出的政治解放纲领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同时,马克思资本批判逻辑的历史唯物主义力度也被弱化了。资本批判的空间本体化本想克服传统批判路径时间偏好,但却用结果追溯原因、用空间压抑时间,把真理的条件性当成真理的具体性,陷入了“空间的超时间化”。他们批评马克思受到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影响,但却不知正是该影响让马克思洞察事物本质,正确区分真理的具体性和条件性,识别共时性空间结构内部的历时性逻辑。所以,“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并把资本主义的空间物化作为批判对象,……却没有空间问题的位置。”[21]这恰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魅力与力量所在。它告诉我们,空间生产理论只是一条历史线索,其本身依然要在历史当中寻求自身的演绎逻辑。因为马克思资本批判逻辑被物化,所以资本批判的空间化才沦为一种意识形态。
(二)资本批判空间本体化的意识形态性质
资本批判空间本体化的另一后果是,批判本身构成了空间拜物教的意识形态景观。在哲学视域中,空间本体化的问题在于,把时间物化为凝固的空间,把以生产关系为内核的社会关系物化为秩序性和结构性的空间,其逻辑预论了现存事物的自然永恒性前提,这是资产阶级理论建构的意识形态偏好。纵观所有剥削阶级的理论结构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认知世界的出发点、方法和结果归根到底都是共时性(空间化)的。福柯指出,在现代科学构造中的那种空间化策略正是资产阶级权力布展和思维规训的基本形式。所以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和其散发出意识形态恶臭时,把自己的科学表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
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历史哲学和辩证法影响的马克思的确对历史时间有所偏好,可是他强调的对历史时间的偏好是强调运动和过程的绝对性,而非突出作为实体的历史时间。这在《哲学的贫困》和《资本论》都已说得很清楚了。若非如此,就不能从根本上瓦解资产阶级理论思路的意识形态规训,不能彻底地批判那种取消历史(时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揭示现代资本的生产方式正是以“时间消灭空间”为基本特征。《资本论》是打破现代资本运动方式被物化(空间化)的最重要的一次理论努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偏好共时性(空间化),而历史唯物主义偏好历时性(时间化),这是马克思资本批判正确性和科学性保证的重要法宝,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解毒剂。这里绝非要抹杀空间生产理论的重要学理价值,而是指出空间理论依然有自己的理论空间。
(三)资本批判空间本体化误认了资本界限
卢森堡认为,没有前资本主义空间,资本主义就要自行崩溃。空间生产理论认为,空间生产拯救了20世纪70年代资本的积累危机,空间让资本得以存续。理论家的反思是有道理的,空间对周期性的资本积累危机而言的确是一种“补救措施”,但也只能是一种“补救措施”。正因为空间是资本运动的外部构成要素,也就在根本上取消了空间对资本来说的界限性质:空间边界作为资本运动的外在界限通过技术被反复打破和重塑是可能的和可行的。作为资本外部构成要素的空间不可能是资本的内在界限。资本的界限只能由资本一般决定,资本的空间运动并不受已有的任何形式的空间限制,因此空间绝无可能构成资本的逻辑界限。
资本界限就是资本在概念一般层面的自我规定和否定,即在黑格尔意义上含有积极规定的否定之双重性质,它只存在于资本一般当中。所以,在马克思具体规定资本界限的四个方面中,[16]396—397都只与价值本身相关系,空间界限并不构成资本界限的内涵。可是,“资本批判的空间本体化”认识不到这个问题,认为资本既有时间界限也有空间界限。这是对资本界限的误认,把逻辑学中资本界限的绝对性错误地等同于在经验中资本运动的实际边界。而在经验中,界限是一种灵活的“度”。资本批判空间本体化试图通过“占有空间”而自行崩溃不可能发生,寄托于诗意和艺术的空间行动更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