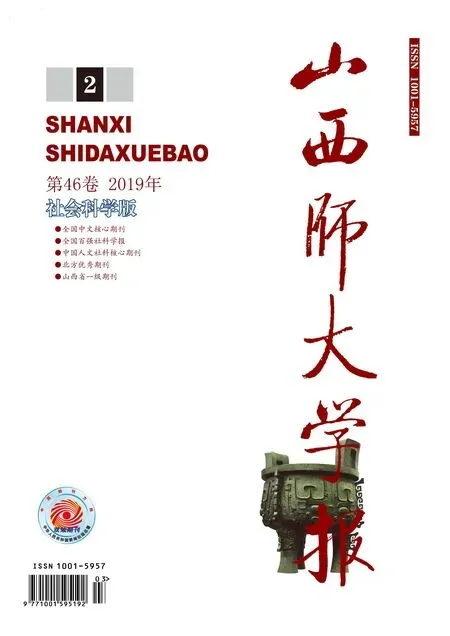晋东南方言非典型人称代词“俺孩”
关 黑 拽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山西方言人称代词很有特点,不仅单数形式、复数标记形式复杂多样,而且在通称形式之外往往还存在一些特殊形式。如宋秀令[1]、乔全生[2]120就曾指出汾阳方言里存在一个特殊的第二人称代词“我儿”,如:
(1) 我儿真亲(可爱)!(转引自宋秀令1992)
(2) 我儿的饭吃啦没啦咧?(同上)
限于研究目的,宋秀令[1]、乔全生[2]120只是简单描述了“我儿”在汾阳方言里的意义和用法,对于“我儿”在其他方言里的分布情况以及历史来源都未能涉及。近期,我们对山西方言进行了更大范围的普查,发现“我儿”的对称用法在山西其他方言里也都有分布,在晋东南地区的方言里,“俺孩”也有与汾阳方言里“我儿”类似的用法。
本文以前期方言调查为基础,集中探讨晋东南方言里“俺孩”的对称用法,尝试结合历史语料探讨山西方言里“俺孩”“我儿”这一类特殊人称代词的历史来源。对这一类非典型人称代词的研究有助于揭示山西方言人称代词的复杂性,也有助于探讨山西方言与汉民族共同语在语法发展上的差异。
一、晋东南方言里“俺孩”的对称用法及其性质
(一)晋东南方言里“俺孩”的对称用法
在笔者的母方言——晋城话里,“俺孩”可以用作对称,在会话交际里称代听话人。当“俺孩”表示对称时,读作[ε213xo51],其中“孩[xo51]”是一个黏着语素,只能出现在表示对称的“俺孩”里。表示对称的“俺孩”已经凝结成词,内部结构紧密,不可扩展,可以自由地充当主、宾语,作定语时需要带上结构助词“的”,如:
(1) 俺孩慢些儿,看跌一跌!
(2) 这是谁给俺孩买的来?
(3) 他打俺孩的圪脑(脑袋)来?
上述三例中的“俺孩”都可以被晋城方言第二人称代词单数的通称形式“你”替换,只是替换后缺少了“俺孩”所具有的亲昵、亲近的感情色彩。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晋城方言里“俺孩”在表示对称的同时,还可以表示他称,只不过随着指代对象的不同,“俺孩”的语音表现以及句法表现也有相应的差异。当“俺孩”表示他称时,音为[ε213xi:o354](严格来说,“[xi:o354]”应是“孩Z”,是亲属称谓词“孩”的Z变韵形式),是一个松散的领属结构,不仅内部可以扩展,“俺”和“孩”也都可以被其他同类成分替换,如:
(4) 俺大孩(我大儿子)、俺二孩(我二儿子)、俺小孩(我小儿子)
(5) 俺闺女、俺爸爸、俺妈、俺爷爷……
(6) 你孩、他孩、咱孩……
除去晋城方言,在一些有晋东南方言背景的作家的作品里也可以看到“俺孩”用作对称的现象,如:
(7) 爸妈叮嘱她:“俺孩到安泽你姑姑家,好好念书,说不定比唱戏还有出息。”(翼城、安泽:王振湖、宋素琴《深山百灵》)
(8) (徐双巧)急忙丢下锄头就向儿子跑去。“柱儿!怎么啦?俺孩这是怎么啦?谁欺负俺孩啦?”(长治:王东满《风流父子》
(9) 财:姐姐你好吧!
冯:俺孩回来了,快坐下吧!(沁源:关守耀、胡玉亭合编《回头看》)
在上述三例对话中,“俺孩”都是用来称代听话人,但说话人与称代对象之间的社会关系并不完全一致,例(7)里父母用“俺孩”称代女儿,例(8)里母亲用“俺孩”称代儿子,例(9)里姐姐用“俺孩”称代弟弟。
此外,在长治市北部的和顺县马坊方言里,“俺孩”也可以指代听话人,[3]如:
(10) 买下油咾,就给俺孩吃烙饼。(买下油之后,就给你吃烙饼。)(转引自宋姝婧,2012)
(二)晋东南方言里“俺孩”的性质
晋东南方言里表示对称的“俺孩”虽然已经凝结成词,其指代功能同通称形式“你”一样,但二者仍存在一些差异。
以晋城方言为例,第二人称代词单数的通称形式“你”只具有单纯的指代功能,而使用“俺孩”在称代对方的同时往往还带有很强的亲昵、亲近的语用意义;其次,通称形式“你”有对应的复数形式——“你家”,而“俺孩”只能称代单个的言谈对象,没有与之对应的复数形式;再次,与通称形式“你”相比,“俺孩”的使用往往有着特定的限制——主要见于父母对子女、成年人对孩子、长辈对晚辈说话的语境。当长辈对晚辈说话时,双方的血缘关系越近、称代对象的年龄越小,“俺孩”的使用越自由;反之,“俺孩”的使用则会受到限制。如老人对自己的孙子、孙女或外孙、外孙女说话时,若对方未成年,则可以很自由地用“俺孩”称代对方;如果对方已经成年,则多用于夸赞、劝诫对方,如:
(11) 他就是个七成儿(指心智不成熟、不懂事),还是俺孩懂话(懂事)!
(12) 俺孩不敢再吸烟了!
当同辈之间会话时,双方的血缘关系越近、年龄差距越大,“俺孩”的使用就越自由;反之,“俺孩”的使用就会受到严格的限制。在其他晋东南方言里,用作对称的“俺孩”往往也有比较严格的使用限制。严格来说,晋东南方言里的“俺孩”虽然可以用于对称,并且已经凝结成词,但是仍不能视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称代词。本文根据陈翠珠[4]对汉语人称代词的分类,将晋东南方言里表示对称的“俺孩”视为非典型人称代词,是通称形式“你”的语用补充式。
宋秀令[1]、乔全生[2]120虽然都将汾阳方言里的“我儿”视为第二人称代词,但根据我们的调查,汾阳方言里的“我儿”在会话中也只能称代单个的听话人,没有与之对应的复数形式;而且“我儿”有着特定的使用范围限制——往往是大人对小孩(包括父母对子女、成年人对自己喜爱的小孩)说话时使用。[1]否则绝对不可以使用。因此,我们也将汾阳方言里的“我儿”视为非典型人称代词。
受各地方言词汇系统差异的影响,晋东南方言里的“俺孩”与汾阳方言的“我儿”虽然构词成分略有差异,但二者在意义、用法、内部结构上都具有很强的平行性,实际上二者也有共同的历史来源。为了行文的方便,下文将“俺孩”“我儿”统称为“我儿”类非典型人称代词。
二、山西方言“我儿”类非典型人称代词的历史来源
山西方言里的非典型人称代词“我儿”“俺孩”异形同构,从历史语料来看,二者的源头是近代汉语史上曾一度出现的非典型人称代词“我儿”。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我儿”用来称代听话人的现象最早见于反映唐五代时期口语面貌的敦煌变文,如:
(13) 瞽叟唤言舜子:“阿耶见后院仓,三二年破碎;我儿若修得仓全,岂不是儿于家了事。”(王重民《敦煌变文集·舜子变》)
此例反映的是舜子后母鼓动舜子父亲设计谋害舜子,其中“我儿”“儿”都是舜子父亲对听话人舜子的称代形式,就指代功能来看,这里的“我儿”“儿”都可以视为一个特殊的对称代词。《舜子变》里就有称谓词“儿”与对称代词“汝”互文的现象,如:
(14) (瞽叟)高声唤言舜子:“阿爷厅前枯井,三二年来无水,汝若淘井出水,不是儿于家了事。”(同上例)
此例中,“汝”与“儿”互文,都是用来指代听话人。与对称代词“汝”相比,“儿”在称代功能之外,还表明了听说双方的社会关系。崔希亮曾指出“儿”“子”“公”“先生”等词在汉语史上不仅具有称代功能,往往还带有社会标记的烙印。[5]而源于称谓名词的“儿”在会话里不仅可以称代听话人,还可以作为听话人的自称形式,[5]但“我儿”只能用作对称。由此可见,与独用的“儿”相比,“我儿”不仅可以指明社会关系、拉近听说双方的心理距离,更有指别、限定的作用。
当然,在汉语史上“我儿”也有表示他称的用法,但其指代对象、整体的结构性质都与表示对称的“我儿”有着明显不同,如:
(15) 后魏高祖名子曰恂、愉、悦、怿。崔光名子曰励、勖、勉。高祖谓光曰:“我儿名旁皆有心,卿儿名旁皆有力。”(《南北朝杂记》)
上例里,“我儿”的指代对象是听说双方以外的他人,指称对象也不限于单个的个体,而是指后魏高祖的四个儿子。此外,“我儿”与“卿儿”对举,进一步显示出表示他称的“我儿”是一个可类推的领属结构。从结构性质以及表达功能来看,称代听话人的“我儿”都可看作是一个特殊的对称代词,只不过其使用范围十分狭窄——往往只见于父母对子女说话的语境。
近代汉语非典型人称代词“我儿”形成的背后有其历史动因。从汉语人称代词发展史来看,人称代词系统先后出现过可以表达谦虚、倨傲、尊敬等语用意义的小类[4],但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类别用来表达亲昵的语用意义,即汉语人称代词系统始终在亲昵意义的表达上存在缺位现象。因此,近代汉语非典型人称代词“我儿”的形成,可以视为汉语人称代词系统亲昵表达缺位的一种补偿手段。非典型人称代词“我儿”在南宋话本、明清小说中都有出现,主要充当主、宾语,也有充当定语的用例,但数量较少,如:
(16) 朱世远真个把那柬帖递与女儿,说:“陈家小官人病体不痊……这四句诗便是他的休书了。我儿也自想终身之事,休得执迷。”(《醒世恒言·陈多寿生死夫妻》)
(17) 衙内见了相公,只得唱个喏。相公道:“教你在书院中读书,如何引惹邻舍妇女来?朝廷得知,只说我纵放你如此!也妨我儿将来仕路!”(《警世通言·卷十九》)
(18) 光蕊便道回家,同妻交拜母亲张氏。张氏道:“恭喜我儿,且又娶亲回来。”(《西游记》,第九回)
三、非典型人称代词“我儿”在共同语和山西方言的非同步发展及其原因
非典型人称代词“我儿”虽然早在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变文就已出现,在明清时期的多种话本小说里也仍有使用,但总体用例数量较少,使用频率不高,如在《施公案》《七侠五义》《说岳全传》《说唐全传》等仿古色彩较浓的公案、历史演义小说中时有出现,而在《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反映清代中晚期北京话的作品里则已经完全不见踪影,在现代汉语普通话的人称代词系统里也未见留存。
虽然近代汉语非典型人称代词“我儿”已经在现代汉语共同语里消失,但在山西方言里还有留存,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由此可见,唐五代时期即已出现的非典型人称代词“我儿”在汉民族共同语与山西方言里呈现出并不同步的发展趋势。这种不同步现象的出现与共同语和山西方言人称代词系统的不同发展趋势有关。
(一)共同语人称代词系统的简化趋势
概括地说,简化是共同语人称代词系统的总体发展趋势。纵观汉语发展史,虽然曾先后出现过一些具有特定语用色彩的非典型人称代词,如“仆”“妾”“奴”“愚”“公”“子”“君”等;[4]但随着汉语的发展演变,这些非典型人称代词在共同语中都逐渐消失,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人称代词系统中也仅剩一个表示尊称的“您”。在简化这一总体趋势的强势影响下,原本以人称代词这类词汇形式表达特定语用意义的手段逐渐让位于能产性更高、使用范围更广的句法组合形式。如“我儿”这一表达亲昵意义的词汇形式就逐渐被其同源异构形式——领属式称呼结构“我的+称谓名词”取代。如:
(19) (俫儿云)爹爹,你写甚么哩?(正末云)我儿也,我写的是借钱的文书。(《元曲选·看钱奴买冤家债主》)
上例中的“我儿”是一个独立的话语成分,它与后面的句子之间没有句法关系,可以带上表示停延的语气词“也”。说话人用它来择定交际对象,引起对方的注意,进而开启一个新的话轮。黎锦熙[6]38把这类话语单位称为“呼位”,目前学界通常称这类话语成分为“称呼语”。[7]
领属式称呼语“我儿”的内部结构比较松散,中间可以加入结构助词“的”以及其他修饰成分,如:
(20) 鸨子上楼来,苦苦劝说:“我的儿,那王三已是往家去了,你还想他怎么!”(《元代话本选集·玉堂春落难逢夫》)
(21) 鸨子说:我的亲儿,王姐夫来了,你不知道么?”玉姐也不语,连问了四五声,只不答应。(《元代话本选集·玉堂春落难逢夫》)
由于内部结构松散,这一结构具有很强的类推性,能产性极高、使用范围极广,因此迅速发展开来,并一直沿用至今,如:
(22) 宝庆倒抽了一口冷气,不过很快又装出了一副笑脸:“我的好四奶奶,您要我预支?咱们不都一样是难民吗?”(老舍《鼓书艺人》)
(二)山西方言人称代词系统的开放性
与共同语人称代词系统总体呈现简化的趋势不同,山西方言的人称代词系统相对开放,在通称形式之外,往往还有一些可以表示特定语用意义的语用补充式。如山阴方言里第一人称代词单数形式既有通称形式“我”,还有带有俏皮、亲热意义的特殊形式“佤”。[8]116因此,侯精一、温端政就曾指出,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和表述意义的细腻性是山西方言人称代词的一大特色。[8]115
山西方言人称代词系统对亲昵、尊敬等语用意义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这为近代汉语非典型人称代词“我儿”在山西方言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土壤。其实,从跨语言的角度来看,山西方言人称代词系统相对开放的特点并不罕见。如崔希亮就曾指出越南语中有两套人称系统:一套是真人称代词(通称,越南语固有的人称代词);一套是准人称代词(用称,使用亲属称谓或其他名词,有独立的也有组合的)。在实际的会话交际中,真人称代词的使用频率并不高,人们总是根据交际双方的长幼、尊卑、亲疏、上下、男女等关系来选择不同的代词形式,很少使用通称形式。[5]
此外,山西方言丰富的语法变读手段[9]也为“我儿”类非典型人称代词的存在提供了有利条件。如晋城方言的“俺孩”在表示对称和他称时,语音形式差异十分明显,当地人可以自如地区分、使用,不会发生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