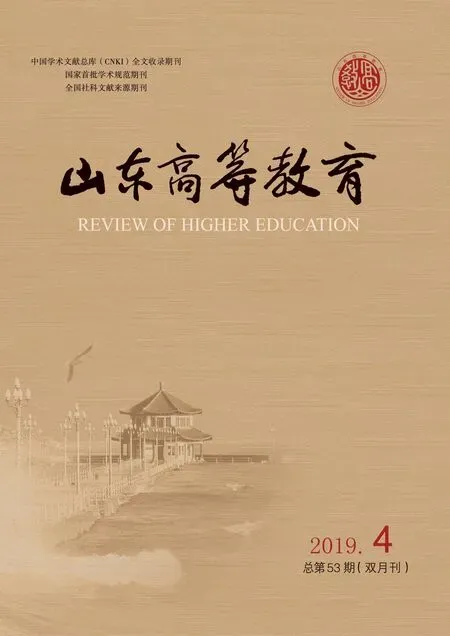赫士与山东近代高等教育
李 涛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100875)
赫士(Watson Mcmillen Hayes 1857—1944)是近代美国著名的来华传教士和教育家,自1882年来到中国,协助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经营登州文会馆,应袁世凯邀请,参与创办了山东大学堂,在晚年创办了华北神学院,推动宗教教育。赫士为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迄今为止,对赫士的专门研究还很少,本文拟就赫士对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贡献做一略述。
一、关于狄考文与赫士的研究
1864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受美国北长老会派遣,来到中国山东登州传教,他先是创建了登州蒙养学堂,随后于1877年更名为登州文会馆,开始提供高等教育。在他的潜心经营下,登州文会馆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为清末民初山东乃至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7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师资队伍、教学仪器设备等多方面都走在当时的基督教学校的前列,培养出了一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急需的人才,在教育、实业、文字出版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弥足珍贵的火种,为山东乃至中国的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狄考文及其创办的登州文会馆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以狄考文文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有:1989年北京师范大学史静寰的博士论文《登州文会馆与燕京大学: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活动研究》是国内第一篇以狄考文为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其后,以狄考文及其登州文会馆为研究的学位论文逐渐增多,主要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祝捷2017年以《狄考文《形学备旨》和《代数备旨》研究》的博士论文、内蒙古师范大学郭建福2018年以《登州文会馆物理实验研究》为题的博士论文,以及清华大学胡凯基2006年的硕士论文《狄考文在华活动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崔华杰2009年的硕士论文《狄考文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李木谢子2011年的硕士论文《狄考文的汉语教学》、河北大学王蒙2013年的硕士论文《狄考文教育活动及思想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刘艳妮2014年的硕士论文《西方人眼里的中国神——以狄考文为例》、青岛大学赵展2009年的硕士论文《登州文会馆研究》、以狄考文所编撰的《官话类编》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等共计19篇硕士论文。
在期刊论文方面,通过检索中国知网可以发现,以“狄考文”为篇名的文章有14篇。如以“狄考文”为主题来进行搜索,可以发现有58篇期刊论文。
200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关志远等翻译、费舍(Daniel W.Fisher)于1911年威斯敏斯特出版社出版的《狄考文传:一个在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一书。费舍是狄考文在大学和神学院的同学,两人长期通信。狄考文去世后,他阅读了大量的狄考文生前的日记和各类信函,用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该书,作为对狄考文的永久纪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2012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山东师范大学郭大松教授编译的《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收集了1891年上海美华书馆出版的《登郡文会馆要览》及《登郡文会馆典章》以及1913年由山东潍县广文学校印刷所刊印的登州文会馆毕业生王元德、刘玉峰著的《文会馆志》,保存了一大批难得的文会馆的文献,为后人研究登州文会馆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提供了一手资料。
赫士自1882年来到中国后,就一直协助狄考经营登州文会馆,直到1908年狄考文去世为止,赫士都是狄考文的亲密伙伴。与目前对狄考文的诸多丰富研究相比,对同样为山东乃至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赫士的研究就实在太少,并没有一本专门研究赫士的专著或传记,实属遗憾。目前能查到的期刊论文仅有内蒙古师范大学郭建福和郭世荣共同撰写的《赫士的科学与信仰——一位在华62年的美国传教士》及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姚西伊的《传教士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嬗变:以赫士(Watson Hayes))为例》。在专著方面,目前所见,仅有山东滕州一中教师赵曰北编著的《历史光影中的华北神学院》记录了赫士对于华北神学院的贡献。
二、赫士对山东近代高等教育的贡献
(一)协助狄考文经营登州文会馆,建成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
近代美国著名来华传教士教育家狄考文1864年来到山东登州传教,并于同年创办了登州蒙养学堂,经过狄考文夫妇的苦心经营,到1877年有了第一批三名毕业生,1881年,狄考文向美国北长老会差会部提出申请,要求将登州文会馆扩建为大学。“长老会本部同意了这一要求,并派赫士和赫士夫人来登州工作。大批良好的物理和化学设备,以及一架很好的天文望远镜也装船运出”。[2]31登州文会馆在长达四十年的办学历程中,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材建设、师资队伍、教学仪器设备等方面取得的成就都是当时的基督教学校和中国传统书院所难以企及的,诸多毕业生为当时的新式学校如圣约翰书院、京师大学堂、山东大学堂等急需的西学教习,被学者郭大松称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1]前言7在这其中,赫士作为狄考文的重要助手,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
1882年,赫士夫妇来到山东登州,加入登州文会馆,协助狄考文的办学与传教事业。赫士来到登州文会馆后,先学习中文11个月,随后就开始在登州文会馆担任多门课程的授课任务。主要讲授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和数学。狄考文认为教育工作是在中国推进基督教事业的最有效的工具,而科学和技术则可以帮助中国人打开眼界、摆脱迷信,他重视教育,主张教会学校提供的教育应当是对人的心灵和性格产生深远影响的全面教育,全面教育将使受教育者成为能干的福音布道者,而这样的全面教育必须以中国语言来授课,使受教育者能在本国人民群众中取得学术声望。赫士赞同和支持狄考文这样的教育理念和原则,他很快变成狄考文的重要助手。除了繁重的教学和传道等任务外,他还与狄考文一起自己动手制造各种教学实验仪器设备。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刘玉峰和王元德在《文会馆志》书中称赞赫士“富有思力,足有智谋,博学强识,狄公依之如左右手,一八九五年受监督任,诸生畏之,鲜不率法”[1]89赫士在登州文会馆从事教学工作18年,是狄考文最重要的合作伙伴。《狄考文传》一书的作者费舍在评价赫士与狄考文的关系时认为,“在传教事业中没有任何一个同事能像他那样让狄考文博士充满信任,多少年他们一直互相往来,互相了解也最深”。[3]213
1888年后,狄考文经常离开登州去上海北京等地参加编书等活动,赫士的教学和管理工作更为繁忙。1895年,他接替狄考文担任了登州文会馆的第二任馆主,直到1901年为止,都一直全面负责登州文会馆的各项工作。赫士任职期间,尽心尽责,成效显著,得到了狄考文的高度评价,狄考文在写给美国北长老会差会部的信中说“学校的领导及主要日常工作都是赫士博士负责,让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学校的命运掌握在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手里”。[3]134
从1882年来到山东加入登州文会馆到1901年离开登州文会馆,将近20年间,赫士先作为狄考文的助手和登州文会馆的教员,后作为登州文会馆的馆主,为登州文会馆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后人永记。
(二)编撰科学教科书,推动中国近代科学教育发展
登州文会馆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大学,所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缺乏合适的教材,尤其是涉及西方科学知识的教材,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满足教学需要,赫士一边教学,一边开始编撰相关科学著述。赫士先后翻译和创作了《天文揭要》《光学揭要》《声学揭要》《热学揭要》等现代科学著作二十多种,许多内容开中国现代科学教育的先河,推动了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发展。
其中,《天文揭要》一书,是赫士根据当时西方较为普及的天文学教材《A Treatise Astronomy》进行整合加工编写的,逻辑严谨、内容简洁易懂,更适合中国学生使用。该书的主要内容上卷包括地球、天文器、视差、岁差、日蚀、月蚀等内容,下卷包括求各地经度的七种方法、潮汐、行星、彗星、恒星、流星、星团等内容。从这些内容看,其天文教育的内容已经非常接近当时的世界最新天文学知识。作为一本先进的天文学教材,该书改变了中国当时的天文认识,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结合,为登州文会馆的天文学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登州文会馆的天文教育培养出了王锡恩、程庭芳、苗永宽等著名的天文学家,对中国早期的天文学形成了一个良好开端,为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4]49
《光学揭要》是赫士根据法国物理学家迦诺的《初等物理学》的英译版第十四版第七章改编而来,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对原著做了删减,内容详实,便于教学。该书开启了我国光学揭要专业实验仪器的时代,无论是学生实验还是演示实验,书中有明确的实验目的、实验仪器、实验过程和实验结论的,就有五十多个。书中还详细介绍了各种显微镜、望远镜、映画镜、尼可镜、投影仪和照相机等实用性很强的光学仪器,书中介绍的“映画镜”是电影最初的原始形式,对后来我国电影事业和电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当时登州文会馆拥有大量物理化学仪器设备,实验仪器设备和教材是配套的,极大地提高了教学质量。[5]
此外,赫士在1890年前后还创办了山东第一份中文报纸《山东时报》,创办了山东乡村邮政,举办了山东第一次篮球比赛,这些都对推动山东乃至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相应贡献。
(三)参与创建山东大学堂,成为山东第一所官办大学,并为中国晚清各省立大学的创办提供样板
山东大学堂是清末新政的产物。经历了戊戌变法的失败以及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战争、辛丑条约的签订等一系列的打击,清政府被迫开始实行新政。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兴办学堂。1901年9月14日(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日)清廷发布上谕:“除京师大学堂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6]5当时在山东主政的巡抚袁世凯,由于之前在登州驻防时就亲临登州文会馆实地参访,考察过学校的现代实验室,与狄考文私交很好,对登州文会馆的办学成就印象非常深刻,还雇佣了狄考文的一位学生到军营任职,并培训军械所的技师。袁世凯在接到清廷的上谕后,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在其他各省还处于观望时,他首先想到了可以参照登州文会馆的成功的办学经验来创办山东大学堂。
在袁世凯的邀请下,赫士率领文会馆自己培养的本校师资张丰年、仲伟仪、王锡恩、王执中、罗绳引及刘光照6人,毕业生刘永锡、郭中印、李星奎、冯志谦、刘玉峰及连警斋6人,当年应届毕业生王振祥和赵策安2人,以及西学教习赫士夫人赫美吉、富知弥、文约翰、卫礼大美籍教习4人共20多人一同来到济南,参与创办山东大学堂。[7]20在带来的人员中,还包括了文会馆的优秀毕业生丁立璜,丁立璜创办了山东理化器械制造所,专门生产教学仪器,既满足山东大学堂的教学需要,也供应全国学校。在赫士的直接参与下,参照登州文会馆的办学经验,拟定了《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1901年11月6日,袁世凯将办学章程连同在省城设立大学堂的奏折《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一同上报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很快批复同意。在上报的奏折中,袁世凯特意提到了赫士,说他“在登州办理文会馆多年,物望素孚,实堪胜任”。[8]340
由于有登州文会馆多年办学的成功经验,山东大学堂采用登州文会馆的课本、教材及教学仪器设备,沿用登州文会馆的办学方法、条规,参照文会馆办学的各项经费开支及预算,只用了一个月,便于济南的泺源书院旧址正式开学,全国最早的省办山东大学堂宣告成立。[7]21袁世凯在朝廷书院改学堂的上谕颁发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在山东建立了山东大学堂,让清廷非常满意。因为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所新式官办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因义和团运动关门停课,袁世凯在全国率先树起新式教育的标杆,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为此,清廷嘉奖了袁世凯和赫士。同时发布上谕,要求各地“立即仿照举办,毋许宕延”。赫士还被邀请为全国设计一套现代教育体系,他的很多建议被纳人晚清的教育改革之中。其中,他的方案中规定星期日在所有官办学校中为法定假日,这是我国正式采用星期日休息制度的开始。
崔华杰在《登州文会馆与山东大学堂学缘述论》一文中,详细比较了“登郡文会馆典章”与山东“大学堂章程”后,认为,山东大学堂在在办学宗旨、教学管理体制、学生招收与培养、课程体系设置等多方面都对登州文会馆进行了直接的“体制移植”正是以赫士为首的教学团队,大学堂才得以文会馆的办学实践为蓝本,制定学堂条规,厘定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短短一个月便正式开堂授课。[9]张美在《登州文会馆与山东教育近代化》一文中在详细比较了山东大学堂与登州文会馆的正斋西学课程设置后认为,这两所学校雷同的课程达12种之多。另外,还有一些课程名称虽然不同,但内容应该是大致相似的。登州文会馆对山东大学堂的课程设置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山东大学堂作为山东近代教育起步的标志,直接启动了山东高等教育的近代化进程。[10]
山东大学堂的成立,对推进、普及全国学堂的成立,起了倡导和示范作用,全国各地纷纷仿效山东办学的经验,争相聘请登州文会馆毕业的学生为教习,因各省办学所需师资太多,文会馆毕业学生有限,后来连文会馆肄业的学生都被聘去。以文会馆毕业和肄业的学生为主力,协助创办了全国各省的大学,对我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贡献很大。山东大学堂的成立,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的。[11]而这份功劳里,作为西学总教习的赫士,自然是当之无愧。赫士在山东大学堂担任西学总教习的时间不到两年,但为山东大学堂奠定了现代大学教育的基础。赫士离开山东大学堂后,他从登州文会馆带去的中国教习,多数仍然继续留下任教,成为山东大学堂的骨干。
遗憾的是,在由山东大学官方主编的《山东大学百年史》一书中,对赫士参与创办山东大学堂一事,仅有“聘请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即现在的教务长)”[6]6短短的一句话,既没有对赫士在山东大学堂创办中的贡献做出评价和肯定,也没有对山东大学堂在课程设置、管理制度、学生培养等方面对登州文会馆的渊源延续,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四)创办华北神学院,推动中国的基督教宗教教育
对华传播基督教是包括狄考文在内的来华传教士的最终目的,狄考文创办的登州文会馆毕业生里,就有不少人从事传教工作。文会馆毕业生的第一选择通常是作教牧,其次是教育,再其次才是从政或从事工商业。毕业生中产生出不少教会领袖,如1892年毕业于登州文会馆的丁立美牧师,布道大有能力,有“知识分子使徒”和“中国慕迪”等美誉,开创了中华学生立志传道团,是山东基督教自立会创始人之一,1923年至1932年期间也在华北神学院任教。在华人教会神学界影响深远的贾玉铭牧师就是1901年毕业于登州文会馆,是中国基督教福音派的著名神学家、神学教育家、解经家,出任过很多神学院、灵修院的教授跟院长,曾任中国基督教长老总会会长,是唯一在国际上被誉为“神学泰斗”的中国基督教神学界人士。赫士创办华北神学院后,贾玉铭牧师被聘为该院教授,并担任副院长。由狄考文弟弟狄乐播和狄考文继室夫人狄文爱德为秉承狄考文的遗志而创办的滕县新民学校是一所培养初级教会人才的学校,其校长刘廉卿就是登州文会馆1902年的毕业生。
赫士与狄考文共事多年,1904年狄考文随着登州文会馆合并迁到潍县组成广文大学,赫士与晚年的狄考文有了更多接触,狄考文在生命的最后三年里,深有感触地说“中国目前最主要的事情我认为是兴办学校和培养一批教师和传教士——这要比花费巨额资金建立新的传教点技巧配套的昂贵建筑物以覆盖广大的区域重要得多”,同时,狄考文对自由主义神仙的蔓延深感忧虑,担心“伴随着英语而到来的书籍和报纸,为不可知论、怀疑论和唯理论等等播下种子,问题是,谁将是真理最后的捍卫者?谁将维护基督教教义?谁又来证明主耶稣基督?”[3]203狄考文的忧虑和追问,无疑深深影响着赫士。
离开山东大学堂以后,赫士被青州共和神道学堂聘为总教习,为适应宗教神学教育的要求,他潜心研究基督教义理,著书立说,编写了《诸教参考》《耶稣实录讲义《教会历史》《信道揭要》等专著,在学界教界产生非常大的影响。1907年,赫士在山东潍县创办女子神学院,1917年该校合并到济南的齐鲁大学神学院,1919年,赫士由于无法忍受自由主义神学思想的蔓延,及“因与齐鲁神科管理及道旨意见不同,长老会学员情愿退出教员亦分离,同到潍县,另立神学”,[12]21退出了齐鲁大学,带领齐鲁大学神学班的部分成员,在山东潍县创办了山东神学院。1922年,山东神学院迁到山东滕县办学,始称华北神学院。在赫士的卓越领导下,华北神学院的各项事务进展很快,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华北神学院就一直扮演着中国基要主义大本营的角色,长期保持中国最大神学院的首要地位,主要是赫士为代表的教授们坚持信仰纯正,大江南北乃至朝鲜、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地,慕名前来求学问道者络绎不绝。1952年8月,华东区神学教育座谈会决定11家神学院校(包括华北神学院)联合,于1952年11月1日成立了金陵协合神学院,华北神学院到此结束。在华北神学院33年的办学历史中,培养了大约一千多名信仰纯正的毕业生,为中国教会输送了最早几代的基层教牧人员,不少人成为当地教会的领袖,为各地教会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信仰、组织和人事基础。[12]158
三、结论
从1882年踏上山东的土地进入登州文会馆,到1944年病逝于山东潍县日军集中营,赫士在山东的62年间一直致力于山东的文化、教育、宗教事业,可以说他把自己的毕业都奉献给了山东这片异国他乡。作为一名虔诚的传教士,赫士来华的最主要目的是服从和服务于传播基督教这一目的。为此,在中国的前半部分时间里,无论是协助狄考文经营登州文会馆还是参与创办山东大学堂,以及编译诸多科学著作,他主要是作为一名教育家,体现了作为一名传教士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为现代文明拓荒撒种的历史作用。当世俗的教育及现代主义的基督教与他的传统传教发生冲突时,他是坚定地站在传教的立场上,尤其是他作为一名基本要义派的传教士,在他看来,基督信仰在本质上不是文化,传教事业的核心是拯救灵魂,不是帮助哪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基督教教育的惟一目的就是传扬维护福音的真理,其他一切世俗性的知识都必须紧密地服务和配合这个核心目标。他们也不绝对反对把文教工作作为传福音的辅助。但是,一旦对这种辅助性工作的投入开始冲击到传福音任务,他们便无法忍受了。赫士的转变恰恰反映了保守派的这种心态,以及他们与在中国现代化事业关系的微妙改变。[13]484-500为此在1903年他因为拒绝崇拜皇帝和孔子而退出山东大学堂,1917年因为与其他教派的理念冲突而退出齐鲁大学神学院。在中国的后半段时间里,赫士的主要精力已经从世俗教育中抽身而出,完全致力于宗教神学教育。他坚信神学教育是反击现代自由主义神学派的最佳手段,主张与其与现代派进行无休止的论战,“更聪明的办法是尽量办好教学,培养出比现代派学校最好的毕业生更好的传道人、牧师和福音工人”。[13]其在齐鲁大学神学院和华北神学院的办学历程中日益明显的基要派倾向为他贏得了名声,成为基督教基本要义派的在华代表。
无心插柳柳成荫。虽然赫士的出发点是在华传播基督教,但不可否认,赫士在中国的漫长岁月里,以其虔诚的热心,为山东乃至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推动了中国传统社会加速接纳现代文明的进程,是值得后人肯定和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