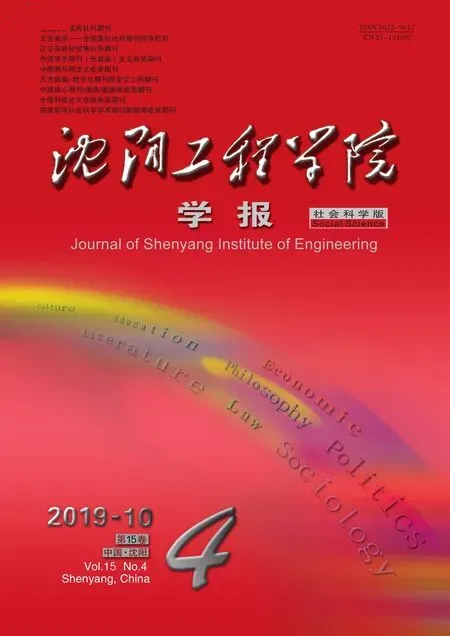李仲元格律诗中的“韵”与“势”
轩小杨
(沈阳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辽宁 沈阳 110011)
就格律诗而言,因其在字数、韵脚、声调、对仗等多方面都有许多规约,这便自然限定了该文体无论抒情还是言志都不易达成汪洋恣肆之势,然而,正是这诸多的审美规范,成就了格律诗总体上平和而隽永的审美特点。如果说,在中国古代(有唐以来)格律诗是文人雅士借以表意达情的主要艺术形式之一,它所言说的也多是古代仕子温良敦厚之情怀,往往在托物寓情、言外之致里寄寓人生感慨。而在当代,格律诗的韵致、雅趣,也吸引一众文人,或咏物抒怀,借以消解世事的烦扰,或寄情于山水,记录下心灵的游历,于喧嚣浮躁的生活中留有一方心灵圣地。与古代文人的格律诗有所不同,当代人抒写的格律诗大多会呈现新时代的意趣,这不仅仅体现在诗歌内容的时代感,尤其在诗的语言、章法、结构等形式方面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在整体风格上由“韵”的铺展而致“势”的激荡,从以往更重视声韵节律的和缓有致到如今情绪意蕴的进一步张扬,便是其中较显明的一种审美拓展。李仲元的格律诗即有此趣向。
“韵”,在汉语字典中有三解:汉语字音中声母以外的部分;和谐而有节奏的;风度、情趣、意味。这里将其与“势”对举,主要取“和谐而有节奏的”之义。如果用视觉感受作比喻,“韵”有如平缓的波浪线,在变化与统一中延展开来,无变化的直线、有变化但生硬且无规则的踞齿线都不构成“韵”。那如波流动之韵,似可作为格律诗平和淡远之风格写照。
“势”不同于“韵”。两者虽都具动态,但“韵”是平缓,在重复的律动中往往呈现静的境界。“势”则带有速度与力量,它不是碧水微澜,漫卷涟漪,而是浪谷波峰,涛浪滚滚;不是渐行渐远,余味曲包,而是蓄积起前进的动能,撼动心弦。
在李仲元的诗作中,这带着速度与力量的“势”让他的格律诗尤具魅力。
一、诗句结构的“动势”
这里所说的“动势”首先意谓动感。这种动感首先与诗词格律有关——声调平仄的转换便是一种有规则的律动,这正是格律诗的妙处所在。但李仲元的诗不限于此,其动感幅度更大、力度更强而形成为动势。这主要表现在诗人对动词的运用上。在他的诗句中,常以动词起句,并在一句之中通过对动词间隔性地连用,即在声调平仄转换处使用动词,有如音乐行进般,起拍(平仄转换处)必为强拍(动词),并且以这种音乐节奏的强-弱(动宾结构)律动,带动声调的平仄律动——如以强弱、强弱、强弱弱,将仄仄、平平、仄仄、平调整为仄仄、平平、仄仄平,显然后者更具力度与速度感,这就使格律诗自身的平仄韵律得以加强。这个特点在他的七言律诗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班超》的首句“宣威抚远战孤寒”,以动词起句,掷地有声,紧随其后是两个动宾结构,合力承起全句,如波涛汹涌扑面而来。再如《卫青》首句“立郡收疆入壮图”,因有“立”“收”“入”三个动词的开启与连续,树立起武将卫青强悍有力的形象,至于诗句是否合于平仄关系倒显得不那么要紧了。这种以动词起句并间隔地连用的方法,在书写英雄武功时颇有气势,也在美誉文治时显得不同凡响。如《韩非》中的“哲天慧地迈群贤”,“哲”“慧”虽本身为名词性,但这里作动词用,与独领风骚之“迈”连动,合力张扬一代俊杰指点江山、气贯古今的视野胸襟。《张道陵》中的“创道离儒称五斗”之“创”“离”,精道地表征张道陵创立学派的开山之功,虽然“称”的力量稍显弱许,主体身份亦显模糊,但有前两个动词的分量,读来亦有气势扑面。此外,《李冰》中的“离堆分水汶江开”、《伯牙》“舞鹤停云妙曲奇”、《列御寇》“继老归庄大道玄”,亦是如此。但这几首(句)因少了一动,诗句的动势便减弱了些。
从上述例举不难看出,李仲元格律诗中的势,端赖以动词起句及其在句中的连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动势大多出现在咏史诗中,这动势让咏史少了古涩与杳渺,多了生动与鲜活,也让诗人笔下的人物更加形象和立体。
就动词在格律诗中起势、造势的作用,我们不妨再以几首诗对比来说。
先以这首写景的七言绝句为例:“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里每句都有一个动词,首联的“鸣”、颔联的“上”极为生动形象,让多彩的画面动了起来;颈联的“含”、尾联的“泊”二字则准确地道出了窗外雪、门前船的状态。但“含”与“泊”虽为动词但展现的是静的景,而“鸣”与“上”虽写动态景观,但却如微风徐徐的吹动、波纹缓缓的舒展般,因其平缓而生成静的意境,因而整首诗带来的是风和日丽、心绪宁静之美感。再以一首抒情的七言绝句为例:“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虽每句有两个动词,但不是有规律(与平仄关系对应)、高频次(七字三动)地出现,其动势便是弱化了的,但这种弱化恰营造了漂泊半生后回到故土时的那种温馨、宁静、安适的情境。再以一首咏史诗为例,杜牧《赤壁》首句“折戟沉沙铁未消”,便用了三个动词,有一定的分量,但第三个动词没在强拍(平仄转换处)上,力度便弱了少许。再看李仲元的“宣威抚远战孤寒”,全然是强(动词)弱、强(动词)弱、强(动词)弱弱的音乐节奏,在动态及气势上更胜一筹。上述可见,在格律诗中动词的位置、数量对于成就作品的总体风格是有一定作用的,而李仲元先生是深得动词之妙用的。
综上,如果说“韵”如同小桥流水人家,“势”则如古道西风瘦马,两者风格迥然,前者妙在趣味雅致漫妙,后者在其意气激荡雄阔。李仲元格律诗中的七言咏史诗更倾向于后者。
二、正言直述的“情势”
王向峰先生将《缘斋诗稿续集》题材概括为“三人咏”——“咏史尊贤颂古人、遍选良俊赞友人、励志抒情见本人”,并肯定诗集“在诗章构结与文辞运用上求文雅而不陷于古奥”。若从诗集言志抒情的特点上看,又似可概括为多正言直述而少含蓄委婉。这一特点在他的自述诗中表现得最明显,诗中大多洋溢着“笑傲江湖”般的情势气魄。
诗人吟咏自我时喜用“笑”字,且大都是以动词词性出现,在描画夜吟得句、游历踏青、清斋闲坐等日常画面时“笑”字往往应声而出。比如“日作六朝龙爪书,夜吟得句笑胡卢”“今朝殊快意,一笑到仙都”“游人最解寻幽趣,笑纳清凉坐玉峰”“年年最是迎春日,笑坐清斋伴水仙”“白头竞是君休笑,好撞青云不老钟”“今年吟罢掀髯笑,八十衰翁老未痴”,无论是佳句天成的欣然喜态,还是游居山水的春风笑颜,抑或时光流逝的笑以面对,诗人都是直抒胸臆,快意畅达。
诗中“醉”字也是常有,如“幸是升平叟,屠苏醉一觥”“年年饯岁醉联吟,今夜流霞苦自斟”“今日又逢文老会,七仙岭上醉瑶池”“老夫醉遍人间酒,只待吴刚酿桂花”“寒香醉染衣,诗咏梅花瘦”,无论是醉美时光还是酒逢知己,如此醉意朦胧的诗句,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所言的“李白一斗诗百篇”“张旭三杯草圣传”,并进而联想到李白诗句的浪漫潇洒、张旭草书的飞扬灵动和那从中喷薄而出令人心动的激情。虽然李仲元先生不似李白那样豪放不羁,更不会同张旭般痴狂疯癫,但其诗中的“醉”,一方面让我们感受到诗人潇洒快意的生命姿态,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感受到诗人真情真性的自然流露,读来俊爽酣畅。
这种抒情言志方式,与“比兴”传统大异其趣。“比兴”讲求“借外物、景物而抒发、寄托、表现、传达情感和观念”,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种托物寓情、“不道破一句”,一直是中国传统美学重要标准之一。比如李白的《夜泊牛渚怀古》:“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诗人写景、怀古、抒情,其对世无知音的深沉感喟却是含而不露,不道破说尽。清代王士禛赞其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典型,认为“诗至于此,色相俱空,正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画家所谓逸品是也”(《带经堂诗话》)。
而上述《缘斋诗稿续集》中意态丰盈、“正言直述”的诗句,更接近于中国传统美学中另一审美原则“赋”。
关于赋与比兴,朱熹这样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李泽厚在其《美的历程》中曾对此作过分析,认为如果从中国文学的源头上说,《诗经·国风》呈现的是“比兴”的审美趣味,先秦散文在某种特定意义上,则可以说体现了“赋”的趣向。前者以抒情胜,后者以说理胜,但后者虽为说理,因其“说理论证的风格气势”而成为审美对象,更因“充满了丰富饱满的情感和想象”,而与中国诗歌的民族美学特征一脉相通。
从审美感受看,“托物寓情”一般含蓄委婉,言近旨远;“正言直述”则酣畅淋漓,更情势夺人。在审美天地里,两者交相辉映、互为补充。但纵观中国美学史,平和淡远的审美品格一直以来处于主导地位,甚至成为民族性格、文化品格的典型特征。而“正言直述”无论是在对作诗还是对作人的审美判断中往往被忽视以致轻视,更不必说在格律诗这一文体中的地位了,史上佳作亦远不及前者。令人欣喜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审美目光也在发生改变,一如《缘斋吟稿续集》中那些率性挥洒的诗篇。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诗集中洋溢的“正言直述”之情势,固然与诗人自身的趣味、性情、修养相关,但与诗人所处之时代同样不无关联。尽管古今文人大都喜于游居于山水,陶醉于笔墨,忘我于华年,但与冷峻时代的文人不同,如今的诗人是“笑写春联换酒钱,万泉河畔一陶然”,“贤愚真幻同今古,笑向逍遥游此身”,内心的自信自足,生活的温暖安适,溢于言表,这是当年寒苦之中的庄、陶所不可比拟的。
三、内在生命的“气势”
邓荫柯先生这样描述李仲元先生的外貌:“仲元先生年过八旬,依然身姿英挺,长发飘拂,目光清澈,好一副玉树临风的姿影。”“他笔下的如珍珠璧玉般美丽的诗词作品则出自他善良美好的天性。”是的,品读诗集,清丽俊雅朗健的诗风扑面而来。诗人明朗豁达的自我吟咏,最能体现其内心深处的从容淡泊,不为俗务缠身的超越与洒脱。他的颂赞友人的诗篇,又可令人联想日常生活中诗人如何以一位“诚挚君子的文化生态面貌和朋友交流”。这一切都让我们感受到,诗人守持着生命原初的清正之气,于喧嚣浮躁的世事之中,留下一道清新美好的风景。
在诗集中占有较大比重的“稽古尊贤”诗作,却能体现李仲元先生钩沉历史的非凡气势。诗集中共收录近年所作200余首咏史诗,其中,既有远古时代的女娲、轩辕、神农、蚩尤,也有传说中的共工、夸父、精卫、嫦娥。进入有文字记录的时代后,则有孔子、老子、左丘明、庄周、商殃、屈原、韩非等一众有着重要历史价值的文化巨匠,所写人物之多,所涉故实之广,见解之深邃,视角之独到,提炼之精要,足见其史学功底。纵横捭阖、以史为鉴,自会有其不同于常人的打量世界的独到目光。或许基于此,才有其咏史诗中那充满力量与速度的“动势”,才有吟咏自我与友人诗篇中那把整个心灵呈现给世界的“情势”。
这内在生命的气势,在诗句的语气上最有体现。如《不眠夜作》:“今我怡然如老鹤,钦清啄料羡阿谁!”真可谓气势了得!一个虚词“阿”的介入,拉长了语调,加强了语气,蓄足了气势,如同京剧舞台上花脸亦或老生的雄傲神态立于眼前,神气活现,叹为观止。虚词妙用,在语气上达到推波助澜的效果,而助动词也起到推动、渲染的作用。如《欧冶子》尾联“尽是穿盔裂甲兵”的“尽是”,不仅写出了战场的情状,也带出诗者内心的情态,对于残忍战争的由衷慨叹溢于纸面。再如《嫦娥》的“俯瞰寰尘万象真,由他圆缺惜冰身”之“由他”的率性洒脱、《精卫》的“纵使滔滔填不尽,痴心聊可慰悲情”之“纵使”的深沉极致,而《大禹》中“大统焉能禅让人”的“焉能”,王道之尊与凌云之势如形表出。此外,诗人常以设问句式,揿起辞章结构的气势。如“神仙洞府谁曾见?菩萨门庭我已通”“数典华人谁忘祖?神洲一脉五千年”,这种结构上的动势,读来亦是心旌摇荡,生出如虹美感。
对于李仲元先生不落尘滓、清雅洒脱、气宇不凡的生命姿态,邓荫柯先生将之首先归为家学的影响,“是仲元先生的父母对他的关爱、教诲、熏陶太美好太精彩太细致了”,另一方面归于后天修为,赞其“作为盛世士子,他有担当有责任有义务”,以一名“俗世君子的风度和风采呈现在世人和朋友面前”,以及“在人情日益浇薄的时代,葆有关东乡亲的淳朴情怀”。如此,成就其不凡的精神气质,而其人的自信自足势必成就其文的气势气度。由此,他的咏史诗才会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他的自述诗才会意态高昴、晴暖尽现;他的评述诗也才会真切潇洒,生动感人。
总之,无论结构、修辞、语态,李仲元的格律诗整体表现为不犹疑,无困顿,不遮掩,以其内在生命的气势,托举正言直述的情势,彰显为辞章结构的动势,形成格律诗中不可多见的畅达俊爽的审美风格。即便如此,其诗中的格律却是极为工整严谨的,正所谓“从心所欲不愈矩”。在这里,“从心所欲”,是情感滋张,是势;“不愈距”,则是诗词格律上的中规中矩。进一步说,前者,是生命境界之高度,后者,是人文修养之深度。在李仲元的格律诗中,两者合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