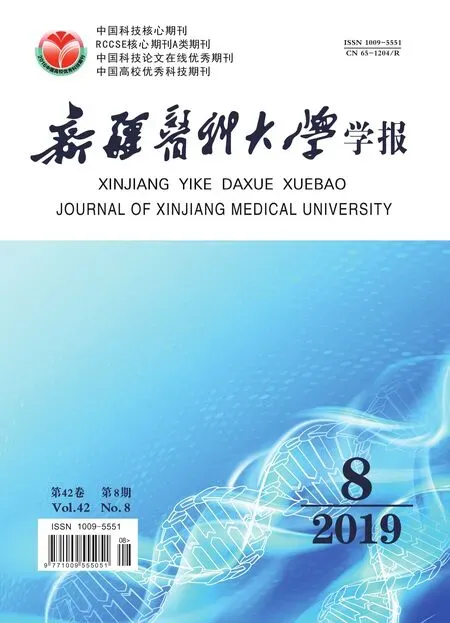ADAM33基因与慢性气道疾病相关研究进展
王 晶, 龚新记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呼吸危重症中心一病区, 乌鲁木齐 830054)
慢性阻塞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和支气管哮喘(bronchial asthma)是两类呼吸科较常见的慢性气道疾病,其发病率和死亡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1-3]。在慢性气道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环境和遗传因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近90%的慢性阻塞性肺病是由长期吸烟引起的,然而,只有25%的慢性吸烟患者发展成为慢性阻塞性肺病[4]。因此,宿主或遗传因素似乎使一些烟草接触者易患与吸烟有关的呼吸系统疾病。此外,有阻塞性气道疾病家族史的吸烟者(如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病)更容易发生慢性阻塞性肺病。因此,有人认为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病可能具有某些共同的易感因素或临床特征[5],故从遗传学角度对慢性气道疾病展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解整合素-金属蛋白酶(a disintegrin andmetalloprotease,ADAM)33基因是在2002年由Van Eerdewegh[6]发现的首个定位克隆基因。目前多项研究已证实,该基因为哮喘易感性的遗传危险因素[3,7-9]。近年来,不少研究发现ADAM33与COPD也存在关联[10-13]。通过ADAM33对COPD和哮喘进行研究,以进一步揭示其发病机制,为临床治疗提供新思路。本文就ADAM33与慢性气道疾病的相关进展做一综述。
1 ADAM33介绍
ADAM33是ADAM家族的成员之一,属于I型跨膜酶原糖蛋白,是一个长度约14 kb的基因,位于20号染色体的短臂(20p13)上,由22个外显子和21个内含子组成。它编码813个氨基酸长的基质金属蛋白酶,并有30个非翻译(UTR)区域,含有7个多态性位点。
ADAM33基因的几个重要生物学功能,包括细胞活化,蛋白水解,黏附,融合和信号传导。ADAM蛋白参与细胞-细胞和细胞-基质相互作用,细胞迁移,细胞-细胞黏附和信号转导。ADAM33转录显示组织特异性,在肺平滑肌细胞和成纤维细胞中占优势,在气道上皮细胞、T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中表达较低[14]。因此,ADAM33表达的变化可导致气道平滑肌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的功能变化。它还与气道上皮细胞损伤后的细胞修复相关,表明在小气道重塑、高反应性和炎症中的潜在作用。
2 ADAM33与哮喘的关联性
由于ADAM33基因具有复杂的差异剪接特性,因此观察到基因产物的高度可变性,大多数变异见于5’末端基因和3’结构域。正常受试者和哮喘患者的支气管活检标本中ADAM33剪接变异体的表达无明显差异。而在中度和重度哮喘中ADAM33的表达增加。在气道平滑肌细胞中观察到,IFN-γ可以下调ADAM33基因。研究表明IFN-γ对ADAM33的mRNA表达的影响,由启动子区调节。 IFN-γ调节ADAM33基因的区别在有和无哮喘的受试者中,可能是由于ADAM33上游区域存在多态性引起的。
2002年 Van Eerdewegh等[6]首次发现ADAM33基因的14个SNP与高加索人群的哮喘患病率之间存在强相关性。Vergara等[15]发现ST 7 SNP的TT基因型是哥伦比亚人群哮喘的危险因素,而H4(GCAGGG)与家族性哮喘相关,V4和T2基因座与血液IgE水平相关。然而,Miyake等[16]并没有发现德国和日本人群中T1,T2或V4基因座与哮喘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在一项涉及台湾哮喘患者和115名健康个体的研究中,Chiang等[17]的研究发现AA,AG和GG基因型以及2组之间A和G等位基因的频率分布存在统计学差异。Yao等[18]的研究也表明哮喘与T1,T2和V4位点的多态性有关。Zhu等[19]的研究发现T1与蒙古族、汉族人群哮喘风险相关,V4仅与蒙古族人群患者相关,而T2与上述人群无相关性。Shen等[20]的研究发现,T2、V4位点与哮喘严重程度相关。Farjadian等[21]对伊朗西南部哮喘患者ADAM33基因的T+1、T1、S1、F+1位点分析,发现病例组和对照组并无明显差异。总之,尽管这些基因座中的SNPs在不同区域和群体中非常普遍,但它们的分布与哮喘风险的关联变化很大。
3 ADAM33与COPD的关联性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ADAM33基因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ADAM33也是COPD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危险因素[22]。Wang等[23]在对312例亚洲人群COPD患者的痰液进行分析时发现,ADAM33基因的T1和Q-1位点与COPD气道炎症的细胞因子和介质显著相关。在一项涉及15例德国COPD患者和152例健康对照的队列研究中,Pabst等[24]发现ADAM33中F+1和S 2在不同亚组分析中均未见明显差异。Sadeghnejad等[25]研究发现5个SNP与COPD相关,分别是Q-1、S1、S2、V-V4,同时还发现Q-1,S1和V-1也与ppFEV1,FEV1/FVC比率和ppFEF25-75相关,S2与FEV1/FVC比率相关,S1和残余体积之间有关联。一项涉及9个SNP的13个病例对照研究的meta分析[11]提示:T1、T2、S1、Q-1、F+1和ST+5与不同人群的COPD风险相关。此外,研究还表明T2,Q-1和ST5表明与欧洲人群中COPD的风险相关,而T1,T2,S1,F1和Q-1表明与亚洲人群中COPD的风险相关。Tan等[12]对438例蒙古人群研究发现,ADAM33中的7个SNP与COPD相关(T +1、T2、T1、S2、S1、Q-1、F+1),单倍型分析显示COPD组中单倍型H1(GGAGGGT),H5(GGAGGGC)和H10(GGGGAGT)的频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而单倍型H11(GGACAGC)在对照组中比在病例组中更常见(P=0.015)。
4 ADAM33与气道重塑的关联性
血管重塑是哮喘气道的另一个特征。来自动物模型的数据表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是哮喘气道中血管生成、血管通透性和结构变化的重要介质。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可以促进哮喘气道重塑。据报道,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在过表达中过量表达。哮喘患儿痰液中成人哮喘气道增加18例,成人哮喘患者肺组织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表达增加,且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Elizabeth等[26]研究表明酶活性可溶性ADAM33(sADAM33)在哮喘气道中增加并且在气道重塑中起作用,不依赖于炎症,且其诱导的气道重塑是可逆的。此外,在过敏原攻击后,在ADAM33沉默的小鼠中,重塑和炎症都被抑制。当在子宫内诱导或离体添加时,sADAM33引起气道的结构重塑,这增强了在使用空气过敏原进行亚阈值攻击后出生后气道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和支气管高反应性。Fang等[14]研究提示:TGF-β1增强气道上皮细胞中ADAM33的表达,ADAM33诱导气道上皮细胞的间充质转变,从而参与哮喘的气道重塑。 Vergara等[15]研究了ADM33在ASM细胞中的表达,发现哮喘患者的ADAM33 mRNA和蛋白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气道平滑肌细胞。Elizabeth等[26]的研究表明1,25(OH)2D3可以抑制气道平滑肌细胞增殖,其对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分泌有负向调控作用。在子宫内缺乏维生素D的小鼠会导致气道平滑肌质量增加和气道阻力。此外,在患有严重哮喘的儿童中,维生素D水平较低与气道平滑肌质量增加有关[27]。Kim等[28]研究证明1,25(OH)2D3抑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诱导的ADAM33在mRNA和蛋白水平的表达,表明表达可能主要在mRNA水平调节。
5 ADAM33与肺功能的关联性
虽然ADAM33是一种膜锚定蛋白,但ADAM33可被检测为哮喘气道中的可溶性蛋白(sADAM33),其中高水平的sADAM33与肺功能降低相关[29]。最近的研究进一步表明,ADAM33内的SNP通过影响COPD的气道炎症过程和改变肺功能来赋予一般人群COPD易感性[30]。 一项涉及1 047例高加索男性合并哮喘或慢阻肺患者的数据研究[31]显示:三个基因(DPP10,NPSR1和ADAM33)的七个变体与1秒内用力呼气量的变化显著相关。即参与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的基因的遗传变异与正常衰老过程中肺功能下降有关。Kim等[28]的研究显示,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ADAM33蛋白水平与哮喘患者的预测FEV1值呈负相关。肺功能下降是COPD和心血管疾病发展的危险因素[32-33]。 Jongepier等[34]的研究也显示,ADAM33基因多态性不仅在哮喘易感性中起作用,而且在其进展中起作用。因此,ADAM33中多态性与FEV1下降的相关性也可能构成COPD发展的风险。在荷兰人群中,SNP S1,S2和Q-1与FEV1下降相关,并且SNP S1,S2,F 1和T2与C OPD的存在相关。在欧洲儿童的另一项研究中,SNP F 1,M 1,T1和T2与较低的FEV1相关。这些差异可能与人群不同有关,也可能与遗传背景相关,因此,需进一步研究ADAM33基因变异在其他人群中的分布。
综上所述,目前,大多数研究提示ADAM33与哮喘和COPD发病相关,但是受选取样本、操作方法不同,所得到的关联性的SNP位点也不同。因此,今后需要建立完善的风险基因体系,以期进一步深入研究COPD和哮喘的发病机制,为临床治疗提供新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