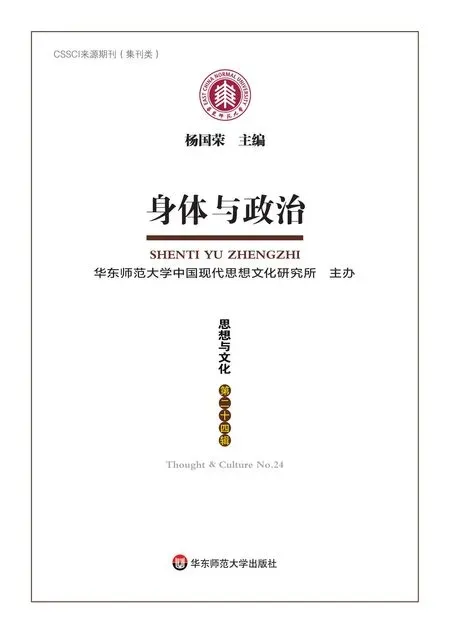屋顶上的后现代主义史诗
——姜文电影之影像风格解读*
《邪不压正》作为姜文“演而优则导”的第六部作品,于2018年7月13日在国内正式上映,并于2019年代表中国内地影片参与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从1995年的《阳光灿烂的日子》、2000年的《鬼子来了》、2007年的《太阳照常升起》、2010年的《让子弹飞》、2014年的《一步之遥》到2018年的《邪不压正》,姜文在“作者电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且风格独特、旗帜鲜明。综观他的六部影片,无论是主题、叙事,还是视听语言、美学风格,都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形成了一条带有姜文印记的创作脉络和影像意蕴。
后现代主义的复仇母题和暴力美学
复仇是中外文学艺术创作的永恒母题之一,是人类盛行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带有鲜明的超常态性和极端性。因此,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复仇的话语表达具有先天优势,它不仅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正义与非正义、英雄与非英雄,而且实现了崭新的反差语意,呈现出陌生化、奇异化的戏剧性效果。
在姜文的六部作品中,复仇一直是其中或隐或现又始终如一的母题。尤其是“民国三部曲”,亦可称作“复仇三部曲”。《让子弹飞》中,最大的转折点是六子被胡万设计陷害,为自证清白取肠而尽后,张麻子下定决心留在鹅城为六子复仇,开始了与恶霸黄四郎的斗争之路。《一步之遥》中,马走日的故事转折也发生在他难忍完颜英的死亡被王天王一次次排成低俗趣味的文明戏,决定为其复仇,于是选择了在王天王表演之时,出其不备地冲上舞台与之一决高下。而在《邪不压正》中,“复仇”这一母体被进一步强化,直接上升为整部影片的主题与叙事主线。故事发生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前,一个身负家仇大恨、自美归国的特工李天然,在国难之时涤荡重重,上演了一场精彩的终极复仇记。
较之其他以复仇为主题的电影,姜文作品中的“复仇”母题带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特色: 对传统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的彻底颠覆,对崇高、奉献、舍己为人的主流价值观的刻意消解,对正义、公平等民族大义的完全疏离,对宏大叙事、线性结构的终极反叛。在国家动荡、战火纷飞的年代,姜文电影中的主人公们勇敢地站起来反抗,但他们的反抗并非出于保家卫国的民族大义和革命热情,而是为了个人的恩怨情仇。由此,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化为时代大背景下的私人化叙述,传统人物的崇高性被彻底瓦解,影片中日常而琐碎的生活片段的重复和交叠,淡化了电影单一、稳定的叙事模式,也消解了主流价值观中美和丑、崇高和低俗、正直与卑鄙之间的界限。影片《让子弹飞》,土匪张大麻子劫了县长的火车,因颗粒无收而决定假扮县长走马上任。他承诺要带给鹅城百姓“公平、公平还是公平”,却始终只能以土匪式的思维来解决问题,并没有百姓带来实质性帮助。而他真正决定留在鹅城抵抗欺压百姓的豪绅,主要是出于为“干儿子”复仇。其复仇的过程,也可谓一波多折,虽是县长,却不能一呼百应,他能带领的唯有自己的几个土匪兄弟。他们在广场上一遍遍号召百姓一起进攻黄四郎的碉楼,却久久无人回应,最终跟随他们的只有一群憨厚笨拙的鹅。《一步之遥》中,马走日的复仇显得更为无力和仓促,即使完颜英的死与他无关,他也不敢告知公众。他胆小懦弱,只能把自己假扮成表哥派来的使者,试图恐吓王天王停止出演低俗的文明戏。努力无果后,他又鲁莽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冲上演出舞台毒打王天王,导致自己立刻被缉拿拘捕。为了换取自由,他甚至答应出演讲述自己杀害完颜英的电影……他的复仇行为就是小人物的无谓抵抗,最终只能以付出生命为代价。而《邪不压正》中,故事背景虽然设定在日本侵华时期,但是主人公李天然回国的目的只有一个——为师傅一家报仇雪恨,或者说,他的复仇也未必是为了师傅,他是为了寻求自己内心的解脱,影片中多次提及他曾经被师兄用枪指着的恐惧,以及多年来他内心经受的煎熬与挥之不去的阴影,复仇其实是对自我的救赎。影片一开始,他从美国意气风发地回到北平,心怀复仇大志,却又踟蹰不决、胆小懦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敢做一些孩子似的小闹剧——偷日本刀、偷日本人的印章盖在汉奸师兄情人的屁股上、用冰碴弹破师兄的眼皮等。他在北平的灰瓦飞檐间肆意奔跑,如入无人之境,却始终像个絮叨的哈姆雷特,迟迟没有复仇的决心。直到最后,他被一心为父报仇的女子——关巧红一步步推动、逼迫,才终于完成了复仇。
姜文对传统复仇母题的消解可以追溯到他的早期作品,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少年们的复仇声势浩大,百来号人拥在桥洞下,手持“武器”(各种铁器、棍子、砖头),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可是瞬间却峰回路转、转危为安,敌我双方在“威震北京的小坏蛋”的调解下握手言和,甚至冲进莫斯科餐厅来了一场狂欢聚会,让人哭笑不得。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复仇的母题必然会有暴力的呈现。“暴力美学”是姜文“硬汉”电影中的又一大鲜明元素,他在多部影片中充分运用暴力美学,并以不同形式进行艺术化的呈现,如硬暴力美学、诗意暴力美学等,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姜文作品中的硬暴力美学往往正面表现暴力,将打斗发挥到华丽炫目的极致。如,《邪不压正》的开头段落,即是姜氏典型的硬暴力美学的呈现。朱潜龙建议师傅卖地不成,一个叩拜,猝不及防地抬头开枪,正中师傅眉心,又连补第二枪,师傅带着脸上两个枪眼倒地而亡。下一个镜头,随行的日本人已手握长刀直冲镜头而来,伴着一声尖叫,师娘由头顶被劈为两半。下一秒,师姐被长刀倏地割断脖子,一颗人头飞出了纸窗,她直立着的身躯重重倒下。轮到李天然时,镜头以极快的速度展现了两组朱潜龙开枪与李天然躲子弹的正反打特写,然后快切到两人的侧面中景,清晰地交代了躲子弹片段,并在其中插入了一组两人的正反打特写,其间快速变化的景别、机位、愈加紧密的枪声辉映着子弹的火光,让人目不暇接。姜文以最直接的方式展现了暴力的全过程,其血腥与残忍最大程度地渲染了暴力的感官刺激,加之快节奏的剪辑,在开场5分钟内便将十八年前的仇恨渊源交代清楚,这一场硬暴力美学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汉奸朱潜龙与日本人根本一郎杀害师傅一家时的穷凶极恶,从而凸显了李天然的仇恨之深。
姜文的作品中也常常呈现诗意暴力美学,即以诗意唯美的镜头语言取代血淋淋的暴力场面,弱化攻击性,赋予暴力特定的仪式感,强调形式之美。在《邪不压正》临近结尾处,朱潜龙带着脸上的三道血痕气势汹汹地打开大门,此时画面呈轴对称构图,朱潜龙处于中心对称轴上,两边是四合院墨绿色的墙与深红色的柱,同时又有两道大开的门在其身后构成富有层次感的景深。在两人拔枪对峙时,全景仍然保持轴对称构图,以根本一郎为画面中心点,两人就像是一条直径的两端,绕着圆心做圆周运动。他们在打斗时用的是同样的招式,因此画面始终保持着对称,而利落的出拳、跳跃、扫腿等招式,以及扬起的满地碎白石,映着四合院清雅的日式风格,犹如一场漂亮的武艺表演,打斗被舞蹈化、表演化,暴力的本质被掩盖,赋予了诗意的美感,只有偶尔几个满脸是血的根本一郎的画面,才能让人想起如此极具美感的画面下,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生死之战。诸如此类的诗意暴力美学镜头还多次出现在姜文的其他几部影片中。如,《让子弹飞》一片“火车大劫案”片头,张麻子连开七枪,镜头在枪的正面特写、侧面特写与火车内惊慌的三人反应中快速切换,且节奏愈加愈快,随后拉着火车的白马四处逃窜,土匪们则头戴麻将面具骑着黑马穿过丛林、踏过河流,溅起漫天浪花。他们一路追上火车,并精准地在快马奔腾中将两把斧子嵌入铁轨,火车遇阻翻了个底朝天,车内的士兵与火锅汤底在车厢内翻滚,直至坠入河中,断成两节。这段死亡数十人的暴力片段,却毫无任何血腥与残忍,反而给人以一种磅礴大气的诗意美感。再如小六子的切腹取粉、鹅城街头的火拼、黄四郎的溅血鸿门宴、汤师爷被炸后的身首异处、《鬼子来了》中马大三被砍下的头、《阳光灿烂的日子》胡同里的少年斗殴等,都将暴力美学融入其中,通过对暴力内容的形式化处理,或营造审美的快感,或消解故事的真实性,张中有驰、独具一格。
后现代主义的空间优位和外化符号
电影的可视性决定了其与生俱来的空间性,莫里斯·席勒曾说:“只要电影是一种视觉艺术,空间似乎就成了它总的感染形式,这正是电影最重要的东西。”(1)引自马塞尔·马尔丹: 《电影语言》,何振淦译,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第169页。《电影艺术词典》把电影空间定义为“利用透视、光影、色彩、人物和摄影机的运动以及音响效果的作用,创造出来包括时间空间在内的四维空间幻觉”(2)许南明: 《电影艺术词典》,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第207页。。综观姜文的六部作品,不难发现,在他的影像世界里,空间不再是简单的物质维度,而是社会、文化、精神等相互交织的产物,带有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空间优位”特色。无论是宏观的空间,如鹅城、北平、上海,还是微观的空间,如广场、火车、屋顶、酒桌等,都可以看到姜文极具特色的电影空间观念。
屋顶一直是姜文电影展现的典型空间之一,是重要的空间符号。《邪不压正》中最令人难忘的是屋顶的设计和展现,姜文把北平四合院的屋顶意象用最为巧妙的方式勾勒出来,谱写了一首屋顶的史诗。屋顶远离地面,靠近蓝天与星辰,是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界线,屋顶之上,是青春、美好和自由之境;屋顶之下,是不安、阴谋、痛苦的源泉。屋檐下的李天然必须时刻谨记复仇之任,忍受内心煎熬,而一旦踏上屋檐,他便进入了另一种状态,是快意恩仇、潇洒恣肆的江湖侠客。电影中有一个段落,李天然给关巧红送完自行车返回时,他欢快地小跑上屋顶,又突然被关巧红叫住,并指挥他举起手、放平、转身,身着白衣短裤的少年在屋顶的逆光里亦步亦趋地做着动作,那一刻,李天然与《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中的马小军完美叠化,形同一人。马小军也喜欢游荡在屋顶上看北京,他常常在米兰家附近的楼顶间转悠,在明晃晃的阳光里挎着军用书包,从一个楼顶爬到另一个楼顶,正如片中独白所言:“我终日游荡在这栋楼的周围,像只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焦躁不安的守候着画中人的出现……”虽然马小军不像特工李天然那样在屋顶如鱼得水,他的动作小心翼翼,甚至有几分笨拙,却也满是少年的无所畏惧和躁动不安,把屋顶当作滑梯,倏地就滑进了青春。站在屋顶上的还有《太阳照常升起》中的疯妈,她立于屋檐,用方言反复吟诵“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那一刻的她,清醒而理智,感慨的正是自身的境遇。姜文电影中以“空间优位”的方式建构起了屋顶世界和地面世界,形成鲜明的对峙关系,但两者又同时存在、形成对话。这既喻示着真实世界的两重性,充分体现了本雅明笔下城市中现代性的游荡者形象,同时也在灰暗现实中给予了来自理想高空的慰藉,充满了浪漫主义情怀。
酒桌是姜文电影另一个典型的空间符号。中国历来有酒桌哲学,无论官场、商界还是普通民众,人们倾向于在酒桌的推杯换盏间,以尽可能柔和的方式谈判、决策,解决棘手的问题,酒桌文化是中国传统处事哲学的精髓所在。姜文的影片中始终贯穿着酒桌的空间符号,在视觉效果上非常巧妙,看似是表面的狂欢,实则反衬出暗流涌动中的刀光剑影,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张力。《邪不压正》有一场蓝青峰、朱潜龙、根本一郎、亨德勒在六国饭店的饭局,四个人心中各怀鬼胎,枉顾左右而言他,话中有话、绵里藏针,但因四方背后都有强大的势力支撑,因而每每陷入交锋局面时,总会有一方话锋突转,借着荤段子嘻嘻哈哈,假装相安无事,在爵士乐与香槟酒中粉饰太平。这场饭局的前身,可以追溯到《让子弹飞》中黄四郎的鸿门宴,黄四郎、张麻子与马师爷三人在圆形酒桌上的位置,构成三足鼎立之势。摄影机围绕圆形轨道运动,在不同机位上运动拍摄三人的镜头,且几乎都为单人镜头,表现了三人虽同在一张酒桌上,但各自为营,势均力敌、相互牵制,看似平静,却波澜壮阔,具有强烈的空间表现力。同样,《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也有一场在莫斯科餐厅的酒桌段落,原本要打群架的两队少年突然握手言和,冲进了餐厅,两群人围站在长桌两旁,摄影机沿着中轴线从他们的碰杯中运动前进,直到停在桌子尽头的“和事佬”——名震京城的小坏蛋处。此时,他处于构图的中心——毛主席像的正下方和其他人的上方,这种空间位置的设计,从视觉上体现出其地位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同时也反映了集体的狂欢只是昙花一现,难以打破固有的等级对立,马小军的旁白印证了这一点,“小坏蛋”不久之后就被想要取代他的孩子们扎死了……酒桌作为重要的交际空间,象征着微型的狂欢世界,打破了阶级、财产、门第、职位、等级、年龄、身份、性别的区分与界限,使人们实现了平等而亲昵的交往、对话与游戏。但事实上,这种平等而亲切的关系和狂欢的氛围都是暂时的,内在的固有矛盾不可消除,空间的叙事张力由此愈加突显,效果斐然。
除了“空间优位”之外,姜文电影中还有对现代人欲望的外化呈现,尤其是对窥视女性身体的呈现。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个体欲望与她者身体的关注,姜文受其影响,往往通过女性某个身体部位的展现,毫不避讳地表达他对女性之美、欲望与性的理解,并以后现代主义的方式将其具象化、符号化。姜文曾经说过,“对于女性,我从来都是仰视的”(3)彬彬有理: 《姜文曾经说过: 对于女性,我从来是仰视的》,“新浪女性”频道,http://eladies.sina.com.cn/feel/xinli/2018-07-20/0752/doc-ihfkffai9282888.shtml, 2018年07月20日。,因此他的影片中大多塑造了“神话”般的女性角色,且常常涵盖了“白玫瑰”与“红玫瑰”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比如,《邪不压正》中风情万种的唐凤仪和隐忍独立的关巧红,《一步之遥》中一片痴情、无法自拔的完颜英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武六,《让子弹飞》中主动献殷勤的县长夫人和敢握双枪对准自己与敌人的花姐,《太阳照常升起》中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疯妈与总是湿漉漉的林大夫,《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洒脱任性的于北蓓和成熟神秘的米兰……这两类女性虽然气质、类型截然不同,却都对影片中的男主人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或是青春的启蒙者,或是成熟的领路人,是精神世界的引领者。
综观姜文的影片,其展现的女性身体不外乎以下部分:
女性的臀。臀部代表生育,是生命的起源、母性的象征。《邪不压正》中,唐凤仪的第一次出场,便是在医院要求李天然为自己打美容针,特写镜头中针刺入她臀部光滑的肌肤;而第二次唐凤仪去家里找李天然打针时,她身着黑色蕾丝点缀的裸色修身旗袍,仅一个简单的落座,镜头便给了两次臀部特写。她如蛇一般穿着高跟鞋妖娆地趴到床上,翘起的臀部在丝绸映衬下勾勒出完美的曲线,散发出足以令人血脉贲张的女性魅力。
女性的脚和大腿。脚在中国缠足的传统文化中是身体最隐秘的部位,是女性的第三个性器官,而裸露的脚则带有性暗示的意味。《太阳照常升起》影片开场就有一段洗脚特写,黑暗中一双洁白娇嫩的脚深入镜头,两只脚在空中犹如舞蹈般交叠、开合,晃动的水影折射在脚底荡漾,当双脚从水底浸湿抬起时,在水珠和灯光相映下,更显肤若凝脂、温润白皙。随后,移动镜头跟随着这双脚一路走过木地板、木楼梯、红泥地、河边与石子路。《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马小军和心驰神往的米兰第一次见面,也是从脚开始。马小军低头捡火柴时,一双穿着黑布鞋的少女的脚从他身边经过,膝盖以上是蓝色的碎花连衣裙,膝盖以下是健康圆润的小腿。在此之前,马小军视线内米兰的出场都仅限于这双脚,一次是床底下的偷窥,一次是公安局门口的擦肩而过。而《一步之遥》中,百老汇式的歌舞表演,大量镜头聚焦于大腿,第一个镜头是满屏穿着渔网袜的大腿构成的三角构图,低机位的摄像机从中穿过,在随后的歌舞表演中,也是满屏大长腿,整场歌舞表演,都格外注重腿部的动作,马走日与项飞田两人的主持从一纵列大腿后开场,又以推开左右两边舞蹈演员的大腿作为表演的结束。
当然,姜文的影片中还有很多具有符号意义的女性身体标识,如唐嫂“天鹅绒般”的肚子、林大夫湿漉漉的头发、米兰的泳衣形象……姜文正是通过聚焦女性的身体部位,展现极致的身体之美,丰富了影片中每一位女性独一无二的形象塑造,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注重视觉狂欢的外化呈现。
后现代主义的荒诞化叙事和戏仿拼贴
姜文曾说过:“电影是梦,在我来说,是想表现一个自己想象中的世界。电影对我的吸引,有一点就是无中生有。无中生有出一个似乎存在的,让你觉得比现实世界还真实的一个世界。”(4)高希希: 《摄像机对准大兵、蓝天和沙漠》,《大众电影》,2002年第9期。在电影的叙事和视听语言方面,姜文的作品表现出一贯的风格: 注重自我的表达,强调个人的主观感受,拒绝传统、排斥循规蹈矩。他的作品中充满了梦境般的场景、非真实的色彩和碎片化的个人记忆,且梦境般的场景展现往往突如其来、出其不意,使人难辨现实与虚幻,在确定与不确定间左右摇摆。比如说,《一步之遥》利用同一事物转场,从完颜英躺在床上时的唇部特写过渡到她坐在车上时的唇部特写,镜头顺着完颜英手臂的伸展方向滑动,逐渐呈现出路边林立的工厂和西式建筑,再沿着弧线回到驾驶座的马走日上,两人呈现出癫狂的状态,镜头也如醉酒般在两人之间肆意摇移。二人一路飞驰,终于在芦苇地停下,马走日朝天空鸣枪,天空便绽放烟花,远处的月亮逐渐朝画面滚来并不断变大,直至充满银幕,上面赫然映着卡通兔的形象,于是两人开着红色敞篷车飞向月亮……《太阳照常升起》中长鸣而来的火车带着滚滚浓烟撕裂了黑夜,路过篝火旁狂欢的人群,被引燃的帐篷突然飘起,犹如飞鸟般追随火车而去。此时的镜头在疯妈的脸部特写与火光剪影中来回快切数十次,且频率不断加快,直至眼花缭乱。而随即的空镜头中,朝霞渐渐从远处渲染了天空,火车由画右缓缓平行驶向画左,下一刻疯妈的剪影出现,她奔跑在瑰丽的天地间,镜头紧紧追随,最终停在轨道处,花团锦簇之中,一个刚降生的婴儿在啼哭,身上洒满了金色的圣光。
“色彩即思想”(5)韩尚义: 《“色彩即思想”——与丁辰、许琦谈〈蔓萝花〉》,《电影艺术》,1962年第4期。,姜文影片中的色彩也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倾向,既有典型的非现实主义风格,又富含深意、意蕴悠远。比如说,《邪不压正》运用色彩变化层层推进故事情节,影片前期多用暗黄、灰白等颜色,以此营造复仇的压抑氛围,而随着复仇的逐渐明朗,影片的色彩也随之明亮,以自然的蓝、绿为主色调。《阳光灿烂的日子》则运用黑白和彩色区分“我”的中年时期与青少年时期,以此表现现实生活的枯燥乏味和青春时代的绚烂多姿。《鬼子来了》全片采用黑白,直至马大三人头落地出现一抹鲜红,既是对抗日战争恐怖、黑暗时期的写照,也寓意着抗争意识的觉醒。《一步之遥》、《让子弹飞》则延续了《太阳照常升起》中浓郁饱满、瑰丽魔幻的彩色,实如戴锦华所言,“奇诡却明艳,冒犯常识却不流于矫情,荒诞却欣愉,恣肆狂欢而书写绝望与残酷”(6)见姜文: 《长天过大云——太阳照常升起》,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在叙事结构上,姜文的影片打破了线性叙事,情节推进更趋碎片化,从结构上拆解了固有的时间脉络,进行重新拼接和组合。以最典型的《太阳照常升起》为例,影片分为4个段落,采用了环形叙事方式与多段式结构,使看似独立的人物随着情节的推进逐渐形成交集,直至拼凑出完整的故事线,首尾相连,从而完成了叙事时空的闭环。
在叙事策略方面,姜文还善于使用后现代主义的戏仿手法。所谓戏仿,又称谐仿,即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其他作品进行借用,以达到调侃、嘲讽、游戏或致敬的目的。戏仿是后现代影像叙事的重要策略之一,“戏仿进入艺术家的符号实践,即产生一种绝望中的狂欢,一种远游中的回归”(7)温德朝: 《戏仿: 喜剧电影叙事的后现代策略》,《电影文学》,2008年第5期。。姜文常常运用这一手法,在电影中建构新的含义来消解原有含义,增加了能指对应的所指范围,扩大了内涵解读的可能性。比如说,《邪不压正》中李天然偷了根本的印章,盖在唐凤仪的屁股上,这一段是对捷克电影《严密监视的列车》的戏仿。《严密监视的列车》是1960年代捷克新浪潮电影运动的扛鼎之作,它用黑色幽默的手法、性的戏剧元素来象征捷克人民的反抗意识和不屈尊严,片中车站调派员胡比克风流成性,喜欢在女电报员的屁股上盖满德文的车站公章,这一举动对德国纳粹的讽刺不言而喻。而《邪不压正》中李天然模仿此举,既是对根本一郎的嘲讽,也是对朱潜龙的挑衅,同时,这一恶作剧式的行为也丰富了李天然的人物形象,有意消解了他的英雄性,增添了少年的稚气与可爱。该片中还有不少姜文对自己电影的戏仿,比如结尾时李天然站在屋顶上连续大喊“巧红——巧红——巧红——”,类似场景同样出现在《太阳照常升起》与《阳光灿烂的日子》结尾处。前者是疯妈抱着孩子在火车顶上呼唤“阿辽沙,别害怕——火车在上面停下啦——他一笑天就亮啦”,后者则是马小军在雨夜高喊“米兰——我喜欢你——”。
戏仿的叙事策略使得姜文的作品更加具有戏剧的张力。《一步之遥》中开头一段就是对《教父》的戏仿,马走日身穿白色衬衫、黑色燕尾服,胸前戴着一朵红玫瑰,从布光、构图到表演,都与《教父》极为相似,但马走日怀中却抱着一只兔子。马走日和兄弟们谈论的事情荒诞可笑,与《教父》中肃穆压抑的氛围截然不同,形成强烈反差,这种戏仿,暗喻马走日看似拥有教父般的尊崇地位,实则岌岌可危,加重了影片后半部分他被权贵玩弄于股掌间的黑色幽默式的悲剧色彩。
当然,戏仿与拼贴的大量运用是一种大胆的冒险。《一步之遥》之所以“票房失利”,原因之一在于影片中出现了大量的戏仿。影片一开场的音乐来自库布里克的《太空漫游2001》,花域选举戏仿好莱坞歌舞片,马走日和完颜英的飞车片段戏仿《雌雄大盗》的邦妮与克莱德,完颜英倒在麦田的段落戏仿《红高粱》里的野合段落……大量的戏仿和拼贴使整部影片的情节支离破碎,叙事碎片化、意识流化,纵然有游离错置的愉悦感,但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却难以理解和接受,因此市场反应惨淡。
姜文作为中国导演中“作者电影”的典型代表,其电影创作带有明显的个人化色彩,对时代的审视,对传统的解构,对自我的迷恋和满腔赤子之心,使得他的作品中的后现代主义影像风格独立于浩瀚的影像世界。在过去20余年的创作中,他已经从马小军、张麻子、马走日中分出身来,成长为屋檐上复仇成功的少年李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