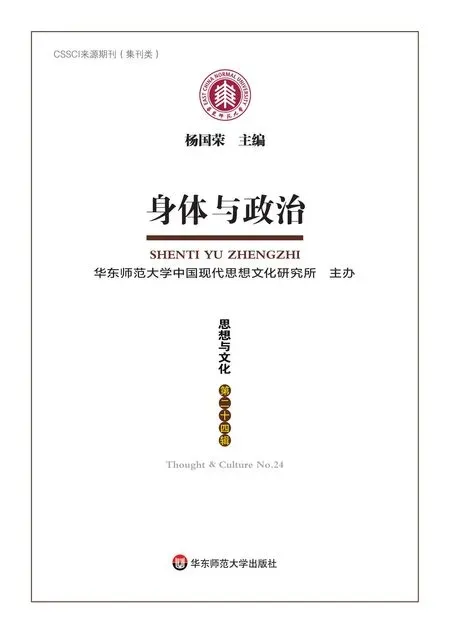理解他者: 具身社会认知*
社会认知的规范和主流进路很少强调主体间的交互,即便当它们提及了交互,也会认为心智之间必须要跨过不可逾越的鸿沟才能得以交流。这种观点认为,交互不是解决的方案,只不过是说明他人心智问题的另一种方式。不妨思考如下的陈述:
社会交互的研究……关注的是两个心智如何通过交互来相互塑造的问题。为了理解交互心智我们必须明白思想、感知、意向和信念如何可以在心智之间传达。(1)W. Singer, D. Wolpert & C. Frith, “Introduction: The Study of Social Interactions,” The Neuroscience of Social Interaction, C. Frith & D. Wolpert (e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2-17.
按照心智理论的规范解释(theory of mind, ToM),由于他人的心智无法直接获知,心智之间的差距只能通过主体心智中的多种认知过程加以弥补,才能为推断他人的心智状态提供方法。主体需要理论推理(民众心理学),或模拟程序,或者二者的结合,以允许一种“读心术”或“心智化能力”的推理形式,从而弥补这种差距。
在这节回顾了一些社会认知传统的心智理论模型之后,我在发展心理学和现象学的资料基础之上概述了一种替代模型。在这种替代模型中,具身的第二人称交互在我们理解他人的能力中扮演了主要(虽然不是唯一的)角色。最后,我讨论了模拟理论(simulation theory, ST)对新近发展的具身模拟进路的辩护。
传统的心智理论很少提及身体如何可能被纳入理解他人的过程,至多认为我们对他人的身体采取一种观察的态度并将其作为构建推理的证据来源。理论论(theory theory, TT)的支持者认为,推理的形成是用一种理论或一组民众心理规则进行心智磋商的结果,这些理论或规则允许主体按照被理解为他人心理状态的信念和欲望对观察到的行为进行推理。模拟论避开理论推理而选择了模拟程序,这种程序运行于个体心智的机制之中。如下即详细说明了外显模拟程序所认识的工作原理:
首先,归附者自身创建模拟状态以匹配目标。易言之,归赋者试图进到目标对象的“心境”之中。第二步是将这些初始模拟状态(如信念)放置到归赋者心理的某些机制中……并允许该机制对模拟的状态进行操作,从而产生一种或多种新的状态(如决策)。第三,归赋者将输出的状态赋予目标……(比如,我们推断或投射出了他人的决策)。(2)A. Goldman, “Imitation, Mind Reading, and Simulation,” Perspectives on Imitation II, Hurley & Chater (ed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5, pp.79-93.
这两种路径共享着几个基本的假设。首先,他们认为主体缺乏达至他人心智的路径,心智是隐藏于行为背后或超乎行为之外的。所以我们就只能用被推断出来的心理状态来解释或预测行为。
理论论和模拟论采纳的第二个假设是理论推理或模拟程序构成了社会认知的主要和普遍方式。因此我们发现了心智理论的支持者所宣称的普适性主张,如下就是其典型的例证:
人们到处用心理术语来解释他人的行为……因为我们所有人都配备了“心智理论”模型(ToMM),只能以心理术语作为它的本能语言来理解他人。(3)J. Tooby & L. Cosmides, “Foreword to S. Baron-Cohen,” Mindblindness: An Essay on Autism and Theory of Min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pp.11-18.
对于我们而言,除了借助心智主义的框架,用其他任何方式都很难理解行为。“人类心智状态的属性好比蝙蝠的回声定位能力。它是我们理解社会环境的自然方式。”(4)S. Baron-Cohen, Mindblindness: An Essay on Autism and Theory of Min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pp.3-4.另参阅A. Leslie, “Theory of Mind as a Mechanism of Selective Attention,” The New Cognitive Neurosciences, M. Gazzaniga (e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pp.1235-1247; U. Frith & F. Happé, “Theory of Mind and Self-Consciousness: What is it like to be Autistic?” Mind and Language, Vol.14 No.1(1999): 1-22。
激进的模拟论认为所有情况下(第三人称的)心智化应用的都是模拟程序。温和派则认为模拟只是心智化的默认方式……我倾向于这种温和派论点……模拟是人际间心智化最原初的根本形式。(5)A.I. Goldman, “Simulation Theory and Mental Concepts,” Simulation and Knowledge of Action, J. Dokic & J. Proust (ed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2, pp.1-19.
第三,它们假设我们和他人的关系总是基于一种观察立场。知觉被表征为主体观察他人行为的第三人称过程,而不是以第二人称的方式与他/她交流。这种观察立场在几乎所有的错误信念测试中都表现得很明显,理论论也将之归为关于心智化能力发展的科学证据。例如,一个被试(通常是儿童)被要求去观察另外两个儿童(有时是木偶)的行为。萨利(Sally)把一块大理石放到了篮子里并且离开了房间;另一个儿童安妮(Anne)将大理石从篮子里移动到了盒子里。当萨利返回房间的时候,被试就会被问到萨利将会去哪里寻找大理石。四岁大的儿童会倾向于正确地回答萨利会去篮子里找;而三岁的儿童则一般回答错误,认为萨利会在石头实际所在的盒子里找。这就证明了三岁的受试者(以及一些自闭症患者)还无法领会持有不同的视角会导致萨利的错误信念;四岁的儿童显然已经发展了能处理错误信念的心智理论能力。(6)H. Wimmer & J. Perner, “Beliefs about Beliefs: Representation and Constraining Function of Wrong Beliefs in Young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Deception,” Cognition, Vol.13(1983): 103-128; A. Leslie & U. Frith, “Autistic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Seeing, Knowing and Believing,”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Vol.6(1988): 315-324.这样的实验设计致使被试只能是事件的第三人称观察者,他们从未参与过事件或者与萨利和安妮交流。理论论研究者同样未指明的是: 即便是最小的非自闭症儿童,通过和实验者的互动,也能轻易获知实验者的意图。
模拟论同样也把观察作为起点,把推理判断作为主体间过程的终点。为了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在大脑运行模拟程序之前我们需要首先去观察他人的行为。整个模拟过程的描述都被观察立场所支配。
理论论和模拟论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之一就是心智化过程究竟是外显(受意识控制的)抑或内隐的。关于内隐模型的最激进版本稍后会进行讨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针对可产生理论化或模拟化的意识或内省形式的外显模型,我们可以提出一个简单的现象学反对意见。简言之,如果认真回顾每天和他人相遇的日常经历,我们会发现自己采取的不是第三人称的观察态度。我们并不总是试图解释或预测他人的行为,或者尝试进入别人的大脑去探知他们的信念和欲望。绝大多数的日常交际都是第二人称交互式的,并且我们理解他人所需要的大部分信息都可即时获取。
一种具身进路
我们称之为具身或交互的进路包含了婴儿时期既已发现的一套复杂的实践。从这个视角而言,许多所谓的心智并不具备隐匿性,而是可以很容易获取的东西。在此可以思考下现象学家马克思·舍勒(Max Scheler)把主体间知觉作为直接知觉的描述:
我们的确相信自己可以直接体会到他人笑声之中的愉悦,眼泪之中的悲伤和痛苦,面红耳赤之中的羞愧,所伸双手之中的恳求……以及言语之中的思想。如果有人根据知觉只是简单的“身体感觉复合体”这一事实,告诉我这不是“知觉”……我会请求他搁置这些可疑的理论,转而面向现象学事实。(7)M. Scheler, The Nature of Sympathy, P. Heath (tran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4, pp.260-261.
这个观点认为我们可以从他人身体的直接感知中获取大量信息,进而对他人的境况有所了解,即从他们的姿势、动作、面部表情、手势、语调和行为中觉察他们的感受和意图。并非舍勒一人持此观点,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也做过许多相似的论述:
看着别人的脸,并审视其中的意识以及一种特殊的意识色调。你可以从中看到快乐、冷漠、兴趣、兴奋、麻木等等……你是否在观察自己以便识别他人脸上的愤怒?(8)L. Wittgenstein, Zette, G.E.M. Anscombe & G.H. von Wright (eds.), G.E.M. Anscombe (tra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229.
一般说来,我并不揣摩他人的恐惧——我可以直接看到这种恐惧。我不觉得我是从外部事物推断出内在事物的可能存在;毋宁说,人类的脸在某种程度上是透明的,我不是在反射光中而是直接在其自身光亮之中看到了它。(9)L. Wittgenstein, Remarks on the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 Vol.II, G.H. von Wright and H. Nyman (eds.), C.G. Luckhardt & M.A.E. Aue (trans.), Oxford: Blackwell, 1980, p.170.
我们不用通过观察自己来了解他人的体验,说明这不是一个模拟过程。并且,我没有在揣摩或推测别人的体验,这也意味着我不是通过理论推断来获得达至别人心智的通道。
尽管从这个角度而言,理解他人并不成问题,但是不等于说他人就是完全透明的,或者所有行为的意义都能被知觉地把握;行为经常是含糊不清的,人们并不总是展现自身的情绪和想法。这里的观点并非说直接知觉可以穿透他人的灵魂并发现他/她内心的情感状态,也不是说我们绝不会被所感知到的信息误导。更确切地说,在日常生活的大多数相遇中,直接感知为理解他人提供了大量重要信息。此外,只有通过这些方法才会让我产生也许还有更多的事情发生在他人身上的想法。
另外,在日常与他人的相遇中,我并没有采取观察的态度;我也不是站在一边思考或试图理解他们在做什么。相反,我以一种具身的方式回应他们,并且我本身就是情境的一部分。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我们自身的运动和情绪系统错综复杂地参与到了对他人的知觉之中,并且这种知觉应视为生成的而不是被动的过程。所以我们称社会认知为社会交往的第一要素。我在这些例子中所感知到的并不是缺乏理解的东西。相反,我对他人的理解是在知觉-动作回路中构建的,这种回路对我正在处理的或我回应他人的事情进行了规定。
在许多发展研究中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据,通常它们可归属于发展心理学家特雷瓦森(C.B.Trevarthen)所说的“初级主体间性”。(10)C.B. Trevarthen,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Early Infancy: A Description of Primary Intersubjectivity,” Before Speech, M. Bullowa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321-347.我们来到世间并非白板一块,因为很快就会被赋予各种内容。发展心理学的相关研究不断地告知我们,新生儿的知觉已经相当敏捷。他可以从周围物体中识别出一张人脸,如果有足够的细节他也可以模仿所看到的表情。(11)A. Meltzoff & M.K. Moore, “Imitation of Facial and Manual Gestures by Human Neonates,” Science, Vol.198(1977): 75-78; A. Meltzoff & M.K. Moore, “Imitation, Memory,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Persons,” Infant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Vol.17(1994): 83-99.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新生儿能以一种生成的、模仿的回应方式自动与微笑(以及其他的面部表情)相协调。(12)L. Schilbach, S.B. Eickhoff, A. Mojzisch & K. Vogeley, “What’s in a Smile? Neural Correlates of Facial Embodiment During Social Interaction,” Social Neuroscience, Vol.3 No.1(2008): 37-50.年幼的婴儿在视觉上被运动所吸引,并且以特定的方式被生物运动所吸引,而在听觉上则被比如母亲的嗓音等特定声音所吸引。婴儿“用一种似乎在[情感上和时间上]相‘协调’的方式对他人的声音和姿势做出回应”(13)A. Gopnik & A.N. Meltzoff, Words, Thoughts, and Theori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7, p.131.。人类婴儿能展现出一系列的面部表情,比如带有复杂情感、手势、韵律和触觉的面对面交互模式,这些都是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缺乏的(14)D. Falk, “Prelinguistic Evolution in Early Hominids: Whence Motheres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Vol.27 No.4(2004): 491-503; E. Herrmann, J. Call, B. Hare & M. Tomasello, “Humans Evolved Specialized Skills of Social Cognition: The Cultural Intelligence Hypothesis,” Science, Vol.317 No.5843(2007): 1360-1366.,并且很显然没有受理论推理或模拟程序的干预。此外,他们能以一种非心智化的方式把身体运动视为情感的表达和目标导向的意向运动,并能把他人感知为行动者。这些都无需高级的认知能力、推理或者模拟技能的参与;相反,它是一种“快速、自动、不可抗拒并且是由高度刺激驱动的感知能力”。(15)B.J. Scholl & P.D. Tremoulet, “Perceptual Causality and Animacy,”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Vol.4 No.8(2000): 299-309.
婴儿在五到七个月的时候就能察觉出情绪表达中视觉和听觉信息之间的对应关系。(16)A.S. Walker, “Intermodal Perception of Expressive Behaviors by Human Infan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Vol.33(1982): 514-535; P. Hobson, “The Emotional Origins of Social Understanding,”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Vol.6(1993): 227-249; P. Hobson, The Cradle of Thought, London: Macmillan, 2002.九个月大的婴儿会跟随他人的视线(17)A. Senju, M.H. Johnson & G. Csibra, “The Development and Neural Basis of Referential Gaze Perception,” Social Neuroscience, Vol.1 No.3-4(2006): 220-234.,开始把头部、嘴部、双手的不同动作,以及更常规的身体动作感知为有意义的、目标导向的动作。例如,鲍德温(D.A. Baldwin)及其同事已经证明了十到十一个月大的婴儿已经能够根据意向边界分析某些连续动作。(18)D.A. Baldwin & J.A. Baird, “Discerning Intentions in Dynamic Human Act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 Vol.5 No.4(2001): 171-178; J.A. Baird & D.A. Baldwin, “Making Sense of Human Behavior: Action Parsing and Intentional Inference,” Intentions and Intentionality: Foundations of Social Cognition, B.F. Malle, L.J. Moses & D.A. Baldwin (ed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 pp.193-206.这种知觉会在婴儿即将一岁的时候,给予婴儿一种针对他人意愿和性情的非心智化和知觉化的具身理解能力。(19)D.A. Baldwin, “Infants’ Ability to Consult the Speaker for Clues to Word Reference,”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Vol.20(1993): 395-418; S. Johnson, “Whose Gaze will Infants Follow? The Elicitation of Gaze-following in 12-month-old Infants,” Developmental Science, Vol.1(1998): 233-238; T. Allison, “Social Perception from Visual Cues: Role of the STS Reg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 Vol.4 No.7(2000): 267-278.这些能力在成年后不会消失,反而会变得成熟和更加复杂。(20)W.H. Dittrich, T. Troscianko, S.E.G. Lea, & D. Morgan, “Perception of Emotion from Dynamic Point-light Displays Represented in Dance,” Perception, Vol.25 (1996): 727-738.这可以在它们参与新任务时,通过对他人姿势、动作、手势、注视和面部表情的微观分析得到确证,直接知觉实践是所采取行动的内在因素。(21)P.M. Niedenthal, “Embodiment in Attitudes, Social Perception, and Emo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Vol.9 No.3(2005): 184-211; J. Lindblom, “Minding the Body: Interacting Socially through Embodied Action,” Linköping: Linköping Studi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ssertation No.1112, 2007.
原初的直接知觉实践并没有对社会认知进行完整的解释,我们直接从他人的具身行为中获取的信息,相比我们能对他人做出的丰富而细微的理解而言还远远不够。随后这种原初主体间性即将被次级主体间性所补充和增强。(22)C. Trevarthen & P. Hubley, “Secondary Intersubjectivity: Confidence, Confiding and Acts of Meaning in the First Year,” Action, Gesture, and Symbol: The Emergence of Language, A. Lock (ed.),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8, pp.183-229.表情、语调、手势和动作伴随着身体得以展示,它们并非毫无根基,并且婴儿很快会开始注意他人是如何与世界交互的。婴儿在一岁左右的时候开始将行为与实际语境联系起来;他们进入共享注意的语境之中,在那里学习事物的意义和用途。共享注意机制的行为表征在九到十四个月左右的时候开始发展。(23)W. Phillips, S. Baron-Cohen & M. Rutter, “The Role of Eye-contact in the Detection of Goals: Evidence from Normal Toddlers, and Children with Autism or Mental Handicap,”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Vol.4 (1992): 375-383.在这样的交互中,儿童注意到他人的身体和表达动作,从而去辨别对方的意图或者去发现物体的意义。当他人注视儿童或者正在看门的时候,儿童可以明白对方是想要食物或者打算开门。(24)这并非是认为他人的欲望和信念都隐藏在心智之中的意向立场;相反,意向性在他人的具身行为之中被感知。他们开始发现他人的动作和表情通常依赖于有意义和实际的语境,并被周围的世界所调节。他人不会首先被给予(从未被给予)为认知上的或者需要解释的客体。他们的行为是在实际的社交背景下形成的,我们将之感知为行为主体。由此可见,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与他人相处的方式,我们的交往通过各种实际的(和基础性的、制度性的)环境来协调。事实上,我们正处于这种实际的环境中,并且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于与他人的关系中(例如,婴儿对他人营养品的依赖),即使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辨别哪些行动者提供食物,哪些行动者在从事其他活动。
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儿童不只是简单地观察他人,他们不是被动的观察者。相反,他们会与他人交往并据此进一步提升在交互情境中的能力。如果说初级主体间性的能力,如在表达性动作和视线方向中对意图进行探查的能力,已足够使儿童认识到自我和他人、他人与世界的双向关系,在次级主体间性中则被赋予了更多的能力。如前所述,共享注意力从大约九到十四个月开始发展,儿童可以在观察他人的注视和他人注视的事物之间变换,以核实检查他们是否在持续注视同一事物。实际上,与此同时儿童也差不多学会了指向动作。在十八个月大的时候,儿童能在特定的情境中理解他人使用工具的意图。他们能够重现并完成别人未完成的目标导向行为。因此,当幼儿看到一个大人试图操作玩具而失败并感到沮丧时,他会很乐意地拿起玩具,并向成年人展示如何打开它。(25)K.H. Onishi & R. Baillargeon, “Do 15-month-old Infants Understand False Beliefs?” Science, Vol.308 No.5719(2005): 255-258.该研究表明婴儿在十五个月的时候就能明显地心智化他人的错误信念。该研究的实验数据显示,当婴儿观察到他人的行为意向和婴儿对环境的了解相冲突时,他们会感到惊讶(或至少会加以注意)。尽管该研究完全以心智化他人信念的心理理论框架来解释这些数据,但是依据感知到的意义(语境化)行为、动作和意图而做出一种替代解释显然是有效的。十二个月大的婴儿从两种意义上解释行为: 他们使用行动者执行的其他动作和情境中的因果约束条件来解释一个模糊的动作;六个月大的婴儿可以将抓握动作理解为目标导向的,十二个月以下的婴儿可以在序列(环境中的行为)基础上来解释动作目标,而无需诉诸隐藏的信念或心理状态。见A.L. Woodward & J.A. Sommerville, “Twelve-month-old Infants Interpret Action in Context,”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11(2000): 73-77。另参见A.N. Meltzoff, “Understanding the Intentions of Others: Re-enactment of Intended Acts by 18-month-old Childre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Vol.31(1995): 838-850; A.N. Meltzoff & R. Brooks, “‘Like Me’ as a Building Block for Understanding Other Minds: Bodily Acts, Attention, and Intention,” Intentions and Intentionality: Foundations of Social Cognition, B.F. Malle, L.J. Moses & D.A. Baldwin (ed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 pp.171-191。
我们对他人行为的理解尽可能发生在最高和最适当的实用层面上。换言之,我们是在最相关的实用(意向性,目标导向)水平上理解他人,可能会忽略亚个人(sub-personal)或者更低水平的描述,同样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会忽略依据信念、欲望或隐藏的心智状态所做的解释。我们不是从身体动作出发然后转向心理事件层面来推断他人的意图,而是在物理情境和主体间环境中将行为视作有意义的。如果在一扇锁着的门附近,我看见你伸手去拿一串钥匙,我就会从门和钥匙以及你的身体姿势和表情中得知你的意图。我们依据他人在语境化情境中设定的目标和意图,而不是抽象地按照他们的肌肉活动或信念解释其行为。环境,不仅是一个物理定位,同样也是一个实际语境和社会情境,无论是关于我们自身抑或是他人的可能性行为方面,都绝不会被中立地(毫无意义地)感知。从这方面来说,世界本身就已经做了许多涉及社会认知的工作。正如吉布森(James Gibson)的可供性(affordance)理论所言,我们关注的都是事物的可能用途,因此绝不是作为一个非具身的观察者。(26)J.J. Gibson,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Boston, MA: Houghton-Mifflin, 1979.同样地,我们把他人感知为行动者,那绝不是存在于某个情境之外的实体,而是作为存在于实际语境中的行动者,这个情境还能澄明其意向(或可能意向)。
关于社会情境的作用和人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还有很多可以探讨的空间。随着儿童的成长,尤其是当他们拥有了被原初和次级主体间性赋予的具身能力,就会很容易学会在情境中应该对他人期望些什么,并且这些期望定义了理解他人的默认文化框架。当我走进教室或者杂货店,我可以直接分辨出谁是教师或收银员,我也可以直观地理解他们在做什么,这些交互活动已足够实现我的特定目的。我们无需使用理论推理或者模拟程序,绝大多数的社会理解是被我们儿童期学会的脚本和短篇故事所塑造的。(27)D. Hutto, Folk Psychological Narrativ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7.我们通常凭借对情境化行动者的知觉就能获得丰富而复杂的理解——即处于一定环境中的行动者同样可以告知我们这个人的所行所思。当我看到行动者的情境性行为及其行为方式和表述内容(比如他/她的姿势和动作风格),这种知觉已经通过我与他们及其他人的互动,此外还依靠我先前的情境化经历、我的习惯化理解方式以及文化规范和习俗等,获知了相关信息,因此在我们日常生活遇到的情况中,理解工作已充分地完成,不必再做进一步的努力。我不必去思考对方的想法,因为理解对方所需要的所有信息已经隐含于他/她的行动和我们共在的世界之中了。
同样,关于叙事在调整我们社会理解中的作用还要进一步说明。我们在幼儿时期就获得了叙事能力,随之而来的是在那些我们对他人行为完全感到困惑的特殊情况下运用民众-心理实践的能力。(28)S. Gallagher & D. Hutto, “Primary Interaction and Narrative Practice,” The Shared Mind: Perspectives on Intersubjectivity, Jordan Zlatev, et al. (ed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8, pp.17-38.如果收银员在柜台上跳舞,或者老师在课堂上扔水气球,那么我们就可以采取观察的姿态,开始理论推理或模拟他/她的可能心智状态。然而,这类做法只是例外,并不是我们理解他人的主要或普遍方式。
内隐模拟或具身实践
初级和次级主体间性的具身实践,涉及直接知觉和实际语境,这与心智理论家把社会认知设想为一个纯粹的心智化或认知化过程的主张形成鲜明对比。然而,最近模拟论诉诸神经科学中的共振系统和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 MNs),为内隐模拟提供科学依据。当然,这就取决于对科学数据的具体阐述。
我们知道,感知者的运动系统在他/她察觉到他人在执行一项意向行动时会被激活。额顶叶皮质的相同或重叠的部分神经区域,尤其是MNs在人类大脑的前运动区、布洛卡区和顶叶皮层,当被试从事特定的工具性行为时,以及当被试观察其他人从事这些行为时都会被激活。(29)G. Rizzolatti, L. Fadiga, V. Gallese & L. Fogassi, “Premotor Cortex and the Recognition of Motor Actions,” Cognitive Brain Research, Vol.3(1996): 131-141; G. Rizzolatti, L. Fogassi & V. Gallese, “Cortical Mechanisms Subserving Object Grasping and Action Recognition: A New View on the Cortical Motor Functions,” The New Cognitive Neurosciences, M.S. Gazzaniga (e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pp.539-552; J. Grèzes & J. Decety, “Functional Anatomy of Execution, Mental Simulation, and Verb Generation of Actions: A Meta-analysis,” Human Brain Mapping, Vol.12(2001): 1-19.一些模拟理论家声称这些过程支持了模拟的外显行为(或与之有神经关联)。(30)Marc Jeannerod & Elisabeth Pacherie, “Agency, Simulation, and Self-identification,” Mind and Language, Vol.19 No.2 (2004): 113-146.然而,内隐模拟理论家却主张这些亚个人过程自身只是对他人意向的模拟。比如加勒塞(Vittorio Gallese)认为,MNs的激活包含“自动、内隐和非自反性的模拟机制”(31)V. Gallese, “Being like Me: Self-other Identity, Mirror Neurons and Empathy,” Perspectives on Imitation, Vol.I, S. Hurley & N. Chater (ed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5, pp.101-118.。根据加勒塞的观点,主体对他人的共情体验在现象学层面是由大脑层面的“镜像匹配神经回路”的活动所支持的,对此他在功能水平上将其解释为“模拟程序,貌似是能够创建他人模式的过程”(32)V. Gallese, “The Shared Manifold Hypothesis: From Mirror Neurons to Empathy,”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Vol.8 (2001): 33-50.。据此假设,在外显的现象学层面上,主体不能外显地(有意识地)进行模拟;更确切来说,模拟过程完全停留在亚个人水平上。
围绕这一内隐的模拟观点目前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共识。让·德塞蒂(Jean Decety)和朱莉·格热泽(Julie Grèzes)以这种方式总结了里佐拉蒂(G.Rizzolatti)的立场:
在不执行动作的情况下,通过自动将行动者观察到的动作匹配到自身的动力指令系统上,然后观察者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开始放电以模拟行动者的观察行为,从而有助于理解被感知的行为。(33)J. Decety & J. Grèzes, “The Power of Simulation: Imagining One’s Own and Other’s Behavior,” Brain Research, Vol.1079 (2006): 4-14.
哥德曼(A.Goldman)将模拟区分为高水平的(外显式)“读心术”和低水平的(内隐式)“读心术”,后者是“简易、原初、自动的,并且很大程度上位于意识水平之下”,对应的原型是“模拟过程的镜像类型”。(34)A. Goldman, Simulating Minds: The Philosophy, Psychology and Neuroscience of Mindreading,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113,147.研究表明,MNs的激活不仅会模拟观察到的行为目标,也会模拟行为主体的意向,因此是一种“读心术”。MNs根据嵌入动作的语境和意向行为来辨别相同的动作。(35)L. Fogassi, P.F. Ferrari, B. Gesierich, S. Rozzi, F. Chersi & G. Rizzolatti, “Parietal Lobe: From Action Organization to Intention Understanding,” Science, Vol.308 (2005): 662-667; M. Iacoboni, I. Molnar-Szakacs, V. Gallese, G. Buccino, J.C. Mazziotta & G. Rizzolatti, “Grasping the Intentions of Others with One’s Own Mirror Neuron System,” PLoS Biology, Vol.3 No.3 (2005): 529-535.神经模拟过程也被用来解释我们如何理解他人的情绪和痛苦。(36)A. Avenanti & S.M. Aglioti, “The Sensorimotor Side of Empathy for Pain,” Psychoanalysis and Neuroscience, M. Mancia (ed.), Milan: Springer, 2006, pp.235-256.奥伯曼(L.M.Oberman)和拉马钱德兰(V.S.Ramachandran)通过很多证据证明镜像神经元系统作为一种内在模拟机制在自闭症的案例中是功能紊乱的(37)L.M. Oberman & V.S. Ramachandran, “The Simulating Social Mind: The Role of the Mirror Neuron System and Simulation in the Social and Communicative Deficits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133 No.2(2007): 310-327.,进而强化了“模拟神经元”负责理解动作、思想和情感的观点。
然而,在被称为“模拟”的亚个人镜像共振过程中尚存在几个概念性的问题。(38)S. Gallagher, “Simulation Trouble,” Social Neuroscience, Vol.2 No.3-4(2007): 353-365; S. Gallagher, “Logical and Phenomenological Arguments against Simulation Theory,” Folk Psychology Re-assessed, D. Hutto & M. Ratcliffe (eds.), Dordrecht: Springer Publishers, 2007, pp.63-78.因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亚个人过程,如MNs的激活,未能符合模拟论中的模拟概念。在该定义中,模拟过程包含两个基本方面: 首先,模拟涉及模型的工具控制,我们以之来理解不能直接理解的东西。第二,模拟包含了一种假设——即我们把自己的心理状态当成理解他人心理状态的模型。相反,亚个人镜像过程的确不具备工具特征,也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实际上它们是自动的并且由他人的行为所诱发。感知者不能激活和启动MNs并以此作为理解他人行为的手段;更确切地说,这是知觉启动中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感知到的动作会唤起这些神经元的激活。此外,由于MNs在自我行动时和他人行动时都会被激活,所以它们在关于谁是行动者方面是中立的。(39)F. de Vignemont, “The Co-consciousness Hypothesis,”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Vol.3 No.1(2004): 97-114; V. Gallese, “Being like Me: Self-other Identity, Mirror Neurons and Empathy,” Perspectives on Imitation, Vol.I, S. Hurley & N. Chater (ed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5, pp.101-118.因此,MNs并不包含需要区分谁是行动者的假设。因为本质上你我都未曾在MNs上登记。(40)N. Georgieff & M. Jeannerod, “Beyond Consciousness of External Events: A ‘Who’ System for Consciousness of Action and Self-consciousness,”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Vol.7(1998): 465-477.
这类问题促使对模拟程序进行一种弱化或最小限度的定义,该定义舍弃了工具化和假设的特征,只把模拟定义为一种简单的匹配形式。(41)A.I. Goldman & C.S. Sripada, “Simulationist Models of Face-based Emotion Recognition,” Cognition, Vol.94(2005): 193-213.然而,这种策略并不能解释应如何去理解那些从事着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活动或者体验着与我们相当不同的情绪的他人。例如,我可能看到有人以特殊的方式行动(比如捡起一只昆虫),并显然在享受它,而与此同时,我对这种行为感到十分厌恶,并做出了一个推开的手势。我的情绪状态和我的运动状态都与他人的相关状态不匹配,但我明显能体会到他/她的情绪和运动状态——它们实际上也激发了我自身的状态。此外,有神经科学证据表明,MNs的激活不必然包含运动系统执行和观察动作之间的精确匹配,但可能涉及“逻辑相关”的动作(如补充动作)或预测未来的动作。(42)G. Csibra, “Mirror Neurons and Action Observation: Is Simulation Involved?” ESF Interdisciplines, http://www.interdisciplines.org/mirror/papers/, 2005; M. Iacoboni, I. Molnar-Szakacs, V. Gallese, G. Buccino, J.C. Mazziotta & G. Giacomo Rizzolatti, “Grasping the Intentions of Others with One’s Own Mirror Neuron System,” PLoS Biology, Vol.3 No.3(2005): 529-535.上述所有内容都与MNs能模拟一切的观点背道而驰。
然而,否认镜像共振过程构成模拟程序的观点,并不是否认MNs在我们与他人的交互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因为它可能会有助于提升我们理解他人或保持持续的主体间关系的能力。MNs激活的另一种更简洁的解释是它构成了直接主体间知觉的神经关联部分。也就是说,铰接式的神经过程包含了不同感觉区域的激活,而且MNs在运动系统中的共振激活,构成了支持对他人意向行为的非铰接式直接感知的一部分,而非模拟他人意图的不同过程。(43)注意,MNs的激活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其对于意向的社会感知可能不够充分。例如,MNs最初是在猴子身上发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猴子具有和人类一样的社会感知能力。参见S. Gallagher, “Direct Perception in the Social Context,”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Vol.17(2008): 535-543。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需要把知觉当作一种生成过程(44)S.L. Hurley, Consciousness in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A. No⊇, Action in Percep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4; F.J. Varela, E. Thompson & E. Rosch, The Embodied Mi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 Cambridge: MIT Press, 1991.,当作包含了感觉-运动技能而不仅仅是感觉输入/加工,当作一种主动、熟练、具身化参与世界的方式,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来自环境的信息。在社会认知的背景下,当镜像共振过程是对他人行为的知觉时,将其视为知觉过程结构的一部分似乎是恰当的。因此,镜像激活不是模拟程序的开始;它朝向的是对他人行为的直接主体间知觉。根据这一解释,MNs的激活正确地符合了对主体间理解和交互的直接知觉解释,并有助于解释这种能力在婴儿期的某些具身实践中就已经发挥作用。这些带有情感的、感觉-运动的、非概念性的以及直接感知的实践,包含了对他人的感知意识并且构成了由知觉主体和被知觉他人共享的共同身体意向性。(45)S. Gallagher, “The Practice of Mind: Theory, Simulation, or Interaction?”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Vol.8 No.5-7(2001): 83-107; S. Gallagher, How the Body Shapes the Mi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结语
从社会认知的具身观点来看,他心并不是隐藏着的和不可通达的。当一个人在周围世界的交互情境中感知他人的行动和表述动作时,主体已经领会了他们的意图;所以没有必要对隐藏的心理状态(信念、欲望等)进行推断。当我看到他人的动作或手势时,我能明白(立即察觉到)它们蕴含的意义;并且在我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我自己的行为和反应有助于构建这种意义。我不仅能看到,而且能对他人的喜悦或愤怒,或对其面部表情、姿势、手势或动作中传达的意图产生共鸣(或对立)和回应。
这种对MNs神经科学可替代性的、非模拟论的解释与更大规模的非心智理论主义、社会认知的交互视角相一致。这种视角认为,在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进行理论推理、模拟、解释或预测之前,我们已经处于依据他人的情境化表达、手势和目的性动作来反映他们的意图和情绪的交互和理解过程之中,这已得到来自发展研究和神经科学等学科证据的支持。对于他人是否关注我们、如何对待我们和他人、其意图是否友好等等的感受,我们已经有了具体的基于感知的理解;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需要在个人层面上对他人的想法或欲望进行理论推理或模拟。此外,我们需要明白把亚个人水平视为模拟或推理的额外认知步骤,没有任何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