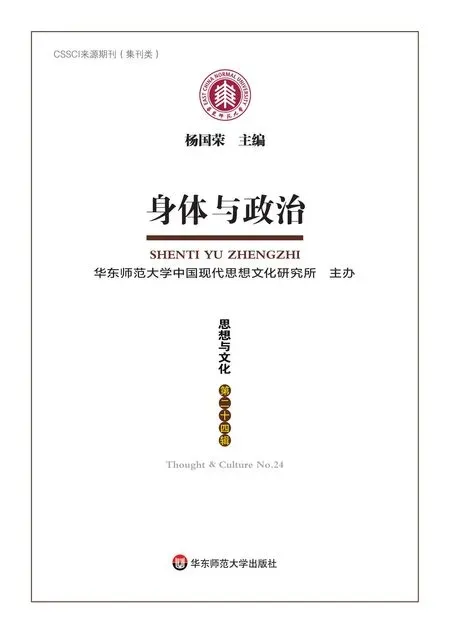公羊学与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特点*
——以“王鲁”说为中心
上古时容有“存二王后”之古制,公羊家由此发挥出“通三统”之义。对此,皮锡瑞《春秋通论》云:
存三统尤为世所骇怪,不知此是古时通礼,并非《春秋》创举。以董子书推之,古王者兴,当封前二代子孙以大国,为二王后,并当代之王为三王;又推其前五代为五帝,封其后以小国;又推其前为九皇,封其后为附庸;又其前则为民。殷周以上皆然。然则有继周而王者,当封殷周为二王后,改号夏禹为帝。《春秋》托王于鲁,为继周者立法,当封夏之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封周之后为二王后,故曰绌周。此本推迁之次应然。《春秋》存三统,实原于古制。逮汉以后,不更循此推迁之次。人但习见周一代之制,遂以五帝、三王为一定之号,于是《尚书》不传舜乃称王。解者不得其说,《周礼》先、后郑注引九皇、六十四民,疏家不能证明,盖古义之湮晦久矣。晋王接、宋苏轼、陈振孙,皆疑黜周王鲁,《公羊》无明文,以何休为《公羊》罪人。不知存三统明见董子书,并不始于何休。《公羊》传虽无明文,董子与胡毋生同时,其著书在《公羊》初著竹帛之时,必是先师口传大义。据其书,可知古时五帝、三王,并无一定,犹亲庙之祧迁。后世古制不行,人遂不得其说。(1)皮锡瑞: 《经学通论·春秋》,《皮锡瑞全集》第六册,北京: 中华书局,2015年,第500页。
汉以后,儒者颇攻驳“通三统”之说,至于其中“王鲁”之说,更以为僭越莫甚,深悖于儒家所持之君臣大义。对此,皮锡瑞推本董仲舒之说,以为“通三统”不独为公羊家所发,实属古代王朝之旧典也。盖每当异姓鼎革之际,新王之于前朝,或绌或存,或新或故,皆封为大国而为二王之后,其旨则在明新王受命于天,且当上法先圣也。
其后,汉廷颇用“通三统”说。据《汉书·梅福传》,武帝时,始封周后姬嘉为周子南君;至元帝时,尊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位次诸侯王。又使诸大夫博士求殷后,然“绝不能纪”。其时匡衡议以孔子世为殷后,曰:
王者存二王后,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统也。其犯诛绝之罪者绝,而更封他亲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义,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绝。今宋国已不守其统,而失国矣,则宜更立殷后为始封君,而上承殷统,非当继宋之绝侯也,宜明得殷后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入远不可得;虽得其嫡,嫡之先已绝,不当得立。《礼记》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师所共传,宜以孔子世为汤后。(2)班固: 《汉书·梅福传》,北京: 中华书局,2016年,第2926页。
可见,当时朝廷皆以《公羊》“存二王后”之说为然,且已先封周后为周承休侯矣。至于殷后,则因“分散为十余姓,郡国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孙,绝不能纪”,故匡衡主张别立孔子后人为商汤之后。然元帝以其语“不经”,遂罢其议。
至成帝时,梅福复议宜封孔子后以奉汤祀,曰:
武王克殷,未下车,存五帝之后,封殷于宋,绍夏于杞,明著三统,示不独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迁庙之主,流出于户,所谓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汤不祀,殷人亡后,陛下继嗣久微,殆为此也。《春秋经》曰:“宋杀其大夫。”《穀梁传》曰:“其不称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之后也,虽不正统,封其子孙以为殷后,礼亦宜之。何者?诸侯夺宗,圣庶夺嫡。《传》曰:“贤者子孙宜有土”,而况圣人,又殷之后哉!……今仲尼之庙不出阙里,孔氏子孙不免编户,以圣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诚能据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孙,则国家必获其福,又陛下之名与天亡极。何者?追圣人素功,封其子孙,未有法也,后圣必以为则。不灭之名,可不勉哉!(3)班固: 《汉书·梅福传》,第2925页。
梅福不仅重申了匡衡以孔子后人为殷后的主张,而且提出“圣庶夺嫡”的新说,即以孔子虽非商汤的嫡嗣,但因其有作《春秋》的“素功”,故宜为殷后。
其后,至成帝绥和元年,诏曰:“盖闻王者必存二王之后,所以通三统也。昔成汤受命,列为三代,而祭祀废绝。考求其后,奠正孔吉。其封吉为殷绍嘉侯。”三月,又进殷绍嘉侯、周承休侯皆为公,地各百里。(4)班固: 《汉书·成帝纪》,北京: 中华书局,2016年,第328页。至东汉建武十三年,封绍嘉公孔安为宋公,周承休公姬武为卫公。(5)范晔: 《后汉书·光武帝纪》,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61页。对此,王葆玹论曰:“穀梁学派如果有思想建树的话,那就是改造孔子‘素王’的理论,放弃极度流行的‘王鲁’说,提出孔子为殷王后裔的新说,并在成帝时促使朝廷正式封孔子‘世为殷绍嘉公’。”(王葆玹: 《西汉经学源流》,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2008年,第178页。)据王氏此说,则此时朝廷封孔子后裔为殷后,并非纯用《公羊》说,而是糅合了《穀梁》的某些理论。
不独汉人尊用“通三统”义,后世朝廷亦颇能行此义者。清末苏舆有论曰:
汉自为一代,上封殷、周,不及夏后,正用此绌夏、故宋、新周之说。……我朝康熙三十八年,圣祖致奠明陵,谕曰:“古者夏殷之后,周封之于杞宋,即今本朝四十八旗蒙古,亦皆元之子孙,朕仍沛恩施,依然抚育,明之后世,应酌授一官,俾司陵寝。”全祖望《三后圣德诗·置恪篇》云:“三统之礼,发自遗经,以存三微,其义最精。”舆谓绌夏、亲周、故宋,犹今云绌宋、新明、故元。古者易代则改正,故有存三统、三微之说,后世师《春秋》遗意,不忍先代之遽从绌灭,忠厚之至也。(6)苏舆: 《春秋繁露义证·三代改制质文》,北京: 中华书局,1992年,第191页。
则康熙帝之施恩于元、明后裔,亦有用“通三统”之政治自觉也。
然“通三统”之说,其于《公羊》诸义理中,最为复杂,其中尤以“王鲁”之义最似骇怪,故后儒之集矢《公羊》者,大多于此。
一、 《公羊》旧义及后人对“王鲁”说的批评
历来治《公羊》者,其说颇有异同,盖自汉时已然,遑论晋、唐以降也。至清嘉、道间,《公羊》再兴,其代表人物刘逢禄本以“述何”为大旨,然又有“匡何”之举,遂启晚清《公羊》学之转变,即由“述何”而至“宗董”也。其后,朱一新、苏舆等保守派学者深憾于康有为变政之祸,乃据董仲舒之说以驳何休以降《公羊》说之讹谬。然今考董、何之论,虽未尽合符节,然就王鲁、三统诸说而论,实无有异焉,足可视为《公羊》旧义也。至于康有为所据以变政者,则纯属于其创说新见也。
何休以“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为通三统。此说颇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其理本为显豁,且非独公羊家所主,亦旁见于《论语》、《礼记》诸书。至于其中又有黜周王鲁之说,则诚属汉人意见,盖欲以《春秋》当一王之法而闰秦统也。且孔子有德无位,是以公羊家又不得不造为黜周、王鲁之说,借此而行黜陟当世大人之事,此所以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也。
然此义虽显豁,而书法则颇曲折,尤涉僭妄,且不见于传文,故后人诋之汹汹。晋王接首发此议,谓“黜周王鲁,大体乖硋”。其后,宋苏轼、陈振孙皆祖此说,谓《公羊传》无明文,至以邵公为《公羊》罪人。(7)参见陈澧: 《东塾读书记》卷十,清光绪八年刻本。清苏舆亦谓邵公实异于董子,谓董子“引《春秋》‘杞子’,乃借以证兴礼之意”,非真欲黜周也。
1. 新周与故宋
“新周”之说,唯见于《公羊》宣十六年传文。董子《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有“亲周”与“亲赤统”、“亲黑统”之文。据此,卢文弨以为,“新周”当作“亲周”。又据《史记·孔子世家》,其中亦谓“据鲁,新周,故殷,运之三代”,可见,史公亦作“亲周”也。
“亲周”之义,较邵公“新周”,似为显豁。盖史公谓“据鲁,于周则亲,于宋则故”,犹三世之异辞,乃据与己身之亲疏远近而不同故也。司马贞《索隐》云:“时周虽微,而亲周者,以见天下之有宗主也。”据此,亲周者,盖孔子是鲁人,又据鲁事而书,故于周为亲也,甚至犹能宗周也,则绝无黜周王鲁之义焉。
此说虽合于孔子尊王之义,然未必得汉人尊《春秋》之旨。今考董仲舒《春秋繁露》,其中明有黜周之文:
《春秋》上绌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春秋》当新王者奈何?曰: 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故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统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农为九皇,而改号轩辕谓之黄帝,因存帝颛顼、帝喾、帝尧之帝号,绌虞而号舜曰帝舜,录五帝以小国。下存禹之后于杞,存汤之后于宋,以方百里,爵号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而殷周为王者之后,绌夏,改号禹谓之帝禹,录其后以小国。故曰: 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8)苏舆: 《春秋繁露义证·三代改制质文》,第198—199页。
据董子说,既以《春秋》当新王,不得不黜周也。且不独黜周,至于上古之五帝、三皇,亦各黜有差,而极于六十四民而已。观乎后世“存二王后”之典,则每当新朝建立,必有黜前朝之事。今以《春秋》当新王,自当黜周,又何疑焉!故就“亲周”之文而言,则孔子犹尊周为既王也;若就“新周”之文而言,则周不再为王,而据《春秋》封为大国,即邵公“使若国文”之说,“新周”即“黜周”也。可见,“亲周”与“新周”,其义正相反,汉人不可能相混淆若此。
“故宋”二字,不见于《公羊传》,而出于桓二年《穀梁传》文:“其不称名,盖为祖讳也。孔子故宋也。”范甯注云:“孔子旧是宋人。”此说显与《公羊》义不同。又,昭八年《穀梁传》云:“外灾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杨士勋疏引徐邈语:“《春秋》王鲁,以周公为王后,以宋为故也。”徐邈盖用《公羊》黜周王鲁之说,然范甯非之,曰:“故犹先也,孔子之先,宋人。”
可见,《穀梁传》中“故宋”之说,实未必有公羊家“存二王后”之义。故章太炎以为,公羊家之说“故宋”,实由误读《穀梁》文所致也。(9)参见钱穆: 《国学概论》,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98页。另参见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刘师培《论孔子无改制之事》相关章节。
因此,公羊家“通三统”之说,虽语涉玄怪,且无文字之凭依,然实由“存二王后”之旧典而来,不可谓为无据。其义则大致有二:
其一,王者必尊贤,尊贤则所以法古,法古所以奉天也,故存往昔故事以备后王取法,此其一也。
其二,王者尊贤不过二代,故封二王后为大国,则自有亲、有故、有绌。公羊家以《春秋》当一新王,则周为胜国,于周为黜,为鲁之宗国则为亲,于三统之序则为新;至于宋,为殷后之大国,于孔子为故,于新封之周为故,于三统之序为故;至于夏,则绌为小国,不为师法者矣。(10)左氏以“绌夏”为绌杞。庄二十七年,春,杞子来朝。《左传》曰:“用夷礼,故曰子。”此左氏之绌杞也。此说全无“通三统”意味。
其实,《公羊》说与《穀梁》、《史记》之说略可相通。盖古礼之祭祖,新死者为鬼,此为新周也;新鬼于生者为亲,旧鬼自疏,此为故宋也;天子止立四亲之庙,庶人叙亲亦不过高祖,则高祖以上旧鬼不专祭矣,此为绌夏。可见,王者尊前朝为先圣之后,或出于祭祀亲故之礼,盖以庙、祧待亲故,而以坛、墠绌小国。非独此也,至于新君即位,例有封赏,亦莫不循此亲、故、绌之义焉。
2.新王与素王
“新王”本指世俗之王,然公羊家以《春秋》当之,此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也。然公羊家本意不过以孔子作《春秋》,后世凛遵之,遂成一世王法,乃造为“以《春秋》当新王”之说。是说实未足怪,诚近理也。汉人又将之与三统、五德说相糅合,而夺秦黑统以予《春秋》,乃为可怪也。而尤可怪者,汉人又兼采图谶之说,如邵公谓孔子“却观未来,豫解无穷”,遂作《春秋》。诸如此论,不独于发明经义无益,反致其常识近理处亦湮没不显,且致人以诽谤之口实耳。
“《春秋》当新王”之说,《公羊传》无明文,然其说实可征于董子说,而其义亦可求诸传文。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公羊传》云:
君子曷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
此言“制《春秋》之义俟后圣”,即汉人谓孔子为后世制法之义,亦即“《春秋》当新王”之说也。其前,孟子谓《春秋》乃“天子之事”,又有知我、罪我之说,皆为新王说张本也。
至董仲舒,则发明“《春秋》当新王”之义尤明白。(11)参见曾亦、郭晓东: 《春秋公羊学史》,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3—325页。其后两汉数百年间,以《春秋》当新王,是说殆成共识矣。《淮南子·主术训》云:“孔子……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锄丑,以成王道,论亦博矣。”《淮南子·泛论训》云:“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说苑·君道》篇云:“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道不亡,周德不作;周道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君子知周道亡也。”《论衡·超奇篇》云:“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则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诸子之传书,素相之事也。观《春秋》以见王意,读诸子以睹相指。”《论衡·问孔》篇云:“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夫子自伤不王也。己王,致太平;太平则凤鸟至,河出图矣。今不得王,故瑞应不至,悲心自伤,故曰‘吾已矣夫’。”《论衡·对作》篇云:“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末之善,贬纤芥之恶,拨乱世,反诸正。人事浃,王道备,所以检柙靡薄之俗者,悉其密致。夫防决不备,有水溢之害;网解不结,有兽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则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论衡·定贤》篇云:“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按《春秋》虚文业,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圣人也。……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可见,新王说不独为公羊家所主,且为汉人之普遍意见也。
是故何休取此说以注《公羊传》,良有以也。庄二十七年,杞伯来朝。《解诂》云:“《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灾。《解诂》云:“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可见,邵公明取汉人意见注《公羊传》也。
至于“素王”一词,始见于《庄子·天道》:
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明此以南乡,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
郭象注云:“有其道,天下所归,而无其爵者,所谓素王自贵也。”后世说“素王”者,皆取此义焉。(12)又据《史记·殷本纪》:“汤命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司马贞云:“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质素,故称素王。”此说似不取通常“有道无爵”之义,且不必指孔子也。康有为则别有一说,谓“素者,质也”,故“质家则称之素王,文家则称为文王。《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故《春秋纬》多言素王。而《公羊》首言文王者,则又见文质可以周而复之义也”,则素王与文王,俱就孔子改制而言,其义一也。(康有为: 《孔子改制考》卷九,《康有为全集》第三集,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5页。)
孔子为素王之说,盖由《公羊传》哀十四年“西狩获麟”文而来,然其义则可由孔子改制、以《春秋》当新王之义寻而致。汉人既以《春秋》当一代王法,则孔子当为王矣;然孔子有德无位,则又不过为素王矣。后儒非议素王之说,盖以《传》无素王之文,且孔子有僭越之嫌也。然考诸董子书,实有明文。
《汉书·董仲舒传》载董子《贤良对策》语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以万事,见素王之文焉。”又云:“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而《春秋繁露·符瑞》则云:“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而董子于《三代改制质文》历陈殷、周受命而王之事,又继之以《春秋》,则《春秋》之为王,其受命无异于殷、周新王。凡此诸说,皆以孔子为素王而行改制之事也。
《春秋》当新王,则孔子受命亦一如真王,必有受命之符焉。故西狩获麟,此受命之符也;孔子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孰为来哉”,则自居素王矣。后世谓孔子避制作之僭,以为不过汉人尊孔所致,孔子实未自居素王也。然考孔子之行迹与言语,不可谓无素王之志也。今据《论语》之文,孔子过宋,自谓“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厄于匡,则自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而孟子述孔子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者,天子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下》)可见,孔子既行王者改制之实,亦有王者之志焉。
素王之说,亦见于纬书。《孝经纬·钩命诀》云:“曾子撰斯,问曰:‘孝文乎驳不同何?’子曰:‘吾作《孝经》,以素王无爵禄之赏,斧钺之诛,故称明王之道。’曾子辟席复坐。子曰:‘居,吾语汝。顺逊以避祸灾,与先王以托权。’”《春秋元命苞》云:“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当兴也。”《春秋演孔图》云:“圣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显天心。丘为木铎,制天下法。”又云:“丘为制法之主,黑绿不代苍黄。”此皆纬说也。
至于古文家,亦习为此论矣。贾逵《春秋》序云:“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又,郑玄《六艺论》云:“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今、古文家言素王如此。又,《中论·贵验》曰:“仲尼为匹夫,而称素王。”《风俗通·穷通》曰:“制《春秋》之义,着素王之法。”《说苑·贵德》曰:“是以孔子历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于全育,烝庶安土,万物熙熙,各乐其终。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泽不洽。于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后人,思施其德,未尝辍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诵其文章,传今不绝。”王充言素王尤伙。《论衡·定贤》曰:“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论衡·问孔》云:“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夫子自伤不王也。己王,致太平;太平则凤鸟至,河出图矣。今不得王,故瑞应不至,悲心自伤,故曰‘吾已矣夫’。”《论衡·定贤》云:“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按《春秋》虚文业,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圣人也。……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可见,孔子为素王,不独为公羊家所主,诚为汉人之普遍意见也。至杜预,始疑此说非通论矣。
杜预以后,疑孔子素王之说者甚多。孔颖达《左传正义》云:
《孔子家语》称齐大史子余叹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无位而空王之也。彼子余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号为素王。先儒盖因此而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
汉儒多谓仲尼实以素王自号,杜、孔乃力辟此说。皮鹿门虽主《公羊》,亦谓此说有自蹈乱臣贼子之嫌。其《春秋通论》云:
素,空也,谓空设一王之法也,即孟子云“有王者起,必来取法”之意,本非孔子自王,亦非称鲁为王。后人误以此疑《公羊》,《公羊》说实不误。(13)皮锡瑞: 《经学通论·春秋》,《皮锡瑞全集》第六册,第492页。
可见,皮氏盖用杜、孔之说,以为唯其如此,素王之义,乃畅通无碍矣。
然素王之说,后儒多集矢于邵公,以为僭窃悖谬之说,孰不知是说本汉儒旧说,且可上推至仲舒也。清末康有为遂假仲舒以明改制之义曰:
自汉前莫不以孔子为素王,《春秋》为改制之书,其他尚不足信,董子号称醇儒,岂为诞谩?而发《春秋》“作新王”、“当新王”者,不胜枚举。若非口说传授,董生安能大发之?出自董子,亦可信矣。(14)康有为: 《春秋董氏学》卷五,《康有为全集》第二集,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66页。
可见,孔子为素王,实以其《春秋》有改制之功而当一代王法也。
3. 王鲁
“通三统”诸义中,尤为后儒所诋议者,则在王鲁黜周之说。鲁本侯国,周实天子,而《春秋》乃礼义之大宗,故若造为此说,则僭越莫甚焉。
案“王鲁”之说,《公羊传》无明文,而邵公《解诂》则颇言之。(15)相关论述从略,参见曾亦、黄铭: 《董仲舒与汉代公羊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3—217页。公羊家又别有改元之说,以证王鲁之义。孔颖达《左传正义》引刘炫难何休语云:
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若然,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鲁得称元,亦应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托王于鲁,则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
盖邵公明言惟王者得改元,而《春秋》王鲁,虽得改元,然不得改正朔,仍奉周正。据皮鹿门所云,则鲁之改元实假托,非实事耳。而孔氏《正义》既非刘炫,亦非公羊说,谓“诸侯于其封内各得改元”,“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托王改元,是妄说也”。蒙文通据此,遂谓诸侯改元而事社稷,犹天子改元而事天地也。
然王鲁之说本出自董子。(16)康有为谓:“公羊传《春秋》托王于鲁,何注频发此义,人或疑之,不知董子亦大发之。”(康有为: 《春秋董氏学》卷五,《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367页。)《三代改制质文》篇云:
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新周,故宋。
《奉本》篇云:
今《春秋》缘鲁以言王义,杀隐、桓以为远祖,宗定、哀以为考妣。
可见,“王鲁”说本公羊家之旧义也。
董子之后,汉人颇言王鲁之义。王充《论衡·超奇》篇云:“长生说文辞之伯,文人之所共宗,独记录之,《春秋》纪王于鲁之义也。”《指瑞》篇云:“夫麟为圣王来,孔子自以不王,而时王鲁君无感麟之德。”又,《越绝书·德序外传》云:“夫子作《春秋》,记元于鲁,大义立,微言属。”《吴人内传》云:“孔子作《春秋》,方据鲁以王,故诸侯死皆称卒不称薨,避鲁之谥也。”许慎《五经异义》云:“今《春秋公羊》说,诸侯曰薨,赴于邻国,亦当称薨。经书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鲁,故称卒以下鲁也。”则汉人尚未以王鲁说为可怪也。
又,《史记·孔子世家》云:
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
司马贞《索隐》云:“言夫子修《春秋》,以鲁为主,故云据鲁。”则王鲁者,据鲁也,即据鲁史记而作《春秋》之义。此说显与公羊家说不同。
汉以后,指斥“王鲁”说者颇多。(17)参见曾亦、郭晓东: 《春秋公羊学史》,第338—340页。然“王鲁”说本出于“新王”说。刘逢禄曰:
王鲁者,则所谓以《春秋》当新王也。夫子受命制作,以为托诸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引史记而加乎王心焉。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制新王之法以俟后圣,何以必乎鲁?曰: 因鲁史之文,避制作之僭。祖之所逮闻,惟鲁为近,故据以为京师,张治本也。(18)刘逢禄: 《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王鲁例》,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52页。
盖《春秋》当新王,其义甚明,然则何以据鲁而有王鲁之怪辞?逢禄以为,“托诸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此其一也;“因鲁史之文,避制作之僭”,此其二也。
又,《礼记·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可见,鲁僭用王礼久矣,其君臣上下皆习焉而不察,则鲁实颇存王礼也。段熙仲据此而论曰:
孔子托王于鲁,以其文献足征,人事浃备,可以见王法,可以明王道,故据鲁而托之,因以正其是非。初献六羽,犹可言也,则正之;八佾,僭天子,不可言者,则讳之。何以讳?以其非礼也。惟鲁之行事可以决嫌疑,正是非。所谓因其可托而托之,非遂王鲁也,若王就鲁之行事以见王法云尔。史公闻此义于董生,此真《公羊》先师之传,非何君一人之私言也。(19)段熙仲: 《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73—474页。
孔子尝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则鲁虽僭,然王礼犹备于此,亦孔子“我爱其礼”之意焉。段氏此说,颇与诸家异,与史公、邵公之说亦未必尽同也。
盖王鲁与《春秋》当新王、孔子素王之说,义虽相关,然旨有不同。《春秋》当新王,乃孔子改制之本怀,《论语》备述孔子损益四代之制,斯其义也。至于素王之说,虽实汉人尊孔以夺秦统故也,然孔子颇以周文自任,观乎《论语》,信乎斯言也。而王鲁黜周之说,孔子虽有“鲁一变至于道”之言,然绝无以鲁继周之义。《春秋》所以假鲁位号者,盖托王以明义也;又因鲁史记以明王义,王鲁实书法之方便,不如“见诸行事之博深切明”耳。故《春秋》一则王鲁,一则许周实天子也,故其称道桓、文,以其能尊周天子也,又屡有讳鲁僭越之文。故刘申受曰:“《春秋》之托王至广,称号名义仍系于周,挫强扶弱常系于二伯,何尝真黜周哉?”(20)刘逢禄: 《刘礼部集》卷四,《释三科例》,光绪十八年延晖承庆堂主刻本。皮鹿门亦曰:“《春秋》藉位于鲁,以托王义。隐公之爵,不进称王;周王之号,不退为公。”(21)皮锡瑞: 《经学通论·春秋》,《皮锡瑞全集》第六册,第523页。可见,邵公非真黜周也。即便王鲁,亦不必黜周也。
逢禄又曰:
郊禘之事,《春秋》可以垂法,而鲁之僭,则大恶也。就十二公论之,桓、宣之弑君宜诛,昭之出奔宜绝,定之盗国宜绝,隐之获归宜绝,庄之通仇外淫宜绝,闵之见弑宜绝,僖之僭王礼、纵季姬祸鄫子,文之逆祀、丧娶、不奉朔,成、襄之盗天牲,哀之获诸侯、虚中国以事强吴,虽非诛绝,而免于《春秋》之贬黜者,鲜矣。何尝真王鲁哉?(22)刘逢禄: 《刘礼部集》卷四,《释三科例》。
若如刘氏所云,王鲁只是托王而已,未必真王鲁也。皮氏则以为,逢禄“黜周王鲁非真”之语,正明假借之义也。
所谓假借,即借事明义也。刘申受谓:“《春秋》之义,犹六书之假借。”(23)刘逢禄: 《刘礼部集》卷四,《释三科例》。对此,皮鹿门《春秋通论》言之极详明,曰:
鲁隐非真能让国也,而《春秋》借鲁隐之事,以明让国之义;祭仲非真能知权也,而《春秋》借祭仲之事,以明知权之义;齐襄非真能复仇也,而《春秋》借齐襄之事,以明复仇之义;宋襄非真能仁义行师也,而《春秋》借宋襄之事,以明仁义行师之义。所谓见之行事,深切著明,孔子之意,盖是如此。故其所托之义,与其本事不必尽合,孔子特欲借之以明其作《春秋》之义,使后之读《春秋》者,晓然知其大义所存,较之徒托空言而未能征实者,不益深切而著明乎!三传惟《公羊》家能明此旨,昧者乃执《左氏》之事,以驳《公羊》之义,谓其所称祭仲、齐襄之类,如何与事不合,不知孔子并非不见国史,其所以特笔褒之者,止是借当时之事,做一样子,其事之合与不合,备与不备,本所不计。孔子是为万世作经,而立法以垂教,非为一代作史,而纪实以征信也。(24)皮锡瑞: 《经学通论·春秋》,《皮锡瑞全集》第六册,第520—521页。
又曰:
黜周王鲁,亦是假借。……《春秋》王鲁,故得改元。托王非真,故虽得改元,不得改正朔。……刘氏(逢禄)谓黜周王鲁非真,正明其为假借之义。(25)皮锡瑞: 《经学通论·春秋》,《皮锡瑞全集》第六册,第520页。
故“借事明义”者,可谓《春秋》书法之大纲。《春秋》之为经,而不为史,正在“借事明义”之书法也。然“借事明义”之说,实承董子、史公而来。《春秋繁露·俞序》云:
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见王公。史记十二公之间,皆衰世之事,故门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号,以正人伦,因其成败,以明顺逆。”(26)苏舆: 《春秋繁露义证》,第159—160页。
清王念孙云:“行事,即往事也。”故因行事而加王心,即孔子据鲁史记旧文,而明王义也。孔子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着明”(《太史公自序》),正谓此也。对此,皮氏《春秋通论》云:
必明于《公羊》借事明义之旨,方能解之。盖所谓见之行事,谓托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以明褒贬之义也。孔子知道不行而作《春秋》,斟酌损益,立一王之法以待后世。然不能实指其用法之处,则其意不可见,即专著一书,说明立法之意如何,变法之意如何,仍是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使人易晓。犹今之大清律,必引旧案以为比例,然后办案乃有把握。故不得不借当时之事,以明褒贬之义。即褒贬之义,以为后来之法。(27)皮锡瑞: 《经学通论·春秋》,《皮锡瑞全集》第六册,第520页。
此段发挥《春秋》王鲁义甚是明晓。
苏舆虽颇非邵公,然亦明假借之义,曰:
缘鲁言王义者,正不敢自居创作之意。孔子曰:“其义窃取。”谓窃王者之义以为义也。托鲁明义,犹之论史者借往事以立义耳。圣人以明王之治,期于拨反,故义曰王义,心曰王心,化曰王化,言曰王言,意曰王意,道曰王道,事曰王事,制曰王制,法曰王法。(28)苏舆: 《春秋繁露义证》,第280页。
盖苏氏疑邵公王鲁说有实尊鲁为王、黜周为公侯之疑,故用“托鲁明义”之说以释疑也。
廖平则区别素王与王鲁,曰:
是《公羊》旧说,主素王而不主王鲁也。王鲁之说,始于董子,成于何君。董子《繁露》言《春秋》有王法,其意不可见,故托之于王鲁云云。何氏因之,遂专主其说。按董子立义依违,首改素王之义,以为托鲁之言。此董子之误,后贤当急正之者也。且其说以王意不可见,乃托之王鲁。托者,假托,实以素王为本根,王鲁为枝叶。因王意不见,乃假王鲁以见素王之义。是董子之言王鲁者,意仍主素王也。(29)廖平: 《何氏公羊春秋三十论》,载李耀仙编: 《廖平选集》下册,成都: 巴蜀书社,1989年,第141页。
廖氏又谓“《公羊》本素王,因素王之义遂附会以为王鲁是也。有震警张惶之色,乃过情虚拟之词”(《今古学考》),“《公羊》精微,具见纬候,凡在枝节,莫不具陈。而王鲁全经大纲,纬书并无其语,而言素王与孔子主王法、乘黑运者,不下三四十见,此可见本素王而不王鲁矣”(《公羊解诂十论》)。可见,《春秋》新王说本不可怪,而素王说乃可怪;素王说犹未可怪,而王鲁说乃真可怪也。后儒乃为哓哓置辩,盖以此也。
然其弟子蒙文通颇不以改制之说为然。其曰:
以何休之义言之,改制之说推本于王鲁,王鲁之说推本于隐公元年。以为诸侯不得有元年,鲁隐之有元年,实孔子王鲁之义,亦即改制之本。然《左氏》称惠之二十四年、惠之十八年,《晋语》自以献公以下纪年,诸侯之得改元,《春秋》著其实。《白虎通义·爵篇》谓“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诸侯改元,即事社稷”,则礼家断其义,安在隐公元年即是王鲁,而衍其说于改制?故改制者,实不根之说,非经学之本义也。郑玄《起废疾》于“岁则三田”之说,以为孔子虚改其制而存其说于纬,则康成亦言改制,又安在改制独为今文之大义微言?由改制故言托古,改制之事不实,则托古之说难言。(30)蒙文通: 《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蒙文通文集》卷三,成都: 巴蜀书社,2015年,第106—107页。
可见,王鲁说本承孔子改制之义而来。蒙氏此论,盖借此而非长素“托古改制”之说也。
二、 “王鲁”本义及康有为建立孔教的政治内涵
汉人视孔子为“素王”。是说本由《公羊传》哀十四年“西狩获麟”一段而来,然其义则可由“《春秋》当新王”之说寻而致。至董仲舒书,始有明文。其《贤良对策》有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以万事,见素王之文焉。”至其《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则历陈殷、周受命而王之事,又继以《春秋》,则《春秋》为新王,其受命亦无异于殷、周之代兴也。公羊家既视《春秋》为新王,则孔子受命亦如“真王”,必有受命之符矣。故西狩获麟,公羊家以为受命之符,而孔子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孰为来哉”,则自居“素王”矣。
后世谓孔子避制作之僭,以为不过汉人尊孔所致,实未自居“素王”。然考孔子一生行迹与言语,不可谓无“素王”之志也。今据《论语》所载,孔子过宋,自谓“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畏于匡,则自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而孟子述孔子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者,天子之事也。”可见,孔子既行王者改制之实,亦有王者之志焉。
汉人又有素臣、素相、素功之说。杜预《左传集解序》谓汉人以孔子为素王、左丘明为素臣。如《论语谶》云:“子夏曰:‘仲尼为素王,颜渊为司徒。’”又,《论衡·超奇》亦曰:“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则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诸子之传书,素相之事也。观《春秋》以见王意,读诸子以睹相指。”又据《汉书·梅福传》,梅福习《穀梁》,然上疏称孔子有“素功”,故其子孙宜封为殷后。此说正发明《公羊》“有君而无臣”之义,以为圣人作《春秋》以垂王法,亦当有贤臣佐其业,则后世儒士著书立说以匡其君,正素臣之事也。
案,孔子本志在效法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王,则孔子欲为“真王”,虽于《论语》中稍露其迹,则真“微言”也。然此意不宣于《春秋》,盖孔子晚年不复梦见周公,则“真王”之志已衰,乃作《春秋》以为汉制,此实“素王”之业也。故孔子实自居“素王”也,汉儒知其意,亦尊其为“素王”。且自汉而言,尊孔子而用孔子所改之制,又何所忌讳耶?故“素王”之说,于汉尚不为微言也。而孔子及身又执持“大义”以褒贬当世大人,恐触时忌,遂为微辞故也。故汉人所谓“微言”者,正在此也。
唯自汉以后,始有疑“素王”之说,如孔颖达《左传正义》云:
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语》称齐大史子余叹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无位而空王之也。彼子余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号为素王。先儒盖因此而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
据此,汉人尚谓孔子为“素王”,故“素王”不为微言。唯后儒以为“素王”乃孔子以素衣之身而窃取立法之权,立“一王之法”,赏善罚恶,“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可谓僭越莫甚。则“素王”之说,亦为君主独尊时代所不容,故乃指为“微言”也。
康长素于此言之甚明,曰:
自汉前莫不以孔子为素王,《春秋》为改制之书,其他尚不足信,董子号称醇儒,岂为诞谩?而发《春秋》作新王、当新王者,不胜枚举。若非口说传授,董生安能大发之?出自董子,亦可信矣。(31)康有为: 《春秋董氏学》卷五,《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366页。
可见,孔子为素王,实以其《春秋》有改制之功而当一代王法也。
至于孔子所以改制者,不过惩于周制之崩坏,乃折衷虞、夏、殷、周四代之制,以成“一王之法”,盖本欲以施行于当世也。可见,孔子改制,非如汉儒所谓“为汉制法”,亦非如后儒所言“为万世制法”也,究其本意,实欲为时王制法而已。虽若鲁定、哀之微弱,及齐景、卫灵之中材,孔子犹期于一试。虽然,此犹下策,盖不得已而谋合作于时君也。(32)《论语》颇载孔子此类自期叹恨之语,如《论语·子路》:“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可见孔子制法,本欲自试,或假君权以行道。唯晚年归鲁,知己之不得真王,乃托《春秋》而行素王之事,诚不得已也。今考孔子一生行事,实欲上效成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建国,赏善罚恶,而终取天下也。故司马迁列孔子于世家,盖深知孔子之志在建国也。
盖孔子之先,乃宋愍公之嫡子弗父何,本当有国而让与其弟,则孔子亦世家之胤也。(33)案,《公羊传》颇褒国君让国之德,如鲁隐公、宋宣缪、卫叔武、吴季札之让是也,又于曹公子喜时、邾娄叔术之让国,著其子孙亦当有国也。故孔子以先祖之让国,则其有国实合乎《春秋》之义也。殇公时,孔子六世祖孔父嘉被杀,其后防叔奔鲁,遂降为士籍,则失国矣。至鲁定公,孔子得为中都宰,后进于司空,至为大司寇,并摄行相事。时孔子有喜色,盖喜其始能得国行道也。当是时也,“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34)司马迁: 《史记·孔子世家》,北京: 中华书局,2013年,第2311页。。盖孔子以新法治鲁,则鲁将“一变至于道”,而成“王道乐土”也。齐人闻而惧,乃归鲁女乐,而孔子知其法终不行,遂去鲁,期于他国而行其道也。其后十数年间,孔子栖栖遑遑,奔走于列国,其志不过期为时君所用,而伸其昔日在鲁未遂之志。可见,孔子晚年作《春秋》而寓新法,然其规模尝大略施行于鲁矣,惜乎未曾真有国耳。
孔子所行道,见于《春秋》之改制。孔子改制之实,则损周文而益殷质,至于折衷虞、夏、殷、周四代古制。既有改制之实,则又当自神其道,故《中庸》曰:“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古帝王欲行其道,尚且欲征信于民,遑论孔子改制乎!故康长素谓孔子“托古”改制,犹摩西假托上帝以降示其律法耳。盖孔子若只为道德意义上的圣人,则躬自修身已足;然若欲使其道行,则必当有国以自尊,以律法绳其民,方能使百姓信从其道耳。
昔孔子出仕于鲁,欲行其教于母邦。其后,孔子去鲁,犹迟迟其行,盖不得已而谋行道于他邦,如西见赵简子而反马,使子贡先楚而期七百里书社地之封。然终见沮于楚令尹子西,则期为当世大人所用,其志尚与居鲁无二。孔子虽宋贤公子之后,今乃托庇于鲁,无先祖遗业可凭据,唯有三千弟子之襄佐,其处境较之汤、文据先祖遗业而王,实又加难焉。故孔子初欲赴公山弗狃、佛肸之召,其后去其母邦,携众弟子周游于诸侯间,又焉知未有得国之志耶?
故刘逢禄论曰: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弗扰为阳虎之党,夫子不见阳虎,而欲往公山,何也?曰: 夫子未尝恕公山也。曰“岂徒哉”,犹言非吾徒也。“如有用我者”,天也。周自平王东迁,谓之东周。《春秋》之作,以平王开乱贼之祸,鲁定公、季平子、阳虎、弗扰,皆叛者也。天用夫子,当复西周之治,岂犹为东周乎?《史记》述夫子之言曰:“昔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倘庶几乎!”此不为东周之意也。(35)刘逢禄: 《刘礼部集》卷二,《论语述何》。
《论语》中“吾其为东周”一节,历来诸家释训不一。今逢禄假《公羊》义释之,又证以《史记》所载孔子之语,则知孔子应弗扰之召,非仕鲁之比,乃欲据其地以为开国之基,盖视为汤之七十里、文王之百里也。然其弟子不知孔子之志,以为仕阳虎之比,则孔子之志小矣。又案,戴望注云:“如有用我者,当继文、武之治,岂犹为东周乎?明天命已讫也。”康有为则曰:“岂徒哉,言必用我也。为东周,言费小亦可王,将为东方之周也。……其卒不往者,殆公山早败,或诚意不足耳。”(36)康有为: 《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517页。则长素深知孔子心意,乃为孔子惜而不得国也。
是以孔子若有国以行其教,则自为“真王”矣。孔子晚年返鲁,唯以删述六经为事,至有“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之叹,盖自知其衰,将不久于人世,遂作《春秋》,欲借此以垂法于后世耳,则不得已而为“素王”之业矣。孔子卒后,诸弟子及后学之徒皆不复有建国之志,不过欲假君权以行孔子教法耳,两千年间,儒士与时君基本采取合作态度,盖始于此也。
孔子此种志向,后世唯公羊家能知之。(37)汉儒谓孔子实以“素王”自号,杜预以后,颇疑此说,即便如公羊学者,亦不谓然。如皮锡瑞曰:“素,空也,谓空设一王之法也,即孟子云‘有王者起,必来取法’之意,本非孔子自王,亦非称鲁为王。后人误以此疑公羊,公羊说实不误。”苏舆则以为,“汉世儒者并以《春秋》为一代之治,盖后人尊孔以尊王之意,非孔子所敢自居也”。章太炎夷孔子为史家,故必破素王之说。其《国故论衡·原经》云:“盖素王者,其名见于《庄子》,伊尹陈九主素王之法,守府者为素王;庄子道玄圣素王,无其位而德可比于王者;太史公为《素王眇论》,多道货殖,其《货殖列传》已著素封,无其位,有其富厚崇高,小者比封君,大者拟天子。此三素王之辨也。仲尼封素王,自后生号之。”则孔子为“素王”制法,不过“素王”诸义之一,且后儒欲以尊孔子所创设故也。子贡谓孔子“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论语·子罕》)。刘逢禄释曰:
天纵之,谓不有天下。圣又多能,周公、孔子二圣而已。(38)刘逢禄: 《刘礼部集》卷二,《论语述何》。
逢禄谓孔子“不有天下”,盖谓孔子不得国以行其道,即未为“真王”也。“圣又多能”,“圣”谓孔子、周公之“内圣”也,“多能”则谓孔子、周公能掌握政权而为创制立法之主也。盖对于中国文明有根本影响者,历史上莫过于周公与孔子,皆因二圣为立法者也。此种地位,犹摩西之于犹太人,穆圣之于阿拉伯人。故中国上古之圣人,上有尧、舜、禹、汤,下有伯夷、叔齐与柳下惠,不过圣而已,然未必“多能”,故不足为立法者也。
孔子又自谓“五十而知天命”。逢禄释曰:
夫子受命制作,垂教万世。《书》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知天命之谓也。(39)刘逢禄: 《刘礼部集》卷二,《论语述何》。
逢禄以为,孔子知天命,乃受命制作《春秋》也。时孔子尝用事于鲁,后虽奔走于列国,盖所制作已了然于胸,唯欲得国以施行耳。至获麟后,乃知天不欲其为真王,乃将其制作寓于《春秋》而垂于后世耳。
又,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子罕》)逢禄释曰:
此言盖在获麟之后与?获麟而死,天告夫子以将没之征。周室将亡,圣人不作,故曰“孰为来哉”,又曰“吾道穷矣”。(40)刘逢禄: 《刘礼部集》卷二,《论语述何》。
麟者,何休以为“大平之符,圣人之类,时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将没之征”。盖其时孔子已衰,又适闻获麟之兆,乃知终不得行道,因自伤“吾道穷矣”。故其作《春秋》,期为后世制法而已。
可见,究孔子之本意,实在于得国自王,即欲为“真王”也。故若能行教于母邦,则自属理想,此即“王鲁”之本义;不得已,则辟土于他国,乃至海外,其旨皆在建立儒教之国也。至晚年归鲁,始不复有“王鲁”之念,而以“甚矣吾衰”自解,乃作《春秋》以行“素王”之事。则“素王”之事,不过作《春秋》而已,又何僭妄焉!较之孔子本欲为“真王”,则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也。后世儒者乃退而求其次,其出则兼济天下,不过以圣臣自比,而辅圣君以行教;退而独善其身,则不过以素相、素臣自况,著书立说,而发明素王之道为事也。
迄于晚清,两千年间,儒者或为圣臣,或为素臣,莫有敢自拟圣人而王鲁者。时中国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非有引西法以济吾道之穷,则无以救中国。故康有为借发明《公羊》之“孔子改制”义,而以“素王”乃至“真王”自任,期以变祖宗之法,乃至数千年孔子之道也。戊戌间,康有为假君权以行“王鲁”之事;民国后,则通过建立孔教以行政党之实,最终掌握政权,犹效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取天下也。
“儒教”之说,盖古已有之,然“孔教”一名,或始于康有为。(41)章太炎即有此说法:“孔教之称,始妄人康有为。”(章太炎: 《示国学会诸生》,载汤志钧编: 《章太炎政论集》下册,北京: 中华书局,1977年,第695页。)然其义本无差异,唯康氏托名孔子以行改制之实,其内涵遂有不同耳。
康有为推行孔教,其意图颇多,且戊戌前后与民国后之孔教实践,康氏之考虑亦多不同。今限于篇幅,仅稍论其假孔教之名以行政党之实耳。(42)其实,早在1895年,康有为在京师、上海成立强学会时,即有此种意图。康有为在其诗序中称强学会为“政党嚆矢”(《康有为全集》第十二集,第174页)。后来梁启超亦说道:“乙未夏秋间,诸先辈乃发起一政社名强学会者。……彼时同人固不知各国有所谓政党,但知欲改良国政,不可无此种团体耳。”(梁启超: 《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辞》,《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九,北京: 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又曰:“盖强学会之性质,实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焉。”(《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同前,第38页。)民国初年,党派迭兴,康氏亦欲成立政党,且命名为“国民党”,然迁延未果,康氏自谓“愧恧欲死,真无以见人”(43)康有为: 《与梁启超书》,《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335页。。旋即谋成立孔教会,虽憾于当时废孔之议,然其别有所图亦不容讳焉。对此,康氏《与陈焕章书》(1912年7月30日)自揭其用心曰:
今为政党极难,数党相忌,以任之力,半年而无入手处。……昔弟在美,以行孔教为任,研讲深明。今若以传教自任,因议废孔之事,激导人心,应者必易,又不为政党所忌,推行尤易。凡自古圣哲豪杰,全在自信力以鼓行之,皆有成功,此路德贾昧议之举也。及遍国会,成则国会议员十九吾党。至是时而兼操政党内阁之势,以之救国,庶几全权,又谁与我争乎?此又所谓远之而近之也。吾欲决开是会,欲托付于弟,而宪子、君勉皆强力者,相与成之,必能尽收全国,可断之也。……弟若专政身于教,实可与任为两大,若仅附托政党,则末之也已。(44)康有为: 《与陈焕章书》,《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337页。
此外,北京孔教会总干事、廖平的门生李时品在1913年6月27日的日记中曾写到,“为长素而立孔教会者,其目的恐不在教”,“今京内外尊孔团体何尝不多,大抵借昌明孔教之名,为弋取政权之计”,他认为这种“明为会考,阴为政党”的做法,“予人以可攻之隙,实他日自败之原”。(45)李时品: 《知类疆立斋日记》,收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特刊第2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民国史组编,北京: 中华书局,1974年,第32页。
此种考虑,足见康氏之政治野心,然颇讳言之,今之治康氏学者亦少有见及此者。由此可见,康氏之意图在于借孔教会以形成议会中事实上的第一大政党,从而实现掌握政权的目的。而此种意图,与其对孔子作为教主的理解大有关系,昔之孔子、今之长素有斯志,亦在情理之中。故考诸戊戌夏以前康党之革命意图,及其政敌诋其“保中国不保大清”之志,可谓灼灼不可掩也。
不过,陈焕章本人似无意于此,他在为《孔教会杂志》创刊号所写“序例”中,即明确宣称“本会非政团”(46)陈焕章:“序例”,《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1号,1913年2月。。故有学者认为,陈焕章在政治上并不主张君主制度,“讳言君臣”,故在袁氏帝制与张勋复辟中,皆采取远离政治的立场,与康氏之积极主动不同。(47)参见韩华: 《民初孔教会与国教运动研究》,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267—271页。即便如此,包括陈焕章本人在内,孔教会中一些主要人物作为国会议员,也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政治活动,所提交的议案也明显体现了康党的政治诉求。
三、 儒教国家与学者治国
汉人“王鲁”之说,一则寄周道于《春秋》,一则期明王于将来也。虽有黜时王不能行道之意,犹孔子伤幽厉之心焉,然其中多讳深之辞。盖孔子虽不必真王鲁,究其志则不可谓无得国自王之意也,故观所作《春秋》,乃所以行儒教以治其国也。晚年孔子归鲁,不复梦见周公,乃据鲁史而明素王之法,思后人有以继其业者。然自秦汉以后,君主制渐成万世不可摇动之格局,于是汉儒以降,唯借君王之势以行《春秋》之法耳,遂不复有得国之志矣。(48)据《汉书·眭弘传》,昭帝时,眭弘推《春秋》之义,以为“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帝命”,因受诛焉。至宣帝即位,乃应眭弘“从匹夫为天下”之说。案,眭弘自谓本董子“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之说,然后儒多谓弘不守师说。此说亦未确,盖孔子本有以匹夫而自王之意,董氏虽未明言,然弘本书生,乃“打通后壁言之”,可谓真知孔子及其师意者也。
此种变化,影响到后世中国政治之根本特点。盖孔门颇具教团规模与性质,一旦孔子真能得国,则与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又何异焉!盖足以为王道之基也。然自秦汉以后,无论是汉魏时的察举制,而是唐宋以后的科举,儒士之理想不过是通过对儒家经典的学习而进入仕途,即作为君权的延伸来实现治国的理想而已。显然,儒士对政治的参与度虽高,然本质上则以认同乃至屈从于君权为前提,故虽有“达则兼济天下”之高远理想,实则不过“得君行道”,去孔子之政治理想可谓远矣。
传统中国因为受此种儒教思想之影响,既有神权国家的特点,又兼具君权国家的性质。盖中国自汉以后,君王素以“天子”的名义进行统治,此为其政治合法性的根本。所谓“天子”,意味着君王乃天之子嗣,因而具有神圣的血统。正因如此,人间的君王当奉行天道,并遵循一代一代君主留下的遗训,毕竟先祖遗训亦属天道的体现。故董仲舒有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此语可谓道尽了君主制的基本精神。然而,天道通常掌握在精通儒家经典的儒士手中,因此,儒士通过对经典的诠释而始终制约着君权。就此而言,中国古代的儒士,与同样传承真主律法的教法学家,具有同样的性质,即凌驾于世俗政府之上。就此而言,传统中国可以说是“儒教之国”,具有神权国家的明显特点。质言之,对于儒教国家而言,作为“天子”的君王,除了嗣位时必要的神圣血统外,整个国家的政治建构和运作,完全依赖于精研儒家经典的儒士和经师。可见,天意在中国政治中的具体表现,不仅包括顶层架构中的君主,而且还有落实天道的儒士和制度设计。可以说,儒教中国从来就不是典型的君主国,尤其不同于西欧教权崩溃以后形成的绝对君主国家。
儒教国家的这种特点,溯源于孔子及后世儒家的理论建构和政治实践,绝非出于秦汉以后帝王对儒家的利用。盖孔子生于周代君权国家崩溃之时,周王虽尚为“天子”,然与诸侯之亲亲关系不复被重视,于是君权之合法性亦随之动摇。故春秋时,周、郑交恶,富辰乃谏于襄王,曰:
臣闻之,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如是,则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郑亲,其若之何?……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扞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左传》僖二十四年)
可见,君臣之间,本以“亲亲以相及”,此周所以“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也。至周之衰,诸侯不独不能“以亲屏周”,而天子亦“不忍小忿以弃郑亲”,则上古君权国家至此而衰矣。
君权国家既衰,则对孔子而言,其上焉者乃取而代之,恢复上古神权国家。盖君、臣、民已非天之子嗣,不复“亲亲以相及”矣,则君不能凭“吾父母宗子”的身份统率人民,故对孔子而言,唯有通过君、臣、民之共奉天道来完成政治合法性的重构。然而,自孟子以后的儒家,则似不复有此抱负,不过以“名世”之“帝王之臣”自任而已。随着刘汉王朝取代嬴秦国家,中国形成了一种新形态的君权国家,此后儒家重建政治合法性的途径殆有二端: 其一,君王乃“天子”,当上奉天道,并掌握政权。其二,臣、民虽非君王之族人,君王亦不为臣、民之“大宗”,但朝臣通过对经典的精研成为天道的诠释者,或通过入仕成为政权的参与者,并通过《春秋》决狱而将天道落实为具体的律法,并以律法引导民众而掌握教权,使民众成为“帝王之民”。因此,何休所言“帝王”之君、臣、民,即强调君、臣、民当奉行上古帝王之道,即《尚书》所言“尊王之道”、“尊王之路”也。
可见,中国自汉以后虽皆行君主制,然君主制的典范实为“三代”。因此,历代儒者都以“复三代”为政治理想,其目的则在规诱时君而已。不过,后世要回归三代时的君主制,却有根本的困难,盖君、臣与民三者之间不再有血统关系,如此,君王统治臣、民的合法性就无从建立,更遑论建构一种新的政治统治的模式。对此,董仲舒在其《举贤良对策》中进行了尝试性的理念建构,从而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新君主制的基本格局。当时汉武帝在其初次册问中,所垂询之问题有二,即天命与情性。对此,董子回答的重点在天命问题,即“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汉以后的君王多起于民间,即便有“赤帝斩白蛇”之类的神话,犹不足以说明汉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对此,自贾谊以来,儒家学者的理论尝试主要有二: 其一,上疏建议汉帝进行改正朔、易服色之类的“改制”,以此表明新王受命的合法性。此种努力始于贾谊,“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49)班固: 《汉书·贾谊传》,第2222页。,迄至武帝太初元年,最终得以完成,即“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50)司马迁: 《史记·武帝本纪》,第605页。。其二,法先王,黜秦政,用儒术治天下。此种努力大略亦始于贾谊,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51)班固: 《汉书·贾谊传》,第2265页。,至董仲舒对册,乃“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而基本得到实现。
综观董仲舒前后三次对册,不难看到,儒家丝毫没有采取与君权相对抗的态度,而是通过君权与教权的结合,完成了新君主国的重新建构。(52)康长素对君主制的批评,或可如此理解,盖长素以共和制为最高政治理想也。自清末以来,长素一方面倡导孔教,另一方面却攻击君主制,盖自长素视之,孔教与君主制本无关涉。自秦汉以后两千年来,孔教与君权始终保持合作关系,并且在长素看来,君主制乃乱世或平世之政治制度,而孔教则通于三世,故将来犹可由孔教主导,创立儒教之国也。民国初,孔教随着君主制的覆亡而亦被打倒,《不忍》杂志附页有康氏所撰《礼运注》广告曰:“君臣之义被攻,而孔教几倒。”(康有为: 《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492页)然长素以为,幸孔教尚有大同之义,故儒教犹能光大于民主共和时代也。故对于长素而言,一方面使孔教与君主制脱钩,其中固有保全孔教之消极意图;另一方面,则通过推动孔教成为国教,从而掌握共和国之政权,实现儒教立国的古老理想。
孔子本与宋儒和基督教意义上的“圣人”完全不同,而是“立法者”。按照霍梅尼的说法,圣人“为人的各种事务制定了法律,并指导人们如何使用,他为人们从胚胎生成到进入坟墓的一切事务提供了指导”(53)霍梅尼: 《教法学家治国》,北京: 线装书局,2010年,第7页。。换言之,圣人或教主一旦建国,就不能仅仅作为道德的表率统治国人,而必须作为“立法者”,即通过制订一套完整的、包罗万象的律法体系来实施统治。因此,孔子既然作《春秋》,那么,圣人必然有建国的意图,乃至部分政治实践的经验。可见,孔子虽时有“待贾”之语,但其志则在效法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建国也,并“自治近者始”,推而使天下莫不被圣人之教也。故其自谓所得未丧之“斯文”,非止施于修身、齐家,实欲治国以至平天下也。孟子亦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此足见先秦儒者之志,尚未欲屈身于君主制也。唯至汉以后,君主制已不可动摇,儒者乃退而求其次,借君权以行道而已。
可以说,孔子始终欲谋建国,至其弟子已无此意,不过唯求出仕而已。其后至孟子,虽亦奔走于列国间,然不过欲诱齐宣、梁惠入道而行仁政耳。孟子曰:“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孟子·公孙丑上》)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又曰:“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孟子·离娄上》)此劝勉时君行仁政也。又曰:“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犹且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孟子·公孙丑下》)此孟子欲为伊尹也。可见,孟子已无创教得国之心矣,故后世儒士能慕孟子,然非真能学孔子者也。虽然,世人犹谓孟子迂阔,盖不知孟子已退而求其次,又焉有创教得国之志哉!
孔子既不得行其志于中国,故不免有化外建国之意,此其所以“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也。《论语·子罕》曰: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戴望注云:“九夷,嵎夷之地,今朝鲜国也。孔子既不得用于鲁,自以殷人思箕子之风,故欲居其国也。陋者,无礼义也。礼义由贤者出,有箕子居而化之,夷变于夏矣,何为陋乎?君子,箕子。”(54)郭晓东: 《戴氏注论语小疏》,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5页。又康有为《论语注》云:“孔子日思以道易天下,既不得于中国,则欲辟殖民之新地,传教诸夷。”(55)康有为: 《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448页。则孔子欲效箕子,而建国于化外也。
又,《公冶长》载孔子语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戴望注云:
此盖孔子失鲁司寇,将去国,心悼伤之辞也。鲁与齐接壤,尽青州海,其东为九夷朝鲜之地,箕子之国,故设言浮海,欲以去之九夷,因其有箕子遗教可以行道也。(56)郭晓东: 《戴氏注论语小疏》,第101页。
孔子不得自售,而不能行道于母邦,遂欲去鲁而独立建国也。
故康长素径以孔子为教主,曰:
《春秋》以孔子为新王,所谓善教以德行仁,为后世之教主者也。教主为民所爱,天下心服,入其教者,迁善而不知,过化存神,东西南北,无思不服,同流天地,非孔子孰当之?此孟子特发明孔子为教主之义也。(57)康有为: 《孟子微》,《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452页。
公羊家有“《春秋》当新王”之说,而长素推衍其义,以为孔子当为教主也。盖教主者,圣人能信其徒众而聚成一共同体也,此实为立国之基,若能得地利天时,则教团可化而为国家也。
在中国,孔子不得行其道,实属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从而根本上改变了以后中国政治的走向。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邵公注云:
是岁盖孔子由大司寇摄相事,政化大行,粥羔豚者不饰,男女异路,道无拾遗,齐惧北面事鲁,馈女乐以间之。定公听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当坐淫,故贬之。归女乐不书者,本以淫受之,故深讳其本,文三日不朝,孔子行。
世人视孟子行仁政为迂阔,然此前孔子用儒教治国,其效盖如此,惜乎孔子未能真有国也。
邵公又注云:“无冬者,坐受女乐,令圣人去。冬,阴,臣之象也。”徐彦疏云:“孔子自书《春秋》而贬去冬,失谦逊之心,违辟害之义,盖‘不修《春秋》’已无‘冬’字,孔子因之,遂存不改,以为王者之法,宜用圣臣,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则可,三年乃有成’是也。”所谓圣臣者,帝王之臣也。盖《春秋》编年,四时具然后为年,虽无事,犹不去时,何况此时尚有事乎?可知此时孔子以“圣臣”自居,而鲁不能用,故道终不行。孔子时居鲁而摄相事,故谦居臣位,盖以为有“帝王之臣”,已足以行道矣。然孔子终去位,则知徒有“帝王之臣”,而无“帝王之君”,道亦终不得行。后世儒士素以“圣臣”自任,然观两千余年中国政治,君王皆非“圣君”,故儒教之法虽颇行于三代以后,然距尧舜之理想国,则终有间焉。
四、 结语
公羊家以《春秋》为“万世之刑书”,其中极具深意,包含着对孔子治国的政治实践和理想的深刻体认。盖唯孔子志在得国行道,而非托庇君权,至晚年又有获麟之伤,遂有《春秋》之作,欲期后人借以“拨乱世,反诸正”也。此种道理,后世少有能“打通后壁”言之者。
考儒家之经典,其大旨不外乎修己与治国两端。所谓修己之法,不过以道德约束一己之身心而已;至于治国,虽有宋儒明德新民之说,然不过一孔之见耳,盖观乎古今中外之政治实践,治国未有不假律法而能行之者,此公羊家所以推崇《春秋》为“刑书”也。故就孔子而言,若仅限于修身至于敦勉门弟子入道,则其所谓立教者,诚如宋儒所言,诚意正心足矣;然孔子毕竟志在为政,至于得国而行教于一方,非假《春秋》而不能也。
然孔子所欲治之国乃儒教国,就其理想而言,本与君主国有根本不同。观儒家素来之政治抱负,当为圣人在位,而儒臣辅佐之,则亦无怪乎宋儒普遍有“致君尧舜”之理想;即便圣人不出,则犹赖圣人所垂遗经遗法以治世。故对儒家而言,唯奉孔子为圣人则足矣,此后不必有圣人,亦不敢有圣人,盖王法俱在,又有经学家掌握其解释之权,诚足以治世矣。正因如此,戊戌变法前后,康长素试图将儒学与君主制度脱钩,而与现代民主制度结合起来,实有鉴于儒学本与君主制无涉之认识。惜乎无论当时少数贤者对儒学之偏见,还是长素本人的保皇实践,反而使国人将儒学与君主制彻底捆绑在一起。此后无论辛亥革命,抑或丁巳复辟之失败,终使儒学成为君主制的陪葬物。
虽然,康氏之种种努力,实属消极,乃欲于新时代保全儒教而使之与政治脱钩而已。然究儒者之本怀则未然,即便如宋儒“得君行道”乃至“致君尧舜”等高蹈之说,犹假君权以行其道耳。今考《论语》诸书中所载孔子行迹,实以汤七十里、文王百里为上焉者,盖儒者欲实践其政治理想,首要在于建国,然后以信奉儒教之学者禀持《春秋》等“六经”以治世临民,务使其教充分付诸现实而已,如此方为儒教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