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起帆:发明出来不等于创新就成功了
黄靖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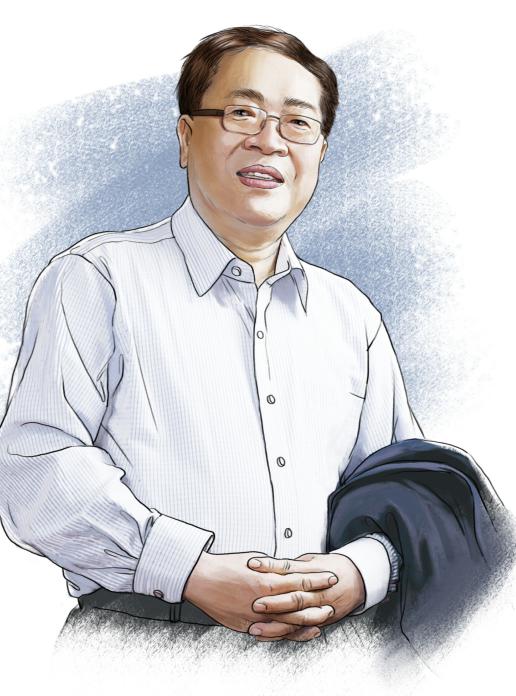
“抓斗大王”包起帆离开上海国际港务集团(以下简称“上港”)已经八年了,但他还是没有“闲”下来。
从上港副总裁的职位上卸任后,他先后担任了市政府参事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国际航运物流研究院院长一职。如今他更常聊起的话题不再是“抓斗”了,而是为上海发展拓宽空间的长江口疏浚土工程,和基于北斗技术的集装箱智能物流系统。
那是他专业和兴趣的延续,与港口、码头有关的一切,他总是能敏锐地捕捉到痛点。
包起帆今年已经68了。人近古稀,但他始终不习惯搓麻将、跳广场舞的生活。
包起帆有两段经历最为人所熟知。20世纪80年代在码头负责修理起重机的期间,因为研发出取代工人木材装卸工作的抓斗,人称“抓斗大王”;其后的1996年,他更带领同事开创了中国水运史上第一条内贸标准集装箱航线。
在2018年12月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包起帆以“港口装卸自动化的创新者”之贡献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有不少像包起帆一样的获表彰者,在自己熟悉的领域耕耘,以小突破,拓展天地,改变了一个行业的面貌。
从他的经历中,我们能感受到一位质朴的创新者,所经历的和时代节奏相呼应的人生道路;同时可以重新认识码头、审视港口经济,为了解当下的发展带来全新的视野。
发明是一百步走了二三十步
南风窗:你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港务局的白莲泾码头做木材装卸工。工作中,是怎么联想到改进抓斗的?
包起帆:因为白莲泾码头水比较深,方便大船靠岸,所以成为了上海港接收木材和生铁的一个专业码头。和很多地方一样,上海需要从外地进口木材,那都是一根根比我还高的木头。那时,工人们进行装卸只能用28毫米粗的钢丝捆绑起来,再利用起重机运到舱外,人在原木堆里作业非常容易出事故,我们都称这些木头为“木老虎”。
我从1968年进港后十余年,11位工人的生命就因此被夺走,重轻伤者达546位。我也遇到过受伤的情况,有一次被挂钩夹住了手,挣扎着放下来后发现大拇指的骨头都露出来了,40多年过去了,你看我手上的疤痕还在。
生产最薄弱的环节就有创新的可能,当时对于我们来说,摆脱危险且繁重的劳动只是本能的愿望,我作为工人就想摆脱工伤的命运。至于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我根本没有想过。在业余工业大学(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前身)半工半读四年后,我利用了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不断修改圖纸,在家里用胶水将图纸贴在大橱和五斗橱上,并用缝纫机做实验,终于在1982年初试制出了第一只木材抓斗。
南风窗:在新技术试验和推广之初,争议是不可避免的,你有遇到过质疑吗?
包起帆:是的。最初形态的木材抓斗试验时,的确可以将大批的原木从船舱里抓出来,很多人就以为包起帆好像成功了。
但事实远不止于此,第一次研制的抓斗还有很多的问题,比如它无法抓取舱舷两侧内的原木,当中间部分的原木被抓出去,舱内的原木就会变成“V”形,还得人工下舱作业,而这是非常危险的—他们有被原木滚落活压的风险。
当你提出了一个想法,就要对不完善的地方负责,甚至有人跟我说,如果你能把原木全部抓取出来的话,我情愿从办公室爬到门口。后来受圆珠笔原理设计的影响,我再次进行改进,发明了“单索抓斗全新启闭机构”,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回头想这件事情,就明白当新的发明被创造出来,只不过是一百步中走了二三十步,还有更多的路在后头。所以很多人以为发明了新的东西出来,创新就成功了,其实不是的,转化的过程比获得成果更难。
在这之前,码头里有过老师傅和工程师进行过类似的改进,但最后都被扔到废钢堆里了,因为他们要不就是缺乏理论知识,要不就是没有一线经验,六年装卸工和四年修理工的经验让我对木材装修和机械加工工艺都很了解,上大学后补齐了科学文化知识,又为我的创新奠定了基础。
南风窗:在这之后,你还有过什么发明?
包起帆:因为码头上还有其他需要装卸的货物,举一反三,我又研究了生铁抓斗、废钢抓斗等工具。一块生铁有三四十公斤重,之前全靠人工搬运,有了抓斗就能很大程度上提高效率,帮助港口装卸从人力化迈向机械化。
不同领域的工具尽管有差异,但是总体的原理都是相似的,建筑、铁路、电力、环卫、核能等行业也能广泛应用改造后的抓斗。当然更重要的是,工人们不再因木头的掉落而伤亡,前几年在连云港,有码头工人对我说,“你的抓斗救了我们”。听到这句话,比我拿到发明奖项的金牌还有意义。
很多人以为发明了新的东西出来,创新就成功了,其实不是的,转化的过程比获得成果更难。
从36到23000个箱位
南风窗:如今上海港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集装箱港口。在你工作之初的情况是否会有不同?
包起帆:我刚进上海港工作的时候,在面积上而言它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港口了,但在世界上还是排不上号的。当时其吞吐量在五千万吨左右,所有的工作以人力为主,根本没有集装箱的说法。
人拉肩扛,码头工人很辛苦,同时整个上海港压船、压货非常严重,所以周总理那时候有一句话: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积压最严重的时候,上海港吴淞口外面锚地里,停了一百多条外国船只,来不及装卸。那时候外国人跟码头会签速遣协议,规定若船到上海港能卸完的,就给报酬,否则就罚钱,目的是为了提高港口效率。
船是靠运费支撑的,如果船一直停在码头上,货物就不能流转,赚钱从何谈起?有人做过统计,我们码头因违规缴纳的罚金数额,相当于有人坐在黄浦江边上,每天把百元大钞不停地扔进去,可见当时我们的经济损失有多严重。那时候一个月只有40元工资的我们,眼睁睁看着钱打水漂,无能为力。可以说,当时上海港的落后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南风窗:后来上海港的发展有了很多变化。其中,90年代的时候,你被调到龙吴港务公司担任总经理,在职期间开设了国内首条内贸标准集装箱航线,当时的考虑和背景条件是什么?
包起帆:1995年的时候,那时整个中国的集装箱都是用作外贸的,至于国内的贸易—比如上海的电视机想到广州去,是散装的,就是箱箱散装运输。我刚到龙吴码头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杂货码头,什么都有,这是不符合运输业发展趋势的。我在国外学习考察过,了解到当时世界上大港口的发展趋势有两点,一是散货的专业化,另一个是杂货的集装箱化。
我上任后,发现码头经营情况很困难,最严重的时候一个星期都没有一条船进来,一天就亏掉了30万元。当时很多人认为公司困难的原因是地段不好,因为位于黄浦江的尾巴,所以没有船会进来。我知道不能坐以待毙,如果企业不变革,只有死路一条。
但是其时情况也有特殊性,上海港和合资公司有共建码头的协议,合同里面规定了合资公司拥有相当大的吞吐量比例,况且其他码头的实际运力已经超过规定比例了,所以外贸集装箱这条路就走不通了。于是我就走内贸,80年代的时候交通部曾发展过五吨的小集装箱,因为三个原因—效益不好、没有实现标准化和为客户带来的价值有限,失败了。
我在操作的时候,遇到的问题也很多,比如外贸箱是不收税的,那么内贸箱如何处理关税?也许一不小心就有犯罪的帽子扣下来了。但是我知道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不是坏事。国外汉堡、鹿特丹等地,比中国面积还小,它们也在做集装箱,我坚持认为中国的内贸集装箱是水运的必由之路,所以我就开始到深圳、广州、厦门等地找货主和合作伙伴。1996年12月15日,第一条内贸标准集装箱航线就这样开通了,叫丰顺号,从厦门开来。现在最大的集装箱船已经能到达23000个箱位了,但是当时“丰顺号”上只有36个箱位。
从此,中国的内贸箱就这样一步步地发展起来。
港口的竞争力
南风窗:退休之后,你的工作步伐没有停下来。如今在国际航运物流研究院任职,你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包起帆:离开上海港后,我就来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在这里组建了一个团队,把我当时在上海港时想做而没来得及做的科研工作转移到了这里。
可以说在这里取得的创新成果不亚于过往,主要完成了兩个比较大的项目。
首先,我们都知道上海的土地资源、港口岸线和深水航道资源越加紧缺,已经到了发展的瓶颈期了。1998年以来,上海开始了长江口深水航道的治理工程,希望能提高上海港的集装箱船舶地装载量。在建设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挖出的疏浚土,它们利用率很低,因为机制、体制和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大部分被废弃了。
因此我组织了一百多位专家,就疏浚土综合利用的课题开展了战略研究,我们希望把这些废弃的资源用到拓展土地空间的目标上,在横沙建设上海深水新港。在新横沙岛将形成56平方公里的生态陆域。我们正在开发后面一块303平方公里的生态陆域,做成以后,上海将拥有很大一片发展腹地。
我在操作的时候,遇到的问题也很多,比如外贸箱是不收税的,那么内贸箱如何处理关税?也许一不小心就有犯罪的帽子扣下来了。
第二件事是我之前一直在做的集装箱物流跟踪与监控系统,是解决整个物流过程中的集装箱偷盗、掉包和走私问题。当我退休的时候,国际标准其实还没有真正发布,蛮可惜的。最近这些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展很快,我们就将北斗技术应用到物流上,这个项目推广得很顺利,现在通过手机下载APP,就能得知包裹的位置了。我国是世界集装箱港口吞吐量第一大国,但在这一领域国际标准的制定中却鲜有中国的声音。在这期间,我们弥补了这个遗憾,分别领衔制定、参与制定和主导修订了三项国际标准,得到了国际上很大的认可。
回想起来,从原来港口的一小块领域开始,我的创新、发明拓展到整个物流领域,到如今探索整个上海的发展空间。我想,退休后的这八年没白过。
南风窗:现如今,重塑港口优势成为城市竞争力的一部分。在你看来,港口的竞争力体现在哪里?
包起帆:港口本身就是一个服务行业,是为整个经济社会服务的。首先是要自动化,但这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低成本;第二是高效,不能像原来一样让货物滞留在码头走不掉;第三是安全,不能东西被搞坏了,这就是做港口的需求。
原来中国港口发展的低成本因素已经弱化了,那么竞争力体现在哪里?就是品质,高品质是我们行业的核心。如果一个港口服务差,安全得不到保障,客户为什么不走?这样的体会来源于一次经历,我看到在德国免税店卖几千欧元的行李箱很快就能清仓,但是法兰克福车站那些十几欧的箱子却总是卖不出去。
我曾经有管理和变革码头的经验,2003年我在上港的时候就开始研发集装箱自动化无人堆场,2009年建成世界上首个全自动散货装卸系统,当年自动化这个词远不如现在热门,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是无用的支出。因为当时码头一片繁荣,工人和司机很多,很便宜,但就像我现在在想上海未来的土地空间一样,自动化和智能化是港口发展的趋势,我们要有前瞻性,所以我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变革,这些都是提升港口品质的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