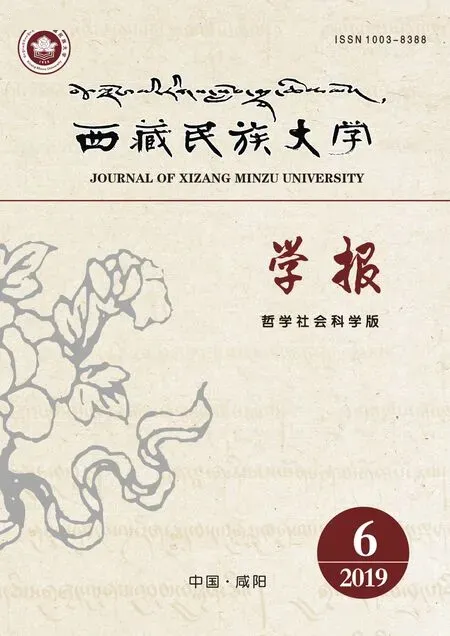游蒙日记(下)
李廷玉 著,韩敬山 校注整理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 北京100081)
按语:《游蒙日记》的著者李廷玉是清末中央政府派往蒙古解决十三世达赖喇嘛相关事务的主要参与人。该书系校注者于2016年公派赴台湾“辅仁大学”访学期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寻获1907年东京影印出版的李廷玉“手抄本”。随后笔者查询到李廷玉《游蒙日记》“铅印本”的出版时间为1915年,为竖排、无句读,全书每页均标明“财政部印刷局印”。1990年1月,由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末蒙古史地资料汇萃》中收录了吴丰培版“手抄本”《游蒙日记》,并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印数500本,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于1991年3月28日即在香港花费180港币自学峰书屋购入此书。因印量稀少,纸张脆硬,加之出版日久,国内诸多图书馆当馆藏珍本,难示学人。有鉴于此,2006年,北京学苑出版社出版一套由李德龙、俞冰主编煌煌200钜册《历代日记丛抄》,其中第158册就收录并影印了1915年“财政部印刷局印”的《游蒙日记》以嘉惠学界。
《游蒙日记》讲述十三世达赖喇嘛北遁蒙古后,清中央政府派出御前大臣博迪苏、内阁学士达寿奉慈禧皇太后、光绪皇帝之密令,北入蒙古库伦劝说十三世达赖喇嘛不得前往俄国。李廷玉以州判及随行委员身份全程参与相关事务,其所记载,恰成为当代研究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蒙古地区活动的珍罕史料。
值得一提的是,吴丰培先生对《游蒙日记》亦做了评判:“惟对于达赖颇多微词,称为刚愎自用,固执不通,妄自尊大,贪吝多疑,未必尽当,乃当时相见之人,观察他的行动,似仍不无可取,又描写他的体态、手段、行动、供给、行踪等较为真实,以目击之谈,乃属第一手资料,可作十三世达赖喇嘛传的补充材料”。
2019年5月,校注者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还找到馆藏博迪苏所著《朔漠纪程》手抄本,里面亦讲述其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咱雅班第达前后达九次见面的第一手记录,并看到1908年8月,郭进修在日本东京神田区集贤馆为《朔漠纪程》写下的序言。
有鉴于此,校注者在校注《游蒙日记》时,与《朔漠纪程》一一对照,并将《朔漠纪程》中与达赖喇嘛见面的谈话记录以注释的方式录入《游蒙日记》的校注稿中,为读者全方位再现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蒙古期间与中央政府代表博迪苏九次对话的现场场景。
校注者此次以“铅印本”为底本,并参考“手抄本”对涉藏事部分重新详尽校注。因原稿几无标点符号,故予断句、标点;原手稿为繁体字,现均改为对应简体字。对于其中因字迹潦草经多方反复查核依然难以识别的少数文字以□表示。由于上述两“手抄本”至今面世已过百余年,文中难免有与今天提法相左及错误之处。为忠实原文,以供研究,未予删减,望读者察之。本刊自2019年第4期起分三期发表,以飨读者。
五月初一日
晴。前在张家口接外务部电,云:驻俄胡星使电称,达赖喇嘛回藏,俄派黄教人四十名随行护卫,当经派带宣北马兵三十名为抵制之计。自至札雅沙比[1]后,连日访得俄布里亚特人来此数十名,统以武官(名打木丁)一员、武弁数员,均著喇嘛服装,藉与达赖磕头为名,相随不去,并决送达赖入藏等情。想外务电称,俄派黄教四十人,即是此股。该武官相貌英挺,各弁亦有尚武精神。惟见余等戎装,则问系日本人否?可知日俄一役后,俄人脑筋中无不有一强悍之日本在也。
七点后,同宜琴乘马,赴东南十里许之喇嘛庙,由西院侧门入。正殿两进,左右正殿称是。右侧殿额书阐寿寺,显庙御笔,内供佛数十尊,皆赤金化身。正后殿额书保安寺,成庙御笔。又入东院西侧门,正门甚宏厰[2],东侧门闭而未启。前正殿设高座,为恭候达赖说法处,旁置黄云缎伞一柄。东侧室列屏风,绘全部西游记。[3]由殿后门出,经小院,再过穿堂,至一大院,正殿七间,左右耳房各三间,东西配殿各五间,存储跳布札(俗名打鬼),应用各装具(该庙每年五月十五日行跳布札[4]以除不祥)。
入正殿,额书普庆寺,毅庙御笔,内正座供喇嘛一尊,名札穆棍多尔济(蒙俗佛死,以木穿尸成孔,涂抹黄油,置诸釜中,以火炙之,尸焦骨枯,碾成细末,带至库伦,以香末或宝石末合骨灰塑成偶像,然后带归佛所旧驻之寺,设位供焉)。
东侧室排列武像十余,均甲胄,佩带弓矢刀矛,英爽有生气。西北隅一将,貌非蒙人,魁梧奇伟,名达哈喇,生前最有武功。西侧室供佛座,名那木囊苏伦[5]。
是日,带领游览各处之喇嘛名白格子久,引入东跨院饮奶茶,并进糖、枣。与宜琴均捧哈达为礼,是庙俗呼东库伦(蒙语大院),为札雅[6]大寺之一。
十钟归来。
午后,购运军粮之马兵王鸣岐至,乃知薛君宝之前赴库养病,至今未痊。向夕,同梯兄走看两公一王所住蒙包,是时各福晋多赴达赖处叩头,并送布施。
五月初二日(略)[7]
五月初三日
晴。乘马往观台尼尔格河(去寓所东南约十五里),树木森蔚,倒影波心,流水淙淙,石随溜转,中多细鳞。河之阳,山高千余尺,野花堆锦,香气袭人。据土人云:河水深常二三尺,若大雨山水暴涨,深乃一二丈不等,且溜急拔木而走。一二日后山洪退,河水如常矣。巨鱼虽多,蒙人不肯网食(守佛家戒律),同往之积君、宜琴云:水清鱼肥,味必鲜美。惜无鱼具取之,只得任其游泳而已。余云:古言临渊慕鱼,不如退而结网,妙喻亦至理耳。
归寓,无事。因调查达赖人格及其行为,略记概要,以供研究。
(达赖之性质)
(一)刚愎自用。前番英藏交涉,一意主战,其噶布伦及戴俸等,不能劝阻。藏臣开导亦置若罔闻,至屡战屡败,逃出藏地,仍刚愎如前。故随出拉萨(达赖喇嘛安禅处)者,只二三十人。
(二)固执不通。英藏之事,不量权力,不度时势,只以痛恨英人,饬三大寺僧合力拒战,且阻藏臣排解及兵连祸结。英则士卒用命,枪械便利,对垒数次,毙藏僧甚多,藏则仍用带架大枪,各兵然放[8]时皆回首避声,不解瞄准。迨逃入蒙境,犹与地方官时常龃龉。
(三)妄自尊大。达赖出入驱逐行人,狎侮番蒙官民,有如土芥。
(四)贪吝多疑。自入蒙界后,凡所供给,悉取蒙民。间日放头,广收布施,其随从、官员、沙比等,除日用外,毫无优待。遇事游移,不能自主,及左右画策,又不肯从。
(达赖喇嘛之状态)
年三十余,身长约四尺,粗眉直竖,目多白睛,鼻小有斑,口阔唇薄,牙齿外露,面色黑而近枯,髭鬚疎少,左足跛行[9],举动有类贫僧,且目好转睛,坐不能定。
(达赖喇嘛之手段)
前五六年,该喇嘛与俄交通,遣使聘问。《泰晤士报》载:俄与达赖定立密约,清国政府业已知之等语。其从中沟通过付之人,则廓尔喀大喇嘛实为主动力。现达赖属下尚有一二俄人为之赞佐。此次削尽蒙人脂膏,决意回藏,想系倚俄人为护符,不然该喇嘛前在库伦一味逗留,今乃竟敢归藏,且现拟遣堪布进京入贡,似恐朝廷知其向俄,姑藉纳款抒诚,以遂其阴险之志。
(达赖喇嘛之供给)
在札雅[10]地方,每日向该库伦索米、面各百二十斤,蒸食麽[11]三百六十六枚(因随侍一百八十三人,每人日发二枚),每五日索羊八十只,其他黄油、柴木并各项日用,各饮食料,不拘定数,索取亦无定时。自本年暮春初旬到此,已驻三月之久,凡王、贝勒、公、[12]台吉各官及蒙民喇嘛等,日事供億,实已力尽筋疲。大约二三年元气难复,较诸前在库伦吸取蒙人膏血,实有过焉。盖彼时达赖随从人少,而库伦地势繁盛,又甲于札雅[13]百倍耳。然蒙俗迷信佛教,虽倾家不惜焉。
(达赖喇嘛之行踪)
前于光绪三十年与英人妄开兵衅,及事已不可收拾,乃于六月十五日携印潜逃,由藏经过青海之玉树番及南北柴达木,又走甘肃界之安南壩安西州入蒙界,走札萨克图汗三音诺颜,直抵土谢图汗之大库伦。在库伦留年余,收取布施甚多,后与该处活佛哲布尊丹巴不睦,于三十一年八月中旬移驻代青王旗(即杭达多尔济属境),病数月,经库伦大臣屡催回藏,或赴西宁,遂于三十二年三月初旬移住札雅班第达。
(达赖喇嘛之随侍)
其逃出时,自噶布伦(职一品)、戴俸(统领)、师本(有司官)、堪布(通经喇嘛)以下只三四十人,至库伦后续来数十人,抵札雅后又来数十人,计共一百八十三人。凡亲近者皆著黄缎袍、黄云缎背心,戴大帽,顶有黄结。中有某喇嘛,年三十余岁,面方色黑,狞眉阔口,而睛多淡白。凡达赖行动,该喇嘛不离左右。其赞画一切者为俄人,其传达公文者,有堪布谢天化(科尔沁人),以下有内从,均留发,又有外从与华俗之辫发同,皆耳堕珐琅,环腕带镯钏,手贯戒指,足著朱靴,身穿绛袍,眉粗眼白,面黑多髭,并有俄属奉黄教者百数十人(布里亚特)随听指使,装饰与喇嘛同。惟脚著洋靴,兼通蒙俄语言。
(达赖喇嘛放头之状况)
每隔一日准蒙民布施,名曰放头,常数百人或千余人(多由他处而来者),合什膜拜,献财帛及牲畜等,达赖以松克他拂其首,各叩头散去。
(达赖喇嘛之动作)
每日赤脚诵经,出常乘马,其就途也,坐黄缎轿,驼、马各数百匹,所得布施,分次寄藏。本年三月间,赴藏驮驼六十只抵青海,被番人劫夺。现达赖所住毡帐,外罩黄缎,内镶红缎,凡支撑木端,皆金银为饰焉。
五月初四日[14]
早微阴,午后雷雨交作,少顷放晴。出门散步,见该处王公、福晋、格格及士民等多持念珠诵经,并向达赖喇嘛叩头,且有距此数百里之王公、台吉并富户携眷来此布施。故达赖喇嘛所得珍物、金、银、牲畜各物,为数甚钜。札雅后山有浮图八座,山腰间有庙一座,向夕来膜拜者颇多,甚或全家合行叩头礼焉。
五月初五日[15]
晴。据土人云:札雅大寺,均畜牧为业。呼图克图岁食进俸,但呼图克图业已圆寂,尚未转生。前蒙人求达赖指示转生活佛地方,达赖云:去此不远,寻即可得云。
五月初六日(略)[16]
五月初七日[17]
大雨。据霍队官云:乌城及科不多,均宣化、绥远,两处兵马分班戍守。前营马兵约二百名,后营百余名,以绥远兵居多数。其瓜期以五年为限,并云前乌梁海驻四总管,只有弹压地方马兵数十名而已。
五月初八日[18]
雨仍未止。同乡翟君(在该处商贩)送来葱、韭少许。据云:蒙人不解食菜,惟内地商家寄此者,恒植数种,以备食料,并云:自达赖驻此,每日售货得银常数百金。惟近年运脚价昂(由口到库坐驼每只七十余两,驮驼四十余两,由库到此牛车二十余两),获利转薄。余答以若由口修铁路到库伦,则商业决然畅旺矣。
五月初九日(略)
五月初十日(略)[19]
五月十一日(略)[20]
五月十二日(略)[21]
五月十三日(略)
五月十四日
雨,少顷放晴。陟南山之腰,有人骨堆砌唐古特字[22],不知起于何年?转赴西山,松涛送爽。据土人云:蒙人身故,置尸于此,任兽攫食,谓为食牲还牲。若过三日不食,则修经忏悔,且以黄油涂尸[23],俾野兽嗅而食之云。[24]
五月十五日
东库伦(又名下库伦)跳布札克,因往观之。各喇嘛及沙比等均华丽古装,逐队跳舞,往返数十次。两侧喇嘛,击鼓鸣号或敲法器,以期应节。据云:所演出各式,系形容一百零八星下界之举动,藉以拔除不祥云。
午后雨至,乃策马驰归。
五月十六日(略)
五月十七日[25]
晴。上库伦(又名西库伦)演掼跤,随钦使往观,达赖遣送酪浆、茶果,少顷开演。各裸体(各穿背心,下体以布蔽之)分队登场,先向喇嘛合什膜拜,然后乃角力胜者仍如前,向达赖膜拜三次,退向负者行抱臂。礼毕,乃散入帐棚中。是日,角力计百余人,达赖赏最有力者三名(赏哈达、普鲁[26]等各有差)以示鼓励。惟第一比狮、二比象、三比虎云。
五月十八日[27]
陟北山之阳,见峰腰石间刻黄教之祖宗喀巴像。按宗喀巴为第一世达赖喇嘛之师,故达赖转生至今十三世,均师祀[28]之。查圣武记[29]载:宗喀巴厌世时云,达赖转生,只及五世,乃知由六世相延不绝者,寔[30]藏番之迷信,然也。
五月十九日[31]
晴。达赖遣人约钦使看跑马射的,因随往。其鹄布列羊皮九张,行耦射,然发矢数四,中者寥寥。惟耦进时,先叩首于达赖前,射毕仍向达赖膜拜。跑马者,皆十余龄小二。是日,赛马共二十三匹,先至者为札萨克图亲马,即献达赖。达赖系以黄哈达,并以酪浆饮之(达赖受马,赐札盟王白镪五十两、哈达一分。该王叩首欢然去)。各马主乃牵所赛各马,依次致颂词,三番而毕。
适大雨,乃归。
五月二十日
乘马赴呼图克图之别墅(去寓所约十里),面积约一里许。曲槛回廊,雕题画栋,屋中陈设与内地略同。呼图克图未厌世时,常于夏间住此处避暑,并云:去此不远,别有御东庐舍一所,其建筑不逊此处云。
五月二十一日[32]
接到库伦延大臣函,附转军机处电一件,钦使公博奉旨于达赖起程后,先行回京。达阁学随护达赖赴西宁候旨,余等应随博先行回京。
五月二十二日
俄布里亚特人又来数十名,押运达赖驮驼数十只,就道赴三音诺颜库伦矣。
五月二十三日
晴。达赖遣派[33]堪布札木扬丹巴充当贡使,拟于二十五日赍供入京。[34]
五月二十四日
大雨,向夕晴。探得俄官所带布里亚特人数十名,佯言归国,寔[35]则派为达赖保护辎重,决于次日首途云。
五月二十五日
晴,据霍队官云:喇嘛庙地方东南,距古北口六百余里,西南距张家口五百余里,并云该处商户[36]一千余家,繁盛之象,甲于库伦。武职设有协都守千等官,住防有宣化马兵一营(百六十名),后拨归经棚一队住守。故寻常应差,不敷派遣等语。
按喇嘛庙与张家口古北口势成鼎峙,自是屯兵要区。往昔朝阳余党窜入该界,因兵力单薄,几成野火燎原之势,则握兵柄者,所当绸缪未雨也。
五月二十六日[37]
雨,少顷即息。闻蒙人云:达赖自三月初七日到此,每日供给约七千余两,均由该库伦摊办。是日,遇塔尔巴哈台人,携妻子为达赖磕头。且云:由前年赴西宁,冀晤达赖,至则始知达赖出藏走入蒙界到此。又闻达赖内赴三音诺颜、库伦,决拟挈眷前往,以了心愿。然资斧告匮,必须求助于人。余观其所携毡帐,夜卧其间,可觇星斗,妻、子均等于乞丐而执迷不悟。有若性成,亦可见黄教之蠹人深矣。
五月二十七日[38]
雨,午后,达赖乘黄缎轿(以四马驮架之)开行,引导骑兵数名,并有作乐。番僧十余名,走里许,达赖下轿,叩拜北山石像宗喀巴毕,乃登轿速行,雨声甚急,随行番众,已淋漓尽致。
五月二十八日
所有远来与达赖磕头之蒙古王公及土民等侨住于此者,均随达赖赴三音诺颜库伦。故札[39]雅附近毡帐[40]已席卷一空。
午后,看札[41]雅东南山麓之地牢,周约六丈,深三丈许,横空列木排。俾犯人坐卧,而顶有大圆洞,以便出入。牢外囚犯头系大锁,重约数十斤。据云:该处词讼,须由载桑理之(有司官)。
五月二十九日
随钦使开行,赴三音诺颜王府地,因饬各兵列伍护卫。是日,宿于胡合苏莫之索木台。
六月初一日
七点开行,午后渡鄂尔坤河,魏部郎车覆,幸该处水浅,未占灭顶。渡河后,询元代和林故城。据蒙人云:城早为墟,只余瓦砾。
是夕,宿于敖兰土鲁。查该处之山多产煤、铁,各矿苗已显露。惜于矿学素未讲求,故质之美劣,引之远近,未能辨云。
六月初二日
六点开行,所见森林多在山之东北。查罕盖一带,地势极高,日球光线无冬夏,先射罕盖东北,故树木发生之象,异于内地之独在东南。盖天时随地势转移,生物亦因有区别耳。
午后,途中遇雨,三点抵达三音诺颜库伦,寓于那王之别业。
是夕,达赖喇嘛放头,蒙民及喇嘛约二千余,[42]均屈膝坐湿地上,敬候达赖叩头献礼物。虽大雨倾盆,皆不肯去云(达赖六月初一日至,住三音诺颜王府第)。
六月初三日[43]
晴,计自入外蒙以来,日光出入时间与内地不同,每日约三点十分晨曦动景,晚约九点五分方坠崦嵫。人谓北冰洋一带,半年一昼夜,其言当不诬也。
午后,禀卸带兵差使,当奉批准,因将弁兵等合拍一照,以为纪念。
夜来,大雨如注,幸板屋尚未渗漏。
六月初四日[44]
晴。闻三音诺颜盟长云:达赖用度,每月万金之谱,均由各旗供给。
按该达赖自光绪三十年六月十五日逃入草地,至今计三十六个月有余,坐耗蒙旗膏血约四十万金内外,其各项布施,如驼、马、牛、羊、车辆、毡房、金、银、币纸、珠、玉、锦繍等,不可计数甚矣。黄教蠹人,而宗喀巴为千秋罪首也。
钦使博公定于来日启程,因令人押送辎重,本日就道,以利遄行。
六月初五日
早六点起程,弁兵列伍饯别,因以温语抚慰,并互行军礼。路经诺勒吉图布喇喀及那里哈达图两索木台,换马赴翁锦,乃乌拉齐误,将余带至呼兰哈达。
上马又行,抵翁锦已六钟。
是日,马上飞走,约四百五十里。
六月初六日
七点开行,路经哲楞走四十里至哈沙图宿焉。据淡然喇嘛云:西藏属之蔑隆地方,本分隶十八土司,归达赖管辖。八九年前,土司互争,川都讨平之,乃归川属。[45]余谓该处不设州县以治之,无论土司,各不相下,且民人肆行劫夺,必至乱端复萌,非长治久安之道也。
六月初七日(略)
六月初八日
五点开行,经栲萨及希保台,至哈比尔噶住宿。
是日,约行二百余里,甲剌[46]莽哈拉来迎钦使,探得达赖由拉萨逃入蒙界,求庇于俄,并进贡物,均俄人阿嘎汪(布里亚特人,充达赖堪布)为之决策。达赖抵库后,俄皇遣使慰问,以礼答报。俄使会晤达赖时,屏退从人,语言诡密,及延大臣迫令达赖离库。达赖又走岱青王府第(亲王名杭达多尔济)小住,阿嘎汪由是回国,未审作何运动。
按俄人垂涎西藏已久,但以英人早下辣手,不克骤遂蚕食之谋,乃专力规取东三省及俄败于日,而东北经营一旦销除大半,不得已稍定喘息,再图东南。适印藏交兵,达赖遁入蒙界,于是阳用羁縻之术,阴逞谲诈之谋,迨达赖堕其术中,然后观衅而动。此俄国人外交之惯手段也。
六月初九日
五点二刻起行,路经默端,抵赛尔乌苏住宿。途中微雨,闻达赖贡使于昨日早间过此。
六月初十日
晤管站部员札拉芬(字静山)、印务笔帖式文端。据札君云:俄人经行台站,以厚赏驱役台差,故沿台呼唤甚灵等语。
按俄人外交手段,始则以利动人,继则从中取巧。迩来俄商往往取道各台,不走商路,所省路费,数倍赏金,而贩货往来,又格外迅速。是以俄人得利,较华商为独厚云。
六月十一日
早五点开行,经库图勒多伦博罗鄂博,抵卓布哩住宿,共走约二百里。探闻达赖进贡传台印照,载明用驼六十只,寔[47]只用驼三十二只,贡使札木扬丹巴拟折驼价二十八只,以足六十只之数(每驼一只,折银五钱),且印照未载食羊,犹欲强索,幸台员未允,折给驼价,仅权给食羊而已。
按达赖此次入贡,原假不腆之贡,掩饰前此贡俄之失,然所用驼只,犹如是之多,则又系借进贡为名,运载藏香、红花、麝香、氆氇等项,为牟利之计耳。
六月十二日至十四日(略)
六月十五日
……途遇达赖贡使札木扬丹巴及番僧数人,并遇为达赖磕头之蒙民十数骑云。
六月十六日至二十日(略)
六月二十一日
阴。追论蒙古之概略:
一(性质)——崇势力、鲜廉耻;有形骸、无思虑;少勇敢、多游移。
二(能力)——耐劳苦、忍饥渴;善驰骋、习风沙。
三(生计)——曰游牧、曰打牲;曰租车驼;曰制浆酪。
四(习惯)——不读诗书、弗谙礼法;迷信佛教、不事佃渔;处污秽而相安,嗜烟酒而无度;未解婚丧之典,不避男女之嫌。
五(交易)——凭牛、羊、驼、马易银,用哈达、砖茶代钱。
六(土产)——曰牲畜、曰皮张、曰毛片;曰蘑菇、曰盐、曰碱。
七(矿质)——金、铁、煤炸。
八(服饰)——无贵贱,皆着长衫,无冬夏,恒戴皮帽,鞋多不袜,衣或不裳。男以黄、紫为章,妇女以珠、玉为饰。
九(饮食料)——牛羊肉、酪浆、奶皮、奶豆腐、黄油、元米、砖茶、奶茶、烧酒、糖盐。
六月二十二日[48]
早九点,随博公参观学堂。是日,凡高等学生四十名,蒙养四十名,各生均演体操。陆军小学堂(生三十名)、巡防队(五十余名),各演走步变排,尚称完整。惟巡防队仍习德操,与现在操典不合。周览各堂屋宇,均整洁可观。
博公令魏部郎震为诸生演说惠爱二字,理由毕。溥都护复申明演说大义,勉励诸生。
午后,凉雨忽来,夜半乃息。
六月二十三日(略)
六月二十四日
阴,午后雨。探得日人米良真雄(年二十余,寓洋务局对门店内)在口[49]侦探时事,考察形胜,并学蒙古语言。又佐籘安之助[50](军人)住口最久,时与蒙民之赴口者阴相接洽。俄商在口运动张库铁路,其谋甚诡,期于必行。
按日人既取南满,必将规画蒙疆,为扼制俄人之计。俄为日败,不克逞志东省,乃决持修筑张库铁路,并达恰克图。主义则大漠横分两段,俾平时取得商贩之利,变则直趋畿辅,为扼喉扼坑之谋,形势所在,人必争之。日与俄皆筹之熟矣。洵可虑哉。
六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略)
六月二十八日[51]
晴。三点开行,过居庸、沙河等处。向夕抵德胜门,共走百四十里。寓宣武门内辟才胡同[52]魏部郎宅。
是日,天气暑甚。
六月二十九日[53]
钦使博公由沙河镇启程。寓地安门外,预备复命,并请圣安。
游蒙日记(跋)
先生以羁縻达赖喇嘛之故,得游大漠南北,并于山脉、地势、风景、人情、矿质、森林、土产、牲畜,无不一一考求,雄乎伟矣。如飞马奔驰,动辄数百,英烈之风,令人不可逼视。虽毳幕生寒,沙场洒汗,在常人不能忍者,而先生独能耐之,则不能不因其事迹折服,其为人也。
窃尝涉猎两蒙舆图,举其著者而言,如军台商站,遐迩每有殊差保障藩篱要害,苦无标识。获观此记,则一目了然。且何者应设施,某事宜置备,寻章加按,特点标彰,足资有心边局者之参考,然则谓先生之日记,为策蒙之先导可也。
中华民国二年三月受业齐兆桂敬跋[54]
跋[55]
蒙古博迪苏之《朔漠纪程》今已整理完毕,即行付印。又取旧藏铅印本《游蒙日记》同时整理。此《日记》与《纪程》乃同时同行之作。著者李廷玉,字石忱,天津人,行伍出身,以州判为博迪苏使蒙的随员。行程虽同,而记事更为详备。凡人情之迷信,风俗之古陋,台站之疲敝,土宜物产之良窳,山川形势之险要,各地庙宇之宏敞,蒙古生活之艰苦,与夫历年治蒙政策之得失,尤以防范沙俄窥窬,三致意焉。对于各地市区的布置,贸易商业物价及矿藏等,无不述及。书前赵序称:“概括列举,洪纤縻遗”,殊非过誉。今以《使喀尔喀纪程》[56]及《朔漠纪程》两书相较,则此书确胜于前者。惟对于达赖颇多微词,称为刚愎自用、固执不通、妄自尊大、贪吝多疑,未必尽当,乃当时相见之人,观察他的行动,似仍不无可取,又描写他的体态、手段、行动、供给、行踪等较为真实。以目击之谈,乃属第一手资料,可作十三世达赖喇嘛传的补充材料。故与《朔漠纪程》二书,不仅视为漠北蒙区地理之书,亦研究藏族近代史者必备参考之作。今查撰究藏族史者,均未及此。特同付印,以供同好。
书中称特尔进即俄人德尔智[57],乃译者之不同。书中地名,前后译音不同,今加统一,偶有错误,也加改正,并加断句。对此书之加工,仅此而已。
吴丰培[58]识。
(全文终)
[注释及参考文献]
[1]经与1915年财政部印刷局出版的李廷玉《游蒙日记(铅印本)》(第34页)比对,发现吴丰培版《游蒙日记(手抄本)》中,写成“咱雅沙比”。详见1990年1月由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末蒙古史地资料汇萃》,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第672页。
[2]经与1915年财政部印刷局出版的李廷玉《游蒙日记(铅印本)》(第35页)比对,发现吴丰培版《游蒙日记(手抄本)》中,写成“敞”字。详见《清末蒙古史地资料汇萃》,第673页。
[3]在博迪苏五月初三的日记中,他写下“庙中设极高法座一,装饰华丽,询系为接待达赖喇嘛之用”(博迪苏:《朔漠纪程(手抄本)》,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1908年,第12页)。
[4]经与1915年财政部印刷局出版的李廷玉《游蒙日记(铅印本)》(第35页)比对,发现吴丰培版《游蒙日记(手抄本)》中,写成“札布”二字。详见《清末蒙古史地资料汇萃》,674页。
[5]那木囊苏伦(1878-1919),外蒙古独立运动领袖。清代外蒙古赛音诺颜部赛音诺颜旗札萨克和硕亲王,尊称为赛音诺颜汗。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12月1日,杭达多尔济与那木囊苏伦等一同拥戴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宣布外蒙古独立,成立大蒙古国,随即驱逐了库伦办事大臣三多等清朝委派的所有官员。外蒙古独立后,任命那木囊苏伦为首任内阁总理大臣。1913年1月11日,在那木囊苏伦任内阁总理大臣期间,大蒙古国方面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所谓《蒙藏条约》。1919年4月20日病逝,坊间传言其被毒死。
[6]经与1915年财政部印刷局出版的李廷玉《游蒙日记(铅印本)》(第35页)比对,发现吴丰培版《游蒙日记(手抄本)》中,写成“咱”字。详见《清末蒙古史地资料汇萃》,674页。
[7]在博迪苏当天的日记中,他写下“据京局来电云,用丙密电本,译不成文,请即查覆等语。查向来密码到局,局中查系密码,即照上开应投之处投递,不能代为译出。自出京来,已发丙密电四次,并无错误,且第四次由赛尔乌苏发电,亦系交库伦转发。此次电仍系致练兵处,乃复电来自京局,非练兵处,尤可疑也。与达阁学商酌,下次发电时,详询练兵处是否接到前电”(《朔漠纪程(手抄本)》,11页)。
[8]经与1915年财政部印刷局出版的李廷玉《游蒙日记(铅印本)》(第37页)比对,发现吴丰培版《游蒙日记(手抄本)》中,写成“燃”字。详见《清末蒙古史地资料汇萃》,679页。
[9]一瘸一拐地走。
[10]经与1915年财政部印刷局出版的李廷玉《游蒙日记(铅印本)》(第37页)比对,发现吴丰培版《游蒙日记(手抄本)》中,写成“咱”字。详见《清末蒙古史地资料汇萃》,681页。
[11]经与1915年财政部印刷局出版的李廷玉《游蒙日记(铅印本)》(第37页)比对,发现吴丰培版《游蒙日记(手抄本)》中,写成“饝”字。详见《清末蒙古史地资料汇萃》,681页。
[12]经与1915年财政部印刷局出版的李廷玉《游蒙日记(铅印本)》(第38页)比对,发现吴丰培版《游蒙日记(手抄本)》中,將“公”字去掉。详见《清末蒙古史地资料汇萃》,681页。
[13]经与1915年财政部印刷局出版的李廷玉《游蒙日记(铅印本)》(第38页)比对,发现吴丰培版《游蒙日记(手抄本)》中,写成“咱”字。详见《清末蒙古史地资料汇萃》,681页。
[14]在博迪苏当天的日记中,他写下“向浮屠膜拜者,踵接于途”(《朔漠纪程(手抄本)》,12页)。
[15]在博迪苏当天的日记中,他写下“拜发代奏达赖喇嘛谢恩及请入贡正折一件、咨奏事处、军机处、兵部、乌里雅苏台将军文各一件”(《朔漠纪程(手抄本)》,12页)。
[16]在博迪苏当天的日记中,他写下光绪皇帝传来的电报圣旨:“博迪苏、达寿电奏悉。达赖喇嘛既称愿即回藏,取道西宁一带行走,著沿途地方妥为迎护。惟现在蒙情困苦,所需驼马务令核减,以恤蒙艰。至该喇嘛遣徒入贡,具见悃忱,著准行。钦此”(《朔漠纪程(手抄本)》,12页)。
[17]在博迪苏当天的日记中,他写下“咨行达赖喇嘛”(《朔漠纪程(手抄本)》,12页)。
[18]公元1906年6月21日,是博迪苏代表中央政府第四次往见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博迪苏当天的日记中,他写下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相见的重要对话:“午后,往见达赖喇嘛,申明电旨之意,并询起程日期。据达赖喇嘛云:现与徒众商酌,尚未定议,大约五月底可以起程。达赖询及藏中究竟如何情形?英人如何交涉?答以藏约已定,一切平靖。达赖云:前在藏时,远隔君门万里,偶欲有所陈奏,或为驻藏大臣阻遏,不得径达。答以藏臣有会商藏事之权,若达赖所陈事关重大,该藏臣断不敢壅于上闻。如果实有阻遏情形,本大臣回京必为奏参,究系何任藏臣,何事未经代奏,请为指明。该达赖茫然不能指实也”(《朔漠纪程(手抄本)》,12-13页)。
[19]公元1906年6月23日,是博迪苏代表中央政府第五次往见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博迪苏当天的日记中,他写下“午后,往见达赖喇嘛。据达赖云:已定期五月二十七日起程,驼马如早备齐,二十七日以前,亦可动身。当询以驼马究用多少?达赖云:日内拟定数目,即行咨明乌城将军,必竭力核减。此次归去,无论藏中情形如何,眷怀故土,势难中止。惟未知朝廷新与英人订约条款若干,可否示知?答以俟到藏后,必由驻藏大臣知照。达赖再三恳询,答以窃闻藏约大致,英人绝不占并藏境,亦不干预藏中内治,中国并不准他国出而干预藏事。达赖云:英人通商一事,可否请朝廷宣示明白,答以上年正月业经降旨云:英人入藏,并未侵占地方。现在西藏业已平靖,一切照常等因。紬绎(笔者注:理出头绪)旨意,则通商一事,自当照常,请勿疑虑。达赖仍以愿睹全约为词,言之不已。因与达阁学密商,现虽携有西藏新约,应否全行宣布,未便擅专,似可电询政府酌夺。达阁学以为然。因答以达赖如欲闻藏中通商情形,可咨明本大臣再为据情代询政府可也。达赖又云:先年藏中行文,皆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会同钤用印文,自达赖第十世时,驻藏大臣琦善来藏,始自行钤印行文,喇嘛无从与闻,可否奏请规复旧制?答以此事关系重要,且事隔多年,其中有无别情,本大臣未携档案,无从详查,似乎不便代奏也。夕间,接达赖喇嘛咨文一件,系请钞示约文,并请转饬地方妥备驼马。”(《朔漠纪程(手抄本)》,13-14页)。
[20]在博迪苏当天的日记中,他写下“复军机处电一件,内陈达赖喇嘛愿闻藏约情形,可否请旨宣示。并请旨严饬乌城将军、甘督、西宁办事大臣多派员弁出境迎护达赖。是夕,库伦差弁送到延大臣一函,内附京电,当译出,云:本日奉旨,达赖喇嘛回藏,是否出自真心,途中有无逗留,均应随时体查,著派达寿随带员弁,沿途照料,将途次情形,随时电奏。俟到西宁,听候谕旨。博迪苏俟该喇嘛起程后,先行回京。钦此。”(《朔漠纪程(手抄本)》,14页)。
[21]在博迪苏当天的日记中,他写下“复军机处电一件,内陈博遵旨,俟达赖由咱雅班第达起程后回京,顺路随达赖至三音诺颜王府第分道东行。寿遵旨沿途照料,并将途次情形,随时奏闻等语。连前电并交霍弁玉福函送库伦延大臣排发”(《朔漠纪程(手抄本)》,14页)。
[22]藏文。
[23]经与1915年财政部印刷局出版的李廷玉《游蒙日记(铅印本)》(第40页)比对,发现吴丰培版《游蒙日记(手抄本)》中,写成“身”字。详见《清末蒙古史地资料汇萃》,688页。
[24]在博迪苏当天的日记中,他写下“达赖遣人馈米、粮、羊肉,受之”(《朔漠纪程(手抄本)》,15页)。
[25]公元1906年6月30日,是博迪苏代表中央政府第六次往见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博迪苏当天的日记中,他写下“咱雅班第达附近各部落王公演掼跤、跑马,为达赖送行,王公等先期约往观。是日乃先往见达赖,谢馈食物,并送达赖黄缎二疋,以申贺意。缘往观者皆须持物为贺也。达赖遣人肃客入行帐,陈酪浆、茶、果,演掼跤者约百余人,分队登场,多裸身,先向达赖合什膜拜,然后相对角技,两人相持,必令一人仆倒为胜。胜者仍向达赖合什膜拜不止,并与负者相抱为礼,跳舞而。是颇得尚武之遗意。”(《朔漠纪程(手抄本)》,15页)。
[26]氆氇。
[27]在博迪苏当天的日记中,他写下“达赖遣人约看掼跤,因料理公牍未竟,辞之”(《朔漠纪程(手抄本)》,16页)。
[28]经与1915年财政部印刷局出版的李廷玉《游蒙日记(铅印本)》(第40页)比对,发现吴丰培版《游蒙日记(手抄本)》中,写成“事”字。详见《清末蒙古史地资料汇萃》,689页。
[29]李廷玉所述魏源著《圣武记》,笔者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查询到1963年8月22日自日本山本书店购置入库的一函六卷《圣武记(附武事余记)》,其中第三卷第十三页原文为:“大雄涅槃,不闻转世,即宗喀巴经亦言达赖、班禅转生,止六七世,自后不复再来。今之黄教,非昔之黄教,尤非古之释教”。
[30]经与1915年财政部印刷局出版的李廷玉《游蒙日记(铅印本)》(第41页)比对,发现吴丰培版《游蒙日记(手抄本)》中,写成“寔”字(“寔”系“实”的异体字)。详见《清末蒙古史地资料汇萃》,689页。
[31]在博迪苏当天的日记中,他写下“达赖遣人约看跑马射的(即爱罕也),张羊皮九张为侯,射者耦进,先稽首于达赖前,然后角射,命中者绝少,甚矣,武备之不讲也。跑马者多蒙古小儿,上下山谷,绝尘而奔,先至者为胜。先至之马,即以献达赖,达赖系以哈达,浇以酪浆,旌其异也。是时,即有小喇嘛牵之向达赖致颂词,各旗王公赛跑之马,陆续遣人手牵以进,各致颂词。其大意系声明何人之马,并赞马之良好,绕马场三遭,三致颂词而退”(《朔漠纪程(手抄本)》,16页)。
[32]在博迪苏当天的日记中,他写下“霍队官自库伦回,带到军机处条电二件,当即译出。一系本日奉旨博迪苏、达寿奏悉。据称达赖喇嘛已定月内起程,取道由西宁一带,着乌里雅苏台将军、陕甘总督、西宁办事大臣等遴派熟习地势番情之员,沿途妥为照料,以利遄行,而资保护,毋稍遗误。钦此。一系枢府训示云:来电已进呈,除沿途照料,已另有电旨外,藏约系外交要政,未便宣示。尊处已将英人不干预藏中政治,亦不占并藏境告知,宗旨已明,何庸疑虑,即饬达赖知之。”(《朔漠纪程(手抄本)》,16页)。
[33]经与1915年财政部印刷局出版的李廷玉《游蒙日记(铅印本)》(第41页)比对,发现吴丰培版《游蒙日记(手抄本)》中,写成“派遣”二字。详见《清末蒙古史地资料汇萃》,691页。
[34]在博迪苏当天的日记中,他写下“乌城蒙妇有来与达赖磕头者,跋涉饥冻,伤一足,不能行,跧伏草中,日乞食以为活,哀其贫老,且悯其愚也。乃给驮驼送之归。午后,达赖遣堪布札木扬丹巴来见,该堪布现充贡使,于二十五日赍贡起程云。”(《朔漠纪程(手抄本)》,17页)。
[35]经与1915年财政部印刷局出版的李廷玉《游蒙日记(铅印本)》(第41页)比对,发现吴丰培版《游蒙日记(手抄本)》中,写成“实”字。详见《清末蒙古史地资料汇萃》,691页。
[36]经与1915年财政部印刷局出版的李廷玉《游蒙日记(铅印本)》(第41页)比对,发现吴丰培版《游蒙日记(手抄本)》中,写成“号”字。详见《清末蒙古史地资料汇萃》,691页。
[37]公元1906年7月9日,是博迪苏代表中央政府第七次往见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博迪苏当天的日记中,他写下“往见达赖喇嘛,询二十七日是否起程。达赖云:明日一准南行。当告以此去沿途照料,有旨著达阁学随同前往。博(迪苏)俟喇嘛起程后,同路至三音诺颜王府第,即分道回京矣。达赖询藏约事已否接回电?答以昨接枢府电示,以条约系外交要政,前既告知英人既不干预藏中政治及不占并藏境,即是约中最要关键。其他各条,电文简约,想未便明示云。达赖请将来电钞示,当即钞电知照”(《朔漠纪程(手抄本)》,17页)。
[38]在博迪苏当天的日记中,他写下“雨。午刻,达赖喇嘛起程,番乐前导,从者百数十骑。达赖乘黄缎肩舆,以四马驾之。行里许,下舆向北山顶石像宗喀巴膜拜,然后去(宗喀巴,为黄教之祖)。查达赖自本年三月初七日来咱雅班第达库伦,住此逾百日。该库伦疲于供億,闻蒙民言此间生计,恐三年不能复旧云。是日,发军机处一电,请代奏达赖起程日期”(《朔漠纪程(手抄本)》,17页)。
[39]经与1915年财政部印刷局出版的李廷玉《游蒙日记(铅印本)》(第42页)比对,发现吴丰培版《游蒙日记(手抄本)》中,写成“咱”字。详见《清末蒙古史地资料汇萃》,693页。[40]经与1915年财政部印刷局出版的李廷玉《游蒙日记(铅印本)》(第42页)比对,发现吴丰培版《游蒙日记(手抄本)》中,写成“氈帐”二字。详见《清末蒙古史地资料汇萃》,693页。
[41]经与1915年财政部印刷局出版的李廷玉《游蒙日记(铅印本)》(第42页)比对,发现吴丰培版《游蒙日记(手抄本)》中,写成“咱”字。详见《清末蒙古史地资料汇萃》,693页。
[42]经与1915年财政部印刷局出版的李廷玉《游蒙日记(铅印本)》(第42页)比对,发现吴丰培版《游蒙日记(手抄本)》中,写成“蒙民及喇嘛二千余”。详见《清末蒙古史地资料汇萃》,694页。
[43]公元1906年7月15日,是博迪苏代表中央政府第八次往见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博迪苏当天的日记中,他写下“午后,达赖遣人请会晤,与达阁学同往。达赖仍询藏约并询驻藏有大臣泰曾忝革达赖喇嘛名号,当告以此次朝廷既遣员慰问,原以保安黄教,注念番民,藏约一事,昨已明示宗旨,当于教权番俗,均无损害。达赖返藏,自可遵约办理。至于有大臣前事,达赖既未奉该大臣录旨知照,事之有无,未携档案,无从确查也(光绪三十年九月,驻藏大臣有泰奏革达赖名号。三十一年,又奏请问复,兹因达赖多疑,故以权词答之)。达赖意欲在三音诺颜王府小住,因催其及早起程,据称驼马备齐,即前进云。是日,发军机处一电,陈明遵旨回京及达赖行至三音诺颜王府第情形”(《朔漠纪程(手抄本)》,18-19页)。
[44]公元1906年7月16日,是博迪苏代表中央政府第九次也是此行最后一次往见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博迪苏当天的日记中,他写下“雨。午后偕魏部郎往见达赖辞行,并见三音诺颜王。据称达赖随从人多,苦于供億,甚恐其去之不速也。该旗盟长亦言,前达赖在咱雅班第达驻一百一十日,即羊只、米面、食物等一项计之,已费银二万二千一百四十余两。余如毡房、夫马、薪柴、零物等项,尚不在内。此款即摊之本盟各旗云。本日接到兵部由驿递回前代奏达赖谢恩原折,奉硃批:知道了。钦此。遂录旨知照达赖”(《朔漠纪程(手抄本)》,19页)。
[45]淡然喇嘛所述并不准确。其所述“八九年前”实为1895年瞻对乱事。自西藏地方官员管理瞻对后,百姓苦于虐政横征,不堪荼毒,数年必一内讧。到此时,瞻对势力更趋强盛,威慑附近土司,迫使依附;噶厦所派官员与明正土司之间更是越界构兵,混乱不断。四川总督鹿传霖要求西藏地方政府撤换瞻对官员无果,遂派遣川军包围瞻对,双方伤亡很大,僧官益西土丹派人向川军投降。有鉴于此,十三世达赖喇嘛答应撤换瞻对官员,并拟出新派官员名单交由驻藏大臣向皇帝报告,请求批准。川督鹿传霖知悉后,即向朝廷建议,瞻对为川省门户,应乘机收回,改归川属,派员管理。但中央政府顾虑此举可能刺激十三世达赖喇嘛及噶厦方面,未允准。详见邓锐龄、冯智主编:《西藏通史·清代卷(上)》,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4月,第563-564页。
[46]经与1915年财政部印刷局出版的李廷玉《游蒙日记(铅印本)》(第43页)比对,发现吴丰培版《游蒙日记(手抄本)》中,写成“喇”字。详见《清末蒙古史地资料汇萃》,697页。
[47]经与1915年财政部印刷局出版的李廷玉《游蒙日记(铅印本)》(第44页)比对,发现吴丰培版《游蒙日记(手抄本)》中,写成“实”字。详见《清末蒙古史地资料汇萃》,699页。
[48]在博迪苏当天的日记中,他写下“参观张家口陆军小学堂及蒙养高等两学堂,规模备具,学生纯谨朴茂,均属边郡之秀。因学生列队欢迎,乃为演说忠君爱国大义,似甚感动”(《朔漠纪程(手抄本)》,21页)。
[49]张家口。
[50]佐藤安之助(1871-1944),日本陆军将军,众议院议员。1895年军事学院步兵少尉毕业后作为关东市政府军部的他,受命担任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公共办公室秘书长,后转任日本驻瑞士使馆军官,在巴黎和会充当全权代表。1919年晋升为陆军少将。1928年参加第16届众议院大选并获胜。
[51]在博迪苏当天的日记中,他写下“入居庸关,宿沙河镇”(《朔漠纪程(手抄本)》,22页)。
[52]李廷玉1906年夏所述北京辟才胡同刚刚从劈柴更名为辟才。此地元朝有大石佛寺,属元大都咸宜坊;明朝胡同称大石佛寺;清朝改称劈柴胡同,相传这一带曾有劈柴市场。1905年,天津人臧佑宸在该胡同内创办京师私立第一两等小学堂,并以“劈柴”二字谐音“辟才”,将该胡同改称“辟才胡同”,取开辟人才之意。今天,这是一条东西走向——东起西单北大街,西到太平桥大街,全长877米,均宽32米,为沥青路面的通车胡同。
[53]在博迪苏当天的日记中,他写下“午正抵京”(《朔漠纪程(手抄本)》,22页)。
[54]关于齐兆桂的生平不详,经查询仅发现两笔:一笔是1916年3月8日被中华民国总统任授为昌武将军行署上士;一笔是1920年江西省长戚扬撰《重修白鹿洞书院碑记》,里面提到了齐兆桂,碑文称:“自科举停罢,横舍漂零,鞠为茂草。变革后,戎马呐,益荒废不堪……前星子县知县汪知本、齐兆桂暨现任吴品藕,先后申请修复,均报可。”
[55]吴丰培为《游蒙日记》所亲撰《跋》,笔者仅发现在《清末蒙古史地资料汇萃》中刊载,详见《清末蒙古史地资料汇萃》,第713-714页。
[56]《使喀尔喀纪程草》为清升寅撰,线装二册,半叶七行,行十六字,无栏线。序一《使喀尔喀纪程草序》,尾叶朱芳曾拜譔并书;序二《使喀尔喀纪程草序》,尾叶愚弟蒋廷恩;序三《使喀尔喀纪程草序》,尾叶确庵徐养灏;题词《使喀尔喀纪程草题词》,尾叶香岩愚弟桂龄拜题,钤“继卿”朱文方印;正文《使喀尔喀纪程草序》,尾叶下钤“继卿”朱文方印。
[57]德尔智(1853-1938),俄国史籍称为洛桑·阿旺·多尔日耶夫;西文史籍称为阿旺·多尔吉耶夫或阿旺·多尔吉·堪德彻加。德尔智用蒙古文书写了自传体日记,该日记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更多关于德尔智的信息,详见李廷玉著、韩敬山校注整理:《游蒙日记(上)》,《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58]吴丰培(1909-1996),当代藏学家。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院,曾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编辑,辅仁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讲师、副教授等职。新中国成立后,调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图书馆工作,从事文献资料的整理和西藏史地研究。著有《清季筹藏奏牍》《清代西藏史料丛刊》《清代藏事奏牍》《抚远大将军允奏稿》《清代布鲁克巴资料汇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