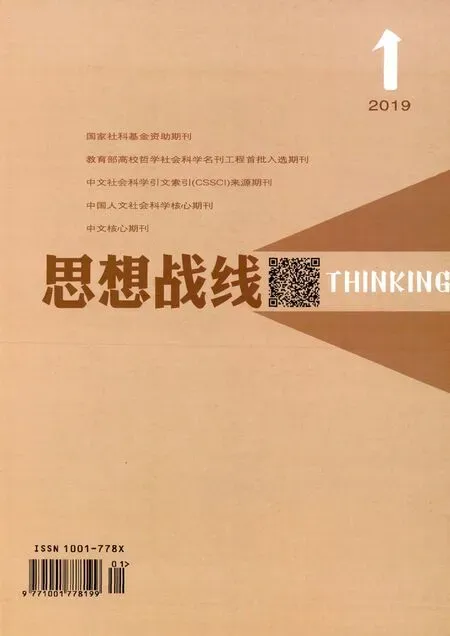间性审美风格与晚明文学现代性
妥建清
在中国以道德是尚的文学—文化传统中,南朝文学或以内容极写声色而被视为“不道德”,或以形式注重声律而被视为唯美主义。无论是刘勰批评南朝文学“轻绮”“力柔”(《文心雕龙·明诗》),还是李白声讨“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大雅久不作》);无论是杜甫警诫“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还是闻一多批判南朝文学为“美丽的毒素”;[注]闻一多:《唐诗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19页。无论是王瑶斥责南朝文学自甘“堕落”,[注]王 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3~284页。还是钱钟书嘲讽梁元帝萧绎的《耕种令》竟为“娱耳目”;[注]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397页。如是种种有关南朝文学“颓加荡”的控诉,[注]“颓加荡”当为英语“decadence”音义俱谐的汉译,今则译为颓废。就汉语语境而言,“颓加荡”一词从词源考古学来看,连类出现于唐代李白的《古风》之中,“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限。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李白此诗直指建安以降魏晋六朝诗风为颓波,声称其诗法渐失而绮丽日盛乃实为颓废的表征。但李白此处所谓“荡”是与“激”对举,因而是“激荡”并非“放荡”之义,因此,李白虽然连类使用“颓加荡”,但重点是“颓”而已。而将英语“decadence”首先译为汉语的当为邵洵美。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30页。邵洵美在《花一般的罪恶》中露骨地歌颂感官享乐主义,并将“颓废”翻译为“颓加荡”(以其诗《颓加荡的爱情》而得名)。颓加荡的汉译显然表征着其所理解的颓废的含义:颓堕,放荡,这也是颓废被冠之以“不道德”的恶谥而遭世人诟病的佐证。往往湮没了对南朝文学审美自觉的理性的反思。[注]不乏为南朝文学“鸣不平”者,如施蛰存认为,南朝宫体诗辞藻绮丽,虽被盛唐李、杜同侪拒斥而遭受压抑,但继则复兴于李贺、李商隐诸人诗歌之中,以致使盛唐诗能开出新的境界。参见施蛰存《唐诗百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75页。章培恒等人将南朝文学视之为美文学,并且指出南朝文学已经发现文学之美。参见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上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61~370页。今人许云和重新反思南朝文学颓废的原因,指出,以宫体诗为代表的南朝文学大肆铺写欲色实是承袭佛经的写法。参见许云和《汉魏六朝文学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81页。实际上,若以“去道德化”的审美眼光来审视南朝文学,南朝文学业已表现出间性审美风格。此种审美风格使用对偶、数典、声律等诸多感性形式,进而显现出融音乐、绘画、建筑等多种审美于一体的间性之美。[注]王 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4页。赓续南朝文学间性—颓废审美风格的传统,晚明社会由于商品经济的支撑性力量,人欲天理化思想的普遍播散,以及文人文化的自觉等诸多原因,宰制中国文学主流的、代表雅正伦理价值的诗歌逐渐衰落,作为晚明文人文化之表征的传奇、小说等通俗文学,则成为了晚明文学的主流,其使用多种审美形式,赋予了晚明通俗文学间性审美风格以新质。
一、文体代降:文体自律与他律的双重合奏
雅思贝尔斯“轴心时代”的反思,着眼于世界文明历史的普遍性架构。其指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中、西、印等不同的文明中心出现了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而三种异质文明的共时性的文明突破,成全了多轴心的文明发展史。此后,各大文明都有了进行自我理解的基本架构,由此形成文明回跃性的特点,“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注][德]卡尔·雅思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4页。轴心期文明突破的实质是以人类理性的自觉为标志,开始对于周遭世界进行理性的认识与反思。
相较于外向超越的西方文化,中国文化认识到“神”的局限性,并未跃出人世来探求神的可能性,而是转向人世之中,藉由精神实体意义上的“道”来代替“巫”所崇奉的“神”,以体“道”的“心”来代替“巫”沟通神人的功能,将巫文化予以理性化,从而形成内向超越的文化类型。巫文化本是融诸多文化形式于一体的大文化类型,具有文化整体性、全息性的特征,“在早期文化实体中,理性的、感情的、想象的和神秘的成分都混杂交织在共史统一体(Synchretic unity)中。神话部分是科学,部分是艺术,部分是宗教”。[注][美]E.拉兹洛:《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闵家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92页。巫文化理性化的后果在于,逐渐出现宗教、诗等各类形式的萌芽。但是,当时的诗歌并未与音乐、舞蹈相分离,而是融合为一体的混合艺术。《虞书·舜典》《乐记》《毛诗序》等都已指出诗、乐、舞的整一性。此种混合艺术的共同命脉是节奏,纵使嗣后各门艺术日益分化,但是仍然保留着节奏的共同要素。[注]朱光潜:《诗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页。诗歌在独立发展的过程中亦出现唐诗、宋词等不断分化的文化现象。诗歌长期以来占据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宰制地位,词较之于诗在字数、用词、韵律、主题等方面都有所变化,但是词作为“诗之余”,仍未跃出诗的领域。散曲则不然,其较之于词更俗,它可以直接进入戏曲并成为戏曲的重要部件。至中晚明,诗歌从中国文学的中心地位逐渐滑落,传奇、小说等通俗文学则成为彼时文学的主流。此种由诗至词再到曲直至小说的文体变迁,主要取决于文体自律和他律两方面的原因。
美国科学史家K.默顿(R.K.Merton)指出,尽管科学史上多种科学发现的独立存在方式是科学发展的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但是,任意单一的科学发现某种意义上都是潜在的多重科学发现。[注][美]R.K.默顿(R.K.Merton):《科学社会学》,鲁旭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70~511页。此说不止适用于科学史,亦适用于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上所谓“文体代降”之说即是此种历时性的多重发现。虞集、叶子奇、胡应麟、焦循等人都有相似的说法。就文体自身而言,单一文体的兴衰可以诉诸博弈论来进行解释。单一文体的自身的形式如同博弈论中游戏者所遵循的游戏规则,面对有限的游戏规则,能够最大程度的挖掘游戏规则潜能的游戏者才能成为优胜者。但是,当游戏规则的潜能被挖掘殆尽之时,其业已表明此种规则的衰落。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就明确指出,诗文代降是由于文体自身形式的固化所致,“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有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注]顾炎武:《日知录集释》,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94页。近人王国维从文学进化意义上亦认为,单一文体的盛衰取决于文体自身的阀限,[注]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3~14页。进而揭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马克思曾以希腊的艺术、史诗为例指出,尽管希腊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但是希腊艺术和史诗依托希腊神话,“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61页。竟然成为西方文化史上的绝响,乃至于希腊艺术和史诗迄今“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62页。马克思由此提出文学艺术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命题。马克思此说表明,文学发展不惟根本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与文学文体自身的盛衰亦密切攸关。实际上,设若认为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那么文学文体的变迁实是文学语言变化的表现形式。此与俄国形式主义所揭示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理论确有相似之处。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形式的变迁系于文学语言的变化,文学语言“由熟转生”(defamiliarization)正是文学语言变化的一般规律。文学语言的变化不仅使得慢审美鉴赏成为可能,而且推动着文学文体的变迁,从而形成所谓“一代有一代文学之盛”。
文学的文体代变亦是与社会、政治等文体的他律方面相涉。刘勰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马克思主义亦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的变迁根本上决定着文学形式的变化。卢卡奇在解释史诗与小说文体所产生的存在状态差异时曾指出,史诗产生的年代是人和世界整一性存在的时代,充满“家园”之感,“彼时是一幸福的时代(happy age),星光闪耀照亮所有可能的路径,星罗棋布(the starry sky)的天空便成为条条道路的地图。诸多事物新奇而不陌生,令人有冒险之感。大千世界宛若家园,因灵魂燃烧之火与天空之星同质。世界和自我,光与火,明显有别而又彼此永不分,因为火是光的灵魂,光是火的外衣……”[注]Georg Lukacs:The Theory of Novel,Cambridge, MIT Press,1978,p.29.西方史诗产生的时代,人与世界是整一性的存在,我“在世界之中”而非在世界之外,原初意义上自我与他者尚未分化为主客体,物我交融的生存状态使得人类获得古典的安详与幸福,卢卡奇赞叹这是人类的幸福时代。而近代人与世界之间的整一性存在分裂了,人与世界的对立取代了人“在世界之中”的原初认识,具有主体意识的人主宰着客体世界,世界之于人类成为被征服的对象,人与世界的“我与你”的亲在关系彻底瓦解。结果,孤独的个体尽管具有理性的自决成为人,但是因与世界家园的分离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而不复为人,充满着永恒的乡愁,渴望着与世界的融合,成全人“在世界之中”的整一性。由此小说出现了,正如卢卡奇所再三嗟叹的“康德的昭昭之心的碎片(Kant’s starry firmament)仅仅闪耀于纯粹认知的黑夜,它不再照亮一切孤独的流浪者的旅途(solitary wanderer’s path)”。[注]Georg Lukacs:The Theory of Novel,Cambridge,MIT Press,1978,p.36.卢卡奇从存在的角度指出,史诗与小说文体的产生与人类社会生存情境息息相关。
中国传统文学由诗发展到词曲,由说话发展到白话小说,如是文体变迁某种意义上亦是因社会生活的不断丰富促使人性的发展需要所致。章培恒等人几经修改的《中国文学史》,即是从中国文学表现人性不断演进的历史角度来重写中国的文学史。其承续初版“个人性”等关键词,明确指出,以人的解放为目的的中国近世文学,肇始于以关汉卿等人为代表的金末元初的文学创作,经历明代、清代的播散最终汇入“五四”新文学的大潮之中。[注]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上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要言之,文学文体的变迁不唯是由于文体自身的代降,而且与文学他律或社会生活,或存在状态、或人性需要等原因都有必然的联系。中晚明之际,戏剧、小说等通俗文体的兴起亦是文体自律与他律合奏的结果。
二、万历五十年无诗:晚明通俗文体的兴起
晚明文人徐世溥曾在一封与友人的信札中评论当时文化界的状况。他列举有明万历一朝的文化界精英,从道德风节到博物穷理,从天文历法到书法字学,从书画词曲到攻玉刻印,均为一时之盛,但是文化界最大的变化即是“无诗”,“癸酉以后,天下文治响盛。若赵高邑、顾无锡、邹吉水、海琼州之道德风节,袁嘉兴之穷理,焦秣林之博物,董华亭之书画,徐上海、利西士之历法,汤临川之词曲,李奉祀之本草,赵隐君之字学。……而万历五十年无诗,滥于王、李,佻于袁、徐,纤于钟、谭”。[注]周亮工:《周亮工全集》,朱天曙编校整理,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年,第94页。徐世溥“万历五十年无诗”之说并非故作惊人之论,晚明诗坛赓续前七子的风流余韵,公安派、竟陵派等人的诗歌创作亦非乏善可陈。但是,徐世溥对当时诗坛大唱衰歌,实是强调晚明诗风纤、佻,与万历五十年间其他方面的文化成就相比,诗歌的文化中心地位业已衰落。如果拉开历史的距离,相较于唐诗、宋词,明代并非以诗词见长,“万历五十年间无诗”不只是晚明诗风不振的结果使然,更是文体代降的规律所致。
宰制中国文学主流的诗歌从中心地位的滑落,乃是社会的“革命”性事件。诗歌作为社会道德教化的主要工具,早在先秦之际就已经被肯定。孔子儒家首先确立诗教的合法性。孔子给予“诗”极高的令誉,“诗”寄予着他“为人生而艺术”的理念。[注]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页。第一,孔子所说的诗主要是指《诗》三百篇,它是作为对话交流的需要为人所引用的。在春秋之际,无论是在外交场合还是其他公共空间,引用《诗》三百篇已经成为普遍性的风气。《诗》三百篇作为公共交流的工具,不仅是当时媒介形塑的结果,纸质媒介的缺乏,口语交流成为主体,而且更是古典时代人与人的亲切感,以及渴望沟通的需要使然,它并没有把人视为主客分化意义上被认知的对象,而是强调主体之间相互商量来涵咏人生。第二,《诗》三百篇至汉代才被尊奉为经,孔子删诗业已开启《诗》三百篇的经典化进程。但是,孔子所论的诗主要是宗教颂辞和历史文献,尽管其中已经具有审美的因素。朱自清、[注]朱自清:《诗言志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页。闻一多、[注]闻一多:《神话与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1页。顾颉刚[注]顾颉刚:《顾颉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7页。等人都从词源学的角度考证“诗”的起源,指出“诗”在原初意义上并非是纯审美的文学类型。实际上,就先秦中国审美思想史而言,由审美意识积淀而形成的中国古代审美思维,具有泛审美化的特点。泛审美并不是纯粹的审美,一方面是说审美的范围广延,举凡自然宇宙、祭祀礼仪等都可纳入审美之域,礼与乐都具有美;另一方面则是说审美与宗教、政治等相混杂,审美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因此,孔子所论的《诗》应当是泛指具有一定的审美意味的作品。第三,孔子论诗应为论人,诗歌作为内在超越的文化类型的代表,尤能表现出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特质。钱穆从中国本位文化的维度指出,中国诗歌具有鲜明的人文精神,传统诗歌的背后总是站着一个人。[注]钱 穆:《中国文学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14页。不惟如是,中国文学的此种人文精神亦表现在中国文学理论之中。从《易·系辞》“近取诸身,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卷九),到刘勰《风骨篇》“词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文心雕龙·风骨》);从曹丕《典论·论文》说孔融“体气高妙”(《典论·论文》),到钟嵘《诗品》“陈思骨气奇高,体被文质”(《诗品》);如是种种,此类气、骨、力、魄等都是人化的结果。正如钱钟书所言,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在于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注]钱钟书:《谈艺录读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93页。中国文学及其文学理论人化的特质,致使孔子儒家更为重视诗歌所具有的美人伦、助教化的重要作用。孔子儒家认为,不应陷溺于诗歌审美娱乐的次要目的,遗忘其道德教化的主要作用。赓续孔子诗教“成教化,助人伦”的传统,孟子揭橥“知人论世”之说。孟子并非是从诗的本体角度出发强调诗歌的审美作用,而是将“人”与“世”置于“知”的首位,通过对诗文的释读进而达至对于人的理解。[注][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嗣后,荀子进一步阐发广义的诗歌的伦理教化作用,指出其关乎国家治乱兴衰:“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注]梁启雄:《荀子简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77~285页。第一,荀子基于人性恶的观点,认为音乐源自人的内心情感,而情感作为非理性之物常常表现为声音的动静,容易流于放荡。由此,荀子提出应通过先王制雅颂之声来规范和引导人的情感。第二,荀子从正反两方面揭示音乐对于国家的治乱与兴亡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音乐依托人心的中介作用,把人对于现实的种种情感予以审美的呈现。因此,音乐之声关乎民心,民心所系国家社稷的安危。荀子认为,音乐之声中平,那么民心和平而不流于放荡。音乐之声庄严肃穆,民心肃静而不溺陷于混乱。如此国家团结,外敌不敢冒犯,百姓也能安居乐业,以至君民皆可同乐,反之则国破家亡。第三,荀子强调“乐和同,礼别异”,通过礼的外在教化和乐的内在审美沟通作用,可以使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和睦共处,最终实现孔子礼乐之治的美好社会愿景。如是种种,诗歌在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传统中所系重大,尽管儒家文化并未赋予诗歌纯粹的审美价值,但是诗能够“美人伦,助教化”,成为实现儒家礼乐之治的社会理想的重要工具。
但是至于晚明之世,彼时社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以白银资本为代表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导致晚明社会陷入失序状态,雅与俗,士与商,道德与娱乐的边界日渐模糊,以至如马克思所言“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晚明社会遂出现浮世绘般的淆乱之境。此种颓废(de-cadence,意为去节奏化,即失序)时代的社会生活,促使人性具有多方面的需要。此种人性需要由现实延伸至于文学领域,进而出现使用音乐、绘画、建筑等多种审美形式于一体的间性艺术形式,诸如以南戏为基础的晚明传奇等。由此,晚明戏剧、小说等作为间性艺术的通俗文体的兴起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戏曲、小说等通俗文体在向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传统文学领域内难以登大雅之堂,文人士大夫常以写戏曲、小说为耻,署具雅号而非真实姓名。纵使清代官修的《四库全书》几乎把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收罗殆尽,但是唯独未予著录戏曲、小说。戏曲、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学的末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以戏曲而言,尽管其起源可以上溯至上古巫觋歌舞和春秋之际的古优笑谑,直至唐宋的歌舞剧及其滑稽剧,但是到元代之时,戏剧才日渐成熟,成为有元一代文学之盛。相较于元代杂剧的兴盛,中晚明消费文化的勃兴为传奇、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创作和传播提供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晚明社会无论在吃、穿、住、行等方面,还是文化消费等领域,都出现为史家所称道的“革命”,中晚明传奇、小说等通俗文学,正是借助消费文化的动力支持才能普遍流行。叶盛在《水东日记》中指出,中晚明书坊在利益的驱动下大肆刻印小说杂书,读者遍及全社会,竟至于官方与士大夫都对此予以认同,“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有官者不以为禁,士大夫不以为非,或者以为警世之为,而仍为推波助澜者,已有之矣”。[注]叶 盛:《水东日记》卷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3~214页。沈德符指出,《打枣竿》《挂枝儿》等民歌的传布,业已达至令人骇叹的境地,“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兴世传诵,沁人心腹。……真可骇叹!”[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47页。尤有进者,“元杂剧”实际上亦是晚明的发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是晚明社会印刷文化型塑的结果。臧懋循的《元曲选》一般是元杂剧研究的基础性文献,被认为真实反映了元代的思想,而其实,臧懋循的《元曲选》需要回到万历年间的语境中来加以研究。选本亦如著述,它也打上时代的烙印,选什么、怎么选以及如何修订,都是与作者以及所处时代密切相关的。现在的研究者通过检视更早流传的少数元杂剧版本认为,臧懋循不仅改写了早期元杂剧文本的效果,诸如臧懋循倾向于大团圆结局,而且更是改变了文本的思想,使其更符合于他所认同的儒家礼教。[注][美]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刘倩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60~161页。
由于晚明消费文化的推动等诸多原因,彼时文士把事关伦理教化的大道融于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化消费的热情之中,指认戏曲、小说等通俗文体亦具有载道的重要功能。相较于近代之文,袁宏道给予民歌俗曲等通俗文体“足以传世”的令誉。[注]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钱伯城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87~188页。明清易代之际的李渔则认为传奇有三美,“有裨风教”被视为传奇的“一美”。(《笠翁文集·香草亭传奇序》)清初的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从历史变迁的维度高度肯定以戏曲、小说为代表的“俗”文化的意义,其指出,“雅”文化源于“俗”文化,只有以“俗”文化的发展为基础,才能创造出新的雅文化,“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戏文小说乃明王转移世界之大枢机,圣人复起,不能舍此而为治也。……”[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106~107页。如是种种,戏曲、小说等通俗文体本为中国传统文学的末流。然而,晚明文士却赋予其事关风教的重要意义,将戏曲、小说等通俗文体抬举至与代表雅正伦理价值的崇高文体诗歌相当的地位,无怪乎王夫之批评到:“万历壬辰以后,文之俗陋,亘古未有。”[注]王夫之:《薑斋诗话》卷二,舒芜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79页。诚然,对俗之理解不尽相同,但是,晚明以传奇、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体的普遍流行,不仅表征着文体代降的规律,而且,其将小说等通俗文学的缺陷与功效无所甄别地进行赞美,实已表现出颓废风格之意。嗣后晚清的严复提倡“新小说”,梁启超竭力强调“新小说”具有不可思议的改造社会的功效,其与晚明文士之说一脉相承。王德威揭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论,为晚清小说被压抑的现代性张本,其认为,晚清文学的启蒙意义正是孕育在严复、梁启超所贬抑的“以浮华代自制”的颓废气质之中,“晚清小说的现代性既不表现于严复心目中的载道理论,也不表现于梁启超的末世想象;它其实是由严及梁所贬抑的‘颓废’气质中迂回而生的”。[注][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页。实际上,此种颓废风格并非肇始于晚清,而是发端于晚明。在此意义上,没有晚明,何来晚清?
三、间性之美:晚明通俗文学的颓废审美风格
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现实”作为文学四要素之一乃是文学的源泉,文学则是现实的镜像,文学通过反映现实进而观察现实的变化,现实则通过文学以便为人所把握。同构于晚明颓废的社会审美风格,晚明以传奇、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由于彼时情欲社会的世情表达的需要,从而显现出间性—颓废文学审美风格。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人欲天理化思想的互动,刺激着晚明消费文化的勃兴,以描摹世情为主的传奇、小说等通俗文学的流行自然不在话下。就晚明传奇而言,尽管其不乏对当时社会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的反映,但主要的仍然是以描摹世俗风情为主的风情剧。郭英德的研究表明,在1587~1651年间,可考的传奇作家作品约为780种,其中可考证题材者631种,风情剧独占泰半之多。[注]郭英德:《明清传奇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61页。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金瓶梅》的出现正是晚明社会的时尚使然,“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谥,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注]《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9~190页。郑振铎亦认为,“在这淫荡的‘世纪末’的社会里,《金瓶梅》的作者,如何会自拔呢?”[注]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载《文学》创刊号(北京:北京生活书店,1933年7月),参见周钧韬《金瓶梅资料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83页。
晚明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情欲书写,也并非弗洛伊德性欲升华理论所说的“未能满足的愿望的升华”,而是“欲望由现实至文本的延伸”。弗洛伊德认为,现实情境中未能满足的愿望诉诸于文艺等幻想的方式制成代替品,给人以想象性的满足。但是,弗洛伊德将文本视为抑制被压抑的性欲盲目、无序的力量,文本作为性欲释放的结果而予以解释。美国学者博萨尼(Leo Bersani)批判性地诠释弗洛伊德的观点指出,艺术创作并非压抑性的欲望的升华,而恰是开放性的“欲望的重复和延展”。在此意义上,文艺创作只是性欲释放的开始而非结果。[注]参见[美]利奥·博萨尼《弗洛伊德式的身体》,潘源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博萨尼改造弗洛伊德的“性欲升华”理论具有积极的意义。以此观照南朝文学,宫体诗人将现实生活中生理的享受衍生至心理,求得更为持久的满足。正如闻一多所批评的:“从一种变态到另一种变态往往是个极短的距离……”[注]闻一多:《唐诗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19页。王瑶亦指出:“这正是把放荡的要求来寄托在文章上,用属文来代替行为的说明。……可以在变态心理上得到安慰,而且即以此为满足。”[注]王 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96页。他们将现实生活中的不满移入文学世界之中,进而表现出所谓融音乐、绘画、建筑之美为一体的,具有间性之美的颓废审美风格。
不惟南朝文学如此,晚明传奇、小说等通俗文学亦是如此。宋明宰制儒家以身体不完善的逻辑预设,强调通过身心合一的修养功夫达至身体完善的理想境界。其秉承孔孟下衍的践体知仁的方式,将伦理化的心视为统领感性肉身的基础性存在,通过心之于肉身的牵引、肉身之于心的向往的心—身日常修习功夫,成就身心合一的儒家身体哲学传统。但时至中晚明,随着消费文化的发展,王阳明“心即理”的思想经王学后裔发挥性的诠释,由伦理本体之心不断扩展至感性的肉身,出现了对感性身体的日益关注。王艮认为,尊道即是尊身,尊身即是尊道,其赋予儒家传统伦理所贬抑的肉身至宇宙大道的境界:“知保身者,则必爱身;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敬人,则人必敬我;人敬我,则吾身保矣……”[注]黄宗羲:《明儒学案》,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15~716页。王艮遵身之说的身体,渐已突破传统伦理化身体的边界,赋予了感性身体一定的合理性。由此,晚明思想文化场域逐渐兴起以身体伦理化的名义肯定感性身体的思想,其表之于晚明审美领域,即是出现以身体间性为基础的颓废审美风格。此种风格既包含文学审美风格,又包含社会审美风格,并且,社会审美风格决定着文学审美风格,文学审美风格反映着社会审美风格。因此,如果说在现实生活世界中,情欲已经穿越雅俗的边界,那么随着此种欲望的流动,在文学想象的世界中,其亦穿越单一文体的阀限,表现出融合多种审美形式的间性—颓废审美风格。马克思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4页。马克思认为,人作为有生命的存在,并不只是自然物或者只具有自然属性,人还需要更高境界的精神诉求与审美追求,但是感性欲望的需要则是人的基本的需要。晚明社会生活的此种情欲诉求,需要彼时文士通过一定的文学形式予以表现,于是戏曲、小说等具有间性之美的通俗文体适足以为用。
晚明传奇、小说等通俗文学作为文人自觉的产物,本质上是一种文人文化,其尤为重视文学形式之美,从而表现出融和多种审美形式的间性—颓废审美风格。以戏曲而言,如果说元代杂剧的繁盛是低层文士“不得已”的结果,那么,晚明传奇的流行则是文人学士“自觉”的产物。追溯元代戏剧繁盛的原因,王国维认为,其与科举制度的废除有关。[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7页。元代蒙古人的统治废除科举制度,并且将人分为四个等级,南人的地位最低,掌握汉文化的知识人过多的精力无处耗散,于是转移至戏曲等文学创作之中,由此元代杂剧方能与唐诗、宋词相互媲美。狩野直喜认为,元代杂剧的兴起,乃是元代低层知识人“不平则鸣”的结果使然。[注][日]狩野直喜:《中国小说戏曲史》,张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1~183页。一方面,元代蒙古统治者不尚汉学,统治阶层的文化水平较低。[注]马克思认为,思想文化的主导权取决于经济领导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2页。)赓续马克思之说,葛兰西进一步提出“文化霸权”的理论。葛兰西指出,以教育方式为基础的文化霸权是统治阶级合法性的表征,它通过主导文化的建构,形塑社会的知识、道德等权力规约系统。([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论文学》,吕同六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页。)由于元代蒙古统治阶层不尚汉学,中国古文学在元代的衰落则是必然,古文学的衰落与元杂剧的兴起是一体之两面。另一方面,由于元代废除科举与等级化的政策导致低层知识人内心产生不平,元代杂剧的作者除少数是文人学士之外,大部分则为低层知识人,元曲即是其“不平之鸣”的结果,正如胡侍所言,“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抒其怫郁感慨之怀,所谓不得平而鸣焉者也。”[注]胡 侍:《真珠船》卷之五,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5页。吴伟业亦言:“士之困穷不得志,无以奋发于事业功名者,……其驰骋千古,才情跌宕,几不减灭屈子离忧、子长感愤,真可与汉文唐诗宋词连镳并辔”[注]徐庆卿辑,李玉更定:《一笠庵北词广正谱》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 748册影清青莲书屋刻本。……由此可见,元杂剧作为元代低层人士“不得已”的产物,成就了元代文学之盛,而中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消费文化的勃兴使得传奇、小说等通俗文体成为文人学士自觉的结果。清人赵翼《二十二史劄记》曾指出,晚明文士通俗文学的自觉有赖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的支撑:“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自放不羁,每出名教外”,“可见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故文人学士得以跌荡于词场酒海间,亦一时盛世也。”[注]赵 翼:《二十二史劄记》订补本(下册),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83~784页。
晚明以传奇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作为彼时文人自觉的产物,尤为重视其形式之美,举凡传奇的唱曲、宾白,乃至结构形式,都表现出“人工化”的特征。按照一般说法,中国戏曲元代之际始告大成,其包含唱(含白)、乐、科(舞)以及剧情,至中晚明则追求形式美的发展。以元、明戏曲的唱曲而言,元杂剧以北曲为主,明传奇以南曲为主。由于元杂剧的主创人员并非文人学士,而是社会下层的知识人,受众亦为低层的妇孺大众,加之元代上至统治者,下至庶众的文化水平都较低,因此,元杂剧一般使用北方方言,喜欢用俗字。中晚明传奇以南曲为主。随着元明易代,南曲在有明一代渐盛。而传奇的作者大部分为文人学士,文人学士以作诗文的态度参与传奇创作,其常常较少使用方言俗字,多用典雅华丽的文字。兼之中晚明出版革命而催生的“知识社会”的形成,传奇得以在中晚明社会广泛播散。因此,就唱曲而言,中晚明传奇由文人学士创作的以南曲为主,从而更为重视戏曲的音乐之美。以宾白而言,元代杂剧的宾白并非出于文人学士的“有心”创作,往往为舞台演出时的即兴之作,宾白自然而不事雕琢。明代传奇由于文人学士的参与创作,其宾白多是典雅的诗文,讲究用字、声律,多事雕琢呈现出绘画和建筑的美。以唱而言,元杂剧严格限制一人主唱,其他人只能道白,不能唱。晚明传奇承继南戏而来,凡登场者皆可唱,又有合唱、分唱、接唱、独唱等不同形式。故而就元、明的戏曲形式而言,中晚明传奇更重视形式的华美。王国维以汤显祖为例指出,元、明杂剧有人工与自然的区别,“汤氏才思,诚一时之隽,然较之元人,显有人工与自然之别”。[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28页。狩野直喜亦指出:“杂剧乃元代古文学之衰而出者,其作者之中有如俳优等无学之辈,故曲中随处可见俗语,即精于文字之雕琢与修辞之技巧者寡也。……然明清传奇之作者不同矣,乃所谓文人学士以其余事而作剧也。彼等有古文学之趣味,故作剧动辄如作诗,亦以曲雅婉缛之字句入之。”[注][日]狩野直喜:《中国小说戏曲史》,张 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4页。由此,中晚明戏曲作为彼时文人文化的表征,融诗词、音乐、舞蹈等多种审美形式于一体,进而表现出间性—颓废审美风格。
最后,晚明传奇等通俗文学的此种间性—颓废审美风格,正可以与西方唯美主义所表现的颓废审美风格进行对话。西方唯美—颓废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波德莱尔从艺术间性(inter-art)的角度指出,颓废审美风格作为文化或文明高度成熟的产物,表现出不同艺术形式的相互融合:“今日每一种艺术都暴露出入侵临近艺术的欲望,画家引入音阶,音乐家使用色彩,作家运用造型手段,而其他那些令我们不安的艺术家则在造型艺术中展现出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哲学,这难道不是颓废的一种必然结果吗?”[注][法]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347页。“现代诗歌同时兼有绘画、音乐、雕塑、装饰艺术、嘲世哲学和分析精神的特点……”[注][法]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23页。如是种种,波德莱尔认识到,以身体间性为基础的审美共通感,不仅承认现代意义上价值分化的正当性,而且强调以审美作为现代交往的重要方式。一方面,美、丑二元对立被美、丑相对说所代替,丑恶遂为审美所肯定;另一方面,其沟通身体五官形成通感,促使各种艺术形式自由交流,表现出间性—颓废审美风格。而此种间性—颓废审美风格打破各种艺术形式的陈规,使用多种艺术形式,正是现代文化或文明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尽管西方近代唯美—颓废主义与晚明通俗文学所表现的间性—颓废审美风格不尽相同,西方近代唯美—颓废主义所表现的间性—颓废审美风格作为审美现代性的重要面向,以审美个性反抗市侩资本主义的庸常,具有审美救赎的重要作用;晚明通俗文学所表现的间性—颓废审美风格则作为文人文化的表征,以审美个性反抗宋明宰制儒家所标举的崇高审美风格传统,具有个性解放的现代意义。但是二者都共同表现着人之为人的觉醒历程,积极探索着“何为美好生活”。
结 语
综上,晚明文士为了回应晚明出版革命所掀起的大众文化消费热情,不仅改写与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而且进行了各种各样文类的实验,诸如戏曲、小说等文类的大量生产,以至于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已无法囊括中晚明时期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作品。此举一方面造成了诗歌由宰制文学中心地位的滑落,一方面则酿成了文本与文类的危机。正如孙康宜所言:“在这个时代中,政治迫害并未能使人沉默,而是造就了一种更新型的文学表达方式。嘉靖时代的读者睿智而好奇,时时有求知之欲、猎奇之心;也引发我们思考这一时期文人最大的弊病: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要求,明代文人总是写得太多,而且在太多不同的文类中耗散了他们的才力。”[注][美]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刘 倩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82页。实际上,此种文本过剩和文类过剩,正是中晚明社会文人文化普遍流行的产物。此种文人文化(或文化过剩)自风格角度而言,实是一种唯美—颓废审美风格。其使用音乐、绘画等多种审美形式,表现出间性—颓废审美风格。此种颓废审美风格尽变宋明宰制儒家所标举的崇高审美风格传统,在文人文化的形式之美的极致性追求中,显现出晚明文士独特的审美个性与审美自由,代表着晚明中国人与文的审美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