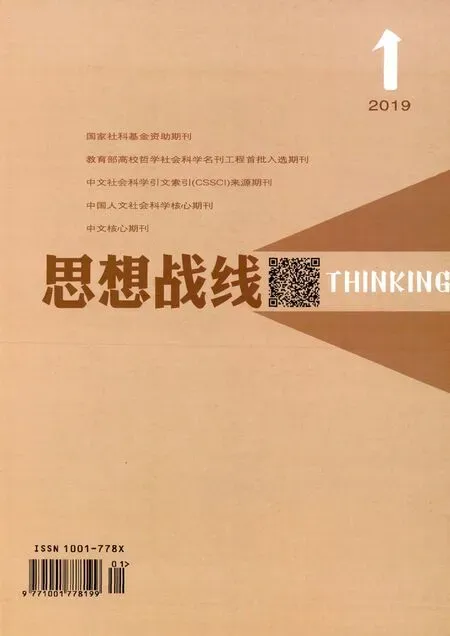从“野生”到“人工”?
——生物社会一体的沙捞越屋燕养殖
余 昕
“到达一个文化的核心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肠胃。”[注][美]张光直:《中国文化中的饮食——人类学与历史学的透视》,郭于华译,载[美]尤金·N·安德森《中国食物》附篇一,马 孆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0页。在人类学者看来,通过食物的获取、制作、消费……可以透视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思想观念、道德体系、生态系统等等。列维-斯特劳斯和道格拉斯,从动物的基本分类原则,来确定宗教仪式中的牺牲以及食品在文化观念中的分类系统,是较早代表结构理论派的饮食与文化研究。随后,马文·哈里斯代表的文化唯物主义,和西敏司代表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奠定了人类学对食物与文化研究的几大转向。此后,人类学对食物的研究延伸至更大的社会领域,比如政治经济价值的创造、象征意义的建构,以及社会对记忆的塑造等等。然而总体而言,目前关于食物的人类学研究,在探索食物与经济、政治、文化等人类社会的关系之外,较少探讨食物生产、消耗所代表的人类社会行为与自然界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问题。
应该注意到,围绕着某一食物的生产而组织的,不仅是人类彼此之间的社会、文化、政治关系,亦是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长久以来,以人类为中心的“驯化”观念,将动物视为生产资料,将食物视为人类劳动的产品或对象,以自然和文化的对立来看待人类、动物、食物。近年来,人类学理论中出现的本体论转向,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和表述人和动物构成的生物—社会整体的视角,这进一步有助于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跨文化贸易等传统议题的知识更新。[注]Tsing, Anna,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对华人饮食的一种特殊食物——燕窝的生产、贸易及消费过程的研究,可为这一视角提供支持。本文以马来西亚沙捞越近20年的燕窝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为案例,讨论围绕着燕窝这种食物组织的人类和动物关系及其社会理论意义。
燕窝是华人饮食中最被珍视的食物之一,它是由原本栖居于环南中国海地区沿岸大大小小的石灰岩山洞中的两种金丝燕(白燕窝雨燕和黑燕窝雨燕)筑造的巢穴。[注]本文所指环南中国海地区包括安达曼(Andaman),孟加拉国湾东南部的尼科巴群岛(Nicobar Islands),海南岛,菲律宾西部的巴拉望(Palawan),越南的沿海和岛屿,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半岛(包括新加坡),苏门答腊,爪哇,小巽他群岛(Lesser Sunda Islands),以及婆罗洲(Borneo)。白燕窝雨燕,即White-nest Swiftlet,学名Aerodramus fuciphagus;黑燕窝雨燕,即Black-nest Swiftlet,学名Aerodramus maximus。很长时间中,燕窝都由这些“野生”雨燕筑造,随后被当地人采摘,贩卖给华人后,经由中国沿海港口到达中国广大内陆地区。[注]余 昕:《燕窝贸易与“海洋中国”——物的社会生命视野下对“乡土中国”的反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年第1期。这两种雨燕在本文调查的马来西亚沙捞越(Sarawak)境内都有分布。[注]Cranbrook. "Report on the birds’ nest industry in the Baram district and at Niah", Sarawak Museum Journal, Vol.33 (54); Lim, Chan Koon., Cranbrook, Gathorne Gathorne-Hardy, Swiftlets of Borneo: Builders of edible nests, Kota Kinabalu: Natural History Publications, 2002, P.8.最晚到19世纪,沙捞越的燕窝采摘和贸易已经相当成熟。1851年,当时管理这一地区的英国人Spencer St. John在拜访巴南中部地区时发现,白燕窝雨燕及其所筑官燕已经成为当地加沿人(Kayan)村落的重要财产,且燕窝采摘已经持续了30年,因此推测这一地区采摘燕窝的活动最晚始于1820年左右。[注]Lim, Chan Koon and Gathorne Gathorne-Hardy Cranbrook, Swiftlets of Borneo, Builders of edible nests, Kota Kinabalu: Natural History Publications, 2002, p.63.通常,按照雨燕的生理节律,山洞中的燕窝1年采摘3次,分别在10月,2月和5月左右进行。采摘时需要借助竹竿或木梯攀爬到几十米高的洞顶,因此该工作主要由当地健壮且富有经验的男性进行,村落其他成员则负责准备工具和食物、捡拾跌落的燕窝等等。总体而言,洞燕采摘是一项复杂而危险的工作,长久以来由于山洞复杂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关系而纷争不断。[注]蒋 斌:《岩燕之涎与筵宴之鲜:砂劳越的燕窝生产与社会关系》,《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论文集》,台北: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2008年。
最近20年来,众多因素推动了沙捞越燕窝生产从洞燕采摘向屋燕养殖的方式转变。[注]指将原本居住于山洞中的雨燕吸引到人工建筑的房屋中筑巢。出于山洞保育和雨燕保护等考虑,沙捞越地方政府加强了对燕窝山洞的监管和控制;对于当地华人而言,养燕业相比种植园、矿产开发、伐木、房地产等产业所需资本较少,中国大陆在过去20年日益攀高的燕窝价格更成为巨大的诱惑;最后,由于印尼爪哇和苏门答腊地区的气候变迁和森林大火,大量雨燕迁徙到沙捞越地区,为该地区的屋燕养殖提供了条件。在上述背景之下,屋燕养殖被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养殖业,被政府、专家与媒体极力推广,在数十年中成为沙捞越燕窝生产的主要方式。据当地专家估计,如今沙捞越1季度屋燕养殖的产量是1吨,而洞燕1季度总共的产量只有300公斤。在上述转变中,屋燕养殖被视为与“原始”因此也是“天然”的洞燕采摘形成对立,且被视为代表了现代养殖业向工业化生产的发展。那么,怎样在社会和经济变迁推动的燕窝生产方式转变中,理解人类和雨燕关系?
一、屋燕养殖:“养燕”乎?“引燕”乎?
现代屋燕养殖业,是20世纪90年代在东南亚地区大量兴起的,为雨燕提供人造居住环境从而进行燕窝生产的经济农业。[注]最晚在19纪末,东南亚地区就有华人建造屋宇,供雨燕居住和繁殖,这项记载与很多老一辈燕窝商人的记忆相符。在他们看来,印尼的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的海岸一带,屋燕养殖业兴起已达数百年。最初吸引雨燕入住的屋宇并未经过特别设计,雨燕定栖之后屋主也不会对房屋加以改造。二战过后,有华人开始利用一些手段特意将雨燕引入事先建好专供其居住的燕屋中,除了在建造燕屋时模仿山洞环境,他们还将山洞中的雨燕鸟蛋取出,放在燕屋中用其他种类的雨燕孵化,几代过后,长成的幼雏会定居在其出生的燕屋中,称为交叉哺育。它的基本方式是通过设计被当地人称为燕屋的建筑,并营造内部气味、温度、声音等环境,模仿燕窝山洞的环境,并在燕屋修建完成之后,通过播放雨燕鸣叫,吸引雨燕入住燕屋并在其中筑巢(即燕窝),同时,通过管理燕屋而对燕窝质量进行控制。[注]Babji, A.S., Nurfatin, M.H., Etty Syarmila, I.K. & Masitah, M,"The 2007 Malaysian Swiftlet Farming Industry Report", Agriculture Science Journal, Vol.33, 2007.。
屋燕养殖的核心,是“引”燕—“养”燕—“筑”燕(窝),与洞燕采摘相比,它表面上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人力对雨燕筑巢过程的干预。在一般人看来,这些生产活动,因为包括占有土地(买地修建燕屋)或牲畜(雨燕)、种植(修建燕屋)/“养”(使雨燕定居)、收获(采摘燕窝)等过程,而与农业或畜牧业相似,屋燕养殖在沙捞越也的确由森林和农业部门同时管辖。因此,屋燕养殖被称为“养燕”,投资修建燕屋者则被称为“燕农”(swiftlet farmers),[注]尽管对这一称谓持有保留意见,但由于这一称号的普遍性,在下文中我将继续使用“燕农”来指称修建燕屋、吸引雨燕筑巢和采摘燕窝的屋燕业从业者。他们为雨燕修建的燕屋也被视为人工环境。然而,通过对屋燕养殖过程,包括建屋和引燕,以及燕窝质量管理方式的仔细分析。下文将表明,以经济作物和工业化生产分析燕窝生产的视角,遮蔽了引燕入屋所体现出的人与自然关系。这一关系的特征,是在燕窝的跨境贸易和全球化网络中,人类对雨燕生长活动的介入和参与,而非源于“驯化”所寓意的人类与自然的认知与分化。
“引燕”的目的在于吸引雨燕入住燕屋,而这并非易事,甚至在很多燕农看来,需要依赖运气或福气。屋燕养殖业具有很大风险,很多燕农的燕屋,在建成之后数年都没有雨燕入住繁殖,因为他们无法控制雨燕飞翔、迁徙以及在何处栖息,也无法为雨燕提供食物。据估计,成功的燕农只占所有养燕业的20%。[注]信息报道人估算数值。因此,养燕业中“运气”或“运势”被视为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而能成功引燕的燕农被称为有“燕福”之人,很快吸引雨燕入住的燕屋被称为“旺屋”。为了使自己的燕屋成为“旺屋”,一些燕农甚至将燕屋供雨燕出入的洞口修建成山洞、铜钱、猛兽大张口的形状,仅仅为了“讨个吉利”。在燕农中,“旺屋”及其所有者往往是聚会时津津乐道的话题,讨论的主题也往往从燕屋设计的技术争论开始,到感叹自己没有“旺屋”所有者那样的“燕福”结束。尽管屋燕养殖者无疑是个体经营者,但这样的福气并不能仅仅依赖韦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 spirit),[注]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苏国勋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它往往会不期而遇地降临。Daro这座小镇的陈氏兄弟,本来经营日用品买卖,有了一定资金后购置物业准备开设旅馆,不料旅馆经营惨淡,不得不停业,购置的2层楼房也被迫闲置。不料一段时间后,雨燕逐渐在该2层小楼定栖,陈氏兄弟立即将其改造成燕屋。如今,他们的小楼每月都有数十公斤燕窝产量。经过一段时间对雨燕生理规律的密切观察,积累了经验和资本后,他们于2011又在Daro周边的农用地建了4座燕屋,养燕已经成为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
运气并不可复制,在同一片雨燕聚居区,可能分布着多个成功程度不一的燕屋。有些燕屋住满雨燕,拥挤不堪,与之距离仅十数米的燕屋却门可罗雀。一些燕农在收获一间“旺屋”后,按照同一形制在同一地点再建一座燕屋后,新建成者却告惨败。对于这种差异,燕农们除了“运气”之外并无更多解释,但很多有经验的燕农亦表示,正如风水一样,“运势”也可以营造:选块好地,虽然不能直接导致引燕成功,但无疑会修得“燕福”。
拥有丰富经验的猎人对猎物的活动和习性需要充分了解,有经验的燕农不仅了解雨燕的习性和生态规律,他们一般都会在建屋之前,就对当地雨燕觅食和迁徙的规律了然于胸。在飞翔航道上建屋,更有可能引来雨燕,因此燕屋选址对引燕成功至为关键。在建屋之前,燕农一般会花上数月甚至半年时间,每天傍晚六七点左右,在雨燕大批归巢时,在可能的选址位置蹲守,观察雨燕的飞翔规律。若有大批雨燕飞过,说明此地在雨燕归巢的航线上,在此建屋更有可能吸引雨燕入住。诗巫的一位酷爱狩猎的老燕农明言,正是猎人对于动物习性的敏锐观察力,让他用燕屋“捕获”雨燕更加得心应手。同样,选址还要考虑附近地区昆虫即雨燕食物的丰欠程度。经验较丰富的燕农会选择在河流入海口处的红树林地区建屋,因为这里植物丰富,足以滋养大量昆虫,为雨燕提供丰富食物。另外,由于雨燕每日的觅食范围可以达到30公里,选址最好是在30公里范围内食物都丰富的地区。自然环境如此重要,甚至有一位财力雄厚的燕农,不惜重金买下一大片土地,在其中栽种各种植物,养殖包括牛羊、鸡狗在内的各种动物,为这个庄园内的燕屋人工打造了一个小型生态环境。
为燕屋营造的“运势”还包括社会环境,即所选位置附近已有的燕屋数量、周围用于其他用途的农业地情况,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以及最重要的“人和”因素。附近燕屋较多,说明这片区域是一块雨燕出没频繁、基础数量较大的“风水宝地”,并且也有“拐走”他家雨燕的可能;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雨燕的觅食群体数量过大,而使食源和环境不堪重负,造成群体数量下降。另外由于燕屋建造的数量较多,这片区域的地皮价格可能超出燕农承受范围。第二,燕屋周围地区的现状和未来发展,也密切地影响着燕屋成败。近20年来,沙捞越在全州内大力发展道路交通建设和经济作物种植,每天都有大量农业地甚至森林被开垦为油棕园,沿海岸线地区也有早已存在的大量椰林、胡椒园和橡胶园。这些经济作物种植园,往往因为生态单一或者大量施用化肥和农药,扰乱或破坏其周围的生态环境,对雨燕生存带来很大影响,因此燕农一般不会选择在离种植园太近的地方修建燕屋。
燕农选址虽然一般倾向于远离已经建成的种植园地,但对未建成或还在规划中的种植园却难以防范。因此在考虑选址的社会环境时,燕农不仅需要考察选址地当下的状况,更需要多方打听消息、凭经验判断其未来规划。一般而言,这类消息会在燕农群体之间流传,但更通常的做法是找到乡村中消息灵通的华人,后者对当地的具体情况和动向更为了解,也能帮助燕农买地和管理燕屋。郑先生和他的合作伙伴在Maludan买了一块地建屋,就是依靠当地周姓华人家族的帮助。每次去采燕窝时,他们必定到周氏兄弟开的茶室中吃饭、喝咖啡,顺便再从后者开的日用品商店中买点当地的亚达糖(沙捞越乡间特有的棕榈糖)、鱼干或其他土产,一来是联络感情,二来是打听消息。周氏兄弟靠贩卖当地的土产和海产发家,现在不仅在当地拥有很多土地,在首府古晋还有多处房产。关于Maludan周围土地动向甚至燕农群体的很多消息,都可以向周氏兄弟探听。
由此可见,屋燕养殖的成败,是在生物和社会构成的整体中被决定的。对于燕农而言,他们不仅应该是一个对环境和猎物了然于胸的猎人,也应该能够通过选址和信息搜集,甚至风水营造等多方努力引导态势发展。但是,“捕猎”雨燕只是屋燕养殖的第一步,与洞燕采摘相比,燕屋引燕能够通过燕屋的经营和管理参与燕窝筑造过程。燕屋选址、屋内的空气湿度和温度、燕屋建材、鸟粪清理程度,以及屋主采收燕窝的时机等等,都对燕窝的质量有重大影响。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燕窝盏身厚薄、含毛量、外观(颜色和形状)的差别,进一步决定了燕窝在远方市场的价格和销路。
燕窝的质量是雨燕筑巢和人类对燕屋管理共同作用的结果。燕窝在雨燕繁殖期内而成,在1个月到数月不等的周期中筑造。在这一过程中,燕农需要精心选择采摘燕窝的时机,既是为了获得更加优质的燕窝,同时也是为了保护雨燕的生命力。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燕农对自己燕屋之中雨燕的呵护和熟悉往往让我惊讶。有很多次,面对不慎跌落巢穴的幼鸟,燕农都会满怀怜惜地将之送回巢穴。很多燕农也总是自嘲:“它们白天就出去,我就像酒店服务生一样打扫房间。”在燕屋这个“人工”环境中,雨燕筑巢和燕窝质量却并不能单由人力控制。根据雨燕的脱毛期、繁殖期和食物丰匮情况,每年春节前后采摘的燕窝被认为燕肉最厚、含毛最少,质量最为上乘,称为“头期燕”。此时燕农会频繁访问燕屋,精心选择幼鸟已经离开的空巢采摘。4到6月作为雨燕的繁殖、孵化、脱毛的高峰期,此时绝大多数燕窝中都有鸟蛋、雏鸟或者亲鸟,甚或燕窝尚未筑造完成。如果屋主杀鸡取卵,过度采摘,燕窝质量会下降,甚至使雨燕数量减少或另迁他处。这绝非是燕农愿意看到的情况。对于燕农来说,鸟蛋和雏鸟都意味着未来时间内更多的成鸟和燕窝,因此他们绝不会以短期利益为局限,中断雨燕的孵化和繁殖,而影响整个燕群的生命力,损害雨燕的正常成长与作息。因此4到6月期间,往往可见急需收成的燕农无功而返。可能是因为上述人造环境的保护和燕农采摘的节制,据鸟类专家估计,最近20多年来,沙捞越的雨燕数量和燕窝产量都有很大提高。
燕屋成败的偶然性、屋燕养殖对生态和社会环境的依赖、人和雨燕的亲密关系均表明,燕农对燕窝的“生产”的关键,并非在于控制自然以实现人类的意愿,他们的行为仅仅是燕窝形成过程中的合力之一,参与到筑造燕窝的生态和社会的整体过程中。这并非意味着燕农的意图、远方市场的喜好不重要,毋宁说,人类最多不过在营造和引导势头往自己欲求的方向发展,却并不能决定这个过程的结果。雨燕、燕屋、燕农及他们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社会关系、时间节律,共同构成了屋燕养殖的生态—社会整体。那么如何以这样的视角理解雨燕和燕农关系?
二、从“野生”到“人工”?
初次见面的燕农总喜欢强调“养燕不同于养鸡”。拥有6间成功燕屋、有10多年经验、喜欢狩猎的杨先生甚至坚称更恰当的词是“拐”(trap)燕,强调屋燕养殖与其说在于“养”,不如说在于“引”,“养燕”(swiftlet farming)一词歪曲了屋燕养殖业的实际情况。那么“引燕”和“养燕”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为何燕农如此反感他人将他们的行为与养鸡等同?
燕农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引燕”而非“养燕”的看法不无道理。建造燕屋的燕农无法限制雨燕的活动,他们只能为雨燕提供比较适宜居住的环境,包括光线、温度、湿度、声音、去除天敌等等,而环境中任何不适宜的因素都可以让它们随时迁徙。燕农需要对燕屋持续管理的目的之一,就是确保雨燕适宜的生存环境以及保证雨燕栖息和繁殖。同样,屋主也无法为雨燕提供食物。雨燕每日在空中活动的时间长达10小时,飞翔范围则在30~50公里,因此燕农也无法圈定属于自己的食源范围。即使燕农能够占有燕屋所在的一片土地,但引燕和养燕的成败中,这些“不可控”的食源、雨燕及其繁殖力,构成了燕农无法也并不试图控制的因素。以一种极端的动物饲养方法“封闭动物饲养法”(confined animal operations,简称CAFO)为例比较,更能凸显“养燕”中体现的全然不同的人类和动物关系:
在尽可能狭小的空间里、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生产出可能多的牛肉、猪肉和鸡肉……其中动物的身体成了媒介……禽类生产可能是工业化农业中最让人触目惊心的例子,因为标准化的鸡“工厂”拥有封闭的、可控的内部环境,而且完全是可以移动的。只要有利可图,任何地方都可以建造鸡“工厂”,这样就可以将资本从土地和当地特定的生产限制条件之中“解放”出来。[注][英]伯恩斯坦:《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汪淳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6页。
上述饲养方法的核心,在于限制动物活动范围、封闭和隔离以防止动物疫病传播、对食物来源和动物生活环境进行控制,以及饲养场所的可移动及可复制等特征,这些都与屋燕养殖方式形成悖反。并且,如果说这种动物饲养法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动物的死亡以获取人类的食物,那么引燕依赖的是雨燕旺盛的生命力和繁殖力,以筑造更多更好的燕窝。
引燕和燕窝筑造过程中,人类活动的目的,在于想方设法迎合雨燕的需求,为其创造一个利于栖息和繁殖的环境,而非对雨燕进行控制、限制或饲养。在屋燕养殖中,雨燕与人类之间建立的是生产者之间、而非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或生产对象的关系。作为亲身参与的生产者,燕农深知自己对于雨燕筑巢过程之干预的局限。然而关于“饲养”的惯有想象的混淆和遮蔽,让人区分了山洞中栖居的雨燕之“野”与燕屋中栖居的雨燕之“人工”,这又直接导致了对燕窝价值和价格认知的差别。在不了解屋燕生产的人看来,屋燕燕窝是“人工”生产的,因此更不“自然”,在价值和疗效上与洞燕相比低了许多,这通过高出屋燕燕窝数十倍的山洞产燕窝的价格得到印证。除此之外,“养燕”二字为燕农还带来了国家管制上的困扰。一方面国家管理以针对养鸡场的模式进行,燕屋随时面临被拆毁或强制迁徙的压力,而这对于燕屋无异于灭顶之灾。另一方面,由于屋燕养殖的兴起,被视为代表了现代养殖业向工业化生产方式的转变,因此政府和行业部门往往用工业化生产的标准性、可控性、可溯源性来要求燕窝生产过程,在遇到对燕窝质量的质疑危机中更是如此。
归根结底,“饲养”意味着“驯化”(Domisitication),二者无疑成为我们想象人类与动物之间关系最重要的方式,以至于很多由人类参与的动物生长繁殖行为,都以此为原型进行理解。在动物的驯化观念中,人类对动物的控制和空间限制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对人类与动物关系理解,往往将动植物视为人类的财产或文化中的分类体系、象征符号,[注]Leach, Edmund, “Anthropological Aspects of Language: Animal Categories and Verbal Abuse”, In E. H. Lenneberg,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4, pp.23~63.或强调其实用价值,核心在于控制、俘获和人类利益。[注]Cassidy, Rebecca and Molly H Mullin, eds, 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 now : domestication reconsidered, Oxford, New York: Berg, 2007; Candea, Matei, "I fell in love with Carlos the meerkat: Engagement and detachment in human-animal relations", American Ethnologist, 2010, no.2.在驯化观念之中,人类和动物分属于不同的领域,二者构成的利用、象征、反映等等关系,不过是自然—文化二分观念的不断复制。这样的观念代表着人类外在且凌驾于自然,作为主体的人类对作为对象的自然具有毋庸置疑的处决权。应该意识到,人类学研究早已经提出对这种关于人类与动物关系认知的挑战,埃文斯·普理查德对努尔人的研究中注意到了人和牛的共生。[注]Evans-Pritchard, Edward, The Nuer: A Description of the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0.英格德(Ingold)关于驯鹿的研究,提出人和驯鹿的关系,是人类个体和家庭之间关系的媒介的观点。[注]Ingold, Tim, "Time,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Animals: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Prehistory, Animals and Archaeology, 1984, Vol.3.这样的视角有助于反思人与自然的二分和对立。雨燕、牛、驯鹿与人类的关系并非限定、控制和利用的关系,不确定性和相互适应、型塑的提法,更能描述人类和动物及其身处的周遭环境。[注]Lien, Marianne E, Becoming salmon: aquaculture and the domestication of a fish,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p.10人类和动物并非分属不同领域,而是在同一个生物和社会的整体中共生。然而,当涉及经济和食物全球贸易时,“驯化”的观念又会如幽灵般潜入我们的意识中心,全球食物贸易研究,往往以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的方式想象动植物生长繁衍,而忘记了食物生产于人类和动物的共生之中。
三、成为燕窝
沙捞越是屋燕养殖业的后起之秀,在生态环境变迁、经济利益驱动、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变化之下,屋燕养殖作为洞燕采摘的替代性生产方式,被政府和燕农大力推动,并在数十年内成为了燕窝生产的主流。毫无疑问,这种生产方式,的确代表了一种新的转向,但对这种转向的理解,并不能以惯有的驯化关系展开。在燕窝生产方式的转变中,充满着模糊、冲突、误解、偶然性和矛盾。
从洞燕采摘到屋燕养殖,表面上是生产方式转变之后,人类更彻底地驯化了(domesticate)雨燕,燕窝因此也从“野物”变成“人工”制品。上述将养燕等同于养鸡、“野生”与“人工”的观念区分,亦都源于对驯化这一概念的坚持。然而,沙捞越的燕农,却发现了这种看法与自身经验的矛盾——他们认为,自己不过是雨燕的服务者。通过对屋燕养殖活动的分析,不难发现,燕农的活动并非在于对雨燕进行限制、控制和饲养,而毋宁说在于想方设法满足雨燕的各种需求,为其繁殖和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燕农从观察雨燕飞行范围、选址修建燕屋开始,就参与到燕窝的形成过程中,随后对燕屋的管理,则是通过为雨燕提供更优的繁殖环境、为燕窝提供更好的筑造条件,从而参与燕窝的形成过程。但这绝非意味着燕农对雨燕的控制,实际上他们对“养燕”这一提法的反对,表明他们深知自己在燕窝形成中不过是“合力”(join forces)之一。[注]Ingold,Tim,Making: anthropology, archaeology, art and architectur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27.换言之,燕农和雨燕在燕窝的形成过程中,是同等重要的参与者,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人和自然、主体和对象之间的关系,而是在生物与社会整体中彼此依赖和共生。
燕农的经验表明,在“野生”的雨燕和“人工”的家禽之间,似乎存在众多的可能性,人类对动物生长繁殖的介入,并不一定遵循线性和单一的驯化路径。而我们想象的贫乏,源于现代性固有的进步、征服、发展观念,以及自然与文化分割观念的桎梏,让我们无法理解世界的真实构成。对这一桎梏的突破,在于从根源上反思驯化的观念。
在社会人类学学科中,驯化具有特定的含义,通常被视为人与动植物关系根本性地改变,即人—动植物关系的基本模式,从非控制转向控制。因此关于驯化的叙事,同样是关于人类如何征服、控制自然和自身动物性的叙事。在这样的观念中,狩猎—采集社会不过是农耕—畜牧社会还未对自然进行控制之前的一个低级阶段,前者与野生动植物的“未驯养”关系及后者与家养动植物的“驯养”关系,构成了进化阶段划分的基础,也构成了区分野蛮与文明的依据。进而,这样的观念亦成为了欧洲人对“人—自然”乃至“人—世界”之关系理解的核心,它被作为人类文明历史转折的代表——在农业和畜牧业革命的基础上,人类财产积累、劳动分化。由此产生的社会划分、私有财产、国家,[注]Childe, V. G., and G. Clark,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1946.正是基于改造自然的程度,欧洲人得以排列出具有高下等级的文明序列:一端为野蛮/野生/自然,一端为文明/驯化/文化,换言之,驯化成为了进化和文明的标志。[注]Lien, Marianne E, Becoming salmon: aquaculture and the domestication of a fish,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是,上述驯化的观念,也处于我们对食物及其生产之理解的核心。食物不仅是人类驯化动植物的结果,也是人类生产能力的体现。食物的获取、制作和消费,无疑代表了人类社会不同的组织方式,并且在很多人类社会中,食物的获得都以驯化作为前提。在本文所反思的驯化观念中,这意味着人类将自然限定为自身世界的一部分、将自然作为生产资料或背景,人类彼此之间的关系,则建立于对自然的控制之上。在这样的视角中,食物和其它动植物,成为了人类社会的对象化产物和背景。类似的,在关于“生产”的观念中,也存在同样的人类社会与自然分离的假设,工厂中生产的产品,和农田、养殖场中的动植物,都是人类活动的——无论作为生产资料还是产品或财产——对象。进而,正如马克思对蜜蜂与建筑师的区分,“生产”也因此构成了人性的基础,产品则是人类对自己意图的实现。[注]Ingold,Tim,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hood, dwelling and skill,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78.在这里,人类不仅脱离于自然,还可以意向性地生产产品、改变自然。
如果说对野生的动植物进行圈定、控制、杂交、选择……使其成为可以为人所用的对象,是驯化的特征定义,那么这一概念的基础,就是将人类和动植物分割成两个互相限制或利用的整体。社会性只属于人类所有者,自然性则只属于动植物所有者。[注]Ingold,Tim,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hood, dwelling and skill,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61~63.在这样的关系中,人类超脱于自然、最终能够控制自然。动植物由于属于自然领域,也终将成为人类社会的财产,构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依据。上述屋燕养殖过程的描述,已经构成对这一观点的最好反驳。雨燕并不可控,燕窝处于不间断的形成过程中。燕农们无时无刻都得面对和承认雨燕的自主性。他们最经常感叹的是,自己就像开旅馆的服务生,每日为雨燕打扫房间,而后者则像旅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在这里,人—动物之间的关系和人—人之间的关系并无二致。
这种不确定性意味着——世界各地的人类学调查结果亦已证明——自然往往并非被动的、被剥削的客体或者食物和资源的仓库,而是充满了生命力和繁殖力。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是被滋养的对象,而不是相反——自然是活的。人类的行为,与其说在控制自然,不如说在维持和再造与这些生命力的关系,正如维持和再造与他人的关系。而如果说驯化代表了某种转变甚至断裂,也绝非是人类和动植物的关系从不能宰治到能够宰治、从人类不能脱离自然到脱离自然的转变。毋宁说,这种关系的转变,是人类身处自然的不同方式的转变,是人类从对自然的信任到主导的转变。信任的关系,除了意味着双方的互相依赖和共生,更重要的是,承认了双方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动物并非被猎人捕获,而是将自己献给猎人,正因动物的自主性,信任的关系也意味着风险。仔细检验狩猎的工具不难发现,这些“原始”的工具往往不在于控制或操纵,其目的往往在于探寻和再现关于动物的生活。[注]Ingold,Tim,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hood, dwelling and skill,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66~72.同样,如果跳出人类—自然的分割,仔细检验包括屋燕养殖在内的多种多样的人类—动物关系,或许能拓展对于驯化和生产的理解。在屋燕养殖这种表面上新兴和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中,人类和雨燕的关系,一方面类似狩猎—采集社会中猎人与猎物之间的信任关系,另一方面也类似放牧人对自己羊群的引导,燕窝则构成了这种生物—社会整体关系的集中体现。
食物生产方式的变化反映了人类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变迁,但围绕着某一食物的生产而组织的,不仅是人类彼此之间的关系,亦是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继续探讨关于食物的贸易和消费如何可能。因此在探讨食物生产方式变化时,应该同时注意到人类—动物关系的维度。Ingold提出“形成中的生物与社会”(biosocial becoming)的概念,[注]Ingold, Tim, and Gi·sli Pa·lsson, eds, Biosocial becomings: integrating social and biologic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表明人从来不处于自然、动物、物之外或之内,人就是自然、动物、物,“驯化”代表的人类—自然二分观的视角,否定了动物内在的生命力,也将人类置于虚空之中。人类不过是万物生长或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元素,不过为其他生物提供了适宜生长的环境;在其中,人类、动物、植物以及器物,都是整体过程的一部分。[注]Ingold,Tim, Making and growing: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organisms and artefacts, Surrey, Burlington: Ashgate, 2014, p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