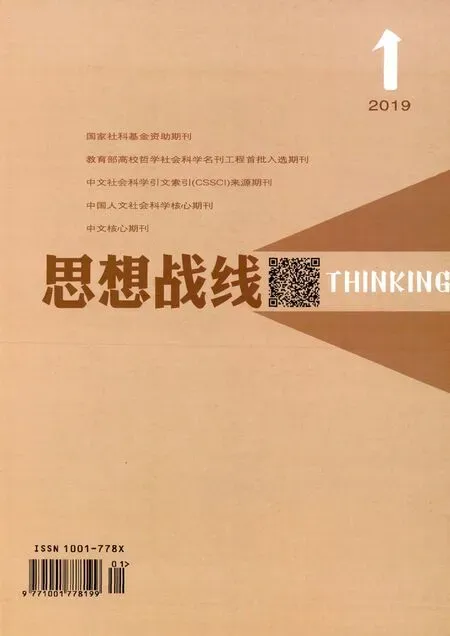中西哲学中的“一”及“同一”
吴福平
传统中西哲学和哲学大家,无不从“一”开始哲学思考和探索。中西哲学史(包括宗教史)中,“一”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注]革栏目·兰顿:《中西哲学中的本体“一”与伊斯兰的“一”》,《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如果说过去的哲学学说有什么共同的地方,那就是他们都试图通过解释自身理性经验的途径,来思考世界的存在或世界的统一性。”[注][德]于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洪佩郁,蔺 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年,第14页。这个“统一性”的基本内涵,便可以看成是哲学意义上的“一”或“一”的重要构件。在哈贝马斯以及阿伦特、德里达、福柯等诸多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看来,随着经验科学的实际进步以及伴随着这种进步而产生的反思意识,哲学反思不仅在科学协作范围内失去意义,而且,黑格尔及一切古典哲学家们一直津津乐道的“同一”哲学,也再不能按全部知识的意义来解释世界,阐述自然、历史和社会的整体,哲学思维由此变成“纯理哲学”而衰败了。20世纪一流的哲学家,如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对这种“被称为哲学的蠢行”发起了最深刻的攻击,他们把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史认定为是“一种错误、一种病态或幻觉的历史”,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哲学”,或者说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已经终结。[注][美]卡弘:《哲学的终结》,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页。然而,我们认为,如果在“一”的探讨中,可以推导出“多等于多,多即是一,一即是零”这样一个哲学“公理”,[注]吴福平,李德昌:《对称性与审美视角下的“势科学-吴福平系数”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或亦可谓之“哲学通式”,“同一”哲学不仅因此造就了中西古典哲学的“辉煌”,而且,基于“一”可以内生出联系与差别、一致性与差异性两个重要的变量,并进而产生老子道家意义上的“势”,产生黄金分割数及自然界的黄金分割现象,[注]吴福平,吴思遥:《“‘0’存在机制”及其存在论意义》,《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那么,中西哲学上的“一”在今天便仍有其重要的地位、作用和价值。
一、从老子的“抱一为天下式”到西方的“同一”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显然肇始于“一”的探究。周易哲学中的虚无本体“太极”,即是“一”。太极一词出自《庄子》:“大道,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论述的正是这个“一”。老子强调:“圣人抱一为天 下 式”(《道 德 经·第二十二章》),也认为“一”为世界的本源、本体。在六祖慧能那里,“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六祖坛经·般若·第一节》)。宋明理学的“理一分殊”、华严宗的“一多相容”等,对“一”(或与“一”相当的本体对象)的基础性、本体性和绝对性,也都作过系统的阐述。在西方传统哲学中,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便热衷于探究这个“一”。他们认为,对“一”的探究,可以“把心灵引导到或转向到对实在的注视”。“一”的基本原理是,同一事物是“一”,同时又是无限“多”。[注][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91页。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强调,“美”本身便是“一”,“正义”本身也是“一”,以及其他东西本身或本体也都是“一”。[注][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27页。亚里士多德指出,“由于‘一’的某一命意在各范畴上分别相符于各范畴之是,元一遂与实是相合,而‘一’却并不独自投入任何范畴之中”,但是却“与实是相联系而存在于诸范畴之中”。[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17页。也就是说,这个“一”虽则在其所指涉的范畴上存在差异,但是显见地都有“实是”、本体等意义。所以,直到近代,西方哲学曾被统一戏称为“一”哲学或“同一”哲学。[注][德]黑格尔:《小逻辑》,贺 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54页。这个“一”即是最高实体,进而使整个西方哲学发展成了实体主义。柏拉图的实体和“一”就是绝对理念,库萨的尼古拉否定神学的实体和“一”就是上帝,黑格尔的实体和“一”即绝对精神。那么,如何来正确理解这个“一”呢?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即“元一”有四义,包括“自然延续之事物、整体、个别与普遍”;“延续的事物,出于本性的生长而成一者,这一类活动较单纯而一致,应是更严格更优先地合乎‘一’的命意”;成为整体而具有一定形式者为较高级的“一”,这一类中,“其延续的原因当以出于自性”;此外,“个体之在数上为不可区分的”或“在形式上,其理解与认识为不可区分的,所有这些足使本体成为一者,便当是基本命意上的‘一’”。[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11~212页。库萨的尼古拉认为,相等按本性先于不相等,联系、“一”按本性先于差异。因此,“一”、相等、联系三者同等地永恒,它们是同一的。“这就是那个‘一’,它同时又是一个三一体。”[注][德]库萨的尼古拉:《论有学识的无知》,尹大贻,朱新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5~16页。黑格尔认为,对于“同一”的真正意义加以正确的了解,是异常重要之事。真正的同一,作为直接存在的理想性,是一个很高范畴。[注][德]黑格尔:《小逻辑》,贺 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49页。“同一”作为自我意识来说,是区别人与自然、人与禽兽的关键。“同一”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同一”之所以“同一”,是因为它们同时包含差别于其内。[注][德]黑格尔:《小逻辑》,贺 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49页。很显然,老子及中国传统哲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和阐释这个“一”的。正因为此,老子才强调“道生一”(《道德经》);进而,他还把“一”的重要性提高到事关天地万物生荣死枯、生死寂灭及“侯王”政权生死存亡的高度来加以阐发: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致之也,谓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正将恐蹶。(《道德经·第三十九章》)
由此深入,如果说天地万物,一致性是存在的理由,差异性是活力的源泉,[注]吴福平,吴思遥:《“‘0’存在机制”及其存在论意义》,《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那么,黑格尔所强调的真正哲学中的“一”或“真同一”,就的确是一个很高范畴。显而易见,“同”是因为“不同”,“不同”是因为“同”。黑格尔所阐发的“同一律”和莱布尼茨所强调的“相异律”是可以“同时共在”的。没有一物不“同一”,与没有一物不“相异”是等价的,具有同等的意义和价值。
二、“同一”哲学与西方理性的四次飞跃
理性是西方哲学探讨的主要问题。邓晓芒认为,从古希腊开始,西方理性精神经历了四次大的飞跃。[注]邓晓芒,赵 林编:《西方哲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79页。本质上,所谓的“飞跃”,也可以看成是“理性”的“一”与多、同一与差异的辩证发展过程。在古希腊以前,在本体论意义上,相当于中国哲学上所说的“天人合一”,理性没有分裂。理性即“逻各斯”,亦即是“一”;在柏拉图以后,出现了主客二分,出现了感性和理性、可见事物和可知事物的区别;到了康德,则进一步把理性析分为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审美理性。而且,如康德哲学虽则受到了黑格尔的深刻批判,但是黑格尔也把“一”理解为“绝对主体”。哈贝马斯认为,“同一”哲学的危机在于,“一”如何能够在不危及自身同一性的情况下成为“一切”呢?[注][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43页。巴门尼德坚持用非存在对抗存在,否定用“一”对抗“多”。普罗提诺认为,“一就是一切,但绝对不是(一切中的)一”。为了成为一切,“一”存在于万物当中;但与此同时,为了保持自身,“一”又超越于万物之外。由此看来,“形而上学当中充满了诸如此类的悖论表述,因为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形而上学徒劳地试图把‘一’本身归纳为客观范畴;但是,作为一切存在者的起源、基础和总体,‘一’首先构成了一种视角,从而使得人们能够把‘多’刻画为不同的存在者”。[注][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43页。为了摆脱这种悖论性的困局,“同一”哲学进而又促成了绝对否定性本体论的产生。否定性本体论的“一”,拒绝一切论证活动,也曾被冯友兰称为西方哲学的“负的方法”,即不能说它是什么,只能说它不是什么。巴门尼德的“存在之存在”论、斯宾诺莎的“观念的观念”,库萨的尼古拉的否定神学,康德的纯粹理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本质上也都是“负的方法”的产物。
显见,《易经》中的“无极”或“太极”、老子的“道”,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否定性本体论。周敦颐《太极图说》中所指的“无极”,也是不可言说,不能说它是什么,只能说它不是什么的“绝对否定性”概念。老子《道德经》开宗明义地指出: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德经·第一章》)
再从老子在第四十二章中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来看,老子的“一”与“道”是有区别的,“一”是由“道”而生的。老子的玄之又玄的“道”也是不可言说,不能说它是什么,只能说它不是什么的一种“绝对否定性”概念。冯友兰梳理了中西哲学传统的两条路子:柏拉图传统和儒家传统,这是形上学本体论的路子;康德传统和道家传统,被称为形上学认识论的路子。两条路子全都各自达到“某物”,这个“某物”也是“一”。并且,在逻辑上这个“某物”或“一”,都不是理智的对象,因为对它作理智的分析就会陷入逻辑的矛盾。因此,“某物”就成了这两条路子共有的“界线”。这条界线也正是康德所说的存在于知和未知、“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界线。越过这条“某物”的界线,达到不可言说、不可思议之境,西方哲学以为极乐,印度哲学谓之“涅梁”,中国哲学则认为,可用以提高人的生活境界,以改进人生。[注]冯友兰:《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哲学》,涂又光译,《哲学研究》1987年第4期。这个“某物”因为是绝对否定性本体论的对象,因而也只能采取“负的方法”来研究、理解和把握。由此而论,中国哲学虽则也是一种“同一”哲学,但从源头上似乎一直便是一种“绝对否定性”的本体论。
“同一”哲学遭到了现代哲学的批评,更遭遇了后现代主义的猛烈抨击和全面解构。哲学史上,我们一般所指的“近代”是指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现代”是指黑格尔至今。自黑格尔之后的现当代哲学,极大地丰富了人的哲学思维,同时也使得通常所理解的哲学在自我批判中失去基础和视域,并且几乎不约而同地都要求与“同一”哲学彻底决裂。西方现代哲学从海德格尔的“存在差别论”开始,正式宣告不仅与绝对本体论,也与绝对否定性本体论势不两立。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哲学陷入了“二元论”困境,并希望用“现象”的“一元论”来取代“同一”哲学的“二元论”,强调“此在”正是世界万物展露自己的场所。[注][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宜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2页。维特根斯坦认为,世界是“我”的世界,这意味着语言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注][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5页。因而,即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已得到解答,也还完全没有触及人生问题。[注][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5页。“整个现代的世界观都是建立在一种幻觉的基础上,即认为所谓的自然律是自然现象的解释。当代人们站在自然律面前就像古代人站在神和命运面前一样,把它视为某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注][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01页。霍克海默、阿多尔诺认为:“面对陌生之物,人们因恐惧而惊呼,这种惊呼之词就成为了该物的名称。它总是在与已知事物的关系里确定未知事物的超验性,继而把令人毛骨悚然的事物化为神圣。”[注][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梁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1页。“神话把非生命与生命结合了起来,启蒙则把生命和非生命结合了起来。启蒙就是彻底而又神秘的恐惧。”[注][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梁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1页。哈贝马斯进而指出:“神话和巫术中所透露出来的对于难以控制的危险的恐惧,反而在具有控制力量的形而上学概念中扎下了根。”[注][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42页。20世纪的科学哲学具有与20世纪的西方哲学一样的基本特征。科学哲学认为,传统哲学因逻辑与诗搅混、理性的解释与比喻搅混、普遍性与类似性搅混而受到伤害,导致空洞的空话和危险的独断论,这样的独断只不过是将一些不可并存的成分混合在一起的“古怪杂物”。“经由类比而造成的有害错误是一切时代哲学家的通病。”[注][德]H.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 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4页。全面反叛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则通过对科学主义、基础主义、整体主义、本质主义和褊狭性的全面轰击,宣告了“同一”哲学和绝对权威、绝对真理、绝对精神、绝对价值的绝对“死亡”。总体来看,西方哲学从“同一”哲学的本体论发展为“绝对否定性本体论”,进而使得经过四次飞跃的理性基础陷入了非理性的深渊,胡塞尔曾对这种非理性主义哲学曲解康德以及超越论哲学先辈的“最内在的动机”,导致超越论哲学出现完全沉没的危险,深表担忧。[注][德]胡塞尔:《第一哲学》(上卷),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06页、第308页、第361页。
三、“同一”哲学与西方哲学思想的四度提升
在西方理性的四次飞跃中,是“同一”哲学的不断深化、系统化的过程。从“同一”哲学到现代和后现代哲学,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则经过了四度提升。首先是当笛卡尔认识到“思”是属于“我”的一个属性,严格来说,“我”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如果我停止思维,也许很可能我就同时停止了存在”。因此,笛卡尔认为,只有“我思”是不容怀疑的。[注][法]笛卡尔:《笛卡尔文集》,江文编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第82页。从笛卡尔在普遍怀疑中提出“我思,故我在”,到康德在“批判的时代”展开系统的“批判”和黑格尔“对事物作思维着考察”,使“同一”哲学达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其次是康德以“我之存在之意识同时即为在我以外其他事物存在之直接的意识”,[注][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200页。破除了笛卡尔“我思”的存在。萨特进而认为,反思并不比被反思的意识更优越,有一个反思前的“我思”正是笛卡尔“我思”的条件。[注][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宜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0页。其三,阿多尔诺认为,康德的先验主体不但需要“统觉”,而且如果要真正发挥作用,进行有效的判断,就必须依赖物质,亦即是“统觉的相反一极”。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整个主观构造的学说,而关于“某种不变的东西、某种与自身同一的东西的观念也就崩溃了”。[注][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 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34页。显见,正是基于阿多尔诺的这一批判,一方面使得“同一”哲学几乎名誉扫地,也使得后现代主义开始重新评估一切价值,并走向了“多中心主义”,整个西方哲学则出现了语言哲学的转向。其四,在语言哲学的转向中,正如罗素在品评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时所指出的:“不管它是否证明就其考察的问题提供了最后的真理,由于它的广度、视界和深度,确实应该认为是哲学界的一个重要事件。”或者可以认为,维特根斯坦等的语言哲学是对西方哲学思想的迄今为止的最后一度提升。维特根斯坦认为,全部哲学都是一种“语言批判”。[注][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2页。因为语言的界限正是可以言说的界限,而可以言说的东西却又恰恰是与哲学无关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现代的世界观本质上是“建立在一种幻觉的基础上”,而世界在本质上是独立于我的意志的。[注][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01页。显见,以他为代表的语言哲学在对西方哲学思想最后一度的批判和提升中,以“同一”哲学为基础和起始的整个西方哲学,正是自此而走向“终结”。
但是,虽则“同一”哲学基础在现代哲学和后现代哲学的围追堵截中,的确动摇了根基,然而,不仅“同一”哲学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而且,其本质和灵魂依然在哲学思辨中作为某种“基因”,成为哲学思考和探索的某种“路径依赖”式的存在而存在,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是笛卡尔的“我思”,康德的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审美理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同一”哲学的产物,而且,马克思的“自由理性”、海德格尔的“此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等等,也都是在寻求探索某种“一”或者是“此在”的“一”。同时,如果说现代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哲学有什么区别的话,只不过是现代哲学过多强调了“一致性”,而后现代主义则过多地强化了“差异性”。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既强调了每个人的自由,也突出了一切人的自由,是“每个人的自由”和“一切人的自由”的有机统一。当马克思把“自由王国”推向“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时,也就是在把“此在”的“自由”推向了一个极限;也就是在“自由”的“多”与“一”的辩证运动中,把“自由”推向了“一”,进而可以看成是一种真正的“理性”的自由,或者说是一种真正的“自由理性”,是在“自由”的理性基础上,实现“理性”的自由的根本保障和最有效、最现实的途径。这种“自由理性”表明,“此在”的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必须以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且“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28~929页.不然,永无可能有“此在”的自由。自由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理性”也是“此在”的“一”,可以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硬核”。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的是一个先天之谜,因此,“存在”需要从存在者中“绽”出,以全面认识和解说“存在”,这正是存在论的核心要务。[注][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5~6页、第34页。海德格尔本质上深受“同一”哲学形而上学的影响,他的“存在”也只不过是在“多”与“一”的对抗中把“此在”推向了一个极限,推向了“此在”意义上的“一”。维特根斯坦“语言批判”的本质,亦如康德的“批判”那样,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其目的是为了划定语言或言语的经验界线,进而为思想划定明确的界限,划清可言说、可思想和不可言说、必须保持沉默的东西的界限。也就是说,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是在语言的“多”与“一”的对抗中,把“此在”的语言、言语、逻辑能力推向了极限,推向了“逻辑哲学”意义上的“一”。所以,他在《逻辑哲学论》中反复强调:“逻辑之所以是先天的,就在于不可能非逻辑地思考。”“唯一的逻辑常项就是一切命题根据它们的本性所彼此共有的东西。”[注][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74页。显见,一切命题本性所彼此“共有”的东西,在“同一”哲学意义上说,这种“共有”便是一个“一”。当然,这个“一”是海德格尔“此在”意义上的“一”。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和“生活世界范式”,也可以看成是“此在”的“一”。哈贝马斯继承了胡塞尔关于生活世界的思想,结合许茨对生活世界概念的现象学分析,同时受奥斯丁、塞尔和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等的影响,建构了以语言为媒介的主体间交往互动的生活世界范式,以及系统和生活世界双重架构的交往行动理论。从哈贝马斯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交往行动以言语为媒介,言语行为具有独立性,[注][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86页。言语行为中的交往理性,是要说明言语本身包含着一种非强制的共识。[注][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83页。如果说维特根斯坦把语言、言语和逻辑能力推向了一个极限,那么,也可以认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在把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能力推向了一个极限,既找到了言语本身包含着的一种“非强制的共识”,也为交往实践找到了一个“硬核”,即由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与主观世界三个世界统合而成的交往行动背景——“生活世界”。而这样的“共识”和“硬核”,就既可以看成是“一”的“此在”,也可以看成是“此在”的“一”。正因为此,可以认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介于先验论和经验论之间的,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调和折中的道路。[注][美]E.M.恩格斯:《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观念述评》,马健行译,《哲学译丛》1980年第5期。对于“同一”哲学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批判来自于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如汉娜·阿伦特所强调的关于人的“复数性”存在。西方研究阿伦特的著名学者玛格丽特·卡凡诺曾指出,与自柏拉图以来的孤寂思想家所打造的哲学传统、把人看成是一单数存在的抽象主体不同,阿伦特的复数性概念强调,人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作为抽象的类,而是作为无数人中的一个人,与他人生活在一起。在她看来,如果人不是彼此差异的——每个人也不同于现在、过去和将来的其他任何人,那么就不需要言说或行动来让自己被理解,只要用手势或声音来传达直接的、同一需求或欲望就够了。[注][美]玛格丽特·卡凡诺:《阿伦特政治思想再释》,陈高华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5页。阿伦特显然陷入了康德意义上的“二律背驰”,如果把她的复数性概念当成“正题”,那么“反题”同样成立,亦即:如果人不是“同一”、“类”的乃至于是抽象的“类”的存在,她所论及的人们彼此间的言谈与行动被彼此所理解是绝对不可能的,甚至于彼此的言谈与行动也不会发生。而且,还必须要看到的是,如若这个世界的“同”是因为“不同”,“不同”是因为“同”,相异律与同一律是等价的,那么,包括汉娜·阿伦特在内的后现代主义者所强调的“复数性”、复杂性、多元化,就都只不过一种“同一”哲学所强调的“同一”问题的一体两面而已。后现代主义所强化的“差异性”与“同一”哲学所强调的“一致性”不仅具有同等价值,也具有“同一”意义。
四、结论与展望
黑格尔曾强调指出:
哲学史上所表现的种种不同的体系,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只是一个哲学体系,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罢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那些作为各个哲学体系的基础的特殊原则,只不过是同一思想整体的一些分支罢了。那在时间上最晚出现的哲学体系,乃是前此一切体系的成果,因而必定包括前此各体系的原则在内。[注][德]黑格尔:《小逻辑》,贺 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4~55页。
在我们看来,黑格尔基于“同一”哲学所下的关于哲学史和哲学体系问题的判断和结论,基于前述对于中西哲学中“一”和“同一”的研究和探讨,今天仍可适用。这首先是因为,我们只不过是生息于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作为“事实的总体”而非“事物的总体”的一个“世界”;其次,如果说全部哲学从形而上学到后形而上学,从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有什么原则性区别的话,则只不过是前者过于强调了绝对性、基础性、一元性、“一致性”,后者则过于强调了多样性、多元性和“差异性”。或者可以认为,前者强调的是“彼在”的“一”,而后者强化的只不过是“此在”的“一”以及“此在”的“一”所必然衍生而出的差异性、复数性。由此深入,如果哲学上的“一”可以内生出联系和差别、一致性和差异性两个重要的内生变量,而且,多等于多,多即是一,一即是零可以成为整个哲学体系的公理或通式,那么,自由便是强迫的。我们没有不自由的自由。这是因为,其一,自由是一种内在必然性,正是因为自由意志有着无限自由选择的可能性,所以才选择了不选择,选择了这种具有“内在必然性”的自由。其二,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强调的,“意志自由在于不可能知道尚属于未来的行为。仅当因果性像逻辑推论一样是一种内在的必然性,我们才能知道这些行为。——知与所知的联系是逻辑必然性的联系”。[注][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5页。如果没有掌握这种“内在必然性”,不能像逻辑推论一样推演出这种“内在必然性”,自由必定是自愿的。自愿的自由,往往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形式的自由”,至多是康德意义上的“消极自由”。其三,内在必然性是绝对运动的产物。内在必然性的自由,本质上必须是一种无限的自由。拥有了这种“内在必然性”的自由,自由不仅是无限的,也必然地是强迫的。自由的强迫性既意味着“一”与“多”、“同一”与“差异”、一致性与差异性的“同时共在”性,也决定了善与恶的并存性。也正是因为善恶的并存性,决定了黑格尔所说的实体性的统一,即最高“实体”只能是排除了恶的“善”。从这个意义上说,巴门尼德用非存在与存在、萨特用虚无与存在对抗“多”与“一”,是因为始终未认识到,恶只能是也必须是“善”的边角料,因为“善”是以“存在”为最高尺度的,而“恶”在黑格尔那里只是一种否定性。因此,“善”也是“强迫”的,相当于康德所说的“绝对命令”。这时的“善”便是扬弃了一切“恶”且涵容了所有“善”的本质、本性的一种“至善”,一种自由的“存在”,这既可以认为是通常所谓的人性论领域的“人择原理”,因为人性若非如此,就不可能尚存在“人性”去谈它;同时,也应当可以看成是胡塞尔所说的超越论哲学需要继续光大的“最内在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