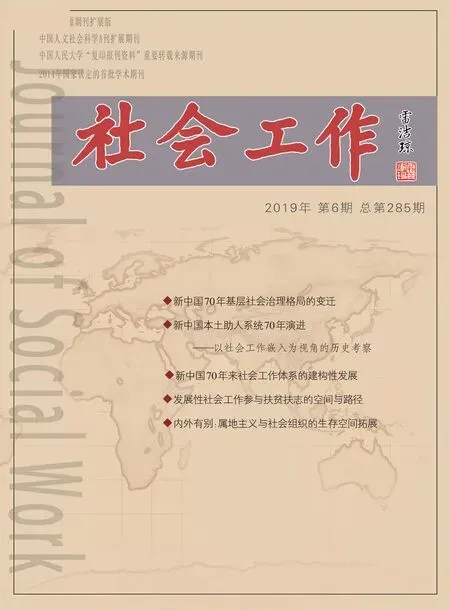农村留守女童性被害的结构归因与防治策略
程肇基 戚务念
程肇基,管理学博士,上饶师范学院二级教授(上饶 334001);戚务念,社会学博士,通讯作者,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大学社会学博士,江西省百千万工程人选(南昌 330000)。
在社会经济转型、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大量地向城市转移,中国正经历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迁移。相应地,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急剧增加,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测算,总数已达1.03亿,其中农村留守女童规模超过3100万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5 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EB/OL].(2017-10-11)[2018-12-24].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20233.html.。因中国农村留守女童数量的庞大、女性与儿童等身份特征的敏感性、性侵对于被害女童的短期与长期伤害以及可能导致的系列社会问题,极易调动广大受众的悲愤怜悯情绪,也能相当程度地触动民众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怀情感。近年来,关于农村留守女童遭遇性侵的新闻频频见诸于报端和媒体。相应地,这一现象得到学术界的关注。
一、研究现状及其检视
(一)研究现状
学界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大多将男女留守儿童看作一个同质的无性别差异的整体,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保护体系虽多有政策建议(黄君,2017)但往往忽视性别立场。即使将其作为一个更加特殊的群体,中国知网中关于农村留守女童的文献多以“性安全”“性侵害”等主题出现。这表明,在农村留守女童群体中,性被害问题更具社会关注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又进一步吸引社会各界对这一群体的关注、认知与支持关爱。现有文献大多就农村留守女童遭遇性侵害的现状、原因、防范策略等展开论述。
就农村留守女童遭遇性侵害的现状而言,目前研究文献大多作出农村留守女童已成为“性侵害最大的受害群体(孟青妹,2016)”“性安全问题情势严峻(刘茜,2016)”且呈现高发状态(钟昭会,2016)的判断,并总结出农村留守女童遭性侵的特点,如强奸案件比例多、性侵女童低龄化、性侵主体熟人化、性侵地点集中化、性侵取证困难化、受性侵多次性、性侵伤害严重等(龙玲、陈世海,2013;王伟,2015;钟昭会,2016)。留守女童受性侵的背后,人们尝试着找出各种原因,如受害人辨别力低、年龄小、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与技能;施害人道德败坏、心理变态;家长监护失位、监护意识与能力不足;学校管理松散,性教育与性安全保护措施缺失;农村文化生活贫乏,法律意识淡薄;等等(田莉芳,2015;何汇江,2015;付玉明,2016)。当前这一主题的研究,提出对策建议似乎成为核心目的甚至是最终目的,如改革户籍制度,给予农民工市民待遇(王进鑫,2008);推进小城镇建设,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郭少榕,2006);让外出父母将子女带在身边(钟昭会,2016)等等。
(二)研究检视
检视现有研究,可以发现大多文献是基于新闻报道以及披露的法院案件而作出整理分析(于阳、张鹤,2018)。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女童性被害问题极其敏感,当事人往往对此讳莫如深,很难找到合适的研究对象,一手研究数据的难以获得因此而改用二手数据。但如果将典型个案、新闻报道作为推论全体的样本并进行概率性的推论则显得不严谨。因为这些二手数据终究缺乏统计学意义以及与总人口、其他群体的参照对比性,尽管其报道量不小且持续叠加,仍不足以作出农村留守女童遭遇性侵现象“极其普遍”“情势严峻”的研判。留守女童被性侵害,堪称社会底线屡次被触犯,对这些事件的报道也符合新闻报道的选择性、显要性、影响力、煽情等新闻价值要素。
儿童性侵害(也称为儿童性虐待,Child Sexual Abuse)是指以满足侵害者性欲为目的,以儿童为对象的性行为(Collin-Vézina、Daigneault、Hébert,2013;Dittmer、Hubel、Hansen,2011)。儿童性虐待所涉及的性行为形式多样(李雪燕,2017),如性侵入、猥亵、接吻、触摸等接触性虐待(Finkelhor,1994),以及露阴癖、窥阴癖等非接触性虐待(Putnam,2003)。如果儿童尚未达到法定性行为年龄,那么无论性行为是否为双方自愿,均被判定为儿童性虐待;如果儿童已达到法定性行为年龄,那么以任何形式在任何地点发生的胁迫性行为均视为性虐待(Pellai、Caranzano-Maitre,2015)。再加上尚未发声的隐案率的存在,那么,现有文献中基于持续叠加披露的案例而作出性侵害特征的诸多概括也未必准确,因此作出定量式的推论易于误导社会大众,让留守女童以及乡村部分成年群体污名化。
农村留守女童的性被害风险究竟源于特殊的生活方式(留守),还是肇因于其他更具普遍意义的因素,抑或兼而有之?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其实这众多原因并非随意地机械叠加,而是存在着特定的结构关系,列举式地原因分析往往缺乏聚焦而找不到重点。也许正是因为调研资料的缺乏,现有研究中对于农村留守女童遭遇性侵的原因分析,表现出大而全式的笼统。高质量研究的缺乏导致相关结论的可靠性及解释力较为欠缺,相应的对策建议难免陷于空泛难以落地,对现实生活中的留守儿童帮助较为有限。
二、研究问题与思路
(一)研究问题
大众观念多认为儿童性侵事件的侵犯者以陌生人居多,但不少研究提到农村留守女童性侵主体的熟人化特点,这个可称为诸多特点中最为醒目的。这里的“熟人”指与受害人认识的社会生活关系较为密切的人,如受害人所在村落的村民和学校教师,甚至为受害人亲属等。其实,在地方性的限制下,乡土中国的基本结构单元是村落社区,乡村社会的常态本就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熟悉”的社会。农村留守女童又生活、学习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学校、家庭、社区)中,能够接触到的对象几乎都是频繁见面的熟人。城乡二元区隔背景下的陌生人作案的机率极小,犯罪主体熟人化本是不言而喻的特征。从社会学意义上看,熟人本是社会资本,熟人本是农村留守女童的保护伞,可是熟人怎么“下得了手”?背后的结构因素是什么?农村留守女童面对这一结构因素为何无能为力?这一结构因素是否内化到农村留守女童的生存心态?甚至进一步追问,以上因素的背后还有更为根深蒂固的观念因素吗?以及这些社会学视角的分析能够给予防治农村留守女童性被害问题什么样的启示?
(二)研究视角与研究思路
社会学的想象力认为,“我们在各种特定环境中所经历的事情往往是由结构性的变化引起的”,从而强调结构分析,即主张将个人经历和困扰置于宏观的社会结构中进行分析,从而超越个人的局部环境和内心世界,以理解个人及社会问题的根源和本质(米尔斯,2012)。仅仅满足于直接原因的寻找是不够的,需要到因果链的源头去寻找根本原因。知其所以然不仅可以加深对事物的理解,还可以就此找到控制事物的法杖以及控制事物所带来的影响。(麦克伦尼,2008:31-35)个案以及典型事件虽然不具有概率论意义上的代表性,但不妨碍我们将个案带到具体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去,在探究现象或事件的过程与机制中发现农村留守女童被性侵的根本原因,并据此作后续类似事件的预防。本文认为,农村留守女童性被害的诸多直接因素中隐藏着一个更加深层的结构性因素,并折射出更深刻的社会问题。即农村留守女童在与成人世界的关系中处于极其弱势的社会地位设定;加之这一乡村社会结构下成人世界对留守女童的传统式教化压制着她们的权能感与独立人格,在面对伤害时普遍感到无能为力。这两大间接原因的背后又透视出一个更基础性的观念命题:人是如何被对待的。这应当作为农村留守女童性被害防治方略的出发点。
作为性侵事件中的当下当事人,尤其是农村留守女童,一般来说不宜作为研究对象,其理由有:一是研究对象不易寻找,二是研究伦理不允许让尚且年幼的儿童再去暴露自己的伤口,三是正处伤痛中难以脱离情境且认知受限。本文所使用的经验材料不是落实一次“研究设计”得来的,作者多年来一直深入赣南、上饶、新余等地观察乡村文化,留意农村留守儿童在学校、家庭与社区生活中的日常状态,留意对农村留守女童群体与其他群体的日常状态进行对比。在实地获得的田野数据以及新闻媒体与法院批露的典型案件等资料基础上,思考农村留守女童性被害事件背后的根本原因,并试图寻找防治方略。
三、最弱势的地位设定:一种结构性因素
将农村留守女童这一群体放在一个更大的结构关系中,如儿童与成人、留守儿童与成人、留守女童与留守儿童等关系框架中,更能观察到其弱势地位。在传统的家庭(家族)关系、学校关系与社会关系中,农村留守女童都是处于最弱势的地位设定中。其实性侵男童的案件也不少见,虽然比例远不如女童①邵海鹏.报告:2015年平均每天曝光性侵儿童案例0.95起[EB/OL].(2016-03-03)(2019-11-27)https://www.yicai.com/news/4756836.html.,但均反映着儿童在社会关系结构中的弱势地位。农村留守女童在这样一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反抗的能力与勇气终将被压制,纵使具备自我保护意识与知识,其被害概率也要高于其他群体。
(一)家族秩序:处于辈分与性别双重作用的漩涡中心
在中国,家庭是最亲密也是最紧密的共同体。在农村地区,主要的社会资本来自于家庭(家族),人丁兴旺是家族势力庞大的核心指标。而其中的“人丁”又主要指男丁。传统家族体系内部秩序结构是这样的:家庭(家族)本位意识形态下的个人服从家族整体,家族辈份主导下的儿童服从成人,男尊女卑意识形态下的女人服从男人。在这样的家族文化中,女童基本上是处于家族体系中最底层的人。本文作者之一在一所农村小学的观察发现,农村留守女童的地位甚至低于在同一个屋檐下的留守男童,她们的弱势地位的设定表现在日常生活(衣着、饮食、家务劳动、亲子沟通)与教育资源的分配等方面(戚务念,刘莉,王欣欣,2019)。在这种男权的村落文化长期打压与熏陶下,不仅农村留守女童,整个农村女童的性别角色期望均较低,最终导致她们较低的成就期望和成就感。在缺乏父母亲保护的情况下,留守女童成为了农村中的最弱势群体,作为不重要的附属物而被疏于照顾。这种性别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女性,最终也只能服从这种不公,甚至会认同这种文化,世世代代都走着同她们母亲一样的道路。
对于留守女童来说,最熟悉的人莫过于自己的亲人。在传统的家庭文化中,一个留守女童在遇到来自家族内部的长者的伤害时,她们往往无能为力,沉默似乎成为她们唯一的选择,即使在成年之后也必须为维持这一关系结构而讳莫如深。一位受害人多年以后回忆起往事时,表示:“那时他(舅舅)对我的感觉是高高在上的权威,是一个族长式的人物。想都不敢想去向自己的母亲或别的人去告发他。即使现在,过年回家有时候我也要去他家吃饭,因为大家都去。”中国社会的舆论氛围倾向于不作熟人性侵儿童的“罪恶”假设。如果旁人提醒,也会被视为“其心歹毒”:“亏你想得出来!他可是亲爹/叔/伯。”长辈往往责骂受害者以及告发人“撒谎”“不懂事”,并试图将此事敷衍、压制过去。即使有人冲破家族关系的沉重枷锁,得到的往往不是家族的保护,而是让自己的生活陷入另一种被排斥孤立的困境。如有新闻报道:贵州一名初二女生欣欣去上海与打工父母团聚时,20天内遭生父多次性侵,而生母竟在旁捂嘴充当帮凶,甚至要求欣欣的妹妹将来也要用“身体”报答父亲。②初二女生20天内遭到生父多次性侵生母竟帮忙捂嘴[EB/OL](2019-04-18)(2019-11-30)http://news.163.com/19/0418/01/ED0QURN00001875P.html受害者个体的尊严维护和安全需求远不如家族的尊严维护与秩序和谐来得重要。
(二)校园秩序:身份等级安排与权力不对等
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尊师重道深入人心,校园代表着安全与神圣。所以,中小学“师源型”性侵犯罪事件往往令人瞠目结舌,不可理喻。在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结构中,老师与学生并非单纯的寓教于学,还带有支配与被支配的从属性关系,预示着身份等级安排与权力不对等。但又不同于普通的上下级关系,学生对老师的情感中更多带有尊敬与信任。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学生已经形成了对教师命令的服从性,而且年龄越小,服从感越强,往往是不经判断地条件反射般执行。乡村,有守望相助之美誉,然而更多的是针对于成人世界而言的,对于儿童世界却并非必然。老师和家长都属于成人共同体的成员,遇到师生冲突时,家长在无意识中更倾向于站在老师立场上而不是学生角度考虑问题,进而无限扩张了老师所拥有的“权力”。乡村社区中民众的尊师重教往往体现出一种盲目的“为学校的大胆管理撑腰、帮衬”,如某生在学校挨了教师严厉的批评后回到家里寻找安慰,结果反而是不问青红皂白地再次遭到批评指责甚至打骂,经此教训后再也不敢轻易地向父母亲“告状”(程肇基,2019)。这种立场甚至在男童性侵案中也不鲜见。大连市瑞格中学一名老师对班上男生猥亵,遇有反抗,则会由猥亵演变成殴打。父母对此的反应则是“说谎”“打你是为你好”(王琳,2018)。一位爸爸则痛恨自己当年的糊涂:“第一次遭到性侵后,女儿给我打电话,请求转学,我劈头盖脸的骂了她一顿,你以为转个学就那么容易,不愿意上学就回来掰玉米!后来,女儿再次告诉我,就算是回家掰玉米,也不去上学了。我这才意识到,女儿连续两次遭到了性侵”。①窈窕妈妈.12 岁女孩遭“爸爸”性侵长达2 年,真相震惊千万父母……[EB/OL](2019-02-21)(2019-11-30)https://www.360kuai.com/
在现实生活中,校园作为一个半封闭的教学场所,一旦学校回避师源型性侵这种现象,那么师源型性侵犯罪的罪前风险评估就几乎为零。一些长期缺少温暖与呵护的留守儿童,一旦遇上“好心的”师长,难免心存感激,难以识别“好心”背后的“歹念”,性侵事件甚至在毫无防备中发生了,甚至有极度缺少关爱的儿童“从性侵中获得了一种被在乎的感觉”(庞晓华、黄艳,2018)。学生做错了事,老师可以惩罚学生且无有还手的可能,而老师做错了事则似乎只能听天由命,使得师生在人格层面上变得极不平等。在中小学“师源型”性侵犯罪中,由于犯罪行为人与受害人在学习生活中不平等的地位,使受害人几乎生活于犯罪行为人的控制之下,受害人没有机会,也不敢报案。根据曝光的“师源型”性侵案例,犯罪地点主要是教室、教师休息室以及其他较为隐蔽的校园场所。(谭晓玉,2007)即使是校园里的公共场所,对于弱势的留守女童来说也可能是安全盲区。一位在寄宿制学校期间的受害人多年以后回忆,男老师侵犯她们的标准模式是:“我有事找你,到我办公室来”。到了办公室,只有老师和这个学生了,学生处于完全无助状态,出了办公室,学生根本不敢说什么。因为一是不知道该向谁去说,二是不知道怎么说,三是根本就没有勇气去说,四是说了也没有人会相信。“在这个体系中,我们能做的很少。”老师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这位学生反思道:“如果上学的时候,或者从小的时候,不带着恐惧的心的话,会好很多。”
(三)二次伤害:乡村社会延续着的“贞洁”文化
农村留守女童的遭遇性侵事件中存在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女童受到侵害,无论是同班同学、家长还是村民,整个大环境都存在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即使在师源型性侵事件中,骚扰、猥亵行为时常会发生在课堂上,当事人还是旁观者都无人敢发声制止。留守女童因更多地受老人管教,关于贞洁文化(古代妇女被强奸,是道德上的污点)等传统观念对于女童则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贞操观念使儿童遭受性侵害后不仅得不到周围环境的接纳和保护,反而受到周遭环境的排斥。当下乡村,受性侵害的女生,也往往被当作“丢丑的人”“不贞洁的人”而成为被指责的对象,“村里的妇女都说我贱,看见男人走不动道”(庞晓华、黄艳,2018)。因为关乎个人、家庭、组织的声誉,使得一些案件即使被受害人家属发现,其家属也大多选择闭而不告,息事宁人。家庭(家族)内部作案事件,可能因其涉及家丑不可外扬、维持家庭秩序的表面和谐等因素外,发生在校园和社区的性侵事件同样大概率地呈现集体沉默或遮蔽状态。湖南某校性侵案中,有旁观学生回家将事情告诉家长后,家长第一反应是让其离受害者“远一点”“不许再和某某交往”。①袁汝婷、阳建,湖南攸县男教师涉嫌猥亵多名女童事件调查[EB/OL](2016-04-22)(2019-12-06)www.china.com.cn在新闻媒体中也不时批露出,受害者的“死党”也不主动去报告或检举,其实个中不泛有为了好顾全好友的面子而保密的成分。对受害儿童的不友好行为远不止此,如一位受害人投河自杀后被村民议论说:不该死在家乡的河里,因为尸检后还是会暴露怀孕了,她的父母还是蒙羞的,要是到更大的河里去死,那就没事了。
在一些性侵害案件中,且不说一些孩子本身可能并不知道被“性侵害”,不知道保存证据的意义与技术,即使女童具备这些知能,也常常因为法律文本的局限而面临着取证与固证困境、立案与胜诉困境。如对于“是否知道被害人为未满14 周岁”的判定时往往更偏向于有利于成人世界的主观认知(是否“知道”)而不是更有利于儿童的事实认定(是否“未满14 周岁”)。即使得到立案或得到社会支持了,但非专业的帮助同样让女童面临着二次伤害的处境。如有的电视新闻没有按要求给受害者打马赛克,取证时警察直接穿着警服开着警车进出村庄与校园,简单粗暴地直接让女童口述受害过程等再次撕裂伤口的取证方式,甚至有村民认为受害家长的维权行为是为了“要钱”。2014年,广西玉林市兴业县大平山镇的留守女童小雨自11岁起遭受村里的中老年人长达两年的性侵,愤怒的父亲发现真相并报警后,女童及其家人被立马遭受敌视,村民称这女童是“卖的”“都是那个小女孩主动(勾引)的”,获刑的10多名中老年人反而被认为是“受害者”。在村民眼中,老人性侵后给了钱,也没有遇到激烈反抗,女童就不值得同情。自从报警后,一道“高墙”将他们一家隔绝在村民之外,“传统舆论会把报警、起诉的人淹死”。自此,小雨的父亲在村里就没有人可说话,他擅长的泥水活再也没有人请他干。当小雨去同学家玩,就会马上被同学的父母从家里赶出去。②刘洁.女童两年被多名中老年人性侵村民称是女孩主动[EB/OL](201401/08)(2019-11-25)https://new.qq.com/rain/a/20140108000556
四、乡村社会的传统教化:权能感的压制
社会结构可以是个体成长的压力与阻碍,同样也可以成为行动者行动可资利用的规则与资源。具有权能的个人能够在社会结构中获得他们应该得到的社会资源,能够掌控自己的空间和发展动力。权能本并不是稀缺资源,“这种权能不但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存在,而且表现为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亦即权力感。无权也不单是指人们缺乏能力或资源,同时亦是指人们会通过一种内化过程,形成一种无权感。(唐咏,2009)”农村留守女童在面对伤害时,普遍感到无能为力,其中有社会关系结构中长期的不平等地位因素,也是乡村社会结构背景对留守女童的长期教化下的独立人格缺失,终致深陷无力感。
(一)性与道德的混淆:性教育的遮蔽
在分析农村留守女童遭遇性侵的原因时,几乎都提到性教育的缺失。家庭教育中缺失性教育,可能由于成人世界浸染的传统文化与内敛含蓄的心态所致。中国的学校教育早已进入现代教育制度系列,却依然有意无意地忽视性教育。在农村传统文化中,“性”是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且有意无意地将性道德与法律混淆。调研中发现,有些边远地区的教育局领导和教师认为当地民风淳朴,对于性方面是保守的,没有进行专门的性教育和性防范教育的必要。各个层次的学校互相推脱责任,小学阶段认为小孩尚幼,没有进行性教育的必要,到初中再说吧;到了初中阶段,却止于生理卫生教材,甚至于对于性生理与青春期教育的章节选择性忽略,“让学生自学”;到了高中阶段,老师们又认为高中有更重要的任务,这些知识应该在初中就教育完了,不能等到高中再进行。不可否认,性教育的缺失,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如前文提到的贵州女孩欣欣甚至“不懂得和(外出打工回来的)父亲睡觉后下体痛意味着什么”。对于“生理卫生”课程的老师,人们有时还半开玩笑半认真说开展性教育的老师是“流氓”。学校开展性教育,也往往是“灭火器”的性教育方式,以社会控制为目的,将教育重点放在向儿童灌输“性危害”“性耻感”等消极、负面的信息上,反而不利于儿童在遇到性侵害时向老师、警察或亲属寻求帮助。从社会学(社会工作)意义上看,性教育本可为女童赋能,使女童具备与成人世界平等相处的知识和能力,具备最起码的保护自己、反抗成人世界的知识和能力。然而,现实的乡村教化,却是客观上无意地令农村留守女童对于性知识的无知、能力的压抑,逐渐地呈现“权能感的消逝”状态。
(二)听话与服从教育,依然是乡村教育的主旋律
听话教育、服从教育,对于乡村儿童来说,依然是教育的主旋律。不少记者反映,在询问受害女生“为什么不反抗”时,得到的回答“家里说要听老师的话”“他是老师,不敢”。笔者在乡村调研时发现,孩子周末接到家长从远方的打工地打来的电话,听的最多的是三句话:好好学习(学习成绩怎么样),听大人的话(听爷爷奶奶的话,听老师的话,注意安全不要玩水不要玩火)。孩子未到上学年龄,家长们便时时告诫孩子,“今后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只有听老师的话才能考出好成绩”。而孩子跨进校门以后,家长们更是除了千叮咛万嘱咐“要听老师的话”,甚至向老师表示“如果他/她不听话,你就打”。平时孩子们放学回家以后,家长们(监护人)经常询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孩子是否听了老师的话,要是得知孩子没有听老师的话,家长便会生气地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孩子进行批评指责甚至打骂一顿。笔者多次询问接到家访通知时家长们的反应,他们均条件反射般地反应:“孩子是否犯错了”,并斥责孩子:“你这个挨千刀的,你又给我犯了什么事,看我不要打断你的骨头抽掉你的后脚筋”。在这种经常性的听话教育与威胁教育下,尚未形成正确判断力的孩子往往会产生这样一种观念:“老师讲的话必须无条件地听从和服从,老师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千万不能拒绝和反抗”。加之传统的师生关系不断地被灌输和强化,学生的弱势地位和服从地位导致其即使面临来自教师或其他成人的威胁也不敢反抗。“自己不是内心的主人,别人才是”,听话的人格特征逐渐养成,人格难以独立。这种长期的听话、服从规训背景下长大的女童,不仅受到学校部分不良教师的利用,一些村民也利用女童这一人格特征行不轨之事。2015年,山东苍山县一位独居的鳏夫,盯上了邻家年幼的三姐妹。女孩们的父亲外出打工多年,母亲早已离家出走。平日里,只有姐妹们相依为命。于是鳏夫趁虚而入,控制了三姐妹,性侵长达数年之久。期间,还不断威胁她们:如果告诉别人(我强奸了你们),你爸爸就会打死你!直到几年后,其中一位女孩怀上了鳏夫的孩子,真相才终于大白天下。案情暴露后,父亲闻讯归来,女孩第一反应竟是恐惧地呼喊:你不是我爸爸,我没有爸爸,你快走吧①菜刀闯江湖.11岁女孩遭同村18人性侵:谁来救救你,我的孩子?[EB/OL](2019-11-01)(2019-11-30)http://www.sohu.com/a/351102336_790433!
(三)应试主义教育导向下的“习得性无助”
调查中发现,学校老师并未认识到农村留守女童的特殊性并给予特殊关注。(戚务念、刘莉、王欣欣,2019)不少学校老师甚至表示,留守女童很少惹祸,是最放心的群体,除非学习特别好或特别差,否则难以得到老师的特别关注。在传统的应试体制中,一切以学生成绩和分数为中心,不仅规训着教师的教学,更规训着学生的身体与精神,刷题技术在操练中逐渐提升,但人的解放意识最终被压抑与禁锢(戚务念,2019)。学校教育体系的“现代”标签,在这一维度上,堪称名不符实。应试主义成为意识形态,并没有增加现代公民意识和平等观念来激发与生成学生自我效能感。在应试教育的规训与惩罚中,学生全部的注意力集中于名次与分数,作为人的个性与尊严被严重低估和忽视,进而导致儿童心理脆弱、能量感不足,防范能力差。长年在外打工的留守女童常常被父母有意地教育要压抑自己的情感,“不要想我们哈……”;或者被教育“当在学校受到伤害时,要向老师寻求帮助”。这导致当这个庇护者变成加害者时,受害者第一反应便是不知所措,甚至怯于反抗。家庭本是受害女童们最大的支持系统,但是当遭遇家人的不理解不支持甚至误解、责骂后,又无法获得外界的其他社会力量支持,便会陷入一种无助的困境之中,反而将自身紧紧包裹,或身心失衡而进入非常态。在这种“习得性无助”心态下,即使存在得以反抗的机会,未成年受害者仍旧会消极对待,甚至默认、顺从施暴行为。加之本就在体力与身份上都处于弱势地位的师生关系、成人与儿童关系的传统结构,进一步加深了人(儿童、女童)的权能感的消逝。有定量研究表明,单纯容忍、过于软弱是儿童性被害“受容性”的重要表征,而不当惩罚、暴力对待可以视为一个“驯化”被害人、强化被害“受容性”的过程,长此以往终成“习惯性被害人”。(赵军,2019)有受害者反思道:“如果是一种平等的师生关系,这样的事情发生概率就会变小,因为如果平等,首先老师不会去做伤害学生的事情;如果平等,学生在面对来自教师的伤害时也敢于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敢于维护自己的权益。”
五、结论与建议
(一)人是怎样被对待的: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与作为防治方略的出发点
基于上文分析,发现农村留守女童遭遇性侵害的原因,在诸多表面的直接原因背后有着更深刻的间接原因,主要体现出社会关系结构中的不平等地位以及在这一结构背景下的儿童的权能感、尊严感缺失,而这两大间接原因的背后又透视出一个更基础性的价值观念命题:人是如何被对待的。如在家族文化中,女童的地位设定基本上是处于家族体系中最底层的人。农村留守女童更是一个不重要的附属物,被性侵害的女童又易被当作“有污点的人”“有问题的人”。在教育系统中,儿童不论性别均是作为应试工具来规训,而不是作为一个未来社会公民来培育。在笔者的观察中,幼儿园和小学阶段的女童留守的可能性更大,而到了初中阶段女童为减轻家庭负担增加家庭收入而辍学打工的可能性更大。2013 年,全国妇联发布《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流动人口在选择携带子女一起外出时更愿意带男童(全国妇联课题组,2013)。据2015年出版的《中国中西部农村留守女童生存发展报告》表明,留守女童独自居住比例显著上升至被调查者的十分之一。(王亦君,2015)当个体不被尊重不被当作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来看待,则被伤害就成为大概率事件,甚至被害人与加害人都视之当然。这就进入到一个整体的社会文化之中,即人在社会整体中如何被对待,个体的尊严被重视程度如何等态度与观念。人的发展人的尊严是社会的整体问题,农村留守女童的易被害性,是一个最弱小群体的尊严不被重视,但折射的是整体社会文化问题。
加强监护、提升防范意识与知识水平等做法只是帮助女童从危险的边缘离开,但并不改变这一群体的日常环境仍处于危险状态。留守状态本身并非儿童性被害风险的真实来源,虽然享受与父母温馨团聚是儿童的基本权利,但消除留守状态也非短期内可以实现,基础性或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即便终结留守状态,性被害风险依旧不会消除。同样地,为矫正农村留守女童性被害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激进批评男权文化、贞操文化,通过破坏性的工作来帮助受害者,这种以暴制暴的作法同样是不可取的。回归理性与现实,回到根源处寻找防治方略,以系统性思维,在未成年人成长的大框架内综合施治,展开针对性的改善措施,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性被害问题的根本途径。
(二)农村留守女童性被害的防治方略
农村留守女童性侵现象确实引起了有关各方的高度重视,并调动了社会情绪,而这些情绪也反映到一系列对策设计上。如强调让儿童意识到这个世界存在的险恶,要与人保持“安全距离”,以防止“披着羊皮的狼”(汤芙蓉,2016);加强师德考评实施、教师职业注册制度、限制师生交流,“教师不能单独给异性学生辅导、补课”(魏红、孙祥淞,2016);将“早恋”、未成年人异性交往与性侵害联系(汪红,2012),开展“灭火器”式的性教育(潘绥铭,2007)等等。不可否认,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保护儿童安全,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举措的方法论是将社会看成一个简单的机械装置,依靠技术来解决社会问题。从实际效果看,这种隔绝式的防范策略并不是根本之策,容易让人感觉到不被尊重不被信任,反而导致不良的社会认知,不利社会资本的积累与社会秩序的建设。因此,农村留守女童性被害问题的防范应当避免进入技术化的隔离框架。具体而言,农村留守女童性侵害防治目标有两个,一是力图降低甚至避免这一类事件的发生,二是采取积极策略让受害女童从阴影中走出来。儿童性虐待预防策略大致可分两种取向:一种是以成人-社会为中心,让成人-社会为预防儿童性虐待负责;另一种是以儿童-主体为中心,目的在于增权赋能。
1.强化国家亲权
在家户制与儒家文化影响下,家本位观念根深蒂固,家庭是儿童保护与儿童福利的主要承担者。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儿童首先属于家庭,其次才属于国家,虽然从法条上说监护权是法定监护权,但在大众观念中监护权生而有之。在“养不教,父之过”的家庭惩戒权主导下,“不打不成器”“棍棒底下出孝子”现象依然普遍。在面对儿童保护与福利问题时,村落成员甚至基层公权力的代表者内心仍然信奉“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不可否认,功能齐全、履职适当的原生家庭是儿童成长的首选,在儿童保护中恢复原生家庭功能也是首选。但是,在儿童如果被作为家庭(成人)附属物的观念占主导的社会,儿童易受伤害的背景下,适当的让公权力介入私领域是必要的,对于类似于易受伤害的农村留守女童等弱势群体尤其如此。国家亲权理论强调国家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认为当未成年人父母缺乏保护能力,或有能力而不履行以及履职不适当的情形下,国家可超越父母亲权,进行强制性干预和保护。一般意义上来看,该理论强调国家是未成年人的最终监护人,国家亲权高于父母亲权,国家在担当未成年人父母的角色时必须以孩子的福利为本位。英美国家认为儿童性虐待是家庭失灵,在儿童的性侵预防和干预中政府已趋处于主导责任(Raymond,2007)。我国也有一些部门负责儿童福利,但因部门庞杂,权责分散,加之儿童保护中需要公安、法院、检察院代表国家强制力的介入,尚没有一个专门的权威部门或政府机构来主导这项工作,从而信息、资源很难协调。强化治安混乱社区(含校园及校园周边)的安保力量,也可以减少儿童暴露在危险情境的机率。当然,国家亲权理论下的儿童保护政策,其真正目的是希望儿童在健康家庭中健康成长,而不是将儿童带离家庭。我国的顶层设计明确提出“要关心留守儿童”,当务之急在于完善留守儿童制度设计,健全保障机制,尤其要真正呵护好当下处于极其弱势地位并将成为“明日母亲”的中国农村留守女童的安全、健康成长。
2.加强对性权力的启蒙与保护
民众对留守儿童性侵等违法犯罪案件,往往诉诸道德谴责,而鲜有法律评价,法律的威慑作用很难凸显,这直接在思想上束缚了受害人对性权利的法律主张。名誉或贞节等传统思想禁锢下,被害人也不敢检举揭发,性侵的隐案率居高不下。即使被害人将加害人诉诸法律、绳之以法,往往面临着巨大舆论压力,从而导致“二次伤害”。因此,有必要将法律问题与道德问题作适当分离,让社会公众意识到性权利作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这需要性权利意识的启蒙和培育,让留守儿童及其家属以及社区民众意识到性权利的不可侵犯性,才能更好地预防犯罪、保护自己。传统的“性教育”往往以简单的传授性生理知识为主以及禁欲教育,将限制和控制青少年的性活动作为第一要务,脱离了积极正面的性权利教育,反而不利于儿童在遇到性侵害时向老师、警察或亲属求助。对性价值持积极肯定取向的全面型性教育,更能既让儿童积极投身日常社会交往,又能识别、回避性被害风险,并在遭遇潜在风险与面临不测时积极应对,遇到性侵害危险也更懂得如何拒绝、处理、求助,即使遭遇不测也可防止进一步造成性(侵害)恐慌。同时,国家在法律建设上作出针对性举动。我国《宪法》中规定了公民享有的广泛权利,但是却没有性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对性侵害往往只是在刑法层面予以规制,对尚未达到刑事制裁程度的性歧视、性骚扰等行为则没有纳入法律规制。这说明儿童的性权利是受法律保护,但在整个公民权利体系中的地位并不高。2013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简称《惩治性侵意见》)仅仅规定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办案程序和法律适用,但对尚未构成《惩治性侵意见》的犯罪行为并未进行法律规制,急需重构惩治性侵害的法律体系,扩大法律保护范围。
3.优化共同体的建设与支持
促进社会关系平等,建立包括儿童在内的人人平等的社会,将农村留守女童个体作为平等的人来对待,提升她们的权能感和尊严感,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根本性的举措,其核心在于让人参与到社会或社区中,参与到共同体中,并且得到有尊严的对待。在传统的社会等级和权威观念根基深厚、人(尤其是包括农村留守女童在内弱势群体)的无权无能无尊严背景下,共同体的建设虽然极其艰难,但仍可作为探索路径①李菲,吴天祎.女童保护论坛:全社会要为儿童撑开一把保护伞[EB/OL](2013-09-15)(2019-12-01)http://www.jyb.cn/china/gnxw/201309/t20130915_552139.html.。农村留守女童的父母常年不在身边,家庭结构的缺损也导致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依赖的社会资本缺乏,又由于弱势心态的灌输而导致她们长期忍辱负重。这需要家庭和学校改善教育方式、融洽亲子关系与师生感情,重视儿童暴力事件的预防和事后处置,防止或消弭儿童因打骂体罚等不当惩罚、遭受暴力侵害等消极人际体验所导致的性被害受容性。亲人和师长本应是儿童遭遇暴力对待后的主要支持力量,如提供人身保护、物质帮助和心理疏导。如果日常生活体验中,亲人和师长反而是打骂、体罚等消极体验的经常来源,则会强化儿童的被害受容性,反而成为促成儿童性被害的关键因素。这就要求家长、老师更新家庭教养方式与学校教育理念,将儿童作为一个平等的人来对待,以更尊重孩子尊严和主体性的现代方式展开对学生和子女的教育。共同体作为一个爱的场所、社会交往的场所以及公共空间,在预防伤害中之所以有效,在于:一是在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可消除等级差异;二是共同体中每个人有展现自己个性的机会,可增强自信心和能量感;三是共同体可以促使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自我负责的人。留守女童生活在共同体中,就是进入了一条自我增能、自我负责的轨道,而不再是消极与自我放弃,在面对伤害或潜在威胁时能勇敢站起来说“不”,进而不易被外界伤害。即使被伤害,在耳濡目染的共同体生活中,也能得到接受与认可以及更多的信赖与支持,并重新解读自己的经历以使人格得到恢复与发展而不是一个人默默承受甚至让伤害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