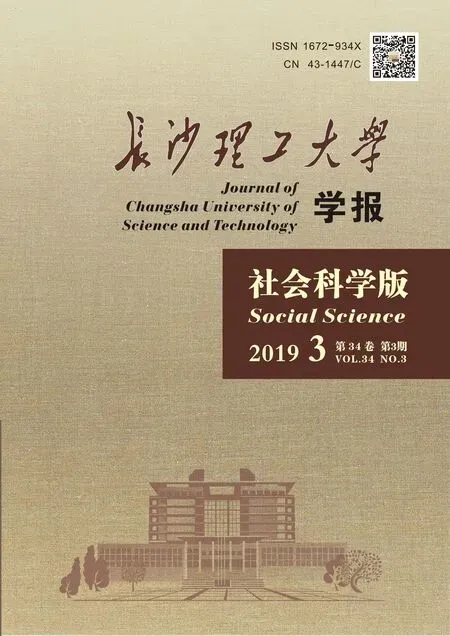情欲与杀伐
——论船山对《诗经·秦风》的解读
黄 伟
(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92)
船山在《诗广传》中对《秦风》的解读是独特的。船山指出,《秦风》没有像《郑风》那样存在燕婉亵情的诗歌,可以看出秦国的夫妇是“正”的,凭借此点,秦国就足以霸王,而关东诸国的人却像鸟兽一样嬉戏居住,所以那么多的国家都敌不过一个秦国。从这点可以看出,船山把“夫妇正”放在国家兴亡的层面上来,这和现代人文学性地解读《诗经》有着极大的不同。船山进而指出,在人的血气中存在“情欲”和“杀伐”这样两种属于阴性的特质。善于治民的王者,应该思考如何调节这两种特质,不能够同时开启,也不能够同时关闭,而朝代的兴亡,也与此有关。周朝的先王,开启情欲,而闭之杀伐;秦国相反,闭之情欲,启之于杀伐。在这样一启一闭之间,强弱的不同、王霸的分别、人心的向背都表现不同。船山认为,秦朝以来,汉朝的诗教接近周朝,而唐朝的诗教接近秦朝。船山对唐朝的诗歌评价并不高,和他独特的诗教观有关。船山的诗教观以“情”为中心,涉及“性”“欲”“气”等多个层面,最终表现为导人于和平、治国于清明、平天下于王道。
一、情欲杀伐
船山在分析《秦风》中的《车邻》和《驷驖》时,对《秦风》有一个总的概括:“秦无燕婉亵情之诗,秦之夫妇犹正也。秦之君臣、父子、昆弟、朋友,其薄甚矣,而夫妇犹正,虽无道,犹足以霸王。而关东之国,禽嬉豸聚,举天下而为一隅困,亦有以夫。”[1](P369)船山认为,《秦风》中的诗歌没有像《郑风》《卫风》中那样燕婉亵情的诗歌,这说明秦国的夫妇是“正”的,相比于五伦中的其它方面,仅仅是“夫妇正”这一项就足以让秦国的国力强盛。由此可以看出,“夫妇”在《诗经》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相对于秦国,关东的国家,如郑国、卫国、陈国等,在“夫妇”这一方面都不如秦,船山用了“禽嬉豸聚”这样一个词,把这些国家的人比作鸟兽和虫子,这是个非常严厉的论断,“夫妇”在人禽之别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接着秦国和关东国家的对比,船山从人的本质属性上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情欲,阴也;杀伐,亦阴也。阴之域,血气之所乐趋也,君子弗能绝,而况细人乎!善治民者,思其启闭而消息之,弗能尽闭也,犹其弗能尽启也。”[1](P369)这就是说,情欲和杀伐都是属于阴性的,人的血气乐于趋向于阴的一面。即使是君子,也不能免于这两个方面,普通民众就更加不能避免了。善于治理民众的王者,应该仔细思考如何在这二者中间达到平衡。情欲和杀伐不能都关闭,也不能都开启。以上可以看出,船山把情欲和杀伐都归于阴的一类,并承认情欲和杀伐都是存在的,君子和普通人都不能避免,治理民众即是调和这两种特质的平衡。这样看来,船山对待情欲的态度和一般意义上把天理人欲对立起来的观点有很大不同。
承认人的基本欲望,是船山诗教观的出发点,然而,把情欲和杀伐联系起来,是船山论诗独特的地方。在比较《豳风》中《东山》与《七月》这两首诗时,船山再次提到这样的观点:“《七月》,以劳农也;东山,以劳兵也。悦而作之,达其情而通之以所必感,一也,然而已异矣。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共焉者也,而朴者多得之于饮食,佻者多得之于男女。农朴而兵佻,故劳农以食,而劳兵以色。非劳者之殊之也,欲得其情,不容不殊也。”[1](P383)船山在分析这两首诗的时候,本意是为了说明农和兵的不同,但为了说明二者的不同,还是得从人的最基本需求出发。船山认为,人的最基本的欲望就是饮食男女,这一点船山在其它地方也多处提到。在这里船山认为,朴素的人多有饮食方面的需求,农民就是这样的;而轻佻的人多有男女方面的需求,士兵就是这样的。农民耕种土地,土地产生粮食,所以农民多得之于饮食,这层意思比较好理解。士兵用于打仗,为什么多得之于男女呢?从前面船山对《秦风》的分析可以看出,情欲和杀伐都是属于阴性,都是血气喜欢聚集的地方,所以这二者往往联系在一起。船山进一步比较周朝和秦朝的异同:“汧、渭之交,河、山之里,天府之国,民腴而血气充,又恶能尽闭哉!启之此,则闭之彼矣,而抑因乎时。故昔者公刘之民常强矣,因乎戎,而駤戾未革也。周之先王闭之于杀伐,而启之于情欲,然后其民也相亲而不竞,二南之所以为天下仁也。逮乎幽、厉之世,民已积柔,而慆淫继之,杀伐之习,弗容闭矣。秦人乘之,遂闭之于情欲,而启之于杀伐,于是其民駤戾复作,而忘其慆淫。妇人且将竞焉,秦风所以为天下雄也。”[1](P369—370)
船山认为,陕西、四川地区的土地都很丰饶,所以民众丰腴而血气充,情欲和杀伐不能够完全抑制,抑制住了一端而另一端又开启了。在周的先王公刘的时代,秦民风强悍,带有戎狄的特性。周朝的先王知道这一点,所以抑制民众的杀伐,而开放引导民众的情欲,这就是《周南》和《召南》以仁泽被天下的原因。等到了周幽王和周厉王的时代,民众长久积柔,渐渐变成了慆淫,慆淫伴随着杀伐,此时杀伐这一端不能抑制了。于是秦人抑制住情欲这一端,又开启杀伐这一端,变得和周朝民众未开化时一样,充满着駤戾之气,即使是妇人,也将与人争胜,这就是秦国的风气为天下雄的原因。
船山把情欲和杀伐归于阴性的根据源于《易经》。船山说:“坤之初曰:履霜坚冰至,言启也;六四曰:括囊,言闭也。”[1](P370)坤卦初爻的爻辞是“履霜坚冰至”,船山认为这是阴性的开启;第四爻的爻辞是“括囊,无咎无誉”,船山以为这是阴性的关闭。阴性的发生发展有一个过程,但不管怎样,阴性总是伴随着严寒肃杀之气。船山在《周易内传》中解释坤卦初爻的时候说:“阴兴必盛,自然之数也。故一生,一杀,不以损天地之仁;一治,一乱,不以伤天地之义。特当其时,履其境,不容不戒,故为占者言之。”[2]在船山看来,阴气一旦兴起,必然会发展到一个盛大的境地,这是自然的理数。生杀之乱,都不会损害天地的仁义,但人在具体的时空环境下,则有可能受到阴气的伤害,所以对阴气的发生要保持警惕。在说明了《易经》的原理以后,船山论述到情欲与杀伐的启闭对社会风气的巨大影响:“虽然,一启一闭之间,强弱之司,王霸之辨,人心风会之醇漓,大可见矣。汉唐都周秦之故壤,其民一也。汉教近周,唐教近秦,而声诗之作亦异焉。”[1](P369—370)
船山认为,在情欲与杀伐的一启一闭之间,可以看出国家的强弱、王霸的分别、民风的醇薄和人心的向背等,这些都可以通过诗歌表现出来。周、秦、汉、唐四个朝代,都是以西安一带为都城,那里生活的民众都是一样的,但风气却不一样。大体说来,汉朝的教化和周朝类似,而唐朝的教化和秦朝类似。船山对唐朝诗歌所承载的教化功能很不以为然,其原因是唐朝诗歌近秦,充满着杀伐之气:“三唐之作,迫矫而无余思,虽北里南部之淫媟,且有杀伐之气焉。”[1](P370)即使是一些艳诗也不能避免。在唐朝的诗人中,船山对杜甫和韩愈的评价尤其不高。船山说韩愈的诗歌和《秦风》中的《车邻》及《驷驖》是一样的:“韩退之何知?以其《车邻》、《驷驖》之音,增之以浮促,倡天下于敖辟褊刻之守,而为誉之曰起八代之衰,然则《秦风》之掣杀摋,亦以起二南之衰与?”[1](P370)船山虽然认为,情欲和杀伐的一启一闭之间体现了诗教的不同,但并未认为二者是同等地位的。在周秦汉唐四朝中,他明显偏向于周朝和汉朝。韩愈的诗歌不足以起八代之衰,就好像《秦风》不能够重现《周南》和《召南》的辉煌一样。在解读了《车邻》和《驷驖》之后,船山在对《秦风》中最著名的一首诗《蒹葭》的论述中,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诗歌和政教的关系。船山写道:“秦人收周土,用周民,而关以临东国,屏周而拥之以令天下,先乎齐桓而霸,霸宛在也。如其周不可戴也,反周之旧,循周之迹,去幽、厉之所伤,沿文、武之所纪,御其民如轻车,而率其道如故辙,周之所以王者,秦即以之王,不待六国之熸而始帝也。王宛在矣,宛在而不知求,逆求而不知所在。典章之在故府,献老之在田间,交臂失之,而孰与为理乎?无已,则逆以取之,四百余年而后得。尤不审,而逆以守之,二世而遂亡。”[1](P371)
在这里船山对秦朝的兴起和灭亡做了深刻的思考。在船山看来,秦国居周朝的故土,统治周的旧民,如果能延续周的王道政治的话,早就可以为帝王了,而不用等到秦穆公称霸以后再过了四百多年才取得天下。秦王朝以杀伐,也就是以逆去天下,到后来以逆守天下,二世而亡。值得注意的是,船山这番对周秦不同政教方式的理解,并没有完全脱离《蒹葭》这首诗本身。船山从《蒹葭》诗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意象,认为这是周朝的政教在水一方;以诗中“溯洄从之,道阻且长”的意象,认为这是秦国不能用周朝的治理方式,只能以逆取天下。船山认为,《蒹葭》这首诗是一首“刺”诗,刺秦国在国家道路发展的选择方面不明智,而通常人们认为的秦朝不仁不义无礼只是这种道路选择下的表现:“天下怨秦之不仁,恶秦之不义,贱秦之无礼,而孰知其一于不智也?蒹葭之刺,刺之早矣。”[1](P371)值得注意的是,船山对《蒹葭》的解释方式既与《毛传》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又脱离了《毛传》,还和今文经学,也就是“三家诗”的解释有异曲同工之处。《毛传》认为《蒹葭》的本旨是:“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3](P422)孔颖达进一步论述曰:“襄公新得周地,其民被周之德教日久,今襄公未能用周礼以教之。礼者为国之本,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故刺之也。经三章,皆言治国须礼之事。”[3](P422)
《毛传》和孔颖达都认为,《蒹葭》一诗的主旨是刺秦襄王不能以周礼治国,将无以巩固秦国。秦襄王是秦国第一代被周朝正式册封的诸侯,因为安定被犬戎攻破的西周王室有功,在周朝东迁以后拥有了周朝无力顾及的岐山以西的土地。因此秦襄王可以说是秦国真正的开国之君,但是秦襄王不能用周礼治民,所以《蒹葭》之诗对秦襄王的政教进行了“讽刺”。
船山在对《蒹葭》的解释中,并没有提到秦襄王个人,而是提到了自秦襄王以来的历代秦国政教,均不能顺用周缘人情制礼之政教,反而逆用戎狄之杀伐。既用逆取天下,又用逆守天下,所以四百多年去之而二世失之。晚清今文学家魏源对此诗有如下解读:“襄公初有岐西之地,以戎俗变周民也。豳、邰皆公刘、太王遗民,久习礼教,一旦为秦所有,不以周道变戎俗,反以戎俗变周民,如苍苍之葭,遇霜而黄。肃杀之政行,忠厚之风尽,盖谓非此无以自强于戎狄。不知自强之道在于求贤,其时故都遗老隐居薮泽,文武之道,未堕在人,特时君尚诈力,则贤人不至,故求治逆而难;尚德怀则贤人来辅,故求治顺而易,溯洄不如溯游也。”[4](P448)魏源解读《蒹葭》,也从公刘、太王等周朝的先王之民谈起,周朝的民众久习礼教,秦襄公不能用礼教化民,反而用戎狄之俗化民,顺逆的形势,由此而产生了分别。魏源也提到,周的忠厚风气尽,肃杀的政令开始流行,这和前面船山论述的情欲与杀伐的对比有相似之处。《毛传》和《孔疏》都还注重秦襄王个人和周朝的礼制,船山和魏源则更注重忠厚之风,以免助长肃杀之气,与“国风”之旨更为接近一些。这一点,可以从对《蒹葭》的第一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解释中看出今古文在解《诗经》的一些不同之处。郑玄笺曰:“蒹葭在众草之中苍苍然强盛,至白露凝戾为霜则成而黄,兴者,喻民众之不从襄公政令者,得周礼以教之则服。”[3](P422)郑玄的解释用了一个对比:蒹葭遇霜而黄,不从襄公政令者遇周礼而服。可见郑玄以周礼为化民的核心,秦襄王如能用周礼则民服矣。“三家诗”中的齐诗认为:“阳气终,白露凝为霜。”[4](P448)又说:“蒹葭秋水,其思量,犹秦西气之变乎?”[4](P448)齐诗的解法更注重天气变化和民族习俗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和上面提到的船山对情欲和杀伐的理解上是一致的。当然,这并不能说明船山一定受到过“三家诗”的影响,《韩诗外传》有文本,“三家诗”的收集整理毕竟是晚清今文经学兴起以后的事情。不过,船山和“三家诗”的相似之处可以从《易经》的坤卦中得到解释。坤之初爻曰:“履霜坚冰至”,这和《蒹葭》中“白露为霜”这一意象是一致的;同时,在人事上,表现为秦襄王,秦国的开国君王不能够用周礼而用戎俗。坤之上六曰:“龙战于野,其血玄黄。”魏源认为秦襄王不用周礼而用戎俗,船山认为秦用杀伐而不用人情,其结果是伤天下而自伤,这就是用阴性之德太过的表现。
二、诗以达情
船山对《秦风》的解读中提出了“情欲”与“杀伐”两种阴性特质,来表现秦和周在政教方面的不同。既然秦在政教方面抑制情欲而主导杀伐而有很大缺失,与之相对的周朝在此方面有什么特点,《诗经》是如何体现的,在这方面,船山以“情”为中心,提出“诗以达情”的《诗经》的中心观点,并对“性”“欲”“气”等与“情”有关的方面做了阐述。
上文中提到,船山认为情欲和杀伐这两种属于阴性的特质不能够都闭合,必须以一种合适的方式导引出来。秦闭情欲而导杀伐,周闭杀伐而导情欲,二者在《诗经》中的表现不同。船山在论述《关雎》的时候认为,“情”是不可避免的,是需要导引出来的:“夏尚忠,忠以用性;殷尚质,质以用才;周尚文,文以用情。质文者,忠之用,情才者,性之撰也。夫无忠以起文,犹夫无文而以奖忠,圣人之所不用也。是故文者,白也,圣人之以自白而白天下也。匿天下之情,则将劝天下以匿情矣。”[1](P299)
这一段话是《诗广传》开头的一段话,几乎研究船山诗学的都要引用到。由于船山提到了夏商周三代的不同,很容易将这个话题往“通三统”方面引。不过,应该注意的是,船山在说道“周尚文”的时候,说的是“文以用情”,也就是说,周朝的“文”是通过“情”来表现的。船山把“文”解释为“白”,这一点值得思考。“白”也就是“表白”的意思,船山认为,圣人之情,可以“自白而白天下也”。所以,船山认为,“情”是一定要表白出来的,如果藏匿天下之情,就是劝导天下人匿情。船山认为,《关雎》在“白情”方面很有代表性:“悠哉悠哉,转辗反侧”这句诗表现了诗人不匿其哀,“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则表现了诗人不匿其乐。这说明了《关雎》很好地表达了诗人的哀乐之情。如果一味地藏匿感情会怎样呢?“匿其哀,哀结而隐;匿其乐,乐幽而耽。耽乐结哀,势不能久,而必于旁流。旁流之哀,懰慄惨澹以终乎怨;怨之不恤,以旁流于乐,迁心移性而不自知。”[1](P299)
在船山看来,如果把“情”藏匿起来,无论是哀还是乐,都会向着不好的方向发展。如果任由这两种感情肆意发展,人最后会变得怨恨,自己的心性被外物改变了但是自己却不知道。船山紧接着论证说,周朝衰败以后,人们无法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感情了,上层和下层之间互相隐匿自己的感情。隐匿感情所带来的后果是“愁苦”,愁苦导致人受到伤害:“淫者,伤之报也。伤而报,舍其自有之美子,而谓他人父,谓他人昆;伤而不报,而取其自有之美子,而视为愁苦之渊薮,而佛老进矣。”[1](P299—300)在这里,船山分析了“情”不能表白的两种后果:一种是怨而伤,伤而报,自己本性的美好自己不能知道,却去寻找其他异端的美好;另一种是把自己美好的本性视为产生愁苦的本源,沉沦于佛老。秦人舍周礼而用戎俗,正是不能认识到礼教治国平天下的美好。《关雎》之所以能够成为王化之基,是因为:“性无不通,情无不顺,文无不章,白情以其文,而质之鬼神,告之宾客,昭之乡人,无吝无惭,而节文已具矣。”[1](P300)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船山所认为的“情”的范围,比一般意义上的“感情”的范围要大。无论是“乐淑女以配君子”,还是“后妃之德”,仍不脱出其男女的范围,而船山认为的“情”,是可以质诸鬼神,告之宾客,昭告乡人的。这样一种“情”的定义,虽不舍男女之情,也不舍亲情,但是更加广阔,扶摇直上,只有“修齐治平”四个字可以概括了。船山对“情”的定义的广阔性,可以从另一段话中体现出来:“君子之心,有与天地同情者,有与禽鱼草木同情者,有与道同情者,唯君子悉知之。”[1](P310)由此可见,在船山看来,《诗经》中“情”的范围是广阔而深远的,这样一种深远,体现了诗教的特性。既然船山对“情”范围定义得如此广阔,其对“情”的基本定义值得讨论,如果脱离日常生活,则不免空泛。船山对“情”有一个基本定义:“情者,阴阳之几也;物者,天地之产也。阴阳之几动于心,天地之产应于外。故外有其物,内可有其情矣;内有其情,外必有其物矣。”[1](P323)“情”是阴阳轻微运动的特征,联系上文中船山把《秦风》中的情欲与杀伐归结为阴性特质,可以看出,船山是把“情”放在“阴阳”这样一个概念下来定义的,不但如此,船山进一步认为,“情”不是凭空而有的,而是和“物”有对应关系。既然天地中有物,人就不能不有“情”。前面提到,船山认为,情欲和杀伐这两种特质在人身上是存在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周秦对情欲和杀伐的不同态度会导致巨大的人文差异呢?在此方面船山有这样的论述:“故天地之间,幽昵之情未有属,而早已充矣;触罅而发,发乎此而竭乎彼矣。先王知其然,顺以开其罅于男女之际,而重塞之君臣、父子、朋友之间,乃以保舒气之和平。舒气之和平保,则刚气之庄栗亦遂矣。先王调燮之功,微矣哉。故知阴阳、性情、男女、悲愉、治乱之理者,而后可与之言诗也。”[1](P393—394)
这一段话和船山论《秦风》的意旨一致。人生天地间,人的隐藏的情感即使还没有具体显现出来,也早就存在了,一旦有合适的土壤,就会生发出来,表现为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先王知道这一点,所以在男女的情感之间开一条缝隙,而在君臣父子朋友之间则保持严格的界限。这样做是为了保持人的舒气的和平,消除男性阳刚之气中的暴烈的成分。先王在调理人的气息方面的深远考虑,如果不明白阴阳、性情、男女、悲愉和治乱道理的人,是不容易理解为什么《诗经》要以“情”为中心的。船山认为,诗教的最高意旨是调理人的气息,达到舒气的和平状态。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人的气息中有温柔敦厚的一面,也有刚劲暴烈的一面。阳气过盛则亢,阴气过盛则杀,只有阴阳处理比较合理平衡的状态,才能导人向善,治国平天下。调理阴阳的途径,是在男女之间开一条缝隙,对男女之间正当的感情予以承认,但是对于君臣父子朋友之间,则应该严格遵守界限。如果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要开导于男女,而塞之于君臣父子朋友,那只能从阴阳方面来解释。男女之间,性别不同,阴阳可以互相推移。在中国古代,父子自不待论,君臣和朋友,都是指男性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都是阳性之间的关系,如果不严守界限的话,则可能阳气过亢而导致和平之气尽而杀气弥漫。前面提到,船山在解释《秦风》的时候说,秦国“妇人且将竞焉”,当秦国的妇女都想去杀伐争夺的时候,秦国将自身强大的能量释放出来,这就是闭之于情欲,启之于杀伐,但这种闭情欲启杀伐的方式终究不能持久,所以秦二世而亡。
通过对人本性中的阴阳特性的思考,船山确立了以“情”为中心的诗教观。既然船山如此重视“情”,这和现代人理解的男女之间的感情有什么区别呢?这牵涉到对“情欲”的理解。船山在解读《秦风》的时候虽然将“情欲”二字连用,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在解释“性”“情”“欲”三者关系的时候,这样写道:“贞亦情也,淫亦情也。情受于性,性其藏也,乃迨其为情,而情亦自为藏矣,藏者必性生而情乃生欲。故情上受性,下授欲。受有所依,授有所放,上下背行而各观其生,东西流之势也。[1](P327)船山比较了“性”“情”“欲”三者的不同。这三者的关系是:“性”为上,“情”在中间,“欲”为下。比较特别的是,船山认为“性”是不能够看见的,通过“情”而表现出来,“情”也可以隐藏起来,这样就滑入到“欲”的级别中去了。所以,船山认为,“情”是从人的“天性”中转变而来的,而“情”本身又可以转变为“欲”的级别中去。既然如此,诗教的功能就是调节人的“性”“情”“欲”三者不同的转变过程,最后达到“致中和”的目的。船山说:“故唯一善者,性也;可以为善者,情也。”[1](P332)性为善,情则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欲。值得注意的是,船山对“欲”的态度是先肯定人的欲望,继而提出要调和节制人的欲望,使人从“欲”的层次向“性善”的层次转变。船山曰:“诗言志,非言意也;诗达情,非达欲也。心之所期为者,志也;念之所觊得者,意也。发乎其不得已者,情也;动焉而不能自持者,欲也。”[1](P325)
如果经过人心甄别后选择的期望,这是志;人感于物而动,不能自已,这是情。如果人见到好的东西就一定想得到,这是意;如果人被外物所控制,不能自己安定自己了,这就是欲。从这里可以看出,船山的诗教观中有“止于至善”的意思。船山认为,那些纵情声色的人,并不能真正实现和满足自己的“欲”。船山曰:“不肖者之纵其血气以用物,非能纵也,遏之而已矣。纵其目于一色,而群色隐;况其未有色者乎?纵其耳于一声,而天下之群声閟,况其未有声者乎?纵其心于一求,而天下之群求塞,况其不可以求求者乎?”[1](P439)
船山认为那些放纵自己于声色犬马的人,恰恰不是“纵欲”,而是遏制自己的欲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人只知道目前的声色,忽视了还有修齐治平之“大欲”存在。船山此论,得之于孟子。齐宣王好色好货,孟子认为如果齐宣王能推此以及天下,而不是将天下之色和天下之货变为私产,则可以王。孟子也承认饮食男女是人的基本欲望,推之可以王四海。可是当齐宣王试图以武力威天下的时候,孟子却认为这是缘木求鱼了。《论语》中卫灵公问陈,孔子行的意思也是一样的。在儒家看来,通过战争杀伐来推行政教、治理天下终究不是正道,而“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鳏寡孤独皆有所养”才是王者所应该实现的目标。这也是船山以“情欲”和“杀伐”判别周秦政教之异同的原因。
三、结 论
船山在解读《秦风》的时候,提出“情欲”与“杀伐”这两种属于阴性的特质,比较了周秦政教的不同。从秦国开国君王秦襄王不用周礼而用戎俗开始,秦国就走上了一条以杀伐谋取天下的道路。周朝的先王则不同,缘人情而制礼,承认人情的基本欲望是饮食男女。人的情感通过诗歌表现出来,观《诗经》中的各国国风,就可以知道各国的政教情况。“情”是船山诗教的核心,由于情上受性,下授欲,所以情既可以引导人向着美好的天性转变,也可能向着禽嬉兽聚的不好境地滑落。诗教的作用,就在于调节人的平和之气,以涤荡人的性情。如果饮食男女的欲望得不到合理满足的话,就有可能导致战争。情欲与杀伐,周、秦政教之异同,人情人心之向背,《诗经》一叶而知秋,见微而知著,君子辨之早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