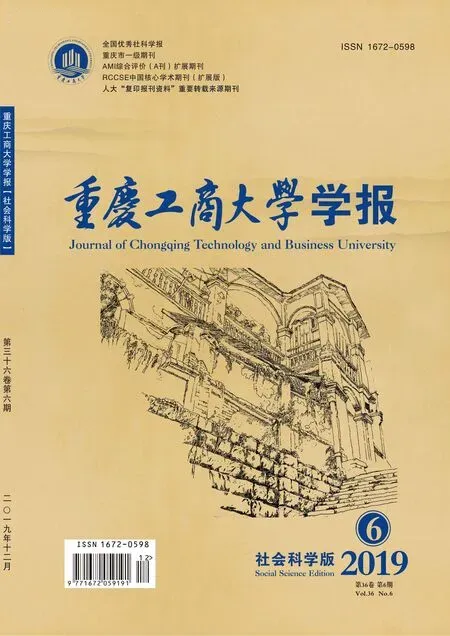汉代石阙艺术研究现状及理路分析
——一个文献综述*
陈绪春
(重庆工商大学 现代国际设计艺术学院,重庆 400067)
一、引言
阙是中国古代建筑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种建筑形象,是设置在宫殿、陵墓、城垣、祠庙、宅第大门两侧以彰显其主人尊贵地位的装饰性建筑物[1],其质地主要有木阙、土阙和石阙,阙作为建筑的出现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那时人们为了防御野兽和外族的侵袭,往往在部落聚居地的周围,搭建由树枝、垒土等筑成的围栏或围墙,为方便进出又在围栏围墙上开出了豁口,并在豁口两侧搭建了供瞭望和守卫的木楼,这种木楼就是阙的雏形;有文献记载,我国周代时期,阙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建筑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进步,在人们能够建造大型门屋后,阙的防御性功能逐渐退化,演变成门外侧的装饰性建筑,明清故宫午门成为宫阙发展的最后阶段和形式。
关于阙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诗经·郑风·子衿》:“纵我不往,子宁不束,佻兮达兮,在城阙兮”;春秋战国时期有关阙的记载就较多了,《左传·庄公二十年》:“郑伯亨王于阙西辟”;《谷梁传·桓公三年》:“……诸母兄弟不出阙门”;《史记·春木记》:“作为咸阳,筑翼阙,秦楚都之”等。阙最初的名称叫“观”,是“于上观望”之意,又名“象魏”系“其上具有法象,其状巍巍然高大”的建筑[2]。阙作为建筑形式其最初功能就是防御,国家出现后,其社会功能得到大大提升,主要有:其一,表示门的含义。《周礼》谓之“象魏”;《春秋经》谓之“两观”;《礼器》谓之“台门”;《说文解字》:“阙,门观也,从门从朔”;《释名》:“阙,缺也,在门两旁,中央为道也”;《广雅》:“阙,门观也”。其二,地位等级的象征。《礼记》:“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内阙一观”;《白虎通义》:“阙者,所以饰门,别尊卑也”。其三,天子发布号令,大臣奏事思过的地方。《释名》:“门阙,天子号令赏罚所出也”;《古今注》:“阙,人臣将朝。至此则思其所以阙多少,故谓之阙”。其四,观天象之功能。《白虎通》载:宫门外则“夹建巨阙以应天宿,虽不如礼,犹象魏之”。因此,阙不仅是汉代建筑的“活化石”,更是汉代社会政治、文化及风俗的载体。
汉代石阙是我国汉代时期人们为了长时间保存而用石材修造在祠庙或陵墓之前的礼制性地表建筑,称为祠庙阙或墓前神道阙,因此,我们现在所说的汉代石阙准确地说主要是指这些祠庙、墓石阙,这些石阙主要分布在南方的四川盆地和北方的中原和山东地区,大多为东汉时期遗存,有的稍晚于魏晋时期,南北朝以后,一般官吏不再建阙,唯有帝王仍保留此制,至元、明、清三代也不复使用,祠庙阙在汉代以后各阶层基本也不复使用[3]。从建筑结构上看这些石阙主要有仿木构建型和土石型两种[4]。汉代石阙除了彰显等级地位等作用以外,其主要功能是通仙通神的标志,是汉人神仙信仰中仙界天门和人仙交通的媒介[5]。经过岁月沧桑的洗礼,汉代石阙已经演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成为一部不朽的石质“汉书”。
二、唐宋以来对汉代石阙的研究简述
唐朝时期,对阙的记载往往在诗歌中,如李白的“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王维的“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等,对汉代石阙铭文的记载有张怀瓘的《六体书论》,其中对沈府君阙的铭文书法进行过“作威投戟,腾气扬波,自魏晋以来所能仿佛也”的赞誉。宋代以来,金石学兴起,众多的金石学者对汉代石阙铭刻捶拓抄录,考释不断,但对阙的建筑构造和装饰雕刻阙研究甚少[6]。北宋碑刻目录学家赵明诚所著《金石录》是最早研究汉代石阙铭文艺术的;南宋洪适撰写《隶释》对渠县的冯、沈二阙及新都的王稚子阙说其铭文皆是八分书,明确三阙书体为典型的隶书;明朝杨慎《观王稚子阙二十二韵》赞其铭文“八分隼尾隶,千年耿不磨”;清朝王荣懿《题王稚子阙》“汉碑今存几,只字重兼金”;清代《渠县志》记载,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渠县邑候王王椿源建亭保护,并有碑记[7];清《与地碑目》[8]所言“沈字,左字,道字、丰字,发笔皆长过三四寸许,令字、交字两笔皆长,为诸阙所未见”。沈府君阙两千年间为世人纷争摹拓,仅清代道光年间就有“数百纸”在海内流传,收藏者称“如得异宝”[9];清,顾蔼吉《隶辩》[10]将渠县冯、沈二阙铭文内容纳入其著录中,充分说明渠县汉阙隶书铭文是具有代表性的;康有为撰《广艺舟双辑》,对高颐阙、冯焕阙、沈府君阙、王稚子阙铭文评价为“东汉之隶体,亦自然之变,然汉隶中有积近今真楷者,如高君阙故、益州、举、廉、丞、贯等字,阳、都字之邑旁,直是今真书,尤似颜真卿”;“孔宙曹全是一家券属,皆以神逸宕胜,极其势而去,如不欲还,冯神道、沈君神道亦此派也”;“冯府君、沈府君隶中之草也”;“东汉分卷,莫古于王稚子阙矣”[11]。进入民国时期,从建筑及考古角度关注石阙的学者开始多起来,法国人色贾兰,1914年对中国西部地区的汉代石阙进行了考察,形成了《中国西部考古记》[12],并拍摄了一些珍贵的石阙图像,使我们有机会目睹石阙在那个时代的风采;建筑学家梁思成和刘敦桢等人对汉代石阙建筑也予以了关注和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并在他们的文献中进行了著述。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石阙艺术的研究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汉代石阙曾经历过“破四旧”的洗礼,但学界对汉代石阙的研究却热情不减,成果不断。
(一)在考古学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首先是围绕地表石阙实体和发掘石阙实体的相关考古研究,1954年现代建筑学、建筑史学家,中国建筑教育及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刘敦桢发表《山东平邑县汉阙》[13],对平邑三阙的形制作了论述,对年代作了考释判断,正式开启了新中国对汉代石阙的研究序幕;1961年建筑学家陈明达先生在文物杂志发表了《汉代的石阙》[14]一文,对河南、山东、四川、重庆等二十三处石阙进行了测绘和介绍,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较完整的石阙研究成果;1965年山东莒南发现汉代石阙[15],第一次从地下发掘出了汉代石阙遗物。十年“文革”期间,对汉代石阙的研究经历过短暂停顿,1975年四川西昌城郊出土石阙[16],成为我国已知石阙分布最西南的一例,为汉代石阙地域分布的扩大提供了实证;1981年耿继武发表《高颐阙》[17]一文,对四川雅安的高颐阙进行了详细考古测量和画像介绍;1983年2月凉山自治州文化局为筹建奴隶社会博物馆,在州内进行一次重点文物考察工作时在昭觉县好谷乡发现东汉石表和石阙残石[18],说明汉代时期的神仙学说已经影响到最西南地区了;1990年河南省博物馆、河南文物研究所、河南省古代建筑研究所主编,吕品编著的《中岳汉三阙》[19]出版,随后的1992年,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徐文彬、谭遥、龚廷万、王新南编著的《四川汉代石阙》[20]出版,这是新中国第一次系统对河南、四川及重庆三地区境内汉代石阙的详细考古专著,具有工具书式的参考意义。1993年5月山东莒县东莞村发现汉代石阙[21],2003年山东平邑县博物馆的王相、唐仕英对皇圣卿阙和功曹阙进行了考古研究[22];随着三峡工程的上马及各地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等,三峡库区长江两岸开始文物抢救性发掘,《重庆忠县乌杨阙的初步认识》[23]《重庆忠县汉代乌杨阙再研究》[24]《重庆忠县邓家沱石阙的初步认识》[25]《重庆忠县邓家沱阙的几个问题》[26]《重庆忠县邓家沱汉代石阙再讨论》[27]《关于重庆忠县邓家沱石阙铭与墓主人的推断》[28]等文章相继发表,学者们对出土的乌杨阙、邓家沱石阙等的年代、复原等进行了全面介绍和深入的考古、辨析研究,使修复后的乌杨阙成为第一个以完整面貌进入博物馆的石阙实物。2012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渠县文管所对渠县汉阙进行了一次完整的勘探调查[29],为文物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考古工作者的不断努力,汉代石阙家族不断增添新的成员,同时,也使石阙这一汉代遗物能更好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至此,全国汉代整残石阙总数已经达到35处46尊,其中山东地区整残石阙5处7尊,河南地区整残石阙4处6尊,四川地区整残石阙20处25尊,重庆地区6处8尊。其次是对石阙的考释研究。在对石阙实体考古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开始关注汉代石阙的考释研究,孙华等相继发表《梓潼诸阙考述》[30]《平阳府君阙考》[31]《四川雅安高颐阙考释》[32]等文章,分别对四川境内的几处重要石阙做了详细考释;唐长寿发表《汉代墓葬门阙考辨》[33],对门阙的表现形式、形制及象征意义进行了阐述;姜生发表《汉阙考》[34],认为汉代石阙是早期道教所追求的仙界的象征符号和人仙两界交通的神学媒介。
(二)围绕汉代石阙展开的相关历史文化研究
一是学者们认为汉代石阙在汉代之所以能够大量修建,首先是与汉代统治者的政治倡导分不开的。宋艳萍《汉阙与汉代政治史观》认为,阙在汉代政治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35],同时她在《从“阙”到“天门”——汉阙的神秘化过程》中还认为,汉代石阙经历了从阳宅的实体建筑逐渐被运用为墓葬的标识物到演化成为灵魂升仙之所的标识物的演变过程[36];其次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厚葬之风的兴起是汉代石阙大量构筑的经济基础[37]。二是从当代人的角度理解汉代石阙文化,黄剑华《话说中国汉阙》[38]认为,通过对部分汉代石阙的研究,汉代石阙向我们透露了极其丰富的信息内容,对其包罗万象的文化内涵做深入的探讨,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陈国生《汉阙的文化意味》[39]说,汉阙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蕴含,精巧的艺术创造和奇特的造型,是一笔珍贵的文化财富;李同宗的《渠县汉阙的文化解读》[40],阐释了阙谓何物、碑阙有别,从阙的建筑、书法和魅力等方面对汉代石阙进行了论述;刘自兵、戴天柱的《巴蜀汉阙历史文化考察》[41]对巴蜀汉阙历史文化、身份等考察后认为,有铭文的石阙墓主人社会政治地位较高,无铭文的墓主人社会政治地位低微,石阙不仅是一种礼制符号,更是一种宗教符号,是汉代社会的巫术工具之一。
(三)汉代石阙建筑艺术研究
1984年刘敦桢先生在《中国古代建筑简史》[42]中第一次将汉代石阙的建筑结构、特点进行了整理,1992年朱晓南《阙的类型及建筑形式》[43]将阙的功能和演变及建筑形式进行了分类;1996年前后王其明先生从建筑的角度进一步对四川忠县的两处汉代石阙进行了详细测量考察并发表了《记四川忠县的两处汉代石阙》[44],对重庆忠县的两处石阙构件进行了详细勘察,得到了第一手忠县石阙构件数据;朱晖《中国古代小品建筑汉阙的建筑艺术魅力》以雅安高颐阙为例进行探讨后认为,汉阙小品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体,其作为建筑规划的参考坐标和建筑形态的视觉发散点,所激发的审美作用不可估量,对当代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中文化特性缺失问题展开思考或将提供借鉴[45];刚政《论汉阙建筑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意蕴》[46]说,汉阙建筑所蕴含的符号学意义在建筑材质和造型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特殊的石刻珍品汉阙又具有多方面的文化价值;田鹏刚等的《乌杨汉阙加固与修复工程》[47]论述了在对重庆忠县出土的乌杨阙建筑使用现代方法进行加固修复的技术研究,保障了复原效果,使石阙重现了历史神韵;《由重庆汉石阙简析汉代建筑特征》[48]认为,两汉时期是我国建筑的青年时期,汉阙建筑为我们研究古代建筑的演变提供了有力证据;于福艳《从画像石中的汉阙艺术看汉代的建筑形式》[49]认为,汉代石阙不仅表现出汉代建筑的形式与特征,同时也从多方面、多层次反映汉代社会文化内涵;《论汉阙建筑的文化特性及其当代意义》[50]认为汉阙既是一种古老的建筑艺术也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表现,其所蕴含的文化特性就是“天人合一”思想文化在石阙建筑上的体现;《汉阙建筑艺术特点及其精神功能》[51]一文认为,汉阙建筑特点主要是仿楼阁建筑模式,是通向天庭的必经之路,说明汉人以阙代仙境的观念;《试析巴蜀汉阙整体构成的秩序之礼》[52]认为,汉代石阙凸显了汉代皇权至上的观念及传统的尊卑秩序;杨光壹在《中国汉阙建筑艺术及其影响研究》[53]中指出,现代仿汉建筑缺少的韵味正是缺乏对古建筑中文化内涵的展现,在物质文化生活不断提高的今天,吸收外来文化或是保留本土特色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四)汉代石阙画像艺术研究
画像艺术是汉代的主流艺术形式,汉代石阙除建筑艺术外,画像艺术是汉代工匠最倾注心血的地方,对石阙众多画像艺术的研究,学者们主要集中在几个重要的画像艺术主题及其图像的研究。
1.西王母及其图像研究
研究成果最多的是“西王母”这个主题。张泽洪等《道教西王母信仰与昆仑山文化》[54]指出,西王母神话与昆仑山的神仙境界,在道教神仙信仰的建构中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西王母女性神仙的优美形象,是吸引女道士成仙的楷模,因此在汉代时期出现了很多的关于西王母的画像艺术;俞方洁在《西王母神话形象演变的隐喻》[55]中进一步说明西王母在汉代盛行的原因,一方面是神仙和长寿思想的社会心理基础,另一方面是为西王母被外戚利用成为篡权者寻找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在民间与官方相互推崇中,逐渐使西王母成为带给人们祥瑞、富贵、平安、子嗣延绵等福祉全能神。韩高年《<山海经>西王母之神相、族属及其他》[56]中揭示西王母神相由司祭者、部落首领再到美丽女神的演化过程;罗焱英《从神话女神到道教女仙》[57]一文从道教神学体系的角度看西王母道教形象的演化;《汉画像西王母的图文互释研究》[58]认为西王母形象演变象征人类征服自然的美好愿望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西王母神话:女神文明的中国遗产》[59]揭示儒家新神系统如何继承、改造、排斥和遮蔽女神崇拜,使西王母被道教接纳和再造;刘宗迪《西王母神话的本土渊源》[60]《西王母信仰的本土文化背景和民俗渊源》[61]二文,首先肯定西王母非西土之神,而是完全的东方本土文化的产物,源于东方的神仙道教信仰,其次进一步证明西王母信仰源于上古时代的秋偿仪式上祭拜的祖妣之神,到汉代演变为以传“西王母筹”为特征的民间宗教。何志国《四川汉代西王母图像的起源》[62]对四川地区西王母图像起源进行了梳理并驳斥了西王母图像形式由外地传入四川盆地的观点;《四川东汉时期的西王母图像:主题与构成》[63]指出四川地区以“西王母”为核心的符号系统,是文化和行为规范构成信仰关系表述形式的途径,其造型符号反映出当时的文化观念及文化体系,成为连接人们内心的文化观念和外部客观世界的媒介;黄剑华在《古代蜀人的天门观念》[64]中指出正是古代蜀人魂归天门、升天成仙的思想观念,开启了西王母信仰的滥觞。域外学者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巫鸿的《论西王母图像及其与印度艺术的关系》[65]《论西王母图像及其与印度艺术的关系(续)》[66]独辟蹊径,从西王母和阴的原则,与昆仑山的融合,从超自然的存在到宗教偶像再到西王母的长生天国的发展过程论述了西王母这个主题的演变和发展过程。
2.“启门”及其图像研究
人们之所以对“启门”主题及图像感兴趣,正如赵碧玉《无故不窥中门——论半启门》[67]中所说,从图像本身和观者两个部分来说,“启门”是一个互动性较强的图式,半开的门,半露的人,无不吸引着我们对她身后空间的好奇;马颖《“妇人启门”图新探》[68]认为,妇人启门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因此,这个图式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谢琪《论“妇人启门”图》[69]从装饰题材上简要分析妇人启门图式;范鹏、李大地《“半开门”画像的发现与研究》[70]认为,“启门”寓意是以西王母对墓主人的接纳,是升仙程式过程重要的符号载体,体现了汉代时期升仙学说对丧葬行为的重要影响;四川大学教授罗二虎《东汉墓“仙人半开门”图像解析》[71]对“仙人半开门”图像解读后认为,“仙人半开门”是东汉中晚期的一种升仙程式,在此过程中道士的作用得到突显,这是早期道教兴起和张天师道在巴蜀盛行的反映;《墓饰“妇人启门”含义蠡测》[72]把“启门”图像解读为墓葬者期望墓主人升天成仙而得到永生的标志;郑岩《论“半启门”》[73]则系统研究了“半启门”这种图像的形式特征及与古代墓葬意义之间的关联;樊睿《汉代画像石中的启门图图式浅析》[74]认为,“启门”图式源于生活,虽主要发挥着沟通世俗和神仙世界,但实际和虚拟两种意义都得到了延续,使汉代人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不同的图式,并形成了各自的风格特点;吴雪杉《汉代启门图像性别释读》[75]认为,“启门”者最早为男子,后转为女性,“启门”图像在两汉呈现出较明显的演化过程,对这一图像性别含义的阐述需要考虑图像自身的发展历史,四川地区的启门图像与西王母信仰关系密切,是西王母的使者的化身,山东、苏北地区的“启门”图像则更多具有世俗色彩,呈现出某种理想的社会性别秩序。
3.伏羲女娲及其图像研究
一般认为伏羲女娲是对偶神,是人类自身对生殖崇拜的结果,陈猛在《汉画像中的日月神——伏羲、女娲》[76]认为伏羲女娲是具备司日月出入的神,是创造人类、规矩天地、主宰万物的人类始祖形象。李丹阳的《伏羲女娲形象流变考》[77]通过文献资料对汉代时期各地伏羲女娲图像进行分类描述后,发现伏羲女娲形象从各自独立到形成对偶神以后统一为人首蛇身形象,再到宋代完全人化后又渐渐趋于独立的演化过程;郑先兴《论汉代的伏羲女娲信仰》[78]从社会生活与宗教信仰的角度认为伏羲女娲神话折射出远古婚姻制进程中夫妻婚姻的形成;张博《浅谈汉画像艺术中的伏羲和女娲》[79]认为,伏羲女娲反映自远古时代一直到汉代的图腾崇拜,有着深层次的哲学寓意及神秘象征;卜友常《汉代伏羲女娲交尾画像浅析》[80]则认为伏羲女娲交尾图像是汉代人对道教房中术迷恋的结果。
4.玉兔及其图像研究
玉兔形象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形象,汉代石阙上出现了较多的玉兔及玉兔捣药形象,对于这些图像学者们是如何解读的呢?叶舒宪《玉兔神话的原型解读》[81]认为,人们对玉兔和玉兔捣药的想象是中国玉文化的大传统要素造就的,月兔想象则是中印文化共同的母题;刘惠萍《汉画像中的“玉兔捣药”——兼论神话传说的“借代”现象》[82]对文献中的两种兔形象,即一为月中兔,二为西王母图像或仙境中的捣药兔的讨论,发现二者原本属不同系统且形态、功能和意义也不相同的两种图像,在流传过程中使月中出现了“捣药兔”的说法,兔形象也因此成为一种月神话传说的定式;张从军《玉兔捣药》[83]认为,无论是在西王母的世界或是嫦娥的月宫,安置玉兔捣药的图像都是汉代人们寻求长生不死的愿望和理想;徐小曼《论汉画像“捣药兔”形象》[84]认为,“捣药兔”不仅代表了汉代人的心理愿望及生命轮回的文化内涵,更表现了对长生不死的追求与历史部落的怀念,是汉代人的思想观念的折射与对生命长存的愿望与追求;高梓梅《汉画像玉兔叙事论考》[85]认为,无论玉兔的哪种形态,其实际都是在讲述人类的故事,是人类生活需求和心理愿望的表现,兔事实为人事。
5.“四灵”及其图像研究
“四灵”亦称“四神”“四象”“四宫”“四兽”等,现在所指的“四灵”是对青龙、白虎、朱雀及玄武的统称。倪润安《论两汉四灵的源流》[86]认为,由四灵组合而成较完备的实物形象最早应出现在汉代初期,两汉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四灵出现了演变并形成了对应的地域特点,西晋以后,“四灵”图像的使用逐渐成消失之势;丁常云《道教与四灵崇拜》[87]认为,道教对四灵的崇拜是源于古代人们对原始动物的敬畏和对宇宙天体联想,道教形成以后四灵成为守护神,宋以后更成其为尊神而受到广泛奉祀;卜祥伟的《四灵信仰及其道教化探微》[88]认为“四灵”形象作为墓门图案与汉代人们时常把四灵画在阳宅门上用以驱邪避鬼的作用相似;贾艳红《汉代的四灵信仰》[89]认为“四灵”既是门户的守护者,又是接引死者升天的使者,是吉祥如意的象征;牛天伟《汉代“四神”画像论析》[90]认为“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作为一个具有方位意义的方阵,其布局在观念层面上是有严格规制的,是由古代的祥瑞动物崇拜,以南为尊的方位观念,阴阳五行思想和天文、神话因素相互融合而形成的。
6.“六博”及其图像研究
六博,又称陆博,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博戏类游戏,因使用六根博箸而称为六博,以吃子为胜,风靡于战国和秦汉时期,隋唐以后逐步销声匿迹[91]。许蓉生《浅议六博的产生、演变及其影响》[92]认为,六博在中国赌博史和体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杨宽《六博考》《六博续考》[93],黄儒萱《六博棋局的演变》[94],崔乐泉《中国六博研究》(上)[95](中)[96](下)[97],通过文献资料对“六博”的基本形态、规则和发展进行了梳理,按照汉代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六博”画像出现在石阙上具有多重含义;姜生在《六博图与汉墓之仙境隐喻》[98]中认为是界定墓室为仙窟的象征,是墓葬仪式实施的一种时空界定符号;程志娟《汉代规矩镜与六博》[99]认为,“六博”是占卜方法的一种,它可以帮助人们得到神灵的指引,避祸得福,这也是“六博”画像经常出现在汉代石阙上的另一个原因;除占卜功能外,金爱秀《汉代的六博文化研究》[100]认为,“六博”是阴阳家对宇宙的认识,具备辟邪功能,这种活动不仅世俗人喜欢,就连神仙也喜欢;王煜在《四川汉墓画像中“钩绳”博局与仙人六博》[101]一文中认为,四川地区汉墓中的“六博”画像可分两类,一类为宴乐六博,另一类为仙人六博,后者以二绳四钩象征观念中的宇宙模式,仙人六博象征以阴阳六爻运行宇宙。
7.其他主题及其图像研究
除了上述对石阙画像的研究外,学者们也对其他一些画像艺术进行了研究。胡广跃在《石头上的中国画——武氏祠汉画像石的故事诠释》[102]著作中,对山东武氏祠阙上的主题图像进行了历史文化解读,为我们全面理解石阙上的图像提供了背景材料。悬璧图研究,牛天伟《略论“天门悬璧”图中璧的象征意义》认为璧为日月的象征符号,其内涵又有和合阴阳、沟通人神的功能[103];吕品《“盖天说”与汉画中的悬璧图》[104],幸晓峰《汉代石阙艺术“悬璧图”》[105]对汉代石阙上各种悬璧图式进行分析后认为,东汉时期璧的使用方法多悬挂,又与传说中代表自然神的鸟兽构成主题,但对悬璧图意义的考证尚有待分析和探讨。“捞鼎”画像研究,张艳秋《汉画像“捞鼎”图的流传与嬗变》[106]根据“捞鼎”图案组合和组合的变化情况,得出该图像流传的路线依次为山东、江苏、河南、四川,到巴蜀后进入转变发展期和消失期,图像结构变化与移民的迁入及当地葬俗等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蹴鞠画像研究,《从汉阙和画像砖石中的蹴鞠图像解析汉代蹴鞠文化》[107]解析汉代蹴鞠活动长久不衰的历史原因。“三鱼共首”画像研究,吴晓玲等《汉画像石中“三鱼共首”图像内涵考析》[108]认为“三鱼共首”画像既是人间生命繁荣的祥瑞象征,又包含着对生命无限延长的神性祈盼。钱树画像研究,美国学者艾素珊《东汉时期的钱树(上)》[109]认为钱树直观形象地表达了通往天国的汉代观念,它的主题是汉代人追求不死和来世的幸福。师旷鼓琴主题画像研究,方萌《“师旷鼓琴”给人的启示》[110]描述师旷鼓琴背后的历史故事和师旷音乐的魅力,指出要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音乐创作的意义;幸晓峰《四川汉阙与〈师旷鼓琴〉》[111]印证了师旷鼓琴故事的真实性又弥补了早已失传的“鱼头琴”的形制图像,对音乐发展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车马画像研究,美国学者巫鸿《从哪里?到哪里去?——汉代艺术中的车马图像》[112]认为车马图像表现了假想的死者灵魂来世的旅行,与丧葬礼仪无关。画像辨识研究,唐长寿《汉画“玃盗女”图补说——芦山樊敏阙“龙生十子”图辨误》[113]对四川芦山樊敏阙上“龙生十子图”做出了实为“仙界宴饮图”和“玃盗女图”的论断,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汉代石阙图像艺术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五)汉代石阙铭文书法研究
汉代石阙上的铭文是标明墓主人身份等信息的直接证据,也是展现汉代书法艺术的第一手资料。《成都汉阙刻石铭文考释》[114]《成都郊区两块东汉墓阙铭文补说》[115]《<成都郊区两块东汉墓阙铭文补说>之补》[116],三篇文章二位学者对成都地区石阙铭文年代问题展开了反复的讨论研究,形成了良好的学术争鸣氛围。蒙静等在《1949年以来巴蜀地区汉代石刻文字的发现与研究》[117]一文中对成都王文康、王君平二阙,昭觉石阙、忠县邓家沱石阙等的铭文内容进行了梳理;泸州市博物馆谢荔《四川汉代碑刻艺术初探》[118],将巴蜀地区汉代石阙铭文艺术归纳为樊敏阙类和李业阙类二种风格,樊敏阙类的风格是“体力笔拙,笔力遒稳,气派宏大,浑厚雍容”,包括夹江杨公阙,梓潼杨公阙和尹公阙在内的均属这种风格类型;李业阙类的风格是“方整劲挺,斩截爽利”,包括昭觉石阙、成都王文康、王君平二阙等在内的属于这种风格;谢凌《四川地区现存主要铭文石刻及其艺术特色》[119]将巴蜀地区石阙铭文艺术风格归纳为:第一类为工整精细、法度森严(高颐阙、平阳府君阙等);第二类为飘逸秀丽、圆静多姿(夹江杨公阙、上庸长阙、尹公阙等);第三类为风神纵逸、劲拔多姿(渠县冯、沈二阙等);第四类为气度宽阔、厚重古朴(王稚子阙、樊敏阙等);徐文彬等认为巴蜀地区石阙铭文艺术风格有三种,“一是以冯焕阙铭文为代表的瘦劲清朗,二是以沈氏阙铭文为代表的流畅飘逸,三是以司马孟台、高颐阙为代表的凝重笃厚”[120];候忠明《渠县汉阙隶书艺术研究》[121]《东汉冯焕阙及其隶书艺术考略》[122],认为渠县的冯、沈二阙铭文书法艺术在书写上兼具石刻与简牍之妙,字里行间充溢着率真与灵性,浪漫抒情;周嘉荃《沈府君阙铭文掠磔飞扬透露的历史信息》[123]从沈府君阙铭文掠磔飘逸恣肆出发认为其透露出的深厚的书法传承,精美的装饰意味和微妙的书者心态三点信息值得我们关注;张凯维《汉代丧葬文化中的阙及铭刻书法》[124],对整个汉代石阙铭文书法艺术风格进行了“方峻挺劲型、敦厚质朴型、劲艺活脱型、端庄典丽”四种分类后,认为将汉代石阙铭文艺术置于宏观丧葬文化的视域之下对民间书风、墓葬书迹等问题的研究有积极意义。
(六)汉代石阙艺术价值及运用研究
汉代石阙作为汉代社会的历史证物,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承贡献是毫无疑问的。成都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冯一下先生在《四川汉阙的价值》[125]首先认为它是保留下来的不可多得的汉代地面建筑实物,这些石阙称得上古代建筑的杰作,是汉代一般建筑的缩影,石阙上的铭文为研究汉代文字书法保存了第一手资料,为研究汉代的典章制度、人物习俗等提供了宝贵资料;唐林《四川汉代画像石的艺术成就》[126]对巴蜀地区石阙画像进行分类后,认为巴蜀地区汉代石阙画像艺术风格纯朴厚重,既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又具有清新的地方特色,也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典范,显示出两汉艺术的巅峰之美,是人类艺术史上的瑰宝;蒋英炬、吴文祺在《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127]论述到,石阙是雕刻绘画与建筑完美统一的装饰艺术,是独具匠心的艺术作品,画像的写实性画面展现了汉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图卷,充满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神奇无穷的世界,彰显出汉代工匠浪漫主义色彩的特质。在汉代石阙运用价值研究方面,吴小萱《汉阙元素在建筑景观设计中的使用》[128]认为,在当今西方建筑文化在中国建筑文化中占主导地位时,提出了直接移植石阙建筑形式、使用汉阙中某些元素再设计和把汉阙符号化等运用手段,将传统文化进行延续,从而形成中国自己的文化特色。
四、汉代石阙艺术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从汉代石阙的研究现状上看,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考古学者的辛勤劳动,汉代石阙在数量上已经从解放初期的20余处增加到了35处46尊,对石阙艺术的研究成果可以用硕果累累来形容,但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我们也发现目前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第一从整体研究上看,以地域范围的研究多,但对各地域石阙的集中、集合及整体图像研究和展现几乎是空白;对南方石阙的研究较多,而对北方石阙的关注却较少;对石阙的比较研究除笔者有微小研究成果外,目前未见有诸如南北石阙的比较,北方石阙的比较等成果出现;第二是目前对石阙上代表性主题画像研究较多,忽略了其他画像的考释和深入民俗的研究,如幸晓峰就提出对悬璧图式的意义等尚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第三在石阙成因上还需要进一步进行专题研究。阙,自古有之,唯汉代石阙盛极,为何魏晋以后除帝王以外在社会上戛然而止?目前这个问题没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基于以上汉代石阙研究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石阙目前的研究方向在于对汉代石阙从图像艺术角度进行集中、集合展现,使石阙从深闺走向大众,在此基础上对汉代石阙艺术的各个方面进行地域之间的比较研究是当下对汉代石阙研究的主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