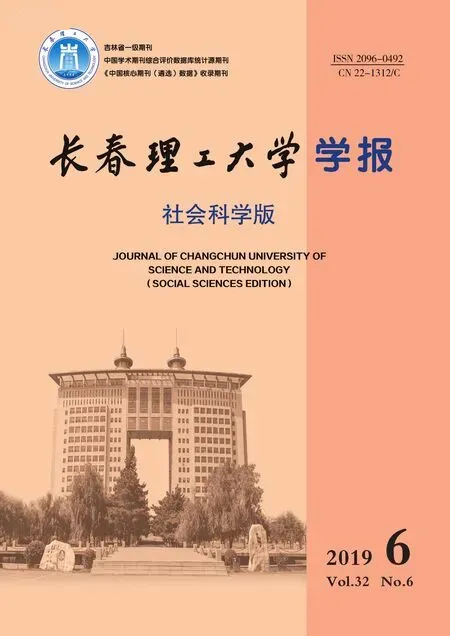钱泰吉《史记》学研究
——以校勘记稿抄本三种为中心
王碧伦,杨洪升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
钱泰吉研究、校勘《史记》三十年,以钱大昕、王念孙、梁玉绳三者研究成果为模板著有专门校勘记。学界对于钱氏撰写三种校勘记的现存孤本未有发现与研究。今笔者以浙江图书馆所藏《钱警石先生<史记>初校本》(以下简称“浙图本”)、上海图书馆所藏《史记校勘记》(以下简称“上图本”)与《闲心静居校书笔记》(以下简称“《校书笔记》”)共三种稿、抄本校勘记为重点考察对象,深入发掘钱氏校勘《史记》在所撰校勘记方面的关系与价值。
一
浙图本不分卷,无行格,共一函五册。每传首页有“某某列传第几”,每页中缝处有“某某传”及叶次。每册首页题下均钤有“唐仁寿读书记”朱文方印,知此本为唐仁寿所藏。首册书衣题名“钱警石先生《史记》初校本”,题下有“祗存四册”四字,右有“子密(钱应溥)检原本,衹存五册,较多一册,余四册与此同”①钱泰吉,浙图藏抄本《史记校勘记》不分卷.十九字。题名笔迹与书内笔迹不类,可证题名者非抄写者。浙图本第五册首页有“甘泉先生《史记校勘记》末册,丁丑夏秋之交洪鲁轩钞赠。唐嘉登子导谨记”②钱泰吉,浙图藏抄本《史记校勘记》不分卷.二十九字可佐证唐仁寿收藏此书时仅为四册,与题下“祗存四册”四字和右侧语相合。
浙图本前四册除唐仁寿藏书印外无任何印记,可知此书并未经他人收藏。从书中内容亦可证之抄写时间,书内校语中多引据王本、柯本、殿本及《四库考证》,而未曾言及中统本。《校<史记>杂识》中载:“辛丑壬寅冬春之交,假拜经楼所藏元中统本欲校未暇……癸卯秋日,重借至学舍。”[1]285辛丑壬寅(1841年与1842年)冬春之际,钱氏首次得见中统本,于癸卯(1843年)秋日方进行校勘。可知1843年秋之前所撰校勘记不包含有关中统本的校记,这与浙图本为1843年春所撰写以及书中不包含中统本校记相合,则抄写时间当在癸卯秋日之后。抄写地点因浙图本缺少关键的第一册而无从得知。
浙图本第五册为洪鲁轩抄赠唐嘉登之册,卷首题下有“讽字室”白文方印。末册首页为上文所引二十九字,下有“子导”朱文方印。唐嘉登为唐仁寿之子。考唐仁寿为1829年生,1876年去世,其间并不含有丁丑年,此丁丑年当为光绪三年(1877年),即唐仁寿去世后一年,洪鲁轩抄写第五册赠予唐嘉登。唐仁寿于光绪二年(1876)下世,所藏之书尽归其子嘉登,此《校勘记》前四册包含在内,而最后一册上有“讽字室”藏书印,为唐嘉登于唐仁寿去世后用其父藏书印钤之。
浙图本第五册为洪子彬(字鲁轩)抄赠唐嘉登之册,时间为唐仁寿去世第二年即1877年,上文已述。洪子彬撰有《鲁轩诗稿》不分卷,集中有《将赴皖垣,作此志别》一诗,后有《壬戌春,皖中重修敬敷书院,李眉生夫子命赋五古一章,即呈湘乡相国、杨仆庵京卿》,前一首题中“皖垣”为安庆别称,由后一首题目可知洪子彬与曾国藩、李眉生曾有交往且于壬戌(1862年)留在安庆,而此时钱泰吉与钱应溥由海宁避难于安庆城中,洪氏是有抄写的可能。《钱泰吉年谱》“(同治)二年癸亥七十三岁”条载:“春,府君步履渐佳,客来谈文,娓娓不倦……桐城方存之茂才宗诚……皆博学多闻,过从尤密。”[1]605方宗诚为洪子彬之师,洪氏曾有“师事方宗诚”印记。方宗诚于钱泰吉去世之年春天与其交往,亦有可能抄到《史记校勘记》,后由洪子彬于1877年传抄,赠予唐嘉登。洪子彬1877年已受李瀚章之知而延入崇文官书局襄校,故洪氏抄赠一事也当在崇文官书局所在地武汉进行。
二
上图本不分卷,黑格白口,四周双边,双鱼尾。首页墨笔题名《史记校勘记》不分卷,下有“王文焘”半朱文半白文方印,“王”字居右为朱文,“文焘”二字居左为白文。后有钱氏跋语与王文焘二跋,钱跋末有单行小字云:“宣统十有五年夏,四月朔录始,至五月五日移录毕。华阳王文焘记于福迎仁。”①钱泰吉,上图藏王文焘抄本《史记校勘记》不分卷.“文焘”二字上钤有“王文焘”半朱文半白文印。次为王文焘跋语,详述抄录与编辑始末,是为王文焘于宣统十五年即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年)五月五日抄成于福迎仁。书中有“石室遗风”、“籀庑”朱文方印,“叔鲁”朱文方印与白文方印各一方,且“恩”字缺末笔避讳。
此校勘记于唐兆榴《可读书斋校书谱》中“五十八岁”条有所记载,其云:“三月手录《史记校勘记》,自正月至五月录至秦本纪。”②钱泰吉,上图藏《甘泉乡人稿》二十四卷余稿二卷年谱一卷附《可读书斋校书谱》一卷.据此可知,此校勘记为钱氏五十八岁即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所撰写,此时距钱氏始校《史记》已近二十年。上图本由书名页等各部分的字迹来看,均为墨笔抄写,且字迹相同或相近,盖为一人所抄。后二跋语落款均为“王文焘识”且下有王文焘印记,可知此三跋为王文焘手跋。由书中除王文焘印记十余种外无他人印记、“恩”字避王文焘父亲王秉恩的讳,可知此书为王文焘抄本。王文焘尾跋语云:“南浔刘翰怡京卿富收藏,且喜假人读阅。藏有学博手缮清本,大人(王秉恩)因荷税假。”③钱泰吉,上图藏王文焘抄本《史记校勘记》不分卷.可知刘承干(号翰怡)藏有钱泰吉手缮清本,《嘉业堂藏书志》载此书,缪荃孙言此书“四卷”,并言:“惜只有《夏》、《殷》、《周》、《秦》四本纪。”[2]此“四卷”对应四本纪而言,然仍较王文焘抄本少《五帝本纪》、《三皇本纪》。《求恕斋日记》中并无此校勘记的相关记录,或为刘承干于宣统二年(1910年)之前得之。王文焘父亲王秉恩从刘氏处借到此本,后由王文焘抄写编辑。
三
上图藏《校书笔记》二卷,无行格。首页“史记”题下钤“警石”方印,除此之外书中无任何印记。每部分题下均署名“嘉兴钱泰吉”,每页中缝有“《校<史记>笔记》卷几”及叶次。每部分正文首行均有“注文脱衍”四字,书中内容也主要以注文的脱衍校记为主。书中遇“复”字缺笔避讳,当是避钱泰吉父亲钱复的讳。书中于书眉与正文旁多修改与增入校语,与原文体例、用语相似,且笔迹一致,当是撰写正文后修改或增入。此书笔迹与上图藏《深庐寤言》几近相同,皆为行书。《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及《中国古籍总目》亦称之为手稿本。综上,此《闲心静居校书笔记》为钱泰吉手稿。
关于书名《校书笔记》,钱泰吉藏书处为“冷斋”,读书处除了“可读书斋”外,还有“闲心居斋”。《甘泉乡人余稿》中有《闲心静居诗》一卷,此诗卷名与校书笔记名均取自“闲心居斋”。由上述考证《校书笔记》为钱氏手稿本,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及《中国古籍总目》仅著录此一种,则此本为孤本可知矣。此校书笔记中对游明本《史记》有所引据。《甘泉乡人余稿》卷一《校<史记>杂识》载:“九月望后,游氏本为蒋寅昉所得,余假至寓斋。”[1]545知钱氏于六十六岁即咸丰六年(1856)九月始从蒋寅昉处借得游明本。《甘泉乡人余稿》卷一《校<史记>杂识》落款为“庚申十二月望,记于借荫居”[1]546,《年谱》“(咸丰)十年庚申七十岁”条载:“二月,杭城初次被陷……乃携家具迁居海盐北乡大兴公墓庐之旁舍。”[1]604知钱氏于咸丰庚申(1860)二月至十二月居住于海盐北乡大兴公墓庐之旁舍,故曰“借荫居”。从此时至同治元年十一月,钱泰吉开始近两年的逃亡生活,已无暇著述,撰写校书笔记时间下限当截止于1860年12月。综上,钱泰吉手稿本《校书笔记》由钱氏自写于1856年9月至1860年12月,撰写地点为海宁官舍或海盐北乡大兴公墓庐之旁舍两地。
四
浙图本为《钱警石<史记>初校本》,上图藏两种分别为《史记校勘记》和《闲心静居校书笔记》。浙图本题名透露出其性质为“初校本”。上图本题名已经直言为“校勘记”,是为成熟校勘记的表现。《校书笔记》则是以笔记形式载有校勘记的内容,看似随笔记录,实则较前二者对校勘学的理解更为深刻。从上文考证的撰写时间上来看,浙图本最先,约为1843年撰写;次为上图本,于1848年成书;末为《校书笔记》,于1856年9月至1860年12月间撰写。撰写时间与题名相结合,始知钱氏撰写顺序和进度。浙图本所据书目《四库考证》、毛氏索隐单刻本、殿本、柯本、王本、阁本、吴校金刻本、汪校宋本,此八种上图本皆有,另较浙图本多中统本等十三种书目。而《校书笔记》在上图本的基础上增游明本等书目,所据书目的逐渐增多亦是钱泰吉随得随校的藏书与校书特点之一。三种书在体例和用语方面也保持着钱泰吉个人的撰写特点:先录异文原文,包括《史记》正文与注文,以括号、空格或“Ο”别之;次列各本异文情况;最后附加按语。对异文情况相同的本子组合进行排列,同时严格遵循正文顶格、下一行注文低一格的格式。钱氏使用符号与空格区分正文与注文的目的在于避免由于自身原因造成正文与注文混淆而形成的二次错误。在文字标记方面,钱氏按语与校语为区别于正文与注文,均用双行小字,在这一点上除浙图本外其他两种校勘记相同。钱氏多以“按”、“案”等方式标注按语,且三种校勘记一以贯之。从体例、用语、所据书目等方面总结三者之间的关系,知浙图本为钱氏初校本,其体例上未能臻于完善,上图本已是成熟的校勘记,对浙图本的瑕疵有所纠正,而《校书笔记》已经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之上,是为对校勘学术的反思,其最大价值在于对注文脱衍情况作单一对象、复杂错误形式的总结,是钱氏对其近三十年《史记》校勘的提炼,对于《史记》注文系统复杂这一问题从校勘学的角度进行阐释,以校勘笔记的形式做学术总结,对传统校勘学术的继承与突破。三者在撰写时间上的顺序亦是钱泰吉个人校勘学术发展的脉络轨迹。
五
三种校勘记均为孤本,其文物价值不言而喻。从文献价值角度考察,三种校勘记各有特点,均保留了钱氏校勘学术不同方面、不同阶段的特色。浙图本保留了钱泰吉初校《史记》时所据书目、校勘记撰写体例等,可以从中看出钱氏在初校阶段对于《四库考证》较为信从且对于校勘记的撰写体例未能臻于完善,正文与注文合写时校语未能用双行小字标识,容易造成与注文的混淆等缺陷,是钱氏校勘学术发展初期的结果。在浙图本的基础上,上图本对前期缺陷进行完善,校语为双行小字,此体例延续到后期《校书笔记》。上图本最大特点为正文与注文分撰校勘记。《校书笔记》的价值在于钱氏对传统校勘学术的突破,在前两种校勘记和近三十年的校勘经验基础之上,对《史记》注文脱衍情况进行归纳,达到了突破校勘学术进而上升到对《史记》各版本整体情况的提纯,是对《史记》版本演进的学术性总结。
清代晚期《史记》校勘工作以张文虎所撰《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以下简称“《札记》”)成就最高,然张氏《札记》与钱氏校勘记三种以及校本存在一定渊源关系,今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首先于校勘工作的准备阶段,《张文虎日记》同治四年(1865)七月初九日载:“缦老出示所校《史记》,商榷开雕格式。”[3]此缦老为周学浚(字缦云),其出示所校《史记》,实是周学浚于安庆会见钱泰吉时,对其校本进行过录,后周氏将过录本带到金陵书局,此事为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跋语》中载:“乌程周缦云侍御学浚借其本过录,择善而从。”①张文虎,国图藏《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五卷.金陵书局本《史记》校勘工作的另一功臣为唐仁寿,此人为钱泰吉门生,曾为钱氏代购明游明本《史记》,对钱氏校勘史记的过程甚为了解。李鸿章将校勘《史记》的工作交予唐仁寿,实是张文虎与唐仁寿共同完成对《史记》的校勘工作,后唐仁寿用周学浚过录钱泰吉校本与己藏《钱警石先生初校本》即浙图本进行整理校勘。从准备阶段来看,首要的参考资料为钱氏校本的过录本与钱氏校勘记的抄本,校勘工作主要的负责人是对钱泰吉校勘过程了解甚详的钱氏门生,可以说金陵书局本《史记》与张文虎《札记》在初始阶段就受到钱氏校勘学的影响。对比张氏《札记》卷首所列十七种校本,除一
“旧校本”外均在钱氏校本之列,仍是以钱氏所用校本为基础展开校勘活动。在具体校勘过程中,仍以钱氏所言为基础而进行进一步阐释,如卷一《索隐序》载:“索隐序。钱氏警石云所见汲古阁单本索隐皆缺此序。案疑毛氏因己见所刊集解本而删之。”②张文虎,国图藏《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五卷.张氏《札记》引用书目中有钱氏未曾参考的资料,如清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明程一枝《史诠》等,且张氏《札记》较钱氏校勘记更进一步发展,其于案语中总结错误类型。但张氏《札记》仍有体例形式上较钱氏欠缺之处,王文焘于钱氏《史记校勘记》卷后跋语言尽其弊:“爰取张啸山刊《史记札记》,校出乃知张氏所记点因学博校本而始,《札记》中‘警石云’者即学博校记……《札记》亦不尽同学博所校,且体例亦不如学博缮本之详。张校正文、集解、索隐、正义,联毋而书,俱作大字点,未注明以何本为主,集解、索隐、正义既不提行,空格点不另加识别……”③钱泰吉,上图藏王文焘抄本《史记校勘记》不分卷.如王氏所言,张氏《札记》较钱氏校勘记欠缺之处俱为体例上的弊端。综上,张氏《札记》在形式上仍以钱氏汇校方式为主,间以其他参考资料辅之,并在校勘记形式上与钱氏相类似,皆保留大量异文,但所引他书资料较钱氏更为丰富。虽张氏《札记》体例缺陷较为明显,但实为张氏《札记》在钱氏校勘记的基础之上,充分吸收钱氏校勘优点,弥补不足之处,获得的长足发展与进步。另,今中华书局本《史记》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实是钱泰吉以三种校勘记为核心的校勘学术的血脉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