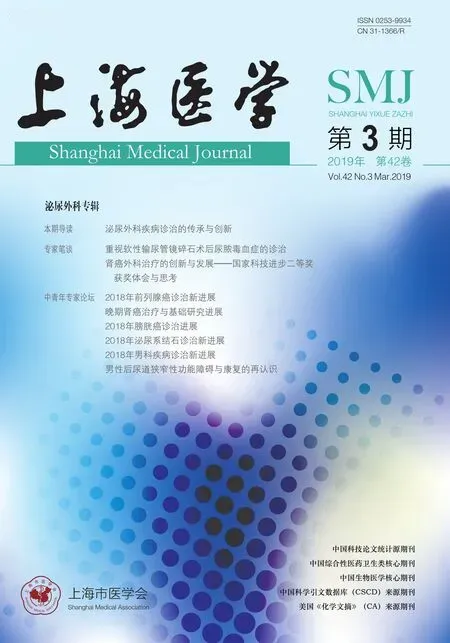晚期肾癌治疗与基础研究进展
徐 可 周启东
回望2018年的肾癌治疗领域,以原发灶减瘤性肾切除术(CN)联合舒尼替尼治疗作为转移性肾细胞癌(mRCC)的主要治疗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多项mRCC相关的Ⅲ期临床试验结果公布,其中CARMENA研究结果证实晚期肾癌行CN前谨慎选择患者的重要性。此外,3项随机Ⅲ期临床试验结果表明了在未经治疗的mRCC患者中,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为主的联合治疗方式较单用舒尼替尼治疗更具优越性,晚期肾癌逐步进入免疫联合治疗的时代。在此,笔者对2018年晚期肾癌治疗与基础研究的最新进展做一盘点。
1 mRCC行CN治疗必要性的争论
新诊断mRCC患者行CN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末,一项在mRCC患者中比较CN+IFN与单纯IFN疗效的研究结果表明,CN+IFN治疗可使患者的总生存期(OS)受益。这些数据和许多靶向治疗时代的回顾性研究结果,为CN在mRCC中的广泛应用提供了基础依据。在过去的10年中,CN成为mRCC患者接受靶向药物治疗前常用的治疗手段[1]。然而,目前尚缺乏针对CN的前瞻性研究数据。
2018年6月CARMENA研究结果于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公布,该试验是一项明确mRCC患者CN治疗价值的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Ⅲ期非劣效性研究。研究将450例初次治疗的mRCC患者随机分为CN联合舒尼替尼靶向治疗组(CN联合舒尼替尼组,226例)和单用舒尼替尼靶向治疗组(舒尼替尼组,224例),主要研究终点为OS,次要研究终点包括客观有效率(ORR)和无进展生存期(PFS)等[2];两组中位随访时间为50.9个月,舒尼替尼组的中位OS为18.4个月,CN联合舒尼替尼组的中位OS为13.9个月。研究达到了其主要研究终点,即舒尼替尼治疗组的OS不劣于CN联合舒尼替尼治疗组。该研究颠覆了以往关于CN在mRCC治疗中的地位,与单用舒尼替尼靶向治疗相比,CN联合舒尼替尼靶向治疗的OS、中位PFS、ORR均无优势;因此,CN的治疗价值受到质疑,不再作为初诊mRCC的标准治疗方法。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该研究的临床适用性受限。在CARMENA研究纳入的患者中,纪念Sloan-Kattering癌症中心(MSKCC)预后不良患者所占比例很高,这些患者大多转移灶偏大,属于瘤负荷较高人群,不是目前CN的主要适用人群,因此可能很难从CN中获益;并且研究中MSKCC预后中等的患者未达到非劣效检验标准,同时缺乏对MSKCC预后良好患者的分析资料;此外,在450例患者中,接受完整的CN联合舒尼替尼靶向治疗的患者176例,单用舒尼替尼靶向治疗的患者206例。各组接受原计划治疗方案的患者数量相对较少,限制了非劣效性研究的有效性。
考虑到上述局限性,CN在合适的mRCC患者中仍发挥着作用。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应强调患者选择的重要性。对于预后良好或中等的mRCC患者,如果肾外肿瘤负荷较低,仍有可能受益于CN;预后不良或肾外肿瘤负荷较高的患者应放弃CN。作为一项非劣效研究,CARMENA研究结果尚未得出单用舒尼替尼靶向治疗的疗效优于CN联合舒尼替尼靶向治疗的结论。换言之,对于mRCC患者,无论在舒尼替尼治疗前是否行CN,都是可以接受的。该研究需要更多的循证医学证据来增强其说服力,进而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2 晚期肾癌开启免疫联合治疗的新时代
自2006年以来,陆续有11种靶向和免疫药物获得批准上市,肾癌的系统治疗也由此得以迅猛发展。这些药物大致可分为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靶向剂、雷帕霉素(mTOR)途径抑制剂或ICI[3],并且以单药应用为主。
2018年初Checkmate 214研究[4]公布了多个早期临床试验的数据。Checkmate 214研究是一项随机Ⅲ期临床试验,比较了纳武单抗[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抗体]+伊匹单抗[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抗体]联合用药(NIVO-IPI)与单用舒尼替尼治疗的疗效。该研究将1 096例未经治疗的mRCC患者随机分为NIVO-IPI组(550例)和舒尼替尼组(546例);在中危和高危患者中,NIVO-IPI改善了ORR(42%比27%)、完全缓解率(CRR,9%比1%)和OS(HR=0.63,P<0.001),但未达到预计改善PFS的效果(NIVO-IPI组为11.6个月,舒尼替尼组为8.4个月;HR=0.82,P=0.03)。重要的是,NIVO-IPI治疗可改善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表达水平高(肿瘤细胞中PD-L1表达水平≥1%)和表达水平低(肿瘤细胞中PD-L1表达水平<1%)的患者的OS。因此,无论PD-L1状态如何,对于新诊断为中危或高危的mRCC患者,均应考虑采用NIVO-IPI治疗。对于低危mRCC患者,NIVO-IPI组ORR(29%)和CRR(6%)均低于舒尼替尼组(52%和11%)。目前,PD-1单抗联合CTLA-4单抗已被美国FDA批准作为晚期肾癌中高危患者的一线用药。2018年欧洲泌尿外科学会(EAU)指南按国际mRCC联合数据库(IMDC)评估结果将mRCC患者分为低危组和中高危组,低危组推荐一线治疗药物为舒尼替尼或帕唑帕尼,中高危组为NIVO-IPI。修改后的mRCC一、二线治疗流程图清晰明了,也凸显了免疫治疗在肾癌治疗中的重要地位。
抗血管靶向药物(如贝伐珠单抗、阿西替尼等)作为目前晚期肾癌的一线治疗药物,其联合PD-1/PD-L1抑制剂的多项大型临床研究近年来陆续开展,2018年公布了两项PD-L1抑制剂联合抗血管靶向药物治疗的大型随机对照研究,分别为IMmotion151和JAVELIN Renal101研究,均获得阳性临床研究结果。
随机Ⅲ期临床试验IMmotion151(NCT02420821)比较了采用atezolizumab(PD-1抗体)联合贝伐珠单抗(VEGF靶向抗体)治疗(Atezo-Bev组)与单用舒尼替尼治疗(舒尼替尼组)PD-L1表达阳性的患者的疗效[5]。在2018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泌尿肿瘤研讨会(ASCO-GU)上报告了来自IMmotion151的初步研究结果,Atezo-Bev组的PFS为11.2个月,显著长于舒尼替尼组的7.7个月(HR=0.74,P=0.02);两组ORR分别为43%和35%,OS数据尚未完全。而意向治疗(ITT)人群(指临床试验中所有满足入组标准,入组后至少服用1次研究药物,且有用药后评价资料的患者)Atezo-Bev组和舒尼替尼组PFS分别为11.2和8.4个月(HR=0.83),ORR分别为37%和33%。不良事件方面,Atezo-Bev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舒尼替尼组,但Atezo-Bev组有近16%的患者需应用糖皮质激素治疗。
随机Ⅲ期试验JAVELIN Renal101(NCT02493751)比较了avelumab(抗PD-L1抗体)联合阿西替尼[VEGF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VEGFR-TKI)]治疗与单用舒尼替尼治疗的疗效。该研究的主要终点是PD-L1表达阳性与ITT患者的PFS和OS,试验数据于2018年初步提交。在PD-L1表达阳性患者中,avelumab联合阿西替尼组的中位PFS为13.8个月,显著长于单用舒尼替尼组的7.2个月(HR=0.61,P<0.000 1);总体人群(ITT患者)中接受联合治疗者的中位PFS(13.8个月)显著长于单用舒尼替尼治疗者(8.4个月,HR=0.69,P=0.000 1);avelumab+阿西替尼组和舒尼替尼组的CRR分别为3%和2%;OS数据尚不完全;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接近。结果表明,该联合治疗方式对于初诊未治的mRCC患者具有很大潜力。在另一项Ⅰb期临床试验中,52例未经治疗的mRCC患者接受了阿西替尼联合派姆单抗(PD-1抗体)治疗[6],队列中IMDC评估为低危患者24例(46%)、中危患者23例(44%)、高危患者3例(6%)和未知风险患者2例(4%),治疗后达到客观缓解38例(73%)、完全缓解4例(8%),中位PFS为20.9个月。
ICI治疗目前被认为是肿瘤治疗史上的里程碑,免疫治疗和免疫联合靶向治疗是未来发展的趋势。然而免疫治疗仍存在诸多问题,如药物费用昂贵、患者应答率低、脱靶效应、肿瘤抗原靶点表达差异等。有价值的生物标志物尚未确定,患者的治疗方案选择仍是难题,肿瘤的分子相关性和基因图谱可能有助于mRCC的治疗选择。由于药物对不同人群、种族间的疗效和不良反应均存在显著差异,国内学者应努力探索适合国人的免疫联合靶向治疗方案,开发中国原创肾癌免疫和靶向药物是重要的研究方向。
3 肾癌基础研究的新进展
肾透明细胞癌(ccRCC)是肾癌中最常见的病理类型,约90%的ccRCC患者的von Hippel-Lindau(VHL)基因失活。VHL的经典靶标是缺氧诱导因子(HIF)的α亚基。HIFα在ccRCC发育早期成为稳定因子,诱导并促进血管生成和细胞内代谢重编程的转录活动发生。探索HIFα以外的能够避免降解过程且促肿瘤发生的VHL底物,为发现ccRCC新疗法提供了潜在可能性。Zhang等[7]研究发现一种新的VHL靶标ZHX2(zinc fingers and homeoboxes 2),其调节NF-κB信号通路促进ccRCC发生,或能成为治疗ccRCC的新靶标,相关的研究成果发表于2018年7月Science杂志上。在VHL缺陷型肾癌中,ZHX2和HIFα转录因子逃脱了被降解的命运。这些因子在细胞内累积,与特定的DNA序列结合,促进肿瘤生长相关基因的激活。而p300和环磷腺苷效应元件结合蛋白(CREB)是转录共激活因子。在肝细胞癌和霍奇金淋巴瘤中,ZHX2是一种肿瘤抑制因子,其机制是转录抑制细胞周期蛋白A和E的表达。这与其在ccRCC中的作用形成对比,在ccRCC中ZHX2通过其在NF-κB靶基因表达中的积极作用来促进肿瘤发生。未来的研究方向将是研究ZHX2在各种肿瘤中的表达及其功能。这些研究强调了在确定某种特定分子是否具有致癌或肿瘤抑制作用时谱系特异性的重要性。
2018年的最新研究发现,最早期的关键遗传改变可能会诱发肾脏肿瘤。桑格研究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发现,首个关键的遗传改变常发生在儿童期和青春期,之后细胞会遵循一种持续性的通路在40或50年后逐渐缓慢进展为肾癌,相关的两篇研究结果发表于2018年4月的Cell杂志[8-9]。通过对33例患者的95个肾脏肿瘤样本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分析,发现患者体内肾癌发生早期所出现的首个遗传改变能够驱动突变的产生。患者体内起初只有几百个细胞发生遗传改变,并且很可能大多数人的肾脏中会有这种所谓的“流氓细胞”存在,随后肾癌开始出现在1%~2%的人群中,这些癌变细胞甚至会在长达40~50年的时间里保持休眠状态,除非个体机体发生进一步突变,否则其不会进展成为肾癌。然而,有些风险因子会促进这些细胞进展成为肾癌细胞,如吸烟、肥胖和肾癌遗传性风险等。在患者被诊断为肾癌之前,能够表征肾癌的标志性基因组事件平均会在40~50年内发生,而首批的肾癌“种子”会在个体的儿童和青少年时期进行播种,了解这些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和时机对于后期研究人员进行肾癌预防和干预至关重要。在超过90%的肾癌患者体内发现了染色体3p的缺失,其常常会携带多个肿瘤抑制基因;此外,35%~40%的患者在该过程中会同时获得染色体5q,即染色体碎裂,这一过程可诱发基因发生突变。因此,通过更深入的研究或许可以帮助指导患者在合适的时间进行有效的治疗。
总之,在过去1年,肾癌的治疗方法与基础研究均有全新的进展。一方面,CN的必要性受到质疑,免疫治疗、免疫联合靶向治疗的疗效得到肯定,原有的CN联合舒尼替尼的治疗方式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基础研究发现了与肾癌发生密切相关的VHL基因新靶标。然而,在治疗手段和基础研究方面均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展望2019年,期待更多的学者对2018年取得的成果进行更深入的探索,提出更多崭新的观点,来帮助临床医师认识肾癌、对抗肾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