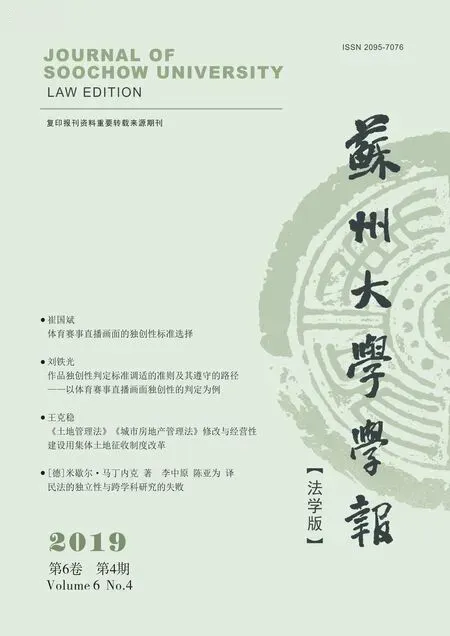敲诈勒索罪中“被害人恐惧必要说”之证伪及其出路
蔡桂生
一、问题的提出
依照我国法律界主流观点,要成立敲诈勒索罪,被害人必须产生了恐惧心理,被告人取得财物则必须建立于此种恐惧心理之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中便以立法部门意见的方式说明,敲诈勒索行为,“是通过对公私财物所有人、保管人实行精神上的强制,使其产生恐惧、畏惧心理(粗体为引者所加,以下几处同),不得已而交出财物”。(1)郎胜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91页。基于该书的影响力,成立敲诈勒索罪需要“恐惧心理”的观点,在我国理论、实务界得到广泛传播,并非难事。在刑法理论上,依张明楷教授的表述,“敲诈勒索罪(既遂)的基本结构是 :对他人实行威胁——对方产生恐惧心理——对方基于恐惧心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如果胁迫行为没有使对方产生恐惧心理,对方基于怜悯心或者其他原因交付财产给行为人的,则只构成敲诈勒索罪的未遂。”(2)张明楷 :《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5-1017页。有鉴于此,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便成为了满足敲诈勒索罪构成要件所必需的不成文要素之一,从而形成了学界多数说(本文将之称为“被害人恐惧必要说”)。该种观点在实务界也很有市场。有人写道 :“敲诈勒索罪的完成形态属于结果犯,即行为人使用了恐吓、威胁等手段,使被害人产生了恐惧感,从而被迫交出财物的,即为既遂;如果未因被告人的行为而产生恐惧或虽有恐惧感,但未交出财物的,均为敲诈勒索的未遂。”(3)韩忠伟 :《关于敲诈勒索罪几个问题的探讨》,载《检察实践》2001年第5期。此外,柏浪涛博士、谷翔先生对“被害人恐惧必要说”的阐述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他们看来,之所以需要恐惧心理,是为了将恐吓行为和生活中的谈条件行为区分开来 :“敲诈勒索往往表现为谈条件的方式,行为人通告被害人 :如果不满足我的要求,我就要实现恶害。而生活中也有许多谈条件的情形,例如甲对乙说 :‘你不请我吃饭,我就将你逃课的事告诉班主任。’这两种行为的区分在于 :生活中的谈条件行为只是单纯的讨价还价,出价方不会以恶害为筹码,还价方也不会产生恐惧心理。而恐吓行为中,出价方是以实现恶害为筹码,还价方会产生恐惧心理。而还价方会不会产生恐惧心理,主要是看出价方的恶害内容是否会威胁还价方的重大利益,例如生命、身体、自由、名誉及财产等。例如,甲乙捡到王某的身份证后,给王某打电话,索要300元,并称若不付钱就不还身份证。该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因为这种行为不会让人产生恐惧心理,属于生活中的谈条件行为。”(4)柏浪涛、谷翔 :《敲诈勒索与行使权利的界限》,载《法律适用》2010年第10期。由此可见,我国理论与实务界对于敲诈勒索罪的理解,几乎没有例外地采用“被害人恐惧必要说”。
然而,众口一词不意味着理论上就没有疑问。虽然1949年以来的刑法草案中,确有规定过“恐惧”作为敲诈勒索(或恐吓)入罪要素的做法,如1950年7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第144条(恐吓)即规定,“以威胁方法使人恐惧而取得他人财物者,为恐吓,处四年以下监禁”。但是,现行《刑法》法条之表述并未以“被害人恐惧”为必要。《刑法》第274条如此规定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条文只规定了“敲诈勒索”之行为及其次数、“敲诈勒索”之对象“公私财物”及其数额。同时,在作为我国财产罪立法参考资料的苏联刑法条文和理论中,也未要求成立勒索罪必须造成被害人恐惧。(5)1960年《苏俄刑法典》乃是总结苏联20世纪50年代立法经验之产物,其第148条(勒索)规定 :对受害人或他的亲近人等,以使用暴力、宣扬侮辱他们的消息或毁灭他们的财产相威胁,要求转移个人财产或财产权,或为某种财产性质的行为(勒索)的,处三年以下的剥夺自由,或一年以下的劳动改造。第95条(勒索国家财产或公共财产)亦未见被害人恐惧字样。参见萧榕主编 :《世界著名法典选编·刑法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847、852页。苏联刑法分则之理论,见苏联司法部全苏联法律科学研究所编 :《苏维埃刑法分则》,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译,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280-282页。有鉴于此,“被害人恐惧”是否确属敲诈勒索罪成立之必要,就仍有可斟酌的空间。
二、“被害人恐惧必要说”之证伪
敲诈勒索行为是利用造成对方的精神强制以获得财产利益。精神强制不一定带来恐惧,但恐惧却必定来源于某种精神强制。比如,对某人施加一种精神强制,胆量大的或者镇静的人虽然不会丧失情绪控制,但会感知到他必须怎样做,才能避免不利后果,此时是一种功利衡量;而胆量小的或者不太镇静的人,则有可能丧失对自己的情绪的控制,此时他虽然也是顺从对方行事,但却会感到恐惧。我国有学者认为 :“恐惧当然会致使精神上受强制状态,但其绝不是被害人精神受强制的唯一可能的原因。尴尬、着急、羞愧、无奈、困惑等心理状态,同样可能导致被害人的精神受到强制。”(6)邹兵建 :《交通碰瓷行为之定性研究》,载陈兴良主编 :《刑事法判解》,第12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页,注释6。该观点正确地注意到了精神强制反映在心理上的多样性,但未注意到,应是精神强制同时引发心理上的多种反应,而非先有多种心理,后导致精神强制。关乎刑法上定性的是精神强制,而非恐惧。例如,被告人为图牟利,挑取他人修建较为豪华的坟墓,从墓中挖取骨灰盒,并将这些骨灰盒分别藏匿,后依墓碑所刻死者姓名,打电话给死者的家属,称如果不支付相应的钱款(约一万元不等),就不告知挖出来的骨灰盒在哪儿。有的被害人付了钱,也有的不付。(7)案情改编自 :《男子盗骨灰盒敲诈陵园未遂获刑一年》,载《方圆》2018年第8期。在这种案件中,被告人盗窃骨灰的行为,无疑符合《刑法》第302条的规定。依据我国家庭伦理观念,该案被害人也会产生精神强制,问题是 :该案利用精神强制索取钱款的行为如何定性?由于有的被害人在恐惧或无奈之下支付了钱款,那么,此种情形宜认定为敲诈勒索罪,而未取得钱财的情形,则应认定未遂。至于被害人会否发生恐惧的心理反应,则并非刑法所关注的内容。(8)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丧葬习俗和家庭伦理不同,被告人若采取盗取尸体的方式进行勒索,则未必能构成敲诈勒索罪。从被害人的角度而言,如果被害人感到了恐惧,那便可以推出,他遭遇了他无法掌控的事件。这种无法掌控,可谓是一种不确定性,亦即被告人的行为确实给这个被害人造成了一种危险的局面。但是,在被告人采取相应举止之时,他是无从知道被害人会不会感到恐惧的(因为这事还没有发生),他只能预计到自己的举止可能具备给对方带来恐惧的性质。对于财产受到损失而言,被害人恐不恐惧其实只是失去财产的可能诱因之一。被告人在采取相应手段时,决定性的是如何获得被害人的财产这个中心问题。至于被害人恐不恐惧,被告人事先并无法确切地认知。被害人会有多大程度的恐惧情绪,对被告人而言,只是一种难以精确计算的偶然事件。
鉴于这样的思考,本文认为,“被害人恐惧必要说”难以成立,换言之,“被害人是否确实产生恐惧并被迫交付财物,不影响本罪的构成”(9)高铭暄、马克昌主编 :《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16页。。具体理由如下 :
第一,“被害人恐惧必要说”无助于归纳社会生活现象。在现实案件中,人们面对他人的威胁时,经常并不是只有单一的心理。被害人有可能产生间歇性的恐惧,有可能生发怜悯,有可能产生困惑,还有可能陷入急躁以希望赶紧摆脱困境。时有发生的情况是,“遭遇一样,身体感受相同,一个人体验到了恐惧,而另一个人体验到的可能是愤怒”;“同一个对象,对它的理解不同,所激发的相应情绪也会迥异。如果……认为它危险,就会感到恐惧;如果……认为它可恼,就会感觉愤怒”。(10)[挪威]史文德森 :《恐惧的哲学》,范晶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第30-31页。如果按照“恐惧心理必要说”的话,被害人在面对被告人行为时的不同的心理,将给被告人带来不同的法律后果,这会导致结论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当被害人同时产生多种心理,或者说具备这些若干种心理组成的混合心态时,被告人应当承担既遂还是未遂的责任,就更难确定。已经有观点指出,“胁迫通常会使得相对人陷于恐惧,但并不局限于此,胁迫行为使得相对人陷于尴尬、着急、羞愧、无奈、困惑等,只要这种心理达到一定程度,同样可被认为属于心理上受强制的状态,应评价为敲诈勒索的行为。”(11)邹兵建 :《交通碰瓷行为之定性研究》,载陈兴良主编 :《刑事法判解》,第12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页。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以被害人恐惧心理作为判断的标准,会容易在下述案件中出现疑难 :被告人曹致春、戴海斌伙同程正(另案处理)经预谋,程正事先将右手拇指砸成粉碎性骨折,于2007 年 4月17日上午,到本市丰台区分钟寺道口附近,程正骑自行车故意碰撞被害人刘恒臣驾驶的帕萨特轿车,并引发与刘恒臣争执后,以右手指受伤为由向刘恒臣索要人民币22 000 元。采用这种方法,曹致春等人一共成功作案六起,并于第七次作案时被警察抓获。法院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12)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07)石刑初字第563号刑事判决书。在该案中,被告人其实是利用虚假的交通事故,骗取被害人的钱财,应该成立诈骗罪,而非敲诈勒索罪。被害人在面对被告人受损伤的手指,有可能会产生对“流血事件”的恐惧,再加上被告人如果索要钱财时口气偏重,便容易认定为敲诈勒索罪。但这样的结论,是建立在对被害人心理的主观把握之上的,具有不确定性,没有注意到,只有先认定强迫行为,才有可能成立敲诈勒索罪。正如我国学者指出的,在本案中认定敲诈勒索罪,是“胁迫行为这一行为要素虚化”(13)邹兵建 :《交通碰瓷行为之定性研究》,载陈兴良主编 :《刑事法判解》,第12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页。的体现。
第二,“被害人恐惧必要说”也不符合敲诈勒索罪这一刑法规范的保护目的。敲诈勒索罪条款的主要保护目的,在于保护财产免受侵犯。只有造成了财产损失,才意味着规范的主要保护目的落空。至于心理上的安全,只是敲诈勒索罪这一条款在保护财产时,可能附带予以保护的某个方面而已,也就是说,该条款是否保护这种心理上的安全并不确定。
第三,“被害人恐惧必要说”因标准不明,难以实际贯彻到底,最后只能再次诉诸被告人的行为来作为适格的判断标准。该说论者就写道 :“还价方(敲诈勒索案被害人——引者注)会不会产生恐惧心理,主要是看出价方(敲诈勒索案被告人——引者注)的恶害内容是否会威胁还价方的重大利益,例如生命、身体、自由、名誉及财产等”。(14)柏浪涛、谷翔 :《敲诈勒索与行使权利的界限》,载《法律适用》2010年第10期。叶良芳博士也在提到敲诈勒索罪的基本结构为恐吓行为——对方畏惧——交付财物——转移财物之后,重新指出 :“行为人所告知的恶害,只要根据社会相当性足以使人产生畏惧即可,至于恶害是否会即刻来临……行为人是否真的会付诸实现、被害人是否事实上产生恐惧,则在所不问。”叶良芳 :《权利行使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年第3期。这在事实上放弃了以恐惧心理作为敲诈勒索行为的认定标准,而是重新诉诸被告人的敲诈勒索行为本身。而且,论者认为的恐惧心理有助于区别恐吓行为和谈条件的行为,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实践中给对方造成恐惧的谈条件行为,比比皆是,但若将这些行为也认定为敲诈勒索中的强迫,并不合适。
第四,“被害人恐惧必要说”不符合刑法条文以被告人作为标准的对话者或者默认的对话者的表述模式。刑法条文中的举止规范的内容,是要求被告人不要去做违反举止规范的事情。只有刑法上的举止规范,才决定被告人是否构成刑法上的不法,并进而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被害人的恐惧心理是必要的构成要件要素,那么,决定被告人在刑法上是否应负责任以及负多大责任的,将不再只取决于其是否违反了刑法上的规范,而是还要取决于被害人在被告人作出威胁行为之后所表现出的临场胆量大小。这将使得法院沦为评定公民胆量的机构,而不再是考察被告人之行为是否违反刑法规范的司法机关。而且,具体案件之被害人“会否产生恐惧”,并不确定 :“一般来说,对于对恐惧感是否存在的评价,必须考虑被害人的具体情况,从一般社会观念出发作出分析。某种恐吓可能不会使一些人产生恐惧感,但是对一些特殊人群(例如,未成年人、年老体弱者、残疾人、女性等)可能会产生威胁效果,所以,以某种方法不会使多数人陷入恐惧而否定被害人实际遭受的精神压制,就显得不太合理。”(15)周光权 :《刑法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3页。这是通过列举法,针对年老体弱者、女性、残疾人、未成年人这样的胆量较小人群,给予刑法上的特别保护。可是,此种列举法的问题在于 :首先,此种列举是不穷尽的,它经不起追问,因为不只是这些人群,而是任何人都会有缺乏胆量的特定事项。反过来,这些列举出的特别受保护群体,也可能会在某些事项上比普通成年人更有胆量,比如,少年人在一些游戏项目上。而且,在这些特别受保护群体的内部,也是情况各异。所以,即使引入年龄、女性、残疾人等,以作为判断特别受保护人群的范围的标准,也不意味着被列入这一范围的人,就都会产生恐惧。其次,此种列举法,只是心理学的标准,而非规范的标准(法学标准),它没有提出一般性的规则。被告人才是刑法条文的默认对话者和适格对话者,除非通过一个一般性规则将被害人所遭受的威胁、要挟的效果,也合理地纳入被告人的敲诈勒索行为之中,(16)被告人在对被害人实施勒索行为之时,只要他事先略有准备,自然也会根据其对被害人的了解和判断,根据不同被害人的不同精神弱点,因人而异地采取他认为可能“有效”的不同的犯罪手段和信息表述。“预估”的基础,是被告人对案件中具体被害人的事先判断,尽管他在多数情况下,只会按照他习惯的方式对被害人的可能反应加以预算。换言之,人们在被告人所采取的胁迫行为之中,也可以发现“预估”的被害人举止的某种“存在”。这种“预估”的举止,借助被告人这一“中介”,也间接地成为了刑法关注的对象。从而使得被告人是否成立犯罪,只取决于其举止是否违反了刑法上的规范,而不是同时取决于刑法上规范和被害人心理素质这样的“双重标准”。这才符合刑法上罪责自负的原则。
第五,“被害人恐惧必要说”难以说明被勒索者是法人的情况。法人的正常决策会受到被告人的影响,但法人本身却并不会像具体的自然人那样产生心理上的恐惧,因为恐惧乃是一种自然人才会有的情绪。以情绪作为构成要件的要素,缺乏应有的确定性。
第六,“被害人恐惧必要说”难以说明犯罪未遂的情形。在钓鱼侦查的场合,行为人实施敲诈勒索行为之时,由于警方监控的存在,被害方实际上根本就不会产生什么恐惧心理,这也根本不妨碍行为人敲诈勒索行为的认定,只是因为缺乏犯罪结果,犯罪仅仅处于未遂阶段而已。所以,决定被告人行为之性质的,只能从被告人一方事前都掌握了什么信息来看,而不能从被害人的事后反应来倒推。
综上所述,“被害人恐惧必要说”疑点众多,难以充当敲诈勒索罪的入罪条件。
三、出路 :以“意思形成自由受到强迫”替代“被害人恐惧”
我国刑法学中之所以流行“被害人恐惧必要说”,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因为对敲诈勒索罪的保护法益缺乏仔细分析。以下笔者便结合法益的一般理论,对敲诈勒索罪所保护的特定法益加以论述。
(一)敲诈勒索罪的附属法益 :意思形成自由
在犯罪客体的复杂客体学说中,存在所谓次要客体。但在法益理论中,与之对应的内容似乎没得到系统性的论述,或者说没有相应的位置。如果对法益理论把握得更全面一些,可以发现,在法益理论中,也有所谓附属法益(17)以诈骗罪法益为例的论述,参见LK-Tiedemann, 1999, Vor § 263, Rn. 21.或次要法益的概念。其中,“附属法益”这一表述,较之于“次要法益”,更为准确,因为在法规范得到落实贯彻的情况下,有的法规范可能带来好几种利益,有时这些利益还属于不同层次的利益,此时只使用次要法益,就显得有些局限,具体而言 :第一,如果囿于主次二分之见,那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似乎除了主要法益之外,只有一种或一些次要法益。第二,用次要法益这一表述,也难以指称那些比次要法益还“更为次级的法益”的情况。像在绑架罪案件中,被绑架人的人身权益、被勒索者的意思自由和财产利益,都是需要保护的利益,而被勒索者的意思自由,就属于比次要利益“财产”更次的利益,故使用“附属法益”,显得更为简明。
鉴于这种理解,可以认为,在抢劫罪条款上,人身权利算是抢劫罪条款得以贯彻时附带得到保护的利益,属于附属法益。和抢劫罪相对应,在敲诈勒索罪中,强迫手段所危及的那些人身权利和其他权利,也应算作附属法益。敲诈勒索罪这一刑法规范的保护目的,是为了保护财产不受到特定方式的侵害。(18)类似见解,参见向朝阳、周力娜 :《对敲诈勒索罪客体的再认识》,载《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2期。这个特定方式,就体现在被告人所采用的手段之中;同时,这个特定方式也意味着,如果被害人的财产不是因为被告人的行为,而是由于风雨雷电之类的自然事件而灭失,则不受敲诈勒索罪这一刑法规范的保护。被害人的人身利益或其他利益是敲诈勒索手段所针对的内容,通过禁用这些手段取得他人财产,也就顺带保护了这些手段所可能涉及的人身权益或其他权益(附属法益)。(19)此亦犯罪客体理论中以“次要客体”的方式所保护的内容。参见赵秉志主编 :《侵犯财产罪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436页。
为何要保护这些权益呢?之所以人们的基本利益或权利应当受到保护,主要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创设出一定的自由空间,从而维持人们的基本生活条件。那么,在敲诈勒索罪中,危及人身权益或其他权益的胁迫手段,意味着对什么自由提出了威胁?究其实质,是公民转移财产的意思之形成不受他人强迫的自由(意思形成的自由)。(20)类似观点,参见林东茂 :《刑法综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页(“意思决定自由受到扭曲”)。德国刑法学中有“意思决定自由”(Willensentschlieβung)和“意思活动自由”(Willensbetaetigung)的用法。例如,“暴力”被理解为“通过使用力量和其他在强度和作用方式上能够侵害他人自由的意思决定或者意思活动的物理效用,而实现的有形的强迫”(粗体为引者所加)。Vgl. Kindhaeuser, 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 II, 2008, § 17, Rn. 4. 但笔者以为,在该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有自己的理解。较之于“意思决定自由”和“意思活动自由”,“意思形成自由”和“意思实现自由”之用词更为准确,因为意思“决定”是瞬间的或一时的事情,而意思“形成”则有一个过程,在意思形成的整个过程中,皆不应受到强迫。至于意思“实现”自由,其较之于意思“活动”自由的优点在于 :第一,意思“实现”自由,更能体现意思在现实世界中的展开,更能和现实对接;第二,使用“意思活动自由”易使人误解为人脑中意思“思维活动”的自由,而意思“实现”自由可以避免这一误会。意思形成自由并不等于免于恐惧的自由。如果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就推导出被害人权益受损,从而进入定罪过程,那就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对于被告人的基本权利而言,这种做法也具有相当的侵犯性。在敲诈勒索罪中,意思形成自由是附带地被加以保护的。在我国刑法中,并无特定的独立罪名对这种意思形成自由予以专门的保护,(21)我国《刑法》与此有关之罪名中,第226条强迫交易罪侵害的客体(法益)是市场交易秩序(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 :《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49页),也有认为该条款同时侵犯了市场经济活动的正常秩序和他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 :《中国刑法解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3页),第236条第1条强奸罪侵害的也是女性的性自由权(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 :《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63页),这是一种依附于性承诺的意思自由,而不是独立的意思形成不受胁迫的自由。而强迫劳动罪所针对的是劳动者的休息权、健康权和人身自由权利(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 :《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75页)。这使得人们无法认为,这属于刑法上独立的法益。倘使我国刑法要使意思形成自由这种附属法益得到专门的保护,则应通过单独创设相应的强制罪或胁迫罪条款,或者至少像俄罗斯刑法中的勒索罪(22)2003年修订的《俄罗斯刑法典》第163条(勒索)规定 :“以使用暴力或以毁灭或损坏他人财产相威胁,以及以散布侮辱被害人或其亲属的材料或散布可能使被害人或其亲属的权利或合法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其他材料相威胁,要求交付其财产或财产权或实施财产性质的其他行为的,处3年以下的限制自由;或处6个月以下的拘役;或处4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处或不并处数额为8万卢布以下或被判刑人6个月以下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参见《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黄道秀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那样,不将财产损害作为认定敲诈勒索罪的必要条件。
基于以上考虑,在我国刑法学中,应当将转移财产时的“意思形成自由不受强迫”视作敲诈勒索罪的附属法益(而非主要法益)。被告人敲诈勒索行为所侵犯的,便是该附属法益。至于“被害人恐惧”只是“意思形成自由”受到强迫时的一种特定心理状态而已。在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区分上,前者的附属法益是保护意思形成自由免受强迫,而后者则是以侵犯人身权利为手段,这意味着“取消”了受害人的意思形成自由。可见,二者在犯罪手段上存在区别 :前者没有达到压制被害人为保卫财产可能进行反抗的程度,而后者具有针对被害人保卫财产之可能反抗的压制性。
(二)附属法益和犯罪既未遂问题
一般认为,法益侵害的出现意味着犯罪的既遂。那么,在法益有非附属法益(或主要法益)与附属法益之分的前提条件下,侵犯哪一法益可以认定犯罪的既遂,就成为了需要作答的问题。有人在针对《刑法》第244条强迫劳动罪进行分析后提出,该条的保护法益不应是意思活动自由,而应该是作为意思活动自由之基础的、被害人有关是否劳动的意思决定自由。该条是实害犯罪,被害人的意思决定自由一旦受到侵害,即可认定犯罪既遂。(23)参见曾文科 :《强迫劳动罪法益研究及应用》,载陈兴良主编 :《刑事法判解》,第15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210、213、214页。应该讲,意思决定自由(准确而言,应是意思形成自由)只能算附属法益,被害人进行现实的劳动,才意味着主要法益受到了侵害。这虽然是强迫劳动罪中的讨论,但却提出了一个在敲诈勒索罪中也有意义的问题 :“意思形成自由”这一附属法益受到强迫,是否也可认作犯罪既遂?
刑法附带地保护某些权益,并不意味着,这些附带地保护的利益受到侵犯,就足以认定犯罪既遂。应该说,只要认定未遂犯罪,从而科处相应的处罚或谴责,就已经对这些附属法益施加了保护。因此,俄罗斯刑法中所采纳的“不需要财产损失,只需要被告人提出交付财产的非法要求,即可成立勒索既遂”的理解,便不宜照搬入我国刑法学中。因为按照《刑法》第274条的规定,并未明确规定敲诈勒索罪是行为犯罪,而是通过数额的方式,明确了它是以财产损失作为结果的实害犯罪。针对敲诈勒索罪的既遂时点,刘明祥教授在列举了行为犯说(只要实施了威胁、要挟方法迫使对方交付财物的行为,即既遂)、恐惧说(造成了对方的精神恐惧,即既遂)、索要说(实施敲诈勒索行为后,到约定地点提取财物时,为既遂)、取得说(被告人取得财物时,为既遂)之后指出,行为犯说、恐惧说和索要说,都片面地强调了威胁或要挟造成他人精神恐惧、侵害人身的一面,没有注意到,取得对他人财物的占有,才是包括敲诈勒索罪在内的所有取得罪侵害他人财产权的实质,因此,被告人未取得被害人的财物,不可能构成本罪既遂。(24)参见刘明祥 :《财产罪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9-301页;高铭暄、马克昌主编 :《中国刑法解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34页。在德国的勒索罪中,仅有意思自由受侵犯的场合,也不足以认定勒索既遂,除非财产损失出现,才算勒索既遂。NK-Kindhaeuser, 2005, § 253, Rn. 44.实务部门也有人写道 :“侵犯财产罪属于结果犯,其危害后果主要在于直接造成公私财产的损失,因此,判断这类犯罪的既遂与未遂,一般应当以公私财物所有权是否实际遭到侵犯为标准。敲诈勒索罪的完成形态属于结果犯,即行为人使用了恐吓、威胁等手段,使被害人产生了恐惧感,从而被迫交出财物的,即为既遂;如果未因被告人的行为而产生恐惧或虽有恐惧感,但未交出财物的,均为敲诈勒索的未遂。”(25)韩忠伟 :《关于敲诈勒索罪几个问题的探讨》,载《检察实践》2001年第5期;类似的,参见娄秋琴 :《常见刑事案件辩护要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8页。尽管论者在该处以“被害人产生恐惧感”作为财产损失之前的中介,不甚合理,但论者在敲诈勒索罪既未遂上的理解,还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综上所述,敲诈勒索罪乃是实害的结果犯罪,应以财产损失之发生作为其犯罪的结果。这样,防止财产归属出现不当改变和保护财产以免受损失,便是该条款主要的规范保护目的。(26)在国外,只要造成财产损失,而毋需被告人实际地控制财产。若是由第三人交付给被告人的,交给第三人就已经算作既遂。Vgl. BGHSt 19, 342 (343 f.); LK-Vogel, 2010, § 253, Rn. 45 f. 这并非没有道理 :不同于传统的有体物,财产性利益经常要通过银行、邮局等中间环节来实现流转。如果要求被告人现实地控制住财产性利益,那么,被害人的财产利益既已流出,但因为中间环节意外地丢失,也不能认定被告人的犯罪既遂,这不符合敲诈勒索罪保护财产的规范保护目的。而且,如果以被告人现实地控制住利益作为标准的话,容易造成既遂时点的不断拖后 :被告人有可能出于安全的考虑,不断地更换财产的保存方式,直到他觉得安全为止。该主要法益遭受侵害,才意味着敲诈勒索罪构成要件之齐备,才是犯罪既遂。
四、结语
我国刑法理论与实务界人士普遍认为,要成立敲诈勒索罪,被害人必须相应地产生了恐惧心理;被告人取得财物必须建立在对方的该种恐惧心理之上。尽管普遍流行的误解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得以纠正,但是,本文仍然认为,这种“被害人恐惧必要说”疑点众多,并不宜用作认定敲诈勒索行为的法学标准。具体而言,采纳这种“被害人恐惧必要说”,既无助于归纳敲诈勒索案件中的社会生活现象,也不符合敲诈勒索罪这一刑法规范的保护目的和刑法条文以被告人作为标准的对话者或者默认的对话者的表述模式。同时,该观点不仅本身标准不明确,难以实际贯彻到底,而且难以说明敲诈勒索未遂和被勒索者是法人的情况。在否认“被害人恐惧必要说”的前提条件下,纵然“被害人可能之反应”或许会在定罪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参考”作用,(27)此为“被害人释义学”的内容,受本文主题与篇幅之所限,“被害人释义学”的问题宜另撰文探讨。可是,法院关注的乃是被告人是否遵守了法律规范,而非被害人在具体案件中如何反应,故只有被告人所“预先估计”到并用于决定自己该如何行动的那些被害人材料,才能在犯罪行为的认定上发挥作用,所以,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被告人之行为而非被害人之反应。
应该承认,多数说之所以采取“被害人恐惧必要说”,乃是出于对敲诈勒索罪所保护的法益缺乏研究所致。除了财产是敲诈勒索罪所保护的主要法益之外,它还保护一定的附属法益——被害人转移财产的意思之形成过程不受他人强迫的自由。并非每个敲诈勒索既遂的案件中,皆存在被害人恐惧。但是,意思形成自由受到强迫,却是每个敲诈勒索既遂的案件中都会发生的。在入罪条件上,应当以“意思形成自由受到强迫”替代“被害人恐惧”。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区别在于,后者以侵犯人身权利为手段取得财产时“取消”(而不只是“强迫”)了对方的意思形成自由,具有针对被害人保卫财产之可能反抗的压制性,而前者缺乏这种压制性。不过,如果被告人只是侵犯了“意思形成之自由”,尚未造成财产损失,则不足以认定敲诈勒索既遂。除非他以侵犯对方“意思形成之自由”之手段,相应地造成了对方的财产损失,才能成立敲诈勒索的犯罪既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