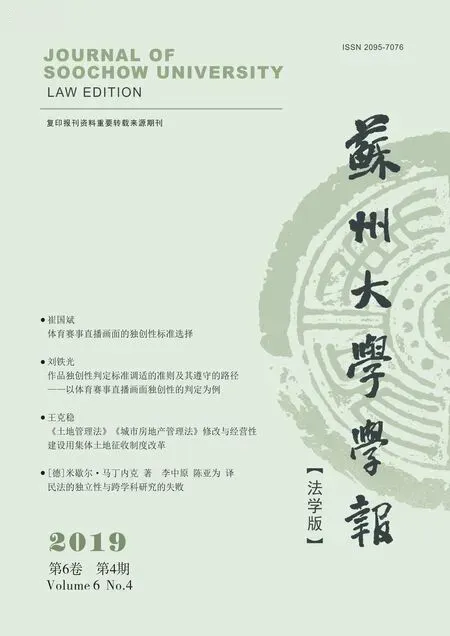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
卢海君
在数字网络环境下,针对广播组织的信号盗播日益严重,广播组织的核心利益日益被侵蚀,但似乎现行《著作权法》对广播组织的相关权益保护非常欠缺,因为,按照《著作权法》的文义解释,广播组织权的“转播权”并不包含通过互联网方式的传播。于是,在现行《著作权法》有关广播组织权的框架下,广播组织很难通过广播组织权的主张来禁止互联网平台、APP对广播组织节目信号的盗播。(1)目前主流学术观点、司法判决、北京高院关于“转播权”的司法解释都不包含互联网方式传播。例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2018)》第6.5条规定 :【广播组织的转播权】广播组织享有的转播权可以控制以有线和无线方式进行的转播,但是不能控制通过互联网进行的转播。与此同时,在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的前夜,有关现行《著作权法》广播组织权的修订工作是重中之重,修法的建议也呈现百家争鸣的景象。争议的焦点围绕在转播权是否延及互联网、广播组织权是禁止权还是许可权等问题上。围绕广播组织权的解释与建构,之所以存在上述诸多争议,一个根本问题在于,对广播组织权的客体缺乏清晰认知。按照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45条之规定,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是“广播、电视”。(2)《著作权法》第45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禁止未经其许可的下列行为 :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转播;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录制在音像载体上以及复制音像载体。前款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为五十年,截止于该广播、电视首次播放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从文义解释的角度,至少在我国《著作权法》的语境中,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是“广播、电视”,而并非其他。然而,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其认为,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界定为“广播、电视”混淆了作品的创作行为和作品的传播行为,将广播、电视节目归类为作品存在逻辑上的问题,有可能使得权利归属机制和授权机制错位,有侵蚀公共利益的嫌疑,缺乏正当性。此种观点认为,只有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认定为信号(信号说),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3)王迁 :《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兼析“以信号为基础的方法”》,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1期。确实,在数字网络环境之下,广播组织权确实需要重新建构,在建构网络环境下广播组织权的内容时,首先应厘清广播组织权的客体。
一、信号说的质疑及广播组织权客体的界定
信号说不仅跟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相左,而且论证逻辑亦存在商榷之处。权利的客体,通常指向的是有价值的东西,例如,所有权所指向的土地、房屋、汽车等。不同于所有权的是,知识产权的客体具有非物质性,通常而言,知识产权的客体所指向的并非物质实体,而是非物质性的创作或创造之产物。例如,著作权的客体,并非“书”这一载体,而是“书”这一载体所承载的作品。即便“书”被烧毁,所有权消失,但作品依然存在,著作权依然存在。这一著作权法的基本认识几无争议。著作权的客体是作品,而并非作品的载体,至少在著作权的语境中,这绝对是共识。然而,为何到了邻接权之中,上述共识就有被颠覆“之嫌”?难道邻接权真的具有区别于著作权的极大特殊性?事实并非如此,不论是著作权的保护,还是邻接权的保护,只不过是第二性意义上的立法模式的选择而已,其所保护的法益客体在第一性上并无本质区别。著作权-邻接权二元结构体系并非世界各国的统一做法,对同样的法益客体,既有采取著作权保护的,也有采取邻接权保护的,即为明证。无论是表演者的表演,录制者的录制,还是广播组织的广播,其本质上都是一种表现形式,同作品并无二致,对其赋予邻接权保护,抑或著作权保护,仅仅是立法模式选择的不同,并不意味着“作品的表演”“录制品”与“广播节目”同作品在本质上有何不同。对作品的表演、对声音的录制、对作品的广播并不仅是机械的传播,其中多多少少凝结了表演者、录制者、广播组织的创造性劳动,这一创造性劳动是值得且应该获得保护的。因此, “创作行为”和“传播行为”所指向的外部世界本质上并无差别。既然如此,对这种本质上并无差别的行为结果进行差别对待缺乏正当性基础。
对于广播、电视节目赋予排他性权利的保护可能有悖公共利益的担心其实来源于对广播、电视节目的错误认识。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要用到已有作品,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广播、电视节目不同于广播组织所播放的作品,这却需要清晰认知。认为如果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界定为广播、电视节目有可能侵犯公共利益,实际上混淆了广播、电视节目与其中所包含的作品。广播、电视节目中包含有作品,但广播、电视节目不同于其中所包含的作品。就好比是,表演者表演作品之后形成的作品的表演,其中有作品的影子,但又不同于作品。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所指向的并非广播、电视节目中所包含的作品,而是广播、电视节目本身。例如,某电视台播放了一部影视作品,该影视作品的著作权法地位并不因为电视台的播放而发生改变。申言之,如果该影视作品处于版权保护期内,电视台对其播放并不会导致其失去版权保护;如果该影视作品已过版权保护期,电视台对其的播放也不会导致其重新获得版权保护。电视台享有权利的对象仅是播放该影视作品之后形成的电视节目,形象但可能并不完全准确的描述是,带有台标的电视节目。信号说认为,假如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界定为广播、电视节目,可能使得已经过了版权保护期的作品重新纳入私人的腰包,从而有悖公共利益。此种理解,实为误解。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是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组织权所能够禁止的仅是电视节目的非法利用,并不能够影响其中包含的作品的著作权法地位。因此,社会公众仍然可以从其他来源获得已经处于公有领域的作品,为何一定要直接复制他人享有权利的广播电视节目呢?
信号说认为,如果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界定为广播、电视节目,再赋予其复制权、发行权、表演权及向公众传播权等,将导致权利归属机制和授权机制错位,有可能造成对广播、电视节目中所包含的作品的著作权的侵蚀,存在严重的正当性问题。事实上,此种担心并无基础,实际上无视了广播组织权权能内容的制度设计。广播、电视节目是多重劳动的结晶,具有内容的复合性,既有作品创作者的劳动,也有广播组织的劳动,从便于理解但可能并不准确的角度,广播节目有点类似于演绎作品,在权利内容的安排方面,也类似于演绎作品,具有独立的禁止权,但不具有独立的许可权。(4)事实上,“邻接权”或“相关权”之表达方式的选取即传达了下述认知 :邻接权或相关权保护的客体是由作品演绎而来,邻接权或相关权的权利设置亦是在著作权的基础之上改造而来。See Tom Rivers, Broadcasters’ Rights: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6 Int’l Intell. Prop. L. & Pol’y 93-1, 93-2(2001).这不仅是理论上的推论,在交易实践中也是如此,如果广播组织仅仅获得作品广播权的许可,是无权将广播节目录制之后进行复制发行的,(5)参见陈佩斯、朱时茂诉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9)一中知初字第108号民事判决书。也无权将广播节目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因此,即使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界定为广播、电视节目,只要是正确理解了广播、电视节目的复合性,便不会产生所谓的权利归属与授权机制错位的问题。
二、广播组织权客体正确界定的法理基础
事实上,广播组织是整个文化产品生产、传播和消费这一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只有正确定位广播组织在这一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才能够正确地对其进行赋权。在著作权法的制度体系中,那些看似错综复杂的著作权、邻接权的设置,事实上都有外部世界的所指。通俗而言,著作权、邻接权背后都有其行业与产业背景,界定著作权、邻接权的内涵应从该背景出发进行。在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和消费中,广播组织无疑占据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广播组织不仅是传播者,同时也是创作者。广播组织所制作的广播、电视节目中不可避免地要用到他人作品,此时,需要获得授权,这既是对他人著作权的尊重,同时也是赋能整个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这一生态系统的重要一环。在认识和理解广播组织在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与播放过程中是否需要及需要何种授权这一问题上,要正视与尊重广播组织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
广播组织播放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或者他人享有邻接权的制品,通常都需要获得权利人的授权。当然,在特定情况之下,为了平衡各方利益,有可能对著作权或者邻接权进行某种限制。以广播组织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为例,在我国著作权法中有广播组织播放已出版录音制品法定许可之规定。(6)《著作权法》(2010年)第44条。由于有此规定,广播组织播放已出版的录音制品,并不需要经过作者的授权许可。依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44条之规定,广播组织并不需要从著作权人那取得广播权的授权,即可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但需要支付相应报酬。而在广播组织播放录音制品的场景中,往往有复制的前期准备工作,如果机械地理解著作权法,尽管广播组织并不需要获得广播权的许可,仍应该取得复制权的许可并且支付版税。如此,广播组织播放已出版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制度便落空。事实上,广播组织播放录音制品本为单一的商业行为,前期的复制行为仅为准备行为,并不具有实质性,已然被广播权所吸收,不具有独立的法律意义和经济意义,广播组织并不应该为单一的商业行为获取双重许可,支付双重费用。为保证著作权的行使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可以从多个维度对某种著作权的行使行为进行评价 :结合行业背景评价某种使用行为是否单一的商业行为,例如,如果广播组织仅是广播,就是单一的商业行为,如果广播组织并不仅仅是广播,还将广播节目录制下来售卖光碟,就是两个商业行为;结合行为的实质对权利进行勘界,例如,复制的本质是作品的非创造性再现并伴有载体的移转,实质是复制件数量的增多,针对的行业是出版业,而广播的实质并不伴有复制件数量的增多,因此,广播实质上并非出版意义上的复制行为;结合权利行使的合理性、合法性评价权利行使是否属于权利滥用,例如,权利人授权广播权而保留发表权即属于权利滥用,因为使用人不发表作品就无法广播作品。未来的著作权、邻接权体系中,由于网络版权时代的到来,复制权的意义式微,以传播权为核心的伞形著作权体系可能是发展的方向。由于文化产业的布局与生态分布,现行著作权和邻接权体系看似纷繁复杂,部分权能之间还有交叉。不过,再次重申,著作财产权背后都有其行业与产业背景,界定著作财产权的内涵应从该背景出发。创作者著作权的保护并不能够存在于真空之中,著作权法制是一个大系统,其中,促进作品的有效传播和公共利益的维护也是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在加强著作权保护的时代强音的同时应该注重权利人、使用者与社会公众之间利益的平衡。权利人或者其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应当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进行,否则可能违背诚信原则,构成权利滥用,导致权利人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失衡,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难以有效实现。由上述举例可见,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已经在创作者、传播者与利用者之间建立了系列利益平衡机制,该机制的一个基本逻辑架构是 :广播组织利用他人成果制作并传播广播、电视节目,需要获得授权并支付相应费用(法定许可除外),广播组织对其制作与传播的广播、电视节目享有法定的专有性权利。尽管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广播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可能需要建构一些规则来应对广播组织权益所遭受互联网的冲击。但是,除此之外,现行《著作权法》所建构的机制并未完全崩溃,准确地说,尚且运行良好。基于此,贸然对现有机制进行釜底抽薪似的革命,风险过大,不可预期。
整个著作权法制就如同一个大机器,广播组织是机器的一个重要齿轮,广播组织不仅要承担义务,而且要享有相应权利,否则,此一齿轮不转动,整个机器也就坏掉了。广播组织利用他人作品制作广播节目,应当获得授权并支付相应费用,这是其义务;广播组织对其劳动成果,即广播节目享有专有性权利,有权禁止他人非法利用,这是其权利。广播节目不仅是广播组织的智力劳动成果,而且也是其投资成果(例如,购买版权的投资),对广播组织付出劳动与投资的产物,广播组织享有一定的权利是理所当然的。区分创作行为与传播行为也许仅是学理之争,包括广播组织权在内的邻接权制度的建构一定是利益推动的结果,(7)See Tom Rivers, Broadcasters’ Rights: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6 Int’l Intell. Prop. L. & Pol’y 93-1, 93-3(2001).只要上述利益具有正当性,对其赋予保护也具有正当性。学理中有如此认知 :区分作品的创作行为与传播行为,是为了赋予作品以著作权的强保护,赋予制品以邻接权的弱保护。(8)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5)京知民终字第1818号民事判决书。上述认识,似乎为误解。邻接权并不等于弱保护,不能以邻接权保护为由降低广播组织权的正当利益保护诉求。例如,在德国著作权法中,存在“摄影作品”与“照片”的区分,对前者赋予的是著作权保护,对后者赋予的是邻接权保护,看似不同,但事实上,两者所获得的保护,在权能设计上,并无实质的差异。(9)参见《德国著作权法》,范长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113页。包括广播组织权的邻接权的诞生是加强了权益的保护,而并非减弱了权益的保护,因为,把广播组织权放在邻接权体系之中,在保护的前提要件中,并无原创性要求。也即是,不问广播组织在广播节目的形成中有无原创性劳动(事实上,广播组织在广播节目的制作过程中,是存在原创性劳动的),只要是广播组织在广播节目的形成中付出了劳动与投资,都对其赋予相应的保护。于是,信号说的担心又出现了 :不要求广播节目具有原创性即对其赋予保护,而且此种保护长达数年,如果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界定为广播、电视节目,必然有损公共利益。在邻接权的体系中,不仅有广播组织权,还有表演者权、录制者权,在一些立法例中,邻接权的范围还相当广泛。表演者权、录制者权指向的是作品的表演、录音制品,对其的邻接权保护也是长达数年,按照信号说的担心,也应该将表演者权、录制者权界定为其他对象,否则也有损公共利益。上述推理显然不成立。因为,作品的表演、录制品不同于其所仰赖的作品,同理,广播、电视节目不同于其中所包含的作品。申言之,广播、电视节目同其所包含或利用的作品是两个不同的客体。信号说实际上误认和混淆了上述两类不同客体,误认为对广播、电视节目的保护会影响到对其中所包含或利用的作品的保护,因此才会得出加强对广播组织权的保护将有损公共利益的错误解读。当然,广播组织权保护期规定的正当性当然不只是与其他邻接权保护类比的逻辑推理,其本质依然是广播组织权保护的利益诉求在著作权法中的呈现。按照“信号说”,广播组织权将不需要保护期的规定,果真如此,将给盗版者留下一个盗版的绝佳漏洞。事实上,法律逻辑自洽与产业利益保护之间本无障碍。“信号说”对广播组织权客体的错误定义不仅有违法律逻辑自洽,更是无视产业利益的合理诉求,理应被抛弃。
三、广播组织权的未来建构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有关广播组织权的规定尽管是时代的产物,对其解读时,也许应该考虑制定《著作权法》时立法者的意图,但现行《著作权法》对广播组织权客体的界定并无问题,广播、电视节目是广播组织劳动与投资的产物,广播组织对广播、电视节目享有一定的权利,合理且正当。不过,在互联网出现之后,对广播组织权益侵害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其中通过互联网盗播广播、电视节目信号从而传播广播、电视节目的行为,对广播组织的核心利益造成了极大侵害,有必要针对此问题进行制度建构。广播组织权建构的本意即在于禁止他人未经授权对其广播的广播、电视节目进行非法利用。基于上述对广播组织生态的分析,广播组织制作广播节目既有原创性,又有一定演绎与汇编属性,所以,在权利归属和授权机制方面,应当遵循演绎作品与汇编著作权行使的规则。广播组织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享有专有性权利(exclusive rights),但在其行使广播组织权时,不得侵犯原有作品的著作权。(10)现行《著作权法》第14条有关汇编作品的规定可供参考 :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其著作权由汇编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既然广播组织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享有专有性权利,其当然有权禁止他人未经授权以任何形式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进行非法利用,在数字网络时代,当然包括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鉴于此,未来广播组织权的内容中,广播组织的转播权应该延及互联网,也即广播组织有权禁止他人通过互联网盗播其播放的广播、电视。同时,基于立法成本节约与避免误读的考虑,修订后的广播组织权应增加广播组织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享有专有权的表述,同时形式上仍以禁止权为中心。因此,未来我国《著作权法》中的广播组织权内容的规定应该如下 :
《著作权法》第 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享有专有权,有权禁止未经其许可的下列行为 :
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转播;
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
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录制在音像载体上以及复制音像载体。
前款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为五十年,截止于该广播、电视首次播放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
上述修订方式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第一,该修订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现行《著作权法》有关广播组织权的规定,具有传承性,不至于由于法律的修订导致实践的断裂。第二,该修订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广播组织的合法权益,但同时又不会侵蚀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制作者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第三,该修订最大限度地正视了广播组织合法权益可能遭受侵害的实践。信号说认为信号具有流动性,认为广播组织权中的转播权限于同步转播,并不包含录播,实际上遗漏了许多广播组织权合法权益可能受侵害的情形。其他广播组织或者互联网平台固定和复制广播、电视节目本身的目的往往就是通过其电台、电视台或者互联网平台进行播放,赋予广播组织以固定权与复制权有利于从源头上防止他人未经许可对广播节目的非法利用。同时,如果将广播组织权限定为转播权,并将转播权限定为同步转播,事实上使得未经许可的录播行为成为合法行为,在体育赛事节目等时效性较强的电视节目中,录播可能并不重要,但许多电视节目并没有太多的时效性,录播行为本身对广播组织的合法权益就会造成极大侵害。鉴于此,固定权和复制权应该是广播组织权的重要内容。第四,该修订尊重了技术中立原则,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该修订尊重了广播组织权的实质,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定义为广播组织播放的广播、电视,而并非其载体,可以智慧地解决实践中很多难题。如果将广播组织权客体界定为信号,有可能产生以下不必要的疑虑 :电视回看信号是否受保护?事实上,不论是何种信号上所承载的广播、电视,其专有权人都是播放该广播、电视的广播组织,因此,广播组织当然有权禁止他人未经授权复制、传播电视回看信号中的广播、电视。第五,该修订保留广播组织权保护期的规定,在保护广播组织合法权益的同时,并没有减损著作权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符合广播组织权的立法宗旨。如上所述,尽管同步转播的情形是侵犯广播组织合法权益的主要情形之一,但并非唯一情形。广播组织对广播、电视节目享有一定期限的固定权和复制权,是防止他人未经授权的非法利用行为的重要一环。
四、结论
在广播组织权的侵犯中,信号是载体,内容是本质;信号盗播是手段,复制内容才是本质。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是广播组织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本质上也是一种表达,此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广播组织权的制度设计应该针对广播组织播放的广播节目展开。整个版权制度就是版权产业利益的隐喻,版权制度为版权产业利益背书并不可耻。信号说纠结于著作权与邻接权保护客体的异同来对广播组织权进行制度设计。然而,在数字网络环境下,广播组织权的设计并不是要满足某种逻辑自洽,而是为了利益实现。信号说不论是否自洽,反而更加严重地损害了广播组织的核心利益。尽管广播组织权的制度设计有公约可以借鉴,但公约本为妥协的结果,并非最优之选择。在解释论上,可以索公约以求“正解”;但在立法论上,处处以公约为圭臬,并非明智之选。整个版权制度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传播技术更迭的历史,从历史演进上看,每一次传播技术的革新都带来了版权制度的变革。在数字网络时代,传播技术的跨界、迭代是趋势,在广播组织权的制度设计中,是要“技术控”,还是要技术中立,恐怕坚持技术中立原则会省去很多庸人自扰之烦恼。广播组织权保护的客体是广播组织播放的广播节目,其中可能包含有作品、制品或其他材料,对“广播”(即广播组织播放的广播节目)的保护不增加也不减损公有领域。(11)广播组织权建构的初衷便是在不减损作者权益的前提之下防止广播节目未经许可被他人非法利用。参见George H. C. Bodenhausen, Protection of Neighboring Rights, 19 Law & Contemp. Probs. 156,157 (1954).对“广播”的保护不会使得其中包含的作品失去版权保护,也不会使处于公有领域的作品重新进入私人的腰包。广播节目中的作品可以是广播组织自制的,也可以是广播组织从他人处获得授权的,不论是何种情况,广播组织对作品的广播并不改变作品的权属与著作权地位。一个广播组织播放了他人享有著作权的电视剧作品,该广播组织可以控制他人对其播放的包含该电视剧作品的广播节目(直观地讲,就是贯标的电视剧作品)录制和复制,但其无权复制该广播节目放在互联网中进行传播,除非该广播组织获得著作权人有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授权。在广播组织权的制度设计中,如果给他人留下了足够多的好的东西,不应吝于赋予广播组织应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