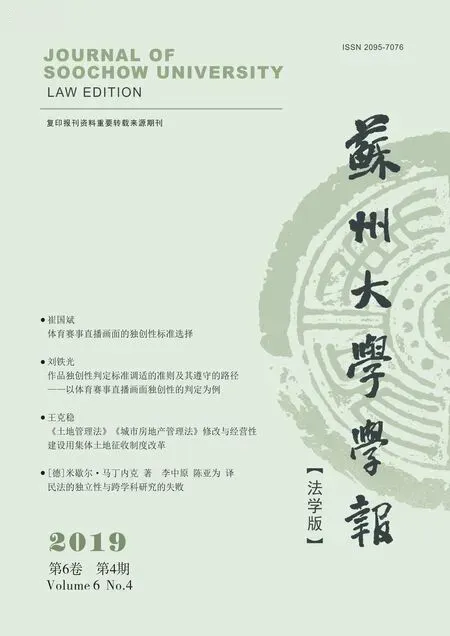法定证据制度的“例外状态”
——以诉讼历史的反思为视角
郝晓宇
一、引言
在证据制度的历史长河中,如果按照韦伯那样以实质/形式、理性/非理性的划分标准来看,法定证据(legal proof)制度无疑是走向现代证据法学形式理性特征的重要一步。在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上,神明裁判制度被教会正式宣布废止,此后,在欧洲大陆的诉讼证明程序里,法定证据制度的重要性越来越毋庸置疑。就法定证据的实质而言 :“法官定罪之前,他必须提出一些预先确定的证据,但是,反过来,一旦面对这些证据,法官就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判定罪行;无论是哪种情形,他的个人意见都无关紧要。”(1)A. Esmein, A History of Continental Criminal Procedu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rance. Trans. John Simpson, Boston :Littile, Brown, and Company, 1913, p.251.
本来,法定证据的设置初衷是出于被告人利益的考量 :要想最后定罪,证明罪行的证据必须达到“比正午的太阳还要清楚”的标准,以防恣意滥用司法权力。可事实上,对于法定证据的预先规定和必然要求,很大程度上却“适得其反”,对于被告合乎情理也合乎法律的恐怖司法刑讯就此开始,以至于接近刑罚的报复效果,不得不扩展到审判定罪之前 :某种程度的犯罪“嫌疑”,就意味着制造与之相应的肉体痛苦的正当性。
尽管按照现代诉讼程序和犯罪认知思维——施以刑罚的前提是罪行得到了确定——我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将刑讯与刑罚区别开来,明确刑讯与刑罚不同的性质和功用,不把二者的范围和意义作广义解释,以免发生不可应对的混淆后果。(2)“我们所说的司法刑讯,是指为了收集司法诉讼的证据而由国家司法人员采取的身体性胁迫……就国家而言,刑讯也被用来在某些情形下获取并非直接涉及司法诉讼的信息。刑讯,必须从诸多用来制裁已经审判定罪的痛苦性刑罚中区别出来。不管多么恐怖可怕,刑罚也不应当称作刑讯。”John H. Langbein, Torture and the Law of Proof: Europe and England in the Ancient Régime, University of Chiago Press. 1976, p.10.但是,这种犯罪与刑罚的思考模式、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相区别的现代证明方法,已经在理解方式中预先设定了法定证据制度的确定历史位置,并且只局限在那个位置来拆解、改造和比较已被自由心证的证明方式替代了的证据历史遗迹。所以,要想真正理解上述法定证据的实质,我们就必须超越刑罚与刑讯的固有解释,甚至只从“刑罚”的视角来解读法定证据与刑讯的关联,或者从“刑讯”的视角来读出坦承供认和刑罚制裁的隐喻。总之,我们需要将法定证据制度的理解方式还原至诉讼历史的演变语境,也就是将调查纠问的公共诉讼还原为一种“例外状态”,才能祛除现代理解方式的预设,真正反思证据、诉讼制度的历史意义。
所以,笔者希望在简要介绍法定证据制度的证明方式、证据种类的基础上,从刑罚实践和认知的转变入手,来展示并思考所谓公共诉讼的“例外状态”。
二、法定证据的证明方式与证据种类
欧洲大陆从12、13世纪开始,对于涉及死刑或者严重身体刑罚(肉刑)的刑事案件,按照罗马-教会法的诉讼程序,证据证明有三条基本规则 :(3)See John H. Langbein, Torture and the Law of Proof: Europe and England in the Ancient Régime, University of Chiago Press, 1976, p.10.
1. 在刑事诉讼案件,法庭可基于两个目击证人的证言来宣告、判处被告。
2. 如果没有两个目击证人,法庭只能根据被告自己的供认坦承来宣告定罪。
3. 间接证据或情况证据(circumstantial evidence),无论具有多大的说服力,都不足以宣告、判处罪行。
首先,我们看到与现代证据体系几乎颠倒对立的确证标准,不是证据在法官或陪审员心理造成的主观说服力,也不是证据自身具备的客观证明力,而是证据能力的法定形式要求,决定着罪与非罪的区别。也就是说,证据证明必须符合事先规定的证明规则,偏离这种法定的证明形式,任何证明或断定均告无效。
其次,在此基础上,证明方式的划分和认定就殊为重要,只有诸如两个目击者证人的完整证明(complete proof),才能符合严重罪行(死刑或肉刑)的定罪前提。除此之外的证明方式,还有直接推论(proximate presumption)或称半证据(half proof),以及间接推论(remote presumption)或称副证、补充性证明(adminicle)的方式,三种方式之间存有复杂、专业的计算拼接规则,但是,任何证据碎片的计算不得贬降严重罪行与完整证明的对应关系。
再次,法定证据系统的建构核心就是死刑 :“在刑事法律制定者的观念中,死刑就是刑法的根本根基。”(4)A. Esmein, A History of Continental Criminal Procedu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rance. Trans. John Simpson, Boston :Littile, Brown, and Company, 1913, p.256.死刑,作为司法制度强调自身的最强表现,不仅是惩罚权力可以达到的最高顶点,也是证据证明要求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或者是施加刑讯的最高限度。
最后,被告人的坦承供认(confession),无论是被动的供认还是主动的坦承,在证据体系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尽管在严重罪行中,只有坦承供认,不得算作完整证据而定罪,但其仍然具备其他证据无法具备的高效证明能力,不仅可以免除繁琐细致的证据组合计算,快速达成证明要求,而且最为关键的是,罪犯“自愿”认罪,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真正征服被告的唯一途径。所有外在的暴力力量,包括刑讯和刑罚在内,都要回归到被告人自己的坦承供认之上。这是外在的调查、纠问、证明机制和内在的臣服、从属、坦承机制最终结合的质点。
在此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再进一步深入到法定证据的具体制度。按照证据类型,当时的证据大致可以分为证人证言、书面证据和推论三种形式,而在完整证明中,最理想的证据类型就是两个适格证人的证言。
分别言之,对于证人证言(testimonial proof),其具体要求为 :(5)See A. Esmein, A History of Continental Criminal Procedu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rance. Trans. John Simpson, Boston :Littile, Brown, and Company, 1913, p.259-260.
首先,必须是两个证人证明同一个事实。不是两个不同或相近的事实,而是相同的一个事实,需要两个证人的共同证明;因为“一个人的声音,等于没有声音”(voice of one, voice of none),但一个证人的证言并非完全无价值,只是不能完整证明而已。其次,证人应该是亲眼所见罪行发生的人,传闻或推测所得,不能构成完整证言。再次,证人的证词必须确凿肯定且需说明缘由。类似于“我相信、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也许可能、如果我记忆正确的话”等话语,不能出现在刑事案件的证明中,这类证词甚至不能构成间接推论。此外,在整个调查纠问的过程中,证词必须保持统一一致,不得更变易换。最后,证人不能是无能力者或被排除反对的人。尽管排除反对的抗辩权利实际应用中受到很多限制,但出于理论的平衡考虑,仍然存在应当排除反对的事由,如亲属、惧怕、仇敌、年龄不足、智力不足、恶名昭著、利益冲突等。
除了证人证言,在少量案件中,书面证据(written proof)也可以用来直接证明犯罪行为,尤其是除了书面证据其他证据很难证明的罪行,比如异端、密谋造反、高利贷、收买证人以及某些需要证人证言和书面证据共同佐证的行为,比如伪造罪。在更为普遍的情形中,书面证据只能构成推论,而且需要得到官方的正式检验或者当事人的接受承认。
在法定证据的体系中,那些显而易见的推论(presumption)也是必不可少的,从推论中也可以得出完整证据的证明,但这种推论需要充足的构建,也就是要么有两个目击证人,要么有书面证据或其他的证明。比如,当时经常假设并作为典范的一个案例 :如果被告人被他人发现手持凶器或身染血迹离开一处随即被发现有人遇害的犯罪地点,那么,对此事实如果有两个符合条件的证人证言,就可以在必要且合理的推论之下构成完整证据。而如果只有一个证人的证言,则只能构成效力次之的所谓半证据,或者说是直接推论的证据。
在推论之中,又可以细分为 :(6)See A. Esmein, A History of Continental Criminal Procedu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rance. Trans. John Simpson, Boston :Littile, Brown, and Company, 1913, p.267.
一般或间接推论(general or remote presumption),比如被告人的一贯恶行,或者之前犯过同样的罪行,这种情形可以引起法官一定的怀疑和调查。
其次是较近推论(nearer presumption),比如在凶杀案中,被告人与被害者的仇敌关系,或者凶杀之前被告人的行凶扬言。虽然不是与行为直接相关,无法构成半证据,但引起的怀疑更大。
最后是直接推论(proximate presumption),比如看到手拿带血凶器从犯罪地点走出。尽管不是绝对不容置疑的事实证明,但足以组成一个半证据。
对于直接推论之外的所有间接推论,包括一般推论和较近推论在内,要么可以使法官决定采取进一步调查,或者导致罚金性质的惩罚,要么可以作为副证或佐证,成为半证据的必要补充。比如 :“被告人的闪烁言辞,声音的颤抖,精神状态的局促不安,或者是沉默寡言……他的住所与犯罪地点的临近,被告佯装的耳聋,或者当面对提问时思维混乱、记忆丢失……被告人糟糕的表述,或者是叫错的名字。”(7)A. Esmein, A History of Continental Criminal Procedu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rance. Trans. John Simpson, Boston :Littile, Brown, and Company, 1913, p.268.以上行为,或者说声名狼藉的任何蛛丝马迹,都必然具备一定的证明效力从而可以当作罪行的某种副证或佐证。
之所以如此详细区分各种推论并且赋予各自不同的证明能力,根本原因在于,只有达到半证据或直接推论,才能够启动刑讯拷问程序。虽然半证据自身的说服力不管多强都不能单独支撑严重刑罚的判决,但如果在半证据的基础上得到自愿的坦承,或者利用刑讯拷问获取了被告的供认,就可以构成完整证据而定罪。简言之,半证据,加上被告人的坦承供认,就等于一个可以定罪判刑的完整证据。可必须注意的是,若是两个重要的半证据或直接推论(不是同一事实的证明),则不能叠加组成一个完整证据,因为 :“半证据不比半真理更具决定力,同理,两个不确定不能组成一个确定,两组半证据也不能组成一组完整证据。”(8)A. Esmein, A History of Continental Criminal Procedu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rance. Trans. John Simpson, Boston :Littile, Brown, and Company, 1913, p.265.
这种自主判断不仅体现在充足指征的性质断定,还表现为法定证据的复杂计算上。事实上,即便是中世纪刑事惩罚和刑事诉讼集大成者,如法国1670年刑法典,也对法定证据体系的诸多规则语焉不详,只是在司法实践中“理所当然”地适用着。(10)See A. Esmein, A History of Continental Criminal Procedu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rance. Trans. John Simpson, Boston :Littile, Brown, and Company, 1913, p.251.这种“理所当然”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法官在具体案件中的专家式判断和专家式计算。比如在那个经典案例中,如果发现了作案匕首和被害人的劫掠物,那么就可以把两个证据各自算作四分之一证据,加起来则构成了半证据。而在更为复杂情况中,就存在复杂的证据加减运算,而背离了后来所谓的一般常识。比如,当时法国的某些法院在处理法定证据时,如果对方针对某个证据提出了异议,那么这种异议并不彻底取消该证据的证明价值,而是把一个证据的效力酌情增减为类似二分之一证据、四分之一证据或八分之一证据。假设有四个人的证言受到了对方异议的攻击,那么其中两个证言的价值各减一半,加在一起就等于一个证言;如果第三个证人的证言减为四分之一,第四个证人的证言减为四分之三,那么他们又可以构成一个证言。于是,尽管这四个证人的证言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对方异议的攻击,但是他们加在一起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明。(11)何家弘 :《司法证明方式和证据规则的历史沿革——对西方证据法的再认识》,载《外国法译评》1999年第4期。
至此,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围绕着死刑所搭建而成的法定证据体系,其间存有严重形式化的法律规定和效力预设,另一方面则是法官在使用刑讯手段时针对证据要求的灵活裁量。也就是说,一方面是证据体系的固定形式 :“这种法律证据体系在刑事领域中把一种复杂艺术的结果变成真理。它所遵循的是只有专家才懂的法则,因此它加强了保密原则”,(12)[法]福柯 :《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0页。另一方面则是刑讯坦承的游刃高效 :“供词能够成为强有力的证据,以至几乎无须补充其他的证据,或者说不需要进行那种麻烦而不可靠的副证组合。如果供词是通过正当方法获得的,那么就几乎能够免除检察官提供进一步的证据(也是最难获得的证据)的责任。”(13)[法]福柯 :《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1页。可是,与其说法定证据体系和司法刑讯的相生相克不过是一种暗自契合或相互证成,以至于前者的“固定性”和后者的“灵活性”交织共存、同生共灭,不如说,这种交织共存、同生共灭的关系仍然缺乏一种理解的契机,那种契机就在于刑罚实践和刑罚认知的转变。
三、刑罚实践和刑罚认知的转变
按照梅因在“古代法”中对“犯罪”行为的描述 :
“所有文明制度都一致同意在对国家、对社会所犯的罪行和对个人所犯的罪行之间,应该有所区别,这样区别的两类损害,我称之为犯罪(climina)和不法行为(delicta),虽然我并不认为这两个名词在法律学上是始终这样一致应用的。古代社会的刑法不是‘犯罪’法;这是‘不法行为’法,或用英国的术语,就是‘侵权行为’法。被害人用一个普通民事诉讼对不法行为人提起诉讼,如果他胜诉,就可以取得金钱形式的损害赔偿。……因此,如果一种侵权行为或不法行为的标准是 :被认为受到损害的是被损害的个人而不是‘国家’,则可断言,在法律学幼年时代,公民赖以保护使不受强暴或欺诈的,不是‘犯罪法’而是‘侵权行为法’。”(14)[英]梅因 :《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36-237页。
按照梅因的区分,现在称之为“犯罪”的众多行为,在古代社会仅仅是“不法行为”或“侵权行为”而已。这种判断的依据在于,一方面,古代并无受到侵害的国家或社会抽象利益,只有针对具体个人的冒犯损害;另一方面,当时并不虑及“罪责”或主观意志,只关心客观结果。
但是,梅因马上表明,我们不能就此断定,对国家做出不法行为这样一种简单而基本的概念,是在任何原始社会中都缺乏的,相反,恰恰可能是因为阻止犯罪的概念被古代社会彻底且有效地理解了,所以才有与现在完全不同的应对手段。他在罗马社会中观察到 :
通报显示,2017年,石油产量小幅下滑,天然气产量增长较快,油气开采呈现“油降气升”态势。2017年全国石油产量1.92亿吨,同比下降4.1%。产量大于1000万吨的盆地有渤海湾(含海域)、松辽、鄂尔多斯、准噶尔、珠江口和塔里木盆地,合计1.73亿吨,占全国总量的90.5%。全国天然气产量1330.07亿立方米,连续7年超过千亿立方米,同比增长8.0%。其中,产量大于30亿立方米的盆地有鄂尔多斯、四川、塔里木、柴达木、松辽和珠江口盆地,合计1070.34亿立方米,占全国总量的88.0%。
“对于严重妨碍国家安全或国家利益的每一种罪行,都由立法机关制定一个单独法令来加以处罚。这就是对于一个犯罪的最古概念——犯罪是一种涉及重要结果的行为,对于这种行为,国家不交给民事法院或宗教法院审判,而专门对犯罪者制定一特别法律加以处理。因此,每一个起诉都用一种痛苦和刑罚状的形式,而审判一个犯人所用的一种诉讼程序是完全非常的、完全非正规的、完全离既定的规则和固定条件而独立的。”(15)[英]梅因 :《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38-239页。
如果梅因不受现代划分罪行因素的限制,那么这种最古老的“犯罪概念”,以及针对每个不同的犯罪者所制定的特别的、非常规的、非固定的法律措施,则不过是模仿个人之间针对不法行为或侵权行为的复仇。在神明裁判的特殊断讼时代,受规则约束的法律解决,仅仅是诸多争议解决方法的一种,当事人除了接受法律规则的约束外,在更广泛的程度上,受私力救济之复仇约束。这种复仇机制,只在意那个已经做成的行为,丝毫不顾及也不追究所谓主观罪责,甚至复仇的施加对象,也不以实际犯下罪行者为限,只要是犯下罪行者所属团体的成员,都有遭受复仇的危险,或者代以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所以,当时的法律诉讼不过是一种非胜即败的止讼方式,只有等到12、13世纪,当中世纪首个庞大的君主政体作为现代国家的起源而形成时,才会出现一系列新的“发明物”。(16)参见[美]约瑟夫·R. 斯特雷耶 :《现代国家的起源》,华佳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首先,诉讼,不再是个人之间的对抗和他们自愿接受的某些解决规则,而是一个人由上而下地强加于个体、对手和当事人;其次,公诉人,这个奇特的角色,开始标示自己为主权者、国王或统治者的代表,当个人之间出现犯罪、冒犯或争议时,仅仅是冒犯或犯罪的发生,就使他成为一种受损的权力;最后也最为重要的是,发明了犯罪行为 :犯罪行为,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侵权,而是个人对国家法律、社会秩序、最高权威的冒犯与损害——“违法行为是中世纪思想的一个伟大发明”(17)Michel Foucault,Truth and Judicial Forms, in the Power :The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Trans Robert Hurley and others. The New Press, 1997, p.1-89.。此后,就是我们熟知的结果 :国家权力占据了整个司法程序,占据了中世纪早期全部个人争议的解决机制。
因此,唯有代表君主权力的法官出现后,并以保护孤寡病弱、打击声名狼藉之名介入到犯罪与刑罚之中时,犯罪、恶意、惩罚的公共意义才显得合情合理并且重要起来,可是 :
“君主的干预不是在两个敌对者之间进行的仲裁,也不只是强制人们尊重个人权利的行动,而是对冒犯他的人的一个直接回答。毫无疑问,‘君权在惩治犯罪方面的行使,是主持司法正义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惩罚不能被认为是对伤害的补充,甚至不能用这种补充来衡量。在惩罚中,总有一部分理应属于君主。而且,即使在惩罚与补偿相结合时,惩罚仍是用刑法消灭犯罪的最重要因素。……因此,惩罚权是君主对其敌人宣战权利的一个层面……惩罚也是强制索取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补偿的一个方式……在最普通的刑罚中,在最微不足道的法律形式的细节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是活跃的报复力量。”(18)[法]福柯 :《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2页。
对于报复,这个广泛弥漫在神判断讼时代的个人精神气质,在法律权力出现的时刻并不十分陌生,但是当报复从私人之间的对抗上升为君主与其敌人(即罪犯)的宣战时,惩罚所担负的报复力量就将突破过去个人复仇机制的所有限制。报复的法律惩罚形式,不再是个体决斗的延续或模仿,不再有任何平等的限制原则,不再依靠任何自然身体的生命强力,惩罚报复,成为无限炫耀、恫吓、残忍和恐怖的权力铭刻仪式。惩罚成为君权能量的最大释放,成为法律秩序的最强宣明。在此,只有彻底剥夺生命或者至少造成肉体伤残的刑罚强力表演——围绕死刑的公开处决,才够得上这种君权力量的要求。死刑,不仅是刑罚含义的完整表达,也是刑罚意义的核心所在;公开处决死刑,成为刑罚权力最光艳耀眼的表演时刻,并将从此延续数个世纪 :
“其(即公开处决)宗旨与其说是重建某种平衡,不如说是将胆敢蹂躏法律的臣民与展示其威力的全权君主之间的悬殊对比发展到极致。尽管对犯罪造成的私人伤害的补偿应该是成比例的,尽管判决应该是平衡的,但是惩罚的方式使人看上去不是有分寸的,而是不平衡的、过分的。在这种惩罚仪式中,应该着重强调权力及其固有的优势。这种优势不仅是君主权利的性质,而且是君主用以打击和控制其反对者的肉体的物质力量的性质。”(19)[法]福柯 :《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3页。
简言之,当政治权力首先表现为一种司法权力,而“犯罪-刑罚”首先体现为君权能力的最大释放,或者成为法律秩序的最强宣明时,只有彻底掠取生命或至少造成肉体残损,才能证明君主权力作为一种物质力量的不可僭越,以至于法律秩序的真实含义就显示为这种不平等力量的对峙张力 :用共同之善来统合犯罪之恶。
所以,按照当时的理解,刑罚的种类只包括死刑或肉刑,类似罚金和监禁的刑罚措施,尚在刑罚理解范围之外。(20)See Georg Rusche and Otto Kirchheimer, Punish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1939, p.62.也就是说,只有打击、控制反对者的生命和肉体的行为,才够得上是一种法律形式的惩罚。这种刑罚观念的结果,就是罪与非罪之间缺乏一种过渡。而对于法律证据制度,缺乏过渡则意味着 :要么达到了完整证据而判定有罪,或者死刑或者肉刑;要么无法满足法定证据的要求,哪怕依靠现有证据完全可以构成确信,也只能判定无罪,或至少不能判定意欲证明的死刑和肉刑。因此,在肉体的生死之间,由于法定证据的形式规定,留与法官决定的内容,往往只是如何处死的问题。(21)See John H. Langbein, Torture and the Law of Proof: Europe and England in the Ancient Régime, University of Chiago Press, 1976, p.34.
可直到18世纪,犯罪与刑罚的那种悬殊至极的力量展示才几乎被贝卡利亚第一次感知 :“即使严酷的刑罚的确不是在直接与公共福利及预防犯罪的宗旨相对抗,而只是徒劳无功而已。”(22)[意]切萨雷·贝卡利亚 :《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无限且极度不平衡的报复力量,根本无法让众人(不是罪犯)在犯罪与刑罚之间形成有效、切实的心理预计,刑罚不应该以违背人道主义的恐怖残暴来显示自身的巨大力量,而应该渗入到细致入微的每一次行为利益的衡量计算中;因此,不是过分,而是最少,不是实际痛苦,而是充分想象,不是本人悔过,而是他人确信,不是疏忽侥幸,而是绝对确定……总之,“罪犯是社会的敌人”,(23)[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3页。而不只是君主的敌人,刑罚绝不能沦为君主力量和罪犯力量之间的报复仪式,而应该体现仁慈、温和,但同时,又要细密、绝对、高效。
已有学者指出,正是刑罚类型的增多和刑罚方式的“温和”,根本上决定了刑讯制度的废除进而决定了法定证据形式的废除,(24)See John H. Langbein, Torture and the Law of Proof: Europe and England in the Ancient Régime, University of Chiago Press, 1976.这对理解司法刑讯和法定证据的关系无疑作出了正确提示。但是,在这一点上,刑罚实践和刑罚认知却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分离。也就是说,在贝卡利亚式的启蒙思想家发现犯罪与刑罚的合理关系之前,诉讼实践领域已经展现出领先于理论的操作。
在法国1670年刑法令中,刑罚的意义和形式早已丰富充盈起来。按照刑罚的等级,有“死刑、拷问、苦役、鞭刑、公开认罪、放逐”,而且还有未被提及的“满足受害者要求、警告、正式申斥、短期监禁、行动限制以及罚款或没收”等处罚。(25)J. A. Soulatges, Traité des crimes Ⅰ, 1976, pp. 169-171. 转引自[法]福柯 :《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5页。在这个封建时代集大成的刑事法律中,不仅把刑讯拷问列为仅次于死刑的刑罚,而且还加入了12、13世纪不曾存在的新刑罚类型,如苦役、放逐等。这种变化无疑提示着在刑罚实践上发生的重大转变 :一方面,监禁作为一种惩罚方式,在势必引起刑罚理论重新定位和估量(如贝卡利亚、边沁)的态势下,已从中世纪晚期开始,逐步进入世俗法庭,在轻微罪行上替代了过去那种血腥惩罚;(26)See Georg Rusche and Otto Kirchheimer, Punish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1939, p.53-71.此外,在16、17世纪,除了死刑和肉刑,新的刑罚方式得以发明,如地中海沿岸国家发明的苦役船刑罚(galley sentence),欧洲北方国家建立的济贫院、教养所、劳改所(workhouse),再加上流放刑罚(transportation)等,(27)John H. Langbein, Torture and the Law of Proof: Europe and England in the Ancient Régime, University of Chiago Press, 1976, p.25-31.这些刑罚类型除了将注意力铺展在了肉体痛苦之外的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极大地充实了生死之间罪与非罪的空白缝隙。
在刑罚实践如此变革的基础上,贝卡利亚式的“仁慈”才呼之欲出 :罪与非罪的区别固然重要,但似乎采取合理有效的刑罚方式更能切中犯罪实质,如果刑罚造成的“痛苦”等级与罪行的严重程度不能合理对应,那么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性质区别都将混乱不明,而只要建立起犯罪与刑罚之间的精确标尺,甚至立法者只要标示出这一标尺的基本点,就足以应对犯罪。(28)“人们能够找到一个由一系列越轨行为构成的阶梯,它的最高一级就是那些直接毁灭社会的行为,最低一级就是对于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所可能犯下的、最轻微的非正义行为。在这两极之间,包括了所有侵害公共利益的、我们称为犯罪的行为,这些行为都沿着这无形的阶梯,从高到低顺序排列。……如果说,对于无穷无尽、暗淡模糊的人类行为组合可以应用几何学的话,那么也很需要有一个相应的、由最强烈到最弱的刑罚阶梯。有了这种精确的、普遍的犯罪与刑罚的阶梯,我们就有了一把衡量自由和暴政程度的潜在的共同标尺,它显示着各个国家的人道程度和败坏程度。然而,对于明智的立法者来说,只要标出这一尺度的基本点,不打乱其次序,不使最高一级的犯罪受到最低一级的刑罚,就足够了。” [意]切萨雷·贝卡利亚 :《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80-81页。在此基础上,“废除死刑”的合理性(来自刑罚本身的合理性)就此显示出来 :死刑,完全可以在刑罚等级中被更加有效的其他刑罚置换顶替。从此,刑罚的重点将不再是以死刑为核心的极端恐怖报复,而是应当如何合理地设置从低到高、逐步升级的刑罚序列,从而让此罪与彼罪或者有罪与无罪的转化过渡符合理性计算。
但是,与其说贝卡利亚式的瞻望和规划是要力图消除刑讯或酷刑,不如说是要把它们正式转变为更加精确有效的刑罚序列,在理性计算上更加普遍可视、坚固必定,贝卡利亚坚信,刑罚的刑讯“强度”,并未就此降低。(29)“每一个人的气质和算计都随着本人体质和感觉的差异而各不相同,刑讯的结局正体现着个人气质和算计的状况……这种方法能保证使强壮的罪犯获得释放,并使软弱的无辜者被定罪处罚……” [意]切萨雷·贝卡利亚 :《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0页。总之,不是克服刑讯,而是克服刑讯的低效、无效或相反效果。所以,我们就需要在刑罚实践和刑罚理论整体扭转的视角中,还原并理解法定证据制度的历史语境。
根据上面的介绍,我们知道法定证据体系实际是一种证据碎片的汇集和拼接 :不是某个证据对于犯罪事实的证明能力,而是一个又一个证据的拼合叠加,才构成了不可动摇的完整证明,证据的每一个碎片都代表了一定的犯罪嫌疑,哪怕是与犯罪事实毫无直接关联的一般推论,甚至是行为不端的名声,都具备毋庸置疑的犯罪证明力。因此,法定证据的实际效果,就是一种“待罪状态”,这种“待罪状态”的最佳体现,就是广泛且普遍适用的半证据与刑讯的组合——既非肯定有罪,也非绝对无罪;前者阻绝法官就此确信定罪,后者又令法官可以就此施加刑讯;结果就是 :不能定罪的合理刑讯,或者正当怀疑的肉体痛苦。法定形式的预先约束,看似造成了不可突破的阻滞和停滞,实际则让刑讯的动力呈几何式增长 :当完整证据的要求无法达成时,刑讯—坦承,往往就成为犯罪证明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块拼图;若刑讯无果,一次刑讯,再次刑讯……理论上,肉体痛苦可以在主体身上无限地重叠、挖掘、衍生。总之,刑讯,占据着“死亡前的一切”。
在此,刑讯确实显示为犯罪嫌疑的惩罚,或者说,调查罪行的行为就是惩罚罪行的行为;对于某种罪行的嫌疑,即意味着惩罚的正当,如在《加洛林纳刑法典》中清晰表述着 :“一个人不仅不应犯下罪行,而且也应该避免所有邪恶的行径,或是败坏名誉或能指征罪行的行径,没有遵守这种行为的人才会招致控诉……被告也应当为自己遭受怀疑的行为提供证明和支持。”(30)John H. Langbein,Prosecuting Crime in the Renaissance: England, Germany, Fra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259-308.
但是,这种调查罪行和惩罚罪行的重叠并未说出主体在调查到惩罚过程中的真正意义,并未指出作为肉体和灵魂统一整体的主体应当扮演的重要角色 :这个主体,与贝卡利亚试图证明的刑罚之下的主体也许正相对立,而对立的意思不过是辩证式的“应当一致”。因为,司法刑讯添补罪与非罪空隙的方式,或者说刑讯的“刑罚”意味,主要目的不是建立由低到高的等级序列,让被告主动计算、衡量罪与非罪的区别和过渡,而是始终围绕在肉体的生死和痛苦之上,它希望刑讯的主体不是精于利害计算,而是自愿地完全臣服、自愿地完全坦承。在当时的诉讼证明制度中,法律主体的在场是如下一则简短、深刻而令人无法评说的档案记录 :
“雅盖,约9岁,热昂·居德罗之子,拘留在监狱,没有刑讯的强制和恐吓,就坦承招供了。”(31)A. Esmein, A History of Continental Criminal Procedu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rance. Trans. John Simpson, Boston :Littile, Brown, and Company, 1913, p.134.
四、公共诉讼的“例外状态”
在了解了上述刑罚实践和刑罚认知的转变、重估后,我们则要返回那个君主和罪犯的公开复仇过程,返回贝卡利亚式的重估之前,或者说重估这种重估。
在刑罚主要体现为君主对罪犯的血腥报复的时代,公开处刑,已是罪行结果的最后展示,事实上,从众所周知的“恶名”开始,大部分案件在公开处刑之前一直保持着秘密且特殊、例外的状态,正是在“例外状态”(exceptional state)之中,一边是内在犯罪意志的确信、转化、审查和坦承,另一边则是外在罪行的揭发、举报、调查、讯问、证明和判决。直到最后执行,每一个层面的每一个阶段,无不要求例外对待。
这就是在诉讼制度的历史中至关重要的一次变革 :从个人对个人的控告制度(accusatory system)转变为调查纠问的公共诉讼制度(inquisitorial system)。本来在控告制度的末期,公共权力已经能够凭借某些理由介入到私人对抗之中,比如当场逮捕的情形、无人可以控诉的情形,甚至公共权力可以仅仅根据怀疑就实施逮捕的某些情形,但这些方式在突破控告制度边界的同时,又遭到地方封建主和旧有贵族按照习惯和特权的抵制,(32)对于这种转变,就有贵族和有产者的态度既有抗拒反对的一面,也有利用接受的一面 :“在12、13世纪统治者和相关社会责任团体的主要目标就是建立有能力和声誉的法庭,从而能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大部分争端。说服有产阶层接受法庭的司法是通过大量、持续的施压来进行的,并且没有政府意愿冒削弱法律程序的危险。但地方伯爵、高级教士和自治镇马上发现如果他们同意根据新的规则玩这个游戏,相比武装斗争,他们可以经常通过法律途径有效地违抗政府。”[美]约瑟夫·R. 斯特雷耶 :《现代国家的起源》,华佳、王夏、宗福长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无形之中,制度的边界在某些时候反而清晰起来。那么,最后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即国王的公诉人,如何介入到刑事诉讼之中呢?我们知道,“不是直接作为起诉人,或者作为案件当事人……而是通过官方调查来介入,通过教会法首先展开的‘调查程序’而渗入其中。”(33)A. Esmein, A History of Continental Criminal Procedu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rance. Trans. John Simpson, Boston :Littile, Brown, and Company, 1913, p.117.
公诉人这个“奇特”的角色,(34)See Michel Foucault,Truth and Judicial Forms, in the Power :The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Trans Robert Hurley and others. The New Press, 1997, p.1-89.在12、13世纪的西欧,以自己作为主权者或君主的代表,在个人之间的冒犯、侵害发生时,仅仅凭借犯罪行为的发生,即表示自己的权力从中受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方面,由于犯罪行为的“发明”,个人之间的侵犯行为已转变为涉及共同体的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不再是一个人冒犯另一个人的私人事件,而是一个人践踏、攻击法律秩序的公共事件;另一方面,由于统治者或主权者是整体法律秩序的代表和保证,违法犯罪,就不只是施害于个人,也不只是破坏公共法律秩序,而是首先对法律秩序的确立者、保护者,也就是主权者,所施行的根本性蔑视和侵害。公诉人,以统治者所代表的法律秩序来要求惩罚犯罪行为,让罪犯直接面对统治者,以法律与和平之名,开启面对面的战争。这种直接性——不是当事人双方的直接性,而是统治者所代表的法律秩序与被告人的直接性——使得最初还仅仅是陪同受害者一起追诉施害者的公诉人,很快就可以而且必须抛开受害人,独自宣明 :“国王是唯一的原告”。(35)A. Esmein, A History of Continental Criminal Procedu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rance. Trans. John Simpson, Boston :Littile, Brown, and Company, 1913, p.118。此外,在一开始,公诉人与法官的关系,不是公诉人促使法官审理案件,而是法官在进行了先期预审调查的基础上,再决定是否公诉。二者的具体关系和历史转变这里不做讨论和细分。
在国家兴起的势头中,公诉制度如火如荼,控告制度则举步维艰。尽管不是即刻废止不用,但由于秉持着当事人双方的旧式的决斗战争模式,原告可能不得不在诉讼期间与被告一同羁押待审,不得不在无法判断案情时凭借古老的司法决斗最后一决胜负,不得不担负诉讼失败后原本希望施加在被告身上的惩罚代价。这种古老的“报复”程序,尽显刻板、严厉、沉重和危险的弊端,在新的公诉程序面前相形见绌。公共诉讼,包括当场逮捕、揭发人举报,无不免除原告作为当事人在控告程序中本应面临的繁重和危险,揭发人、法官和公诉人会主动地调查、纠问恶行,被害当事人仅仅需要向法官告诉、举报案情,并在公诉程序中申请类似民事侵权性质的赔偿,就能在毫无负担和代价的前提下,既看到犯罪人受罚,又得到金钱赔偿。总之,只要确信君主临在的法律秩序不仅广泛存在而且不可损害,原告就能坐待其利。
但是,尽管在14、15世纪,个人控告程序的适用案件寥寥可数,几乎濒临消亡,刑事诉讼仍然将其称为“一般正常程序”(ordinary procedure),而调查、纠问的公诉制度,则是“特别例外程序”(extraordinary procedure)。之所以保持这种称呼和定位,原因显然不是顾及实际案例的适用比例,而是因为一般情形与特殊情形的形式要求存在根本差异。也就是说,一般的控告起诉程序,诉讼过程仍然保持公开,原被告双方可以平等控辩、自由举证、交叉质问,任何破坏形式平等的措施都不可使用。而特殊的纠问程序则不受此限,此种程序遵从的是秘密原则,被告的辩护权利极其受限,更为重要的是,刑讯可以正当适用。在法国,直到1498年颁布的法令,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清楚区分‘一般’程序和‘特殊’程序,并指明如何选择两种程序以及各自遵守什么形式要求。”(36)A. Esmein, A History of Continental Criminal Procedu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rance. Trans. John Simpson, Boston :Littile, Brown, and Company, 1913, p.146.
众所周知,上述特殊例外程序将是后来诉讼程序的主要方式,其秘密的、不平等的、刑讯的手段也频遭诟病。带着刑讯的顽疾,纠问制度在17世纪彻底确立后(以法国的1670年刑法令为代表),又在一百年后的法国大革命的浪潮中被迅速颠覆,虽然检察公诉制度得以保留,但在启蒙、人道的基础上,大量公开、平等、对质的原则被重新提出,并且,严格禁止刑讯拷问。与此同时,某种程度上导致刑讯拷问的证据制度领域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那种由法律预先规定证据形式的桎梏被自由评价证据的心证原则所代替,似乎刑讯的“根基”被就此拔除,确定罪行不必再受僵硬刻板的法定证据限制,陪审团或法官完全根据现有证据事实即可判定是否有罪、如何惩罚 :从此,刑讯的必要性丧失了。
可是不管证据证明方式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人道主义的观念如何深入人心且不容置疑,即便在文明发达的现代司法制度中,滥用刑讯的丑闻仍旧不绝于耳。反对刑讯的呼声,似乎不再是对恶劣司法环境的抗议,也不是对司法制度改革(比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的要求,甚至不是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即可概括道尽的理性问题,而是根本溯及司法诉讼制度本身 :只要那种司法诉讼制度存在,刑讯拷问就与生俱来,不可消除。
正是这种理论与实践、规范与适用之间的悖谬和分离,促使我们必须超越反对刑讯的纯粹人道信念,也必须超越实践操作的纯粹规范建制,而首先反思在12、13世纪调查纠问的公诉制度出现之后,为何适用于大量案例却依旧长期保持特殊、例外程序的意义——反思“例外”的悖谬式“合理”与“必然”。
如果说法律之为法律的关键,根本上不在于标明违法、制裁违法的那种强制力量,而是通过重复那个“违法”行为却不遭受任何制裁来把自己呈现为一种例外的存在的话,(37)[意]吉奥乔·阿甘本 :《神圣人 :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那么,这绝不是说“一个不具逻各斯的纯粹暴力宣称要实现一个没有任何现实指涉的表述,而是说明,例外状态标示着一个门槛,在其间逻辑与实践无法彼此确定”。(38)[意]吉奥乔·阿甘本 :《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9-60页。换言之,例外状态是法与非法混淆不清的地带,但这种混淆不清的前提却恰恰是法与非法的各自分离。从公诉制度开始,在君主权力控制下的司法诉讼程序,就在发明犯罪的基础上,熟稔于这种“创立/取消”法律秩序的辩证游戏(以创立法律秩序为名而取消法律秩序)——既泾渭分明,又无法区分,既是维护公共法律秩序,同时又是把罪犯置于君主主权的敌对位置而恣意打击、折磨、致死;既是法律秩序层面的必然要求,同时又是超越法律秩序层面的无限制结果;既是可以严格规范的法定过程,同时又是无法作出任何规范的自由决断,总之,“例外状态,就是这个权力的‘约柜’收纳于其核心的事物”(39)[意]吉奥乔·阿甘本 :《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6页。:
“外部定在之间的各种关系构成理智的无限性,因此没有任何自在的界限来划清什么是有害的和什么是无害的;又从犯罪方面说,也没有任何自在的界限来划清什么是有嫌疑的和什么是没有嫌疑的,什么是应予禁止或监视的和什么是不受禁止和监视、不启人之疑、免予查询和盘问,因而是容忍的。一切细节都是由风尚、整个国家制度的精神、当时状态、目前危险等等来规定的。”(40)[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72页。
所以,要想理解纠问公诉制度为何会最终取代对抗控告制度,或者理解秘密刑讯程序为何会被迅速广泛采用并且成为不可根治的顽疾,就必须首先理解为何公共诉讼在例外状态中能够开启逻辑与实践无法区分的地带 :
“在法规范的情形,对于具体个案的指涉则需要‘诉讼’——其总是涉及复数的主体,且最终以判决宣告的高潮结束,亦即,一个以制度权力保证其对于现实之操作性指涉的表述。”(41)[意]吉奥乔·阿甘本 :《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9页。
公共诉讼所要面对的任务,是沟通、连接起法律秩序与法律适用。这种连接过程或沟通方式,既无法内含于秩序,也无法从秩序中推导,正如在法律结构中,主权者的决断无法从秩序规范中导出,(42)如施米特所说 :“作为一个真正且纯粹的决定,秩序的建立不能来自于一项既存规范的内容,也不能来自一套既存的秩序,否则,该秩序的建立就会是现行规范的自我适用,或是现存秩序的外延,从而不能说是秩序的建立,而只是秩序的再建立。”[德]卡尔·施米特 :《论法学思维的三种模式》,苏慧婕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或者在语言学里,言说行为不能从语言中得出一样。公共诉讼的行为,就类似于应当遵守法律秩序的主权者如何行动的问题,或者应当符合语言规则的言说主体如何言说的问题,这恰恰是秩序、语言、法律为了得以适用而不得不自我悬置的领域,否则它们就将继续保持纯粹逻辑范畴而无法完成指涉现实的转变。换言之,正是语言本身表明了必然存在非语言的言说,使得言说者不得不面对语言的内在指涉;正是法律秩序本身要求着法律秩序之外的无法区分地带,使得主权者可以在超越法律秩序的意义上针对罪犯(其行为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法律秩序)无任何限制地采取刑讯拷问、刑罚报复;若缺失这种无法区分、无法限制的例外地带,语言和法律都将失去任何指涉现实、规范现实的可能意义。于是,也许可以说,正是法律秩序要求得以适用的普遍逻辑,在根源上导致了实践这种秩序的手段不受任何限制。
只有在这种前提下,才能理解上述刑罚之为报复的含义。犯罪行为,绝对不是与后来民事行为请求权类似的一种纯粹法律适用的“构成要件”,或者是触发启动国家刑罚权的一个具体犯罪事实,或者仅仅是违背法律规则而已;犯罪行为,是对法律秩序的绝对违背,是对“和平”的彻底打破,是对君主权力赤裸裸的敌对和挑衅。犯罪行为的严重性,不仅仅是局限于事实层面而与秩序无关——即无论具体行为怎样,秩序本身不受动摇(43)施米特对此有着准确的观察 :“在规范论的观点之下,具体状态就根本不可能会有与秩序相对立的无秩序存在。”[德]卡尔·施米特 :《论法学思维的三种模式》,苏慧婕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而是直接触及整体秩序的存废 :犯罪行为所显示、证实的“恶”根本不容于共同理性、公共意志所要求的“善”,正是根深蒂固的价值判断不允许任何模棱两可的试探。只有这样,法律权力延续数个世纪的极不平衡和过度展示——刑讯、酷刑(死刑)——才在逻辑上合理起来。
所以,任何以规范的、人道的价值观念来批判这种司法实践的不规范、不人道,其实仅仅停留在了秩序价值的表层。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反对刑讯、反对酷刑的人道主义呼吁者,与施行刑讯、施行酷刑的反人道人士,都是同一逻辑要求的产物,也是同一秩序的维护者。问题在于,在无法区分秩序与非秩序、法律与非法律的中间地带,同样也无法区分开人道与非人道、残忍与非残忍。某种非法的无秩序,或者非人道的残忍,正是法律秩序或者人道仁慈的必然结果或必经之路。如果后者是普遍意愿的一种善,那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善的非善手段,或者由善导致的善与非善的必然无法区分的例外地带。
只有在这种例外状态的意义下,法定证据制度的历史语境才可能逐步地被挖掘、展示出来,而法定证据制度所担负历史角色,也才能真正得以获知。
五、结语
在证据法学的理性主义传统下,法定证据制度往往只是某种有待批判、有待否定的对象。当人们轻易地将对法定证据的关注重心转移到司法刑讯和供认坦承之上时,往往忽略了司法刑讯和坦承供认在诉讼、证明过程中具备的真正意义。在刑罚实践和刑罚认知整体转变的视角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定证据制度借助刑讯和坦承所力图维持的罪与非罪的过渡地带,它除了牵涉到后来所理解的刑罚范畴,还具有与后来法律刑罚完全不同的作用,而只有在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公共诉讼连接起法律秩序和非法律秩序的前提下,那些超越人道意义的法律规范价值才可能逐步展示出来,这是我们追溯并理解法定证据制度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