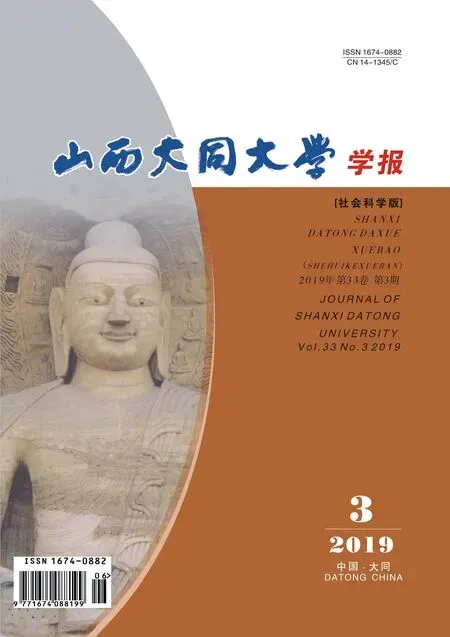论白居易讽谕诗中的民生观
罗浩春,付兴林
(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如是说:“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1](卷5,P2794-2795)其讽谕诗的兼济性质主要体现在他深入里巷、揭露时弊、为劳苦大众代言诸方面。对此刘熙载给予高度评价:“代匹夫匹妇语最难,盖饥寒劳困之苦,虽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无间者也。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闾阎,目击其事,直与疾病之在身者无异。”[2](P352)学界对白居易讽谕诗中的民生观时有论及,但仍有诸多未尽之处。以下拟结合白居易的仕宦经历、讽谕诗篇、诗论主张、价值追求,对其讽谕诗中民生观之具体体现、产生原因以及民生观的价值与局限性,进行一番深入细致的考察。
一、白居易民生观在讽谕诗中的体现
“衡量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就是要看他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其遗产中有多少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因素,有多少‘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3](P541)白居易“属于未来”的民生观主要表现为对时令反常、物生夭阏的怜悯,对弃贫趋富、悖礼违孝的关注,对劣官败政、不识寒俊的鞭挞,对邪虏贪婪、朝政日衰的痛惜等四个方面。
首先,白居易在诗中表现了对时令反常造成的物生夭阏、土瘠民贫的现实的充分关注与深切怜悯。白氏诗中叙写了许多自然灾害,其中描写旱灾的诗歌有《贺雨》《夏旱》《月夜登阁避暑》3 首,描写雪灾的有《春雪》《村居苦寒》2 首,描写水灾的有《大水》1 首,描写蝗灾的有《捕蝗》1 首。《夏旱》记录了元和九年(814)天下大旱、民不聊生的情景,诗中描述了旱灾的严重程度——“金石欲销铄,况兹禾与黍”。[1](卷1,P62)连金石将欲被太阳熔化,更何况脆弱的禾苗呢?诗句虽显夸张,但却道出了旱灾给农业带来的极大破坏性。“在旱灾时实行的祈雨活动,是唐代最为频繁举行的因灾祭祀活动”。[4](P201)《贺雨》一诗则记录了朝廷为感动上天降雨而豁免地赋、多出宫女等的行为,这种特殊的祈雨方式更显诗人仁民爱物的情怀。《春雪》一诗记录了元和六年(811)二月,寒气不退、降雪不减的极端恶劣天气:“月晦寒食天,天阴夜飞雪。连宵复竟日,浩浩殊未歇。大似落鹅毛,密如飘玉屑。”[1](卷1,P36)寒食时节当是和暖之时,然天气乖谬至此,导致万物衰残、物生夭阏——“上林草尽没,曲江水复结。红乾杏花死,绿冻杨枝折。”[1](P36)面对一片苍凉之景,作者忧虑物性受损,有伤农时——“所怜物性伤,非惜年芳绝”。[1](卷1,P36)
其次,唯利是图、弃贫趋富和抛弃父母、孝道沦丧的不良社会现象也引起了诗人的关注。如诗人在《读史五首》(其五)中,借用历史人物表现了时人不择手段追求财富的扭曲行为:“遂使中人心,汲汲求富贵。又令下人力,各竞锥刀利。”[1](卷1,P103)在《议婚》一诗中,诗人通过富家女与贫家女的婚嫁情况,揭露了当时人们弃贫趋富的普遍趋势:“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见人不敛手,娇痴二八初。母兄未开口,已嫁不须臾。”[1](卷1,P80-81)富家千金在婚嫁时炙手可热,家人尚未同意,议亲的人纷至沓来。相比之下,贫家女子则是:“几回人欲聘,临日又踟蹰。”[1](卷1,P81)可见相貌端庄、贤良淑德在金钱财物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世风日下的另一体现是孝道的沦丧。诗人在《燕诗示刘叟》序言中有云:“叟有爱子,背叟逃去,叟甚悲念之。叟少年时,亦尝如是。故作《燕诗》以谕之矣。”[1](卷1,P53)刘叟少年时抛弃自己的父母,而今又遭自己的爱子所弃,因果报应的背后反映的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整体下滑。
其三,劣官败政、人才见弃的吏治腐朽现象也是白诗关注的焦点。白居易曾作《江州司马厅记》,认为司马一职是“尸素之尤蠹者”。[1](卷5,P2733)诗人认为居官而不尽责、白吃国家俸禄的行为,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而现实情况是官员不仅为官不作为,而且还有施加苛刑重赋、滥使民力、造名立碑等丑陋行为。如《杜陵叟》描写了官吏急敛暴征的虎狼行为,揭露了免租“德音”延迟发布的政治黑幕。“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敕牒榜乡村”。[1](卷1,P223)这是统治者惯用的技俩,即在灾情发生的时候,朝廷会下达免除灾区赋税的诏令,而地方官员为了超额完成任务,向上邀功,延迟发布诏令,仍旧急敛暴征。《立碑》中鞭挞了一些官员毫无政绩,却争求立碑扬名的丑恶行径。吏治的腐败不仅反映在劣官败政方面,在选材用人上也存在极大的弊端。白居易诗中多借物喻人,道出了寒俊进阶之难的现实。如《叹鲁二首》(其一)用季桓、阳货的典故,揭露了富贵重于才能的不良世风:“所托得其地,虽愚亦获安。彘肥因粪壤,鼠稳依社坛。”[1](卷1,P132)又如《羸骏》一诗中描绘了一匹失主饥饿的千里马,由于消瘦的身躯,连相马者也不愿承认其价值。显然,此诗具有借马喻人之深意。
第四,白居易在诗中也表现出对黠虏贪婪、朝政日衰的国情的担忧。元和四年(809),白氏作《山阴道》一诗,痛斥回鹘狡黠的马政给唐朝经济以及无辜百姓带来的巨大损耗——“每至戎人送马时,道旁千里无纤草”。以马易绢,劳民伤财——“五十匹缣易一匹”“缣丝不足女工苦”。[1](卷1,P231)《旧唐书·回纥传》有云:“自乾元之后,(回纥)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其使候遣继留于鸿胪寺者非一,蕃得帛无厌,我得马无用,朝廷甚苦之。”[5](P5207)回鹘易马重点在于利益谋取,根本无视唐朝现实需求,暴利之下其贪婪之心昭然若揭——“谁知黠虏启贪心,明年马多来一倍”。[1](卷1,P231)《卖炭翁》中诗人直接批判了当时的弊政——宫市。“所谓‘宫市’,就是皇宫里需要物品,向市场上去购买,随便给点钱——实际是公开掠夺人民财物的一种方式”。[6](P99)《轻肥》中又以宦官之酒池肉林与江南人食人的现状作对比,极大地讽刺了宦官专权的飞扬跋扈、骄奢淫逸——“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1](卷1,P92)
二、白居易民生观产生的原由
白居易民生观的产生既得益于对传统民本思想和儒家诗教的继承,又受前代诗人思想的影响,同时,诗人自身成长和仕途进阶的经历以及补政救失、感念皇恩的思想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一)民本传统,美刺沿袭 “民本”思想最早见于《尚书》,“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7](P177)《春秋谷梁传》中云:“民者,君之本也。”[8](P13)历代士子承袭这种民本思想,对民间疾苦往往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与同情。从白氏家世“自鍠至季庚,世敦儒业,皆以明经出身”[9](P2)以及白氏“十年之间,三登科第”[1](卷1,P2793)的仕宦经历,可见出诗人受儒学影响之大之深。其讽谕诗中反映的农民耕作之辛苦、天气乖谬给庄稼带来的不利影响、孝道沦丧的不良社会现象以及官员残暴、尸位素餐等问题,都体现了诗人对儒家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兼济”与“独善”是儒家奉行的为人处世的两种选择。诗人后期虽追求富足闲适的生活,但亲民爱民之心却始终如一。他在杭州刺史任上兴修水利,在苏州刺史任上修筑山塘,晚年又开凿龙门八节石滩,都印证白氏造福黎民的心迹。“虽然白居易一生特别是晚年与龙门佛教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又旁鉴老庄,儒、释、道三教通融,但骨子里主要还是儒家思想。说到底,‘兼济天下’永远装在白居易的心里,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变化,永恒不变的是他那颗亲民爱民的心,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天下的黎民百姓”。[10](P190)
白居易兼济天下的民生观还受儒家讽谏诗教的影响。《孔子家语·辨政》云:“孔子曰:‘忠臣之谏君,有五义焉;一曰谲谏,二曰戆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讽谏,唯度主而行之;吾其从讽谏乎。’”[11](P159)将讽谏列于首位,可见这种委婉的表达方式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儒家讽谏诗教提倡的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即要求以诗歌批评时政、揭露时弊。白氏在《与元九书》中就高度赞扬了诗歌的讽谏作用:“言者无罪,闻者足诫,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1](卷5,P2790)受儒家讽谏诗教感染,诗人在《新乐府序》中明确提出“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1](卷1,P136)的观点,强调诗歌应具有美刺褒贬、补察时政的功能,要求诗歌真正做到“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1](卷1,P47)
(二)源追杜甫,承袭张、王 安史之乱后,出现了以写民生疾苦为主要内容、写实人生为创作倾向的文学思潮。以时事入诗是杜甫的创造,而将这一手法发扬光大的莫过于白居易。在白居易早期应试所写的《百判道》《策林》中就反映出直面生活、贴近时代、论说时事的创作精神。在《百道判》中有对科场、官场、军界、社会丧葬礼仪等的思考,体现出强烈的忧虑时政的情怀;[12](P39-78)针对社会问题和国政衰朽的现实,白居易在《策林》中提出为君为圣之道、施政化民之略、求贤选能之方、整肃吏治之法等对策。[12](P146-261)其后的《新乐府》更是诗人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痛刺和极谏,是其以时事入诗写法的直接体现。罗宗强先生指出:“在把写实引向触及时事这一点上,可以看出白居易常常有意学杜甫。他的《宿紫阁山北村》,简直就是杜之《三吏》写法;《村居苦寒诗》也有杜的那种感慨世事、顾念贫寒而深心自愧的特色。”[13](P179)可见杜诗与白诗之间确有源与流的启承关系。
在杜甫与白居易之间,张籍、王建起了桥梁作用。王建诗歌多写民间情事,描述的事件大都平易近俗,体现出向通俗化方向趋进的痕迹,如《当织窗》描述贫家女纺织之辛苦,反映压在人民肩上的赋税之沉重。张籍则是“唯以同情之心写所见,而田夫野老之辛苦,征夫思妇之悲怆,尽在其中,”[13](P173)以同情心写实,作品中自然流露讽谕之意。白居易在《酬张太祝晚秋卧病见寄》中称张籍为“高才”,道自身为“短羽”。[1](卷1,P485)可以看出白居易对张籍“秉高义”“富贵视如云”[1](卷1,P346)的高洁人格的钦羡以及对张籍诗歌反映现实、注重教化的推崇。张籍的诗歌创作理念与白氏“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1](卷1,P136)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首先,二人都注重追求诗歌内容的质实性,如在写底层民众的生活困境上,张籍有云:“共知路傍多虎窟,未出深林不敢歇。”[14](卷383,P4292)再如白居易则道:“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1](卷1,P227)写农民劳作之辛苦,张籍云:“一年耕种长苦辛,田熟家家将赛神。”[13](卷382,P4291)白居易则道:“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1](卷1,P62)反映弃本逐末的社会现象,张籍云:“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长为贩卖翁。”[14](卷382,P4287)白居易则云:“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1](卷1,P241)等。其次,二人都注重诗歌的政教作用。张籍《学仙》诗云:“求道慕灵异,不如守寻常。先王知其非,戒之在国章。”[14](卷382,P4298)白居易《两朱阁》亦指出当时佛寺渐多带来的危害,“忆昨平阳宅初置,吞并平人几家地。仙去双双作梵宫,渐恐人间尽为寺。”[1](卷1,P208)张籍《董公诗》云:“公衣无文采,公食少肥浓。 所忧在万人,人实我宁空。轻刑宽其政,薄赋弛租庸。四郡三十城,不知岁饥凶。”[14](卷382,P4300)白居易《新制布裘》亦云:“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1](卷1,P65)此外,张籍的《商女》《勤齐》诗中体现了对社会不良风气的矫枉之意,这与白氏在《井底引银瓶》等诗中体现的自觉教化民众的思想高度一致。张籍、王建尚实的主张与实践,都在白居易之前,他们在诗歌创作中力求新变,为后来白居易关注民生时事的写实创作树立了榜样、做好了铺垫。
(三)家贫少苦,仕途艰辛 白居易虽出生书香门第,但早年却过着食不果腹、颠沛流离的生活,正如其《朱陈村》中所述:“昼行有饥色,夜寝无安魂。东西不暂住,来往若浮云。”[1](卷2,P512)正是少年时代漂泊经历奠定了日后贴近底层、了解百姓疾苦的思想基础,为他在诗歌中替人民“鼓与呼”做好铺垫。如他在十一二岁逃避藩镇割据的战火时,目睹战乱中人民生活的惨状:“离乱失故乡,骨肉多散分。江南与江北,各有平生亲。平生终日别,逝者隔年闻。朝忧卧至暮,夕哭坐达晨。”[1](卷2,P512)
白居易的仕进经历亦使他多关注民生时事。白居易并无显耀的世系,是无出身、无官资的白身人,而“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贯”,[1](卷5,P2793)凭靠的是科举考试这一途径。《文献通考》卷37《选举考十》载记道:“吏部则试以政事,故曰身、曰言、曰书、曰判。然吏部所试四者之中,则判为尤切。盖临政治民,此为第一义。必通晓事情,谙练法律,明辨是非,发摘隐伏,皆可以此觇之。”[15](P354)这就要求科考士子必须熟悉民情,了解民生疾苦。白居易在准备吏部科目选的过程中拟作了《百道判》,其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涉及民生问题,表现了突出的人文精神。在白居易备考制举拟作的《策林》中,针对农民困苦、遭受盘剥等问题,提出一些兴善除弊、归利于民的主张,充满浓厚的民本思想。
(四)补政救失,感念皇恩 白居易自叙其讽谕诗歌反映民生疾苦的目的是“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1](卷5,P2792)他认为采诗可以观风,诗之音义对统治者了解风俗民情有极大的意义:“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窦也。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1](卷5,P2790)故其作诗直歌其事,以期补察时政,为统治者巩固政权而服务。
感念皇恩的心态,也强化了他施政御民的意志。《初授拾遗献书》一文充分表达了白居易对宪宗的知遇之恩:“臣所以授官已来,仅将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宠,但未获粉身之所耳。……倘陛下言动之际,诏令之间,小有遗阙,稍关损益,臣必密陈所见,潜献所闻,但在圣心裁断而已。”[1](卷5,P3324)为答谢皇帝提拔之恩,白居易立志致君济人。拾遗之职在于“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1](卷5,P3324)《初授拾遗》诗中就明确表达了他知恩图报、鞠躬尽瘁的愿望:“天子方从谏,朝廷无忌讳。岂不思匪躬?适遇时无事。”[1](卷1,P20)
三、白居易民生观的价值
白居易在诗中彰显的“人民性和民主性因素”,不仅给当时社会带来了巨大震动,也对后来士人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对当时社会来说,白居易民生观有“疾贪暴、活疲民”的功效。白居易所处的中唐时期,持续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以及藩镇割据、牛李党争造成的朝政不稳、社会离乱都对唐王朝的经济发展、秩序重建造成巨大破坏。在这样的背景下,白居易创作的旨在“疾贪暴、活疲民”的讽谕诗,无不彰显着感念苍生的民本主义思想的光辉。需要说明的是,白居易在继承儒家民本思想的同时,将自身“好刚不好柔”的刚直品行熔铸其中,形成一种大无畏的激进民本主义思想,在当时上层统治者中引起强烈震动:“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1](卷5,P2792)“平心而论,由于受儒家‘仁政’理想和民本主义传统的影响,我国历史上的文人士大夫,对于民间疾苦一般都可能表现出一些关注和同情的倾向,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像白居易在元和前期的政治实践和文学实践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但歌民病痛,不识时忌讳’的激切态度,‘誓心除国蠹,决死犯天威’的大无畏精神,则确属凤毛麟角,罕与其匹的。”[3](P337)
其次,白诗中的民生观对后世的士人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晚唐五代时期,朝代更替频繁,战争连年不断,士人十分推崇白居易诗歌的政教精神,主张用诗歌来干预现实,针砭时弊。皮日休最欣赏白居易,其代表作《正乐府》十首深刻地反映了晚唐社会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对黎庶细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可以说是深受白居易讽谕诗的影响。皮日休“欲以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者也”[16](P107)的创作理念与白居易新乐府诗歌的主张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宋代文人对白居易关心民生、积极讽谏的精神十分称赞,王禹偁自谓“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17](卷65,P733)戴复古诗题云“敬效白乐天体,以纪其事”,[17](卷2813,P33469)明言自己的诗效仿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在元代,白居易讽谕诗亦影响深广。元代西域诗人对白居易的接受,绝非个别现象,甚至可以说是蔚然成风。他们有意效仿白居易讽喻诗关注民生的传统,如廼贤、马祖常和萨都剌等西域诗人。[18]时至明清,白居易亦深受时人重视,如陈维崧“将词与‘经’‘史’相提并论,继承和学习了《诗经》与白居易‘新乐府’的讽谕精神,赋予词体以庄重的内容,写出了深刻的内涵,他的大量词作细致地反映了明末清初的国事,被称为‘词史’”。[19]
四、白居易民生观的局限性
首先,白居易创作讽谕诗的动力存在偏颇。白居易讽谕诗的创作目的是“愿得天子知”,立脚点不是为广大百姓谋取利益,而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服务的。因此,上层统治者对白居易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其创作行为。唐宪宗就曾因白居易的直言进谏而勃然大怒,谓:“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5](P4344)统治者的排挤打压使白居易讽谕诗的创作失去原动力,对民生的热切关注也随着抒写日常生活的闲情逸趣而逐渐淡化。
其次,白居易关注民生的深度不够。白居易在诗中对官与民的阶级划分十分明晰,以官员之身份探视百姓的生活和心理,往往情感较为单纯,对民生的抒写也较为表面。我们只要将他与杜甫进行比较就可清楚地见出两人民生观之别。杜甫之民生观来自内心的切身体会,将个人遭遇与广大人民的苦难结合,具有与民同悲、感同身受的复杂情感。白居易“为君”而作的讽谕诗展现的大都是第三人称视角(多为上层官员)对下层民众的悲悯之情。如“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1](卷1,P65)“岂无穷贱者,忍不救饥寒?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1](卷1,P85)以第三人称抒情,在情感抒发上稍显淡薄。而杜诗以己推人,情感过渡自然,更显真挚。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20](P201)杜甫从“吾庐独破”想到“天下寒士”茅屋俱破,诗人博大仁厚的胸襟和崇高远大的理想由此可见一斑。又如《无家别》以第一人称视角写一位战败归来的士兵,亲见故乡残败、亲友凋零的悲惨情状,情感真挚强烈、浸入骨髓。因此,与杜诗相较,白诗在情感抒发上自是稍显逊色。前人在比较两人的优劣时云:“尊老杜者病香山,谓其拙于纪事,寸步不移,犹恐失之,不及杜之注坡蓦涧似也。”[2](P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