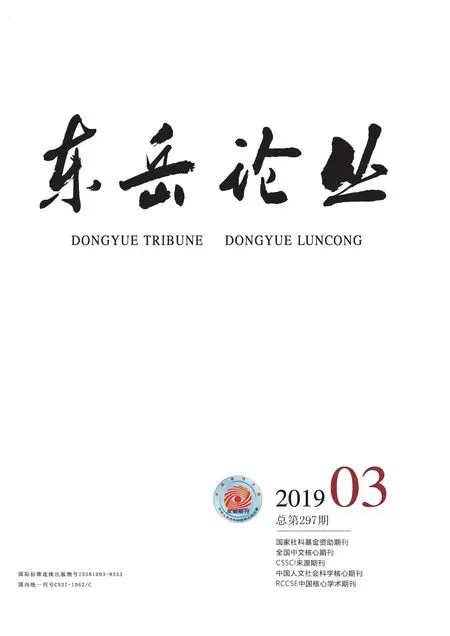超越悖论:论消费社会中人的解放
杜松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191)
消费社会的到来,一方面为人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为人的解放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其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也造成了人的种种困境。因此,消费社会中“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以凸显。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是时代发展和理论创新的需要,是对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在当代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更为马克思人学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另外,研究这一问题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我国现既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处于从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过渡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探讨如何超越人的发展悖论,实现人的解放,不仅有利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而且有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消费社会中人的发展悖论
在消费社会中,我们永远都是按照消费物品的模式对人进行判断与评估,个体生命历程被断裂为一系列的短期计划和一段段的插曲。永无止境的消费,使我们的生命像耶稣钉于十字架一样,被钉死在永恒的消费上。在这一个永劫回归的世界里,无法承受的重荷,沉沉压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在面对汹涌而来的物品时,我们却变得束手无策,无所适从,生命开始轻得不能承受。在消费社会中,我们常常痛感消费无法承受之重,又面临着选择无法承受之轻。正是在这种重与轻的悖论中,个体生命被撕裂了,承受着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煎熬。正是这些,导致了人的发展出现一个又一个悖论。
(一)贫乏与丰富:人的社会关系发展悖论
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社会交往的发展和社会关系异己性的克服两个方面。在消费社会中,这二者都呈现出悖论式发展的特征。第一,社会交往的贫乏与丰富悖论。这种悖论式发展主要表现在交往目的与交往形式、交往主体与交往范围、精神交往与物质交往的贫乏与丰富上。展开来看,交往目的不再是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基本需要,而是成为满足人的单一的物质消费需要。以消费为主要目的之交往,则使消费者身份成为交往的唯一主体,进而导致交往主体的片面化发展。由此出发,必然引起精神交往的贫乏化。与之相对,则必然是以消费为中心建构起来的物质交往的形式的丰富和范围的扩大。第二,社会关系异己性克服过程中贫乏与丰富的悖论。这种悖论式发展主要指克服社会关系异己性过程中内容的贫乏与形式的丰富。内容的贫乏是指:在消费社会中,人根本无法克服社会关系的异己性,这种克服本身就是苍白空洞的。换言之,消费社会中,人不仅没有克服社会关系的异己性,反而在物化的社会关系中越陷越深。形式的丰富则是指消费社会中人在试图克服社会关系异己性过程中所采取的花样繁多的手段,即通过“审美化生存”或是“回归原始”等等来超越异化的社会关系,实现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但是这些形式多样的努力,依旧只是无用功而已。
(二)自由与受控:人的活动及能力发展悖论
人的活动及能力的发展主要指的是人的实践活动及作为其外化表现的各种实践能力如劳动能力、社交能力等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中,工作和闲暇则是表现人的活动及能力发展的最主要的方面。因此,这种悖论式发展主要表现为自由的选择工作与受控的闲暇之矛盾。作为一个流动性的现代社会,消费社会允许人自由地选择工作方式和场所,随意地安排工作时间和计划,甚至可以选择不工作。工作的自由,带来了闲暇时间的增多,似乎从表面上促进了人的活动及能力的自由发展。但是,从本质上看,这种闲暇时间却是受控的。因为“休闲并非对时间的自由支配,那只是他的一个标签,其基本规定性就是区别于劳动时间的束缚。所以它是不自主的:它是由劳动时间的缺席规定的。自由时间本身也变得越来越需要直接或间接地被购买以被‘消费’”,“休息、放松、散心、消遣也许都是出于‘需要’,但它们自身并没有规定对休闲本身的苛求,即对时间的消费”①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页。。人的闲暇时间被消费活动全面挤占,自由时间完全等同于消费时间。与此同时,人的闲暇时间也呈现出加速化的特征。人在闲暇中感到的不是放松,反而是紧张,不是自由,反而是强制,不是快乐反而是痛苦。在眼花缭乱的消费品面前,每个人都急于做出选择,都竭力使自己跟上物品更新换代的速度。“我们竭尽全力使自己更有效率,力求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乃至每一秒钟能做更多的事情。自工业革命将世界变得高速运转以来,对速度的崇拜就将大家逼到了崩溃极限。挣扎在精疲力竭的边缘,身体和心理在不断提醒我们:生活的节奏已经失控。”②奥诺德:《放慢生活脚步》,李慧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导语。因而,看似自由的选择和放松背后,实则饱含着无奈的追赶和疲于奔命的痛苦。
(三)真实与虚假:人的需要发展悖论
消费社会中,消费不再是满足需要的中介手段,而是需要的不断再生产,“需要是依据生产的目的,作为一种消费的力量被再生产出来的。”③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需要本身被从主体身上剥离开来,成为消费的属性。于是,消费制造出了虚假的需要。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广义的需要区分为需要和需求两类,其中需要是指基于人的本性出发所产生出来的基本的真实需要,需求则是指因特定利益而从外部世界强加给人的虚假需要。基于此,人的需要发展悖论表现为需要和需求二者界限的消失上。正如鲍曼所说:“‘真正的’或合法的需要同‘虚假的’或应谴责的‘伪’需要之间神圣的界限已经被取消。”④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郇建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具体来看,这种悖论式发展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需要的单一化,货币成为真正的需要;二是需要的虚假化,“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要机敏地而且总是精打细算地屈从于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第121页。三是需要的矛盾化,“一方面所发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另一方面产生着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⑥《1844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北京:人 民出版社,2000年 版,第120页,第121页。。由此出发,人的需要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
(四)独特与一致:人的个性发展悖论
人的个性发展悖论主要是指作为主体的个体在发展时呈现出独特性与一致性的矛盾。在消费社会中,每一个个体都要作为主体而独立存在,却又被统一的消费者身份所束缚。在强调个性发展独特性的同时,却又把符号消费确立为人们体现个性的唯一手段。“在一个由个体组成的社会里,每个人必须是个体。至少就此而言,如此之社会的成员偏偏就不是个体的、与众不同的或者独一无二的。恰恰相反,他们之间是极其相像的,因而他们必须依从一样的生活策略,使用共有的——通常是可辨认的、清楚的——象征,让其他人相信他们确实是那么做的。在个性问题上,是没有个体的选择的。”②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生活》,徐朝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第19-20页。个性的独特性不过是被制造出来的满足其一致性消费者身份的手段而已。“所有展示在陈列柜中的自我组装的器具,都是工厂按最新款式批量生产的。你的自我所具有的最不同于流俗的特征,只有在他们被转化成时下最为常见、最为广泛使用的流通货币时,其价值才能够得到认可。”③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生活》,徐朝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第19-20页。也就是说,人的个性发展不仅是一种悖论,而且还成为一种特权。一方面,拥有所谓个性的人是那些成功的消费者,他们从最新商品的限量版中获得个性。另一方面,那些被排除在消费体系之外的人,则无法拥有个性,在日益消失的传统安全网络中固守自身,既无法参与,又无法逃离。在此意义上,消费社会中人的个性的发展愈发显得矛盾重重,步履维艰。
二、资本逻辑与人的消失
消费社会,作为“物的依赖性社会”,其本质上遵循的仍旧是资本逻辑。资本逻辑全方位地塑造了消费社会。首先,从作为社会主要关系的物化关系来看,它的产生及发展都是资本逻辑发展的结果。其次,作为社会主要活动的消费活动来看,它的重要性的凸显是资本逻辑关注重点转变的结果。再次,从作为上层建筑的消费意识形态来看,它的出现是资本逻辑控制形式改变的结果。第四,从作为社会运行的新逻辑符号逻辑来看,它不过是资本逻辑的符号化表现而已。因此,资本逻辑造成消费社会中人的全面性、自由性、真实性与独特性的消失,导致人的悖论式发展。
(一)物对人的全面包围
消费社会中物对人的全面包围,是造成人的社会关系发展悖论的主要原因。追根溯源,资本逻辑是其背后的主因。因为资本“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9-390页。消费社会中物对人的全面包围,只是资本自身增殖的需要和拓展空间的结果。
正如鲍德里亚指出的那样:“目前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⑤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一方面,物品消费的多样化普遍化促进了交往的丰富化全面化。消费社会的发展,进一步打破了民族心理、文化惯习和时间空间等对交往的限制,加强了人们之间的联系,拓展了交往空间,从形式上丰富了人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消费社会中“物体系”的包围,加剧了人在物化关系中的沉沦。物化程度的加深进一步推动了物化人格的发展,形成了对物体系的完全依赖,造成人的全面性的消失,导致了人的社会关系发展的贫乏性。
在人与物的关系上,人所面对的不再是具体的物,而是被装具系统所操控的物体系。物不再是人的感觉器官的延伸,而是被技术体系所决定的抽象物。由此,人与物的关系变得愈发疏离。人只能从外端按照系统的要求作用于物,人的行为愈发机械化和模式化。而这种机械化、模式化,必然导致人的社会关系发展的贫乏化。这是由于:作为人的社会关系发展主要表征的劳动,在装具体系的作用下,被同质化为无差别的操控机器的过程。总之,“在物的包围”下形成的物化关系加剧了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假、疏离和功能化,人的存在方式的形式化和空洞化,造成了人的社会关系形式上丰富性与内容上贫乏性的悖论式发展,进而造成了人的全面性的消失。
(二)消费①这里的消费,是从广义上来理解的作为生产的消费,即马克思所说的和生产具有直接同一性的消费。活动对人的形塑
消费在社会发展中主导作用的凸显,使其成为人的活动及能力发展的主要载体,进而从整体上形塑了人。实际上,消费在社会发展中主导地位的凸显是由资本逻辑的发展决定的。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积累重心已由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如何发现和刺激消费,成为资本实现自身价值增殖的关键环节。由此出发,资本便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了消费领域。资本逻辑正是通过将消费塑造为社会的主要认同方式和控制机制,来达到价值增殖的目的。消费,一方面作为认同方式促进了人的活动及能力的自由发展,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控制手段加剧了人的活动及能力的受控性。因此,它从整体上形塑了人的活动及能力,导致了人的活动及能力的悖论式发展,造成了自由的人的消失。
作为认同方式,消费促进了人的活动及能力的自由发展。消费所具有的区隔性和建构性,不仅为差异化、个性化和多样化生产提供了可能性,而且成为个体躲避外界压力和进行自由活动及发展能力的可能性路径。第一,消费方式的改变促进了弹性化定制化生产的出现。这种生产方式的改变,增加了劳动者的闲暇时间,使其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自由地活动及增进自身的能力。第二,消费活动,作为一种新型的认同方式,重构了社会的阶层,进一步冲破了阶层对人的活动及能力发展的限制,推动了其自由发展。
作为控制机制,消费造成了人的活动及能力发展的受控性。消费作为一种控制机制,主要体现在重塑社会文化心理和社会控制手段上。第一,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如“我消费故我在”“消费即自由”等信条,将人的活动及能力的发展狭隘地限制在消费活动上,进而呈现出单一化的特征。第二,作为一种新型控制手段的消费,强化了社会对人的控制,进一步限制了人的活动及能力的自由发展。作为控制手段的消费,不仅扩大了控制的范围即由肉体到头脑,由宏观到微观,而且还增强了其控制力度即由强制实施到自愿认同。因此,在这种机制的运作下,消费社会一方面按照其意愿塑造出一个又一个合格的消费者,另一方面又使自身成为一个完善的全景敞视监狱,使身在其中的人们无处可逃,进而导致了人的自由的消失。
(三)消费意识形态② 消费意识形态,主要是指在现代媒介技术的中介作用下,通过各种手段将“我消费故我在”等消费主义观念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操纵人的需要。对需要的操控
资本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性质,“把社会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一定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说成是一般的、永恒的形式,说成是自然的真理,而把这种生产关系说成是社会劳动的绝对(而不是历史的)必然的、自然的、合理的关系”③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85页。,就使“资本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成了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因而“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正是通过这一特质,资本逻辑塑造了消费意识形态,从而实现对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控制,进而操控人的需要,将其塑造为满足资本增值逻辑的虚假需要。也就是说,在消费意识形态的作用下,人的真实需要与虚假需求之间的界限模糊,一切需要都被同质化为消费的需要,“社会要求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作抑制性的发展,个人的需要本身及满足这种需要的权利就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于凌驾其上的批判标准”①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进而导致需要发展虚假化。
从需要的产生来看,虚假的需要并不是人的自发内在需要,而是由外部力量强加给个人的需要。这种需要本身实际上一种抑制性的需要,因为它是人们被动接受的需要;从需要的目的来看,虚假的需要满足的并不是人的真正需要,而是资本增殖的需要。这种需要本身实际上是对人的真正需要的压制,因为它以资本的需要取代了人的需要。因此,消费社会中,无论需要的产生还是目的来看,其发展都是消费意识形态操纵的结果。而时尚的出现,就是消费意识形态操控人的需要最典型的例子。在时尚哲学中,我们需要某物并不是指我们对其实际的使用价值有所需要,而是指我们对某物所代表的地位象征意义和品味审美价值的渴求。时尚中的需要意味着“应被需要”,即“在这个一项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既不是消费者也不是被消费物,而是消费的幻象和作为消费艺术的消费。”②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这些恰恰表征了人的需要的真实性的消失。
(四)符号逻辑对个性的重构
消费社会中符号逻辑的出场,重构了人的个性。究其本质来说,资本逻辑决定符号逻辑,而符号逻辑只是资本逻辑在消费社会的最新出场形式。因为无论是从构成符号价值基本范畴的符号价值和象征价值来看,还是从构成符号价值主要内容的符号交换的差异逻辑和象征交换的抽象逻辑来看,它们都是由资本逻辑决定的。因为它们都是资本增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共同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向前发展。
一方面,消费社会中,由符号交换的差异逻辑所表征的人的形式个性③形式个性,指的是通过外在符号表现个性的形式。如月光族和布波族的形式个性就完全不同。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因为不同体系中符号所指的意义千差万别,所以人们会因选择及表征方式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形式个性。另一方面,由象征交换所表征的抽象逻辑导致了人的个性发展的同质化。这种抽象逻辑,实际上是把能指与所指的对立转化为意指的过程。而其中符号所代表的是“能指与所指辩证统一的表意符号,这一符号并非与实在一一对应,即商品的意义并非由其用途来规定,而是与符号系统内部的相互差异和秩序相联系。”④高亚春:《符号与象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这种表意的抽象化和单一化必然导致人的独特性的消失。
三、悖论的超越与人的解放
前文中已经指出,资本逻辑在消费社会发展形式、表现形式、控制形式及出场形式的新变化是其主要根源。既然如此,消费社会中人的发展悖论究竟如何超越,而人的解放又何以可能?实际上,这两个看似不同的问题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因为人的解放就是超越人的发展悖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解放的实现,始终是在现实的实践语境中产生的。“现实的个人”,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那样:“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一旦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人的实践活动,就是人的解放的前提。因此“任何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本身”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也就是说,人的解放问题就是“现实的人”以实践的方式超越人的发展悖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问题。具体到消费社会的语境中来看,这种解放的可能性路径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破除物对人的全面控制,实现人的社会解放
在消费社会中丰盛物的包围中,人在物化关系中愈陷愈深,沦为物体系控制的工具,加剧了人社会关系的物化发展,导致了人的社会关系发展的悖论,阻碍了人的解放的实现。为此,必须破除物对人的全面控制,回归人与物之间正常的关系,使得人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主体,才能实现人的社会解放。而这则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前提和基础。
从本质上看,人的社会关系的物化发展,就是工具理性的过度发展导致的。因此,破除物对人的全面控制,就要重构理性本身。而重建理性本身,重要的是重建好这样一些理性:一是生态理性。生态理性主要指“生态地和整体地看待世界和生命,看待人的存在和世界的存在,并整体地和生态地去生存的思维视野、思维境界、思维取向和行动原则”①唐代兴:《生态理性哲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页。生态理性的提出,是为了应对工具理性过度扩张导致的生态危机和人类自身存在危机。倡导生态理性,就是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倡导有限度的和谐生活。二是公共理性。消费社会中工具理性和形式化管理结合在一起,以大众传媒等技术手段为中介,牢牢地控制着人的一切(甚至包括人的无意识领域),将人驯化成资本逻辑发展的一个环节。公众不需要思考,只需要按照广告宣扬的方式来进行生活就够了,公共理性被大众的集体无意识所取代。因此,必须重建公共理性。重建公共理性,就是重建起公共生活对个人独立性的保障作用和公共伦理对私人道德的促进作用。三是恢复价值理性。价值理性就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其它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②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6页。恢复价值理性这一说法的提出,是为了应对价值理性的日趋边缘化态势。因为工具理性的泛滥和高扬,带来了价值理性的衰落,并且由此导致人的发展的虚无化、单一化和片面化。因此,恢复价值理性,就是重新找寻生活世界的意义和价值,重新确立起理性的价值维度,并以此来破除物对人的全面控制。
(二)消除消费意识形态的幻觉,实现人的政治解放
消费意识形态的确立,将消费建构为一种价值体系,即将消费视为人确证自身和获得自由的唯一手段,将消费自由视为其他自由的前提和基础。消费自由取代了政治自由。政治退出了个人生活,政治自由让位于消费自由。只要能够自由地进行消费,那么其他一切的自由也都无足轻重。人们沉浸在消费意识形态所营造的自由幻觉中不能自拔。但是这种所谓的自由背后,隐藏着消费社会对人的控制形式的隐蔽和个体政治自由的消失。消费社会以一种“貌似自由的、超快捷的控制形式”取代了原来社会旧有的惩戒形式,以一种连续的、每时变化的、自动变形的造型取代了原来社会对人固定的、特定的监视模式。
为此,鲍曼指出,“在今天,任何真正的解放,它需要的是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③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8页。。具体来看,消除消费意识形态的幻觉,实现人的政治解放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唤醒作为消费者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正如马克思将无产阶级视为人类解放的主体一样,只有通过呼唤无产阶级主体性的回归,才能发挥无产阶级变革的革命性作用,才能实现人的政治解放。虽然在消费社会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貌似已经消失了。“被注意的二次剥削中,所产生的关系是工人阶级在流通领域中作为资本的购买者群体出现,因此也产生了没有阶级的表象。”④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商品美学批判》,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6页。只是表象,为此更需要唤起身为无产阶级的意识自觉,打破消费社会意识形态营造的平等自由的表象,实现人的政治解放。
第二,超越消费社会虚假时间观。作为社会规训的主要手段,时间还可成为人类摆脱限制的重要途径。自由的真正可能性就在于获得自由时间。在消费社会中,诸如拟像时间和景观时间的出现恰恰符合了“消费神话”的要求,强化了消费社会对人的控制,导致了规训的隐匿,造成了人的政治自由的消失。因此,为实现人的政治解放,必须对其进行超越。
第三,构建真正的共同体。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政治解放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进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建立起真正的共同体。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人才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人的政治解放才能彻底实现。尤其是在消费社会中人们貌似通过消费获得表面自由平等的当下,人的参政热情日益降低的当下,构建起以联合起来的自由自觉的人类活动代替单一同质且异化的消费活动的真正共同体显得格外重要。
(三)扬弃符号逻辑对人的异化,实现人的精神解放
符号逻辑主要指资本逻辑以符号的形式在社会和人的发展中起支配作用。符号逻辑的出现,加深了人的异化:一方面,符号逻辑导致了人自身存在的符号化。人自身存在符号化是指人被整合进消费社会的符号体系中,成为一种功能性的商品和地位的象征,导致人自身存在的商品化景观化,导致了人的自我价值的失落,加剧了人的精神世界的空虚。另一方面,符号逻辑导致了人的情感的符号化,“在关于真诚的工业文化之中,被消费的还是真诚的符号。而这种真诚再也不像存在及表象的记载中那样与无耻或虚伪对立。在功能关系中,无耻和真诚互不矛盾地在同一种符号操纵中”①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页。,加剧了人的精神世界的失落。基于此,只有扬弃符号逻辑对人的异化,才能实现人的精神的解放,进而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全面发展。
为此,扬弃符号逻辑对人的异化,需要做到:第一,重构真实的自我定位体系,扬弃符号逻辑对人的精神同质化的控制。以消费社会中人的身体的符号化进而导致人自身存在的景观化商品化为例。扬弃符号逻辑对人的异化,就必须做到正确地认识到:身体虽然是人的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但却不是人的全部,也不能代表和反映出人的精神价值,更不能被整合进消费社会的符号逻辑中,自觉地充当起符号逻辑谋杀人的精神生活的同谋。
第二,理性对待由现代媒介技术构建起来的广告话语体系,回归真实多彩的精神生活,扬弃符号逻辑对人的精神世界丰富性的扼杀。现代传媒技术将整个真实世界包装为由各种广告所建构起来的影像世界。“这个设计的幕后人员向前所表现的各种形象会以剪影的样子通过背景的各种人造光线,投射在洞穴的后壁上,展现出各种偶像的形象。囚徒身上的枷锁只是附属物,但是却令人神往,即便没有其他的束缚,人们也会坚定不移地将目光投向屏幕。”②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商品美学批判》,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页。在这个世界中,人们似乎只需通过观看就能感受到所有的温暖和美好,人们似乎只需通过接受就能获得所有的幸福和满足。人们沉浸在大众媒体所描绘的迎合广告性和与娱乐性的幻想世界之中。因此,消费社会中人的精神世界不但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反而在无休止的消费中不断退化,变得萎缩了。
正如马克思所说:“‘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因此,探寻消费社会中人的解放问题,始终要立足于消费社会这一具体的历史语境。只有把握住作为消费社会主导逻辑的资本逻辑,才能更好地理解消费社会中人的悖论式发展的原因,进而找出实现人的解放的可能性路径。也就是说,要实现消费社会中人的解放,就必须立足于现实的实践,超越人的发展悖论,从而实现对资本逻辑的全面超越,最终确立人的解放的可能性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