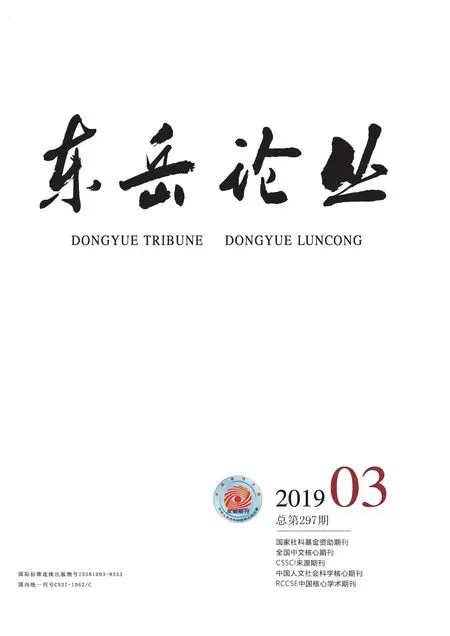毛泽东革命话语的现代性维度
张 明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210046)
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权力话语,革命席卷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切现存的社会秩序都必须置于革命的审判台上接受评判。革命也因此成为衡量中国20世纪社会进步与否的唯一标准,在20世纪中国具备了无比至上的道义优先性。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延续了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谱系——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从洪秀全到孙中山的近代中国革命斗争史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页。,构成了中国近代以来革命史上最为重要的一幅篇章。这不仅因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民族独立解放、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因为这场革命对近现代中国产生了深层次影响——从社会意识、思想文化观念层面改造了近现代中国,并且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延续到当代。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德里克在评述20世纪中国革命与历史之间关系时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对于社会的意识的深化根本上是20世纪初开始的革命变革的产物。”②[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1页。然而,由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在探索性实践中的曲折发展,尤其是伴随着纠正毛泽东晚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所导致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失误,以及“后冷战”时代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在种种非议与责难之中——“告别革命”之声层出不穷,原先作为“热词”而存在的革命似乎在顷刻间销声匿迹,原先作为毛泽东思想核心话语的革命概念以及作为毛泽东时代记忆主题与历史遗产的革命,却成为饱受诟病的批评性对象,似乎在当前历史条件下谈论革命已经成为脱离时代、不合时宜的奇谈怪论。然而,是否“革命”真的已经远离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否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真的如一些批评意见所认为的那样是无任何意义的糟粕?这不仅是毛泽东研究所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而且更是关涉如何总结过去革命实践、如何理解当下建设实践以及如何把握中国未来走向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在学界诸多研究因避免惹上“不合时宜”的“过激”色彩而极力撇清毛泽东研究与革命的关联性之时,国内仍有一批学者从认知性研究视角出发、从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的真实历史境况出发,在历史真实与当代审视相互碰撞视角的指引下展开了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研究。不仅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伟大革命话语资源的当代发掘问题,明确从伟大社会革命的高度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强调党要以勇于革命的精神推动伟大的社会革命①《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599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重新思考“毛泽东与革命”这样一个具有恒久性历史意义的话题,全面而系统分析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纠正学界关于毛泽东革命思想问题上的诸多错误论断,有助于清晰揭示毛泽东革命思想的整体性面貌、为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当代激活及其“出场”某种富有建设性意义的积极思考空间。
一、革命:毛泽东研究“记忆之场”争夺的焦点
当前毛泽东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必须要引入新的视域与角度,这是目前国内学界已经基本形成的一个理论共识。其中,研究毛泽东及其革命斗争的理论与实践构成了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毛泽东研究的主流话语,围绕这一主题形成了大量丰硕的研究成果。但随着对毛泽东研究的“去神圣化”以及“后革命氛围”的强化,革命这一原先充满激情与理想的神圣话语,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为现代化等中性词汇所取代。因而使得似乎在当前现代性话语高涨的背景下再谈论革命已显得陈旧与落伍,革命也据此日益“缺席”毛泽东研究之中而被迅速边缘化。据笔者在CNKI中不完全检索与统计,2018年以毛泽东为题发表的学术论文共计1102篇,而其中进一步以革命为主题的论文仅为49篇,仅占总数的4%左右。这无疑与毛泽东以革命为实践主线索的身份设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间距。并且更为尬尴的是,与主流学术界关于毛泽东研究中革命主题与话语边缘化趋势相对立的是,社会大众意识层面关于毛泽东及其革命实践之间讨论却呈现出持续升温的状况——“毛泽东热”的周期性回潮与革命话语的冷落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②宋婕:《中国革命的现代变奏——毛泽东革命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页。。甚至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那里,关于毛泽东与革命历史的所谓“再认识”“再发现”构成了这一错误思潮歪曲、丑化、否定毛泽东的主要发力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围绕革命建构出毛泽东的思想肖像已然成为当下中国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相互争夺与较量的重要维度,因为不同意识倾向在围绕毛泽东与革命问题上因各自政治立场、利益纠葛、理论偏好等因素的限制,完全有可能达到截然不同的理论结果。之所以会产生如上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的:
第一,革命是承载中国共产主义实践的重要平台。共产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经典作家那里更多地是从理论层面解决这一问题的。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并未能够亲自目睹共产主义从理论向实践转变的完成,这一转变的胜利是由苏联“十月革命”所开启的。中国共产党人推动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从一开始就不是将其作为一种单纯的理论学说而接受的,而是作为一种能够求解中国独立与富强问题的“改变世界”理性工具而接受并加以运用。因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始终带有强烈的实践性与革命性。革命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实践的核心话语,主要由两个方面的原因所共同构成。一是革命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权力话语,通过革命书写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成为一种集体共识。中国共产主义实践作为中国近现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的延续,必然继承了近代以来形成的政治文化基因与集体历史记忆,因为彼时革命已然成为判断社会是否进步的最终标准,一切社会存在都必须置于革命的理性台上进行审判,革命也因而具有了无比崇高的道德至上性。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作为核心主题)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从根本上形塑了革命主题在其中所具有的显著影响。因为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规定性——作为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对偶性存在,还是近代中国意识变革的线索——以反传统循环论历史观而出现的进步史观,它们都共同催生了阶级斗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中国共产主义实践史中的非替代性地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主要是以其唯物史观(历史唯物论)中的阶级斗争学说而被接受、理解、选择和运用的。”①李泽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5页。当然,这里需要区分的一个理论质点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视域中的革命与之前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中的革命概念尽管存在着密切关联,但二者之间仍然具有重要的差异。以往革命在近代中国思想发展史中往往意味着一种革旧布新的进步史观,其存在样态具有多样性——因为只要是对旧的形式(可以是旧思想观念、旧文化、旧统治秩序)的革除便意味着革命,因而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就具备了多元化存在形式,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将1800年至1985年这一广阔的历史阶段都称之为“伟大的中国革命”②[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所谓革命被赋予了新的理论意蕴,这就是以阶级斗争为主宰的全新运动形式。阶级斗争与阶级革命构成了界划中国共产主义实践的重要标准,其也因此成为承载中国共产主义实践的主要记忆载体。
第二,革命是勾画毛泽东理论与实践肖像的核心维度。实事求是而言,毛泽东因个体经历的丰富性,使得他的身份“出场”呈现出巨大的多元性与差异性,军事家、哲学家、政治家、诗人等都构成了描绘毛泽东思想与生平的不同维度。也就是说,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勾画可以从多重角度加以展开,但在上述复杂多元的面相中能否把握住毛泽东思想肖像的总体性特征,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倘若仅从单一的维度或视角出发理解毛泽东,很容易形成对毛泽东身份的固化判断,将毛泽东身份局限为某一方面或某一角色,这其实是研究者基于自身学科与视域偏见而形成的“洞穴假象”。正如有学者所明确指出的那样,“从研究对象的总体性特征看,最符合毛泽东身份定位的就是把他看作革命家和政治家。”③徐俊忠等著:《毛泽东与当代中国——认知性研究的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5页。换言之,能够从总体上对毛泽东理论与实践进行描摹的关键词,在某种意义上只有革命方能承担,这不仅与毛泽东作为革命家的这一主要出场身份密切相关,而且更为关键的是革命构成了毛泽东理论与实践的核心话语与逻辑基础。在毛泽东理论与实践深层逻辑框架内,革命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的理论可以被视为革命话语的总结、凝练与表达,毛泽东的实践可以被视为革命活动的呈现——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维度的不断革命形式。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进行的,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思想政治上的革命,因此,他提出革命要不断向前推进,即“不断革命”理论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9-351页。。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革故鼎新的革命时代的话,毛泽东为世界思想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思路——革命现代性。”⑤李松:《契合与歧异:毛泽东的鲁迅论——兼论毛泽东的革命现代性思想》,《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也就是说,在毛泽东那里,一切理论与实践的价值旨归都可以通过革命与否来衡量,革命构成了刻画毛泽东理论与实践的终极标准。
第三,革命构成了当下如何评议毛泽东及其时代的关键词。尽管毛泽东的个体生命已经消逝,但是他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并未消除,反而在一定条件下呈现出影响不断增强的效应。当下,由于毛泽东本人多面相的存在以及研究主体基于各自不同政治立场、理论偏好与情感纠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关于毛泽东的认知与理解非但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共识性认知与判断,反而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出歧义丛生的多元化存在,尤其是伴随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更是搅浑了大众日常意识层面业已形成的固定化认知与判断。如何评价与认识毛泽东,构成了当前拷问中国毛泽东研究领域乃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政治与理论议题。其中,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革命,构成了当前理解与认识毛泽东的重要切入点,因为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与判断直接催生了关于毛泽东的不同认知路径。为了进一步讨论的方便,这里我们不妨采取一个相对略显化约主义的分析模式,即从对待这一问题的三种不同倾向出发展开相关讨论。一是全盘肯定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及其实践。这一评价模式认为,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具有巨大价值与深远意义,甚至包含他晚年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很明显,上述对待毛泽东革命的理论姿态,直接为毛泽东刻画了一副“善毛”(Good Mao)的形象,无视乃至人为掩盖毛泽东晚年“革命”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无疑存在人为美化与刻意拔高的嫌疑,这与主流意识形态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科学评价之间存在着差异;二是全盘否定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及其实践。这一评价模式通过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若干历史阶段历史细节的拼接、夸大处理,进而得出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不具备任何合理性与进步性的否定性判断,直接为毛泽东描绘了一副“恶毛”(Bad Mao)的形象,这很明显与主流意识形态关于毛泽东功绩是第一位的判断之间严重对立;三是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及其实践。这一评价模式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具体历史情境出发,从中国近现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的宏大谱系出发,在充分肯定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深刻指出其晚年领导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等所谓“革命运动”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很明显,这一评价模式既不拔高也不矮化毛泽东的革命理论与实践,它为毛泽东所刻画的是一副“历史毛”(Historical Mao)的形象①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的上述三重划分,主要受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齐慕实(Timothy Cheek)教授在南京大学相关讲座的影响,特此表示感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何认识与评价毛泽东的革命理论与实践,直接关涉如何描绘毛泽东思想肖像的问题。革命构成了当下不同力量争夺毛泽东解释权与话语权的核心,而对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科学勾画的关键就在于进行这种革命记忆之场的争夺。因为革命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革命的当事人也大多已经逝去,革命的细节与记忆也随着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而相对模糊,所以,在毛泽东与革命问题上就具备了可以被建构与反建构的争夺空间。
二、现代性:毛泽东革命话语的理论内核
既然革命构成了当下毛泽东研究“记忆之场”争夺的焦点,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理解毛泽东革命思想的理论规定性,这是相关研究者都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不同学者从不同维度对毛泽东革命思想的轮廓进行了描绘,有的从纵向不同历史阶段出发描绘了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还有从横向不同内容与形式出发描绘了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等等。尽管从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出发可以比较清晰地勾画出毛泽东革命理论的基本面貌,但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上述两个维度紧密相连,难以做到泾渭分明的区分,纵向界分里面始终存在着横向界分中相关因素的纠缠。因此,如何实现上述两个维度的协调统一,这是考验目前毛泽东革命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不妨参考宋婕教授《中国革命的现代变奏——毛泽东革命思想研究》一书的操作方式,即打破传统横纵区分的研究范式,以现代性为中轴勾连了毛泽东革命理论的不同阶段、不同维度,为毛泽东革命理论勾画了一幅较为立体而丰满的思想图景。
第一,政治革命是毛泽东走向现代性的原初动力。中国现代性的开端并非如西方一般是基于自身内部因素作用的“内生型”产物,而是在殖民主义现代性侵略、扩张的历史背景下以被动姿态卷入到西方现代性浪潮之中的无奈选择。纵观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其中一根不变的“红线”便是所谓持续不断进行的“古今中西”之争。“古今”就是中国“本位文明”的前现代属性与现代性之间的“间距”问题,而“中西”就是西方现代性浪潮对于中国旧有文明形态的内在冲击及其引起的后续综合效应。上述构成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热题”的争论,究其实质而言,实际上彰显了一种焦虑的心态,即一切前现代文明形态遭遇西方现代性扩张所带来的复杂心理感受——共同焦虑。而之所以产生焦虑的关键原因就在于,西方现代性不仅是作为一种西方的文明(中西维度),同时又彰显了一种现代的文明形态(古今维度)①丁耘:《儒家与启蒙——哲学会通视野下的当前中国思想》,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6页。。可以说,现代性问题构成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几代人都致力于求解的元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经过曲折的探索与艰辛奋斗,最终走向了通过共产主义革命实现中国现代性的政治革命道路。通过政治革命途径求解中国问题,成为毛泽东走向现代性的逻辑起点。毛泽东选择的政治革命道路既不同于西方一般意义上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路径,也不同于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代表、以苏联“十月革命”经验为样板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政治革命路径,而是深刻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规定性与中国特殊历史实践个性化冲动之间所形成的复杂多变的张力关系格局。具体而言:一是将“夺取政权”视为政治革命的中心任务,而这一任务的实现必须要依靠枪杆子的力量、依靠农民阶级、土地革命和统一战线的共同作用;二是将“党-军-民”三位一体关系视为政治革命的模型,其中政党是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工具,军队是战斗队、工作队与生产队的三者合一,民则构成了政治革命的主体与最终落脚点;三是将新民主主义理论中的价值理念与斗争策略视为政治革命的现代图样,其中,政治革命的目标即是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而农村包围城市仅仅是实现政治革命的斗争策略②。
第二,经济革命是毛泽东应对沉重现代性压抑的重要工具。尽管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人民开始了以一种自主性姿态重构自身现代性问题的新历程。但由于中国在物质生产与经济发展等方面所呈现的巨大落后性——现代化正是作为现代性物质层面的最显著形式,使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时刻面临着“落后的焦虑”与时刻提防被开除“球籍”的紧迫感。因此,“‘打破常规’是和平时期毛泽东‘革命’概念的另一种表达,是毛泽东‘经济革命’的核心话语。”③宋婕:《中国革命的现代变奏——毛泽东革命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5-150页,第153页,第208页为了实现在经济革命领域内的跨越式发展,毛泽东将农业集体化与合作化视为“从渐进到跃进的革命型经济发展路径”。为了从理论层面为经济革命的跃进式发展提供话语支撑,毛泽东重申了所谓积极的平衡观,即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只有不断地打破平衡才能推动事业的发展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351页。。当然,经济革命始终是在特定制度领域内加以推进的,而毛泽东认为,经济领域的跃进式发展必须打破旧制度、旧框架的束缚,从而创造出不同于苏联模式所规定的僵化、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此,毛泽东主要围绕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求索之路。一是通过重归“延安经验”(双重领导下的全面动员、全民参与)、虚君共和思想以及“两参一改三结合”等改革非常规路径下的经济管理体制;二是通过创制“工农商学兵”结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为经济革命提供新型制度模型与价值目标。其中,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毛泽东那里,人民公社既是实现经济革命的重要手段,又是完成经济革命的价值旨趣。因为他认为,人民公社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提供了重要支撑,并且这种支撑主要是建立在人民公社“大办工业”的基础之上,这一发展战略为求解中国现代性的困境与压力提供了突破性尝试。“在这一过程中(人民公社“大办工业”——引者注),农民得以真正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主体而不是看客。”⑤宋婕:《中国革命的现代变奏——毛泽东革命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5-150页,第153页,第208页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后来人民公社“去工业化”的政策调整无疑是釜底抽薪,它将人民公社划归为纯农组织而丧失了其本应具有的推动工业化的功能,使其最终陷入困境而走向终结⑥徐俊忠,苏晓云:《“去工业化”与人民公社的困境》,《现代哲学》,2009年第5期。。
第三,文化革命构成了毛泽东求解现代性困境的方略。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性之弊病——诸如主体客体化、工具理性化以及官僚科层制等,一方面是毛泽东在领导经济建设时着力避免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是伴随经济理性化进程中自发出现的产物。二者之间呈现出的共生型矛盾对毛泽东的经济革
②宋婕:《中国革命的现代变奏——毛泽东革命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0 5年版,第8 5-1 5 0页,第1 5 3页,第2 0 8页。命战略产生了严重挑战,如何求解上述问题构成了毛泽东在建国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不得不着重思考的一大问题。革命与生产之间似乎出现了某种难以调和的非平衡性,二者似乎陷入了某种两极对立的僵化局面,抓生产建设必会导致革命激情的消却,而紧抓革命又必然会导致生产的偏废。经济革命领域所面临的现代性困境急需从另一种维度加以突破与整治,而毛泽东将求解这一问题的视角转向了文化领域。在毛泽东看来,所谓政治革命只能完成民族国家的重构,经济革命也仅仅是从客体层面推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只有文化革命才能完成整个社会成员的心理重构,从而更能巩固新生社会秩序、巩固生产发展。在此背景下,“抓革命促生产”成为毛泽东内在的必然逻辑选择,这里所言的“革命”主要不是政治与经济革命,而是涉及到灵魂深处的文化革命。为此,毛泽东进行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探索性实践:一是重构了当代中国的文化权利格局,一改以往精英文化的霸权主义逻辑,将文化的领导权与话语权还给普罗大众;二是以马克思主义改造大众文化,尤其是对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文化领域的主流地位,成为整合大众文化领域的核心话语;三是大力弘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主义,通过灵魂深处的“斗私批修”以重构国人的伦理道德与价值观念。从上述层面来看,文化革命构成了毛泽东求解中国现代性困境与现代化难题的最深层、最彻底的努力①宋婕:《中国革命的现代变奏——毛泽东革命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98页。。
三、重思革命: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当代审视
诚然,毛泽东晚年确实在革命问题上走向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误区,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造成了不利影响。也正因为如此,在毛泽东之后的时代尤其是伴随经济理性化进程的加剧,革命也慢慢退居于人们记忆的深处,而在个体作为原子化般“经济人”的存在方式下——以追求主体利益最大化为价值旨归,又必然催生人们不愿意再次触摸、回忆革命及其年代。在上述背景下,毛泽东革命思想在学术研究与大众生活中遇冷也似乎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可解释性,这一方面因为毛泽东晚年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失误导致了全盘否定毛泽东整体性革命实践的倾向,另一方面因为“后革命氛围”下经济理性化进程必然催生崇高的消解与革命退却的尬尴。然而,随着毛泽东时代的渐行渐远——提供了相对较长的审视距离,特别是随着历史当事人的逐渐逝去——使得研究得以摆脱主观情感因素的纠葛而达到较为理性客观的程度,尤其是在当下社会历史发展境遇与毛泽东革命时代呈现出巨大差异性与对比性之时,为重新思考毛泽东的革命思想提供了较为宽阔与理性的空间。在当代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必须正确处理如下几个基本问题。
一是重思毛泽东革命思想的科学理论原则问题。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横跨了毛泽东一生,倘若将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描绘为一副宏大历史画卷的话,很明显,这幅历史画卷的底色应当是由革命所构成的红色,因为革命在毛泽东那里具有无比至上的崇高性与优先性。但是,在对待毛泽东革命思想的问题上,应当树立科学的理论态度,即坚持毛泽东革命思想的整体性与阶段性区分的科学态度。也就是说,尽管革命横跨了毛泽东的一生并成为定位毛泽东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基准线,但对于毛泽东革命思想的研究必须坚持具体的历史的态度,进行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分析与评价。对此,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两种极端化错误倾向:一者是基于毛泽东晚年发动“文革”的错误而从整体上否认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历史意义与价值,甚至采取过度联想的方式将晚年革命错误还原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二者是以绝对化态度承认毛泽东革命思想的意义,否认毛泽东晚年在革命问题上存在任何错误,甚至人为拔高晚年文革的理论与实践。上述两种理论姿态都是以绝对化、片面化思维对待毛泽东的革命思想,未能正确区分作为革命话语的理论与具体历史阶段革命实践之间所形成的复杂张力关系,未能具体历史地分析不同时期毛泽东革命理论与实践的性质及其评价问题。正确的理论姿态应当是:科学划分毛泽东革命思想的不同历史阶段,从总体上肯定毛泽东革命思想的意义与价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在此基础上也不回避毛泽东晚年在“文化革命”问题上所犯下的错误。当前历史条件下,重思毛泽东革命思想的立足点主要不是为了回到“革命年代”——因为历史前进的车轮已经证实和平与发展构成了当代世界的主题,这种理论上的重新思考也不是为了通过揭露毛泽东晚年“文化革命”的错误以实现鞭笞、否定毛泽东的意图,而是在立足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历史性实践的背景下,通过总结发掘毛泽东革命思想中的理论瑰宝、总结晚年革命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以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理论启示。
二是如何安置现实主义语境下革命理想主义的冲动问题。诚然,纵观毛泽东的一生,革命的理想主义激情抑或乌托邦的冲动构成了其显著的特质,理想主义的激情与冲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得以在前现代历史境况下整合社会政治共识、动员革命力量,不断完成系列革命目标的重要保障所在。乌托邦理想的灌输与教化功能不仅仅存在于革命战争时期,而且在毛泽东“不断革命”理念的指引下自然延续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性试验之中,并内化为毛泽东时代求索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重要结构性要素,这种乌托邦的信仰与理想主义激情在国外学者那里甚至直接构成了“毛主义”的本质特征所在①[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张宁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但必须要承认的是,这种革命的理想主义激情在毛泽东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性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消极作用,因为它脱离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历史情境,以理想取代、剪裁现实,最终走向了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相结合的误区,急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型,在理论与经验准备不足的基础上必然会导致转向对革命战争年代经验的依赖。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正确处理了革命主义理想与现实主义实际之间的恰当张力关系,总结了毛泽东晚年在求索中国现代性问题中凸显出的过分理想主义弊病——“价值迷、事实盲”(韦政通语)②韦政通:《毛泽东的性格与命运》,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363页。,即过分侧重于马克思主义所预设的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之替代方案的社会主义理想,并以急切的心态在无视客观历史局限性的基础上强力推行这一理想化方案,而无视在理想与现实矛盾性条件下造成的困境问题。但随着市场经济理性化程度的增强,却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即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盛行与革命理想主义退却的尬尴。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资本现代性逻辑冲击下社会主义的理想共识究竟能够在大多程度上能够达成,社会政治资源的整合与动员能力又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能够保障社会主义现代性方案的成功建构,这些都构成了后革命氛围下乌托邦理想究竟应当如何安置的重大问题。德里克认为,应当以新的方式来理解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想象未来的可能性方案,它将乌托邦的冲动转向对当前压迫和不平等问题的关注,而这无疑构成了解放的真正含义③③胡大平:《后革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德里克“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6页。。倘若从广义上将毛泽东的革命理解为一种不断变革的无止境分裂的矛盾过程,亦即意味着一种不断趋向“新”的动态变化过程。那么,毫无疑问,其对于在市场经济浪潮之中的当代中国现代性困境的求解,以及对于现实主义语境下理想主义激情的安置等问题都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三是毛泽东革命思想历史遗产的当代发掘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当今世界已经步入后革命时代,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已经显得落后、陈旧并且与时代主题已然脱节。因此,重温毛泽东的革命思想于理论和实践都不具备任何价值与意义。对上述观点,笔者不敢苟同。诚然,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与理论从表面上而言,确实与当下的具体历史实践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空间。但摒除具体的结论与观点不谈,从抽象的方法论层面而言,毛泽东的革命思想与当下具体实践之间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毛泽东革命的历史遗产仍然存在进一步发掘与探索的空间。诸如,在当下毛泽东(晚年)革命理论与实践饱受诟病的不利条件下,国外有学者明确提出应当具体历史地分析毛泽东革命理论的价值与意义。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针对修正主义历史观居于“主流”地位时,国外主流学者的目标就是在为革命的批判性守护中发出针锋相对的声音①George Benton;Lin Chun.Was Mao Really a Monster?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e Unknown Story,Oxon:Routledge,2010,p.6.。国外学者为毛泽东革命思想进行辩护,除了一些左翼学者坚定的“理论情结”之外(全面肯定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尤其是晚年的革命理论与实践,认为以文化革命为代表的毛泽东的思想为抵抗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大部分主流学者都是从客观历史层面出发展开严肃认真的学术探讨,他们辩护的目的是为了维护革命在毛泽东思想肖像勾画中的合法性地位,为了维护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历史性价值与意义,以客观历史性姿态拒斥对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妖魔化处理。正如齐慕实教授所言,“虽然不再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加深了我们对现当代中国的理解,但是对革命问题兴趣的转移却可能在我们理解中国、包括理解中国当下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引起曲解和误读的风险。”②(加)齐慕实:《“革命”作为历史话题的重要性》,《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10期。当然,除了从宏大历史叙事层面出发对毛泽东的革命思想进行批判性辩护之外,还有学者从具体微观视角发掘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当代价值与意义,诸如哈佛大学的裴宜理教授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裴宜理认为毛泽东游击战理论与当代中国治理之间关系存在密切的关联,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中所呈现的“游击政策风格”(Guerrilla Policy Style)集中凸显了“拥抱不确定性”(Embracing Uncertainty)对于“适应性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所具有的重要意义③Sebastian Heilmann;Elizabeth J.Perry.Embracing Uncertainty:Guerrilla Policy Style and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in Sebastian Heilmann;Elizabeth J.Perry(ed.).Mao’s Invisible Hand: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1-25.。很明显,这一研究倾向从直接意义上构筑了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当代“出场”形式、发掘了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当代价值与意义。毛泽东的革命话语、革命思维以及革命行为等,仍然或隐或现地支配着当代中国最普通层面的大众日常生活与意识,这也是国外有学者将其称之为“日常生活的毛主义”(Maoism of Everyday Life)的主要考虑所在④。
概言之,革命既是毛泽东本人书写其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范式,也是后人勾画毛泽东思想肖像的重要中介。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并未随着毛泽东及其革命时代的远去而消逝,也未因毛泽东晚年在革命问题上的失误而被全盘否定,相反,它仍然是一座有待进一步发掘与开放的学术富矿。如何回到毛泽东的时代具体历史地定位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如何在现代化语境中科学处理革命的激情与现实主义话语之间的张力关系,如何发掘毛泽东革命思想这一历史遗产中的合理之处为当下现代化建设所用,仍然是有待学界同仁进一步追问与探索的开放性问题。④[加]齐慕实,张明:《毛泽东与毛泽东研究的当代境遇及其展望——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齐慕实教授访谈录》,《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