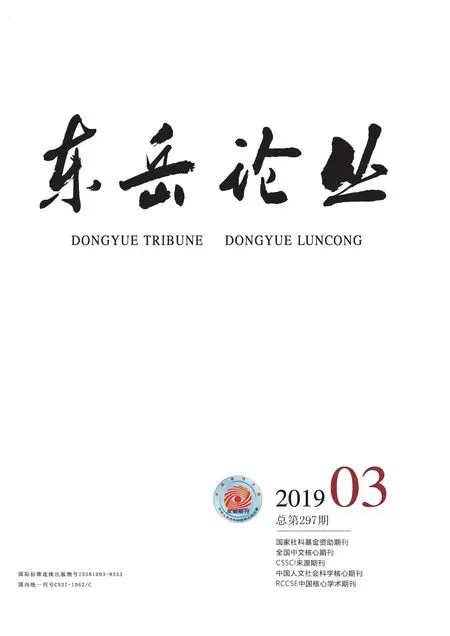论蒋光慈的革命文学创作与侠文化
陈夫龙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一
蒋光慈对黑暗社会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与体验,他的内心深处早就埋下了不平和反抗的种子,同时也萌蘖出自由和解放的希冀。现实中的蒋光慈以其真实行动向黑暗社会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挑战,同时他以血与火浇铸的革命文学创作书写着诗学正义,使他的文本世界成为刺向黑暗社会的复仇利刃,宣泄着时代的反抗意志和复仇情绪,鼓吹着暴力革命,张扬着革命尚武精神,从而使社会正义和社会公道得以伸张与维护。这充分说明特定时代的社会思潮和蒋光慈的侠文化心理取得了精神沟通与价值耦合,他的复仇精神、反抗意志和革命尚武精神在大革命的时代洪流中找到了现实释放的平台。
蒋光慈以一颗桀骜不驯、热血爱国的心灵感受着大革命时代的脉搏,以强烈的现代理性和崇高的革命理想来迎接与拥抱这个黑暗如磐却激情燃烧的时代。于是,“蒋光慈运用他从莫斯科取回来的马列主义,发自内心地提倡与黑暗社会进行斗争的文学,提倡反抗的革命文学。他毫无掩饰地公开声明,自己不做一个政治家,要做一名革命文学家,要当中国的拜伦,去为祖国为人民征战一生,洒尽最后一滴鲜血”!①吴腾凰:《蒋光慈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页。与同时留学苏俄的刘少奇、任弼时和肖劲光等人选择职业革命的道路不同,蒋光慈最终选择了革命文学创作来作为自己从事革命工作的方式,他宁愿做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吹鼓手,他坦诚地说:“我只是一个粗暴的抱不平的歌者,我但愿立在十字街头呼号以终生!”②蒋光慈:《鸭绿江上·自序诗》,《蒋光慈文集》(第1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版,1982年版,第87页。可以说,蒋光慈是在以文学的方式为广大底层民众打抱不平,伸张革命正义,捍卫社会公道,可谓以笔行侠或以文行侠的现代革命之侠。“在这样革命思想的启蒙时代,蒋光慈乃是把马列主义的鲜明的旗帜插到文艺园地上来的旗手。”③黄药眠:《〈蒋光慈选集〉序》,《蒋光慈选集》,北京:开明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综览蒋光慈的创作,可以发现他的革命思想发展变化的轨迹。他在马列主义革命思想指导下,在创作中大力发掘侠文化精神中的复仇精神、反抗意志和革命尚武精神以及对自由平等与正义公道的追求,并赋予其革命的理想和激情,犹如一把革命的复仇利刃直刺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的心脏,鼓舞着广大革命民众的复仇情绪和反抗精神,使他们认清历史的使命和时代的任务,从个性解放、个人反抗逐渐走向集体主义的革命道路上去。蒋光慈坦言:“我生适值革命怒潮浩荡之时,一点心灵早燃烧着无涯际的红火,我愿勉力为东亚革命的歌者!”①蒋光慈:《〈新梦〉自序》,《蒋光慈研究资料》,方铭编,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显而易见,蒋光慈的文学创作既不同于象牙塔里的闭门造车,也有别于软香巢中的风花雪月,而是肩负着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的革命文学,呈现出鲜明而强烈的政治倾向性、革命功利性和时代进步意义。
从革命的角度来看,蒋光慈是一个自觉承担时代任务和历史责任的作家,他的创作堪称革命时代精神的传声筒。正如蒋光慈所言:“朋友们,请别再称呼我为诗人,我是助你们为光明而奋斗的鼓号,当你们得意凯旋的时候,我的责任也就算尽了!……”②蒋光慈:《鸭绿江上·自序诗》,《蒋光慈文集》(第1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87页。这道出了他的革命文学创作的动机和宗旨,这也是革命时代文学的共有特征。具体到蒋光慈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既有革命时代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共同特征,也因他的侠文化精神在小说文本中的艺术投射而呈现出独特的时代精神内涵和现实意义。
二
蒋光慈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个人英雄主义和暗杀恐怖主义相胶合的复仇情节,这是侠文化精神和无政府主义思想耦合纠结形成的侠客式反抗的典型体现。他的小说中的个人复仇或恐怖暗杀成为情节发展的重要关节和推动力量,这与中国共产党提倡的集体革命斗争存在着很大距离。可以说,这与他幼年时代爱读游侠事迹和青少年时期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是分不开的。蒋光慈小时候倾慕朱家、郭解等古代游侠的为人,青年时代渴慕俄国虚无党女侠苏维亚,这种幼年记忆和早期经验以及内心中的反抗精神积聚在创作,就演化成为暗杀复仇的故事情节和叙事动力。
蒋光慈小说处女作《少年飘泊者》的篇首录作者自己的《怀拜轮》诗句为序:“拜轮啊!你是黑暗的反抗者,你是上帝的不肖子,你是自由的歌者,你是强暴的劲敌。飘零啊,毁谤啊……这是你的命运罢,抑是社会对于天才的敬礼?”③蒋光慈:《蒋光慈文集》(第1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充满了强烈的反抗情绪和复仇精神。小说文本一开篇就将主人公汪中——安徽某县一个佃农的儿子,置于极限情境之中:父母因交不起地租被地主刘老太爷活活逼死。陷入生存绝境的少年汪中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他怀着对地主和黑暗社会的刻骨仇恨,开始了四处飘泊的流浪生涯,走上复仇之路。这与传统武侠小说中父母被害——家破人亡——绝处逢生——飘泊天涯——拜师学艺——回乡复仇——惩恶扬善的基本情节极为相似。只不过汪中最终参加了革命,以革命方式向黑暗社会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复仇。汪中从父母的悲惨遭遇中获得了深刻的生命体验,在黑暗的社会中,到处都是冷酷自私,没有点仁爱和光明,穷人只能落得个悲剧命运。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惨无人道、正义公道荡然无存的社会里,法律和制度往往是苍白的,现实中大多充当了统治阶级的遮羞布和保护伞,对穷人而言,实为罪恶的枷锁。当现行法律和制度无法真正做到主持正义、为民作主的时候,现实中遭受不幸和灾难的人们就只有采取以暴抗暴的方式,铤而走险,手刃仇敌,报仇雪恨。但当时的汪中没有反抗的能力和雪恨的本领,只有在想象中实现自己的复仇计划。在父亲惨遭地主刘老太爷的家丁毒打之后,少年汪中的内心燃烧起复仇的火焰:
当时我想到这里,我的灵魂似觉已离开我原有的坐处。模模糊糊地我跑到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径自出了家门,向着刘家老楼行去。……我走向前向刘老太爷劈头一菜刀,将他头劈为两半,他的血即刻把我的两手染红了,并流了满地,满桌子,满酒杯里。他从椅子上倒下地来了,两手继续地乱抓;一班贵客都惊慌失色地跑了,有的竟骇得晕倒在地上。
大厅中所遗留的是死尸,血迹,狼藉的杯盘,一个染了两手鲜血的我。我对着一切狂笑,我得着了最后的胜利……①
这是汪中潜意识中的个人暗杀复仇的想象,彰显出他的复仇欲望和报复冲动,体现了一个孤苦无助的少年对地主恶霸和人间罪恶的强烈抗议,以及誓雪人间不平的愿望,在文本深层寄寓着作者对自由、平等、正义和公道的渴盼。安葬完父母之后,汪中想去投奔桃林村的土匪。他崇拜那些劫富济贫的土匪,想借助土匪的力量,为父母报仇,但途中得知桃林村的土匪已被官军打散,他的复仇愿望也就无法实现,于是继续飘泊于人生的江湖。在作者的情节设置中,无论是想象中的复仇欲望,还是现实中入伙土匪而不得,都意味着侠客式或绿林好汉式的个人复仇不是穷人的最好出路,也不是通往革命的光明大道。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理性的现代革命意识,作者并未让少年汪中付诸个人复仇的实践,而是让他踏上飘泊流浪之途,一步一步地走上革命道路。“他走了相当一段孤独的叛逆道路,身上流注着不惜与命运抗衡的倔强的生命力。他虽然身世卑微,与拜伦以‘游记’为题的长篇叙事诗的主人公处境大异,但他也为社会所放逐,四海飘泊,足迹及于皖、鄂、沪、粤诸地。作者赋予他佃户孤儿、流浪奴仆、乞丐、店员、旧礼教迫害下的失恋者、工人、工运干部、革命士兵等多重身份,从而窥见了乡村及城市、商界及工厂的种种黑暗和罪恶”②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3页,第63页。。在四处飘泊的流浪生涯中,汪中这个生性爱反抗和爱打抱不平的青年终于走上了革命道路。他考入了黄埔军校,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以革命的方式抑强扶弱,仗义行侠,向黑暗社会和不合理的制度复仇。最后,他在攻打惠州城的战斗中英勇牺牲,成就了一个侠义革命英雄的光辉形象。汪中身上有太多的蒋光慈的影子,可谓蒋光慈的人格精神和人生经验在文本中的艺术折射。“蒋光慈虽然追慕拜伦的‘千古的侠魂’,他笔下的汪中甚至心神向往于《史记》记载的朱家、郭解等豪侠之士,带点朱、郭的打抱不平、扶助弱者的侠骨;但汪中毕竟把个人的反抗发展为阶级的反抗,并最终为人民的反帝、反军阀的事业捐躯,他已经跨越了‘拜伦式英雄’的孤独和秦汉时代侠客的偏执,而具有高尔基早期小说中‘流浪汉’人物的平民反抗性”③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3页,第63页。。小说主人公汪中经历了由个人复仇欲望和反抗意志走向阶级对抗的革命道路这样一个鲜明的生命轨迹,完成了他由侠客式个人英雄主义向革命者集体主义的思想转变,带有鲜明的现代革命正义色彩。
小说《鸭绿江上》讲述了莫斯科留学生宿舍内的一席围炉夜话。在高丽留学生李孟汉叙述的他与金云姑的历史中,蕴含着一个国恨家仇和侠骨柔情的故事。李孟汉和金云姑都是高丽贵族后裔,日本占领高丽后,两家老人深愤亡国羞辱和同胞受难,出于民族大义和爱国热情,辞官避世,隐居林泉。从此,李孟汉和金云姑在鸭绿江畔的海滨玩耍嬉戏,两小无猜,感情日笃。李孟汉的父亲被日本当局杀害,母亲投海自尽,他成了一个孤儿,被金家收容,受到金云姑的关心和安慰。但日本当局要斩草除根,李孟汉面临生命的危险,不得不与金云姑痛别,连夜逃离祖国,开始漂泊异邦的流亡生涯。后来,金云姑参加了革命,担任高丽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妇女部书记,有一次参加工人集会,被日本警察逮捕,以煽动罢工的罪名将她投入监狱,最后她屈死于狱中。祖国沦亡,同胞受难,家人被害,爱人屈死,自己流亡异国,这一系列不幸、灾难和屈辱降临到高丽青年李孟汉身上。父亲的民族大义,母亲的义不受辱,爱人金云姑的侠义爱国,金家的义薄云天,都在这个弱国子民的内心深处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同时也埋下了反抗侵略和民族复仇的种子。在莫斯科这块革命圣地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高丽青年,“兼具留苏的革命党人和弱小民族的亡命客双重身份,家室破毁之哀陪伴着民族沦亡之痛,为爱人复仇和为祖国献身表现为高度① 蒋光慈:《蒋光慈文集》(第1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6页。的一致,于沉哀至痛之中透露出执著的理想追求”①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4页,第66页。。这预示着身怀家仇国恨的李孟汉,必将走上为祖国而英勇奋斗,实现民族复仇和解放大业的道路。小说文本中的复仇精神和反抗意志被提升到了民族大义的高度,寄寓着作者对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的深沉思考。
如果说在小说《少年飘泊者》和《鸭绿江上》中,作者对复仇的描写和表现有所节制的话,那么到了后来的许多小说中,则表现出对复仇意识和暗杀恐怖行为的激赏,甚至走向极端的迷狂。
小说《短裤党》“是一首粗糙而响亮的革命暴动者之歌”②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4页,第66页。,在高度的革命激情下充斥着强烈的复仇情绪和反抗意志。该小说叙述了大革命后期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失败情况,而以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作为故事的结局。一九二七年春,为了迎接北伐军的到来,党的领导者史兆炎等人在上海组织发动了总同盟大罢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大罢工迅速升级为武装起义。纱厂党支部书记李金贵在率领工人纠察队攻打警察署的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其妻邢翠英得知丈夫的死讯后,满怀义愤和复仇的怒火,腰间别好菜刀,冒雨独闯警察署,一举砍死了两个警察,她自己也牺牲在警察的弹雨之下。邢翠英的刺杀行为带有盲动性和冒险性,犹如复仇女侠,又像苏维亚一样的虚无党人,她的行刺举动既带有为夫报仇的个人英雄主义特征,又充满了以暴抗暴、血债血还的革命色彩。另一位女性形象华月娟,是党的妇女部书记,倾慕俄国虚无党人的作为,甚至自比为中国的女虚无党人。无论是邢翠英复仇的盲动冒险,还是华月娟以虚无党人自况,都体现了作者强烈的反抗意志和复仇意识,折射出蒋光慈早年深受侠文化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
在小说《野祭》中,章淑君是一位具有侠魂的现代女性,胸怀大义,乐于助人。在革命文学家陈季侠赁居于她家期间,章淑君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和体贴,并对陈季侠产生了好感,心生爱慕之情。但注重相貌的陈季侠反应淡漠,章淑君求爱未果。她压抑着内心的痛苦发愤阅读革命书籍,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逐渐成长为革命女战士。陈季侠一见钟情的郑玉弦,不仅不理解他的革命文学事业,而且当反革命政变一来,就对陈季侠避之千里之外。陈季侠终于鄙视这个内心浅薄渺小的女子,逐渐感到章淑君的可爱与可敬。在章淑君被反动当局秘密处决之后,陈季侠买了鲜花和玫瑰酒,来到吴淞口,面对大海,为这颗革命的侠魂举行了深情的野祭,表达了他对章淑君的忏悔和怀恋:“归来罢,你的侠魂!归来罢,你的精灵!这里是你所爱的人儿在祭你,请你宽恕我往日对你的薄情。唉!我的姑娘!拿去罢,我的这一颗心!”③蒋光慈:《蒋光慈文集》(第1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78页,第364-365页。作者不仅以陈季侠凭吊女战士章淑君的“侠魂”的形式,表现出对国民党当局的大屠杀暴行的愤怒抗议,展现了革命语境下犹豫彷徨的进步知识分子在爱情选择中所彰显出来的人格提升,而且更借助小说人物陈季侠之口表达了对国民党统治的深入思考和不满愤懑:
我是一个流浪的文人,平素从未曾做过实际的革命的运动。照理讲,我没有畏避的必要。我不过是说几句闲话,做几篇小说和诗歌,难道这也犯法吗?但是中国没有法律,大人先生们的意志就是法律,当你被捕或被枪毙时,你还不知道你犯的是哪一条法律,但是你已经是犯法了。做中国人真是困难得很,即如我们这样的文人,本来在各国是受特别待遇的,但在中国,也许因为说一句闲话,就会招致死刑的。唉!无法的中国!残酷的中国人!……但既然是这样,那我就不得不小心一点,不得不防备一下。我是一个主张公道的文人,然而我不能存在无公道的中国。偶一念及我的残酷的祖国来,我不禁为之痛哭。中国人真是爱和平的吗?喂!杀人如割草一般,还说什么仁慈,博爱,王道,和平!如果我不是中国人,如果我不同情于被压迫的中国群众,那我将……唉!我将永远不踏中国的土地。④蒋光慈:《蒋光慈文集》(第1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78页,第364-365页。
陈季侠的思考和不满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遭受挫折,跌入低谷。许多革命者和进步知识分子经受着革命幻灭后的痛苦,陷入了迷惘、动摇、彷徨,甚至随时丧失生命的绝境。在法律糟践、世道不公、人道不存、兽道横行的黑暗社会,一切被压迫者只有反抗,才会有更好的命运和光明的前景。章淑君为革命献身的精神、为实现社会正义而斗争的侠魂,使陈季侠接受了一场灵魂的洗礼,坚定了革命的信念,增强了斗争的力量,他在这次野祭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和希望:“这一瓶酒当作我的血泪;这一束花当作我的誓语:你是为探求光明而被牺牲了,我将永远与黑暗为仇敌。唉!我的姑娘!我望你的魂灵儿与我以助力……”①蒋光慈:《蒋光慈文集》(第1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78页,第419页,第415页,第419页。这预示着陈季侠这个革命文人要以章淑君的“侠魂”为激励,奋起反抗。作者的这种探索和昭示,会给苦闷中彷徨、恐惧中动摇的革命者和进步知识分子带来希望的曙光与前进的动力。
小说《菊芬》的主人公菊芬是一个出身于富庶人家的天真、活泼、美丽、纯洁的少女,在男友薛映冰提供的革命书籍影响下,深受革命正义观念的鼓舞,“为着被压迫的人们,为着全人类”②蒋光慈:《蒋光慈文集》(第1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78页,第419页,第415页,第419页。,逐渐走上革命道路。菊芬经历了重庆“三·三一”大屠杀和武汉“七·一五”事变,目睹了血腥恐怖的局面。在严峻而艰难的革命形势下,反动势力日益猖獗,这个满腔革命热情的青年女性于极度的苦闷和绝望中奋起反抗,产生了杀人的念头,她说:
人生总不过一死,死去倒干净些,你说可不是吗?我想我不病死,也将要被他们杀死,不过宁愿被他们杀死倒好些。我现在也不知因为什么缘故,总是想杀人,总是想拿起一把尖利的刀来,将世界上一切混账的东西杀个精光……江霞同志,你想想,为什么敌人能够拚命地杀我们,而我们不能够拚命地杀敌人呢?呵,杀,杀,杀尽世界上一切坏东西!……③蒋光慈:《蒋光慈文集》(第1卷),上海:上海文 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78页,第419页,第415页,第419页。
这种充满恐怖气息的暴力话语发自一个美丽可爱的革命女性口中,似乎不可思议,但如果将此暴力话语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就可以得到一种理解和阐释。在血腥恐怖的年代,面对敌人的屠刀,革命复仇观念会大大激发一个革命者的反抗意志,使一个温柔的女性变得坚强镇定或冷酷无情,义无反顾地走上抗争之路。陷入绝境之中的菊芬毅然决定搞暗杀,试图以这种极端的手段,达到革命复仇的目的。尽管她也意识到了暗杀不是唯一的正当手段,但当时的她作为一个弱女子,实在忍无可忍,除了暗杀,别无选择。最后,菊芬铤而走险,刺杀政府W委员,但没有成功,当场被捕。小说文本中的叙述者江霞在读完了菊芬的信后,深受鼓舞,将菊芬作为效法和崇拜的对象:
我的心火烧起来了,我的血液沸腾起来了……我不为菊芬害怕,也不为菊芬可惜,我只感觉到
菊芬的伟大,菊芬是人类的光荣。我立在她的面前是这样地卑怯,这样地渺小,这样地羞辱……我
应当效法菊芬,崇拜菊芬!我应当永远地歌咏她是人类史上无上的光荣,光荣,光荣……倘若人类历史是污辱的,那么菊芬可以说是最光荣的现象了。④蒋光 慈:《蒋光慈 文集》(第1卷),上海:上海 文艺 出版社,1982年 版,第378页,第419页,第415页,第419页。
毫无疑问,菊芬的个人暗杀行为颇有古代刺客之侠的特点,彰显一派女侠风范。但这种盲动冒险的行为却因作者设置的历史语境和赋予的革命激情,而具有了革命的正义性和历史的合理性,从而使菊芬的暴力话语和暗杀复仇行为也获得了一种历史的理解与同情。
复仇女侠菊芬的暗杀行为,意在以革命的红色恐怖对抗反革命的白色恐怖,反映了蒋光慈在没有找到正确的斗争出路的情况下对革命的情绪化理解,折射出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流行的左倾盲动主义的幼稚病。到了小说《最后的微笑》中,这种盲动冒险和恐怖暗杀情绪更加强烈,甚至主人公在复仇的意念中进入一种迷狂状态。性格懦弱的青年工人王阿贵因在工会做事而被工头张金魁开除,一度陷入生存危机和精神痛苦的绝境。他的胸中燃烧着复仇的怒火,因暴晒得病,在热昏中,为了妹妹日后免受侮辱,差点把妹妹投进池塘溺死,又想去撞汽车,以死换取抚恤金让父母好好生活。工会领袖张应生劝他不要想着消灭自己,要想怎样消灭敌人。在张应生的劝慰和指引下,朴素的求生意志和强烈的生命尊严时时冲击着王阿贵的,经过艰难的精神炼狱,他的反抗意识觉醒了。于是,王阿贵盗走张应生的手枪,开始踏上了暗杀之路。复仇的火焰在王阿贵心中激情地燃烧,他义愤填膺,断然杀死了工会特务刘福奎和工头张金魁等为非作歹、为虎作伥的敌人。王阿贵曾为自己的暗杀复仇行为而困惑,是革命党人沈玉芳的正义伦理原则使他内心坦然而磊落,并感到自己“不但是一个胜利者,而且成了一个伟大的哲学家”①蒋光慈:《蒋光慈文集》(第1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 9 8 2年版,第5 2 1页,第5 4 0页,第1 4页,第6 5页。。这坚定了他暗杀复仇的信念,增强了他反抗的动力。王阿贵在枪杀工贼李盛才之后遭到了巡捕们的包围,但他临危不惧,从容自杀。王阿贵虽然死了,“但是在明亮的电光下,在巡捕们的环视中,他的面孔依旧充满着胜利的微笑”②蒋光慈:《蒋光慈文集》(第1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521页,第540页,第14页,第65页。。诚然,王阿贵的暗杀行为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在一个黑暗的社会里,他敢于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邪恶势力宣战开火的复仇精神和义勇行为,的确能给黑暗中痛苦呻吟却又无法找到现实出路的底层民众带来抗争的勇气和生存的希望。
复仇情绪在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中更是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宣泄,如果说菊芬是一位复仇女侠的话,那么主人公王曼英则成为了一个疯狂的复仇女魔。于大革命后期走上革命道路的王曼英,当过女兵,上过战场,也曾手刃过敌人。在革命进入低潮的时候,她陷入了彷徨、苦闷和迷惘,发生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在看不到革命出路和光明前景的绝境中,她信奉了虚无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其拯救这个世界,不如毁灭这个世界,这种人生信条促使她以扭曲的方式向黑暗社会复仇。“她现在是出卖着自己的身体,然而这是因为她想报复,因为她想借此来发泄自己的愤恨。当她觉悟到其它的革命的方法失去改造社会的希望的时候,她便利用着自己的女人的肉体来作弄这社会……”③蒋光慈:《蒋光慈文集》(第1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521页,第540页,第14页,第65页。于是,王曼英凭着姿色,以自己的身体为武器,在现实中疯狂地捉弄资本家的公子、买办少爷、傲慢的政客、蹩脚的诗人,以此实现复仇的快慰。这种疯狂的非理性行为充分表明了“曼英是在向社会报复,曼英是在利用着自己的肉体所给与的权威,向敌人发泄自己的仇恨……”④蒋光慈:《蒋光慈文集》(第1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 9 8 2年版,第521页,第540页,第14页,第65页。很显然,传统的礼法和伦理道德在她心里荡然无存,她是在利用身体资本力量向整个社会挑战,甚至在她怀疑自己染上了梅毒之后,竟然想用梅毒来毁灭这个让她深恶痛绝的世界。在王曼英向社会疯狂报复的过程中,曾收容过险些沦落风尘的小姑娘吴阿莲,是小阿莲对卖淫行为的痛恨使她动摇了病态的复仇观念。在与革命者李尚志的交往中,她又增强了生活的信心。于是,王曼英这个掉队的革命孤鸿,在疯狂的复仇中逐渐拥有了清醒的理性,她的病态的复仇心理开始有了矫正和医治的可能。在王曼英深陷绝望想到吴淞口投海自杀之际,新鲜的田野风光使她感到不可名状的愉悦,求生的意志被重新唤起,她终于获得了人性的复苏。王曼英开始到纱厂做女工,以满腔热情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特别是当她得知自己并未患梅毒时,更燃起了生命的激情。她最终以健康的身体和健全的灵魂与革命者李尚志重新相爱。王曼英——曾一度被阴云遮掩的年轻的月亮终于冲出重围,获得了革命的新生。
小说《野祭》《菊芬》《最后的微笑》和《冲出云围的月亮》等革命文学作品构成了作者创作的“光慈时代”,这些作品均创作和发表于“四·一二”事变爆发后。当时的中国正笼罩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之下,反革命力量不断向革命力量举起罪恶的屠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民众惨遭杀戮。如何反抗?以何种方式反抗?中国革命道路该向何处去?这一系列严峻的现实问题摆在每一个有良知的革命者面前。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一度沉浸于哀伤、幻灭、动摇和焦灼渴盼、激情奋起这两种情绪思潮相纠结胶合的氛围中。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蒋光慈以革命文学创作的方式表达了他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和对革命出路的探索。在具体创作中,他还创造性地采用了“革命+恋爱”的主题模式,革命题材和恋爱题材相结合,刚柔相济,侠骨柔情,可以说是传统武侠小说侠男侠女模式的现代翻版和创造性转化,“二者的结合表明作家力求克服早期作品的粗而不精,以刚柔相济的手腕探索在历史转折关头,革命青年苦闷和悲愤、迷惘和奋起的精神世界”⑤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9页。。尽管这类作品在艺术情调上带有虚无倾向的偏激和浪漫主义色彩的憧憬,但毕竟体现了作者可贵的时代思考和艺术探索。作为“革命+恋爱”小说的始作俑者,蒋光慈曾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创作潮流,这是他的文学史贡献。更可贵的是,他在“革命+恋爱”小说逐渐走向公式化、模式化的境遇下,不仅认识到该主题模式的流弊,而且以创作本身来参与这种流弊的纠正。这就是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正面描写土地革命的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将农民运动题材拓展为农民武装斗争题材,不仅扩大和丰富了作品的社会内容与思想内涵,而且成功地塑造了工农革命领导者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张进德是作者塑造的工农革命领导者形象,他出身于农村,对黑暗的社会充满了叛逆情绪和反抗精神,仗义行侠,敢作敢为。成为矿工后,他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教育和洗礼,积极从事工人运动,成为工运领袖。为了逃避资本家的迫害,他返回故里,仍然保持革命者的本色,继续战斗。他联系和发动贫苦农民组建农会,被推举为农会主席,宣传革命思想,打倒土豪劣绅,掀起了暴风骤雨般的农民运动。随着时局逆转,新军阀公然背叛革命,支持地主民团下乡取缔农会。在生死攸关之际,张进德沉着冷静,坚强而勇敢,率领民众奋起反抗,解除旧军队的武装,毅然组织了农民自卫队,撤退到三仙山上与敌人周旋。在严酷而艰难的斗争形势和革命考验面前,张进德表现出坚定勇敢、大义凛然和镇定自若的革命侠义风范。在农民自卫队队长李杰壮烈牺牲的情况下,他带领这支农民革命队伍突出重围,向金刚山进发,继续从事武装斗争。革命知识分子李杰,出身大地主家庭,因与农民姑娘自由恋爱遭到父辈的破坏而背叛了地主阶级家庭,考进黄埔军校,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他长期在外求学,逐步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大革命时期,他回到家乡组织农民运动,与自己出身的阶级作殊死搏斗。面对地主集团的阴谋暗杀和反动军阀的镇压,他临危不惧,勇敢地反抗,和张进德一起组建农民自卫队,进行坚决地斗争。经过一番家庭感情和革命义务的搏斗,他终于赞同革命农民的义举,忍受内心的巨痛和精神的折磨,下令火烧李家老楼。最后,李杰在三仙山率部突围时英勇牺牲。临终前,他向张进德嘱托道:“你是很能做事的,同志们都很信任你,我希望你此后领导同志们好好地,好好地进行下去……”①蒋光慈:《蒋光慈文集》(第2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13页。从李杰的遗言中,可以看出他对革命充满了希望。在走向革命的过程中,李杰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和家庭,理性地克制对毛姑与何月素的爱恋,拒绝了父亲的招降书,忍受着大义灭亲的悲痛,不断赢得了农民的信任,完成了他由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逐渐成长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心路历程,体现了他坚定的革命精神和反抗意志。张进德和李杰是蒋光慈塑造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教育下不断成长的革命侠义英雄形象,在他们身上寄托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和革命愿景。与前此“革命+恋爱”小说主题模式相比较,《咆哮了的土地》作出了纠正的努力,主要人物比菊芬、邢翠英和王阿贵等盲动主义复仇者也多了些革命的理性。
毋庸置疑,张进德和李杰领导的农会与自卫队在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上,仍然存在着盲动主义倾向。这一方面或许是土地革命时期斗争局势的现实侧影,一方面是流氓无产者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综合影响下的结果。对于蒋光慈而言,流氓无产者思想是“他自幼迷恋的游侠传统”,小资产阶级思想就是“他青年时期接受的无政府主义”②,正是这两方面的结合,使他的作品经常出现暗杀复仇情节和盲动主义情绪。
三
从整体上看,蒋光慈的小说具有鲜明的自叙传色彩和强烈的复仇精神与反抗意志。他“代表社会的良知,以笔为剑,向一切的社会不平、一切的强权势力、一切的黑暗腐朽挑战,所表现出来的反叛、正义、无私、无畏、自我牺牲等精神品格和干云豪气——这些传统侠义精神的现代承传”①陈夫龙:《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研究述评与反思》,《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都沉潜于他的革命文学创作之中。尤其是《野祭》中的陈季侠、《菊芬》和《弟兄夜话》中的江霞,甚至《少年飘泊者》中的汪中,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可以说是蒋光慈的化身,陈季侠以“侠”命名,江霞也有江湖侠客的寓意,汪中生性爱反抗,爱打抱不平,慨然仰慕抑强扶弱的朱家郭解,这都与他的精神气质和行为特征极为相似。蒋光慈不仅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人格精神熔铸于小说文本肌理,更可贵的是,他能够在生命激扬的浪漫情绪中积极地发掘和张扬复仇精神与反抗意志,并赋予小说文本革命的激情,这对于黑暗中摸索出路的革命民众是一种莫大的鼓舞,有利于激发他们的革命尚武精神。作者以革命文学创作参与现实的革命斗争实践,虽不满当时的左倾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路线,但在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斗争方式时,他的作品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个人暗杀复仇行为就是带有盲动主义倾向的重要体现,这是时代的局限和作者思想的局限。具体到作品中,这种以暴制暴、以恶抗恶的红色恐怖行为体现了革命尚武精神,既表现了革命者对黑暗社会和反动当局的刻骨仇恨,也再现了当时革命局势的一种特点,并因革命因素的加入而呈现出社会正义性与革命合理性。随着现实革命斗争形势的变化和作者革命思想的发展,小说主人公的斗争方式也逐渐摆脱了个人暗杀复仇行为的非理性冲动甚至盲动,而不断走向集体主义的斗争道路。
可以说,蒋光慈的小说“融合了古代侠客、拜伦式英雄、高尔基早期作品中‘流浪汉’的多种素质”,“增添了叛逆者的豪侠气”②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这是蒋光慈在马列主义暴力革命思想指导下对传统侠文化进行现代性改造的结果,他把古代游侠、拜伦式个人主义英雄和中国革命时代特色以及革命尚武精神有机结合起来,赋予小说文本中的复仇情节和反抗情绪以革命激情与正义观念,从而使传统侠文化在阶级革命语境中凸显出鲜明的现代革命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