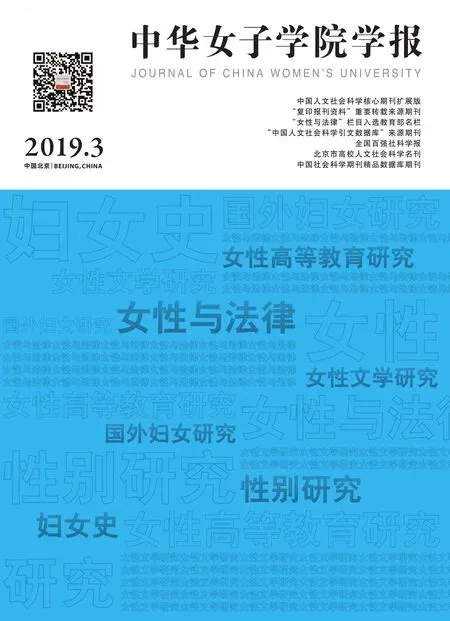普遍主义、差异主义与后现代女性主义
——法国三代女性主义思想之观照
栾荷莎
法国女性主义是世界女性主义重要的一部分,其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普遍主义(Universalisme)、差异主义(Différentialisme)和后现代女性主义(Féminisme Postmoderne)。本文将着重探讨以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为代表的法国第一代女性主义的普遍主义理论主张,以及以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为代表的法国第二代女性主义的差异主义理论主张,厘清两代之间的差异与局限,进而讨论以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为代表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试图超越前两代女性主义的努力。
一、“两代”概念的提出
19世纪末以来发生的两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推动了女性处境的深刻变革,期间出现过多种多样的立场和主张。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在1995年发表的《妇女的时间》(Le Temps Des Femmes)一文中,针对女性运动提出“两代”(Deux Générations)的概念。包括妇女参政运动在内的第一代女性深深地根植于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之中,“渴望在作为计划和历史的线性时间之中替自己争得一席之地”。[1]352这一代女性争取与男性同等的工作权利、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转而拒绝接受习惯上被视为女性的或母性的因而与参与历史格格不入的属性。[1]352第二代女性则几乎拒绝整个线性时间,并对政治产生严重怀疑。“这些妇女对女性心理及其象征体现颇感兴趣,试图赋予那种过去文化充耳不闻的内在主观性的、有形的经验以一种语言。”[1]353克里斯蒂娃所想象在当时的欧洲已经初露端倪的第三代女性的特点,是把男人/女人的二元对立视为形而上学。这里克里斯蒂娃所谓的“代”并非是一种简单的时序,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意指空间,一个肉体的、欲望的心理空间”。[1]367
克里斯蒂娃不是唯一对女性主义进行代际或立场划分的学者。法国学界一般认为,女性主义经历了三代,或者说三股思潮:普遍主义、差异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三代或三种立场跟克里斯蒂娃提出的概念类似。普遍主义把女性特殊性视为社会建构的结果,主张两性在相似中平等;差异主义则反对抹杀性别差异,重视女性的性别特征和身体语言;后现代主义则致力于解构男人/女人范畴的二元对立。
21世纪以来,由于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世界范围内女性主义意识再次抬头并且来势凶猛。对法国三代女性主义思想进行深入剖析,能更好地把握法国乃至西方框架下的女性主义伦理的核心问题,从而对我国的女性运动历史和当前社会现实形成一种有效的观照,对女性主义问题提供更多的思考维度。
二、从波伏娃到西苏:普遍主义与差异主义的代际交替
如果说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发生的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中同时存在普遍主义和差异主义的主张,在第一次浪潮结束后,波伏娃把女性主义最终引导到普遍主义的轨道上来。波伏娃在1949年发表的著作《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中,首先揭示了性别差异深深地根植于生理事实之中,以致看上去不可逾越。根据波伏娃的存在主义伦理观,任何主体都具体地通过计划把自己确立为超越性,但过去女性由于无法节制的生育而被限制在家庭的狭小世界中从事家务劳动,从而被剥夺了超越性。另外,女性一生中的每个阶段,从青春期、怀孕、分娩到绝经期,都伴随着危机甚至事故,这严重影响了女性的超越性。“女人对物种的屈从,她的个人能力的局限,是极其重要的事实;女人的身体是她在世界上所占处境的基本因素之一。”[2]59-60相比之下,男性的生殖功能并不妨碍他的超越性,一旦男人破解了生育的奥秘,女人就注定被赶下台,即恩格斯所说的“女性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3]54
而后,波伏娃意识到这种性别差异中有一些人为的、压迫的、专制的东西在里面。她反对任何生物决定论或本质主义,她把性别看作纯粹的社会建构。具体来说,人们通常认为的女性特征,无论缺陷还是优势,都不源自生理的既定,而是由于其处境造成的,由于其他者的地位造成的。波伏娃摒弃差异主义,认为差异观念是把女性封闭在私人空间和母亲职能之中的借口,会导致等级化和社会排斥。平等只可能在两性相似的范畴内实现。相似是一个和平的观念,而差异是一个战争的观念。普遍主义模式才是女性解放的道路,女人通过参与过去仅限于男人参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来达到与男人的事实平等。在《第二性》的末尾,波伏娃倡导一个超越了性别差异化的理想社会。
波伏娃是第一个在哲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女性,“她支持自由事业,反对自然必然性,促进了避孕和终止妊娠的合法化,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做出了贡献。”[4]而波伏娃的哲学和生活方式在法国乃至全世界有众多追随者,其中一些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性运动中发展了她的普遍主义思想。
差异主义一代并不是在普遍主义一代结束之后才出现的。在法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爆发的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中,普遍主义和差异主义两极已经浮出水面:MLF(妇女解放运动的简称,全称为Mouvement De Libération Des Femmes)中的一些团体坚持不懈地为女性争取更大程度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权利;而另一些团体则对这种普遍主义女性主义的态度有所保留,甚至是提出了相反意见。一个实例很能说明问题:波伏娃联合创建了《女性问题》(Questions Féministes)杂志,该杂志旨在对性别去自然化和去本质化;与之相对立的是安托内瓦特·福克(Antoinette Fouque)主持的团体“精神分析与政治”(Psychanalyse Et Politique),该团体旨在揭示女性无意识的特殊性,以及女性特有的“力比多”(Libido)。这实质上预示了波伏娃代表的过去的女性主义与福克代表的未来的女性主义的代际交替。[5]在波伏娃逝世时,差异主义女性主义者安妮·勒克莱尔(Annie Leclerc)在文章中对波伏娃的女性主义思想有所质疑,而福克则毫不客气地庆幸一种不宽容的、男女相似的、仇恨的、不育的普遍主义的终结。[5]
福克虽然在思想上与波伏娃相对立,但她在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中并未发表很多著述。在法国学者中,是西苏正式宣告了差异主义一代的到来。她在当时被归类到差异主义的行列,但她的思想同时具备后现代主义特征。1974年西苏在巴黎第八大学创立了女性研究中心和女性学博士点,这些在法国都是首创。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苏发表了一系列探讨女性气质、女性主义和女性写作的作品:1975年发表了《新生儿》(La Jeune Née)和论文《美杜莎的笑声》(Le Rire De la Méduse);1976年发表了论文《性或头?》(Le Sexe Ou La Tête?);1977年发表《来写作的女人》(La VenueàL’écriture)。《美杜莎的笑声》成为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女性主义论文之一。这篇论文可以被看作是跟弗洛伊德、莫斯和拉康等现代思想家们的对话,也是跟德勒兹、德里达和福柯这样的当代思想家的对话。[6]12西苏写作此文的目的是造成一种历史效果,针对菲勒斯中心主义机器的代理人,也针对主要由女性构成的普通读者。
自1949年波伏娃《第二性》的发表直到西苏《美杜莎的笑声》问世之前,女性主义思想并没有显著的发展,尤其是“性别差异”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美杜莎的笑声》之所以能够在西方引起轰动,是因为它清晰地表达了新一代女性尚未表达出的愿望,与此同时,该论文创立了构思和书写女性问题的新方式。[6]12虽然《美杜莎的笑声》最初发表在《弓》(L’Arc)的专号《西蒙娜·德·波伏娃与女性奋斗》(Simone De Beauvoir Et La Lutte Des Femmes)中,但西苏看上去并没有向波伏娃致敬的意愿。相反,而是有意要超越波伏娃并在女性主义历史中嵌入自己的思想。波伏娃主张女人应该认同的普世价值实质上是男性价值,她并没有对整个父权文明提出质疑;而西苏则致力于通过宣扬女性价值来摧毁逻各斯中心思想和菲勒斯中心思想,包括仅仅有利于男性的虚假的普遍主义。
西苏深受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影响,在与卡特琳娜·克莱芒(Catherine Clément)合著的《新生儿》一书中指出,整个西方文明体系包含无数个等级化的二元对立,其背后隐藏着男人/女人的二元对立。[7]116这种二元对立是一个战场,一个词语只有毁灭与之对立的词语才能获得意义。在父权制度下,男人总是赢家,并且跟“主动”这个意义联系在一起;而女人则是输家,并同“被动”联系在一起。[7]117女人要么是被动的,要么是不存在的。父权制从历史和文化中排挤女性,引导女性痛恨女性,让自己成为自己的敌人,动员女人用巨大能量来反对她们自己,从而成为男性活动的执行者。在《美杜莎的笑声中》,西苏宣告新女性的到来。她宣布女性从远方的回归:“现在妇女从远处、从常规中回来了:从‘外面’回来了,从女巫还活着的荒野中回来了;从潜层,从‘文化’的彼岸回来了;从男人们拼命让她们忘记并宣告其‘永远安息’的童年回来了。”[8]190由于女性性特征是能够跟父权制相匹敌的力量,西苏对此感到欢欣鼓舞,并试图把女性特殊性从残缺转化成优势。
三、从“女性文学”到“女性写作”
普遍主义思潮主要反映在女性对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的参与,而差异主义思潮则主要体现在对文学与文化的批判上。当差异主义一代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形成气候时,两代的交锋与博弈主要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尤其是女性写作理论领域。
在法国,直到20世纪初期,“女性文学”才成为研究对象。“女性文学”这一概念有时候是一个明显贬义的词条。
在敏感性和个人抒情性占主流的时代,女性文学获得一定的重要性。但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现代文学实质上是“男性文学”,“女性文学”从此被贴上“平庸”的标签。[9]
在现代意识形态占主导的背景下,波伏娃在论及女性创作活动时完全采纳男性标准并视之为普世标准。波伏娃深受写作的标准化概念影响,在女性的写作中只看到一种受压迫的、无意义的文学。显然,波伏娃是在重复某些针对女性文学创作的陈词滥调。在《第二性》的最后一章《走向解放》中,波伏娃针对女性文学给出了严厉的判词。在她眼中,由于从小到大的边缘化处境,女性无法把握世界的全貌,而只能通过一种特殊的幻象;[10]567女性无法承担起对既定的世界的焦虑,她不质疑这个世界,不去抗辩,不揭示这个世界的矛盾,相反,世界对她来说仅仅是感觉与情感的源泉;女性的写作通常缺少形而上学的反响,缺少黑色幽默;女人喋喋不休,是蹩脚的作家,仅限于描述私人生活:她的家庭生活、她的经历、她的世界;很自然,女人最擅长的文体是书信、私人日记、回忆录、自传体小说、诗歌;她们通常在女性自恋和自卑情结之间徘徊,这让她们的创作更加贫乏。[10]570-571
波伏娃多次把女作家跟男作家相比较。她承认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和乔治·艾略特都是非凡的、有反抗精神的女性,但同时又觉得她们缺乏司汤达那样的讽刺、从容、平静的真诚,也缺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那样的丰富经历。[10]573对波伏娃来说,《米德尔马契》不如《战争与和平》,《呼啸山庄》没有《卡玛左立夫兄弟》的宽广;[10]573女性自传很真诚,却不能跟《忏悔录》相比;[9]没有任何一个女作家写出《审判》《白鲸》《尤利西斯》或《智慧七柱》。[10]575简而言之,波伏娃认为女性文学总体平庸,女性没有创造出有价值的作品:“有些女人很狂热,有些女人很有才能,却没有女人将两者融合创造出天才。”[10]572
波伏娃深受“普世”文化的影响,认同一种中性的、无性化的写作,这也是她在《第二性》中为女性文学创作指出的道路。她预见到,当所有人类能够超越性别差异化时,女人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和作品中揭示整个现实,而不只是她个人。只要女人还在为成为人而抗争,就不可能成为创造者。[10]578
1966年波伏娃在日本发表了题为《妇女与创造力》的演讲,其针对女性文学和艺术创作的观点跟在《第二性》中类似。波伏娃首先反驳了妇女在政治、艺术、哲学等领域鲜有伟大成就是因为妇女天生平庸的观点,认为这是由于社会把妇女限制在低人一等的地位上,从而使其发挥受限。[11]458波伏娃重申真正伟大的作品是跟整个世界抗辩的,而跟整个世界抗辩需要对世界负有深深的责任感,现代妇女应当对世界有责任感,应当有能力与世界抗辩,但传统妇女的形象渗透在女性从小的教育中,深深地妨碍妇女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11]459-474
今天看来,波伏娃倡导的无性化文学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假定了男人创作的文学是中性的和普世的。事实上,任何文本都不是无性化的,性别与文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任何作家都是有性别的,但作家的文本与其性别之间可以有不同的关系,这取决于作家在写作中如何自我想象,以及如何想象自己的主体性:一些女作家明显带有女性的印记;一些男作家的文本也透露出女性气质;还有的作家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目的,在其文本中故意擦去性别的痕迹。过去,男人以性别差异的名义制定了“女性特殊性”。女作家总是徘徊于被接受的渴望和离经叛道的需要之间。为了找到自己的位置、声音,她们不得不冒迷失自我的风险小心隐藏或者特意彰显她们的差异性。[9]这两极的典型是法国两个名为玛格丽特的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像男人一样写作,而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则像女人一样写作。
如果说普遍主义者波伏娃建议女性在文学创作中抹杀性别差异,在《第二性》出版的25年后,差异主义者西苏在《新生儿》中,提出了描写女性气质和性别差异的“女性写作”(criture Féminine)概念,而后这一概念出现在其论文《美杜莎的笑声》中。正是由于西苏,“女性写作”问题才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法国文化辩论中占据中心位置。自20世纪70年代差异主义思潮占上风以来,“女性写作”逐渐代替了“女性文学”,后者被认为是男人发明的概念。
在《美杜莎的笑声》中,西苏对女作家的数量之少感到遗憾。但令她最感到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任何写作嵌入了女性气质,并且大多数女作家的笔法跟男作家毫无差别。[8]192西苏在《性或头?》一文中重复了此观点:“直到现在,大多数写作的女人不认为她们是作为女人在写作,而是作为写作而写作。她们声称性别差异毫无意义,在写作中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没有确定的差别……她们其实在实践一种男性写作。”[12]西苏揭露写作与菲勒斯中心主义传统的同质性。对她而言,毫无疑问写作中存在性别的痕迹,只不过长时间以来,写作一直被男性文化和理性主导,否定了性别差异;因此写作是压抑,它成为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压抑女人的一个场所,一个聚集所有性别对立符号的场所,一个女人从来没有话语权的场所。西苏宣布要结束写作的菲勒斯中心主义传统。她提醒人们注意性别对立总是对男人有利,并且这是一种历史文化局限,会有越来越多的书写嵌入不可减损的女性气质。此外,“大部分男女读者、批评家和作家们是出于无知而不愿承认或者公然否认女性与男性写作之间具有区别的可能性或相关性。”[8]198
西苏指出,写作在传统上或被概念化为“女性的”,或被概念化为“男性自慰”(写作的女人则是为自己制造一个纸质的阴茎),或被概念化为传统意义上的“双性”,其实质也是中性。西苏主张的“女性写作”同传统的写作概念决裂,它旨在发掘女性的力量,发明不被男人提出的形象异化的女性形式,一种前进中的女性形式。“女性写作”不能被定义,西苏解释道:“因为这种实践永远不可能被理论化、被封闭起来、被规范化——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然而它将总会胜过那种控制调节菲勒斯中心体系的话语。它正在而且还在那些从属于哲学理论统治之外的领域中产生。”[8]197-198
《美杜莎的笑声》一开头,西苏就号召女性书写女性气质:“我要讲妇女写作,谈谈它的作用。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8]188类似的命令式在此文本中反复出现。如果说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肯定女人的写作始终是女人的,但很难定义什么是“女人的”;西苏也没有为此下定义,即使西苏认为女性气质有太多可以写:性欲、情色化、身体。西苏虽然号召“妇女必须写妇女,男人则写男人”[8]190,但实质上,她认为在“女性写作”中,关键的不是作者的生物性别,而是文本本身,因为“女性写作”的本质,是书写女性气质和性别差异。因此,男人并没有被排除在“女性写作”之外。男性的书写中鲜有女性气质,但毕竟还存在。
在《美杜莎的笑声》中,西苏认为女性的文本是研究性别差异的文本,它打破菲勒斯中心主义逻辑,劈开二元对立的封闭性,并且在无限的文本性中找到乐趣。西苏试图摆脱“女性”和“男性”的二元对立,甚至是“雌性”和“雄性”的二元对立,因为她坚定不移地相信所有人类本质上的“双性”性质。西苏反对传统的、中性的、源自阉割恐惧的双性。她提出与之对立的“另一种双性”,它不排斥差异,也不排斥任何一个性别;相反,它包含两个性别,并且增加了差异。[8]198-199基于历史和文化原因,男人被迫要维持阴茎荣耀的单一性,被阉割情结所折磨,而生物学意义上的女人在成为女人的过程中并不抹杀女孩身上潜在的双性气质,而这种气质本来在男孩身上也存在。女人更加拥抱双性并从中受益:女性气质和双性气质相辅相成,换句话说,“妇女是双性的”[8]199,因此女人为双性写作而生。
四、迈向后现代女性主义
在女性主义运动浪潮中,性别差异问题没有被简单地抛却,而是成为女性主义理论与争论的关键。法国的两代女性主义者对待性别差异的态度截然相反,这是有其历史原因并符合女性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的。
在历史上,父权制建立在性别差异的基础之上,女性的生理特征成为其遭遇社会排斥的逻辑前提。普遍主义一代为了打破禁锢,首先要否定生理差异决定性别分工。她们肯定女人跟男人在本体论上的平等,主张两性应该在相似而非差异中平等。普遍主义把女性从矫揉造作的、人为的女性气质和无节制的生育中解放出来,使女性有机会通过参与社会生活而获得独立。但普遍主义者在女性气质中只看到了残缺,并把男性当作完整的性别。她们认为男人是文明和“普世价值”的创造者,力图把女性性属的效果最小化,以期待上升到男人的高度。她们提出的“解放的女性”的模板,实质上是男人、无性化、超我的人,导致女性在集体向男性同化的过程中迷失自我。这在文学创作领域非常明显。根据波伏娃的观点,男性批评家想把女性作者封闭在保留给女性的狭小世界,而女性作者希望平等地跟男性谈论整个宇宙,从而抛弃了女性文学这一概念。[13]577她们隐藏女性气质,主张或实践跟男作家一样的写作。
在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的第二阶段,差异主义占了上风。一方面,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女性表现出跟男性一样的思考能力和抽象能力,这样的女性形象已深入人心。在此基础上,一些知识女性才能够对其性属进行游戏,把过去残缺的地方变成优势。[14]另一方面,一些女性对以男人为模板的解放模式始终抱有怀疑态度。在这种背景下,法国出现了主张性别差异和创造女性特有语言的女性作者。《美杜莎的笑声》就是一个关于“女性写作”的政治、理论、审美和象征的声明。当西苏提出“女性写作”的时候,女作者们都是在菲勒斯中心主义体系内进行无性的创作。一种从女性身体和冲动出发的女性书写对父权文化无疑是具有颠覆性的。西苏的理论保持了一定的开放性。她没有给“女性写作”下定义,“女性写作”不是根据作者的性别来判断,但它一定要表现出开放性、女性气质和双性气质。“女性写作”把性欲与文本性联系在一起。“然而,把身体,包括女性身体写入文本是几乎整个20世纪先锋计划的特点。‘女性写作’的创新在于,在社会、政治和文化运动的背景下,这一审美计划由几位女性引领,而不是几位男性。”[15]495“女性写作”的另一贡献在于把19世纪以来“女性文学”的耻辱变成积极和正面的。[15]495
简而言之,“波伏娃把女人从生来是低等的女人的屈辱中解放出来,而‘女性写作’则试图还‘生来是女人并成为女人’以尊严。”[9]每一代女性主义思想对女性解放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也不可避免带有时代局限。波伏娃代表的普遍主义主张的女性解放道路导致女性性别特殊性的抹杀以及女性的雄性化,而西苏代表的差异主义主张重新发掘女性气质的价值则容易重新落入本质主义的陷阱,并把女性重新禁锢在私人空间。就此问题,倡导第三代女性的克里斯蒂娃用后现代的逻辑提出了解决方案:“二元世界只能是无休止的战争,无任何解决方案。所以要改变逻辑。既不是本质,也不是他者:多元宇宙由无穷无尽的特殊性构成。虽然每个人都深植于生物性别二元性中,每个人在他内心深处都创造出一个特殊性别。”[16]16-17如果两性完全相同,那么谁主宰谁的问题必定会引发战争,所以,“如果想重建和谐,我们就必须认定每个人在特定时刻都要承受去势,有时候是女人,有时候是男人。应该承认,作为‘消极’、‘附属’、‘第二’的女性气质,是可以分布在两性中的。”[17]210-211